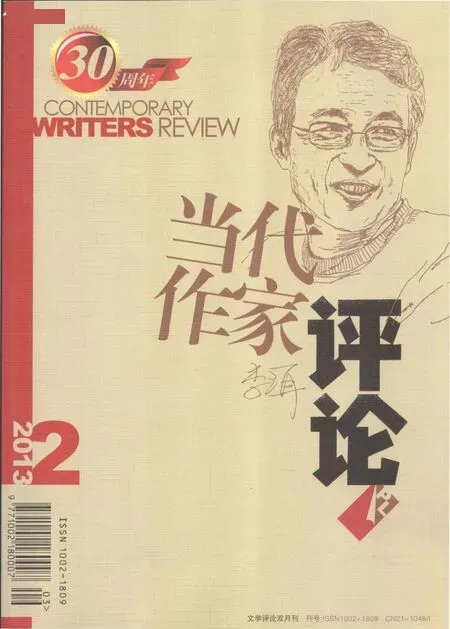想象中的想象之書
2013-11-14 08:57:34黎紫書
當代作家評論
2013年2期
黎紫書
直至小說寫完,我按鍵將它發送到出版社的郵箱,那以后我坐在書桌前凝視著計算機顯示器與顯示器背后的窗與窗外漸漸降落的暮色與暮色中漸漸顯影的月亮,其時我仍然在質疑自己何以立志要寫一部長篇小說。
何以我那么處心積慮要寫一部長篇?
為什么?
我先把“虛榮心”排除。這是一尾河豚中的含毒部位,我一直在小心翼翼地避開它,盡一切努力將它從我的余生中除凈。事實上我無法想象寫一部長篇小說究竟能給我帶來什么,我甚至不確定這于我算不算一樁明智之舉。畢竟我心里明白,作為小說寫手,以我淺薄的人生閱歷與學養,以及我那缺乏自律與難以長期專注的個性,實在不適宜“長跑”,而強撐著勉力寫一個不像樣的作品,它帶給我的很可能是一個消化不了的遺憾,又可能是一個不容易被寫作同儕們遺忘的笑話。
但我仍然羞于啟齒地渴望著寫一部長篇。
二○○四年,我在香港浸會大學創辦的國際作家工作坊中初次與中國大陸的作家蔣韻及臺灣的駱以軍相遇,在香港待了將近一個月。記得當時蔣韻把一個正在書寫中的小說帶在身邊,就在那一個月內完稿;工作坊的活動結束以后,她也誕下了她的新作,一個長篇。
而駱以軍,我還記得他在香港期間聽說了與他同年紀的董啟章其時正在寫著生平第一部長篇小說(后來知道是《自然史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他為此表現得相當焦慮,并且我也在那里初次聽駱以軍透露了他亦有寫長篇小說的想法,卻苦于當時的生活環境所不允許。……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2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0
紅豆(2022年3期)2022-06-28 07:03:42
科普童話·學霸日記(2021年4期)2021-09-05 04:28:51
小學生作文(低年級適用)(2019年12期)2020-01-18 07:50:36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9期)2019-10-17 02:25:50
學與玩(2018年5期)2019-01-21 02:13:06
中國化妝品(2018年6期)2018-07-09 03:12:42
小學生優秀作文(低年級)(2018年5期)2018-04-24 02:05:29
讀者(2017年15期)2017-07-14 19:5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