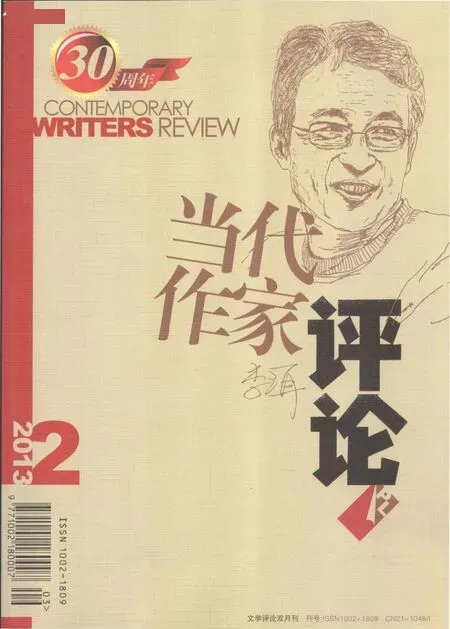朱天文的文學創作精神流變——以《世紀末的華麗》、《荒人手記》和《巫言》為中心心
2013-11-14 08:57:34金進
當代作家評論
2013年2期
關鍵詞:小說
金 進
一、設限與淪陷:花憶前身,還愿胡蘭成
朱天文曾說自己對胡蘭成的理論“全盤接收”。的確,朱天文太愛胡蘭成,她的早期創作亦步亦趨地踐行著胡蘭成的文化理論。朱天文認為胡蘭成給予她最大的影響是視野,一種“目送歸鴻,手揮五弦”,“寫小說也是一樣:你就是寫寫寫,但卻注意著小說之外的世界。我想這樣的視野是胡蘭成留給我們的最大資產”。胡蘭成的自我文化期許非常大,這一點影響到早期朱天文的創作,如散文集《黃金盟誓之書》中動不動就是文化、臺灣氣質等等,再如“臺灣的這三十年來絕對不是偶然的,為了我們民族將來更大的事業,臺灣的存在便是人事之上更有三分天意。以我辦出版社的切身體驗,這是極艱辛不易,然又是自助天助的幸運和喜氣的。因此,我們不做荊軻的慷慨悲歌,而寧是效法國父的浩然之氣。今日在臺灣,我是不生此身生何身?不生今世生何世?我就是這里了”(《春衫行》,一九八一)。類似這種寫作很多,很多時候帶有“卒章顯志”的效果,但更多的時候有點言不及義,內涵也少了很多。
胡蘭成自曝“我是直接傳承得五經與莊子”,縱觀其著作,他的文化理論涉及基督的神道、佛教的禪宗、《詩經》的國風、四書五經、《離騷》和老莊的楚文化等等影響,試圖弘揚漢文明,并讓其與西洋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競爭與對話。朱天文曾稱自己的小說集《傳說》是對逝世的胡蘭成的獻禮:“我不能親至蘭師靈前哭拜,蘭師仙靈有知,不忘金秋的約定,僅以這本《傳說》奉上。……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2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0
紅豆(2022年3期)2022-06-28 07:03:42
英語文摘(2021年2期)2021-07-22 07:57:06
文苑(2020年11期)2020-11-19 11:45:11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9期)2019-10-17 02:25:50
作品(2017年4期)2017-05-17 01:14:32
中學語文(2015年18期)2015-03-01 03:51:29
西南學林(2014年0期)2014-11-12 13:09:28
小說月刊(2014年8期)2014-04-19 02:3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