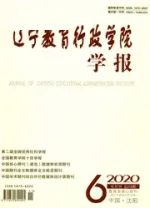北魏邊疆經營與北鎮問題
王明前
廈門大學,福建 廈門 361005
史學界對北魏經濟史的研究已經取得了顯著成就。尤其對北魏前期社會性質以及遷都前后均田制、三長制對經濟轉型的影響諸問題建樹頗多,亦對北魏各經濟區域的經濟發展狀況做出過一定探研。北魏雖然統一北方,但是北面和南面分別面臨游牧民族柔然和東晉南朝的軍事威脅,邊疆問題始終困擾著北魏統治集團。對此,學術界尚缺乏必要關注。筆者認為,邊疆問題影響北魏政治的始終,并最終演化為傾覆北魏皇祚的導火線。筆者不揣淺陋,擬以上述思路為線索,分別對北魏不同方向的邊疆經營做條陳縷析,進而探索邊疆問題的焦點北鎮問題與遷都之間的關系,以期增加學術界對北魏經濟史的學術認知。
一、北魏對西部疆土的經營
北魏對西部疆土的經營,是在先后攻滅盤踞關中及其以北地區的赫連夏,以及割據涼州的北涼的過程中逐步展開的。早在太宗明元帝拓拔嗣時期,河西游牧部落便不斷向北魏境內遷徙。永興三年(411年)六月,“西河胡張賢等率營部內附”。[1](P51)神瑞元年(414年)五月,“河西胡酋劉遮、劉退孤率部落等萬馀家,渡河內屬”。[1](P54)神瑞二年(415年)二月,“河西胡劉云等率數萬戶內附”。[1](P55)之后世祖太武帝拓拔燾奪取統萬,摧毀為患多年的赫連夏政權,加之先期已從夏手中奪取長安,從而獲得了歷史上西部重要的關中經濟區。
根據世祖“修其教不改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的經濟策略,涼州成為北魏重要的畜牧業區,保留其原有區域經濟特色。“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馀萬匹,橐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高祖即位之后,復以河陽為牧場,恒置戎馬十萬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每歲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彌滋矣”。[1](P2856)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十月,北魏打敗吐谷渾王慕利延后,吐谷渾貴族伏念等“率其部一萬三千落內附”。[1](P98)吐谷渾鄰近河西,又是被晉王伏羅率領的涼州駐軍擊敗,因此這些吐谷渾民戶被安置于涼州從事游牧生產的可能性更大。460年,北魏“發并、肆州民五千人治河西獵道”,[2](P4053)是一項旨在溝通平城中心經濟區與河西涼州經濟聯系的宏觀經濟行為。
在保留涼州游牧區域經濟特色的同時,北魏也通過移民屯墾加強涼州的農業經濟基礎。對此,崔浩力諫世祖:“昔平涼州,臣愚以為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人。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遷民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御邊而已,至于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闊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強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1](P825)崔浩充分考慮了涼州的軍事地理價值,并參考西漢成例,力主移民農墾,為涼州迅速融入北魏國家經濟一體化作出貢獻。袁翻則建議把內附北魏的柔然部落安置在涼州。他認為“其婆羅門(柔然部落首領名——筆者注)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余里,正是北虜往來之沖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于事為便,即可永為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加以配衣,仍令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應徙之兵,隨宜割配,且田且戍。雖外為置蠕蠕之舉,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后,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他預計:“入春,西海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為群,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1](P1542-1543)從而實現實邊、撫民兼顧的綜合效益。北魏奪取上邽后,劉潔“撫慰秦隴,秋毫無犯,人皆安業。世祖將發隴右騎卒東伐高麗。潔進曰:隴土新民,始染大化,宜賜優復以饒實之。兵馬足食,然后可用。世祖深納之”。[1](P688)高祖孝文帝元宏延興年間,朝議欲廢敦煌之戍“,欲移就涼州”。韓秀力排眾議,表示:“敦煌之立,其來已久,雖土鄰強寇,而兵人素習,縱有奸竊,不能為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進斷北狄之覘途,退塞西夷之路。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愿徙。脫引寇內侵,深為國患。且敦煌去涼州及千馀里,舍遠就近,遙防有闕。一旦廢罷,是啟戎心,則夷狄交構,互相來往。恐丑徒協契,侵竊涼土,及近諸戍,則關右荒擾,烽警不息,邊役煩興,艱難方甚。”[1](P953)以上地方官員的施政思路均與崔浩相仿,追求農墾實邊的政治與經濟效益。
北魏屯田條件相當惡劣,如不能實現自給,則需內地物資支.。這就使運輸問題顯得十分棘手。蒲古律鎮將刁雍建議以船運代陸運,提高運輸效益。泰常七年(422年)他上表稱:“奉詔高平、安定、統萬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谷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來往,猶以為難,設令載谷,不過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滯陷。又谷在河西,轉至沃野,越度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余日乃得一返,大廢生民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二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前被詔,有可以便國利民者動靜以聞。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栗,溯流數千,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民用安樂。今求于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為一舫,一船勝谷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功,輕于車運十倍有余,不費牛力,又不費田”。[1](P868)刁雍對蒲古律鎮有一整套嚴謹的農墾方案。他事先對水文、山川地理狀況做了翔實的調查后,上書請求在富平艾山興修大型水利工程。他指出:“夫欲育民豐國,事須大田。此土乏雨,正以引河為用。觀舊渠堰,乃是上古所制,非近代也。富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跡。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余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昔為之,高于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于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頹。渠溉高懸,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按舊引水,水亦難求。今艾山北,河中有洲渚,水分為二。西河狹小,水廣百四十步。臣今求入來年正月,于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地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筑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高渠,即循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訖。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丈,絕斷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馀頃。一旬之間,則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實。官課常充,民亦豐贍。”鑒于“平地積谷,實難守護”的窘境,他建議:“求造城儲谷,置兵備守。鎮自建立,更不煩官。又于三時之隙,不令廢農。一歲,二歲不訖,三歲必成。立城之所,必在水陸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辦”。[1](P867~869)當然,在處置柔然的問題上,北魏也曾有過重大失誤。如永平元年(508年),朝廷擬議遷徙顯祖時安置在高平、蒲骨律二鎮的柔然降戶千余至淮北。太仆卿楊椿引前例“先朝處之邊徼,所以招附殊俗,且別異華戎也。今新附之戶甚眾,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自安,是驅之使叛也”。他提醒朝廷:“且此屬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濕熱,往必殲盡”。[2](P4585)事實不幸果然如楊椿所料。
關中地區雖然在前秦、后秦時期得到了大力發展,但是在被赫連夏占據后,經濟逐漸凋敝,直到北魏攻滅夏政權后才得以逐步恢復。世宗宣武帝元恪時,華州刺史元燮上書建議選擇地理位置更優越的馮翊古城取代李潤堡,理由是前者和洛陽之間有更便利的水路交通優勢。他陳述道:“竊見馮翊古城,羌魏兩民之交,許洛水陸之際,先漢之左輔,皇魏之右翼,形勝名都,實惟西蕃奧府。今州之所在,豈唯非舊,至乃居岡飲潤,井谷穢雜,升降劬勞,往還數里,譐誻明昏,有虧禮教。未若馮翊,面華渭,包原澤,井淺池平,樵牧饒廣。采材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陪削舊雉,功省力易,人各為己,不以為勞。”[1](P518)尉撥“出為杏城鎮將,在任九年,大收民和,山民一千余家,上郡徒各廬水胡八百余落,盡附為民”。[1](P729)可是,至孝文帝時,關中形勢仍不穩固。“關右之民,自比年以來,競設齋會,假稱豪貴,以相扇惑。顯然于眾坐之中,以謗朝廷”。[1](P1048)北魏為穩定洛陽中心經濟區,對關中從安全角度大力經營。永熙(533年)二年,賀拔岳任都督雍華北華等二十二諸軍事,“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部趣涇州平涼西界,布營數十里,使諸軍士田殖涇州”。[1](P1783~1784)
二、北魏對沿南朝邊境州郡的經略
北魏對沿南朝邊境的經略,在南北朝紛爭的時局背景下,自然以軍事屯墾為主要行政方向。北魏考慮到“自徐揚內附之后,仍世經略江淮。于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于道路”,統治成本高昂。于是“令番戍之兵,營起屯田,又收內郡兵資與民和糴,積為邊備”。[1](P2858)而這必然要求北魏必須事先關注戰略據點的選擇,因為這一戰略據點其實也正是這一地區的經濟中心。
淮南是北魏從南朝奪取的新疆土。景明四年(503年),任城王元澄上表陳述壽陽對經略淮南的利害。他指出:“蕭衍頻斷東關,欲令巢湖泛溢以灌淮南諸戍。吳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余里,眾庶惶惶,并懼水害。脫乘民之愿,攻敵之虛,豫勒諸州,纂集士馬,首秋大集,應機經略,雖混壹不能必果,江西自是無虞矣。”之后世宗下詔“發冀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并壽陽先兵三萬,委澄經略”。[2](P4530)高閭則進一步指出:“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源本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既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眾糧運難可充。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溯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鎮,舟船素畜,敵因先積之資,以拒始行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實難。忠勇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且安土樂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后,恐為敵擒。”他進而建議:“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渡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于伊洛。畜力以待敵釁,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效可期。”[1](P1207~1208)高閭旨在提醒孝文帝,當前尚無充足實力經略淮南,因此斯時遷徙淮南兵民于淮北以圖再舉更為明智。而且從景明四年(503年)六月朝廷“發冀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千匹,增配壽春”[1](P196)來看,北魏對邊境地區的經略除就地屯田外,尚需經常從內地調撥人畜加以充實。
北魏在淮南大力興辦軍事屯田,對鞏固遷都后的河南經濟中心區具有戰略屏障意義。范紹任郢州義陽郡太守,“值朝廷有南討之計,發河北數州田兵二萬五千人,通緣淮戍兵合五萬余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為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于勸課,頻歲大獲”。[1](P1756)正始元年(504年)九月,世宗“詔緣淮南北所在鎮戍,皆令及秋播麥,春種粟稻,隨其土宜,水陸兼用,必使地無遺利,兵無馀力,比及來稔,令公私俱濟也”。[1](P198)
地處西南邊境的雍州,政治軍事環境復雜多變,因此北魏強調軍事屯墾,以鞏固邊境安全。顯祖獻文帝拓拔弘時,劉藻任北地太守,“時北地諸羌數萬家,恃險作亂,前后牧守不能制。奸暴之徒,并無名實,朝廷患之,以藻為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附。藻書其名籍,收其賦稅,朝廷嘉之”。[1](P1549)孝文帝時,崔亮任雍州刺史,“讀杜預傳,見為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為碾。及為仆射,奏于張方橋東堰谷水造水碾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1](P1481)仇池是長期獨立于南北朝的氐族聚居區,叛服無常。皮喜任仇池鎮將,“申恩布惠,夷人大悅,酋帥強奴子等各率戶歸附,於是置廣業、固道二郡以居之”。孝文帝也十分重視仇池的戰略地理位置。他認為:“仇池,南秦之根本,守御資儲,特須豐積; 險阻之要,尤宜守防;令奸覘之徒,絕其僥幸。勉勤戎務,綏靜新俗,懷民安土。”[1](P1132~1133)但至正光年間,“仇池武興群氐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絕”。直到張普惠任西道行臺,“至南秦,停岐、涇、華、雍、豳、東秦六州兵武,召秦州兵武四千人,分配四統;令送租兵連營接柵,相繼而進,運租車驢,隨機輸轉”,[1]1741形勢才稍有好轉。南秦州情形類似。杜纂“詣赭陽、武陰二郡,課種公田,隨供軍費”。[1](P1905)正始四年(507年),北魏“開斜谷舊道”,[2](P4574)以溝通梁、益州與內地的聯系。
東南邊境的青州,先后處于南燕和劉宋統治之下。納入北魏版圖后,得到大力經營。泰常八年(423年),北魏攻克青州,“魏軍至,無所得食”。世祖派刁雍為青州刺史。刁雍“撫慰士民,皆送租供軍”。[2](P3753)太和七年(483)正月,孝文帝“詔青齊光東徐四州之民,戶運倉粟二十石,送瑕丘瑯邪,復租算一年”,[1](P152)用豐荒互贍的辦法調劑地區經濟交流。
北魏對徐州的經略,仍然以軍事屯墾為主要方向。但是,由于鞭長莫及,起初效果并不理想。“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府,任其私用,常苦饑寒”。彭城鎮將薛虎子建議在徐州屯田,認為“徐州左右,水陸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萬余頃。若以兵絹市牛,分減戍卒,計其牛數,足得萬頭。興力公田,必當大獲粟稻。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耘植,馀兵尚重,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于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于后兵資,唯須內庫,五稔之后,谷帛俱溢。匪直戍士有豐飽之資,于國有吞敵之勢”。[1](P996~997)此議深得孝文帝贊賞。同時也可證明最初北魏對邊鎮的經略更多采用的是從內地抽丁實邊的辦法。此外,李彥任徐州刺史,“延昌二年(513年)夏,會大霖雨,川瀆皆溢。彥相水陸形勢,隨便疏通,得無淹漬之害”。[1](P889)崔鑒任東徐州刺史,“于州內冶銅以為農具,兵民獲利”。[1](P1103)
總體而言,直到世宗時南部邊地與內地的整合仍不成功。盧昶反映:“荊揚二州,屯戍不息;鐘離、義陽,師旅相繼。兼荊蠻兇狡,王師薄伐,暴露原野,經秋淹夏。汝潁之地,率戶從戎;河冀之境,連丁轉運。”各地自身經濟基礎不穩固,自然難以保證各經濟區域整合的成果。正始元年(504年)崔光痛陳:“義陽屯師,盛夏未返;荊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群生憔悴,莫甚于今。”[1](P1489)
三、北魏長城的修筑
為保衛北部邊境免遭柔然侵犯,捍衛農耕文明成果,北魏繼承歷代中原王朝傳統,致力于長城的修筑。太宗泰常八年(423年)二月,“筑長城于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備置戍衛”。[1](P63)孝文帝時,源賀提出在筑長城的同時輔以屯田的北疆防御策略。他建議:“請募諸州鎮有武健者三萬人,復其徭賦,厚加賑恤,分為三部。二鎮之間筑城,城置萬人,給強弩十二床,武衛三百乘。弩一床,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以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殖,并戍并耕,則兵未勞而有盈畜矣。又于白道南三處立倉,運近州鎮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備不虞,于宜為便。不可歲常舉眾,連動京師,令朝廷恒有北顧之慮也”。[1](P922)可惜此議未能通過。而持同議的源懷經過不懈努力,終獲朝廷認可。他請求世宗“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筑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如此,則威形增廣,兵勢亦盛。且北方沙漠,夏乏水草,時有小泉,不濟大眾。脫有非意,要待秋冬,因云而動。若至冬日,冰沙凝厲,游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1](P928)同時,北魏對北鄰柔然的內附要求欣然接受。宗室拓拔孚建議:“借其所閑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寬仁,縻以久策”。[1](P426)這當然比修筑長城的政治成本要低。長城的修筑為北魏農業經濟的轉型構筑了外圍屏障。“建筑長城和拓拔化農業發展有密切關系,因為長城本身意義,就是分隔草原與中原兩種不同文化類型的象征”。[3](P37)
盡管北鎮以軍事防御為主要功能,但其經濟生活一旦與內地隔絕,不僅會損害北鎮的經濟基礎,更會危害國家安全。因此,有識之士呼吁朝廷重視北鎮與內地的經濟聯系問題。高閭首先肯定長城有五大利處:“計筑長城,其利有五:罷游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游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1](P1202)他進而建議:“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難以御敵。可寬其往來,頗使欣慰,開云中馬城之食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畿甸之民,饑甚者,出靈丘下館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貧,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以溢其處。開關馳禁,薄稅賤糴,以消其費。清道路,恣其東西,隨豐逐食,貧富相贍。可以免度兇年,不為患苦”。[1](P1205~1206)同時,均田制也未貫徹到邊地。“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場統戍,階當即用。或值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民溫恤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御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強敵,即為奴虜,如有執獲,奪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馀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于溝瀆者常十七八焉”。[1](P1539)
四、北鎮與遷都問題
北鎮本來是維護平城中心經濟區安全的屏障。平城時代,北魏對北鎮十分重視。神鹿二年(429年),世祖“徙柔然高車降附之民于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貢賦,命長孫翰、劉絜、安原及侍中代人古弼同鎮撫之。自是魏之民間馬牛羊及氈皮為之價賤”。[2](P3812)世祖時,趙逸任赤城鎮將,“綏和荒服,十有余年,百姓安之”。[1](P1145)但是到孝文帝時,北鎮經濟問題已很嚴重,尤以糧食缺乏為甚。因此,為穩固北部邊境的經濟基礎,高閭建議:“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干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矟,修立戰場,十日一習。采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御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御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后分散其地,以筑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1](P1201~1202)這其實仍然是采用軍事屯墾方法解決北鎮的軍糧問題,力求經濟自給。
盡管歷史傳統和北魏自身實踐均證明軍事屯墾是解決邊境經濟問題的有效手段,但是,“北鎮與伊洛社會組織不同。遷于洛陽的北人早已成為編民,中國傳統的宗法組織成為他們的社會組織,但北鎮卻不相同,除一部分編民外,更多的是府戶、部落與罪人”。[4](P154)這使鮮卑人在遷都后由于國家經濟重心南移而必然出現族群分化。結果,遷都后北境經濟發展滯后于南部。“北邊荒遠,因以饑饉,百姓困弊”。[2](P4533)特別是北魏朝廷因遷都和漢化,對北鎮問題的態度早已不如平城時期那樣重視。“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奸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過弄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改”。[1](P430)源懷則上表反映均田制在北鎮落實不力的弊病:“景明以來,北蕃連年災旱,高原陸野,不任營殖,唯有水田,少可災畝。然主將參僚,專擅腴美,瘠土荒疇給百姓,因此困敝,日月滋甚。諸鎮水田,請依地令分給細民,先貧后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訟者,鎮將已下連署之官,各奪一時之祿,四人以上,奪祿一周。北鎮邊蕃,事異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別。沃野一鎮,自將已下八百馀人,黎庶怨嗟,僉曰煩猥。邊隅事鮮,實少畿服,請主帥吏佐五分減二”。[1](P926)
為此,北魏朝廷對北鎮居民極力安撫。肅宗時,“以沃野、懷朔、薄骨律、武川、撫冥、柔玄、懷荒、御夷諸鎮并改為州,其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酈)道元持節兼黃門侍郎,與都督李崇籌宜置立,裁減去留,儲兵積粟,以為邊備”。[1](1925)這是遷洛后的北魏對六鎮的一次區域經濟整合努力,試圖給予六鎮與內地一樣的政治待遇。熙平二年(517年)十月,詔稱“北京根舊,帝業所基,南遷二紀,猶有留住。懷本樂故,未能自遣,若未遷者,悉可聽其仍停,安堵永業。門才術藝、應于時求者,自別征引,不在斯例”[1](P226)這些都試圖協調南遷洛陽后原平城中心區與洛陽新中心區之間的關系。北魏朝廷此詔表面上表示并不因遷都而偏廢舊都,希望未遷者“安堵永業”,但是兩地自然條件和經濟基礎迥異,加之政治中心隨遷都而南移,國家經濟整合的基點和重心也必然相應南移。
孝文帝以果敢的決心強制推行漢化,遷都洛陽,改姓易服,成為中國古代著名的改革事件,為后世史學家高度肯定。其實,通過上述分析,孝文帝遷都的時機并不十分成熟。因為北魏經濟尚處于由游牧生產方式向農耕生產方式的轉化過程中,北境雖然通過長城的修筑和自身的軍事實力阻擋了柔然的襲擾,但是南部與南朝邊境地區的拉鋸局面仍然使疆土變動不定。孝文帝以“代在恒山之北,為九州之外,以是之故,遷于中原”[1](P359)的理由遷都,如果作為選擇可以進一步促進各經濟區域整合的新重心,本身并非不明智,但是遷都后孝文帝仍然不斷南伐的舉動則充分證明,孝文帝遷都與漢化的最主要動機并不是致力于鞏固農耕生產方式的轉化成果,以洛陽為中心致力于境內各經濟區域的整合,而是以洛陽為跳板南下實現統一。孝文帝的國家行政意識過于超前,在并未充分鞏固和消化生產方式轉化成果的條件下,便把南征作為主要任務,這至少不是最佳選擇。其實,北魏經過世祖到孝文帝幾代帝王對南朝的持續用兵,特別是趁南朝宋齊交替之際,憑借本來就占有的軍事優勢,陸續將青、齊、徐、兗諸州和淮北、淮南納入版圖,更加強了北魏的地緣政治優勢。北魏所需要的是在充分實現自身各經濟區域的整合,以提高其綜合經濟基礎特別是主體農業經濟的基礎的同時,等待南朝政局出現可資利用的變局。而北魏計不出此。孝文帝南遷后想利用南朝齊梁交替之際不斷南征,雖然有局部勝利,但是斯時南朝局勢迅速穩定,而北魏自己反而延誤了促進國家經濟一體化的最佳時機。孝文帝去世后,由于漢化進程過于急進,代北和遷洛鮮卑人逐漸發生族群分化,北部邊境屏障自我坍塌。北魏終于嘗到了邊疆問題處理不當的苦果。
綜上所述,邊疆問題影響北魏政治始終。雖然北魏的邊疆經略取得了顯著成就,但是由于北魏經濟尚處于由游牧生產方式向農耕生產方式的轉化過程中,不僅南部與南朝邊境地區的拉鋸局面仍然使疆土變動不定,而且北鎮問題因孝文帝漢化進程過于急進而激化,并最終演化為傾覆北魏皇祚的導火線。
[1](北齊)魏收.魏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2](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6.
[3]逯耀東.從平城到洛陽——拓拔魏文化轉變的歷程[M].北京:中華書局,2006.
[4]孫同勛.拓拔氏的漢化[M].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