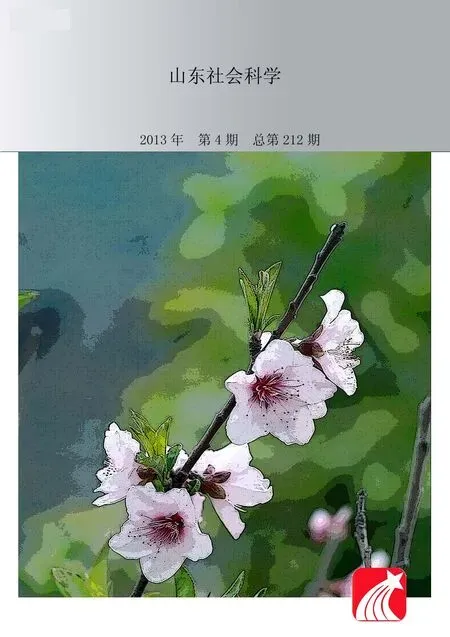南大德文專業的風流云散
——以若干人物為中心
葉 雋
(中國社會科學院 外國文學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一、1950年代:南大德文專業的精英薈萃
1952年,借助院系調整的大勢所趨,南京大學的德文學科似乎迎來了一個大發展的“天時地利”。于是乎,還僅是1947年建起德文學科的南京大學(前身為中央大學),一下子坐擁南方各主要大學的德文精英人物,一時間群賢畢至、薈萃英華。或許原有的學科底氣多少決定了其發展的可能,令人遺憾的是,南大德文專業的合并式發展似乎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曇花一現”的宿命。作為當事者的張威廉這樣回憶道:
1952年院系調整時,調來了同濟和復旦的德語師資和圖書;師資有陳銓、廖尚果、凌翼之、賀良諸教授,焦華甫講師,德國女教師陳一荻和作家布盧姆,真可說是人材濟濟,盛極一時。但為時不過十年,便就風流云散了;圖書數千冊,主要是從同濟調來的,其中有些今天難得的古本,如1823年出版的《席勒全集》。①《我學德語的經過和對德語教學的點滴看法》,載張威廉:《德語教學隨筆》,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頁。院系調整后復旦大學的外國語文系僅設俄文、英文兩組。俄文組即原復旦大學外國語文系俄文組;英文組由復旦大學外國語文系英文組及滬江大學、圣約翰大學、震旦大學三校的外國語文系合組而成。可參見《華東區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方案》,教育部檔案1952年長期卷,卷14。轉引自胡建華:《現代中國大學制度的原點:50年代初期的大學改革》,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頁。這位布盧姆是一位德國女士,即朱白蘭(德語原名KlaraBlum,拼音為DshuBailan,1904—1971)。1949年她重回北京,1952年擔任復旦大學德語文學教授,同年9月轉到南京大學任德文專業教授。關于朱白蘭,可參見夏瑞春:《永遠的陌生者——克拉拉·布魯姆和她的中國遺作》,載印芝虹等主編:《中德文化對話》第1 卷,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260頁。
以上諸君,再加上南大德文專業本來已有的商承祖、張威廉等人,真的是可謂“人才濟濟”,與北大德文專業相比,也是未遑多讓(其時北大德文專業的領軍人物為馮至,另有楊業治、田德望、嚴寶瑜等人)。就當時的德文學科格局來說,南北大學倒真的是名副其實,如果將專以外語語言教學為務、集中全力于培養實用性外語人才的北外排斥在外的話,南京大學-北京大學的對峙,倒恰是形成學術性的德文學科的基本格局,這也符合中國現代學術史傳統里的“南北對峙”②早在1917年時,北大校長蔡元培當其履新之初開始轟轟烈烈的北大改革之際,東南大學(南高師)就有與北大分庭抗禮的意味。而相對胡適等人掀起的新文化運動的熱潮,吳宓等在南方以東南大學為基地主張文化保守,雖然寂寞,但對文化史發展的意義來說卻并不遜色。。這樣一種狀態基本上一直保持到1964年中國科學院設立外國文學研究所。①這樣說,主要是以德語文學研究為取舍的標志。就德語教學來看,到了1956年時,上海俄專、哈爾濱外專分別更名為上海外國語學院、哈爾濱外國語學院,開始增設德語專業(與英語、法語同時);1954年成立的北京對外貿易學院、1960年成立的上海對外貿易學院也都在外貿外語系下設有德語專業;1964年10月制定的《外語教育七年規劃綱要》中指出要大量增加英語學習人數、要適當增加法、西、阿(拉伯)、日、德語的人數。參見付克:《中國外語教育史》,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72、74、77頁。這些學院顯然主要以培養實用性的德語人才為主,德語文學研究的學者當然也就仍主要集中在北大、南大這兩所綜合性大學。實事求是地說,這樣一種借助政治權力運作而形成的“數花獨放”,其實并不一定符合學術發展的自身規律。事實上,同濟、復旦、清華等校德文學科的消逝,也確實未曾換來南大、北大德文學科的“輝煌鼎盛”。按照張威廉的話來說,從人才鼎盛到“風流云散”,也不過十年間事耳。為什么竟會是這樣的呢?
初時的制度設計并未調整,仍是德文組,只不過先由南京大學、復旦大學兩校德文組組成;同年,同濟大學德語組亦并入。外來德文教師包括:陳銓、廖尚果、陳一荻、朱白蘭、焦華甫等。這種敘述與張威廉的回憶是基本一致的。1955年,德國語言文學教研組成立。1956年,民主德國葛來福教授任教于德文專業;9月,高教部下通知,德、法、英、俄四專業從1956年秋季入學新生起改為五年制;實際上德、法二專業自1957年起入學新生方改為五年制;1956年德國文學方向招收研究生,導師為商承祖、陳銓、葛來福,學生為吳永年;1956—1957年德文組師資共11 人,學生77 人。②參見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編:《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院史紀事》,2002年。1957年,楊武能考入南大外文系,進入德文專業就讀,他給我們留下了自己如何由學俄語而轉為學德語、由重慶而南京的求學歷程:“由于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中蘇友誼不幸破裂,搞俄語的人在1957年突然多了,我不得不放棄俄語改學德語。于是離開故鄉的俄文專科學校,從山城重慶順江而下,千里迢迢地到了虎踞龍盤的石頭城中,就讀于南京大學的德國語言文學專業。然而因禍得福,南大德語專業不僅素有做文學翻譯和研究的傳統,而且教我們的是商承祖、張威廉、葉逢植等一些當時在全國出類拔萃的學者、專家。從二年級開始,老師已陸續在課堂上教我們一些文學名著,其中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正是大詩人歌德的一些代表作……”③《自序》,載楊武能:《走近歌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頁。應該說,此期的南大德文專業師資的精英薈萃在學生眼中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證,而且反之也確實在學生培養上得到一定的體現。至少,能夠培養出楊武能這樣的學生,就是一種證明,雖然其日后成就至少要提及其在社科院外文所師從馮至讀研究生這一學術背景,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在1950年代末期作為本科生就已在《世界文學》上發表譯作④《自序》,載楊武能:《走近歌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頁。。當然,值得深入追問的,自然還是主事者的思路與策略。
二、作為主事者的商承祖與張威廉
就南大德文專業來說,商承祖(1899—1975,亦用名章孫)與張威廉(1902—2004)無疑是可以負起責任的人。⑤關于商承祖,參見葉雋:《出入高下窮煙霏——追念商承祖先生》,《中華讀書報》2005年8月17 日;葉雋:《文章猶在未盡才——日耳曼學者商承祖的遺憾》,《中華讀書報》2008年10月22 日。關于其父商衍鎏,參見葉雋:《有時空望孤云高——念商衍鎏先生》,《中華讀書報》2005年7月20 日;柏樺:《商衍鎏與德國漢學》,見http://www.chinulture.cn/forum-viewthread-action-printable-tid-951.html,下載于2011年3月10 日。關于張威廉,參見葉雋:《先生百齡,乘風而去》,《讀書》2005年第2期;葉雋:《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的“德國文學學科”歷程——張威廉先生的歷史記憶》,《博覽群書》2005年第4期。因為在范存忠之后,商承祖曾長期擔任南大外文系主任;而張威廉則是德語教研室主任。
這種制度性變化,是在1954年開始實行的。當時將德文組一分為二,即德國語言教研室(主任張威廉)、德國文學教研室(主任陳銓)。德文專業課程與英、法、俄各專業一樣設置為四類:1.政治理論;2.對象國文學語言技術訓練;3.對象國文學語言理論;4.中國文學史和現代漢語(重點是現代文學史和寫作實習)。⑥參見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編:《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院史紀事》,2002年;葉雋:《德語文學研究與現代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31頁。
顯然,在南大德文學科的發展史上,起到重要作用的首推商承祖。作為現代早期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一頁,商氏家族與德國淵源頗深⑦也可以說商氏世家與福氏世家(福蘭閣、傅吾康父子)都可算是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標志性家族,當然還可以加上衛氏世家(衛禮賢、衛德明父子)。商家的第三代,即商承祖長子商志馨(1923—1971)1953年起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后改名上海譯文出版社)任德文編輯;女兒商志秀在1952年畢業于南京大學德語專業,任北京的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北京外貿學院)德語教授,也都和德國有關。,而商承祖更是借得東風之便,能有少年留德之可能⑧按照其弟商承祚的記錄:“1912年德國漢堡大學派員來華為該校東亞系招聘漢文教師,我父鑒于當時國內軍閥混戰,局勢很亂,決定應聘出國,并攜長兄承祖、二堂兄承謙去讀中學。”參見商承祚:《我父商衍鎏先生傳略》,載《歷代碑帖法書選》編輯組編:《商衍鎏、商承祚書正氣歌》,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5頁。該書未標頁碼。,從此結下與德國的不解之緣。從13 歲留德到弱冠前后再歸國,再到旋即就學北大新設的德國文學系,商承祖的德國之路可謂是一帆風順。作為北大德文系開創者的德國學者歐爾克曾毫不吝惜地稱贊商承祖是最好的學生,①Oehlke,W.:In Ostasien und Nordamerika als deutscher Professor:Reisebericht(1920-1926)(在東亞與北美做德國教授:旅行報告(1920-1926)).Darmstadt & Leipzig:E.Hofmann,1927.S.38.而商承祖顯然也受乃師影響頗深,對萊辛、克萊斯特都頗有興趣。商承祖可謂是早期具備跨學科條件的學者,因為他先后跨越了民族學、漢學、日耳曼學等多個學科,早年隨父赴德時不過10 多歲的少年而已,自然打下了非常好的德語口語基礎;日后入北大德文系,果然皎皎然不群于眾。大概是在1930年代他再度赴德,在漢堡大學留學(1931—1933年注冊),以《中國“巫”史研究》(Schang,Tschengtsu:Der Schamanismus in China-eine-Untersuchung zur Geschichte der chinesichen“wu”.Hamburg:o.V.Diss.phil.Hamburg,1934)的博士論文獲民族學(V?lkerkunde)博士學位。②參見Harnisch,Thomas:Chinesische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Geschichte und Wirkung ihrer Studienaufenthalte in den Jahrenvon1860 bis 1945(中國留德學生——1860 至1945年間留學的歷史和影響).Hamburg: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Asienkunde,1999,S.468.但商與漢學關系也非淺,不僅是指他曾同時在漢堡大學任漢語講師(LektorfürChinesisch),而是其論文也同時接受了漢學教授的指導,如他在論文后記中致謝的J?ger 與Forke,都是德國著名漢學家。③商承祖還曾與漢學家一起合作做人類學調查。1928年夏,他和嚴復禮到廣西進行少數民族研究,在凌云縣北部六個瑤族村寨考察一個月,翌年發表了《廣西凌云瑤人調查報告》。他還曾調查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參見顏復禮、商承祖:《廣西凌云瑤人調查報告》,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1929年1月;章學清、張佑中:《著名德國語言文學家商承祖教授》,見http://www.poetic.com.cn/go.asp?id=15841&ttt=,下載于2006年1月23 日。以這樣的學術背景出長德文學科,自然易于開辟道路、有所規劃。但遺憾的是,在很長時期之內,商承祖都是在中央大學教授公共德語。
張威廉1933年應陸軍大學之聘教德語,陸大課多乃邀北大同學、時任教于中央大學的商承祖兼課;抗戰爆發后,陸大、中大均內遷重慶,商承祖請張威廉兼課于中大。當時德語都是公共外語,時間約是1943年。由于中央大學外文系主任范存忠(1903—1987)的戰略思路,乃于1947年時建設了德語專業。按照張威廉的說法:“這個人很有眼光,要把德語作為一個專業搞起來。當時德文做公共課已講了很長時間了。”④葉雋:《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的“德國文學學科”歷程——張威廉先生的歷史記憶》,《博覽群書》2005年第4期。范存忠這樣闡述其擔任學術行政職務間的作為:“從1931年回國起至1949年解放前夕為止,我一直在原中央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任教授、系主任、文學院院長等職。這期間經歷了八年抗日戰爭和三年‘內戰’的動亂時期,但中央大學文科各系科仍保持了相當的規模。我不搞宗派,因此,在任職期間,我主張兼容并包,從各方面羅致人才。當然,由于見識有限,也難免帶來一些不好的后果。”⑤范存忠:《我的自述》,解楚蘭記錄整理,載王守仁、侯煥镠編:《雪林樵夫論中西——英語語言文學教育家范存忠》,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頁。所以,從總體來說,南大德文學科是在外國文學學科群的整體規劃下建設起來的,范存忠是總設計師,而商承祖與張威廉是開辟者,也是同事,在學術組織和管理方面,前者的分量更重些。有論者在描述南大德文專業1952年合并后的盛況后,突出強調了系主任商承祖的功用:
……隨著以后的各次運動,特別是反右運動以后,就風流云散,盛況不再了。在此條件下,商先生認識到:培養年輕教師,使之迅速成長,已是當務之急。他就制訂了一套翔實的科研計劃:每周要舉行一次學術討論會。每位教師(包括他本人) 要選定一個題目(作家評論或作品分析) ,在認真閱讀原著的基礎上,寫出心得體會,在討論會上宣讀,聽取意見后再整理成文。這對于年輕教師來說,無疑是一種非常有效的、迅速提高水平的措施。他還要求年輕教師根據各人的興趣和特長開設選修課,如修辭學、語言學、詞匯學、語法學、語言史、文學專題選讀等。這一措施大大調動了年輕教師的積極性,發揮了他們的特長,使得他們得以迅速成長。⑥章學清、張佑中:《著名德國語言文學家商承祖教授》,參見http://www.poetic.com.cn/go.asp?id=15841&ttt=,下載于2006年1月23日。但具體到德文專業的發展,還需要進一步的材料挖掘以及復雜的歷史現場還原后才能深入推究分析。
從這段敘述來看,商承祖對學科發展是有一定意識的,他甚至試圖進行一些制度性的建設,譬如每周學術討論會的設想。課程設置與教員興趣的相結合,這是一個很好的思路,而且既立足于實際工作之需要,同時也能將教師的積極性發揮出來,更重要的是,可以迅速使之進入學術研究的狀態和窺得學術門徑。當然,一個重要的前提是,主持者是否具有足夠的學術積養和高水準眼光。應該說,就教師培養來說,這種培養是有效果的,尤其是他自己課程的后續性方面,“對于他所親自講授的文學史和文學選讀課,他也挑選了兩位年輕教師給他們開小灶來精心培養,使他們能夠接替他,以便騰出更多的時間來搞好整個外文系的工作。他是傾心竭力、手把手地扶助這兩位年輕教師成長的:教材由他親自打字后付印;參考資料由他首先閱讀后用紅筆將重點處劃出;講稿由年輕教師寫成后由他親自審閱;上課時他坐在后排聽講,課后由他提出修改意見后再由年輕教師整理成文。經過了這樣幾道關卡,他才放心地向年輕教師交班。”①章學清、張佑中:《著名德國語言文學家商承祖教授》,參見http://www.poetic.com.cn/go.asp?id=15841&ttt=,下載于2006年1月23日。應該說,這樣一種師資傳幫帶的效果是不錯的,多年之后,已成為著名學者的楊武能如此回憶自己在南大德文專業老師引領下走近歌德的歷程:“是啊,我永遠忘不了在老師們帶領下讀歌德的情景:《浮士德》和《少年維特的煩惱》盡管在課堂上只能學幾個片段,但卻讀了《五月之歌》、《漫游者的夜歌》、《普羅米修斯》和《神性》等為數不少的抒情詩,而且讀得十分地專注、癡迷。跟敢于用自己的靈魂和魔鬼打賭的老博士浮士德一樣,跟多愁善感、狂放不羈的維特一樣,英雄的普羅米修斯也深深打動了我……諸如此類既鏗鏘有力而又洋溢著人道精神的詩句,都難以磨滅地銘刻在我心中,鼓舞著我在困頓重重的人生之路上前行,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②《自序》,載楊武能:《走近歌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應該說,此期的學生培養,也正是在商承祖的整體學科發展思路下而展開的,因為師資水平的提升就必然會帶動學生質量之提高;而學生之桃李滿天下,則反之又會提升學校和學科的聲名。這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關系,但我們更關心的,則還是學科史本身的問題,為什么1952年院系調整帶來的群英薈萃的效應沒有足夠顯現出來呢?
三、廖青主與陳銓的命運
祝彥(1926—)教授在給我的信中說過,廖青主(廖尚果)與陳銓乃是南大的名教授。③祝彥教授給葉雋的信,時間不詳,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祝彥簡歷見http://baike.baidu.com/view/877268.htm,下載于2012年8月10日。可見,在當時的國內學界,廖青主、陳銓可謂是名聲遐邇。南大有這樣的名學者,應是一個學科和一個學校的驕傲,但遺憾的是,當他們從外校合并而來之際,德文學科似乎并沒有充分發揮出他們的作用。
那么,我們關心的當然是,如果說陳銓因了政治因素而不得不“忍氣吞聲”,那么廖青主究竟是為什么要離開校園?1957年,廖青主向南大校方提出要求提前退休,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南京大學與系主任個人相處得不愉快有關”④廖乃雄:《憶青主——詩人作曲家的一生》,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頁。。如此,南大德文學科于1950年代風流云散的學術史問題,可以浮出水面。當初訪張威廉先生時,就覺得他對這段事情“語焉不詳”,似乎不愿多說;⑤2004年我采訪張威廉先生時,他曾約略提及南大外文系當時復雜的人事與社會背景,但基本屬于語焉不詳。本指望日后再有機會重訪繼續溝通,可惜的是張先生于當年即魂歸道山,這段學術史看來很難通過當事人進行了解了。而日后嘗試訪問商氏之女商志秀(1928—),則又被回避。看來,作為1950年代南大外文系德語學科當事人的商承祖、張威廉、廖青主、陳銓等,都是不能忽略的關鍵人物。試圖深入追問這一問題,乃是探討學科史研究的必有之意。
廖青主(1893—1959)是中國現代音樂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學修養也非常好,應是學科史值得關注的學者。在留意音樂之外,青主對德國精神文化也甚有修養,留學德國10年間,除順利完成學業獲得法學博士學位之外,也大量涉獵了康德、黑格爾、叔本華、萊辛、歌德、海涅等人的作品,其中對海涅更是情有獨鐘,非常喜好。他對海涅的作品信手拈來:“Heine 說得好:我有一種極和平的意志。我的愿望是:‘……窗外有花,門外有樹,如果天帝更要使我幸福不過,那末他應該使我得到這樣的歡喜:把六個至七個我的敵人,吊死在這些大樹底下。那時我便要把我的敵人生時對我所造的各種罪惡寬恕——是的,我們要寬恕我們的敵人,但是,在還未曾把他們吊死之前,我們是不能夠把他們寬恕。’——我并非要曲解前人的話,我現在只就Beethoven 來說,如果我們對于我們敵人,不是要把他們吊死了之后,才把他們寬恕,那么,先前那一度慘烈不過的戰爭,不是完全沒有意義么?——Madame!外面又起了一片慘殺的槍聲,全酒店里面的人們,都驚惶起來,但是,我們是用不著驚惶的,我們保留著我們的思想和愛。”⑥青主:《詩琴響了》(1930年),轉引自廖乃雄:《憶青主——詩人作曲家的一生》,中央音樂學院2008年版,第25頁。其實何止如此,青主對德語語言學、文學都有相當深的研究和造詣,不乏洞燭之見:
Ein jeder kehrt vor seiner Tür!
這是Goethe 的一句話:每一個人要打掃他的門前。就表明上看來,好像和我們中國那句俗話:各人自掃門前雪,除了少一個雪字之外并沒有什么區別,但是它的意思是并不一樣的,在德文是說各人要檢討自己的錯誤,在中文是勸別人不要多管別人的閑事。
Die Haare stiegen ihmzu Berge 或Seine Haare richteten sich empor,或seine Haare standen zu Berge。
譯成中文:他的頭發豎立如山,或豎立起來。誰不想起我們中國怒發沖冠那句話呢? 但是它的意思并不一樣,在德文是由于恐怖,在中文是由于憤怒,頭發豎立起來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
由于上面舉的那兩句例句,我們可以見得:凡學習德文的字句都要探本窮源,決不宜只在字面上做工夫,即是說:我們要徹底明白它的意思。文字是用來表現人們的思想的,但是德國人拿文字表現思想的方式,往往是和中國人不同的,所以我們學習德文,要了解德國人用來表達他們思想的方式,決不可以拿我們中國人表現思想的方式來解釋德文。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一點,但是這并不是說:德國人表現思想的方式處處和中國人不同。有許多地方,他們和我們表現思想的方式是相同的,我們就拿頭發來說吧!中國有“千鈞一發”這個詞,蘇東坡論張子房,亦有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發,這樣拿一根頭發表示危險的程度,在德文亦是有的,比方說:
Sein Leben hing an einem Haar。
他的生命只系在一根頭發之上。
Er hat mehr Schulden als Haare auf dem Kopf。
他的負債比頭上的發還要多。
(這) 是用來象征眾多的。如果用來象征稀少,亦可拿一根頭發來做比喻: Ihm wurde kein H? rchen gekrümmt。沒有彎曲到他的頭發,亦即是中國話:沒有動到他一根頭發的意思。
我們學習德文,腦子里不要存有成見。中文和德文相同的表現思想的方面固然是很多,但是遇著不相同的地方,總不是強不同以為同,那便對了,根據這個理解,來學習德文的成語句,大約不會有什么錯誤了。①青主遺稿,轉引自廖乃雄:《憶青主——詩人作曲家的一生》,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153頁。
如此不惜長篇引用,乃是為了說明廖青主的學養問題。雖然討論的是語言詞義的問題,但引用的例句有歌德之語,足見其對文學的熟悉,而中德比較引用的例證之佳、論述之清晰,更使其能從簡單的語義學追問背后的文化成因,可見其學貫中西之學養厚重。更重要的是,“自從他在大學執教以后,幾乎沒有一天,他不在思考他從事的專業與學識。他習慣于幾乎每天總要數小時之久地伏在他那張古色古香的紅木書桌上,面對著成堆的德文文法書和各種辭典進行德語與德意志文學的鉆研”②廖乃雄:《憶青主——詩人作曲家的一生》,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頁。。這樣的學者,為什么竟會與南大德文學科有些格格不入呢?
陳銓(1903—1969)的命運似乎更可感慨,他早年可謂是才氣橫溢,是現代文學史、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更在抗戰時代扮演了文化場域的重要角色。即便就德文學科來說,他是中德比較文學學域的開辟者,能夠出現陳銓這樣的人物,當引為學科的驕傲。我曾當面問過作為當事者的張威廉先生,后者似乎有些含糊其詞:“人很多的,他們都過來了,而且帶了很多書和資料。象陳銓、廖尚果他們,陳是寫劇本的,《野玫瑰》很有名,后來被打成右派。廖是搞音樂的,也很有才。但他們個性也比較強。”③葉雋:《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的“德國文學學科”歷程——張威廉先生的歷史記憶》,《博覽群書》2005年第4期。事實上,陳銓在這段時間,也并非完全停止了自己的學術活動,如他就撰寫過《對張威廉先生〈泰爾報告〉的補充意見》(1955年),未刊稿,此文對張威廉關于席勒劇作《威廉·退爾》的報告,從時代問題、道德問題等方面提出商榷意見。季進等:《陳銓:異邦的借鏡》,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頁。張威廉關于此劇的思想,可參見《席勒劇本〈威廉·退爾〉、〈唐·卡洛斯〉和〈杜蘭朵〉簡介》,載張威廉:《德語教學隨筆》,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139頁。陳銓對席勒是有研究的,但此時他的學術話語權利顯然受到限制,有關論述都未能發表;但這種對自己學術意見的表達欲望和真誠,確實可以見出其作為德文學者的可貴一面。盡管比較隱約,但仍給我們留下了印照于史實、語境與時代背景進一步考察的可能性。實際上,像陳銓這樣的人物,1949年之后的境遇可分為兩個階段,1949—1957年基本還可正常進行教學活動,但在1957年全國性的反右運動的大潮下,作為右派的陳銓處境則相當艱難。1952—1957年間,陳銓在被“發配”為外文系資料室管理員之前,④對這一點,時為南大德文專業學生的楊武能有回憶。參見楊武能:《“圖書管理員”陳銓》,《文匯讀書周報》2006年1月6 日。另相關敘述,也可參見楊武能:《圓夢初記》,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還是有過5年為人師表的愉快生活的:
……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他所熱愛的德國文學與德語教學當中,他嘗試用比較語言學的方法,采用英語授德語課,讓學生們輕松掌握和理解德語,同時又提高了學生的英語水平。他為高年級的學生開設戲劇課,除了課堂講授,還利用業余時間,熱心指導學生排練德國劇作家的名作,深受學生們的歡迎。陳銓甚至還可以和一些留在南大的德國人交往,相互之間就像中國人走親訪友一樣無拘無束,還和一位德國教師一起編寫了一本德文教材。教學寫作之余,陳銓也會陪著子女家人去看看電影或戲曲演出。①季進與陳光琴(陳銓之女)訪談記錄,載季進等:《陳銓:異邦的借鏡》,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165頁。
然而,往事如風,即便曾經善待陳銓的南大,也擋不住政治運動爆發時的“山雨欲來”;雖然1961年他成為最早脫掉“右派”帽子的人員之一,但隨即而來的文化大革命②陳銓在這段時間的經歷,可參見季進等:《陳銓:異邦的借鏡》,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175頁。,則將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幾乎拖入另一重深淵。作為德文學者的陳銓自然也就很難展現其閃耀的光芒。陳銓的命運,在相當程度上說明了南大德文專業雖匯聚一代人才于一地,卻為何最終得了個“風流云散”的結果的主要原因。陳銓的個體命運、南大德文專業的命運,不過都是時代風云的一角縮影而已。其實,何止是南大,又何止是德文專業,又何止是陳銓?整個中國都籠罩在時代風云的歷史詭譎之中。
1952年,如果說廖青主已經是年近花甲,那么陳銓尚未及知命。而此時的商承祖,才53 歲,正是一個人文學者的黃金年華,他若能夠以一個學術領軍者的眼光和睿智,將這些精兵強將用好,則不但是一個學校的振興機會,對于整個德文學科史來說也是一次難得的樹立“南方學統”的大好機緣。其實南大并不缺乏這個傳統,早在民初時代,東南大學就以“南雍學術”之名而與北京大學相抗衡。③有論者提出“南雍學術”的概念,溯源歷史,強調國子監是國家教育行政最高機構兼最高學府,并以明代南京、北京國子監并立的狀況作比。認為在1910-1920年代,南雍具有新的含義,即特指當時南京的最高學府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東南大學(此皆今日南京大學之前身)等。并引述論證,或謂“北大以文史哲著稱,東大以科學名世。然東大文史哲教授實不亞于北大。”或謂東大與北大,“隱然成為中國高等教育上兩大支柱”。參見王運來:《留洋學者與南雍學術》,載田正平、周谷平、徐小洲主編:《教育交流與教育現代化》,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188頁。在我看來,這一概念可以下沿,即由歷史到現實中,均可以一種南北對峙的模式去考察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路徑。在1950年代以前,由南高師到東大而中央大學的發展路徑,借助政治因素,基本可以認為與北京大學形成南北鼎立的格局;在1950年代以后,尤其是1980年代以來,南方由于復旦大學(稍近還有浙江大學)的迅速崛起,尤其是借上海的地利之便,使其漸有成為南方教育/學術中心之勢,但總體而言,說南京大學代表了南方學術,仍不會有太大爭議。而在文革結束之后,復任南大校長的匡亞明,以一種博大的氣度排斥一切干擾而引進程千帆,為南大的文科振興而請來大師。程千帆對中國古代文學學科的意義,是怎么高估都不過分的,這不僅是一個學派或學校的復興,甚至攸關中國現代學術整體場域的學科興廢之關鍵。學術領袖的大局意識和戰略眼光之意義,或正在此。遺憾的是,作為邊緣的德文學科,恐怕少為領導者所關注(如范存忠者畢竟是鳳毛麟角,這與其學術養成和眼光有關),所以陳銓這樣人物的命運自然也就是不難理解的。作為學生的楊武能曾經深深同情被安排到圖書室做管理員的陳銓,因為作為一個具有敏銳學術感覺的學生,楊武能似乎已經感受到這位管理員老師的價值,他曾感嘆“多虧南大外文系有一個藏書豐富而且對學生也開架借閱的圖書室”,并且特別提及和他作為德文學生直接相關者——“其時管理德文圖書的乃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和學者陳銓,盡管他被視為不可接近的‘大右派’,學生有問題還是向他請教”④《自序》,載楊武能:《走近歌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頁。。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陳銓作為學者仍可從學術薪火相傳的斷續香煙之中感受到的一點點溫馨,畢竟還是有學生想要求知的。然而,陳銓的悲劇命運,卻是那個大時代不得不然的結局。當然,我們也可以比較一下陳寅恪的情況,也是最后20年,相比較陳銓的近乎全面噤聲,陳寅恪卻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學術成果;如果說陳寅恪缺乏可比性的話,那么賀麟(1902—1992)總是可以的。當年曾同為清華弟子,日后又先后留學美、德,在1940年代顯赫一時的戰國策派運動中,陳、賀亦為其中核心人物。1950年代之后,彼此的命運既有近似之處,也不完全一樣。賀麟終于作為哲學家而名世,并留下為數不少的著述,譬如煌煌的《精神現象學》譯稿(和王玖興合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而陳銓基本上在學術與文學上都保持了沉默,所存《精神現象學》譯稿,只殘留了一小部分。⑤我們鮮有人知道,陳銓是當初與其事者之一。《精神現象學》殘稿,載季進、曾一果:《陳銓:異邦的借鏡》,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204頁。對陳銓這樣一個才華橫溢的人來說,實在是太可惜了,最后的20年,他寂寞無聲。我想他大概是不情愿如此的,作為一個學者和思者,思考總是必需的事情,讀書也是必需的事情,沒有讀書如何來思考?沒有思考如何來寫作?沒有寫作如何來讀書?這幾者之間本就是相輔相成的關系,然而陳銓的最后20年,確實是著述凋零。這固然首先是大背景的制約,但與他身在其中的南大德文學科與外文系的“小環境”究竟有怎樣的關系呢?
相比較作為外來人的廖青主和陳銓,商承祖對張威廉無疑是更信任的。像張威廉這樣的人物,屬于資質相對平平,為人亦鋒芒不露者,且潛心學術與翻譯,是大家都喜歡的好好先生,譬如廖青主就和張威廉有過學術交誼①廖青主“在南京這幾年內除了授課講解德意志文學以外,還進行了不少翻譯工作。這應當感謝他的同事張威廉教授,是他主動向青主推薦民主德國安娜·西格爾斯的中篇小說《一個人和他的名字》,說:如果青主愿意翻譯,他可以拿去給上海文藝出版社的負責人吳朗西先生出版”。參見廖乃雄:《憶青主——詩人作曲家的一生》,中央音樂學院出版2008年版,第153-154頁。。而廖青主和陳銓就不同了,前者在音樂學方面卓有成績,對文學也相當熟稔,更兼曾有革命元勛的政治資本,年歲亦高;陳銓更是才華橫溢,不但在中德比較文學、德國思想史研究方面都作出過開辟性的成果,而且更是一個享有聲譽的作家和思想界風云人物。對于這樣的同事,焉能心中沒有半點提防?作為學科領導者的商承祖,或許難免受到這樣的思路的影響。張威廉的朦朧說法或許也提供了某種印證,他說陳銓、廖尚果都很有名、很有才,“但他們個性也比較強”②葉雋:《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的“德國文學學科”歷程——張威廉先生的歷史記憶》,《博覽群書》2005年第4期。。雖然他的話語焉未詳,但其中表達的個體生性與時代語境之間的沖突碰撞是清楚的。但如果僅將問題僅歸結于人事的糾葛也是有局限的,實際上南大德文學科的發展問題,除了可能的“瑜亮情結”與“時代語境”之外,還有一個“青黃不接”的問題,也就是學術薪火承傳的問題,這一點結合馮至門下的人才濟濟可能看得更清楚。如果說廖青主、陳銓是因為政治背景的關系,而不太可能有機會施展長才的話,那么商承祖、張威廉究竟出了怎樣的弟子?雖然像吳永年、董祖祺等人可能偏重于語言學方面,但在文學領域確實是未出現能夠比肩同儕的第三代學者。葉逢植(1929—1990年代,卒年不詳)或許是另外一個可舉的例子③葉逢植簡歷見http://baike.baidu.com/view/6268480.htm,下載于2012年8月10 日。,他大致該算是第2.5 代人,是楊武能的老師,但又是商承祖、張威廉他們那代人的小字輩,本可以作為承繼者而別出手眼,可事實則大不然。作為學生的楊武能一方面強調其“多才多藝”,另一方面則指出其“未能在自己本行出類拔萃,一展長才的主要原因乃是“旁騖太多”④楊武能:《懷才不遇奈若何——懷念葉逢植老師》,《出版廣角》2002年第2期;《多才多藝 可佩可嘆——懷念恩師葉逢植》,載楊武能:《圓夢初記》,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1-85頁。。如此才華橫溢的葉逢植都未能在學科史上贏得地位,更遑論其他人?南大德文學統的某種意義上的“斷裂”,或許可以與北大德文學統的“傳薪”形成一種對照。那么,我們要問的或許是,當商承祖晚年也遭到文革迫害、1975年因病去世之際,他是否也意識到了這些問題,或者竟是,他已然認為,通過自己的精心規劃,南大德文學科已可以薪盡火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