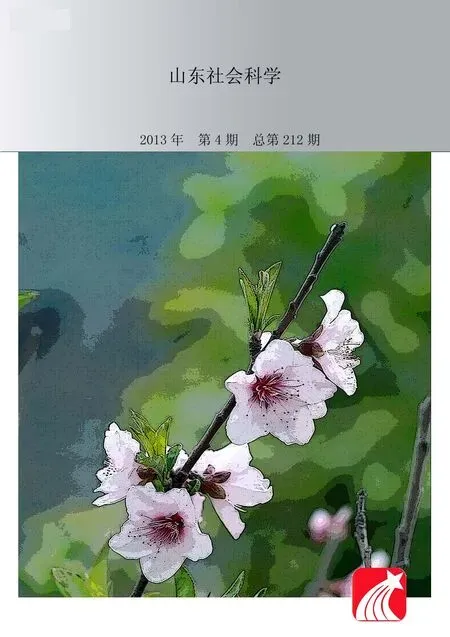南希·弗雷澤關(guān)于全球化時(shí)代公共領(lǐng)域的構(gòu)想
賀 羨
(復(fù)旦大學(xué) 哲學(xué)學(xué)院,上海 200043)
南希·弗雷澤是紐約社會(huì)研究新學(xué)院的哲學(xué)、政治學(xué)教授,是英美批判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理查德·羅蒂贊賞她對(duì)當(dāng)代左翼所面臨的問題的分析,認(rèn)為她是美國(guó)最受關(guān)注的哲學(xué)家之一。注Kevin Olson(ed),Adding Insult to Injury.Verso,2008,p.69.她與哈貝馬斯、阿克塞爾·霍耐特、查爾斯·泰勒等人的論爭(zhēng)推動(dòng)了女性主義理論、批判社會(huì)理論和正義理論的發(fā)展。
公共領(lǐng)域理論是哈貝馬斯商談?wù)卫碚摰幕A(chǔ),也是其政治哲學(xué)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在《公共領(lǐng)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以下簡(jiǎn)稱《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中大致勾勒出了這一理論的基本輪廓,提出了“公共領(lǐng)域”概念,而后在《在事實(shí)與規(guī)范之間》進(jìn)一步發(fā)揮。公共領(lǐng)域是個(gè)體討論公眾事務(wù)或共同利益問題、形成公共輿論的社會(huì)生活領(lǐng)域,它一方面通過讓國(guó)家對(duì)公民負(fù)責(zé),為政治統(tǒng)治的合理化設(shè)計(jì)出一種制度機(jī)制,另一方面設(shè)計(jì)了特定的對(duì)話互動(dòng),指出討論應(yīng)該向所有人開放,參與者作為伙伴進(jìn)行商談,“開放準(zhǔn)入觀念是公共性規(guī)范的核心含義”。注Nancy Fraser,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in Craig Calhoun(ed.),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Cambridge,MA:MIT Press,1992,p.118.公共領(lǐng)域作為公共輿論的生成空間,應(yīng)該是包容的、公平的。公共性應(yīng)當(dāng)質(zhì)疑那些不能經(jīng)受批判檢驗(yàn)的觀點(diǎn),并保證那些可以經(jīng)受檢驗(yàn)的觀點(diǎn)的合法性。此外,公共領(lǐng)域還作為一種政治力量整合公共輿論的載體,它應(yīng)把市民社會(huì)意識(shí)轉(zhuǎn)化成表達(dá)這種公民意志的國(guó)家行動(dòng)。“這兩個(gè)觀念——公共輿論的規(guī)范合法性和政治有效性——對(duì)民主理論中的公共領(lǐng)域概念至關(guān)重要。沒有它們,這個(gè)概念就失去了其批判力量和政治立場(chǎng)。”注Nancy Fraser,Transnationalizing the Public Sphere:On the Legitimacy and Efficacy of Public Opinion in a Post-Westphalian World,in Theory,Culuture﹠Society,2007(24),pp.7-8.在哈貝馬斯看來(lái),資產(chǎn)階級(jí)公共領(lǐng)域正是這樣一種結(jié)合合法性與有效性的形式,只不過現(xiàn)在還是一個(gè)未完全實(shí)現(xiàn)的理想。然而弗雷澤指出,資產(chǎn)階級(jí)公共領(lǐng)域與開放平等的公共性理想是相違背的:基于性別、階級(jí)、種族偏見的排除規(guī)則把一部分人阻擋在政治生活之外,并且這種準(zhǔn)入也只對(duì)民族國(guó)家中的公民才適用。弗雷澤認(rèn)為,哈貝馬斯的話語(yǔ)政治概念以“民族國(guó)家”為核心范疇,隱含了一個(gè)威斯特伐利亞[注]“凱恩斯—威斯特伐利亞架構(gòu)”(Keynesian-Westphalian frame)指戰(zhàn)后民主福利國(guó)家鼎盛時(shí)期正義爭(zhēng)論的國(guó)家領(lǐng)土基礎(chǔ),大致從1945年到20世紀(jì)70年代。哈貝馬斯把現(xiàn)代性政治話語(yǔ)的起源從法國(guó)大革命向前追溯到了“三十年戰(zhàn)爭(zhēng)”(1618-1648)和作為戰(zhàn)爭(zhēng)結(jié)束標(biāo)志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1648)。《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又稱《1648年和約》,是神圣羅馬帝國(guó)的皇帝分別在德意志的奧斯納布呂克和明斯特同瑞典人和法國(guó)人簽署的和約的統(tǒng)稱,它所要解決的主要是各邦國(guó)與帝國(guó)之間的宗教信仰問題、各封建等級(jí)同帝國(guó)和皇帝之間的關(guān)系問題、德國(guó)與周邊國(guó)家的關(guān)系問題等。因此,它實(shí)際上是把宗教和約、國(guó)內(nèi)和約和國(guó)際和約融為一體,不但為神圣羅馬帝國(guó),也為歐洲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嶄新的秩序。哈貝馬斯認(rèn)為,“三十年戰(zhàn)爭(zhēng)”的結(jié)束,帶來(lái)了一個(gè)現(xiàn)代民族國(guó)家體系。而民族國(guó)家在現(xiàn)代國(guó)家政治和國(guó)際政治中一直都是一個(gè)核心范疇。弗雷澤并不關(guān)注此條約的實(shí)際成就,而是用這一詞來(lái)指一種政治想象,即它作為相互承認(rèn)的主權(quán)領(lǐng)土國(guó)家體系塑造了世界,這種想象體現(xiàn)了戰(zhàn)后第一世界關(guān)于正義的爭(zhēng)論架構(gòu)。參見曹衛(wèi)東:《曹衛(wèi)東講哈貝馬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第71-73頁(yè);Kevin Olson(ed),Adding Insult to Injury.Verso,2008,p.273,注1以及Nancy Fraser,Reframing Justiceina Globalizing World,in New Left Review,2005(36),p.2,注1.的政治想象,即有界政治社群及其領(lǐng)土國(guó)家的框架。然而在全球化時(shí)代,這個(gè)框架具有明顯的局限性,已無(wú)法應(yīng)對(duì)諸多跨國(guó)問題,因此應(yīng)予以超越。
一
在《重新思考公共領(lǐng)域》一文中,弗雷澤認(rèn)為,公共領(lǐng)域在產(chǎn)生之初就是男權(quán)主義的,它把女性排斥在公共辯論之外,這一點(diǎn)可以從“public”與“pubic”的詞源聯(lián)系上得到印證。除了性別排斥,早期公共領(lǐng)域中還存在階級(jí)排斥,“仁慈的、平民的、專業(yè)的、文化的俱樂部和社團(tuán)網(wǎng)絡(luò)都不是對(duì)所有人開放的。相反,它是一個(gè)訓(xùn)練場(chǎng),終究是資產(chǎn)階級(jí)男性階層的權(quán)力基礎(chǔ),這些男性把自身視為一個(gè)‘普遍階級(jí)’,并準(zhǔn)備宣稱他們是進(jìn)行統(tǒng)治的合適人選。因此資產(chǎn)階級(jí)形成過程暗含了市民社會(huì)特定文化和聯(lián)合公共領(lǐng)域的闡述”。[注]Nancy Fraser,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in Craig Calhoun(ed.),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Cambridge,MA:MIT Press,1992,p.114.哈貝馬斯認(rèn)識(shí)到了性別排斥與公共領(lǐng)域從貴族向資產(chǎn)階級(jí)轉(zhuǎn)移有關(guān),但他并沒有對(duì)這個(gè)問題進(jìn)行充分考察,有關(guān)某一階級(jí)的公共領(lǐng)域,他也沒有進(jìn)行深入研究,所以弗雷澤認(rèn)為“鼓吹準(zhǔn)入性、理性和地位等級(jí)懸置的公共性話語(yǔ)本身就是作為一種區(qū)別策略出現(xiàn)的”。[注]Nancy Fraser,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in Craig Calhoun(ed.),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Cambridge,MA:MIT Press,1992,p.115.
此外,哈貝馬斯把公共性與地位之間的關(guān)系想象得過于簡(jiǎn)單了,他借助“中立化”對(duì)地位差別存而不論,把自由主義公共領(lǐng)域理想化,沒有對(duì)其他眾多的非自由主義的、非資產(chǎn)階級(jí)的競(jìng)爭(zhēng)公共領(lǐng)域進(jìn)行考察。事實(shí)上,資產(chǎn)階級(jí)公共領(lǐng)域中的公眾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公眾,與資產(chǎn)階級(jí)公眾同時(shí)產(chǎn)生的還有大量其他公眾,如民族主義公眾、精英女性公眾和工人階級(jí)公眾等,它們從一開始就反對(duì)資產(chǎn)階級(jí)公眾的排斥規(guī)范,闡釋不同類型的政治行動(dòng)和公共演講規(guī)范。例如,十九世紀(jì)北美女性即使沒有投票權(quán),也可以通過其他途徑參與公共生活,因此那種認(rèn)為女性被排除在公共領(lǐng)域之外的觀點(diǎn)本身就是意識(shí)形態(tài)的,它依賴于具有階級(jí)和性別偏見的公共性觀念,認(rèn)為表面意義上的資產(chǎn)階級(jí)公共訴求才具有公共性。因此,有學(xué)者認(rèn)為資產(chǎn)階級(jí)公共領(lǐng)域既是一種烏托邦理想,也是一種統(tǒng)治工具。然而,弗雷澤并沒有完全否定資產(chǎn)階級(jí)公共領(lǐng)域的作用,而是在批判其四個(gè)建構(gòu)假設(shè)的基礎(chǔ)上,發(fā)現(xiàn)了后資產(chǎn)階級(jí)公共領(lǐng)域觀念的一些相應(yīng)因素:
第一個(gè)假設(shè)是,公共領(lǐng)域中的對(duì)話者忽略地位差別,似乎以平等的身份進(jìn)行商談,假設(shè)社會(huì)平等不是政治民主的必要條件。事實(shí)上,在沒有任何正式排除的情況下,社會(huì)不平等也可以影響商談不平等,弗雷澤引用了一個(gè)對(duì)男女共同參加會(huì)議的觀察:與男性相比,女性更容易被打斷、發(fā)言更少、更容易被忽略或得不到回應(yīng)。在這種情況下,商談變成了統(tǒng)治的面具。風(fēng)尚和禮儀支配的資產(chǎn)階級(jí)公共領(lǐng)域的對(duì)話非正式地把女性和平民階級(jí)成員邊緣化、阻止她們作為平等伙伴進(jìn)行參與,即使她們?nèi)〉煤戏▍⑴c的資格,仍然會(huì)受到妨礙。對(duì)社會(huì)不平等存而不論并不能促進(jìn)參與平等,相反它更有利于社會(huì)統(tǒng)治群體。
第二個(gè)假設(shè)是,競(jìng)爭(zhēng)公眾的多樣性增長(zhǎng)是背離而不是趨近更廣泛的民主,單一的綜合公共領(lǐng)域比多元公眾更可取。事實(shí)上,分層社會(huì)的基礎(chǔ)制度框架在統(tǒng)治/從屬的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中產(chǎn)生了不平等的社會(huì)群體。在這樣的社會(huì)中,不可能完全實(shí)現(xiàn)公共辯論和商談中的參與平等。如前所述,社會(huì)不平等使公共領(lǐng)域中的對(duì)話過程向統(tǒng)治群體的利益傾斜,特別是只有一個(gè)單一綜合公共領(lǐng)域時(shí)更是如此。這時(shí),從屬群體成員不會(huì)再有相互商討其需求、目標(biāo)和策略的場(chǎng)域,也將失去那些不受統(tǒng)治群體監(jiān)管而進(jìn)行交往的場(chǎng)所。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太可能找到合適的詞語(yǔ)表達(dá)自己的思想,只能保持沉默,結(jié)果在綜合公共領(lǐng)域中就不能表達(dá)、捍衛(wèi)自己的利益,掩飾統(tǒng)治的商談模式就不太可能被揭示出來(lái),這種模式把弱者吸納進(jìn)虛假的“我們”。弗雷澤認(rèn)為,參與意味著用自己的聲音說(shuō)話,同時(shí)通過方言和風(fēng)格來(lái)構(gòu)建、表達(dá)自己的文化身份,包含多元競(jìng)爭(zhēng)公眾之間爭(zhēng)論的安排比單一的綜合公眾能更好地推進(jìn)參與平等理想,她將這些非正統(tǒng)的公眾稱為“亞反公眾”(subaltern counterpublics),他們可以在“主流公共領(lǐng)域”中有效地表達(dá)自身觀點(diǎn)和利益。因?yàn)檫@些占主導(dǎo)的理解和交流手段使邊緣的和被排除的群體處于劣勢(shì),所以他們不得不創(chuàng)造自己的“亞反公眾”來(lái)重新命名他們?cè)馐艿牟徽x,“從屬社會(huì)群體的成員創(chuàng)造、傳播反話語(yǔ)來(lái)塑造對(duì)其身份、利益和需求的相反理解”[注]Nancy Fraser,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in Craig Calhoun(ed.),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Cambridge,MA:MIT Press,1992,p.123.,其增長(zhǎng)能夠提高從屬階層的參與。弗雷澤把第二次女性主義浪潮所提出的概念(如約會(huì)強(qiáng)奸和性騷擾)的發(fā)展和普及當(dāng)做這一方面的典型。同時(shí)她強(qiáng)調(diào),亞反公眾并不總是有效的,其中一些顯然是反民主的、反平等主義的,甚至那些帶有民主和平等主義意向的公眾有時(shí)也在實(shí)踐非正式的排斥和邊緣化模式。“只有那些為了反抗主流公眾排斥而出現(xiàn)的反公眾,才有助于拓展對(duì)話空間。原則上,先前不受質(zhì)疑的假設(shè)將得到公開討論。一般而言,亞反公眾的增加意味著話語(yǔ)爭(zhēng)論的擴(kuò)大,在分層社會(huì)中是一件好事。”[注]Nancy Fraser,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in Craig Calhoun(ed.),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Cambridge,MA:MIT Press,1992,p.124.總之,不管在分層社會(huì)還是在平等主義社會(huì)中,多元公眾比單一公眾更能實(shí)現(xiàn)參與平等理想。
第三個(gè)假設(shè)是,公共領(lǐng)域中的對(duì)話應(yīng)該囿于關(guān)于共同福祉的商談,私人利益和私人問題的出現(xiàn)總是不受歡迎的。這涉及到公共領(lǐng)域的界限問題,即公共性之于私人性的界限。哈貝馬斯關(guān)于資產(chǎn)階級(jí)公共領(lǐng)域論述的核心是,資產(chǎn)階級(jí)公共領(lǐng)域是“私人個(gè)體”商談“公共問題”的對(duì)話場(chǎng)所,公共成員通過商談能夠發(fā)現(xiàn)或創(chuàng)造一種共同利益。在對(duì)話的過程中,參與者由利己主義的私人個(gè)體轉(zhuǎn)變?yōu)槟軌驗(yàn)榱斯餐娑餐袆?dòng)的、具有公益精神的集體。這里的“私人”和“公共”有若干不同的意思,“公共”意味著:與國(guó)家相關(guān)的、對(duì)每個(gè)人開放、關(guān)注每個(gè)人、涉及共同福祉或共享利益。“私人”則意味著:涉及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中的私人財(cái)產(chǎn)、涉及親密的家庭或個(gè)人生活包括性生活。這樣看來(lái),私人利益在政治公共領(lǐng)域中沒有合適的位置,至多它們是商談的“前政治”起點(diǎn),在辯論過程中最終被轉(zhuǎn)化和超越。在政治話語(yǔ)中,“公共”與“私人”的劃分經(jīng)常把某些利益、觀點(diǎn)和主題非法化而為另一些保留商談的空間,使自身利益和群體利益相抵觸,使參與者(尤其是那些相對(duì)無(wú)權(quán)的人)無(wú)法弄清其利益,隱含了資產(chǎn)階級(jí)的、男權(quán)主義的偏見。因此,一個(gè)持久的公共領(lǐng)域觀念必須容納被資產(chǎn)階級(jí)、男權(quán)意識(shí)形態(tài)視為“私人的”、不允許公開討論的利益與議題。
第四個(gè)假設(shè)是,起作用的公共領(lǐng)域需要在市民社會(huì)與國(guó)家之間作出嚴(yán)格區(qū)分。根據(jù)“市民社會(huì)”的不同表達(dá),對(duì)這個(gè)假設(shè)也有兩種不同的理解,第一種理解是,如果市民社會(huì)意味著私人調(diào)節(jié)的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那么堅(jiān)持國(guó)家與市民社會(huì)的分離就是捍衛(wèi)古典自由主義。弗雷澤認(rèn)為,自由放任資本主義不能促進(jìn)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平等,最終需要實(shí)現(xiàn)某些政治管制的經(jīng)濟(jì)整頓形式和再分配(如市場(chǎng)社會(huì)主義)。第二種理解是,“市民社會(huì)”意味著非政府或“亞級(jí)”社團(tuán)的聯(lián)結(jié),它既不是經(jīng)濟(jì)的也不是管理的,而是“聚集起來(lái)形成公眾的一群個(gè)體”,那么市民社會(huì)應(yīng)該與國(guó)家相分離,這確保了更大范圍的檢驗(yàn)。這些“個(gè)體”不以任何官方身份參與公共領(lǐng)域,公共領(lǐng)域是作為國(guó)家的對(duì)應(yīng)物、非政府話語(yǔ)意見的非正式鼓動(dòng)實(shí)體。在資產(chǎn)階級(jí)觀念中,公共領(lǐng)域的超政府特征賦予它所產(chǎn)生的“公共輿論”以獨(dú)立、自由和合法性的光環(huán)。因此,資產(chǎn)階級(jí)公共領(lǐng)域觀念認(rèn)為(聯(lián)合的)市民社會(huì)與國(guó)家的明顯分離是可取的,它促進(jìn)了弗雷澤所謂的“弱公眾”,其話語(yǔ)實(shí)踐只存在于“意見”的形成中,不包括決策制定。如果這種公眾話語(yǔ)向決策制定擴(kuò)展,那么將威脅公共輿論的自主,因?yàn)楣妼⒂行У爻蔀閲?guó)家,失去對(duì)國(guó)家的批判話語(yǔ)監(jiān)督的可能性。但當(dāng)考慮議會(huì)權(quán)威時(shí),這個(gè)問題就變得復(fù)雜了。自從自治議會(huì)在國(guó)家中行使公共領(lǐng)域職能時(shí),就出現(xiàn)了一個(gè)主要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換,弗雷澤稱自治議會(huì)為“強(qiáng)公眾”,其話語(yǔ)既包含意見形成又包括決策制定。議會(huì)是運(yùn)用國(guó)家權(quán)力話語(yǔ)權(quán)威的場(chǎng)合,最終產(chǎn)生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決策(或法律)。隨著議會(huì)自治的實(shí)現(xiàn),(聯(lián)合的)市民社會(huì)與國(guó)家的界限模糊了。不可否認(rèn),議會(huì)自治的出現(xiàn)以及(聯(lián)合的)市民社會(huì)與國(guó)家之間界限的模糊代表了一種民主進(jìn)步,公眾意見的力量得到強(qiáng)化,代表它的實(shí)體被賦予把這種“意見”轉(zhuǎn)換成權(quán)威決定的權(quán)力。因此,一個(gè)合理的公共領(lǐng)域觀念應(yīng)該同時(shí)考慮到“強(qiáng)公眾”與“弱公眾”,并把它們之間的關(guān)系理論化。
綜上所述,弗雷澤認(rèn)為哈貝馬斯的公共領(lǐng)域理論不足以批判后期資本主義社會(huì)的現(xiàn)存民主,必須對(duì)公共領(lǐng)域批判理論進(jìn)行重構(gòu),為此她提出了四項(xiàng)任務(wù):第一,批判理論應(yīng)該說(shuō)明后期資本主義社會(huì)中社會(huì)不平等腐蝕公眾商談的方式;第二,它應(yīng)該闡明在后期資本主義社會(huì)中不平等如何影響公眾之間的關(guān)系、公眾如何被有區(qū)別地賦權(quán)或分割,以及某些公眾如何被迫孤立并服從其他公眾;第三,它應(yīng)該揭示在當(dāng)代社會(huì)中如何能夠廣泛地討論某些被標(biāo)識(shí)為“私人的”利益和議題,以及這些問題的解決途徑;最后,它應(yīng)該說(shuō)明后期資本主義社會(huì)中某些公共領(lǐng)域的過度軟弱如何剝奪“公眾意見”的實(shí)踐力量。
二
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中,哈貝馬斯對(duì)公共領(lǐng)域的研究在兩個(gè)層面上同時(shí)進(jìn)行,一個(gè)是經(jīng)驗(yàn)的和歷史的,另一個(gè)是意識(shí)形態(tài)批判的和規(guī)范的。在這兩個(gè)層面上,公共領(lǐng)域被概念化為是與有界政治社群和主權(quán)領(lǐng)土國(guó)家(經(jīng)常是民族國(guó)家)共存的。無(wú)疑,這一直不是完全明確的。哈貝馬斯關(guān)于公共領(lǐng)域的論述至少依賴六個(gè)社會(huì)理論假設(shè):(1)在公共領(lǐng)域的領(lǐng)土基礎(chǔ)方面,把公共領(lǐng)域與在邊界領(lǐng)土之上運(yùn)用主權(quán)的現(xiàn)代國(guó)家機(jī)構(gòu)聯(lián)系起來(lái);(2)在公共領(lǐng)域的參與主體方面,把公共領(lǐng)域討論的參與者視為一個(gè)有界政治社群的伙伴成員;(3)在公共領(lǐng)域討論的主題方面,把公共領(lǐng)域討論的首要主題設(shè)想為對(duì)政治社群的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進(jìn)行適當(dāng)安排;(4)在公共領(lǐng)域的交流方式方面,把公共領(lǐng)域與現(xiàn)代媒體聯(lián)系起來(lái),使交流超越距離,把空間上分散的對(duì)話者集中到一個(gè)公共場(chǎng)所中,然而,哈貝馬斯暗地里通過關(guān)注國(guó)家媒體尤其是國(guó)家出版和國(guó)家廣播把“公共性”領(lǐng)土化;(5)在公共領(lǐng)域的交流媒介方面,默認(rèn)公共領(lǐng)域討論是完全可理解的、在語(yǔ)言上是清楚明白的;(6)在公共領(lǐng)域的淵源方面,把公共領(lǐng)域的文化本源追溯至十八、十九世紀(jì)的印刷資本主義的信件與小說(shuō)。它把這些資產(chǎn)階級(jí)風(fēng)格歸功于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主體立場(chǎng),通過它個(gè)體把自身預(yù)想成公眾成員。這六個(gè)假設(shè)都存在于政治空間的威斯特伐利亞架構(gòu)中。
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中,公共性是與現(xiàn)代領(lǐng)土國(guó)家和國(guó)家想象聯(lián)系在一起的,哈貝馬斯沒有質(zhì)疑現(xiàn)代領(lǐng)土國(guó)家民主化過程的威斯特伐利亞框架,而是預(yù)想了恰好處于其中的民主商談模式。“在這個(gè)模式中,民主需要通過公共交流的領(lǐng)土邊界過程、受國(guó)家語(yǔ)言的引導(dǎo)、通過國(guó)家媒體轉(zhuǎn)述產(chǎn)生一個(gè)國(guó)家公共輿論的實(shí)體。……它有助于把國(guó)家政治統(tǒng)治理性化,應(yīng)該保證威斯特伐利亞國(guó)家的行動(dòng)和政策反映國(guó)家公民在對(duì)話中形成的政治意志。因此,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中,公共領(lǐng)域是(國(guó)家)威斯特伐利亞民主的關(guān)鍵制度成分。”[注]Nancy Fraser,Transnationalizing the Public Sphere:On the Legitimacy and Efficacy of Public Opinion in a Post-Westphalian World,in Theory,Culuture﹠Society,2007(24),p.11.在哈貝馬斯看來(lái),公共領(lǐng)域概念在其深層概念結(jié)構(gòu)中完全是威斯特伐利亞的,“只有近年來(lái),一方面由于后冷戰(zhàn)的地緣政治的不穩(wěn)定性,另一方面由于與‘全球化’相聯(lián)的跨國(guó)現(xiàn)象增強(qiáng)的顯著性,它才在跨國(guó)框架中反思公共領(lǐng)域理論中變得可能且必然”。[注]Nancy Fraser,Transnationalizing the Public Sphere:On the Legitimacy and Efficacy of Public Opinion in a Post-Westphalian World,in Theory,Culuture﹠Society,2007(24),p.8.事實(shí)上,哈貝馬斯在《包容他者》中已經(jīng)指出,民族國(guó)家正受到內(nèi)部多元化與外部全球化的雙重挑戰(zhàn),全球化的趨勢(shì)使民族國(guó)家內(nèi)在主權(quán)的局限性充分暴露出來(lái)。一個(gè)民族國(guó)家想要捍衛(wèi)其內(nèi)在主權(quán)的話,就很難加入到全球一體化的進(jìn)程當(dāng)中;而要投身到這個(gè)進(jìn)程中去,民族國(guó)家就必須作出一定的讓步,把自己的部分主權(quán)讓渡給全球化的機(jī)構(gòu)。面對(duì)這一困境,哈貝馬斯嘗試為民族國(guó)家尋找新的合法化理由,以便順應(yīng)全球化大潮,即走向一種“后民族國(guó)家”的世界格局。按照哈貝馬斯的理解,這種新的世界政治共同體就是一種沒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內(nèi)政,其基礎(chǔ)是建立在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和非政府組織基礎(chǔ)上的全球公民社會(huì)。然而,匈牙利作家皮特·艾斯特哈茨(Peter Esterhazy)指出,哈貝馬斯構(gòu)建的“后民族格局”“不過又是一個(gè)超級(jí)大國(guó)(歐洲國(guó)),一個(gè)尋求與美國(guó)平起平坐的‘歐洲民族國(guó)家’”[注]曹衛(wèi)東:《曹衛(wèi)東講哈貝馬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頁(yè)。,實(shí)際上仍然沒有擺脫威斯特伐利亞框架的窠臼。
因此,弗雷澤試圖重構(gòu)公共領(lǐng)域概念使之適應(yīng)后威斯特伐利框架,后威斯特伐利亞框架實(shí)際上是一種新的全球政治框架。在后威斯特伐利亞世界中,公共領(lǐng)域溢出了國(guó)家邊界,形成了不再以共同的語(yǔ)言、出身、血緣以及地域等為基礎(chǔ)的“跨國(guó)公共領(lǐng)域”。事實(shí)上,弗雷澤對(duì)后威斯特伐利亞框架的構(gòu)想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她對(duì)《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的批判分為兩種:一種是合法性批判,另一種是有效性批判。前者關(guān)注市民社會(huì)中的關(guān)系,主張《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模糊了剝奪一些名義上為公眾成員的人作為公共辯論的完全伙伴、與他人平等參與的能力的系統(tǒng)障礙的存在;后者關(guān)注市民社會(huì)與國(guó)家的關(guān)系,主張《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沒有指出剝奪政治力量在對(duì)話中產(chǎn)生的公共輿論的系統(tǒng)障礙的全部范圍。然而,兩種批判仍然導(dǎo)向有界政治社群的商談民主前景,它們繼續(xù)把公眾與領(lǐng)土國(guó)家公民等同起來(lái),其目標(biāo)都是要在現(xiàn)代領(lǐng)土國(guó)家中使商談民主更進(jìn)一步。
在《公共領(lǐng)域的跨國(guó)化》(2007)一文中,弗雷澤修正了上述批判的理論前提,指出“不管問題是全球變暖還是移民、女性還是貿(mào)易協(xié)定、失業(yè)還是‘反對(duì)恐怖主義的戰(zhàn)爭(zhēng)’,目前公共輿論的變動(dòng)很少停留在領(lǐng)土國(guó)家邊界內(nèi)。在許多情況下,對(duì)話者沒有構(gòu)成民眾或政治公民。她們的交往通常既不存在于威斯特伐利亞國(guó)家中,也不通過國(guó)家媒體傳播。此外,辯論的問題通常就是跨領(lǐng)土的,既不能被置于威斯特伐利亞空間中,也不能通過威斯特伐利亞國(guó)家得到解決。”[注]Nancy Fraser,Transnationalizing the Public Sphere:On the Legitimacy and Efficacy of Public Opinion in a Post-Westphalian World,in Theory,Culuture﹠Society,2007(24),p.14.這對(duì)哈貝馬斯的《在事實(shí)與規(guī)范之間》關(guān)于公共性的討論也同樣適用,哈貝馬斯在這本書中集中考慮有效性問題,它把法律當(dāng)作交往權(quán)力轉(zhuǎn)化成統(tǒng)治權(quán)力的適當(dāng)工具,區(qū)分了權(quán)力的正式的民主循環(huán)與非正式的非民主循環(huán)。在前者中,弱公眾影響強(qiáng)公眾,最終控制國(guó)家機(jī)器;在后者中,私人社會(huì)權(quán)力和根深蒂固的官僚利益控制法律制定者、操縱公共輿論。“哈貝馬斯承認(rèn)非正式循環(huán)通常勝出,他在這里提供了關(guān)于民主國(guó)家中公共輿論有效性缺陷的更完整論述。”[注]Nancy Fraser,Transnationalizing the Public Sphere:On the Legitimacy and Efficacy of Public Opinion in a Post-Westphalian World,in Theory,Culuture﹠Society,2007(24),pp.13-14.“哈貝馬斯支持社會(huì)整合的后民族主義形式,即‘憲政愛國(guó)主義’[注]有學(xué)者將其譯為“憲法愛國(guó)主義”,而哈貝馬斯用這一詞表示德國(guó)人對(duì)于目前憲法制度的普遍認(rèn)同,因此譯為“憲政愛國(guó)主義”更貼切。(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其目標(biāo)是剝開國(guó)家主義的包裹,解放民主國(guó)家。但是在這里他實(shí)際上贊同一種更加純粹的威斯特伐利亞公共性觀念,因?yàn)樗澩环N更具有排他性的領(lǐng)土觀念。”[注]Nancy Fraser,Transnationalizing the Public Sphere:On the Legitimacy and Efficacy of Public Opinion in a Post-Westphalian World,in Theory,Culuture﹠Society,2007(24),p.14.
三
在這種情況下,理論界出現(xiàn)了“跨國(guó)公共領(lǐng)域”、“流散公共領(lǐng)域”、“全球公共領(lǐng)域”這樣的表述。弗雷澤認(rèn)為,目前跨國(guó)公共領(lǐng)域的出現(xiàn)可以被視為另一種“公共領(lǐng)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但在她之前,學(xué)界對(duì)這種新的公共領(lǐng)域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的論述還很不充分。她為了澄清問題、提出可操作性的公共領(lǐng)域批判理論,主張回到威斯特伐利亞公共領(lǐng)域理論的六個(gè)建構(gòu)假設(shè)上來(lái),認(rèn)為這些假設(shè)都是反事實(shí)的:
(1)在公共領(lǐng)域的領(lǐng)土基礎(chǔ)方面,現(xiàn)在的領(lǐng)土國(guó)家(不論貧富)都與國(guó)際組織、政府間網(wǎng)絡(luò)和非政府組織分享許多關(guān)鍵的管理職能。這種情況不僅適用于相對(duì)較新的功能,如環(huán)境監(jiān)管,而且也適用于傳統(tǒng)功能,如防衛(wèi)和治安。這些組織現(xiàn)在的確被霸權(quán)國(guó)家所掌控,然而運(yùn)用霸權(quán)的模式已不同于以往:霸權(quán)不是求助于排他的、不可分割的國(guó)家主權(quán)的威斯特伐利亞模式,它越來(lái)越通過解體主權(quán)的后威斯特伐利亞模式來(lái)運(yùn)作。因此,公共領(lǐng)域理論的第一個(gè)前提在經(jīng)驗(yàn)上是站不住腳的。
(2)在公共領(lǐng)域的參與主體方面,當(dāng)今的公共領(lǐng)域與政治成員身份不能共存。由于移民、遷徙等現(xiàn)象,現(xiàn)在每個(gè)國(guó)家領(lǐng)域內(nèi)都有非公民,對(duì)話者經(jīng)常既不是族人也不是伙伴公民。因此,他們的觀點(diǎn)既不代表共同利益也不代表任何民眾的普遍意志。
(3)在公共領(lǐng)域討論的主題方面,外包、跨國(guó)企業(yè)和“離岸商業(yè)登記”(offshore business registry)使基于領(lǐng)土的國(guó)民生產(chǎn)在很大程度上只存留于觀念上。由于布雷頓森林資本控制的全天候(24/7)全球電子金融市場(chǎng)的出現(xiàn),國(guó)家對(duì)貨幣的控制現(xiàn)在非常有限。調(diào)控貿(mào)易、生產(chǎn)和金融的基礎(chǔ)規(guī)則應(yīng)由跨國(guó)機(jī)構(gòu)來(lái)制定,它們向全球資本而不是向任何公眾負(fù)責(zé)。
(4)在公共領(lǐng)域的交流方式方面,“分眾媒體”(niche media)變得豐富多樣,它們致力于使國(guó)家權(quán)力的運(yùn)用服從于公共性檢驗(yàn)。即時(shí)電子、寬頻和衛(wèi)星信息技術(shù)繞過了國(guó)家控制,使直接的跨國(guó)交流成為可能。所有這些發(fā)展標(biāo)志著交流設(shè)施的“解國(guó)家化”(de-nationalization)。
(5)在公共領(lǐng)域的交流媒介方面,當(dāng)語(yǔ)言群體在地域上是分散的、更多的言說(shuō)者會(huì)多種語(yǔ)言時(shí),許多國(guó)家事實(shí)上是多語(yǔ)言的。同時(shí),英語(yǔ)作為全球商業(yè)、大眾娛樂和學(xué)術(shù)界的通用語(yǔ)得到鞏固,所以單一國(guó)家語(yǔ)言的預(yù)設(shè)就不再成立了。
(6)在公共領(lǐng)域的淵源方面,由于文化混雜性與混合化、全球大眾娛樂的出現(xiàn)、視覺文化的崛起,哈貝馬斯認(rèn)為支撐公共領(lǐng)域?qū)υ捳咧饔^立場(chǎng)的那種民族文學(xué),不再能為團(tuán)結(jié)提供共同的社會(huì)想象了。
總之,對(duì)公共輿論的每個(gè)構(gòu)成因素而言,公共領(lǐng)域逐漸成為跨國(guó)的或后民族的,先前威斯特伐利亞國(guó)家公民交往的“誰(shuí)”(who),現(xiàn)在經(jīng)常是一個(gè)分散對(duì)話者的集合,而不能構(gòu)成一個(gè)統(tǒng)一的民眾。在跨國(guó)社群中,先前植根于威斯特伐利亞國(guó)民經(jīng)濟(jì)中的交往的“什么”(what),現(xiàn)在已經(jīng)遍及全球,然而并不體現(xiàn)在同樣廣闊的團(tuán)結(jié)與認(rèn)同中。曾經(jīng)存在于威斯特伐利亞國(guó)家領(lǐng)土的交往的“哪里”(where),現(xiàn)在被解域?yàn)榫W(wǎng)絡(luò)空間。曾經(jīng)依賴于威斯特伐利亞國(guó)家出版媒體的交往的“如何”(how),現(xiàn)在涵蓋了斷裂的、重疊的視覺文化的廣闊跨語(yǔ)言連結(jié)。曾經(jīng)對(duì)公共輿論負(fù)責(zé)的主權(quán)領(lǐng)土國(guó)家,現(xiàn)在是公共與私人跨國(guó)權(quán)力的不規(guī)則混合物,既不能被輕易識(shí)別也不能被認(rèn)為是應(yīng)負(fù)責(zé)的。
那么,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亞框架的跨國(guó)公共輿論如何能夠在規(guī)范上具有合法性、在政治上具有有效性呢?弗雷澤從下述兩個(gè)方面對(duì)這個(gè)問題進(jìn)行了思考:首先考慮規(guī)范合法性問題,這涉及到兩個(gè)標(biāo)準(zhǔn):包容的范圍和參與平等的程度。前者關(guān)注“誰(shuí)”被授權(quán)參與公共討論,后者關(guān)注參與者“如何”互動(dòng)。按照包容標(biāo)準(zhǔn),討論必須在原則上對(duì)所有受決策結(jié)果影響的人開放。威斯特伐利亞框架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參與平等標(biāo)準(zhǔn),而忽略了包容標(biāo)準(zhǔn)。然而在全球化時(shí)代,公民身份不再能夠代表受影響的人了,一個(gè)人的生存條件不再完全依賴于政治社群的內(nèi)在構(gòu)建了,而是越來(lái)越多地受到其他外在的和非領(lǐng)土結(jié)構(gòu)的制約。面對(duì)這個(gè)問題,弗雷澤起初采納“所有受影響者原則”(all-affected principle),認(rèn)為所有潛在受到?jīng)Q策影響的人都應(yīng)該作為伙伴參與共同事務(wù)的商談,但是在《非常規(guī)正義》一文中,她認(rèn)為“所有受影響者原則成為蝴蝶效應(yīng)的‘歸謬法’(reductio ad absurdum)的犧牲品,它把所有人都變得受一切事物的影響。它不能識(shí)別道德相關(guān)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在抵制它試圖避免的一刀切全球主義時(shí)遇到麻煩。因此,它不能為決定“誰(shuí)”提供一個(gè)有說(shuō)服力的標(biāo)準(zhǔn)。”[注]Nancy Fraser,Abnormal Justice,in Kwame Anthony Appiah(etc.),Justice,Governance,Cosmopolitanism,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Reconfigurations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Humboldt-Universitat zu Berlin,2007,p.135.她轉(zhuǎn)而提出“所有從屬者原則”(all-subjected principle),“根據(jù)這一原則,所有從屬于特定統(tǒng)治結(jié)構(gòu)的人都有一個(gè)與之相關(guān)的、作為正義主體的道德立場(chǎng)。把人們變成正義伙伴主體的既不是共同的公民資格或國(guó)籍,也不是共同擁有抽象的人格,也不是因果相互依存的純粹事實(shí),而是都從屬于一種統(tǒng)治結(jié)構(gòu),這一結(jié)構(gòu)為他們/她們之間的互動(dòng)設(shè)置了基本規(guī)則。對(duì)于所有統(tǒng)治結(jié)構(gòu)而言,所有從屬者原則使道德關(guān)懷的范圍與受影響的范圍相配。”[注]Nancy Fraser,Abnormal Justice,in Kwame Anthony Appiah(etc.),Justice,Governance,Cosmopolitanism,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Reconfigurations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Humboldt-Universitat zu Berlin,2007,pp.135-136.這些統(tǒng)治結(jié)構(gòu)不只局限于國(guó)家,還包括能制定強(qiáng)制規(guī)則的非國(guó)家主體,因此,所有從屬者原則為后威斯特伐利亞公共輿論的合法性提供了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
其次考慮政治有效性問題。在公共領(lǐng)域理論中,當(dāng)且僅當(dāng)公共輿論被政治力量所調(diào)動(dòng),使公共力量負(fù)有責(zé)任,保證后者的實(shí)施反映了市民社會(huì)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意志時(shí),它就是有效的。這涉及到兩個(gè)標(biāo)準(zhǔn):轉(zhuǎn)化標(biāo)準(zhǔn)和能力標(biāo)準(zhǔn)。根據(jù)轉(zhuǎn)化標(biāo)準(zhǔn),市民社會(huì)中產(chǎn)生的交往權(quán)力必須首先轉(zhuǎn)化成具有約束力的法律,然后再轉(zhuǎn)化成行政權(quán)力。根據(jù)能力標(biāo)準(zhǔn),公共權(quán)力必須能夠執(zhí)行在對(duì)話中形成的意志。前者關(guān)注從市民社會(huì)到公共權(quán)力的交往權(quán)力流動(dòng),后者關(guān)注行政權(quán)力實(shí)現(xiàn)公共計(jì)劃的能力。過去的公共領(lǐng)域理論假定,公共輿論的接收者是威斯特伐利亞國(guó)家,它應(yīng)該被民主地構(gòu)建,因此沒有阻斷從弱公眾到強(qiáng)公眾的交往流動(dòng),能被轉(zhuǎn)化成具有約束力的法律。同時(shí),威斯特伐利亞國(guó)家具有運(yùn)用這些法律的必要行政能力,以便實(shí)現(xiàn)其公民的目標(biāo)并解決相關(guān)問題。因此,威斯特伐利亞國(guó)家被認(rèn)為是實(shí)現(xiàn)公共領(lǐng)域有效性的轉(zhuǎn)化標(biāo)準(zhǔn)和能力標(biāo)準(zhǔn)的適當(dāng)工具。盡管威斯特伐利亞框架刺激了對(duì)轉(zhuǎn)化標(biāo)準(zhǔn)的興趣,但卻模糊了能力標(biāo)準(zhǔn),它只強(qiáng)調(diào)國(guó)家公共領(lǐng)域產(chǎn)生的交往權(quán)力是否足夠強(qiáng)大以致影響立法、限制國(guó)家行政。相應(yīng)地,討論集中在什么應(yīng)被當(dāng)做市民社會(huì)與國(guó)家之間的民主權(quán)力循環(huán),而沒有過多討論國(guó)家監(jiān)管塑造公民生活的私人權(quán)力的能力,舉例來(lái)說(shuō),一些理論家認(rèn)為,經(jīng)濟(jì)實(shí)際上是國(guó)家的,民族國(guó)家能夠以國(guó)家公民的利益對(duì)其進(jìn)行調(diào)控。但是在全球化時(shí)代,如果現(xiàn)代領(lǐng)土國(guó)家不再擁有調(diào)控其經(jīng)濟(jì)、保證其國(guó)家環(huán)境完整、為其公民提供安全和福利的行政能力,那么應(yīng)當(dāng)如何理解公共輿論有效性的能力標(biāo)準(zhǔn)呢?這個(gè)問題涉及到國(guó)際法和跨國(guó)機(jī)構(gòu)的權(quán)責(zé)問題,是后威斯特伐利亞框架不可繞過的具體問題,雖然弗雷澤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當(dāng)前的公共領(lǐng)域理論也只提供了少許線索,但是疑問本身就指明了進(jìn)一步研究的目標(biāo),即如何創(chuàng)造新的跨國(guó)公共權(quán)力,并讓它們對(duì)新的跨國(guó)公共領(lǐng)域負(fù)責(zé)。
- 山東社會(huì)科學(xué)的其它文章
- 論中國(guó)勞動(dòng)力人口對(duì)外輸出問題
- 山東省上市公司企業(yè)文化建設(shè)問題與對(duì)策研究
- 企業(yè)領(lǐng)導(dǎo)團(tuán)隊(duì)內(nèi)部社會(huì)資本如何影響經(jīng)營(yíng)成長(zhǎng)績(jī)效
——基于領(lǐng)導(dǎo)團(tuán)隊(duì)凝聚力中介效應(yīng)的分析 - 人口高速老齡化的理論應(yīng)對(duì)
——從健康老齡化到積極老齡化 - 金融危機(jī)、審計(jì)質(zhì)量與真實(shí)活動(dòng)盈余管理
- 基于PVAR的基金持股比例與股價(jià)波動(dòng)的關(guān)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