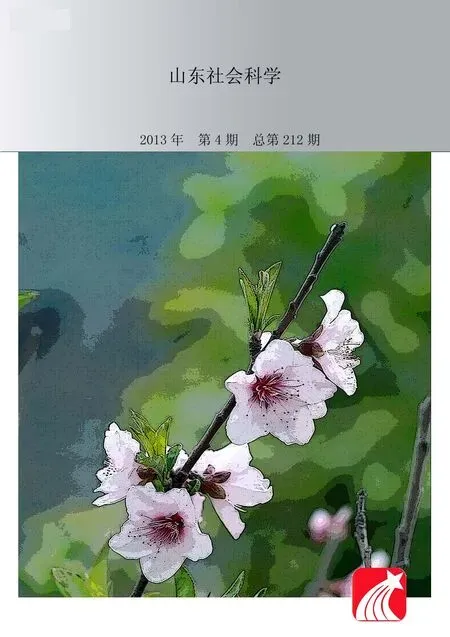我國刑事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的改革及其評價
史立梅
(北京師范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875)
我國1997年刑事訴訟法確立了控辯式庭審方式,旨在加強控辯雙方在庭審中的對抗,以實現庭審功能的實質化。但實踐中證人出庭作證率普遍低于5%的狀況,導致大量證人證言筆錄在法庭上被使用,控辯雙方無法質證,法官難以審查證言真偽,審判的結果依然取決于庭后閱卷,審判重新淪為看形式、走過場。這種缺乏程序公正的審判,極容易導致社會公眾對審判結果公正性的質疑,甚至影響司法活動本身應當具有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為解決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的這一難題,本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將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作為一項重要內容列入其中,以期通過強化證人出庭來增強我國庭審活動的公正性,但其實效如何尚待司法實踐的進一步檢驗。如果僅從法條內容上來看,新刑事訴訟法對證人出庭作證問題的改革是全方位的:不僅明確了必須出庭作證的證人范圍,而且初步建立了親屬間拒絕作證制度;不僅確立了強制證人出庭作證制度,而且規定了證人處罰措施;不僅建立了證人保護制度,而且賦予了證人獲得經濟補償的權利;不僅規定了普通證人出庭作證的義務,而且規定了警察出庭作證的義務。以下本文就分五個專題對上述修改進行一番檢視和評論。
一、證人出庭作證的范圍
無論是采行直接原詞審理原則的大陸法系國家,還是奉行傳聞證據規則的英美法系國家,均不要求刑事訴訟中所有的證人都必須出庭作證。普遍的做法是采取原則加例外的立法模式,即在一般性地要求證人出庭提供證詞的前提下,通過法律明確規定可以不出庭作證的證人范圍。比如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803、804條將不必出庭以及不能出庭的證人作為傳聞證據規則的例外進行了規定;《德國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款對允許在法庭上宣讀的詢問證人筆錄的范圍進行了規定;《日本刑事訴訟法》第158條第1款則對法院可以在庭外詢問證人的情形進行了規定。我國1997年《刑事訴訟法》對于證人是否必須出庭作證未加以明確規定,但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出臺的《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41條對此進行了補充規定,即“證人應當出庭作證。符合下列情形,經人民法院準許的,證人可以不出庭作證:(一)未成年人;(二)庭審期間身患嚴重疾病或者行動極為不便的;(三)其證言對案件的審判不起直接決定作用的;(四)有其他原因的。”從立法方式上來看,本條規定也采取了原則加例外的方式,但是從內容上來看,其中的幾項例外規定過于粗疏,尤其是“有其它原因的”規定過于籠統,為執法和守法留下了很大的空白,實踐中可以任意出入,從而使“證人應當出庭作證”的規定流于形式。
盡管我國訴訟法學理論界與實務界對于證人應當出庭作證基本上能夠達成共識,但對于究竟應該如何界定證人出庭作證的范圍,則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絕大多數學者認為應當采用原則加例外的立法方式,同時對例外情形要盡可能規定的明確、具體。比如有的學者認為應當將證人出庭的例外情形規定為兩大類:一類是證人因死亡、疾病、路途遙遠、下落不明等客觀原因不能出庭;另一類則是控辯雙方對證言無爭議,證人在客觀上沒有必要出庭。[注]宋英輝主編:《刑事訴訟法修改問題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頁。也有的學者主張明確列舉可以使用詢問筆錄或者書面證言的情形。[注]樊崇義等著:《刑事訴訟法修改專題研究報告》,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91頁。盡管學者們在例外情形的具體表述上不盡一致,但觀點基本趨向一致。與學界的觀點相反,我國司法實務界并不認可這種原則上出庭、例外情形下不出庭的方式,而是傾向于對應當出庭作證的證人范圍進行明確界定。比如2009年在北京檢法機關出現的“關鍵證人出庭作證”的改革探索,要求屬于檢法機關確定的“關鍵證人”,即對于查明案件中存在爭議的關鍵問題能夠起到幫助、證明作用的重要證人,必須出庭提供證言。[注]龍平川、李曉娟:《北京探索“關鍵證人”出庭作證機制》,《檢察日報》2009年6月11日第4版。
新刑事訴訟法顯然采納了實務界的觀點,根據該法第187條第1款的規定,“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并且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異議,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據此,應當出庭作證的證人必須同時具備以下三個條件:第一,必須是關鍵證人,即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這排除了那些非關鍵證人出庭的必要性。第二,證言必須屬于控辯雙方有異議的證據。控辯雙方無異議的證言,即便對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也不需要證人出庭。第三,必須是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即便屬于控辯雙方有異議的關鍵證人的證言,如果法院認為證人不出庭也能調查清楚的,也有權決定證人不必出庭。上述三個條件分別從證言的證據價值、控辯雙方對證言的態度以及法院的自由裁量權方面對應當出庭作證的證人范圍進行了界定。
顯然,新刑事訴訟法在證人出庭作證范圍的問題上,采取了非常務實的態度:如果原則上要求所有的證人都必須出庭作證,在我國現有的司法資源和民眾法律素質現狀之下,很難具有現實可行性。與其規定一個根本難以實現的制度,反而不如集中力量確保最重要的那部分證人能夠出庭作證。這種修改法律的思路具有相對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決證人出庭難的問題。但是,從理論上來說,新法對證人出庭作證范圍的界定頗有不妥之處:其一,在確定證人出庭范圍問題上,法院擁有過大的自由裁量權。新刑事訴訟法第187條第1款實際上賦予了法院雙重裁量的權利:一是證人證言是否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需要由法院進行裁量;二是證人是否有必要出庭作證,仍需要由法院予以裁量。在法院不能保持客觀、公正、中立立場或者怠于對證人證言進行查證的情況下,辯護方仍難以實現與關鍵的控方證人進行對質,證人出庭作證率仍然會比較低。其二,對于經法院確定應當出庭作證的證人,如果其拒不出庭,或者雖然出庭,但其拒絕提供證言,其審前的詢問筆錄或者書面證言應如何處理,法律并沒有明確規定。在這一問題上,法律對證人證言和鑒定意見采取了不同的態度:根據新刑事訴訟法第187條第3款的規定,經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因此,從新刑事訴訟法第187條前后文的規定來看,對于應當出庭而拒不出庭的證人,其證言筆錄仍有可能被合法地采納為定案的根據。這種程序性法律后果的缺乏,將會進一步導致法院怠于傳喚證人出庭作證。其三,作為調整我國刑事訴訟活動的根本法律,刑事訴訟法應具有一定的預見性和超前性,被動地局限于社會現狀,雖然可以確保法律在短時期內發揮實效,但若從長期發展的角度來看,則不利于我國刑事司法文明程度的整體推進和提升。畢竟這種嚴格限制出庭證人范圍的立法模式,在目前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是較為少見的。總之,相對于1997年刑事訴訟法而言,新法對證人出庭作證范圍的明確界定是一種進步,但這種界定的方式與內容仍與學者們的期待存在一定差距。
二、強制證人出庭措施
在證人應當出庭而拒絕出庭的情況下,賦予法庭以相應的強制證人出庭的權利,是兩大法系國家的普遍做法。在英美法系,證人拒絕出庭作證將被指控犯有藐視法庭罪,法官有權力對其判處罰金或監禁。在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也大多有強制證人出庭的處罰措施。比如《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110條和第111條規定了對證人的傳訊、罰款和監禁措施;《德國刑事訴訟法》第51條規定了對拒不到庭的證人采取的強制拘傳、拘留和罰款措施;日本《日本刑事訴訟法》第150、151條也規定了對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的證人可以予以罰款或者拘留。上述國家有關強制證人出庭的措施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如傳喚、拘傳等強制證人到庭的保障性措施;另一類則是如罰款、拘留等對拒不到庭的證人采取的處罰性措施。強制證人出庭措施的存在,一方面可以督促證人積極履行出庭作證義務,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懲罰消極證人體現司法活動的嚴肅性和權威性。我國1997年刑事訴訟法和相關的司法解釋均未對強制證人出庭的措施加以規定,因此,雖然司法解釋要求證人出庭作證,但實踐中對于無正當理由拒不出庭的證人,司法機關也無相應對策,最終只能使用書面的證言筆錄。這也是導致我國證人出庭率低的一個重要原因。
新刑事訴訟法彌補了原有法律之不足,對強制證人出庭的措施進行了規定。根據新法第188條第1款,“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根據新法188條第2款,“證人沒有正當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絕作證,予以訓誡,情節嚴重的,經院長批準,處以10日以下的拘留。被處罰人對拘留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復議。復議期間不停止執行。”上述規定體現出我國強制證人到庭制度的三個特點:第一,對證人采取強制到庭措施或者處罰措施的前提,必須是證人經通知無正當理由拒不出庭。因此,在強制證人到庭或者處罰證人之前,法院應詢問證人因何不到庭,給證人說明理由的機會。第二,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能成為強制到庭的對象。這里法律雖然沒有明確賦予親屬之間享有拒絕作證特權,但是如果被告人的上述親屬拒絕到庭提供證言,法院不能強迫其到庭。這在效果上等同于確立了親屬間拒絕作證的權利。第三,從本條文在法律中所處的位置和內容上來看,只有人民法院才有權強制證人出庭作證并處罰不到庭的證人,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沒有強迫證人提供證言的權力。因此,對于拒不出庭的控方證人,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無權強制其出庭,只能向法院提出申請,由法院決定是否采取強制證人出庭的措施。
新法關于強制證人出庭的規定對于確保符合法定條件的證人出庭作證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與舊法相比無疑是一個進步。但是,新法第188條的規定仍有一些未盡事宜,需要由法律或者司法解釋予以進一步明確:第一,證人如果有正當理由不能出庭,比如因為證人已經死亡、患有嚴重疾病或者路途十分遙遠、下落不明等情況,那么該證人之前曾提供的證言筆錄或者書面證言能否被法院采納作為定案根據?第二,如果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出庭作證,那么其之前提供的證言應如何處理,能否被法院采納為定案根據?第三,證人如果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或者到庭后拒絕提供證言,在對證人進行處罰后,其之前提供的證言應如何處理,是否還能夠被法院采納為定案根據?上述三種情形的共同特征都是該名證人曾經向公安司法機關提供過證言,并且均不能在審判時到庭作證。如果一概采納這些書面證言,那么法律所規定的證人出庭作證又將成為一紙空文;但是如果一概排除這些書面證言,那么又可能會導致那些重大犯罪分子因為指控證據不充分而逃避法律的制裁。也許正是基于這種兩難選擇,立法者在新法中回避了這一問題。法律上未規定不等于實踐中不會發生,況且上述情形在實踐中發生的機率還比較大。
對于這一問題,筆者認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有關對質權條款例外的判例對我們頗具有啟發意義。1980年的羅伯特案和2004的克勞福德案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對質權條款的例外問題上形成的兩個典型判例:根據羅伯特案,如果控方證明了證人不能出庭,那么只有在該證言具有“明顯的可靠性”的前提下才具有可采性。這種可靠性可以從以下兩種途徑推斷出來:其一,該陳述屬于某種根深蒂固的傳聞例外;其二,該陳述的可靠性有特別的保證。[注]OhioV.Robert,488U.S.56(1980).根據克勞福德案,對質權條款禁止采用那些不到庭證人的證言,除非證人確實不能到庭以及被告人事先有交叉詢問的機會。[注]CrawfordV.Washington,541U.S.36(2004).上述兩個判例都沒有一概否定未到庭證人證言的可采性,只不過在采納標準上,二者分別側重了實體層面和程序層面。基于這兩個判例的啟發,筆者認為,針對不能出庭證人的證言,我們可以采取綜合標準解決其可采性問題:首先,由提供證據的一方就證人確實不能出庭作證提供證明。其目的是促使舉證方盡可能去尋找、說服證人出庭,只有在舉證方盡一切努力仍不能獲得該名證人出庭作證的情況下,才允許舉證方向法庭提出采納該書面證言的要求。其次,由法庭審查該證人是否曾經在以前的程序中就該證言接受過控辯雙方的當面質證,或者是否曾經給過控辯雙方進行當面質證的機會。如果控辯雙方曾經有過這樣的機會,那么該書面證言可以采納作為定案的根據。最后,如果該證人在以前的訴訟程序中未接受過質證,那么舉證方應當就證言的可靠性提供證明,這種證明可以是基于常理或者邏輯,比如此證言屬于證人在臨終前的陳述或者違反證人自己的利益;也可以是基于對證人品行或者對陳述內容本身等情況的綜合判斷,但是不能以案內其他的證據來佐證。應允許對方就這種證明進行反駁。在聽取雙方意見的基礎上,法庭如果認為該書面證言可靠則可以采納其作為定案根據。但是該證言不能成為證明被告人有罪的唯一根據,即該證言如果屬于唯一的指控根據,則法庭必須排除其可采性。
三、證人保護制度
正如丹寧勛爵所說:“沒有一種法律制度有正當理由能強迫證人作證,而在發現證人作證受到侵害時又拒絕予以救濟。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來保護證人是法庭的職責。否則,整個法律訴訟就會一錢不值。”[注][英]丹寧勛爵:《法律的正當程序》,李克強等譯,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頁。完善的證人保護制度是打消證人作證時的畏懼心理,促使證人出庭作證的重要保障。從各國法律規定的證人保護具體措施來看,證人保護包括事前保護、事中保護和事后保護三種。事前保護包括為證人及其家屬提供貼身保護、提供隱蔽住所等等措施;事中保護包括利用網絡和視聽技術在庭審中對證人進行錄像詢問、改變證人的聲音和容貌等等措施;事后保護則包括改變證人的身份、遷居或者整容等等。與其它國家相比,我國的證人保護制度極其不完善。雖然我國舊《刑事訴訟法》第49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但由于缺乏具體而規范的保護措施,實踐中,證人因懼怕報復而不愿、不敢作證的情況比比皆是,這是造成我國證人出庭率低的一個重要原因。
雖然一直以來我國缺乏有關證人保護的專門法律規定,但在司法實踐中,一些公安司法機關基于辦理刑事案件的需要,也在探索證人保護的方式和措施問題。比如深圳市寶安區檢察院就制定了《自偵案件證人保護工作規定》,并成立了專門的證人保護小組,為職務犯罪案件中的證人提供偵查中、起訴中和起訴后的保護。[注]黃晟、李佳茹:《深圳寶安區檢察院首創證人保護制度》,《中國青年報》2005年6月21日。北京市石景山區法院則提出建立證人事前保護制度,即在刑事審判中,可建立證人詢問室(密問室),通過音頻系統完成證明內容、證人詢問等相關步驟,減少其與被告人或被害人正面接觸的機會。[注]季褚鴻:《“秘問室”是證人出庭的“軟著陸點”》,《新京報》2011年1月7日A04版。這些實踐中的探索雖然具有明顯的區域局限性,但卻為我國證人保護制度的立法完善提供了一定的經驗。本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在很大程度上填補了證人保護立法的空白。除了保留1997年刑事訴訟法第49條有關證人保護的原則性規定之外,新法第62條對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中的特殊證人保護問題進行了專門的規定。根據本條第1款規定,對于上述犯罪案件中的證人、鑒定人、被害人等“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采取以下一項或者多項保護措施:(一)不公開真實姓名、住址和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措施;(三)禁止特定的人員接觸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及其近親屬;(四)對人身和住宅采取專門性的保護措施;(五)其他必要的保護措施。”根據本條第2款的規定,“證人、鑒定人、被害人認為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請求予以保護。”根據本條第3款的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依法采取保護措施,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配合。”根據上述規定,新法所建立的特殊證人保護制度包括以下幾項內容:第一,證人保護的范圍限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和毒品犯罪等重大、復雜案件的證人、被害人、鑒定人或者其近親屬;第二,負責證人保護工作的機關是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但有關的單位或者個人應當予以配合;第三,保護措施可以是法律規定的其中一項,也可以同時采取多項措施;第四,證人有請求公安司法機關予以保護的權利。
新刑事訴訟法所確立的證人保護制度在我國具有開創性,對于確保重大、復雜案件的關鍵證人出庭作證,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和意義。但是從刑事訴訟活動的整體角度來看,上述規定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之處,有待于法律或者司法解釋予以進一步完善:第一,對證人的保護不應僅局限于幾類犯罪,而應擴大到所有需要保護的出庭證人。只有證人保護覆蓋的范圍足夠廣泛,才能徹底打消證人作證的顧慮,才能推動證人積極出庭作證。第二,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都負責證人保護工作,既容易引起這些機關之間互相推脫,也不利于證人保護的連貫性和有效性。應確定專門的證人保護機構,并確保該機構有足夠的經費和人員完成證人保護工作。第三,完善的證人保護措施應包括證人作證之后的事后措施,以確保證人及其近親屬不因作證而遭受犯罪分子的打擊報復,這是證人在履行作證義務的同時,應當享有的正當權利。第四,對證人的保護不應以犧牲被告人的正當程序權利為對價,不能以保護證人的名義剝奪被告人與關鍵的控方證人進行對質的權利。這樣一來,第62條第1款第1項所規定的“不公開證人的真實姓名、住址、單位等個人信息”就存在著以下兩個問題:其一,這種不公開是否包括對被告人甚至其辯護人都不公開?其二,這種不公開是否包括審判階段?如果這兩個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么這實際上就是在很多國家甚至國際刑事審判機構都存在廣泛爭議的“證人匿名作證”問題。對于匿名證人作證,很多國家持否定態度,包括審判最嚴重的國際犯罪的國際刑事法院都將證人身份的保密限制于審前階段(《羅馬規約》第68條第5款)。但也有的國家對此采取了容忍的態度,比如德國《刑事訴訟法》第68條第3款規定了“如果公開了證人的身份、住所或者居所就對證人或者其他人員的生命、身體或者自由造成危險之虞的,可以許可證人不對個人情況作出回答或者只是告訴以前的身份。”但這種隱匿是有限的,因為本款接著還規定了“但是在審判中證人應當說明他是以何種身份了解到他所提供的事實的”。同時本條第5款也規定了“必要時,對證人可以向涉及他在本案中的可信性的情節,特別是他與被指控人、受害人之間的關系發問”。這些規定說明,在德國為保護證人而允許隱匿其真實身份的措施,不得妨礙控辯雙方對該證言真實可信性的調查。有關證人匿名作證的問題目前在我國尚屬于新生事物,但隨著證人出庭的強化和證人保護的加強,這一問題勢必在我國越來越多地呈現。理論界應加強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以推動相應的法律規范早日出臺。
四、證人補償制度
給出庭作證的證人以適當的經濟補償和報酬,是世界各國的通例,包括美國、德國、日本、俄羅斯等國家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的法律都對證人補償制度進行了規定。根據這些國家的規定,證人補償的費用一般由國家來支付,補償的范圍主要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補償性的費用,如證人因作證而支付的交通費、住宿費、生活費等;另一部分則是因證人的作證行為而支付給他的報酬。我國1997年刑事訴訟法對于證人補償問題只字未提。實踐中,有地方的檢法機關嘗試建立證人補償制度,比如北京市西城區檢察院于2009年6月出臺了《刑事案件關鍵證人出庭作證及經濟補償工作辦法》,將補償出庭證人的做法機制化、規范化。[注]甘浩、傅沙沙:《北京關鍵證人出庭收獲補償》,光明網2009-12-11。但是有關證人補償的經費來源、范圍、補償標準等問題在我國并沒有統一的認識。
新刑事訴訟法首次明確了證人補償問題,根據法律第63條的規定,“證人因履行作證義務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應當給與補助。對證人作證的補助,列入司法機關業務經費,由同級政府財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單位的證人作證,所在單位不得克扣或者變相克扣其工資、獎金及其他福利待遇。”根據本條規定,我國證人補償制度的內容包括以下幾個部分:第一,證人補償的范圍包括證人因履行作證義務而實際支出的交通費、住宿費、就餐費等各種費用,不包括支付給證人的報酬;第二,證人補償的經費由司法機關從業務經費之中支出,由同級政府財政予以保障;第三,有工作單位的證人,其工資、獎金及其他福利待遇不因作證而受影響。上述有關證人補償的法律規定將會有利地推動我國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的貫徹落實。但筆者認為,為體現公平原則,鼓勵證人積極出庭作證,對于沒有工作單位的證人,可考慮給予其一定的報酬,具體數額可以參考本地區的平均日工資水平確定。同時,賦予出庭證人向司法機關請求支付相應的經濟補償和報酬的權利,對于司法機關無正當理由拒絕支付的,證人有權通過訴訟的方式進行追索。
五、警察出庭作證制度
在英美法系國家,基于傳聞證據規則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警察作為證人出席法庭接受控辯雙方的詢問和質證,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在大陸法系國家,雖然警察出庭作證不是一種普遍要求,但是有的國家也允許警察在某些情況下出庭作證,比如法國、德國、日本的法律都有相關的規定。[注]參見王超:《警察作證制度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112頁。從兩大法系有關的法律規定來看,警察出庭作證一般基于兩類情形:一類是警察就執行職務的過程中了解到的案件事實情況出庭作證。如果警察是在非執行職務的過程中目睹了案件事實的發生或者了解到與案件有關的事實,只能作為普通證人出庭作證。另一類則是警察就偵查行為比如訊問、搜查、扣押、鑒定等的合法性出庭作證,以解決控辯雙方就證據的可采性產生的爭議。
我國1997年刑事訴訟法并未就警察出庭的問題進行規定,相反,法律第28條還規定了擔任過本案證人的偵查人員應當回避,這就在警察和證人之間劃了一道涇渭分明的界限。1999年的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刑事訴訟規則》第343條規定:“公訴人對于搜查、勘驗、檢查等偵查活動中形成的筆錄存在爭議的,需要負責偵查的人員以及搜查、勘驗、檢察等活動的見證人出庭陳述有關情況的,可以建議合議庭通知其出庭”,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38條也有類似規定。上述司法解釋雖然要求偵查人員必要時出庭接受詢問,但實踐中偵查機關往往以一紙書面的情況說明書來應對。這一方面是因為這些司法解釋只具有部門規定的效力,難以對偵查人員產生強制力;另一方面則因為我國一直都缺乏明確而嚴格的傳聞證據規則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盡管警察作證問題在我國一直缺少法律上的依據,實踐中某些地方公安司法機關仍然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2006年10月1日,福建省廈門市湖里區法院、區檢察院、湖里公安分局聯合出臺《關于偵查人員出庭作證的若干實施意見》,對偵查人員出庭作證事項、程序作出了詳細規定。根據本意見,偵查人員可以就以下六項事實出席法庭進行說明并接受質證:(1)目擊的案件事實,偵查人員可以就其親眼所見的犯罪過程、現場情形等真實情況向法庭予以說明;(2)接案、破案、到案的經過,證實被告人是否存在自首、立功、未遂等量刑情節;(3)現場勘察、搜查、扣押、辨認等取證情況,證實該偵查是否合法、提取物是否原物等;(4)通過秘密偵查、誘惑偵查等特殊手段獲取的證據;(5)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對證據取得及偵查行為的合法性提出異議且有一定依據的;其他需要偵查人員出庭予以說明的。[注]梅賢明:《偵查人員能否出庭作證?》,《人民法院報》2007年12月23日。上述意見出臺之后在我國引起了廣泛的爭論。2010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國家安全部聯合發布了《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對于我國刑事訴訟中的警察作證問題進行了明確規定。根據本規定第7條,公訴人對被告人審前供述的合法性負有證明責任,必要時可以提請法庭通知訊問人員出庭作證,對取得的供述的合法性予以證明。經依法通知,訊問人員或者其他人員應當出庭作證。這一規定可以視為我國最高公安司法機關對實踐中的改革探索在一定程度上的認可,同時也為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改過程中解決警察出庭作證問題奠定了基礎。
新刑事訴訟法中涉及警察作證的條款主要體現在第57條和第187條第2款。根據第57條的規定,“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的過程中,人民檢察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現有證據材料不能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檢察院可以提請人民法院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有關偵查人員或其他人員也可以要求出庭說明情況。經人民法院通知,有關人員應當出庭。”顯然,本條規定是對《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的認可與繼承。根據第187條第2款的規定,人民警察就其執行職務時目擊的犯罪情況作為證人出庭作證適用第1款的規定。根據這兩個條文的規定,目前我國警察出庭作證制度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警察出庭作證的事項包括兩種:一是就證據的合法性問題出庭作證,二是就執行職務時目擊的犯罪情況出庭作證。第二,偵查人員就證據的合法性出庭既可以基于人民檢察院的提請和人民法院的決定,也可以基于偵查人員本人的要求。第三,警察就執行職務時目擊的犯罪情況出庭,需符合證人出庭作證的三個條件,即其證言對定罪量刑有重要影響,公訴人、當事人或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異議以及人民法院認為警察有必要出庭作證。新法關于警察出庭作證的規定,標志著我國正式建立起警察作證制度,從而在立法上結束了以往有關這個問題的諸多爭議和困惑。但從內容上來看,新法的規定仍然顯得過于粗疏,不僅警察出庭作證的范圍十分有限,而且未賦予被告人及其辯護人請求警察出庭的權利,同時對于警察拒絕出庭的后果也未提及。這些問題均有待于出臺進一步的法律或司法解釋予以解決和完善。
以上本文對新刑事訴訟法中有關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的修改進行了總結和歸納。從總體上來看,新法對我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均做出了回應,在體系上已經建構起一套較為全面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與舊法相比進步十分明顯。然而正如筆者在文中所分析的,目前這套制度仍不夠精細化,遺留了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希望隨著實際操作中這些問題逐漸顯現、逐一解決,早日推動我國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走向成熟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