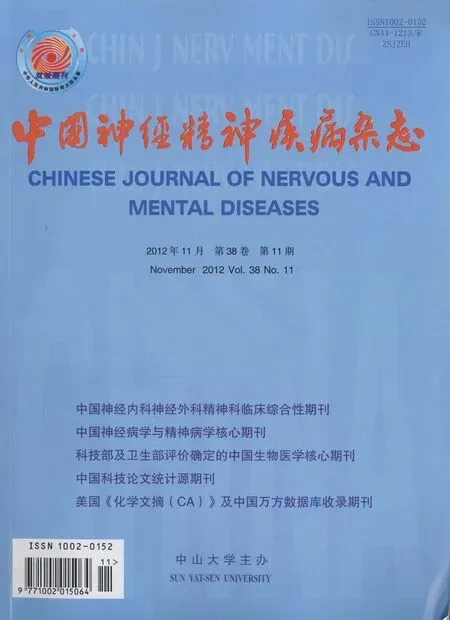難治性抑郁癥治療前后外周血白細胞Bcl-2 mRNA表達研究☆
抑郁癥是一種高患病率、高復發率、高致殘率、高自殺率以及高負擔的常見精神障礙。盡管經過正規的治療,大部分患者的病情能得到有效緩解,但仍有約20%~30%的患者成為難治性抑郁癥[1]。神經營養假說認為抑郁癥可能存在神經細胞的凋亡現象[2,3],而外周血 B 細胞淋巴瘤白血病-2 基因(B-cell lymphoma Leukemia-2,Bcl-2)Bcl-2 具有抑制凋亡的作用[4]。研究[5-7]顯示抑郁癥患者和應激動物模型的神經細胞和外周血淋巴細胞的Bcl-2基因表達下降,而經抗抑郁藥治療后,Bcl-2基因表達上升。那么難治性抑郁癥是否在神經凋亡的程度上有別于非難治性抑郁癥呢?盡管,已有一些研究[8-10]發現難治性抑郁癥的某些大腦環路功能和某些腦區的細微結構較非難治性抑郁癥變化更為明顯。但有關難治性抑郁癥Bcl-2基因表達的變化尚未見報道。本研究比較了難治性抑郁癥、非難治性抑郁癥和正常對照組之間外周血Bcl-2基因的表達水平,并觀察抗抑郁治療后Bcl-2基因表達的變化,以探討Bcl-2基因在難治性抑郁癥可能的發病機制和治療中的變化。
1 對象和方法
1.1 研究對象 為2006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就診于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上海市心理咨詢中心門診及住院的抑郁癥患者,包括治療前和治療后。入組標準:①符合國際疾病分類-10(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10)“抑郁發作”診斷標準;②年齡18~65歲,男女不限;③17項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17)評分≥17分;④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⑤有足夠的視聽水平以完成研究必需的檢查。排除標準:①目前為“抑郁發作”的雙相障礙患者;②妊娠或哺乳期婦女,或計劃妊娠者;③患有下列嚴重疾病:窄角型青光眼,癲癇,心肌梗塞,不穩定性心絞痛,充血性心衰,嚴重肝硬化,急慢性腎功能衰竭,嚴重糖尿病,再生障礙性貧血,中重度營養不良及其它嚴重神經、心、肝、腎、內分泌、血液系統等軀體疾病或可能干擾試驗評估的疾病;④物質依賴、器質性精神障礙及精神發育遲滯者;⑤曾出現嚴重過敏反應者。
其中治療前是指抑郁癥急性發作期,未經正規抗抑郁治療;治療后是指治療前患者入組后接受正規抗抑郁治療(包括SSRI類、SNRI類或NaSSA類)治療滿8周者;難治性抑郁癥是指抑郁癥患者入組前已經過至少2種作用機制不同的抗抑郁藥物足量(如米帕明≥150 mg/d)、足療程(6周)治療效果不佳(HAMD減分率≤50%)。
共收集抑郁癥患者49例,男23例,女26例,平均年齡(45.06±13.01)歲。其中難治性抑郁癥組23例,平均年齡(43.22±12.78)歲;非難治性抑郁癥組 26 例,平均年齡(46.69±13.24)歲。
健康對照組:來自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職工、研究生、進修醫師及上海市靜安區精神衛生中心及上海消防局職工。年齡18~65歲,漢族;HAMD17評分<7分;排除既往及訪談時存在的各類精神疾病、腦器質性疾病、較嚴重的心腦血管疾病及肝腎功能等重大疾病史、物質濫用等及精神疾病家族史。
健康對照組51例,男25例,女26例,平均年齡(39.19±12.54)歲。各組之間性別和年齡上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486,P>0.05;F =2.978,P>0.05)。
該研究通過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精神衛生中心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受試者均已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方法
1.2.1 臨床一般資料收集和評估 對所有入組患
者進行一般資料(包括年齡、性別、文化程度、職業、精神疾病家族史等)和發病情況(發病年齡、病程和復發次數等)調查,采用HAMD17評估抑郁發作的嚴重程度及癥狀特點以收集基線水平的數據。并在入組后半年到一年隨訪,以剔除雙相障礙。對51例健康對照進行一般資料調查,采用一般心理健康調查問卷(GHQ)、抑郁問卷(CES-D)調查排除抑郁癥等精神疾病及嚴重軀體疾病,并收集一般資料包括年齡、性別、文化程度等。
1.2.2 cDNA的提取和轉錄 提取外周血 1 mL,EDTA抗凝,離心分離白細胞,TrizoL處理白細胞,氯仿/異戊醇抽提RNA,并用異戊醇離心沉淀得到RNA,75%乙醇洗滌后溶于40 μL DEPC水中。用Dnase I酶處理RNA,然后用氯仿、異戊醇、70%乙醇再次抽提RNA,并溶解于30 μL Rnase free水中。使用逆轉錄試劑盒(Qiagen,Chatsworth CA)和隨機引物合成cDNA備用。
1.2.3 TaqMan熒光實時定量 PCR 采用 TaqMan MGB探針法在384孔ABI Prism 7900序列檢測系統(Applied Biosystems,CA,USA)上進行熒光實時定量PCR擴增,分析目的基因的表達水平。以管家基因GAPDH(glyceraldehyde-3-phosphate dehydrogenase,購于 Applied Biosystems,CA,USA)作為內對照基因來標化目的基因的表達水平。將51例正常對照的cDNA混合作為標準品,在每個384孔反應板上均測定此標準品的目的基因和內對照基因的表達曲線以作為待測樣本的基因表達量的參照。每個待測樣本的目的基因和內對照GAPDH基因均重復3次。同時分別設立3個陰性對照孔。TaqMan熒光實時定量PCR擴增的反應體系均根據美國ABI公司提供的推薦方案。
1.2.4 比較 Ct值法 采用比較 Ct值的方法[11(Comparative Ct Method)進行相對定量,用SDS version 2.0軟件(Applied Biosystems)進行數據采集。熒光定量PCR的結果以Ct值顯示,Ct值為每個反應管內的熒光信號到達設定的預值時所經歷]的循環數,Ct值越大,表達量越低。平均△Ct為樣本目標基因平均Ct值減去內對照GAPDH平均Ct值。用健康對照組的平均ΔCt值為標準(calibrator)計算出每個患者組的 2-ΔΔCt(每個患者組的 ΔΔCt=每個患者組的平均ΔCt-正常組平均ΔCt),來計算表達差異的倍數。以每個樣本2-ΔΔCt代表目的基因的表達水平。
1.3 統計學方法 使用SPSS 16.0進行統計分析。通過t檢驗和方差分析比較組間基因表達差異的顯著性水平。3組樣本的性別和年齡的比較采用卡方和方差分析;三組樣本的Bcl-2基因的表達量比較采用方差分析,并采用Games Howel進行兩兩比較;治療前后的Bcl-2基因表達量的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與臨床特征的相關性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檢驗水準 α =0.05,雙側檢驗。
2 結果
2.1 各組外周血白細胞Bcl-2基因的表達量 治療前抑郁癥組患者外周血白細胞Bcl-2基因表達量低于正常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差異(t=-4.438,P<0.01)。TRD 組、非 TRD 組和正常對照組外周血白細胞Bcl-2基因表達水平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F=11.468,P<0.001),兩個患者亞組均低于對照組,TRD組又低于非TRD組,見表1。
2.2 各組治療后外周血白細胞Bcl-2基因的表達量 抑郁癥患者組治療后Bcl-2基因表達量較治療前上升(t=-2.040,P =0.047)。分組分析顯示,TRD組治療后Bcl-2基因表達量較治療前上升(t=-2.090,P =0.048),而非難治性抑郁癥組治療后基因表達量上升無統計學差異(t=-1.116,P=0.275)。詳見表 1。
2.3 各臨床指標與Bcl-2基因表達量的相關性分析
抑郁癥組患者經抗抑郁治療后,HAMD17量表平均減分率為71.45%,其中TRD組HAMD17量表平均減分率為62.23%,非TRD組HAMD量表平均減分率為82.97%。抑郁癥組治療前Bcl-2基因表達量與 HAMD17(r=-0.174,P=0.310)、HAMA 總分(r=-0.047,P=0.781)、起病年齡(r=0.177,P =0.302)、病程(r=-0.147,P =0.515)無顯著相關性。治療前后Bcl-2基因表達量的變化與HAMD17總分減分率之間無顯著相關性(r=0.072,P =0.677)。

表1 抑郁癥組與對照組Bcl-2表達量
3 討論
神經營養假說認為神經網絡的可塑性改變可能是抑郁癥病因機制之一,抗抑郁治療通過調控與神經可塑性相關的信號轉導和基因而起到抗抑郁的療效。應激會導致與認知和情緒相關的某些腦區的神經細胞出現萎縮,雖然神經細胞具有可塑性和神經再生功能,但慢性刺激或嚴重的刺激將可能導致細胞凋亡。
Bcl-2基因是最早從濾泡性B細胞淋巴瘤細胞染色體上發現的,能在各種不同的正常組織和細胞的激活過程中表達。Bcl-2基因及其表達蛋白的作用在于普遍保護細胞免受多種刺激誘導的凋亡,阻止不同刺激引起的凋亡,維持細胞存活,稱其為凋亡抑制因子。因此,Bcl-2的抗凋亡作用很可能是凋亡過程的最后共同途徑。除了抗凋亡作用,Bcl-2因具有加強細胞內鈣通道活性、激活CREB-ERK通路等作用而促進神經突觸和軸突的形成和再生[4]。
有關應激動物和抑郁癥患者Bcl-2表達研究中,大部分研究[4-6]結果顯示抑郁癥動物模型應激動物的大腦某些區域,如海馬、邊緣葉,Bcl-2基因表達和蛋白表達量下降,但也有部分研究[12,13]得出截然相反的結果,這些研究發現實驗動物應激后海馬部位Bcl-2含量上升,抑郁癥患者外周白細胞Bcl-2蛋白含量上升。Bravo等[13]認為應激后Bcl-2表達量上升,可能與慢性應激后激活了抗凋亡的機制有關。由此說明,應激后或抑郁癥患者Bcl-2表達量出現不升反降的現象,提示抗凋亡功能的抑制。本研究結果提示抑郁癥患者外周血Bcl-2基因表達水平下降,而難治性抑郁癥患者下降更為明顯,說明抑郁癥患者外周血淋巴細胞抗凋亡能力下降、神經突觸形成和再生能力的下降,且難治性抑郁癥患者的抗凋亡能力和神經再生能力下降更為明顯。有關難治性抑郁癥具有更突出的神經系統損傷,同樣被其他的研究驗證,如一些研究[8,9,14]發現難治性抑郁癥患者,大腦的某些環路功能、海馬部位細微結構變化等更為明顯,甚至某些基因的的多態性可能成為預測抑郁癥患者是否難治的早期預測指標。
有關抗抑郁治療對于Bcl-2的作用,大部分研究[6,15,16]結果顯示,抗抑郁藥(如嗎氯貝胺、丙咪嗪、文拉法辛、氟西汀、西酞普蘭等)均能提高Bcl-2的表達量。本研究中,抑郁癥患者經過抗抑郁治療8周后,其外周血白細胞Bcl-2基因表達量上升。雖然,本研究和國內外多項研究都證實抗抑郁藥物的治療對Bcl-2的表達有上調作用,但這種作用的實際臨床意義卻并不明確。有研究發現抗抑郁藥治療后,其海馬Bcl-2蛋白的上升與BDNF的上升呈平行關系,并受ERK1/2信號通路的磷酸化調節。因此,本研究發現抗抑郁治療后患者Bcl-2表達上升,間接說明了臨床上常用的抗抑郁藥可能具有激活和改善抗凋亡能力、促進神經再生的作用,并提示抗凋亡和促進神經再生可能是抗抑郁作用的機制之一。
然而,本研究中根據患者是否難治進一步分組分析后,發現只有難治性抑郁癥患者經抗抑郁治療后Bcl-2表達上升明顯,非難治性抑郁癥治療后Bcl-2表達上升不明顯。說明,難治性抑郁癥患者在急性期治療期間,其抗凋亡能力已經得到一定修復,而非難治性抑郁癥患者在治療初期抗凋亡能力修復不明顯。回顧本研究入組的難治性抑郁癥和非難治性抑郁癥患者的治療效果,其HAMD17減分率分別為 62.23%和 82.97%,即大部分難治性患者經本次治療得到明顯的改善,但總體療效低于非難治性抑郁癥患者。說明外周血Bcl-2基因表達水平的上升并不與HAMD17減分率呈平行關系。
本研究中,非難治性抑郁癥患者雖經抗抑郁治療后,抑郁癥狀得到明顯改善,但神經系統的修復尚需更長的時間,這可能正是抑郁癥的維持和鞏固治療的神經病理機制之一。而本研究中難治性抑郁癥患者經8周抗抑郁治療后,Bcl-2基因表達上升較非難治組明顯。在Reus等研究[16]中發現氟西汀和奧氮平聯合治療比單一藥物治療改善中樞神經系統細胞活性更為顯著。因此,筆者認為本研究中難治性抑郁癥患者急性期治療后外周血Bcl-2基因表達量上升明顯,這可能是本研究中難治性抑郁癥患者在藥物選擇上多集中于雙通道抗抑郁藥或多藥聯合治療,可能更快的促進神經系統再生和修復的功能。
此外,在本課題組既往的研究[18]中,同樣發現了亞綜合征抑郁的患者外周血Bcl-2基因表達下降,說明抑郁患者在疾病早期就存在抗凋亡的抑制。同樣,本研究中發現Bcl-2基因的表達水平與臨床特征(包括病程、發病年齡、HAMD17總分、HAMA總分及治療前后HAMD17減分率等)進行相關分析,發現Bcl-2基因的表達水平與這些臨床特征無顯著相關性。說明外周血Bcl-2基因表達量與疾病的長短、嚴重程度等可能不存在直接的關系,抑郁患者Bcl-2基因表達量早在疾病早期或疾病輕度狀態時就已經出現。從本研究結果來看,外周血Bcl-2基因表達量的變化與HAMD17減分率并無明顯相關性,可能是抗抑郁治療后外周血相關生物學指標的變化存在時間滯后性。在一項研究注射鹽酸氯胺酮快速治療難治性抑郁癥的研究中[18],發現鹽酸氯胺酮快速治療難治性抑郁癥后,抑郁癥狀在短時間內得到了改善,但外周血BDNF的量并未見相應的上升。
本研究探究的是外周血Bcl-2基因的表達水平,雖然不能完全代表中樞Bcl-2基因表達的真正水平,但在中樞組織取材困難的形勢下,外周血基因表達水平的變化在某種程度上與中樞相關基因表達呈正相關。此外,較之采用腦組織的動物模型和尸腦組織研究,外周血的研究更能體現患者活體的真實狀況,并且更易于研究成果向臨床應用轉化。
本研究在設計上,尚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改進之處。首先,本研究入組病例在治療藥物的選擇上采用開放式選擇,對臨床藥物選擇上并未做嚴格的規定,而只是相對統一在SSRI和SNRI類藥物的治療,不利于進一步分析具體藥物與Bcl-2基因表達的關系。其次,本研究樣本量較少,很難從臨床特征和治療藥物上做更多的分型和分析。第三,藥物治療激活抗凋亡機制的過程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而本研究中患者組治療觀察時間僅為6~8周。在將來的研究中,如果能在以上的不足進行彌補,將有助于更好地探究外周血白細胞Bcl-2基因表達水平與抑郁癥的關系。總之,本研究結果發現難治性抑郁癥患者外周血Bcl-2基因表達量低于非難治性抑郁癥和正常人,難治性抑郁癥經急性期抗抑郁治療后能提高Bcl-2基因的表達水平。說明難治性抑郁癥患者外周血淋巴細胞抗凋亡能力嚴重受損,而抗抑郁治療能改善抗凋亡的功能。
[1]朱紫青,季建林,肖世貴主編.抑郁障礙治療關鍵[M].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142-143.
[2]Drzyzga LR,Marcinowska A,Obuchowicz E.Antiapoptotic and neurotrophic effects of antidepressants:a review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studies[J].Brain Res Bull,2009,79(5):248-257.
[3]江文慶,杜亞松.抑郁癥病理生理機制的神經可塑性假說[J].上海精神醫學,2006,18(2):117-119.
[4]Jiao J,Huang X,Feit-Leithman RA,et al.Bcl-2 enhances Ca(2+)signaling to support the intrinsic regenerative capacity of CNS axons[J].EMBO J,2005,24(5):1068-1078.
[5]Kosten TA,Galloway MP,Duman RS,et al.Repeated unpredictable stress and antidepressants differentially regulate expression of the bcl-2 family of apoptotic genes in rat cortical,hippocampal,and limbic brain structures[J].Neuropsychopharmacology,2008,33(7):1545-1558.
[6]Kubera M,Obuchowicz E,Goehler L,et al.In animal models,psychosocial stress-induced(neuro)inflammation,apoptosis and reduced neurogenesis are associated to the onset of depression [J]. Prog Neuropsychopharmacol Biol Psychiatry,2011,35(3):744-759.
[7]Szuster-Ciesielska A,Slotwinska M,Stachura A,et al.Accel-erated apoptosis of blood leukocytes and oxidative stress in blood of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on [J]. Prog Neuropsychopharmacol Biol Psychiatry,2008,32(3):686-694.
[8]Guo WB,Liu F,Xue ZM,et al.Alterations of the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s in treatment-resistant and treatment-response depression: A resting-state fMRI study[J].Prog Neuropsychopharmacol Biol Psychiatry,2012,37(1):153-160.
[9]Guo WB,Sun XL,Liu L,et al.Disrupted regional homogeneity in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a resting-state fMRI study[J].Prog Neuropsychopharmacol Biol Psychiatry,2011,35(5):1297-1302.
[10]Murray F,Hutson PH.Hippocampal Bcl-2 expression is selectively increased following chronic but not acute treatment with antidepressants,5-HT(1A)or 5-HT(2C/2B)receptor antagonists[J].Eur J Pharmacol,2007,569(1-2):41-47.
[11]Livak KJ,Schmittgen TD.Analysis of relative gene expression data using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and the 2(-Delta Delta C(T))Method[J].Methods,2001,25(4):402-408.
[12]Djordjevic A,Djordjevic J,Elakovic I,et al.Fluoxetine affects hippocampal plasticity,apoptosis and depressive-like behavior of chronically isolated rats[J].Prog Neuropsychopharmacol Biol Psychiatry,2012,36(1):92-100.
[13]Bravo JA,Diaz-Veliz G,Mora S,et al.Desipramine prevents stress-induced changes in depressive-like behavior and hippocampal markers of neuroprotection [J].Behav Pharmacol,2009,20(3):273-285.
[14]Zhou Y,Qin LD,Chen J,et al.Brain micro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revealed by diffusion tensor images in patients with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 compared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before treatment [J].Eur J Radiol,2011,80(2):450-454.
[15]Xu H,Steven Richardson J,Li XM.Dose-related effects of chronic antidepressants on neuroprotective proteins BDNF,Bcl-2 and Cu/Zn-SOD in rat hippocampus[J].Neuropsychopharmacology,2003,28(1):53-62.
[16]Reus GZ,Abelaira HM,Agostinho FR,et al.The administration of olanzapine and fluoxetine has synergistic effects on intracellular survival pathways in the rat brain [J]. J Psychiatr Res,2012,46(8):1029-1035.
[17]李則摯,張晨,洪武,等.亞綜合征抑郁B細胞淋巴瘤白血病-2基因表達研究[J].中國神經精神疾病雜志,2011,37(5):307-309.
[18]Machado-Vieira R,Yuan P,Brutsche N,et al.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and initial antidepressant response to an N-methyl-D-aspartate antagonist[J].J Clin Psychiatry,2009,70(12):1662-1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