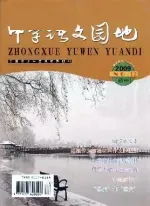從兩種文化的碰撞看土司制度的衰亡
——讀阿來的《塵埃落定》
2011-08-15 00:49:31劉治軍
中學語文
2011年21期
劉治軍
一、傻子——兩種文化碰撞的產物
“這本書寫的是一個土司家族的衰落史”,也即是一種區域文化,特定藏文化在外來漢文化的漫性沖擊下裂變并逐步同化的過程。小說的主人公非常特別,是由一系列矛盾因素組成的傳奇人物“我”——一個傻子。
首先,“當一種沒有強大物質力量保障的文明或文化面對另一種強大的外來文明或文化的突然侵襲時,木然表現出一種愚鈍的、木訥的狀態”。嬰粟、槍炮、妓女、梅毒,這些外來文化屬性的種子在傳統的土司文化中生根、發芽并茁壯成長。傳統的土司文化或文明被不自覺地注入了一定意義上的“新鮮”,土司文化和文明被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因此麥其家族在外來文化和文明的沖擊下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曇花一現式的昌盛。但這種昌盛在類似“聰穎”的外來漢文化面前,類似“愚鈍”的土司傳統文明和文化的活力程度二者之間的落差清晰可見,而傻子便是這種落差形象化的反映,因此,傻子看起來確實有點“傻”。
其次,在麥其家族所有人的眼中,他有一種天生的智力障礙。而麥其土司同父異母的大兒子并不傻,因而可以看出麥其土司與漢族女人的結合象征著土司文明和文化與外來文明和文化的對話,而這兩種文化的碰撞,本族文化受震蕩,表現出一種“愚鈍”的狀態。因此,傻子是有著豐富寓意的喻體,是在特定文化狀態下的具體物化。
第三,傻子見證了土司制度的興衰,同時他又是阿來精心塑造的人物形象。……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湖北教育·綜合資訊(2022年4期)2022-05-06 22:54:06
金橋(2022年2期)2022-03-02 05:42:50
銀潮(2021年8期)2021-09-10 09:05:58
農村百事通(2020年11期)2020-06-27 14:05:13
遼金歷史與考古(2019年0期)2020-01-06 07:44:44
小天使·一年級語數英綜合(2018年9期)2018-10-16 06:30:16
作文周刊·小學一年級版(2016年42期)2017-06-06 22:20:27
中國衛生(2016年7期)2016-11-13 01:06:26
中國衛生(2016年11期)2016-11-12 13:29:18
中國衛生(2016年9期)2016-11-12 13:2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