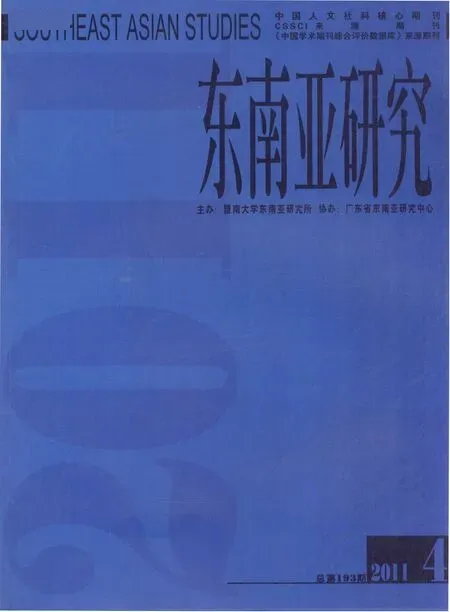非傳統安全與中國—東南亞國家的安全關系——以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水資源開發問題為例
潘一寧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廣州 510275)
非傳統安全與中國—東南亞國家的安全關系
——以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水資源開發問題為例
潘一寧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廣州 510275)
非傳統安全;中國—東南亞國家關系;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安全化
本文論述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水資源的開發既有利于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安全,但又會引發利益沖突,這一問題的“安全化”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安全化”是各方利益相互博弈以達成妥協的過程,也是一種合作安全的社會建構過程。通過“安全化”,在橫向關系上,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的國家彼此間展開利益的討價還價而逐漸達成妥協與合作;在縱向關系上,社會群體和個人的權益得到國家的關注。但本文也同時指出,非傳統安全問題如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的水資源開發爭端最終走向“去安全化”也是一個必不可少的過程,它與“安全化”過程構成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問題的提出
進入21世紀,“非傳統安全”(Non Traditional Security,NTS)已成為國際社會的熱門議題。一方面,它是學術界對“安全”這個國際關系核心概念在理論層面上不斷擴大和深入認識的結果,另一方面,它反映了冷戰后國際社會和國家政府對政治和軍事之外安全因素的日益關注。非傳統安全的概念寬泛,涵蓋經濟、社會、文化、人口、環境等方面的各種安全問題,它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在內容、主體、手段及理念方面都體現多元化,國家不再是安全的唯一行為主體和安全指涉對象,軍事威脅也不再是挑戰安全的唯一根源。
在冷戰后的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安全關系中,軍事威脅可以說不是一個主要的問題或緊急事態。除了在南海爭端上隱存著某種軍事沖突的潛在危險外,層出不窮的、影響深遠的“存在性威脅”更多是非傳統安全問題,如非法移民、跨國販毒、走私武器、海盜劫持商船、恐怖主義威脅、病毒傳染、自然環境污染、水資源爭奪等等。這些非傳統安全危險與軍事安全問題最大的不同是,其存在實際上較有利于或者說更能促進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協商合作,而非敵意對抗。2002年以來,中國和東南亞國家在抗擊非典、反恐、禁毒、打擊國際經濟犯罪等非傳統安全領域中都進行了積極有效的對話合作[1]。因此在一定意義上,以“合作安全”來表述當前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安全關系是適宜的。
然而,非傳統安全問題由于在形式和內容上多樣而復雜,對不同國家的安全威脅也存在時間或程度上的差異,因此各國政府往往對這些問題并不敏感,不容易給予足夠的重視,以致國際安全合作不一定會自動實現。學者們常常指出,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在非傳統安全方面的合作頗為滯后,主要表現為合作渠道的不暢通和合作機制的缺失或失靈。結果,使得本來可以成為促進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廣泛合作的催化條件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卻有可能會變為損害雙方友好關系的因素。瀾滄江—湄公河水資源開發問題便是一個典型的事例。
關于瀾滄江—湄公河水資源開發對次區域安全的影響,西方學者和媒體自20世紀90年代末就予以了極大的關注,但以批評和指責中國為主,大有挑撥中國和東南亞國家關系的意味①如:D.Blake,“Proposed Mekong Dam Scheme in China Threatens Millions in Downstream Countries”,World River Review,June 2001;J.Borton,“Mother of Rivers:China's Dams Pose Threat to Way of Life for Nations Downstream”,Washington Times,6 September,2002 等。。新加坡學者伊芙琳·吳 (Evelyn Goh)在2004和2005年也曾分別發表了兩篇相關論文,其研究比西方學者較具客觀性和學術性。其中最有價值的觀點是,她指出了非傳統安全問題“安全化”的多層次過程,并認為綜合安全、人的安全和經濟安全三種安全概念的結合運用,可能更有助于理解和解釋東亞國家的生態安全問題②見 Evelyn Goh,“The Hydro-Politics of the Mekong River Basin: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in R.Thakur and E.Newman eds.,Broadening Asia's Security Discourse and Agenda ,Tokyo: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2004;Evelyn Goh,“China in the Mekong River Basin:the Reg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Resource Development on the Lancang Jiang”,in Mely Caballero-Anthony et al.eds.,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n Asia:Dilemmas in Securitization,England: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6。。到目前為止,國內學術界研究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開發與合作的論文至少有上百篇,但從非傳統安全角度探討這一問題的研究屈指可數③相關的兩篇論文是:黎爾平:《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政治信任度研究》,《東南亞研究》2006年第5期;黎爾平:《非傳統安全視角下云南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研究》,《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尚屬欠缺。
本文擬論述在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的經濟發展中,水資源開發和利用既有利于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安全,但又會引發利益矛盾和沖突,這一問題的“安全化”(securitization)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安全化”是各方利益相互博弈以達成妥協的過程,也是一種合作安全的社會建構過程。通過“安全化”,在橫向關系上,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各國彼此之間可以展開利益的討價還價而逐漸達成妥協與合作;在縱向關系上,社會群體和個人的權益可以得到國家的關注。但同時,本文贊同巴瑞·布贊和奧利·維夫 (Ole Waever)等學者的觀點,即安全問題并非越多越好,“安全應當被視為消極的,是作為常規政治處理問題的一種失敗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非安全化 (desecuritization)是長期的最優選擇,因為它意味著,不把問題說成是‘我們要加以反制的威脅’,而是將問題從威脅—防衛這種序列中剔除掉,使之進入普通的公共領域中。”[2]因此,非傳統安全問題如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的水資源開發爭端最終走向“去安全化”(“非安全化”)應當是一個必不可少的過程,它與“安全化”過程構成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一 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的經濟發展與合作安全
很多國外學者提到中國開發瀾滄江水資源時,都在不同程度上持不客觀、欠公允的態度,往往片面強調中國的經濟發展給周邊國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而對中國促進瀾滄江—湄公河流域的綜合性開發以推動次區域國際合作并實現各國共同繁榮的善意和努力視而不見。有鑒于此,筆者認為有必要首先在此指出,中國在瀾滄江的水資源開發總體上是有利于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國家之間的合作安全的。
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也稱大湄公河次區域(Greater Mekong Sub-region,GMS),特指瀾滄江—湄公河流域經濟區,包括了中國 (云南和廣西)和五個東南亞國家——緬甸、老撾、泰國、柬埔寨和越南。該地區最重要的特點是大部分國家或地區都屬經濟欠發達地區,大多數居民都處于貧困落后的生活狀態,由此又滋長了不少危害社會穩定的因素,如毒品生產和跨國販賣、軍火走私、非法移民等。因此,發展地區經濟以改善民生和穩定社會秩序無疑是該區域各國政府的首要任務和追求目標。
早在20世紀50年代,湄公河地區四國——泰、越、老、柬就成立了“湄公河協調委員會”(Mekong Committee),試圖在水資源共同開發和利用方面進行合作。但國際冷戰導致這些國家相互間發生對抗,因此直到90年代冷戰結束后,在亞洲開發銀行 (簡稱亞行)的促進之下,湄公河流域國家才再度啟動了經濟合作發展計劃,擬在交通、能源、環境保護、人力資源開發、貿易與投資、旅游和通訊等多方面進行廣泛的國際合作。中國自1994年開始重視大湄公河流域的經濟合作發展,到2000年前后,已積極而全面地參與了該區域的經濟合作發展規劃、投資及建設,并發揮重要的推動作用。目前,在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的合作發展中,已形成了多樣的、復合型的國家合作機制[3]。其中最重要的是,亞行組織的領導人會議、部長級會議及高官會議的三層次論壇、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下的部長級會議以及以湄公河委員會 (Mekong River Commission,MRC)為主導的部長級會議。經過各方十余年的努力,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的經濟合作發展取得了引人矚目的實際成效。很多論文對此已作論述,本文不再贅言。
本文要強調的是,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在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的經濟合作發展有三點值得注意:
第一,中國參與和推動次區域經濟合作發展具有善意,體現中國的綜合安全觀。2000年以來,中國在國家和地方 (云南和廣西)層次上所制定的經濟發展戰略規劃都表明了雙重目標:一是推進中國西部地區大發展,二是加強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間的合作關系。就后者而言,中國方面是從地區戰略安全利益角度考慮來參與次區域的經濟合作發展的,并且將這一行動視為對東南亞國家“睦鄰、富鄰、安鄰”外交的具體實踐,視為最終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關鍵,因而十分注重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間在經濟合作發展中平等、互信、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則。
第二,瀾滄江—湄公河的水資源開發和利用是次區域經濟合作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在瀾滄江的水資源開發計劃是符合次區域經濟發展規劃和合作框架協議的。在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的水資源開發和利用中,水電能源的發展是重心。不僅是中國云南,老撾、緬甸、柬埔寨和越南都紛紛制定了大規模修建水電設施的宏偉計劃,各國都希望以此促進國家農業、林業和工業的迅速發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消除貧困。與此同時,在大壩、水電廠、電網的建設以及水電利用和貿易方面,中國與次區域的東南亞國家都已建立起雙邊合作建設與互惠共享的關系。因此,如果孤立地看待和評價中國在瀾滄江進行水資源開發和利用的問題,那將導向片面的結論。
第三,通過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的經濟合作發展,次區域的經濟增長明顯加快,已展現出該地區國際合作發展的活力和光明前景,迄今為止所取得的成就對改善民生,加強各族團結,推動社會進步,穩定地區秩序,促進中國與鄰國的經濟一體化已起了積極的作用,進而又有利于增進中國與次區域東南亞國家之間的協調與合作,彼此間的相互信任,使雙方穩定地邁向“戰略聯盟和伙伴關系”。對這種合作安全,中國的重大作用與貢獻是毋庸置疑的。同時應該看到,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在次區域的合作安全機制已逐漸形成,盡管很不完善,但并不缺失。這種合作機制以經濟為中心,涉及政治、社會、文化、人口、環境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各方面協調合作。
二 瀾滄江—湄公河水資源開發問題的“安全化”
瀾滄江—湄公河的水資源開發和利用顯然不是完美的。在此過程中,突現了兩大問題:一是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二是各方利益的矛盾。這兩方面問題在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項目中往往是比較容易忽略的。相較于第一個問題,政府更關注開發和利用的經濟效益;至于第二個問題,政府的綜合安全戰略盡管考慮到保障個人、集體和國家不同層次的安全利益以及國家與國家間的利益分配,但在實施中總有“重國家層次的利益而輕個人和集體利益”以及“重自我國家利益而輕他國利益”之傾向。瀾滄江—湄公河水資源開發問題的“安全化”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和發展的。
冷戰后,各國政府普遍接受新安全觀,這是非傳統安全問題得以“安全化”的前提。“新安全”意味著國家之外的集體和個體都可以成為安全指涉對象 (security referent objects),超越政治和軍事領域的問題都可以成為安全事務 (security issues)。“安全化”是指公共問題高度政治化,被國家視為“存在性威脅” (existential threat),需要動用國家資源、采取緊急措施 (包括軍事行動)予以制止[4]。筆者認為,“安全化”的重要性不在于某一公共問題最終被成功地定義為國家安全事務或國際安全事務,而在于這一公共問題政治化的過程,包括兩個層面:其一,相關利益者相互博弈而達成妥協的互動;其二,各利益方通過“表達意見”或“制造安全”而達到集體認同的言語—行為(speech act)建構。因此,我們應看到,瀾滄江—湄公河水資源開發問題的“安全化”實際上有其必要性,它是次區域各國之內和之間的利益分配調整過程,也是中國與次區域東南亞國家間合作安全的社會建構過程。
電力關系到國家經濟的持續發展和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因而能否持續不斷地提供廉價而清潔的電力能源成為國家經濟開發規劃中的一個重點。瀾滄江—湄公河擁有極其豐富的水能儲量,根據中國學者的估算,理論上蘊藏有約9萬多兆瓦 (MW)水力資源,其中可開發的水能是6萬多兆瓦,且干流的地形地質條件優越,利于開發,但次區域各國普遍的水能開發利用率卻不到6%[5]。近年來,沿岸國家或地方政府 (主要是上游國家)都制定了宏偉的建筑水壩、電站和輸電網計劃,旨在充分利用瀾滄江—湄公河的水電資源。不僅于此,中國方面還希望通過水力開發的整體規劃建設,能夠有效地調控水流量以減輕旱澇災害,并促進農業水利灌溉設施的完善,提高河流的航運能力。在中國政府看來,這是一個具有巨大社會經濟效益、功在千秋的綜合安全工程。
然而,水力工程建設對生態環境具有正負兩方面的后果。對于非政府環保組織來說,大規模建筑水壩更多的是危害生態系統。環保人士認為,建壩過程中的森林砍伐、水土流失、河道淤積、河水污染、生物多樣性減少、濕地生態系統退化等等對整個流域的生態環境造成最嚴重的威脅。因此,這一群體運用公布研究報告、在公眾媒體發表文章、向政府游說等方式,首先將建壩問題作為對生態安全的“存在性威脅”提到了政府的安全議程上來,甚至掀起了反壩運動。換言之,環保群體通過生態安全的言語—行為觸發了水資源開發問題的政治化或“安全化”的進程。
與此同時,水力工程建設也對個體利益產生一定的不利影響。利益攸關者主要是沿岸的漁民、農民以及因建壩而搬遷的山民,代表這些個體利益的民間團體或一些非政府人權組織通常以請愿、游行、靜坐、制造輿論等方式來表達意見,提出:建壩導致漁民的捕魚量減少而生計困難,農民原有的部分土地被剝奪,移民由于長期休養生息的環境被改變而難以適應和生存,政府的經濟補償或安置費不足,建壩地區的居民并沒有分享到水電發展的紅利,生活沒有得到明顯改善等等。他們要求政府從人的安全 (human security)角度來考慮那些深受建壩影響的人群的利益。
生態安全議題和人的安全議題的提出,促使政府作為水資源開發工程的主要負責者以及作為一個國家的主要安全行為主體,不能不在修壩問題“安全化”過程中顧及到個體、社會和國家利益的合理分配,這實際上有利于完善政府的綜合安全觀和國家綜合發展戰略。
水力工程建設也引起上下游國家之間的一些利益矛盾和沖突。從戰略安全角度來說,下游國家深切擔憂上游國家對徑流水量進行控制,以至將下游國家置于一種不安全狀態。從生態環境和經濟利益考慮,下游國家懷疑上游國家的建壩工程會破壞生態環境并造成下游國家漁業和農業的損失,對人民的生命財產構成威脅。從企業的利益來看,上游國家之間在水電貿易方面可能會產生電價競爭,而弱小國家的企業擔心其處于不利的競爭地位。使問題更復雜的是,這些矛盾和沖突中又往往隱含了大小國不對稱的相互依存關系,即次區域東南亞中小國家對中國“強勢”的疑慮。中國不僅是綜合實力意義上的大國,而且在瀾滄江—湄公河的地理位置中占據了上游的優勢。因此,在上下游國家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中,突出的現象表現為次區域國家常常把問題責任的矛頭指向中國。
2000年湄公河地區發生嚴重洪澇,致使下游國家的人員和財產遭受很大損失,于是,對中國在上游建壩的質疑和抱怨開始此起彼伏。2010年整個瀾滄江—湄公河流域又發生了百年一遇的大旱,下游國家的一些非政府組織和媒體對中國瀾滄江水電開發的指責更是甚囂塵上,認為上游大壩建設不但不能有效地調控水流量,反而加重了下游國家的旱澇災害。這一問題成為了2010年4月初在泰國華欣召開的首屆湄公河委員會峰會的一個關注焦點以及中國與湄公河下游四國對話的重要議題。湄公河委員會峰會的實質正是下游國家敦促上游國家對它們的利益和疑慮給予更大的關切。
次區域外的一些大國如美國、日本和印度也十分重視瀾滄江—湄公河流域的戰略意義和經濟發展,并通過亞行、世界銀行或其他各種區域組織不同程度地參與了大湄公河的合作開發,成為該區域的利益相關國或利益關切國。在經濟合作過程中,這些國家頗為強調生態安全與人的安全理念,同時還非常警惕中國在該區域中的戰略安全主導地位和作用。因此,它們力圖對次區域國家的經濟發展以及合作安全關系施加影響。在中國筑壩問題上,這些國家以多種形式表示支持湄公河下游國家的看法,反對中國的大規模水力工程建設計劃。
次區域內外國家間的利益博弈,甚至權力斗爭,使瀾滄江—湄公河的水資源開發問題更加政治化,加重了安全的話語。但我們可以看到,通過對這一“存在性威脅”的爭論,國際關系中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得以引起各國政府的重視,國家安全領域和安全利益得以重新界定,地區合作安全的內涵得以深化。具體而言,各國政府在考慮確保自身國家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同時,不能不注意跟其他國家進行公平合理的資源和收益分配,不能不注意維護人類社會共同的生存環境。同樣重要的是,“共同利益困境”又使次區域各國對合作機制產生了更大的需求。由于各國政府都把水資源開發看作是效益大于成本的綜合安全工程,是促進地區合作與穩定的重要舉措,因此它們并不希望這一具有積極意義的國家工程會演變成一種危害國家間關系的“存在性威脅”,于是它們愿意為化解各相關利益國之間的矛盾而進行對話與協調,這就為次區域的合作機制不斷發展和完善提供了巨大的動力。其結果是,水資源開發問題的“去安全化”進程被開啟。
三 中國對水資源開發問題“去安全化”的努力
如果“安全化”是把一個普通的公共問題變為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安全事務的話,那么“去安全化”應該是讓普通的公共問題回到“普通的公共領域中”。同時,如果“安全化”是通過“威脅—防衛”的傳統安全言語—行為來建構安全的集體認同的話,那么“去安全化”就應該是以“合作—共贏”的新安全言語—行為來重構安全的集體認同。
在上述的前一種“去安全化”過程中,普通的公共問題能夠回到普通的公共領域中的關鍵在于溝通以及提供溝通的平臺,即對話協調機制。而在后一種新安全言語—行為的社會建構過程中,最為必要的則是增強相互了解和信任,強調合作與共贏的主旋律。
近年來,中國作為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合作發展的重要推動者和負責任的上游大國,在水資源開發問題的“去安全化”過程中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可以歸結為三方面:
首先,中國政府日益重視對瀾滄江—湄公河流域水力開發工程的綜合研究,在國際法、生態環境、人權、可持續發展經濟等方面的觀念意識不斷增強,尤其是按照國際環境公約對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生態環境的共同保護問題采取了積極參與的態度和政策,并且在瀾滄江沿岸的生態環境監測、評估、建設、修復、管理工作上取得了較大的進展。2005年5月,中國在上海組織召開了第一屆大湄公河 (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環境部長會議。會上,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祝光耀明確表示:“中國政府把做好本國在該區域的環境保護作為加強區域經濟合作的基礎。”[6]
2008年第二屆環境部長會議之后,中國又決定在云南和廣西實施大湄公河次區域核心環境項目,建立生物多樣性走廊,承諾保護上游地區的天然林,控制區域內的水土流失現象。這一系列舉動都表明中國政府同次區域各“利益攸關國”合作共贏的意愿和決心。
其次,中國政府積極推動地區合作機制的進一步發展,提高和改善次區域各利益方的溝通平臺,冀望通過密切交流、協調及合作,增加各方對長期絕對獲益的期望,而減少對短期相對獲益的憂慮。生態環境保護合作機制的建立和提升最為突出,可以被認為是對原有次區域合作機制的一個重要補充,也是緩解各利益方對生態安全和人的安全的憂慮的一大舉措。大湄公河生態環境保護的合作機制起始于1995年,最初以“環境工作組會議”為形式。正是在中國政府的大力推動下,大湄公河國家自2005年啟動了“環境部長會議”,把生態環保機制推向更高層次,而“核心環境項目” (CEP)也得到了更全面的開展和實施,強調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及社會公正相結合、相平衡的原則,突出了環保和扶貧的任務和目標。由此,大湄公河生態環境保護的協調合作機制擴展為三層次的綜合機制[7]。此外,中國—湄公河委員會對話機制也在不斷地加強和拓展。中國自1996年就與湄公河委員會建立了正式對話伙伴關系,在水力資源開發問題“安全化”過程中,中國政府更加重視這一溝通平臺。2011年4月,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宋濤在參加泰國華欣對話會議時,提出了中國在未來深化與湄公河委員會良好合作關系的具體建議,其中包括:繼續利用好現有的中國—湄公河委員會年度對話機制;拓寬合作平臺,充分利用中國—東盟自貿區全面建成的重要契機,加強多領域合作;歡迎湄公河委員會和次區域國家專家來華考察和進行技術交流,中方也愿派人赴湄公河委員會進行短期工作交流;增進溝通,加強互信,共同客觀、公正地向公眾和媒體介紹瀾滄江—湄公河水資源開發利用的真實情況和合作成果。這些建議都得到了湄公河委員會的贊同[8]。
再者,中國政府以更開放的姿態主動與大湄公河國家進行有效的對話協調,并加大次區域上下游國家經濟利益共享的力度,使湄公河下游國家真正了解和分享中國在瀾滄江修建水力工程的正面成果。自從2002年4月中國水利部與湄公河委員會簽訂關于中國水利部向湄公河委員會提供瀾滄江—湄公河汛期水文資料的協議之后,中國方面每年都向湄公河委員會秘書處提供瀾滄江汛期水文資料,以協助下游國家預防洪災。2011年,為幫助下游國家更好地抗旱減災,中國方面又向湄公河委員會應急提供了大量的瀾滄江旱季水文數據。為了增信釋疑,2010年6月,中國還邀請了湄公河委員會以及國際河流水電開發生態環境研究工作委員會(ESCIR)的官員和專家參觀景洪和小灣大壩,實地考察中國對瀾滄江水量調節的技術問題以及相關的經濟發展項目、環保建設和移民安置工作。此次參觀給湄公河委員會官員專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湄公河委員會秘書處首席執行官杰瑞米·博德(Jeremy Bird)肯定了中國在水電開發建設方面所做的積極有效的探索以及形成的一些好的經驗和做法。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對湄公河國家的水力工程建設也增加了投資和技術援助,并同水電需求最大的國家泰國和越南分別簽訂了多項合作開發及水電共享協議。根據2008年中國政府公布的《中國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國家報告》顯示,中國在參與次區域水力能源合作方面的設想是:“最終建立起統一的GMS電力市場,在次區域范圍內實現電網互聯及自由的電力交易,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聯網效益,優勢互補,互惠互利,平等共贏。中國愿意與其他GMS各國家拓展能源合作,包括提高能效、發展替代能源,以確保次區域的能源安全。”[9]
總的來說,由于湄公河中小國家和各種非政府組織都或明或暗地非議中國的水電工程,因此中國上述推動“去安全化”的努力顯得十分必要和舉足輕重。一方面,中國積極主動的態度和開放行為,能夠扭轉湄公河各國政府和民間對中國所謂“不透明”的負面看法,使矛盾各方能夠在“普通公共問題”的溝通平臺上進行坦誠的對話,這有利于次區域國家友好地解決有爭執的普通公共問題,有利于各方今后更進一步的協調合作。另一方面,中國起表率和帶頭作用,有益于樹立負責任的上游國家、次區域大國的形象,舒緩下游中小國的疑慮,增強相互了解和信任以及對長期合作共贏的信心,進而有利于合作安全言語—行為的建構。毫無疑問,這些“去安全化”的努力僅僅是個開始,瀾滄江—湄公河水資源矛盾的最后解決仍需要次區域各國政府繼續加強溝通,長期合作,真正走向“川流永不息,彼此共甘美”的共贏格局。
結語
冷戰后,非傳統安全問題日益成為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安全關系中的重要安全事務。“安全化”與“去安全化”是非傳統安全問題產生與解決的兩個過程,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安全化”使各方利益有機會相互博弈以達成妥協,而“去安全化”則進一步促進國家間合作安全關系的社會建構。
以瀾滄江—湄公河水資源開發為例,生態安全問題、個體利益問題以及次區域內外利益攸關國的收益分配和權力斗爭問題,導致水電綜合發展工程逐漸高度政治化,安全的話語不斷加重,呈現出“安全化”趨勢,這一非傳統安全問題的產生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安全關系造成直接或間接的不利影響。但另一方面,通過對這一“存在性威脅”的爭論,各國政府不能不對生態安全和人的安全給予更大的關注,這又有利于完善政府的綜合安全觀和國家綜合發展戰略,同時,大小國之間以及上下游國家之間也在此過程中得以相互重視對方的利益和權利。由于“共同利益困境”,次區域各國對合作機制產生了更大的需求,各國政府愿意為化解各相關利益國之間的矛盾而進行對話與協調,由此推動“去安全化”的進程,使矛盾各方能夠在“普通公共問題”的溝通平臺上進行坦誠的對話,促進更多的協調合作行為。不僅于此,對話溝通和協調合作的過程還使得各國開始以“合作—共贏”的新安全言語—行為來重構安全的集體認同。
瀾滄江—湄公河水資源開發的矛盾和沖突只是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安全關系中的一個非傳統安全問題,它向我們展現了非傳統安全問題產生與解決的兩個過程,對我們觀察和理解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安全關系中的其他非傳統安全問題提供了一定的幫助。
【注 釋】
[1]詳見方軍祥:《中國與東盟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的現狀與意義》,《南洋問題研究》2005年第4期。
[2][4]Barry Buzan et al eds.,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Boulder,Colorado: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1998,pp.29,23-24.
[3]詳見賀圣達:《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復雜的合作機制和中國的參與》,《南洋問題研究》2005年第1期。
[5]見唐海行:《瀾滄江—湄公河流域的水資源及其開發利用現狀分析》,《云南地理環境研究》1999年第1期。
[6]《中國環境報》,2005年5月26日。
[7]詳見李霞:《中國參與的大湄公河次區域環境合作》,《東南亞縱橫》2008年第6期。
[8]《外交部副部長:中國愿與湄委會等開展務實合作》,2010年4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dt/wjbxw/t677592.htm
[9]“三部門發布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國家報告”,2008年3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gov.cn/jrzg/2008-03/28/content_930725.htm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the Securit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Pan Yin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
Non-traditional Security;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Lancang-Mekong Sub-region;Securitization
The paper attempts to justify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hydro-power in the Lancang-Mekong Sub-region would contribute to the cooperative security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on the one hand,but would also create anxiety and interest conflicts on the other hand.The“Securitization”of the issue is inevitable and necessary.It is the process of bargaining and compromise among different interested parties as well as the social construct of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the sub-region.But the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at“desecuritization”of the issue is equally important,as it helps to build mutual confidence,release anxiety and eventually overcome differences.
D822
A
1008-6099(2011)04-0031-06
2011-04-04
潘一寧,博士,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責任編輯:郭又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