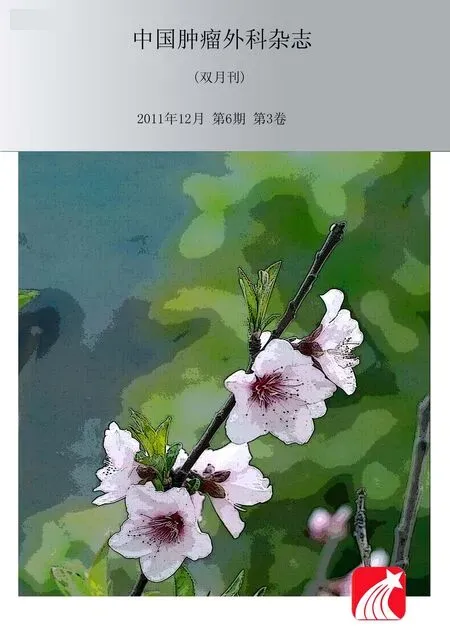乳腺癌分子亞型分類及其與新輔助治療的關系
孫尚韶, 王玉璽, 梁 品
乳腺癌是女性常見惡性腫瘤之一,盡管目前在早期診斷及輔助治療方面取得顯著進展, 但其發病率和死亡率仍不斷增加。僅2006年,美國報道的200 000例新發浸潤性乳腺癌中,就有40 000例發生死亡[1]。傳統的病理診斷分型方法曾一直被視為“金標準”,但經過長期隨訪發現,無論是哪一種病理分型或分級對治療策略都沒有太大的幫助。近來實驗發現,通過用免疫組化和(或)基因分析方法檢測藥理學標記物(ER、PR、Ki67、HER2)的表達,可將乳腺癌患者進行亞型分類[2]。許多證據表明,乳腺癌的治療效果與激素受體和HER2的表達有關,而與傳統的病理分型無關[3]。本文綜述近年來乳腺癌的研究和進展,探索其分子分型和免疫組化分型,旨在揭示此種新的分型方式比傳統的病理分型在乳腺癌的診斷、輔助治療及預后方面更有優勢。
1 乳腺癌各分子亞型的特點
通過“內在的”基因譜將乳腺癌分成5種不同分子亞型[4],雌激素受體陽性的包括管腔A型和管腔B型,雌激素受體陰性的包括HER2型、基底型、正常組織型[5]。目前仍不清楚這5種亞型是相對獨立的個體還是一個有聯系的整體[6]。
1.1 管腔型乳腺癌
管腔型乳腺癌的特點是表達ER、PR、Bcl-2及CK8/18受體。根據有無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 (HER2)的表達進一步分為管腔A型和管腔B型。HER2在不同文獻中提到的方式不同,EGFR2、C-ERB-2、NEU、ERB-B2都是指同一受體。此外,兩種管腔型還表達GATA3、ESR1和FOX1等標記物[7],且GATA3在A型中有較高表達。
1.1.1 管腔A型 特點是ER受體高表達,尤其是在腺體導管腔上皮內呈直線性分布,其預后較好[8]。典型的管腔A型乳腺癌免疫組化特點是ER受體陽性和(或)PR受體陽性,HER2陰性。純原位小葉癌都是管腔A型,大部分浸潤型小葉癌也屬于此型。Millican等[9]研究703例浸潤性乳腺癌患者中管腔A型比例最高,占51.5%,管腔B型和HER2型所占比例最少。
1.1.2 管腔B型 管腔B型除了表達ER和(或)PR之外,還表達EGFR1和細胞蛋白E1[10],HER2陽性。此外,CK18、CK19 和CK7/8等管腔型細胞因子都被認為是此型的標記物[11-12]。
1.2 基底型乳腺癌
基底型乳腺癌易發生于絕經前的婦女(8%~20%),其特征是ER、PR、HER2受體低表達,CK5/6和(或)EGFR受體高表達[13]。EGFR受體在總體乳腺癌中表達率為6%,而在基底型乳腺癌中高達25%[14]。基底型乳腺癌通常表現出抑癌基因P53的變異和原癌基因BRCA1的攜帶。大約80%的BRCA1基因攜帶的乳腺癌都是基底型[15]。此外,基底型乳腺癌還表達波形蛋白(94%)、 CK14、CK17和HER1,且大多數的基底型乳腺癌CK5/6和CK8/18染色陽性,但這并不能作為其診斷依據[16]。研究表明,波形蛋白和CK5/6的高表達可以作為基底型乳腺癌的特定標識物[17]。基底型乳腺癌有著較高的肺、腦轉移率和極高的復發率與腫瘤相關死亡率,但是很少經腋下淋巴道轉移到肝臟、骨骼、大腦和肺臟,且腫瘤相關死亡率與腫瘤的大小和淋巴結的狀態及轉移部位無關[18]。
1.3 HER2型乳腺癌
HER2陽性有兩種不同的亞型,一種是趨向基底型的ER陰性型,另一種是趨向于管腔B型的ER陽性型(可能表達PR)。一些HER2型還表達EGFR[19],大部分此型腫瘤細胞會不同程度地表達CK8/18,但均不表達P53。HER2型腫瘤細胞呈低分化,預后不佳[20]。
1.4 正常乳腺組織型乳腺癌
正常乳腺組織型有5種陰性指標分別是:ER、PR、HER2、CK5和EGFR。基底細胞CK5/6陽性,管腔細胞CK8/18陽性。基底細胞表現較高的增生性,而管腔細胞則表現高分化性。目前尚未知此型中是否有哪種干細胞能進行自我更新。正常乳腺組織的型基因分型更接近基底型乳腺癌,但預后略好于基底型。除了基底型癌核分裂指數略高一些之外,正常乳腺組織型和基底型是有重疊的。
Raica等[21]對42例浸潤性乳腺癌患者的研究,發現ER、PR、HER2、CK5/6、EGFR、P53、Bcl-2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表達,其中管腔A型有22例(52.38%),管腔B型有2例(4.76%),基底型有6例(14.28%),HER2型有7例(16.66%),正常乳腺組織型有5例(11.9%),HER2伴ER陽性有2例,伴ER陰性有4例。除此之外還研究了CK8/18、Bcl-2和P53的表達來補充證明其分子亞型的分類。
2 “三陰”表型
“三陰” 乳腺癌表型特點是缺乏ER、PR、HER2的表達,從分子分型看,更趨向于基底型和正常乳腺組織型,該型占所有乳腺癌的10%~17%。從流行病學來看,“三陰”乳腺癌患者在40歲以下乳腺癌組占23%,在40~49歲組占16%,50歲以上組占11%。
Mullan等[22]研究823例基底型乳腺癌中有150例(18.22%)為“三陰性”乳腺癌,但由于部分“三陰”乳腺癌缺乏CK5/6或EGFR的表達,因此該型乳腺癌不足以定義為基底型癌。大多數髓樣癌表現出ER、PR、HER2陰性,EGFR、CK5/6、CK14、 CK17、P63陽性,同時與90.8%的基底型乳腺癌一樣表現出化生的特征[23],基于“三陰”特點,以及CK5/6表達和免疫組化分析,髓樣癌可能是基底型乳腺癌的一種亞型。此外,應用P63和CK14檢測,93.8%具有“三陰”表型的化生癌亦可被歸入基底型乳腺癌。相當一部分的“三陰”乳腺癌因表達CK18而曾被誤認為是管腔B型。
近有資料顯示,“三陰”乳腺癌異構性很強,治療效果不佳,通常在1~3年內復發,大多數在治療5年內死亡,預后不良主要歸因于腫瘤病理組織上都是Ⅲ級表達[24],且約有96.8% “三陰”乳腺癌呈Ⅲ級表達[25],淋巴結的位置和狀態對判斷預后沒有幫助。 雖然目前唯一有效的治療方案是化療,但乳腺癌細胞的高增殖率和TP53基因的變異都影響紫杉類藥物療效。當前臨床試驗發現順鉑、紫杉醇類及衍生物都對“三陰”乳腺癌有作用。最近還發現達沙替尼(一種SRC途徑抑制劑)對“三陰”乳腺癌也有效,但還需個體化研究的證實。
3 分子亞型與生存預后的關系
應用基因分型進行乳腺癌患者分類與評估其預后仍然有爭議。其中一些觀點認為其具有臨床意義,但是必須明確是ER陽性的腫瘤。管腔A型具有較長的生存率,管腔B型比管腔A型預后差,基底型和HER2型生存期較短。“三陰”乳腺癌被分成基底型和正常乳腺組織型,其預后也不同。并且“三陰”乳腺癌有較高的復發率,腦轉移的風險和死亡率均較高,因此需要進一步的輔助治療[26]。
4 分子亞型與輔助治療的關系
乳腺癌的新輔助化療方案已經證實是一種有效的治療方式,并且可以根據乳腺癌分子分型與其對應的治療反應,選擇出更為有效的治療方案,避免化療的副作用,使化療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個體化治療。目前乳腺癌的分子分型仍未完善,不同的檢測技術方法和評估標準也會影響分子分型的結果。Osamu Gotoh等提出的快速矩陣檢測技術是目前比較容易的基因檢測方法之一[27]。分子分型不僅有助于判斷預后,還有助于預測腫瘤對治療的反應。應用基因芯片技術對乳腺癌進行分子分型,較傳統的分類能更好地反映腫瘤的生物學行為。但由于其不適用于福爾馬林固定,標本不易石蠟包埋,且費用昂貴,實際操作困難,目前只能局限于實驗室,因此尚難廣泛應用于臨床。盡管如此,此技術在蛋白質水平上對乳腺癌進行分子分型已成為新的研究熱點[28]。隨著生物技術的發展,新的基因分子靶點的發現也將不斷對現有分型進行補充和發展,為臨床上進行個體化治療提供重要的依據。
研究表明管腔型乳腺癌可采用輔助荷爾蒙他莫昔芬治療[29],針對治療靶點主要有3種:抗血管增生,穩定微管和DNA修復。基底型可以采取阻斷MAPK,AKT旁路和P53的變異來制定化療方案。而“三陰”乳腺癌多采用蒽環類和紫衫烷類藥物輔助化療。
多年來,從30%的臨床治療失敗病例中得出結論是應盡量避免過度治療[30]。ER陽性的患者可采用激素替代治療,但管腔型對化療又不敏感,同樣ER陰性患者對化療反應亦不同,因此ER陽性和陰性的乳腺癌治療就需要根據腫瘤的生物學特性來決定。在HER2陽性組中,用HER2抗體聯合化療可明顯提高預后質量,顯著減少腫瘤復發。但并不是所有陽性者對抗體治療都敏感,可能會受抑癌基因PTEN減少和原癌基因CXCR4增加的影響。沒有用ER受體抑制劑而單純使用蒽環類化療藥的標準治療,對大部分患者沒有療效。因此迫切需要新的靶向作用生物標記物。有關針對分子分型采取的術前化療的作用,目前尚存在爭議。一些研究報道稱,分子分型可以預測術前化療反應,但只是針對ER起作用。大樣本研究發現,基底型和HER2型對蒽環類輔助化療要比管腔型敏感。在輔助化療方面,應用紫杉醇12周后再加用5-氟尿嘧啶、阿霉素和環磷酰胺新的輔助化療對接近45%的基底型乳腺癌有明顯的療效。因此術前采取細針穿刺活檢采樣進行分子分型對化療方式的選擇有指導意義。Sotiriou C等通過此方法來區分對阿霉素和環磷酰胺的敏感者和不敏感者,同時,此種方法也很容易用來動態觀測化療后的藥物效果。但是,仍沒有一種生物標記物能用來預測腫瘤轉移患者的化療反應,而大部分依靠對激素受體和P53的反應作用來評估療效[31]。
近10年來靶向治療被廣泛使用,表皮生長因子受體抑制劑在乳腺癌治療中的應用已被認可。臨床乳腺癌患者中表達c-kit的基底型腫瘤應用伊馬替尼和舒馬替尼治療后預后較好,因此c-kit基因可作為靶基因,但是c-kit靶向治療的效果卻是依靠腫瘤的流行病學和作用機制進行推測的,而這兩方面理論尚不明確,因此無法解釋其治療反應率低的原因。新近報道中,抗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貝伐單抗)可以提高經紫杉醇治療的轉移癌患者的生存率。此研究中超過60%是激素受體陽性而HER陰性者,提示抗血管內皮新生階段對于管腔型癌有效。顯然,我們需要尋找新的特異性治療措施,只有取長補短才能最大發揮腫瘤藥物的治療作用,同時盡可能減少其副作用。
[1] Morris SR, Carey LA. Molecular profiling in breast cancer[J]. Rev Endocr Metab Disord, 2007, 8(3):185-198.
[2] Dabbs DJ, Chivukula M, Carter G, et al.Basal phenotype of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recognition and immunohistologic profile[J]. Mod Pathol, 2006, 19(11): 1506-1511.
[3] Reis-Filho JS, Westbury C, Pierga JY. The impact of expression profiling on prognostic and predictive testing in breast cancer[J]. J Clin Pathol, 2009, 59(3):225-231.
[4] Mackay A,Weigelt B,Grigoriadis A, et al. Microarray-based class discovery for molecular classification of breast cancer: analysis of interobserver agreement[J]. J Natl Cancer Inst, 2011, 103(8):662-673.
[5] Nielsen TO, Hsu FD, Jensen K, et al. Immunohistochemical and clin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basal-like subtype of invasive breast carcinoma[J]. Clin Cancer Res, 2004, 10(16):5367-5374.
[6] Fan C, Oh DS, Wessels L, et al. Concordance among gene-expression-based predictors for breast cancer[J]. N Engl J Med,2006, 355:560-569.
[7] Wang X, Gotoh O. Accurate molecular classification of cancer using simple rules[J]. BMC Medical Genomics , 2009, 2:64.
[8] S?rlie T, Wang Y, Xiao C, et al. Distinct molecular mechanisms underlying clinically relevant subtypes of breast cancer: gene expression analysis across three different platforms[J]. BMC Genomics, 2006, 7:127.
[9] Millican RC, Newman B, Tse CK, et al. Epidemiology of basal-like breast cancer[J]. Breast Cancer Res Treat, 2008, 109(1):123-139.
[10] Laakso M, Tanner M, Nilsson J, et al. Basoluminal carcinoma:a new biologically and prognostically distinct entity between basal and luminal breast cancer[J]. Clin Cancer Res, 2006, 12(14 Pt 1):4185-4191.
[11] Habashy HO, Powe DG, Glaab E, et al. RERG (Ras-like, oestrogen-regulated, growth-inhibitor) expression in breast cancer: a marker of ER-positive luminal-like subtype[J]. Breast Cancer Res Treat , 2011, 128(2):315-326.
[12] Hoenerhoff MJ, Shibata MA, Bode A, et al. Pathologic progression of mammary carcinomas in a C3(1)/SV40 T/t-antigen transgenic rat model of human triple-negative and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J]. Transgenic Res , 2011, 20(2):247-259.
[13] Rakha EA, EL-Sayed ME, Green AR, et al. Breast carcinoma with basal differentiation:a proposal for pathology definition based on basal cytokeratin expression[J]. Histopathology, 2007, 50(4):434-438.
[14] Faratian D, Bartlett J. Predictive markers in breast cancer-the future[J]. Histopathology, 2008, 52(1):91-98.
[15] Schnitt SJ. Will Molecular Classification Replace Traditional Breast Pathology?[J].Int J Surq Pathol , 2010 , 18(3 Suppl): 162S-166S.
[16] Chen M HS, Yip GWC , Tse GMK, et al. Expression of Basal Keratins and Vimentin in Breast Cancers of Young Women Correlates With Adverse Pathologic Parameters[J]. Mod Pathol, 2008, 21(10):1183-1191.
[17] Livasy CA, Karaca G, Nanda R, et al. Phenotypic evaluation of the basal-like subtype of invasive breast carcinoma[J]. Mod Pathol, 2006, 19(2):264-271.
[18] Fulford LG, Reis-Filho JS, Ryder K, et al. Basal-like grade III 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 of the breast: patterns of metastasis and long-term survival[J]. Breast Cancer Res, 2007, 9(1):R4.
[19] Chivukula M, Bhargava R, Brufsky A, et al. Clinical importance of HER2 immunohistologic heterogeneous expression in core-needle biopsies vs resection specimens for equivocal (immunohistochemical score 2+) cases[J]. Mod Pathol, 2008, 21(4):363-368.
[20] Tamimi RM, Baer HJ, Marotti J, et al. Comparison of molecular phenotypes of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and invasive breast cancer[J]. Breast Cancer Res, 2008, 10(4):R67.
[21] Raica M, Junq I, Cmpean AM, et al. From conventional pathologic diagnosis to the molecular classification of breast carcinoma:are we ready for the change?[J]. Rom J Morphol Embryol, 2009, 50(1):5-13.
[22] Mullan PB, Millikan RC, Molecular subtyping of breast cancer:opportunities for new therapeutic approaches[J]. Cell Mol Life Sci, 2007, 64(24):3219-3232.
[23] Hicks DG, Short SM, Prescott NL, et al. Breast cancers with brain metastases are more likely to be estrogen receptor negative, express the basal cytokeratin CK5/6, and overexpress HER2 or EGFR[J]. Am J Surg Pathol, 2006, 30(9):1097-1104.
[24] Rakha EA, El-Sayed ME, Green AR, et al. Prognostic markers in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J]. Cancer, 2007, 109(1):25-32.
[25] Tan DS, Marchió C, Jones RL, et al.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molecular profiling and prognostic impact in adjuvant anthracycline-treated patients[J]. Breast Cancer Res Treat, 2008, 111(1):27-44.
[26] Edith AP, Alvaro MA, Cathy AA, et al. Adjuvant therapy of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J]. Breast Cancer Res Treat, 2010, 120(2):285-291.
[27] Burstein HJ, Elias AD, Ruqo HS, et al. Phase II study of sunitinib malate, an oral multitargeted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in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previously treated with an anthracycline and a taxane[J]. J Clin Oncol, 2008, 26(11):1810-1816.
[28] Carey LA, Dees EC, Sawyer L, et al. The triple negative paradox: primary tumor chemosensitivity of breast cancer subtypes[J]. Clin Cancer Res, 2007, 13(8): 2329-2334.
[29] Jacquemier J, Charafe-Jauffret E, Monville F, et al. Association of GATA3, P53, Ki67 status and vascular peritumoral invasion are strongly prognostic in luminal breast cancer[J]. Breast Cancer Res,2009, 11:R23.
[30] Andre F, Pusztai L. Molecular classification of breast cancer:implications for selection of adjuvant chemotherapy[J]. Nature Clinical Practice Oncology, 2006, 3(11):621-632.
[31] Pusztai L, Mazouni C, Anderson K, et al. Molecular classification of breast cancer: limitations and potential[J]. Oncologist, 2006, 11(8):S868-S8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