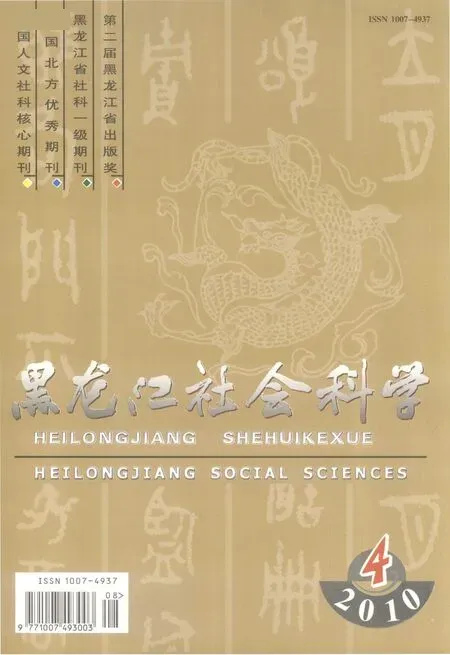網(wǎng)絡(luò)化世界的語言文字應(yīng)用:閱讀與寫作
李景艷,凱瑟琳·李
(1.哈爾濱工業(yè)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哈爾濱 150001;2.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xué)文學(xué)院,墨爾本)
網(wǎng)絡(luò)化世界的語言文字應(yīng)用:閱讀與寫作
李景艷1,2,凱瑟琳·李2
(1.哈爾濱工業(yè)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哈爾濱 150001;2.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xué)文學(xué)院,墨爾本)
由于傳播速度快、閱讀廣泛,信息社會(huì)的文字寫作極為重要。在魚目混珠的文字作品中,總有行間段落令人咀嚼回味、流連忘返,因其通俗易懂、風(fēng)格迥異或是意義非凡。筆者將其稱之為“警語式文體”。“警語式文體”運(yùn)用時(shí)下的傳媒語類傳授必要的哲學(xué)、知識(shí)和技能,努力將一個(gè)較大的篇章分解成較小的,易操作的語段。這些語段是經(jīng)過思索和技能、滿載激情與呵護(hù)雕琢而成的。它們充分說明了生活在信息社會(huì)或者網(wǎng)絡(luò)世界并非意味著我們應(yīng)該忘卻我們首先并最終是“學(xué)習(xí)語言的軀體”,這一唯一使我們成為人類,成為“文字人”的屬性。
文字;“文字人”;“警語式文體”;信息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世界
一、“文字人”與“警語式文體”
長(zhǎng)久以來,筆者一直鐘愛把我們定義為“文字人”。盡管創(chuàng)作于上世紀(jì)中期,但Bu rke的觀點(diǎn)在今天看來與以往一樣正確。他的定義之所以重要,是因?yàn)樗粢鈱⑽覀兊摹胺?hào)創(chuàng)造”、“符號(hào)使用”能力囊括其中:“學(xué)習(xí)語言的軀體/遂而變成了文字人/人類是/符號(hào)創(chuàng)造、符號(hào)使用、符號(hào)濫用的/動(dòng)物/否定概念的發(fā)明者/用我們自制的器具/從我們的自然狀態(tài)中分離出來/受等級(jí)精神的激勵(lì)/獲取死亡的預(yù)知/且?guī)е昝栏唷薄1疚纳婕暗木褪亲址到y(tǒng)。大體上講是關(guān)于人類使用該系統(tǒng)的兩種方式——閱讀和寫作以及如何塑造后者以使前一種經(jīng)歷盡可能有意義。盡管我們時(shí)下生活在所謂的不可改變的信息社會(huì)里,“以計(jì)算機(jī)邏輯為基礎(chǔ)的信息技術(shù)已經(jīng)使我們的世界網(wǎng)絡(luò)化了”。然而書面文字蔑視所有的預(yù)言,拒絕成為過眼煙云。即便在一個(gè)現(xiàn)在似乎很多人都推崇圖像的世界里,我們繼續(xù)需要文字,并且永遠(yuǎn)都將需要。因?yàn)檎鏒onW atson所觀察的,“圖畫統(tǒng)治:但是文字定義、解釋、表達(dá)、統(tǒng)一我們的思想和我們的知識(shí)。它們幫助我們表達(dá)原有的想法、接受新思想,所有這一切都源于文字”。
遵循W atson的觀點(diǎn),筆者認(rèn)為書面文字——無論文字形式還是像素形式——對(duì)我們“文字人”來說仍至關(guān)重要。盡管文字所提供和接受的大部分語境以往從未存在過,或者在過去的若干年中文字發(fā)生了巨變。我們生活中的主要變化——因特網(wǎng)——引發(fā)了人類生存所有方面信息的激增,但大部分信息仍然通過文字傳播。作為人文學(xué)科的教師,筆者希望此種傳播能夠更加流暢,邏輯上能夠更加雄辯;但是作為民主公共領(lǐng)域的公民,我們?yōu)槟苈牭饺找鏀U(kuò)大的領(lǐng)悟 (像素)文字的不同聲音喝彩。當(dāng)然,文字寫作是一回事,而贏得讀者則是另一回事。因此,我們?cè)絹碓礁械轿淖秩粢暰€需要變成“警語式文體”。“警語式文體”是筆者創(chuàng)造的術(shù)語用以描述某一類文體,或者描述文體自身具有的一種特質(zhì)。這種特質(zhì)能夠吸引視線、贏得讀者,并且能在信息超載的社會(huì)環(huán)境里存留在讀者的記憶中。“警語式寫作”這一術(shù)語只有在當(dāng)今世界的信息社會(huì)才可能有意義。我們大多數(shù)人現(xiàn)在都熟悉“片語”這個(gè)術(shù)語——代表一種簡(jiǎn)短而精辟、能夠捕捉人們視線并存留腦海的短語或句子,且能在與眾多其他信息狂轟濫炸的博弈中取得成功。“片語”的英文對(duì)應(yīng)詞是 sound bite,通常也寫作 sound byte。這種拼寫轉(zhuǎn)而令人想起時(shí)下我們生活中的一個(gè)主要元素——將信息傳輸至電腦的數(shù)據(jù),由無數(shù)的零和一按序列組成。這些序列每 8個(gè)一組來計(jì)數(shù),稱作“字節(jié)”。“字節(jié)”一詞在英文中是其他三個(gè)詞 b inary d igit eigh t縮略而成的。當(dāng)筆者鍵入這些英文詞的時(shí)候,每個(gè)字母都需要一個(gè)信息節(jié) (即 8個(gè)位)。例如:由三個(gè)英文字母組成的詞“bit”需要三個(gè)信息節(jié)。由此可見,“字節(jié)”這個(gè)術(shù)語是一種文字游戲,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cè)谄聊簧蠒鴮懙乃形淖侄际恰白止?jié)”,因?yàn)闃?gòu)成這些文字都需要我們傳輸多個(gè)字節(jié),即便我們沒有意識(shí)到是這樣做的。
誠然,如同“片語”一樣,有些“警語式文體”可能會(huì)很搶眼,但只不過因?yàn)樾问缴匣ㄇ?并非因?yàn)樗鼈兏嬷x者任何新鮮的內(nèi)容或制作精細(xì)且有趣。這樣的“警語式文體”不會(huì)存留在人們的記憶之中,鮮有立足之地,會(huì)轉(zhuǎn)瞬即逝。我們這里所議的“警語式文體”的質(zhì)量是一種能將大量的含義濃縮成幾個(gè)詞,或至少某種結(jié)構(gòu)上非常經(jīng)濟(jì)的短語。用較少的文字即能傳情達(dá)意的寫作并不一定遜色,在這一點(diǎn)上詩歌便是一例。詩歌的語言往往精煉到極致,萃取精華,且不會(huì)被視為比長(zhǎng)篇大論遜色絲毫。這也并非意味著詩歌創(chuàng)作機(jī)械式地需要簡(jiǎn)單的詞匯,盡管簡(jiǎn)單的詞匯自身所表達(dá)的意義并非簡(jiǎn)單。現(xiàn)以W illiam CarlosW illiam s的著名詩句《紅色的手推車》為例:“如此地依賴 /于/一輛紅色輪子的 /手推車……”
文字的魅力不僅取決于其應(yīng)用的具體場(chǎng)合,往往還要與眾多日益增加的其他傳媒項(xiàng)目相抗衡。當(dāng)某一讀者在同一個(gè)房間內(nèi)開著電視機(jī)或收音機(jī)的時(shí)候,也許耳朵里還塞著音樂播放器耳機(jī)。如果他正在看電腦屏幕上的文字,也許隨時(shí)提示音都會(huì)響起,也許在屏幕的某個(gè)角落“氣泡”都會(huì)閃現(xiàn),或者也許二者同時(shí)發(fā)生,提示他收到新郵件。他的手機(jī)也會(huì)響起或者響個(gè)不停,甚至于老式的電話機(jī)也加入到刺耳的噪音中。因此,文字不僅要首先吸引視線,當(dāng)紛繁的爭(zhēng)奪讀者眼球的其他媒體形式橫沖直撞時(shí),還要在讀者的心中立足。這就是信息社會(huì)的生活現(xiàn)實(shí),我們可以為此感到悲哀,也可以認(rèn)同其各有利弊,甚至于可以解讀其為信息過于繁雜的社會(huì)。正如 Sco ttD rumm ond對(duì)于網(wǎng)絡(luò)寫作所言“我們生活在一個(gè)網(wǎng)絡(luò) 2.0世界”。其含義為日新月異的技術(shù)進(jìn)步已經(jīng)使網(wǎng)絡(luò)步入了一個(gè)全新層次的互動(dòng),使用戶對(duì)網(wǎng)絡(luò)內(nèi)容做出回應(yīng)并進(jìn)而創(chuàng)造他們自己的網(wǎng)絡(luò)內(nèi)容,或者以一種新的形式展現(xiàn)他人的文字。
一般性的信息技術(shù)使得一些新的通訊形式成為可能。我們不妨列舉一些這樣的形式:網(wǎng)絡(luò) 2.0郵件、聊天及聊天室、新聞網(wǎng)絡(luò)、互動(dòng)百科全書、社交網(wǎng)站、博客、論壇、網(wǎng)絡(luò)電話、手機(jī)短信。諸如此類的大多數(shù)通訊形式需要使用因特網(wǎng)到來之前業(yè)已存在的語言形式——在很多情況下口語甚至于俚語形式。盡管可以使用特殊的縮略形式,甚至于某些特定群體內(nèi)使用的詞匯以及一些表情圖標(biāo)。但大多數(shù)網(wǎng)絡(luò)語言反映的只是出現(xiàn)在面對(duì)面群體活動(dòng)中所使用的內(nèi)群體類語言 (手機(jī)短信縮略語例外)。另外,該媒體群體中的大部分所展示的語言應(yīng)用與以往圖書和雜志規(guī)定的作品質(zhì)量同樣雅觀、豐富且令人折服。正是這種最出色的寫作風(fēng)格才可以稱得上我們所說的術(shù)語“警語式文體”。
二、從用戶創(chuàng)造的詞匯到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
下面是一則“警語式文體”的例子,是從一個(gè)名為 Trekearth的公共攝影網(wǎng)站用戶創(chuàng)作的作品中選取的。該網(wǎng)站的使命是“通過攝影了解世界”。會(huì)員可將自己的照片上傳到該網(wǎng)址,并且講解攝影技術(shù)層面的東西,簡(jiǎn)單描述畫面。如果他們?cè)敢獾脑掃€可以評(píng)議他人照片的拍攝質(zhì)量,評(píng)論可以在攝影作品間超鏈接,或者鏈接到外部網(wǎng)站——網(wǎng)絡(luò)語篇的最佳特征之一。下面這段描述是對(duì)一幅攝影作品的說明,作品中有一對(duì)老人走在市場(chǎng)附近的大街上。作品攝于 2008年 6月法國西南部Domm e小鎮(zhèn)。
當(dāng)我閑逛Domm e古老的大廳市場(chǎng)時(shí),第一次看見了他們。他們的舉止和不茍言笑的動(dòng)作顯示他們并非夫妻;不知為什么,兩人的對(duì)話似乎過于激烈、過于緊急,果然男士最終走開了。我注意到那輛摩托車強(qiáng)烈的顏色與窗前和男人旁邊的花相映成趣,便決定將這些元素包括在照片中。右側(cè)市場(chǎng)的墻角似乎也建議我偷覷他們,我也恰好是這樣做的,因?yàn)槲規(guī)е鄼C(jī)尾隨了他們好幾分鐘。
這是一段很好的“警語式文體”的例子。為了吸引讀者的注意力,該網(wǎng)站攝影作品的語言描述必須與極具說服力的攝影技術(shù)相競(jìng)爭(zhēng),但不是在所有的競(jìng)爭(zhēng)中都會(huì)取勝。我們選錄這段是因?yàn)槊枋銎鹗加趧?dòng)作的中間,一種寫作手法——叫做插敘——據(jù)說是公元前一世紀(jì)羅馬詩人 Ho race推介的,并一直是用來吸引讀者注意力的好方法。短文隨意、可信,但低調(diào)的語氣明確地透露了文字背后的一種認(rèn)同感,是 Sco ttD rumm ond所說“注入人格交際”的一個(gè)例子,是成功網(wǎng)絡(luò) 2.0寫作的一個(gè)基本特征。本例中生動(dòng)的視覺描述以及有趣的選詞,所有這些都增加了它的感染力。
這個(gè)網(wǎng)站是 2003年由在科威特服役的美國海軍后備役軍人 Eric M.Johnson創(chuàng)建的,為后來在Geo rgeM ason大學(xué)攻讀英語碩士學(xué)位奠定了基礎(chǔ)。Johnson說他的網(wǎng)站“力爭(zhēng)做包括莎士比亞完整作品的最好的免費(fèi)網(wǎng)站,并為學(xué)者、演員以及所有莎翁愛好者而準(zhǔn)備。開放來源莎士比亞網(wǎng)站包括全部作品的 1 864全球版。這個(gè)版本是半個(gè)多世紀(jì)以來最完整可靠的單集莎士比亞版”。在鍵入 Shakespeare一詞和誦讀十四行詩第四節(jié)之間,這小節(jié)含有一行筆者永遠(yuǎn)喜愛的“警語式文體”——“natu re taketh no thing bu t do th lend”(自然無所索取而只是給予)——大約 10秒鐘過去了。
長(zhǎng)久以來,筆者一直喜愛詩人A d rienne R ich的一首詩《生活在罪惡中》:“她原以為工作室會(huì)自行保持原狀:/在愛的家俬上沒有灰塵。/半異端邪說,去奢望水龍頭響聲小一些,/窗格上的玻璃免于層層污垢……”我們已經(jīng)盡力展示優(yōu)美而有力的語言范例——“警語式文體”的一個(gè)主要特征之一 ——全部是從網(wǎng)絡(luò)上摘錄的。誠然,兩段這樣的節(jié)錄均在網(wǎng)絡(luò)發(fā)明之前即已存在,但一段 (選自 Trekearth網(wǎng)站)是特別為網(wǎng)絡(luò)創(chuàng)作的,并且事實(shí)上直接鍵入網(wǎng)站的對(duì)話框內(nèi),就像網(wǎng)絡(luò)用戶輸入網(wǎng)絡(luò)語言一樣。這些網(wǎng)絡(luò)用戶通常被稱作“生產(chǎn)消費(fèi)者”,因?yàn)樗麄兗认M(fèi)又生產(chǎn)網(wǎng)絡(luò)內(nèi)容。確實(shí),因特網(wǎng)慣有的內(nèi)容是語言,在那里可以發(fā)現(xiàn)大量的、不同類型的語言,因而它不是一個(gè)相同成分組成的語言媒介。如果談?wù)撍芯W(wǎng)絡(luò)語言,那么我們不得不包括半文盲或者甚至一些個(gè)人博客中的無知狂言以及莎士比亞作品的電子版本。我們無法相信現(xiàn)存的任何術(shù)語能夠有意義地囊括這兩個(gè)極限,因?yàn)榫W(wǎng)絡(luò)語言的風(fēng)格多種多樣,加之因特網(wǎng)起源之前即已具有諸多風(fēng)格,因此每一種語類都特異于各自的話語群體。
三、網(wǎng)絡(luò)語作為“警語式文體”?
然而,我們可以用網(wǎng)聊或網(wǎng)絡(luò)語言指代那些源于因特網(wǎng)或信息技術(shù)使用、且現(xiàn)已進(jìn)入普通用語的詞匯。例如,“美工教室”(Pho toshop)一詞,表示一種處理圖像的計(jì)算機(jī)軟件,現(xiàn)已收錄到牛津英語辭典的草稿中。但是,早前我曾見過“Pho toshop”在下面這個(gè)句子中用作動(dòng)詞:“新聞網(wǎng)絡(luò)可能幫助很多人緩解9.11帶來的壓力。但是如果我們不想在我們‘人類焦慮的永恒日歷’(Focillon)上添加大量其他恐怖日子的話,就應(yīng)該少花時(shí)間妖魔化我們的敵人,而用更多的時(shí)間描繪(Pho toshopp ing)一個(gè)我們確實(shí)都能生存的未來。”有趣的是該句子的作者其實(shí)賦予“美工教室”一種比喻或暗示的含義。而詞典草稿中的定義或本義是:“編輯、控制,或使用電腦圖像編輯軟件數(shù)字式地改變(一個(gè)攝影圖像)。”
此前筆者提及過用較少的詞匯濃縮或淡化意義是“警語式寫作”的主要特性。比如,俳句 (Haiku)就是一種極為濃縮的形式。借鑒了這種觀點(diǎn),無疑旨在表明文本不拘泥于空洞的交換。2007年世界詩歌日,為發(fā)現(xiàn)最佳的短信浪漫詩,英國的一家手機(jī)公司舉辦了一場(chǎng)競(jìng)賽,競(jìng)賽參加者可以使用縮略和非縮略詞匯。以下便是獲勝的參賽作品:“潮濕的瀟瀟雨/沖淡了今天的情性。你的短信/支撐我浮在斑斕的霓彩之上/像一艘紙船,以致/浸入肌膚/我仍在嬉笑。”然而與文化普及之前的年代具有不可思議共性的是,如今的信息社會(huì)很大程度依賴于視覺媒體,因其優(yōu)于任何以文本為基礎(chǔ)的交流方式。無論我們考慮的是現(xiàn)代印刷式的大眾傳媒還是萬維網(wǎng),似乎都可以看出圖片成為主宰,在某種程度上文字可視為“寄生于圖像”。不過筆者認(rèn)為這只是在某些交流情景下而已。比如 Trekearth網(wǎng)站的圖像信息就多于文字,因而人們不可能閱讀所有照片的說明。由于有了網(wǎng)上新聞,即便是我們中最熱心的讀者,瀏覽的圖像也會(huì)比閱讀的文章多。有證據(jù)表明我們?yōu)g覽網(wǎng)頁的方式與閱讀書籍或其他印刷類文本不同。但是如果沒有文字,網(wǎng)絡(luò)也不會(huì)如此有趣和豐富。即便程度各異,我們都是“文字人”。雖然我們的世界已轉(zhuǎn)化成信息社會(huì),但這一點(diǎn)還未改變。
四、死一般的詞匯?
然而,W atson相信文字在垂危。這是他《死亡句子》一書的中心論點(diǎn):“盡管英語在全球分布,但語言本身正在縮減。每年都有大量新詞生成,但是我們的孩子和領(lǐng)導(dǎo)人的詞匯量卻越來越小。拉丁語和希臘語已被擠出大部分新聞工作者的英語,一些‘晦澀的’詞匯成了禁忌除非它們屬于經(jīng)濟(jì)貿(mào)易術(shù)語。你為你的讀者寫作,而你的讀者掌握的詞匯卻比過去少,并且沒有時(shí)間查閱那些不熟悉的詞。政治語言也針對(duì)同樣的讀者、用同樣的傳媒方式鏈接讀者,因而逐年地衰變……如同公共公司,公共語言正被修剪得缺少修飾和微妙。”W atson將這種由此而得來的、糟糕的英語形式稱作“經(jīng)營語言”,并認(rèn)為它“對(duì)于信息時(shí)代或許如同機(jī)器和流水線于工業(yè)”,換言之,是一種乏味的奴役形式。他把這類語言最糟糕的一些例子稱作“黃鼠狼語言”。據(jù)說最初源于 19世紀(jì)美國的政治,黃鼠狼語言從句子中汲取意義如同“一只黃鼠狼將蛋液吸干、蛋殼丟在一邊完整無損”。羅斯福總統(tǒng)明確地用該詞匯描述威爾遜總統(tǒng)用“全球志愿培訓(xùn)”代替“征兵”。“黃鼠狼語言”概念也被媒體批評(píng)家使用,特別是 Stuart Hall和 No rm an Fairc lough。
值得注意的是,如W atson所指出的,英語寫作最致命的例子至少是由那些社會(huì)上掌握最大權(quán)力和資源的人創(chuàng)造的。起初源于貿(mào)易,而后滲入政治、傳媒以及“各種社會(huì)機(jī)構(gòu)”。W atson斷言正是管理至上主義的語言特性成為今天的公共語言。然而確實(shí)如此嗎?作為從事傳媒工作的研究者,筆者欲立即做一些實(shí)證測(cè)試以檢驗(yàn)W atson斷言的正確性,于是察看了《時(shí)代報(bào)》的主頁并點(diǎn)擊了“今日新聞”。然后筆者隨意點(diǎn)擊了兩則新聞,并且拷貝和保存了每則新聞的前十行,以便細(xì)細(xì)咀嚼。
第一篇文章,《美國的氣候之爭(zhēng)也許會(huì)被邊緣化》是這樣開始的:“任何一個(gè)國家面對(duì) 21世紀(jì)最大挑戰(zhàn)所作反應(yīng)的有效性取決于兩個(gè)國家:美國和中國。這是澳大利亞氣候變化之爭(zhēng)中很少提及的一個(gè)令人尷尬的真理。美、中兩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幾乎占了世界的一半,除非它們能夠達(dá)成一致務(wù)必減排,否則國際社會(huì)希望能夠?qū)⒋髿庵袦厥覛怏w的濃度穩(wěn)定保持在一個(gè)避免災(zāi)難性后果的水平上將十分渺茫。兩位美國總統(tǒng)候選人在各自最近的對(duì)華政策說明中,均表示了十分高興與中國一道減排的愿望。然而,達(dá)成如此一致的障礙很大。”作者 Fergus G reen在文章開頭運(yùn)用了兩個(gè)雙關(guān)語。第一個(gè)與一部新近著名的有關(guān)氣候的紀(jì)錄片的片名相呼應(yīng),A l Go re制作的一個(gè)尷尬的真理。鑒于題材的相似性,這是一個(gè)最恰當(dāng)?shù)暮魬?yīng)。第二個(gè)雙關(guān)語在句法上高度仿效 Jane A usten的著名開首語“這是一個(gè)世界公認(rèn)的真理……”取自她的小說《傲慢與偏見》。盡管文章的語氣是一種客觀的“重要新聞”,Green盡可能使用強(qiáng)力的動(dòng)詞以及有趣的形容詞“渺茫”;還有頭韻法“十分高興的愿望”。總之,我們?cè)谖淖珠g看到了一種對(duì)細(xì)節(jié)的關(guān)注,正是這種關(guān)注使得這篇散文充滿了具有捕捉視線能力的“警語式文體”。由于開篇雙關(guān)語的使用,文章的論點(diǎn)在相當(dāng)時(shí)間內(nèi)有極大的機(jī)會(huì)存留在讀者的記憶中,主要取決于這篇散文并未“被修飾得過分而微妙”,也并非管理至上主義式的語言。
然而,在第二則新聞開篇的若干行內(nèi),我們發(fā)現(xiàn)了一種非常不同的文體。這則新聞的標(biāo)題為《“新一代住房”為邊緣者開啟大門》:“緩解無力購房的任何戰(zhàn)略中的一個(gè)關(guān)鍵性因素是必須提高安全且購買得起的住房。盡管聯(lián)邦及州政府正致力于改善邊緣者的生活——一份聯(lián)邦白皮書十月即將公布,并且一項(xiàng)全國性廉租房協(xié)議有望在年底出臺(tái)——對(duì)于那些無力購房的人而言,找到一個(gè)既安全又負(fù)擔(dān)得起的住處已經(jīng)變得幾乎不可能了。這樣的事實(shí)必須得到廣泛的承認(rèn)。一些機(jī)構(gòu)的使命本該是幫助窮困的人,但往往卻束手無策,只是將這些人安置在專用的公寓內(nèi)。一對(duì)夫婦以每周 370澳元的價(jià)格只租得一間還不足一般起居室大小的房間——沒有廁所、沒有廚房,到了第二周末錢就已蕩然無存,無法維持生活。這就意味著人們?cè)诟L(zhǎng)時(shí)間內(nèi)買不起房,而買不起房的時(shí)間越長(zhǎng),東山再起就越發(fā)困難。”冷眼一看文章的開頭似乎源自政府媒體,因?yàn)閹滋烨盀橹贫ㄈ珖夥砍凶庑杂?jì)劃,聯(lián)邦政府引入立法。筆者發(fā)現(xiàn)盡管幾家新聞報(bào)道都觸及了這個(gè)話題,卻沒有找到一篇可以被視為該段基礎(chǔ)的文章。然而,在一個(gè)政府網(wǎng)站我們發(fā)現(xiàn)了這樣一個(gè)例子:“2008年 3月,澳大利亞聯(lián)邦政府委員會(huì)就一項(xiàng)具有突破性的新聯(lián)邦政府財(cái)政安排中的關(guān)鍵性因素達(dá)成了一致,并于 2008年年底完成。這項(xiàng)新的框架協(xié)議將給專項(xiàng)撥款帶來重大的改變,即為實(shí)現(xiàn)國民政策目標(biāo)聯(lián)邦政府撥給各州或領(lǐng)地的款項(xiàng)。當(dāng)前住宿援助項(xiàng)目就是通過專項(xiàng)撥款解決的。”雖然推測(cè)出此類“經(jīng)營式”文章清晰的含義很難,但這位未署名的政府作者似乎努力為一項(xiàng)新的倡議提供信息。在這篇文章中各種各樣的角色得以構(gòu)建:“澳大利亞聯(lián)邦政府委員會(huì)”、“新的財(cái)政框架”以及“住宿援助項(xiàng)目”。但是這些角色也不足以使這篇文章免于夸張。文章講述了一個(gè)協(xié)議、安排、框架和項(xiàng)目的世界,沒有人,更看不出“警語式文體”。
顯然,這并非報(bào)刊文章較有代表性的樣本。但它表明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警語式文體”的例子,即便“黃鼠狼語言”司空見慣。盡管經(jīng)營式語言也許是一種現(xiàn)代化現(xiàn)象,但語言缺乏清晰度的現(xiàn)象卻已存在了很久,或許與人類連詞成句的歷史相仿。
五、信息社會(huì)的文字
浮夸文體的存在已有幾個(gè)世紀(jì)的歷史了。W illiam s引用了一段 16世紀(jì)的寫作為例:“借助于長(zhǎng)久以來持續(xù)不斷精煉我們的語言、為萬事提供精煉而從事的學(xué)習(xí)和經(jīng)歷、告誡如何精煉的智慧與判斷,如果使用和慣例在逝去的歲月中對(duì)于那些狡黠、那些不肯放棄卻肯定在我們的寫作中保持的機(jī)智毫無抱怨,那么我們的語言確實(shí)無法令人信賴,完全是隨意的信手拈來。”同樣,長(zhǎng)久以來作家們一直在創(chuàng)作清晰的文章,并且為浮夸文體提出建議。下面的例子(也是W illiam s所作):“在眾多的其他課程當(dāng)中,我們應(yīng)該學(xué)的第一課是我們永遠(yuǎn)不受任何怪異的、學(xué)究氣的用語的影響,表達(dá)力求通俗。既不尋覓過于華美優(yōu)雅,也不圖求過分輕松隨意;施展最少的智慧,以適合大部分人講話的風(fēng)格。有些人將自己的母語拋在腦后去追求異國風(fēng)格的英語。”很清楚,對(duì)于我們應(yīng)如何最佳地將文字組合的憂慮并不是什么新鮮的事。但是W a tson認(rèn)為當(dāng)今的浮夸以及書面文字的微妙和美感“之死”很大程度上是“經(jīng)營”語言傳播的結(jié)果,值得人們注意。為什么經(jīng)營語言在增加?早前,筆者提到W atson的觀點(diǎn),他認(rèn)為這類語言幾乎取代了機(jī)器和流水線,工業(yè)時(shí)代重要的因素。
這種想法與羅伯特·哈桑在《信息社會(huì)》一書中表達(dá)的觀點(diǎn)不謀而合。在書中,哈桑闡述道:“信息,以觀點(diǎn)、理念、革新和對(duì)于每一可想象主體的普通數(shù)據(jù)為表達(dá)形式……已經(jīng)取代了作為社會(huì)中心組織力的勞動(dòng)和恒星相對(duì)靜止的邏輯和機(jī)械。”尤其是,他認(rèn)為在我們的經(jīng)濟(jì)體系中,生活的每一個(gè)方面都已被“金融化了”。借此,他意味著金融知識(shí)是主要的流通貨幣。換言之,在當(dāng)今的社會(huì)里,我們擁有貨幣買賣以及使用貨幣投機(jī)的總的支配——并非基于工業(yè)制品或任何真實(shí)之物的紙質(zhì)資本。諸如此類的空虛經(jīng)濟(jì)需要自身種類的語言以證明其存在——引用W atson的若干措辭為例:革新而進(jìn)取;持續(xù)發(fā)展;增長(zhǎng)(作及物動(dòng)詞),比如擴(kuò)大經(jīng)營、發(fā)展經(jīng)濟(jì);利益主體;底線理論;受生產(chǎn)驅(qū)使;磨耗;非沖突的;內(nèi)含、附帶損害。這些詞匯著實(shí)與被黃鼠狼吸干的空洞蛋殼相似——一種動(dòng)物的名字,W atson用來暗喻商業(yè)語言——一種“警語式文體”,如果曾經(jīng)有該種文體的話。
此類商業(yè)語言可能已將其觸角延伸到社會(huì)的所有領(lǐng)域。即使作家們自己不想使用這種語言,但如果想要與政府或企業(yè)辯論某個(gè)問題時(shí)卻發(fā)現(xiàn)他們使用的竟是對(duì)方的語言,就像筆者早前介紹的那篇文章的作者。該作者并非來自商界,而是來自公益團(tuán)體,因此大概需要定期處理一些業(yè)務(wù)。除此以外,隨著世界“金融化”步伐的加快,媒體中金融消息的比例在增長(zhǎng)。這無須記者們操勞。銀行提供帶有專家評(píng)論的新聞節(jié)目的來源,并為新聞采播人員提供新聞采集所需的照相機(jī)及器材,節(jié)目以留有銀行的記號(hào)或徽標(biāo)的背景結(jié)束。對(duì)于報(bào)刊,他們會(huì)仿效新聞特寫的方式刊登新聞,就像所有企業(yè)和想要將材料打入媒體的個(gè)人一樣。在繁忙、人員短缺的新聞中心,許多這樣的新聞幾乎未經(jīng)編輯即投入印刷發(fā)行。
但是A dam D everell提醒我們就每一則單純旨在為某個(gè)商業(yè)企業(yè)招徠生意的新聞而言,也會(huì)有一個(gè)對(duì)該群體有益處。對(duì)此,筆者欲加補(bǔ)充:在每一個(gè)媒體中發(fā)表的“黃鼠狼語言”式的句子中,我們都可以找到一個(gè)漂亮而微妙的。無論受何種干擾,這些詞匯都能夠吸引讀者視線,令記憶深刻。
W atson的斷言也許是正確的。他指出經(jīng)營語言已經(jīng)感染了全球化信息社會(huì)中公共語言的方方面面,經(jīng)營語言已經(jīng)無處不見:“私人和公共領(lǐng)域……麥當(dāng)勞、你的金融機(jī)構(gòu)、你的圖書館、你的地方議員、你國家的情報(bào)組織,經(jīng)營語言奪門而入,闖進(jìn)你的電話:來自當(dāng)?shù)卣⒛愫⒆拥膶W(xué)校、銀行、保險(xiǎn)公司和電話公司的信件……”但是,對(duì)于哈桑的觀點(diǎn),筆者予以強(qiáng)烈地爭(zhēng)辯,我們認(rèn)為“同在生活中一樣,悲情主義在理論上是一種無力的表現(xiàn)”。語言代表了我們的身份,我們是語言——事實(shí)上我們是“文字人”——并且我們可以通過感染戰(zhàn)勝語言的死亡。在這種情況下,微生物源于新自由主義,但也很容易源自極權(quán)主義,其容易程度如同 Geo rge O rw ell很久以前在他的著名小說《一九八四》中闡述的一樣。可以這樣講,《一九八四》是一部既反映社會(huì),又反映語言的小說。
六、工業(yè)行動(dòng)——為“警語式文體”
此戰(zhàn)役的盟軍不難找到。我們不妨試著和大型企業(yè)中較有影響力的人物聊一聊。問他們——就像我們?cè)?jīng)做的——如何看待大多數(shù)同仁的語言運(yùn)用,或者他們公司公共語言的使用。看一看他們對(duì)此是否滿意,通常他們是不會(huì)滿意的。但他們往往不知道如何改變現(xiàn)狀。當(dāng)你想要對(duì)他人表明一種觀點(diǎn),尤其是一個(gè)大規(guī)模組織的人,也許你應(yīng)該嘗試另一種方法——寫信。盡可能寫得明智而優(yōu)雅,審慎思考并雕琢每一個(gè)句子,構(gòu)建與作者及目的適合的道德觀、感染力和徽標(biāo)。你可以通過電子郵件或慢件方式發(fā)送,最好選擇慢件,因?yàn)樗苡行乱?筆者總是設(shè)想我的收信人手捧著我的來信的情景。面對(duì)電腦屏幕上諸多內(nèi)容的紛擾,信件較之電子郵件給予收信人更多的關(guān)注,收到這種信件的人現(xiàn)在越來越少了。時(shí)下主要的觀點(diǎn)是我們必須通過快速發(fā)一個(gè)電子郵件來回復(fù)幾乎所有事情,或者干脆不予理睬,因?yàn)橛肋h(yuǎn)有其他更緊迫的事情。然而,筆者認(rèn)為沒有什么事情比用心、用情地使用語言更緊迫,除了與愛人、朋友和孩子交談,但這些往往也是關(guān)于用心、用情地使用語言。
當(dāng)我們有好的理由時(shí),就可以寫這樣的信——給市長(zhǎng)、同事、上司、大企業(yè)的高層人士。我們并非總能得到我們想要的回復(fù),但我們幾乎總能得到回復(fù),這些回復(fù)表明收信人對(duì)于我們的信給予了相當(dāng)?shù)乃伎肌.吘?人是“文字人”,會(huì)對(duì)認(rèn)真編寫的文字作出反應(yīng),這些精心雕琢的文字能夠誘使讀者暫時(shí)不予理睬其他的信息而抽時(shí)間來閱讀。筆者把這樣的擊中目標(biāo)的字字句句稱作“警語式文體”,并非因?yàn)槲蚁胗眠@樣的字眼迎合信息社會(huì),而是因?yàn)槲蚁胱屨Z言——雅觀的、犀利的、謹(jǐn)慎構(gòu)建的——以與在這個(gè)飛速旋轉(zhuǎn)的世界通常潦草數(shù)筆的“腐朽”的語言較量。甚至以其自己的名義,去贏得勝利。無論是個(gè)人還是與工作相關(guān)的信件,這種努力均無需受到限制:一封寫給編輯的郵件信件也可成為精雕細(xì)琢的“警語式文體”的媒介;一則評(píng)論或博客中的帖子、甚至于平常你自己的博客也不失為這樣的媒介。
每當(dāng)我們聽到“黃鼠狼語言”,可以停下來發(fā)出質(zhì)問。正如 Fairc lough指出的那樣,政客和某些商業(yè)巨頭使用的特殊的“黃鼠狼語言”表明“全球一體化”是不可避免的力量,人類無力與之對(duì)抗。又如Bu rke在我們先前引用的詩中所描述的,人類是“文字人”,語言是我們發(fā)明的,語言構(gòu)筑了我們的現(xiàn)實(shí):“我們不能指望通過現(xiàn)實(shí)了解一個(gè)詞匯的意義;相反,我們必須通過語言了解現(xiàn)實(shí)的意義。詞匯為我們帶來知識(shí)——為我們創(chuàng)造現(xiàn)實(shí)。”不是所有我們寫的或讀的詞匯都能是“警語式文體”,但我們肯定可以致力于消除自己寫作中的“黃鼠狼語言”,并且強(qiáng)烈地反對(duì)在他人的作品中使用這樣的詞匯。
這就是本文的哲學(xué)思想。“警語式文體”,如W atson所言,不是一種提供“實(shí)用原則”的“手冊(cè)”,也不會(huì)在與“黃鼠狼語言”的對(duì)抗中有什么幫助,但它運(yùn)用時(shí)下的傳媒語類傳授必要的哲學(xué)、知識(shí)和技能,努力將一個(gè)較大的篇章分解成較小的、易操作的語段。這些語段是經(jīng)過思索和技能、滿載激情與呵護(hù)雕琢而成的。它們充分說明了生活在信息社會(huì)或者網(wǎng)絡(luò) 2.0世界并非意味著我們應(yīng)該忘卻我們首先并最終是“學(xué)習(xí)語言的軀體”,這一唯一使我們成為人類,成為“文字人”的屬性。
〔責(zé)任編輯:王曉春〕
H1
A
1007-4937(2010)04-0089-05
2010-05-10
李景艷 (1963-),女,山東泰安人,副教授,語言文字教育學(xué)博士,研究員,從事語言教學(xué)理論及實(shí)踐、跨文化交際研究;凱瑟琳·李(1953-),女,英國威爾士人,高級(jí)講師,博士生導(dǎo)師,從事媒體語言、語篇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