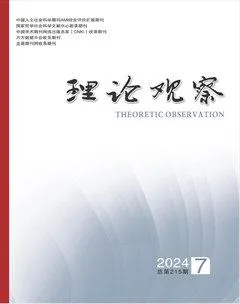乾隆年間山西靈石鄉村禁賭探賾
摘 要:乾隆年間山西賭博問題嚴重,并引發了眾多命案,嚴重破壞了鄉村社會秩序。為了實現鄉村社會的穩定,鄉紳群體主持了鄉村禁賭活動,部分鄉紳試圖通過對本村落的范圍內的參與賭博及開場窩賭人員罰金、罰戲、送官等措施重構被賭博破壞的鄉村社會秩序,但并未達到預期效果。清朝禁賭實質上是統治者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而推行的政治舉措,鄉紳主持下的鄉村禁賭則是鄉村熟人社會中長輩對晚輩的教化,是鄉村對于官府禁賭政策的反饋,一旦官府無暇顧及,被壓制的鄉村賭博則會死灰復燃。
關鍵詞:乾隆年間;碑刻文本;山西靈石;鄉村禁賭
中圖分類號:K2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 — 2234(2024)07 — 0114 — 06
禁賭是清代社會治理的重要方面,深受國家與地方的重視,清朝統治者為了禁賭制定了體系完備的禁賭法律,鄉村社會也曾組織開展各項禁賭活動。當前學界對于清朝時期的禁賭研究已十分深入,成果較為豐富。王美英、魏忠、潘洪鋼等學者從清朝整體視角著手,認為由于乾隆年間禁賭政策的寬松及官員的腐敗,使得乾隆之后社會賭博問題日益嚴重,并一直持續到清末。①在區域禁賭研究中,學界對于賭博問題的研究多集中在廣東②、徽州③等南方工商業發達的市鎮,認為商品經濟的發展及朝廷社會控制力的減弱使得南方地區的賭博問題愈加嚴重。山西的禁賭研究主要集中在澤潞地區,朱文廣、魏曉鍇等學者④認為清朝澤潞地區的禁賭主要是對后世賭博的防范,而清朝澤潞地區禁賭活動由于禁賭令并未得到長期落實而效果不佳。當前學界對于晉中地區鄉村賭博的研究相對較少,本文嘗試以晉中地區靈石縣乾隆年間的禁賭碑為切入點,嘗試窺探乾隆年間官府及地方鄉紳在面對鄉村賭博日益嚴重情況下的反應。
一、乾隆年間靈石鄉村賭博概況
(一)乾隆年間靈石鄉村的賭博現象及危害
清代是中國歷史上賭博最為繁盛的時代,參與賭博的人群更是廣泛包括了社會各個階層。[1]清朝初年,受到明末“馬吊”廣泛流行的影響,社會賭博之風盛行,太宗曾“諭管刑部事貝勒濟爾哈朗曰:近聞游惰之民多以賭博為事,夫賭博者耗財之源,盜賊之藪也,嗣后凡以錢及貨物賭博者,概行禁止,違者照例治罪。”[2]順治年間,“南之馬吊,北之混江牌,乃市井事,士大夫好之窮日累夜,若癡若狂。”[3]康熙年間,江浙一帶“斗馬吊牌”盛行,“雖士大夫不能免”,且“近馬吊漸及北方,又加以混江、游湖諸戲”。[4]雍正時期,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對安徽巡撫提出“又如賭博一事,萬不可寬者。”[5]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對山西巡撫伊都立提出的“嚴保甲,查私鑄,斷燒鍋,禁賭博”[6]等都反映出社會的賭博問題已然十分嚴重。面對日益嚴重的賭博問題,雍正皇帝曾以強硬態度對賭博進行全面打擊,賭博風氣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遏制。
乾隆皇帝即位后,為了緩和緊張的社會關系,采取了較為寬松的政治措施,甚至乾隆皇帝本人“嘗于幾暇,取 《列仙圖》人物繪群仙慶壽圖用骰子擲之以為新年玩具。”[7]寬松的政治環境和乾隆皇帝的帶頭參與使得賭博活動又逐漸興盛,“賭博之風,莫甚于今日”[8]。“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編氓徒隸,以及繡房閨閣之人,莫不好賭”[9]。乾隆年間的賭博不僅是對社會風氣的破壞,更是催生了一系列刑事案件,嚴重危害了朝廷對基層的治理。僅就山西地區而言,因賭博而致殺人的案件便屢見不鮮,“案犯年未十五,因賭負債,窩主剝衣辱之,遂懷恨購毒潛入其家投毒”。[10]此類惡性案件屢屢出現,乾隆皇帝為此提出“朕覽山西情實人犯冊內,因賭博釀成人命之案甚多,皆因疎縱賭具賭博所致”[11]。數量眾多的刑事案件致使“山西按察使唐綏祖奏稱稱、晉省民風。好尚賭博。應嚴定地方官失察之例。除于咨題案內、牽連賭博、地方官應查參者。仍逐案咨題、隨招附參外。其僅止賭博。或斗毆自盡命案、牽連賭博、例應外結者。”[12]
賭博活動不僅在城市之中十分繁盛,偏遠鄉村亦因“官離此數十里,不得知道。”[13]而成為賭博活動的重要地區。浙江建德縣就有婦人因“其丈夫日逐賭場,并將家內什物竊去,以供賭博”而“哭甚哀”[14]的情況。鄉村賭博的情況并不僅僅出現在江浙地區,在山西地區也屢屢出現,“僻在萬山中,財資不通,人勤苦多”[15]26的靈石鄉村賭博問題亦十分嚴重。乾隆年間的靈石鄉村“游手賭棍來往不絕,誘引子弟習染日迷”[16]460,甚至有“開場窩賭,引誘子弟”[16]459、“專以賭博為生”者[16]484。嚴重的賭博使得社會治安遭到了極大的破壞,“輿圖覽之,自京都、省郡、州城、府市,以至一邑一鄉,其紳紟棍徒相聚為賭者,或敗產棄業受累于終身,或漂流西東拋妻撇子,或因爭起釁致傷其性命”[16]507。嚴重威脅到清朝的政治統治,因此,在官方的主導之下,廣大鄉紳主持的禁賭活動在靈石縣開展。
(二)靈石縣鄉村賭博的時空分布
由于鄉村賭博材料的欠缺,對于鄉村賭博問題的記載多集中于鄉村碑刻資料。碑刻作為官方意志在鄉村傳播的重要載體,現存的碑刻資料雖不能全面準確地反映古代鄉村社會禁賭的效果,但通過對碑刻的分析亦能窺探出鄉村社會對于朝廷詔令的反饋及當時賭博的分布區域。
通過現存的禁賭碑的空間分布可知,靈石縣現存的禁賭碑主要集中在靈石縣金莊里、張志里(如圖1)等遠離縣城、交通不便的西部山區。從禁賭碑的鐫刻時間來看,靈石縣現存的九通禁賭碑中有八通屬于乾隆年間,主要集中于乾隆二十六年到乾隆四十五年(如表1),但道光年間亦有一通禁賭碑存在。此外,漫河村禁賭碑還于光緒二十六年進行了重新鐫刻。現有禁賭碑刻的時空分布表明乾隆中后期靈石縣官府加強對于偏遠鄉村禁賭的重視力度,朝廷的禁賭政策已然推行到靈石縣的廣大偏遠山區鄉村,并得到了鄉村的積極響應。而道光年間出現的禁賭碑及光緒十六年漫河村對禁賭碑的重鐫則表明乾隆年間的賭博活動并未被徹底禁絕,官府對于鄉村禁賭的要求一直持續到清末。
通過對乾隆中后期靈石縣禁賭碑設立位置的整理,可見在空間分布上呈現出集中在西部山區這一特點。筆者認為這一現象應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著密切的聯系。
首先是靈石西部山區鄉村在乾隆年間生活富足,游民數量激增,享樂主義盛行。明中后期以來,山西的商品經濟發展十分迅速,逐漸出現了有較大影響力的區域性商幫——“晉商”。清初出于政治的需要,統治者給予晉商販賣鹽、茶等商品的資格,商業日漸發達,促進了以“八大皇商”為代表的晉商團體的崛起。參與到商業活動中的百姓在擁有財富之后開始貪圖享樂,修建深宅大院后逐漸參與到賭博之中。同時,康熙時期玉米等高產經濟作物的傳入,以及雍正時期攤丁入畝的實行,推動鄉村人口在這一時期迅速增長。靈石縣“順治二年,戶三千一百三十二,口兩萬二百一十四,嘉慶二十一年,清查實在戶一萬九千一百九十二,口十三萬三百二十一”[15]97,嘉慶末年較于順治年間翻了六倍,在古代較為落后生產力的情況下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大批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在土地生產力無法于短時間內得到提升的情況下,這部分剩余勞動力逐漸演變為游民,成為社會重要的不安定因素。當“因旱未雨,農民閑暇”時,極易出現這些游民中的“賭棍乘隙入村賭”[16]487的情況。而官府有限的衙役逐漸在處理鄉村事務中捉襟見肘,靈石西部山區鄉村賭博活動自然難以得到官府的有效遏制,這也促使其在乾隆年間禁賭碑的設立。
其次是靈石西部山區鄉村交通不便,官府對靈石西部山區鄉村的管控力量不足。靈石縣“襟汾面嶺,南北衢途涖斯土者,外修牧圍,內課農桑”[16],縣域內連接太原與霍州僅有的兩條路線,即仁義鋪、常家山鋪、韓信嶺、高壁鋪、冷泉鋪等急遞鋪所構成的急遞鋪路線和冷泉關、雀鼠古道、瑞石驛、仁義驛等構成的驛路[17]都分布于汾河兩岸,并未能輻射到汾西的廣大山區。多山的地形和南北橫穿的汾河嚴重阻礙了靈石縣之間的交流,也阻擋了位于汾河以東的官府對汾河以西廣大地區的有效管控,再加之部分在市鎮受到打擊的賭博分子因躲避官府追查而轉入鄉村,使得靈石西部山區的鄉村賭博大量存在。同時,由于古代制度推行的滯后性,保甲制在乾隆年間并未在靈石縣西部山區得到徹底貫徹執行,同時鄉村舊有的里甲制已無法對于百姓實行有效的管控[18],鄉村社會出現了一定時期的官方權力真空,朝廷的禁賭詔令自然也無法在鄉村得到有效地貫徹執行,在此基礎上的鄉村秩序官府已無力管轄,賭博活動也在此時愈演愈烈。
最后是靈石西部山區鄉村教育較為落后,未能實現儒家思想對鄉村的有效教化。靈石西部山區鄉村由于“地僻民貧”,官方的儒家教化并未能實現。而受到參與商業活動的鄉村百姓的影響,山西的重商風氣則得到大量的有效傳播。重商主義思想沖擊了傳統封建秩序,使得冒險主義盛行。山西高度發達的商業使得商人在山西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晉商所引領的民風習俗也發生了根本的轉變。人們不再追求入仕做官,排在四民之末的商賈一躍成為四民之首”。[19]山西巡撫劉于義提出“但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其次寧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讀書應試。”[20]25再加之康乾時期大興文字獄,社會文化壓抑,在鄉村社會追求儒家文化的熱情急轉直下。山西地區私塾的教育內容也不再是四書五經,而是也逐漸向“實用性”靠近,開始教授商業活動所需的各種技巧,以及蒙語、滿語、俄語等外語。[19]缺少儒家倫理熏陶的社會風氣不可避免地出現些許松動,本就薄弱的宗族權威遭到更大的沖擊,官府不易直接控制的鄉村社會逐漸出現了開始嘗試突破傳統道德,追求個性的解放,尋求賭博等刺激行為。
二、乾隆年間山西靈石的鄉村禁賭的治理
(一)鄉紳對于鄉村禁賭的主持
朝廷作為社會禁賭活動的主導者,是鄉村禁賭的重要保障,但由于官府力量的有限,其在鄉村的禁賭活動則主要是在鄉紳的主持下展開的,鄉紳為鄉村禁賭活動的糾首和舉事人。鄉紳是指在地方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地方權力掌握者,根據不同鄉村鄉紳的不同身份,可以將鄉紳分為在地方事務中代表官方意志的保長、甲長和鄉約、在傳統鄉村社會中決定家族大小事務的宗族耆老,以及在地方社會中有一定影響力和號召力的地方鄉紳。
保長、甲長和鄉約是鄉紳角色的主要組成部分。清朝初年,山西所承襲明朝的里甲制度在處理地方事務當中逐漸顯示出不適應性,雍正年間的里甲首事賦稅造假嚴重影響了國家賦稅的征收。為了應對賦稅問題,清政府開始尋求更為有效的基層制度,在地方推行“保甲順莊”。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細化了保甲法的各項規定,并要求“凡甲內有盜竊邪教,賭博賭具,窩逃奸拐,私鑄私銷,私鹽踩鞠,販賣硝磺,并私立名色,斂財聚會等事,及面生可疑,行跡詭秘之徒,責令專司查報”[12]。山西巡撫塔永寧積極響應,在山西建立起完善系統的保甲體系。此外,鄉約也是鄉村事務重要的參與者。鄉約是清初為宣講圣諭而設,到乾隆年間,“晉省村莊,無分大小,俱設有鄉約。其名目雖與村長相殊,其責任實與村長無異也。”[21]鄉約在鄉村公共事務中已然成為地方權力的重要掌握者和執行者,與保長甲長共同成為構成鄉紳的重要組成部分。
宗族是地方鄉紳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封建社會,我國長期存在“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22]的情況,宗族作為地方權力的重要掌握者和地方秩序的重要維護者,逐漸形成了一整套宗族內部的運行規則,包括對于家族成員的行為規范和懲處措施。但是由于華北地區的宗族并無族產的存在,北方宗族凝聚力遠不如基于族產基礎上的南方宗族勢力強大,對于公共事務的決策權也較之南方明顯薄弱,基本僅起到號召主持作用。因此北方的宗族耆老的權力亦與鄉約的權力相似,大多數為利用自身及官府的影響力而教化震懾百姓,在禁賭中則體現為“許族長協同牌甲稟官究責”[16],而非利用族規進行實質性的刑罰懲處,地方宗族亦為鄉紳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深井村、蕃義村的楊氏家族、樓珍村的鄭氏家族都是以宗族為核心,宗族成員充當禁賭活動的經理、糾首,其已然成為地方鄉紳的重要組成部分。
基于宗族基礎之上,一個村落內數個宗族的情況使得鄉紳的來源不僅限于本宗族,而是數個宗族鄉紳的協商聯合,逐漸形成了凌駕于宗族之上而囊括整個村落的公共權力,這種公共權力的執行者亦為囊括眾多宗族的鄉紳群體組織。例如泉則坪村主持設立禁賭碑的是本村劉、成、馬三姓16位鄉紳[16]。在數個宗族并立的鄉村社會,作為主持禁賭活動的舉事人為了增強鄉村的權力的權威性,通常還會在各個宗族鄉紳聯合的基礎上不斷吸納地方其他知識分子及威望人士的參與,以加大禁賭的效果。漫河村的禁賭活動是在溫、趙、宋、王、倪、韓、郭、楊、喬九姓12位糾首的主持之下展開的,其中既有監生趙邦杰,又有溫氏宗族的參與,還有其他具有地方影響力的人物參與,其體現出的是一種與鄉紳協商致力于社會秩序穩定的公共權力。[16]
鄉紳作為鄉村禁賭碑設立的主要主持者,其不僅積極擔任禁賭活動中的倡導者與管理者,還積極地為禁賭碑的設立出資。
鄉紳作為禁賭活動支持者,積極地參與到鄉村禁賭事業中,擔任禁賭活動的經理、糾首。同時,鄉紳作為地方的權威和宗族事務的主持者,在鄉村事務中通常掌握著話事權,還積極對于百姓的行為進行教化。
同時鄉紳也是禁賭活動中的重要出資人。禁賭活動作為一種持續性活動,往往“勞力廢財”,[16]1088為了保障禁賭的順利推行,鄉紳還時常出資相助。
(二)鄉紳采取的鄉村禁賭措施
鄉紳主持之下的禁賭活動作為一種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措施,所要達到的最終目的是重塑社會風氣。靈石境內現存的眾多禁賭碑中都明確提出了“嚴禁賭博,以正人心,以清風氣”,[16]566進而使得村民“恪遵嚴禁,各守本分”。[16]485最終通過禁賭,“將見害事一除,利端潛興,不惟□日之村落得以安靜,即后世之子孫亦□永□無事之福云爾”。[16]459基于此,民間禁賭并非對朝廷禁賭法令的嚴格執行,而是基于鄉村社會內部的一種道德約束,禁賭的措施往往折射出一種警醒意味,最終目的是實現對百姓的有效教化,故而常常通過道德懲罰作為主要的懲治手段,很少涉及肉刑。
民間禁賭主要采取道德約束和金錢懲治等措施。基于民間教化的目的,民間禁賭懲處措施主要為獻戲與金錢的罰沒,其中尤其以金錢的罰沒為主。金錢的罰沒是懲治賭博的主要措施,對于金錢的罰沒數量大多數為“三兩”[16]484或“五兩”。[16]485同時,還提出“立功有賞、包庇受罰”,打擊對于賭博的包庇,鼓勵百姓的檢舉揭發。為了打擊包庇行為,鄉紳提出“如知情洵者罰銀三兩”[16]487。為了加強禁賭效果,鄉紳充分發動廣大村民,提出“倘有一人能捉并獲賭具者,公內酬銀二兩。如知情洵者罰銀三兩。”。[16]487為避免鄉村禁賭中的賭徒歸屬而影響禁賭效果,鄉紳提出“凡屬村境,一概查拿。”[16]487且“欲賭不遂,村中混罵者即以賭論”。[16]487鄉紳對賭徒的罰款大致為五兩左右,對知情不報者的罰金大致為三兩左右。對于罰款金額的確定,應當亦有其當中的考量。嘉慶版《靈石縣志》記載當時“捕役八名工食銀四十八兩,門子一名工食銀六兩,皂吏四名工二十四兩,馬夫一名工食銀六兩”[15]。當時的大多數縣級胥吏的一年俸祿為六兩,此處對于罰金確定為五兩,根據嘉慶年間糧食“每石折銀一兩四分九厘七毫九絲四微五抄六麈六渺一埃一漠”[15]來計算,五兩銀子的購買力應當為五石左右,應當為當時普通之家一年的正常糧食需求量。這個數量即能對賭徒形成一定的打擊,而又不至于過于沉重使其難以生存。
罰戲也是懲治賭博的重要措施,罰戲的數量也大多為三天。在娛樂活動極其匱乏的古代鄉村社會,戲曲無疑是百姓最為主要的娛樂活動,亦是鄉村社會中影響力最大的社會行為。通過對于賭博者的罰戲亦在最大程度上壯大鄉村禁賭聲勢,能通過社會輿論來對賭徒進行道德譴責、對百姓進行警醒,加強對于禁賭的宣傳效果。故而“凡有捉獲者除票糾之外,獻戲三期”。[16]487在鄉村禁賭中,罰金和罰戲往往是同時進行的,并且逐漸成為一種社會默契而廣泛實行,參與賭博及“村中開場窩賭”[16]484者“嗣后倘若有犯,罰戲三天、銀五兩,一定不恕。是為約。”[16]485對賭博者罰戲還有以信仰來約束賭博的深刻內涵。北宋以后,隨著山西戲劇的發展和民間信仰的發達,在無戲臺“不惟戲無以演,神無以奉,抑且為一村之羞也”①的觀念指導下,逐漸形成了神殿與戲臺相結合共同構成神廟的建筑形式,再加之山西高度發達的信仰使得每個村落都擁有多種形式的信仰場所,特別是關帝信仰更是達到了村村有關廟的程度,而作為村落信仰中心的廟宇也就成為處理村落公共事務的中心。“神前獻戲三天”[16]484亦是在以村落信仰來對賭博者及窩賭者進行道德上的批判和精神上的壓力,以百姓對神靈的敬畏警醒百姓,將禁賭活動加之以神的意志,塑造出對于賭博會使人神共憤的精神壓力。此外,戲劇中所宣揚的懲惡揚善的觀念亦對百姓進行潛移默化的教化。
民間禁賭的最后手段是“送官究治”。清朝嚴刑峻法以禁賭博,提出“凡賭博財物者,皆杖八十,攤場財物入官,其開張賭坊之人同罪”[23]。雍正三年又加重處罰,“凡賭博不分兵民,俱枷號兩個月,開場窩賭及抽頭之人,各枷號三個月,竝杖一百,在場財物入官”,并規定“地方保甲,知有造賣賭具之人,不行首報者,杖一百”[23]。嚴厲的律法使得其對于百姓有極大的震懾力,鄉村禁賭由于是在官府的主導下進行的,故而鄉村禁賭的措施亦不能忽略官府的作用。當鄉村的賭博活動逐漸超出鄉紳所能控制的范圍時,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官府勢力介入,故而民間常常將“送官究治”作為鄉村禁賭的最后手段。以“許糾首赴縣具稟,以究其罪。”[16]459來震懾百姓。正謂:“民雖不知王章可遵,豈不知肌膚可愛?即不知肌膚可愛,詎不知桎梏難逃。嘖嘖詳文,煌煌明訓,敢云弗從?”[16]507
三、乾隆年間山西靈石鄉村禁賭效果
乾隆年間的鄉村禁賭是一場試圖整頓社會風氣的政治活動,但對于禁賭的效果而言,是十分有限的。在鄉村禁賭活動正在轟轟烈烈進行中的乾隆四十一年,出現了“靈石縣趙張氏等因女張趙氏賭博、偷竊、不服管教,將其勒死一案”[24]。嘉慶、道光年間,靈石縣因賭博而釀成人命的案件亦層出不窮,這表明鄉村賭博的社會風氣并未得到有效逆轉,禁賭活動一定程度上來說是失敗的。道光年間出現的禁賭碑及光緒年間對于禁賭碑的重鐫表明,直至道光、光緒年間靈石西部山區的賭博活動仍很活躍,甚至比乾隆年間更為嚴重。
在探討鄉村的禁賭時,要充分考慮到朝廷的禁賭律令和鄉村約定俗成的禁賭措施,黃宗智提出“只有兩者兼顧,才能把握歷史真實”[25]。實際上,統治者對于鄉村禁賭的目的也僅是通過禁賭來遏制鄉村過剩的社會不安定因素。即使是嚴厲禁賭的雍正皇帝,亦在禁賭中要求官員“加重不可陡然而舉,凡事皆當逐漸相機而增減。”[20]7因此,鄉村禁賭雖然是國家意志在鄉村的執行,但其禁賭的措施并不是朝廷法令在鄉村的嚴格執行,而是鄉紳在鄉村社會范圍內對于百姓的教化和號召,其要實現的最終目的是通過官府刑罰的恐嚇和鄉紳的教化而讓鄉村賭博有所收斂,不至于惡化到動搖社會秩序的程度。
對于參與賭博者而言,鄉村禁賭的措施并不是對以往賭博的追責,而是對這種不良行為的勸告,這明顯與朝廷禁賭律令違法必究精神有所沖突,但是官府對這種沖突持默許態度。對于官府而言,在乎的并不是禁賭律令的嚴格執行程度,而是政策所產生的效果,甚至為了恢復社會秩序這一目的可以忽視禁賭律令這一手段的執行情況。即使在禁賭中出現“巡查捕役、鄉約地方逐處抽取規例,規例到手,不但不查拿解究,抑且拘隱出結。”[26]、“關廂內生員之家,竟有公然開場賭博者,聚集無賴,深藏密室之中,地方保長既不敢問,晝夜呼盧,罔顧法紀。”[27],在社會風氣并未遭受劇烈惡化的情況下官府亦未做出強烈的反應。
但是,也正是這種寬容,致使在朝廷對鄉村的管控力逐漸下降或者朝廷無力顧及鄉村時,鄉村出現了賭博與禁賭的相互博弈,而在中央朝廷逐漸失去對地方的強大控制時,就逐漸演變成社會層面更深層次的秩序混亂,例如清末的廣東地區,正是由于前人禁賭的不徹底,使得在官府忙于解決外國列強侵略與國內的太平天國運動而無暇顧及禁賭活動時,出現了賭博之風有所抬頭,直至清政府無力管控廣東地方時更是一發不可收拾,最終演變為“賭國”。
〔參 考 文 獻〕
[1]潘洪鋼.清代的賭博與禁賭[J].江漢論壇,2008(09):61-66.
[2]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卷十一)[M].北京:中華書局,1985:155.
[3]汪師韓.葉戲原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4.
[4]王士禎.分甘余話(卷一)[M].北京:中華書局,1989:19-21.
[5]余金.熙朝新語(卷八)[M].上海:上海古籍書店影印本,1983.
[6]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四五)[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6:231.
[7]徐珂.清稗類鈔(第十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6:4895.
[8]龔煒.巢林筆談(卷四)[M].北京:中華書局,1981:107- 108.
[9]錢泳.履園叢話(卷二十一)[M].北京:中華書局,1979:578.
[10]顧麟趾.山右讞獄記(光緒二十四年冬飲廬刊本)[M].臺北:文海出版社,1996:7-8.
[11]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二五[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6:15.
[12]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二百五十[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6:15
[13]世宗憲皇帝朱批諭旨(卷一百三十九)[M]//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14]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M].北京:中華書局,1960:28.
[15]王志瀜.靈石縣志(嘉慶二十二年刻本)[M].太原:三晉出版社,2019:26.
[16]景茂禮,劉秋根.靈石碑刻全集[M].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4.
[17]張憲功.明清山西交通地理研究[D].陜西師范大學,2014.
[18]段自成.清代北方推廣鄉約的社會原因探析[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04):97-100.
[19]王晉麗.明清時期晉商與徽商倫理比較研究[D].山西大學,2020.
[20]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折匯編[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25.
[21]石麟奏為遵議內閣侍讀仙保條奏弭盜安民辦法一折事:乾隆三年九月初六日[B].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宮中朱批奏折04-01-01-0024-017).
[22]秦暉.傳統中華帝國的鄉村基層控制:漢唐間的鄉村組織[J].中國鄉村研究,2003(01):1-31.
[23]田濤,鄭秦,點校.大清律例(卷三十四)[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531.
[24]英廉題為會審山西靈石縣趙張氏等因女張趙氏賭博偷竊不服管教將其勒死一案依律分別定擬請旨事: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十三日[B].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閣題本刑部02-01-007-023486-0010-0000).
[25]黃宗智.清代的法律、社會和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26]田文鏡.撫豫宣化錄[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232.
[27]陸隴其.三魚堂文集[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20:261.
〔責任編輯:包 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