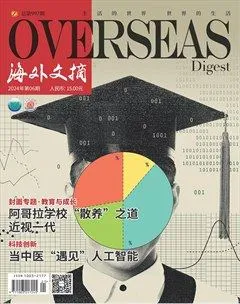一個16歲女孩的減肥手術
一只不理解的熊

| 下定決心 |
2022年秋天,16歲的亞歷珊德拉·杜阿爾特前往休斯頓郊外的得克薩斯兒童醫(yī)院看內分泌科醫(yī)生。她從10歲起就患有多囊卵巢綜合征,最近又患上了前驅糖尿病。醫(yī)生提出了一項可能對她有益的手術。這個手術可以幫助她減輕體重,從而改善與肥胖有關的問題。
亞歷珊德拉笑容靦腆,說話輕聲細語但充滿自信。她說自己“一開始有點懷疑,因為這畢竟是個手術”。但她的母親加布里埃拉·韋萊斯建議她考慮一下。“在我小時候,我媽媽就知道我患上了肥胖癥。”亞歷珊德拉說。
這些年來,亞歷珊德拉似乎嘗盡了一切辦法。她一度不吃碳水,甚至只喝水。她求助于商業(yè)產(chǎn)品,從康寶萊到減肥藥再到代餐奶昔。在絕望和希望的驅使下,她還使用過據(jù)說可以燃燒脂肪的神奇乳液。青春期似乎讓情況變得更糟。她說,醫(yī)生說的話“和別人說的那些話差不多”:按照政府發(fā)布的膳食指南吃飯,多吃蔬菜,什么都可以吃,但不要過量。
母親勤勤懇懇地為她準備飯菜,用她喜歡的方式烹飪蔬菜。亞歷珊德拉自己也盡量少吃,每餐只吃一盤食物。她的直系親屬中幾乎每個人都體重超標,包括她的父親和雙胞胎弟弟,但他們并沒有像她這樣努力作出改變。看著他們吃冰淇淋和蛋糕,她盤里的蔬菜頓時不香了。“我非常喜歡吃甜食。”她說。
嘲笑是從五年級開始的。亞歷珊德拉吃東西時,同學們會盯著她看,對她評頭論足。由于悲傷和焦慮,她尋求過心理咨詢,還為此停學了一個月。高中轉學后,她終于不再受欺凌,但父母知道她仍然深受其害。女兒還能忍受多久?在醫(yī)生建議進行胃腸道減肥手術后,他們咨詢了一些朋友,認為這對女兒來說是一個明智的選擇。但亞歷珊德拉自己并不確定。
這家人見到外科醫(yī)生何塞·羅德里格斯時,他很快就告訴他們,手術不是“捷徑”。事實上,亞歷珊德拉首先必須完成醫(yī)院嚴格且全面的行為和生活作息計劃。該計劃為期六到九個月,它將證明她改善健康狀況的決心,同時也為手術和術后生活作準備。許多青少年覺得這一步太難:據(jù)羅德里格斯估計,預約成功的患者中,只有不到1/3最終接受了手術。對亞歷珊德拉來說,這個計劃里的任務與她已經(jīng)嘗試過的事情差不多:記食物日記、多喝水、制定睡眠時間表。她還被要求鍛煉身體。作為一個喜歡在臥室里跟著韓國流行歌曲跳舞以及常和朋友一起去健身房的人,亞歷珊德拉覺得這也不難,“說實話,我覺得很容易。”
亞歷珊德拉還去看了營養(yǎng)師、心理學家、婦科醫(yī)生和社會工作者,也接受了各種檢查:抽血、超聲、X光、睡眠研究……每就診一次,她就越來越愿意接受手術。亞歷珊德拉說,其他方法從未真正解決問題,“無論減掉多少磅,我都會胖回來,有時甚至胖得更多。這讓我感到氣餒,好像我還不夠努力似的。”
| 肥胖危機 |
美國兒童肥胖率約為20%,而在上世紀70年代,這一比例僅為5%;另有16%左右的兒童屬于超重。隨著兒童年齡的增長,肥胖率也在上升:2至5歲的兒童中,肥胖患病率約為13%;而在青少年中,這一比例超過了22%。亞歷珊德拉身高1.55米,體重95公斤,身體質量指數(shù)超過了重度肥胖的臨界值。如果不接受治療,亞歷珊德拉幾乎不可避免地會一直肥胖到成年。肥胖時間越長,她就越有可能出現(xiàn)慢性健康問題,如關節(jié)疼痛、呼吸和睡眠問題。更嚴重的是,有些肥胖的孩子還會患上曾經(jīng)被認為是成人才會得的疾病:高血壓、糖尿病、脂肪肝。肥胖還會加重心理健康問題:患有肥胖癥的青少年比沒有肥胖癥的青少年更容易產(chǎn)生自殺的念頭。

外科醫(yī)生何塞·羅德里格斯正在給亞歷珊德拉做手術。
重度肥胖癥是青少年群體中增長最快的疾病。疫情期間,美國兒童身體質量指數(shù)的增長率翻了一番,增幅最大的是已經(jīng)超重的兒童。肥胖癥并不只是美國人的專利,在全球范圍內,兒童肥胖癥的發(fā)病率到2035年可能增長一倍。
面對如此嚴峻的事實,美國兒科學會在2023年1月發(fā)布了第一份“臨床實踐指南”,供肥胖兒童的護理人員參考。該學會建議立即開始“健康行為和生活方式強化治療”,并將其稱為肥胖管理的“基礎”;這種方法取代了以前的“觀察等待”策略。身體質量指數(shù)較高的青少年應選擇藥物治療,嚴重肥胖者還可選擇手術治療。該指南的主要作者莎拉·漢普爾向我講述了長達數(shù)年的審核過程。她說:“這是一份循證指南,沒有超出證據(jù)范圍的內容。”
司美格魯肽是用于減肥的最新藥物之一。就在美國兒科學會發(fā)布指南前不久,該藥物被批準用于12歲及以上的青少年。這類藥物似乎提供了一種很有前景的治療方法,但眼下還無法知道它們是否會在青少年中廣泛使用。此外,我們還不清楚這類藥物能否治療嚴重肥胖癥;就目前而言,外科手術仍然是治療嚴重肥胖癥最有效的方法。手術更加成熟,過去十年接受減肥手術的青少年顯著增加。
這些建議一經(jīng)公布,其篩查和治療方法就遭到了猛烈批評,尤其是司美格魯肽等藥物和亞歷珊德拉選擇接受的手術。批評者稱,這些方法過于激進,使兒童的身體受到不必要的審視和操縱,可能會扭曲他們對自我的看法,而且治療手段可能導致進食障礙,造成的損害更甚于肥胖本身。一些批評者質疑身體質量指數(shù)這種存在爭議的標準,稱醫(yī)生根本不應診斷兒童肥胖癥。但漢普爾強調,“是否接受治療取決于患者的家庭”,而不是醫(yī)生。

亞歷珊德拉在得克薩斯兒童醫(yī)院等待手術。
2023年6月,亞歷珊德拉抱著有軟軟耳朵的白色毛絨玩具和印有灰色刺猬圖案的紅色毯子,在術前準備區(qū)等待。她很緊張,但“沒有媽媽那么緊張”。加布里埃拉點點頭,說:“我可能想得太多了。”亞歷珊德拉的父親靜靜地坐在她身邊。她在素描本上畫畫,讓自己保持忙碌,最后她把臉埋進了毛絨玩具里。
| 基因突變 |
體重的頑固性可以歸因于我們的生理結構。哥倫比亞大學醫(yī)學中心兒科分子遺傳學部主任魯?shù)婪颉とR貝爾說,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學會了抵御身體脂肪流失,這樣才不會滅絕。科學家們仍在努力解密這一進化過程。根據(jù)已經(jīng)存在半個多世紀的“節(jié)儉基因”假說,我們體重增加并保持下去是為了幫助我們熬過周期性饑荒。現(xiàn)在,人類的生存不再那么需要躲避捕食者,隨機的基因突變使我們的體重上限越來越高。如今,我們的大腦可能會調節(jié)體重,使其保持在上下閾值之間。畢竟,饑餓帶來的直接危害比肥胖更大。萊貝爾說:“你無法通過限制卡路里讓一個人長期維持較低的體脂水平。”
神經(jīng)科學家、《饑餓的大腦》一書的作者斯蒂芬·居耶內特說,我們的大腦“無意識地維護著較高的體重”,甚至為此讓新陳代謝放緩。位于大腦深處的下丘腦主宰著這個嚴格調控的系統(tǒng)。下丘腦和杏仁差不多大小,主要負責判斷我們是否饑餓,并據(jù)此促使我們增加或減少食物攝入量。它還幫助控制新陳代謝。下丘腦對來自身體各部位(包括脂肪細胞和內臟)的信號作出反應,其中一種信號是瘦素。當身體脂肪增加時,脂肪細胞會釋放更多的瘦素,這個瘦素信號會傳遞到下丘腦,向大腦發(fā)送一個“飽腹”信號,告訴我們身體已經(jīng)儲存了足夠的能量,不需要再進食了。
少數(shù)嚴重肥胖的兒童天生缺乏瘦素,這是劍橋大學代謝科學研究所教授薩達芙·法魯基發(fā)現(xiàn)的一種基因突變。他們的胃口就像無底洞。法魯基認為,這種突變的極端影響清楚地體現(xiàn)了生物學對食欲的“強烈”作用。當法魯基向這些兒童注射瘦素后,他們的食量變小了,過多的瘦素甚至使他們完全停止進食。法魯基說:“我們可以通過瘦素的注射劑量來控制他們的進食量。”換句話說,食欲并不完全受我們的意識或意志力控制。在食物攝入受到限制時,胃饑餓素分泌增加,從而使我們吃得更多。另一種重要的激素是胰島素,它幫助我們把攝入的食物轉化為能量,并控制血糖等影響我們進食量的物質。
“饑餓絕對是一種本能,”居耶內特說,“我們無法決定自己是否會餓,是否會渴望進食。”雖然我們可以控制一餐或一周的食物攝入量,但我們無法控制一生中的每一次進食。我們大腦中與下丘腦密切相關的獎賞系統(tǒng)也會鼓勵我們尋找高熱量食物。“大腦可以通過很多不同的方式偷偷攝入卡路里。這些調控系統(tǒng)的觸須無處不在。”

肥胖患兒需均衡膳食,嚴格限量。
遺傳因素對兒童體重的影響可能達到70%甚至更高。單基因突變極為罕見。代謝科學家法魯基指出,幾乎所有肥胖癥兒童都是“多種不同基因變異的累積效應而導致食欲大增”。截至目前,我們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大約1000種基因變異,其中大部分會影響食欲和饑餓感,可能還有成千上萬種變異有待發(fā)現(xiàn)。法魯基說,每種變異的影響可能都不大,最多可能導致一個人比另一個人重兩三公斤,“但累積在一起,或許就能解釋為什么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發(fā)胖”。
| 肥胖外因 |
但是,如果我們的基因在上個世紀沒有發(fā)生重大變化,那么為什么孩子們會越來越胖呢?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我們的基因與周圍環(huán)境在進化過程中出現(xiàn)了不匹配。肥胖癥患兒通常具有更高的肥胖遺傳風險,即便這種風險不一定顯現(xiàn)。法魯基說:“環(huán)境很可能揭開了他們的遺傳易感性。”他們周圍環(huán)境的最大變化是他們所吃的食物。以前的食物成分與現(xiàn)在不同,數(shù)量也更有限。遺傳學家萊貝爾提到了“人類環(huán)境的變革”,并指出我們的基因“變化得不夠快,尚未適應過去75年的發(fā)明”。現(xiàn)成食物數(shù)量大大增加,吃東西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比如,打開手機應用程序或者去“免下車”快餐店。許多美國人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想什么時候吃就什么時候吃。
如今,兒童吃的食物中近70%是超加工食品,食品界常用的分類系統(tǒng)將其定義為“大多使用工業(yè)專用配料、通過一系列工業(yè)技術和工藝制作而成”的食物。這些食物是我們曾祖父母從沒吃過的東西:薯片、能量飲料、即熱食品。它們被認為是導致大量兒童患上肥胖癥的重要原因,它們似乎讓我們吃得更多。美國國立衛(wèi)生研究院發(fā)現(xiàn),即使飲食中的熱量、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脂肪、糖、鹽和纖維都是定量的,但如果這些食物是超加工食品,被要求自由進食的受試者仍然會在不知不覺中平均每天多攝入500卡路里的熱量。
紐約大學營養(yǎng)學名譽教授瑪麗昂·內斯特爾說:“任何孩子都會選擇超加工食品。”她認為,食品營銷管制放松應追溯到里根總統(tǒng)時期,“1980年后,孩子們成為了目標群體。”公司開始積極地向孩子們推銷產(chǎn)品,因為他們容易受影響,而且是潛在的終身顧客。超加工食品對父母也很有吸引力:它們價格便宜,可以在食品柜和冰箱中保存數(shù)年。“所有食品公司都在努力銷售產(chǎn)品,”內斯特爾說,“這就是體制,如果這種體制讓孩子變胖,抱歉,無心之過。”

13歲的德魯·基思靠改變生活方式減掉了9.5公斤。
過去幾十年,一些超市的食品種類從7000種增至40000多種。哈佛大學醫(yī)學院兒科教授、波士頓兒童醫(yī)院肥胖預防中心聯(lián)合主任戴維·路德維格說,這些現(xiàn)代工業(yè)產(chǎn)品根本就不是食品,“家長和我們所有人都應該反擊,不要讓這成為常態(tài)。”美國兒科學會敦促醫(yī)生們“向政府提出更多要求”,以改善出售給兒童的食品。哥倫比亞對超加工食品征稅;智利出臺法規(guī),限制在學校銷售、在廣告中宣傳超加工食品。然而,北卡羅來納大學營養(yǎng)學教授巴里·波普金認為,美國不會很快頒布類似政策,“我們需要一個大膽的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局,而不是這些不想得罪人的軟弱官僚。”
| 減肥手術 |
在得克薩斯兒童醫(yī)院,亞歷珊德拉在手術室里睡著了。她躺在傾斜的病床上,腳低于頭。主刀醫(yī)生羅德里格斯戴著一頂史努比花帽子,身穿手術服,在亞歷珊德拉的腹部開了五個半英寸的切口。手術室里播放著輕柔的音樂。羅德里格斯向切口里塞入迷你攝像頭和手術工具。亞歷珊德拉的內臟出現(xiàn)在手術室的四面屏幕上。
亞歷珊德拉的肝臟邊緣因脂肪堆積而變得圓潤。羅德里格斯推開一堆堆軟黏的黃色脂肪,露出胃部。粉紅色的胃布滿了紅色血管,像細樹枝一樣。麻醉師把一根胃鏡從亞歷珊德拉的口腔伸進胃里。羅德里格斯現(xiàn)在可以直接觀察胃內的情況,并用手術器械對胃組織進行切割和縫合。接下來是他認為最困難的一步:從一個微小的切口中取出切除的器官(約占整個器官的80%)。為確保剩下的胃部已經(jīng)完全縫合,麻醉師通過胃鏡向胃里注入空氣。現(xiàn)在,亞歷珊德拉的胃就像一只纖細的襯衫袖子(袖狀胃切除術因此得名)。羅德里格斯將水灌入她的腹部,如果出現(xiàn)氣泡,表明胃的某個部位還有縫隙。結果,水靜止不動。手術在一小時內完成。亞歷珊德拉的大部分胃現(xiàn)在放在一個托盤上,冰涼而暗沉。

醫(yī)生給17歲的蓋奇· 羅賓斯開了司美格魯肽。
在另一個房間里,明亮的淺綠色墻壁上掛著兒童的繪畫作品,亞歷珊德拉的父母坐在橙色的椅子上等待。羅德里格斯用西班牙語告訴他們:“沒有失血,很好。”在術后區(qū),亞歷珊德拉的麻醉剛過,不停地扭動著身體。每動一下,她都感到疼痛。加布里埃拉說:“看到她這個樣子,我很難受。”她用手撫摸著女兒的額頭,懇求她躺著別動。亞歷珊德拉發(fā)出了一聲呻吟。
羅德里格斯告訴我:“一開始,醫(yī)院的業(yè)務人員認為手術量不夠,不能為此專門建立項目。但顯然,事實并非如此,而是恰恰相反。”2010至2017年間,全美接受減肥手術的青少年人數(shù)翻了一番多,而且還在繼續(xù)增加。“青少年肥胖手術縱向評估”項目的數(shù)據(jù)顯示,接受減肥手術的青少年體重減輕的情況與成年人差不多:身體質量指數(shù)大約下降了25%。這些青少年中約90%在術前需要服用控制糖尿病的藥物,但術后均不需要;術后五年,與成年后再接受手術的患者相比,這些青少年的糖尿病、高血壓等病癥更有可能得到緩解。項目主要研究員托馬斯·英奇說:“對患有這兩種疾病的青少年來說,及早進行手術比等到成年后再手術更有利。”數(shù)據(jù)顯示,即使在手術十年后,它也能帶來長期益處。此外,青少年患者的術后并發(fā)癥似乎并不比成年患者更多。
| 術后變化 |
密歇根大學生理學和內分泌學教授蘭迪·西利從分子層面研究減肥手術的效果。他說:“病人的體重減輕了,與此同時,他們也不那么餓了。”西利強調,體重減輕并不僅僅是因為變小的胃限制了進食量,許多化學變化也是原因之一。起到關鍵作用的似乎是膽汁酸和腸道中的抗菌肽,這兩種物質在術后都出現(xiàn)了明顯增加。西利還在梳理這兩種物質發(fā)揮作用的確切機制。另外,袖狀胃切除術切除大部分胃組織的同時,也切除了分泌饑餓素的區(qū)域,而饑餓素水平的降低會減少食欲。“減肥手術之所以如此有效,是因為很多因素都發(fā)生了變化。”西利說。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掃描結果顯示,術后患者大腦中對食物線索的反應似乎與節(jié)食患者不同,這點主要體現(xiàn)在下丘腦周圍以及獎賞和認知控制區(qū)域。不過,改變腸道解剖結構是如何改變大腦的,這仍然是一個神秘的現(xiàn)象。西利認為,這基本還是“一個黑箱”。這似乎讓所有人都感到驚訝,甚至包括做手術的醫(yī)生。“我只是一名普通的胃腸外科醫(yī)生,”英奇說,“從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接觸腦外科的知識。但是,嘿,事實似乎就是這樣。”
只有極少數(shù)符合條件的重度肥胖青少年真正接受了手術。他們面臨的障礙難以逾越:尋找兒科減肥外科醫(yī)生,經(jīng)歷漫長而艱辛的保險授權過程——這還是在保險覆蓋手術的前提下。英奇說:“我們見過各種拒絕批準兒童手術的把戲。”
有些父母迫切希望幫助掙扎中的孩子,只能在沒有保險的情況下選擇讓孩子接受治療。2021年,阿凱莎·斯特德斯蒂爾服藥自殺未遂,之后她和母親阿納斯塔西婭從佛羅里達州趕往墨西哥蒂華納接受減肥手術。這次旅行費用(包括手術費)約為6500美元。阿納斯塔西婭說:“人們質疑我為什么把她帶出國做手術,但他們不知道我們經(jīng)歷了什么。她被霸凌,幾天不吃飯,要自殺。”2023年夏天,阿凱莎告訴我,她的體重減輕了1/3。她穿著一件黑色交叉吊帶上衣,笑著收拾房間,即將去佛羅里達州立大學開始新生活。她說:“除了放棄,還有其他選擇,不用節(jié)食把自己餓死。”
| 影響一生 |
盡管肥胖癥的治療可能伴隨著風險,但醫(yī)療機構的普遍態(tài)度是,肥胖癥的潛在負面影響過于明顯、不容忽視。安德魯·斯托克斯是波士頓大學的人口學家和公共衛(wèi)生專家,他在研究人們的體重史并充分考慮到吸煙和疾病等重要因素后發(fā)現(xiàn),肥胖與壽命明顯縮短有關。他說,研究無法預測每個患者未來會怎么樣,但會揭示“概率和相對風險”。他補充說,肥胖是“一個累積的過程”。
“博加盧薩心臟研究”是持續(xù)時間最長的流行病學研究之一。它在20世紀70年代招募了一批兒童作為研究對象,并一直跟蹤研究到他們中年時期。該研究發(fā)現(xiàn),兒童肥胖與心血管和腎臟變化存在關聯(lián),而這些變化會在兒童成年后發(fā)展成疾病。基層兒科醫(yī)生萊拉·莫納漢把身體質量指數(shù)作為一種篩查工具來幫助預防疾病。她說,為什么要等到異常情況出現(xiàn)后再采取行動呢?“這就像說某人有高血壓,但沒有心臟病發(fā)作,那我們?yōu)槭裁催€要測量他的血壓呢?”

6歲的阿里亞·湯普森體重一直在增加,其血液檢查結果顯示前驅糖尿病相關指數(shù)異常。
“我更自信了,我再也不想躲在夾克或連帽衫里了。”亞歷珊德拉告訴我。手術四個月后,她的體重減輕了20多公斤,她很高興能在返校節(jié)上第一次穿上裙子。亞歷珊德拉的母親說:“我為她感到驕傲。她現(xiàn)在狀態(tài)特別好。”
亞歷珊德拉的健康狀況改善了,這意味著她可以停止服用糖尿病藥物。與所有接受減肥手術的患者一樣,她余生將一直服用維生素,部分原因是她的胃腸道發(fā)生了改變,不能有效地吸收營養(yǎng)。她在16歲作出的決定將影響她的一生。
在肥胖癥專家法蒂瑪·斯坦福看來,這是一件好事:以這種方式改變亞歷珊德拉的健康是臨床醫(yī)生應該采取的辦法。十多年來,斯坦福一直在使用美國兒科學會推薦的許多治療方法。有些患兒推遲接受更有效的治療,然后長大成為了肥胖癥患者,這可能會對他們的健康造成更大的危害,也更難治療。斯坦福希望在患者還年輕的時候就打斷其疾病的進展,“很多人仍然有一種非常強烈的觀念,認為如果不是靠節(jié)食和運動減下來,就一定是失敗者。”如今,像亞歷珊德拉這樣的兒童能夠獲得更有效的治療方法,也可以過上更長壽、更健康的生活,這也正是美國兒科學會發(fā)布如此全面而緊迫的指南的原因。

18歲的塔奇拉·愛德華茲患有糖尿病、高血壓和多囊卵巢綜合征。
亞歷珊德拉仍然堅持鍛煉,但在繁重的高二課業(yè)和日常鍛煉之間很難取得平衡。手術后,和家人出去吃飯沒有以前快樂了,因為她現(xiàn)在很容易感到飽。即使菜肴味道鮮美,她想多吃點,也吃不下,因為她已經(jīng)不餓了。糖會讓她感到惡心,所以即使有時很想吃甜食,她也會盡量避免。亞歷珊德拉說,手術前她非常沮喪,為減肥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卻感覺“一事無成”。而現(xiàn)在她說:“看到自己付出的努力終于有了結果,我感到很振奮。”
編輯: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