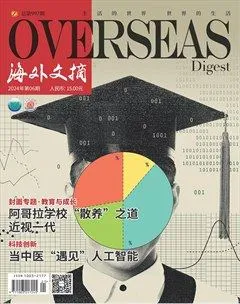近視一代
一只不理解的熊

| 全球趨勢 |
從事驗光工作十年后,瑪麗娜·蘇注意到,來到她診所的孩子們有些不同尋常。越來越多的孩子需要戴眼鏡,而且年齡越來越小。其中不少孩子的父母視力都很好,他們對孩子視力下降感到困惑。老實說,瑪麗娜·蘇也不知道原因。
她所受的教育告訴她,近視是一種遺傳病。幾十年來,美國的教科書一直是這樣寫的:父母有一方近視,孩子需要戴眼鏡的幾率會增加一倍;如果父母雙方都近視,孩子戴眼鏡的幾率就會增至四倍。多年來,她診斷過的很多近視孩子的父母確實都是近視眼。她告訴我,這些父母往往會嘆氣:哦,不,他們可別也近視啊!但是,情況正在惡化。這一代孩子的視力突然變得比他們父母更差。瑪麗娜·蘇看到了越來越多沒有遺傳因素卻近視的孩子,她曾問自己:“如果近視只是遺傳的,那為什么這些孩子也會近視?”
瑪麗娜·蘇注意到的這個現象其實世界各地都有。在東亞和東南亞,這種轉變最為明顯:短短半個多世紀里,該地區青少年和年輕人的近視比例從大約25%躍升至80%以上。
美國上一次進行全國范圍近視調查是在本世紀初,12至54歲群體中有42%近視,而這一數據在上世紀70年代只有25%。雖然沒有近幾年的大規模調查數據,但我詢問過美國各地的眼科醫生是否看到了更多近視的孩子,得到的答案是:“當然”“的確”“毫無疑問”。
在歐洲也是如此。與父輩和祖輩相比,現在的年輕人更有可能需要佩戴眼鏡。非洲和南美洲的一些發展中國家近視率最低。據估計,如果目前的趨勢繼續下去,到2050年,全世界將有一半人口近視。
這一趨勢所帶來的后果不僅僅是近視兒童數量激增。近視患者在中年時更容易出現青光眼和視網膜脫落等嚴重問題,而這些問題又可能導致永久性失明。一開始風險很小,但度數越高,風險就呈指數級增加。近視的年齡越小,以后的情況就越不容樂觀。2019年,美國眼科學會召集了一個特別工作組,將近視視為一個緊迫的全球衛生問題。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眼科學教授、美國眼科學會政府事務醫學主任邁克爾·雷普卡說:“我們正在試圖阻止幾十年后的失明大流行。”
| 復雜成因 |
我們視力顯著下降的原因似乎顯而易見:環顧四周,你會看到無數孩子沉迷于手機、平板電腦和筆記本電腦。眾所周知,長時間近距離用眼會消耗遠視儲備。400年前,德國天文學家約翰內斯·開普勒認為自己視力不佳的部分原因是長時間學習。過去,英國醫生發現牛津大學學生的近視率比部隊新兵更高,學風嚴謹的城鎮學校的學生近視率比農村學校更高。19世紀晚期的一本眼科手冊甚至建議避免一切用眼工作來治療近視——“如果可能的話,去海上航行”。
20世紀初,專家們一致認為,近視是由“近距離工作”引起的,包括閱讀和寫作以及如今的看電視和刷手機。舊金山灣區的驗光師利昂德拉·容說:“很久以前,人類是狩獵者和采集者。”我們依靠敏銳的遠視力追蹤獵物、尋找成熟的水果。但現代生活基本是近距離的室內活動。“我們通過外賣軟件覓食。”
這個解釋符合直覺,但很難證實。“每有一項研究證明近距離用眼對近視的影響,就有另一項研究推翻這個結論。”加州圣布魯諾市的驗光師托馬斯·阿勒說。看書和看屏幕的時長似乎無法完全解釋近視的發生和加重。
一些理論急于填補這片真空:或許研究中的數據是錯的——受試者沒有準確記錄自己近距離用眼的時長;或許近距離用眼期間是否短暫休息比用眼總時長更重要;或許毀掉視力的不是近距離工作本身,而是它剝奪了孩子們戶外活動的時間。主張戶外活動重要性的科學家又分為兩派:一派認為促進眼睛發育的是明亮的陽光,另一派認為是廣闊的空間。
現代生活中有些東西正在破壞我們的遠視力,但到底是什么?這個問題會讓你陷入各種科學解釋的迷宮,我就遇到了這種情況。我曾向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視光學教授克里斯汀·威爾德索特詢問各類近視理論在生物學上的合理性。在兩個小時的談話中,她多次停下來指出接下來的內容很有爭議。但她也表示,這些理論本質上是一枚硬幣的兩面:近距離工作很久的人本來也不會花太多時間在戶外。無論哪種理論是正確的,關于保護孩子視力的實際結論都是:少看屏幕,多參加戶外活動。

現在,科學家們已經不再相信近視純粹由遺傳決定。這一觀點在上世紀60年代大行其道,并在學術界流行了幾十年,因為當時的研究表明,同卵雙胞胎在近視方面比異卵雙胞胎更相似——前者具有相同的遺傳背景,后者則不然。基因的確在近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棘手的問題在于,同卵雙胞胎不僅擁有相同的基因,還受到許多相同的環境刺激。
眼鏡、隱形眼鏡和激光手術都能幫助近視者看得更清楚,但這些方法無法從根本上糾正近視的解剖學問題。健康的眼睛像一個球體,而近視的眼睛像一顆橄欖。要減緩近視加劇,就必須阻止眼睛變長。我們已經知道如何做到這一點,那就是“近視控制”,或者叫“近視管理”。
| 控制措施 |
過去20年里,亞洲的眼科醫生發現特殊鏡片和眼藥水可以減緩兒童近視加劇。近視研究專家瑪麗亞·劉告訴我,她第一次對近視產生興趣是在十幾歲的時候,當時她在天才兒童學校看著同學們一個個戴上了眼鏡。學校競爭激烈,她記得自己從早上六點半到晚上十點幾乎都在室內學習。大學畢業時,和其他幾乎所有同學一樣,她也戴上了眼鏡。
幾年后,她開始作為眼科住院醫師實習,遇到了許多佩戴角膜塑形鏡(OK鏡)的年輕患者。這種夜間佩戴的隱形眼鏡會改變角膜的形狀,使光線在白天更準確地聚焦于視網膜,從而實現暫時性的視力改善。瑪麗亞·劉注意到,戴角膜塑形鏡的人似乎比戴眼鏡的人視力更好。長期使用角膜塑形鏡能否在某種程度上防止眼球老化,進而阻止近視加劇?事實證明,亞洲的其他科學家和醫生也注意到了同樣的趨勢。2004年,一項有關角膜塑形鏡的隨機對照研究證實了瑪麗亞·劉的預感。
那時,她在伯克利攻讀視覺科學博士課程,研究近視問題。她的同學們都在研究基因治療和視網膜移植等聽起來很高端的課題,不明白她為什么要研究“這么無聊的東西”。最后,她來到威爾德索特教授的實驗室工作,研究小雞的近視問題。
大多數人類嬰兒天生遠視。我們的眼軸一開始有些短,在童年時長到合適的長度,然后停止生長。經過數百萬年的進化,這一過程已非常精確。眼睛進化后期望看到的是自然光線和遠距離視覺,如果環境信號錯誤——不管是由于近距離工作過多、戶外活動時間不足、兩者兼有還是其他因素——眼軸就會不斷變長。這個過程是不可逆的。瑪麗亞·劉說:“你無法讓變長的眼軸縮短。”不過,你可以通過抵消錯誤的信號來阻止眼軸變長,這就是近視控制的目的。
獲得博士學位后,瑪麗亞·劉成為了伯克利大學的一名助理教授,她開始設想建立美國第一家近視控制診所,在研究和實踐之間架起一座橋梁。
學校行政官員對此持懷疑態度。眼科中心的臨床主任認為,此類診所不會給視光學專業的學生帶來好處,也不會吸引到足夠多的患者,獲得經濟回報。但在2013年,瑪麗亞·劉還是憑一己之力創辦了伯克利近視控制診所。她在周日借用檢查室接診,不收取額外報酬,也沒有放棄任何教學或臨床任務。幾個月內,她的日程表就排滿了。現在,這家診所每周開診四天,有1000名患者前來就診——其中一些人驅車數小時穿過灣區的車流來到這里。
| 亞裔焦慮 |
2022年春天的一個周六早上,我到達診所時,校園里其他地方還很安靜,但診所內已經擠滿了在這里接受培訓的視光學專業學生和住院醫師。身材嬌小、留著整齊波浪卷發的瑪麗亞·劉在診所里穿梭,效率驚人。前一刻,她還在檢查患者眼睛;下一刻,她已經在安撫一位家長;后一刻,她又告訴工作人員打印機出了故障。
診所提供三種治療方法:角膜塑形鏡、多焦軟鏡和阿托品滴眼液。前兩種療法可以改變眼球的光學特性,產生讓眼軸停止變長的信號;而阿托品是一種藥物,低劑量的使用似乎能通過化學方式改變眼球的生長通道。這些療法可將近視發展速度平均減緩50%左右。2021年,美國驗光協會的循證委員會向其成員發布了一份關于如何使用近視控制方法的報告。不過直到最近,這些療法仍未被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用于近視控制。在美國,這些療法只能算作“超適應癥用藥”,換言之,醫生可以在特定情況下自行決定是否采用。因此,使用這些療法的前提是找到合適的醫生。
瑪麗亞·劉的診所在亞裔人口眾多的灣區取得了初步成功,這并非巧合。我在美國多個城市采訪過的眼科醫生都說,前來要求控制孩子近視的家長通常是亞裔。我在診所遇到的家長中,亞裔確實占了很大比例。很多人是從其他移民或亞洲朋友那里聽說近視控制的。
瑪麗亞·劉還有一部手機,用于管理三個聊天群,群里是北美地區孩子接受近視控制的家長。問題不分晝夜地涌來。“我早上起來的第一件事就是看這個聊天群:誰丟了鏡片?誰的眼睛紅了?誰還有其他問題?”她說,“然后臨睡前再看一遍。”她和一位患者家長一起建立了第一個群。在達到群成員人數上限后,他們創建了第二個和第三個群。現在,三個群里共有1500名家長。
| 治療前景 |
灣區的收入中位數較高,這也是該地成為近視控制沃土的另一個原因:治療費用昂貴。我在診所遇到的許多家長都是工程師或醫生。在伯克利,一副角膜塑形鏡的價格超過450美元,初次驗配費用1600美元,這還不包括每年多次復診的費用。軟性隱形眼鏡一年的費用從幾百美元到1000多美元不等。阿托品滴眼液一年的用量也要數百美元。孩子的近視控制通常要到十幾歲或二十出頭才結束。這些治療不在醫保范圍內。
跨國眼保健公司如今將近視控制視為一個炙手可熱的潛在市場。它們正在爭取獲得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對新型鏡片和阿托品改進配方的批準,后者可以獲得專利,而不是作為更便宜的非專利藥出售。商業動機顯而易見:如果到2050年全球一半人口近視,那將是一個巨大的潛在客戶群。“我們從未遇到過這樣的商機。”“視鏡”光學公司前首席醫療官喬·拉蓬說。這家加州小公司的近視控制技術已被眼科保健巨頭庫博光學和依視路聯合收購。
2019年11月,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了美國第一種專門用于減緩近視發展的治療方法——庫博光學生產的一種名為“美視”的軟性親水接觸鏡。另外,還有更多的療法正在美國進行試驗,其中包括幾種改變眼球光學特性的眼鏡。有的已經在歐洲和加拿大上市。伊利諾伊州迪爾菲爾德的驗光師巴里·艾登說,這些眼鏡一旦在美國獲批,“將打開近視治療的閘門”。他解釋道,越早開始減緩兒童近視的發展,效果就越好。
瑪麗亞·劉告訴我,她希望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批準在未來能促使視力保險至少部分覆蓋近視控制,讓更多家長負擔得起這種治療。與此同時,庫博光學加大了“美視”的營銷力度。在我居住的布魯克林公園坡社區,一家驗光店最近掛出了“美視”的大幅廣告,上面有兩個面帶微笑的孩子。舊金山市中心的一位驗光師告訴我,看過“美視”廣告的家長現在都會到她的診所點名咨詢。對近視控制來說,口碑時代正在結束,大眾廣告時代已然開啟。
在驗光配鏡行業,近視控制常常與正畸相提并論——希望為孩子提供最好條件的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父母不惜為此花費數千美元。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比較也很貼切。正畸也是一種針對現代病的現代解決方案。人類學家驚奇地發現,穴居人的牙齒整齊得令人難以置信。當我們的祖先從咀嚼生肉和蔬菜轉為食用煮熟、加工過的谷物后,考古記錄中才出現了歪牙。現在,我們的頜骨因用得太少而變弱,牙齒也更加擁擠和歪斜。而正畸是我們對不適應現代生活的身體進行改造的方式。
我們可能還不清楚整天盯著屏幕和長時間待在室內對我們有什么影響,也不知道哪個因素對我們的傷害更大,但我們明確知道的是,近視顯然是我們的生活方式與生物構造相悖的結果。我采訪過的驗光師都說,他們努力推動人們養成更好的用眼習慣,比如限制看屏幕的時間和進行戶外活動,但也只能到此為止了。如今,讓青少年遠離手機可能與讓嬰兒吃生肉一樣不切實際。
正因如此,我們陷入了當下的困境:每天往眼睛里放置化學物質和塑料片,希望欺騙眼球回到自然狀態。
編輯: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