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荒涼的魚薯店
2024-06-01 00:00:00武陵驛
江南
2024年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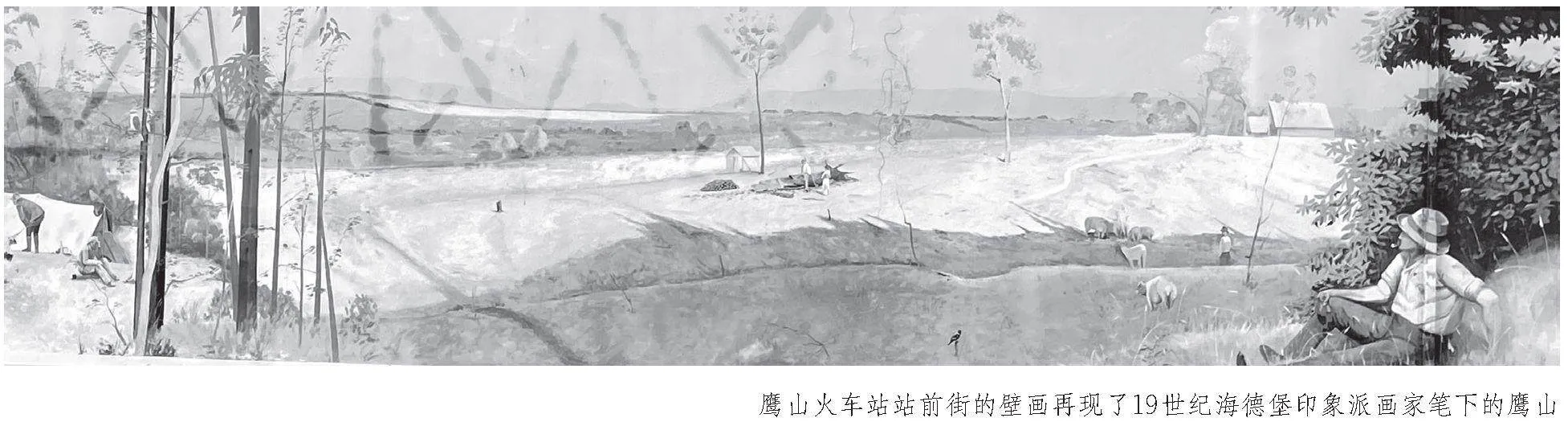
一
當心臟生病,我感受到了來自胸腔深處的不規則悸動。這些日子以來,從日常繁忙生活里消失了的是我,坐在窗下琢磨光影移動了多少的是我,閑到有心思重讀《福爾摩斯探案集》《人生的枷鎖》和《人間失格》,甚至開始爬梳比人生還要漫長的《追憶似水年華》。自秋季突然患病以來,生理上心理上的雙重荒蕪,讓我每天只剩下一種運動:出門散步,數點黃葉落在山道上。
在奧斯丁醫院,有時候,醫生護士問我的職業,我總是說我寫東西。有時候,他們也會有興趣追問下去,我會告訴他們我寫了什么在寫什么,但寫作即便是種職業,他們也不會放我離開,仿佛認定了我的職業是病人。他們沒有錯,我現在是專業患者。對于心臟病患者,離開奧斯丁醫院的安全是有條件的。我必須成為一個居家病人(out-patient)。作為居家的專業患者,我不能擅自獨立行動,即使散步,也須兩人同行。
那次下山散步,是與表情慣常很酷的兒子內森一起。他沉默,步速盡量配合我。他的耳機里充斥日本流行音樂,頭腦里盤旋著與大學工業設計課程無關的東西,我不管他是不是聽進去,指向那個畫著魚和鷹的小小店面說,瞧,世界上最荒涼的魚薯店。
我們就是這樣發現了山腳下這家世界上最荒涼的魚薯店。其實,這家店開了好多年,但以前我總是行色匆匆,無數次到車站到郵局,經過店門口,不過頂多隨意一瞥,如此荒涼的地段,開魚薯店會有什么生意?我的疑問是漫不經心的,這家店居然病病歪歪,開到如今也未倒閉,我有點驚異。……
登錄APP查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