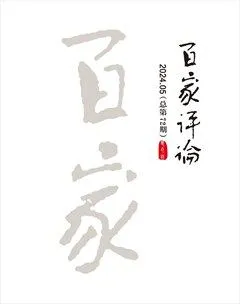歷史轉(zhuǎn)折中的啟蒙神話及其限度
內(nèi)容提要:在《長征》一詩中,駱一禾對20世紀中國左翼革命表達了高度的肯定和贊頌,凸顯了其與80年代“新啟蒙”思潮的某種錯位。但是,駱一禾將革命高度美學(xué)化的思路又顯現(xiàn)出其間的強烈共振,而在這種復(fù)雜關(guān)系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駱一禾的“中國視野”。通過對其詩學(xué)理念的梳理和闡釋,分析其背后的思想脈絡(luò),可以看出:駱一禾既承接和轉(zhuǎn)化了20世紀的革命資源,又將其表述為“絕對的現(xiàn)代”神話,二者之間的連接點則是強烈的“民族新生”意識。這暗示了80年代含混、曖昧、充滿歧義的過渡性特征,也體現(xiàn)了駱一禾作為80年代詩人的典型性。
關(guān)鍵詞:駱一禾 新啟蒙 革命 中國視野
引言
重讀駱一禾的詩歌與詩論,不難發(fā)現(xiàn)其宏大的文明視野、世界想象和對現(xiàn)代文化、線性進化論思維的批判性立場,對浪漫主義詩學(xué)的提倡與80年代詩歌主潮的某種“不合時宜”a,但其所攜帶的理想主義與烏托邦激情又深深契合80年代的文化氛圍b。同時,其在詩中對20世紀中國左翼革命的強烈肯定卻又似乎與“告別革命”的時代訴求并不相稱c。由此,并非僅作為一個詩人(狹義的詩歌創(chuàng)作者),更是作為“新啟蒙”知識分子的一員、作為“正反社會主義經(jīng)驗和現(xiàn)代文明的產(chǎn)物”d,駱一禾在何種意義上想象中國;或者說,經(jīng)由與80年代種種思潮的相悖或契合,駱一禾提請著何種文化資源、達成了怎樣的自我認同,又與歷史和現(xiàn)實建構(gòu)了怎樣的想象性關(guān)系,其間蘊含著怎樣的時代信息?本文試圖從其《長征》一詩e及其他文本切入,對上述問題做出簡要回應(yīng)f,并希望由此勾勒、反思其“歷史與文化意識作為一個特定時代的歷史視角所造就的闡釋世界方式的獨特性”g和局限性。
一、對革命的啟蒙式書寫
對于“長征”這一在20世紀中國左翼革命史上極為重要的轉(zhuǎn)折點,駱一禾在詩中稱其為偉大的“歷史的道路”,作為“中國的心臟”,既區(qū)別于“軍閥和紳士們”和“1840年——1940年”“所有的對外戰(zhàn)爭”,也區(qū)別于“農(nóng)民”歷來的生存狀態(tài),標志著“一種新生”,“寫在亞洲中部”和“世紀的內(nèi)心”。而在該詩的表述中,“長征”之偉大首先即在于“把歷史教給了農(nóng)民”。如果說“由于無產(chǎn)階級的出現(xiàn)才使人們意識到,自由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h,那么也正是由于把握了“歷史”的“農(nóng)民”主體的出現(xiàn),使人們意識到20世紀中國左翼革命的獨特性與有效性。如果參照李澤厚在其影響深遠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一文中將20世紀中國的“文化啟蒙”與“政治救亡”相對立的二分法,駱一禾的這種表述無疑顯現(xiàn)出了與80年代中期的“新啟蒙”思潮的明顯錯位。而從這樣的歷史體認出發(fā),駱一禾對世界的想象也就不同于現(xiàn)代化視野中的“先進—落后”想象,而是被中國獨特的社會主義道路所啟發(fā)/表征的“第三世界”,并寫道:“望著那些久已去世的領(lǐng)袖/第三世界的英雄/在這個年頭我還能說什么呢”。由此,駱一禾頗有意味地區(qū)分了兩類人:一是在現(xiàn)代化意識形態(tài)中作為中心和理想鏡像、在冷戰(zhàn)結(jié)構(gòu)中作為世界另一極乃至參與左翼革命的人,二是與中國當下“在和平里待膩了”而“不懂歷史”的“才子們”,駱一禾甚至將其類比為“軍閥和紳士”“土財主的軍紳政權(quán)”。或許可以說,駱一禾在此展現(xiàn)出一種超越民族國家的、關(guān)于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世界想象,但需要指出的是,基于這首詩的表述,駱一禾的立足點和出發(fā)點是強烈的關(guān)于“中國新生”的意識,并在與中國當下現(xiàn)實的對比和批判中明確地提請著革命的精神資源。但復(fù)雜之處在于,這一“中國”既非所謂“封建歷史”的中國,也并不是以美國為范本的現(xiàn)代化意識形態(tài)中落后的中國和“文革”這一社會主義道路極端化的中國,而是以“長征”作為標識的、處于無產(chǎn)階級革命初期的“中國”。
由此,駱一禾相對于“新啟蒙”思潮的獨特性似乎漸次顯露,但聯(lián)系上文所提及的“長征”“把歷史教給了農(nóng)民”的表述,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這一說法凸顯的首先是革命的啟蒙與烏托邦的面向,而非以暴力破壞與重建秩序的現(xiàn)實面向i。同時,談到“啟蒙”勢必涉及誰啟蒙誰的問題,而在駱一禾的詩中,充當這一啟蒙者角色的是“長征”而非具體的革命者或革命知識分子。如果參照毛澤東在農(nóng)民落后的、封建性的一面和進步的、革命性的一面之間做出的著名論斷:“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nóng)民”,二者在主語和主體想象的微妙錯位之間所蘊含的豐富意味就更為明顯。也就是說,這一對“長征”的人格化、主體化和本質(zhì)化想象所內(nèi)含的問題意識,已然不再是作為革命領(lǐng)袖的毛澤東必須完成的革命動員和政治詢喚、進而建構(gòu)“人民—國家”的歷史任務(wù),而是經(jīng)由對革命歷史的重新敘述與評判,在80年代的時代語境中再次啟動某種整體性的中國想象、并確認這一想象的坐標系的方式。
進而,我們可以引出駱一禾賦予“長征”的另一層內(nèi)涵,即“中國的心臟”這一身體性修辭所攜帶的“生命——中國——長征”同構(gòu)的意味。“處在長征的影響中/不等于了解長征/正像知道苦難/不等于了解苦難/——這種不同是絕對的/哲學(xué)的和血肉的”。顯然,經(jīng)由這種“絕對的/哲學(xué)的和血肉的”區(qū)分,“長征”在此進一步占據(jù)了某種世界觀的地位,而它所天然地呼喚的一個重要概念“人民”,則被駱一禾描述為一個“經(jīng)歷了頻繁的戰(zhàn)爭與革命”卻“未完全兌現(xiàn)”的“歷史地發(fā)展的靈魂”j。由此,一個“繼續(xù)革命”的主體訴求似乎呼之欲出,也可以說:在“中國新生”的強烈意識中,駱一禾將由“長征”所標識的革命視為一次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創(chuàng)世行動,這與其將寫詩視為“創(chuàng)世”k之舉或有異曲同工之妙,其訴求則在于重建對于世界的整體性認知,并在此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新人”。其間值得關(guān)注之處在于,80年代的“革命”已然成為一種體制性話語,而如何經(jīng)由對這一話語的重返與重估,將內(nèi)含其中的烏托邦目標從體制化的權(quán)力機器中剝離,進而重新確立革命的可能性與有效性,或許也正是駱一禾的詩與詩論所蘊含的某種想象。這與丁玲這樣的革命知識分子也有相通之處,即“嘗試通過自我改造和主體修養(yǎng)從內(nèi)部克服這種裂痕,并將自我提升到另一個更高境界。從這個意義上,她始終將‘革命者的自我’視為一個未完成的、展開中的過程。”l
具體到駱一禾這里,這一未完成、或曰持續(xù)生成的狀態(tài)同時被賦予“人民”和“我”,也正展現(xiàn)出其“中國視野”,而這一論述源于其詩論中一個先在的規(guī)定,即個人、進而是抽象的人的生命必然處于不間斷的生成狀態(tài),逐漸走向“滋長、壯大和完美”m。在這一過程中,主體的生成當然具有豐富的可能性,進而包含深廣的歷史容量。而在駱一禾的論述中,這一抽象的“新人”訴求,其實最終落實在了“新詩”、進一步說是“中國新詩”的身上,由此,駱一禾強調(diào)詩歌的文明價值,并認為其應(yīng)該也能夠如古希臘史詩、神話或希伯來神話般為文明的發(fā)展提供奠基性的價值準則與力量n,而這種詩歌將刷新我們感受世界的方式,并“伴生一種特殊的世界觀”,進而塑造“中國大地”所需要的新人o。也正是基于這種認知,駱一禾提出“新詩意識”的說法:在80年代后期“后浪推前浪”的詩歌現(xiàn)場,“古典之美和現(xiàn)代之美同樣經(jīng)受著新詩意識的轉(zhuǎn)化和錘煉”p。“新詩意識”顯然是這一表述中的主體,那么,何謂“新詩意識”?參照駱一禾的相關(guān)論述,或許可以概括為:中國的歷史與現(xiàn)實“對于新生和杰出的中國詩歌的呼喚”,并致力于“使民族的靈魂舒張發(fā)展”q。在這里,民族意識的自覺被同構(gòu)于詩歌意識的自覺,同時,借助這一“生命——詩歌——中國”的坐標系,駱一禾也同樣對五四進行了某種重述。
如果說80年代通過“啟蒙”與“救亡”的二元對立,建構(gòu)了自身最大的神話,即把自己講述為又一個五四,并以此在所謂“現(xiàn)代性”的脈絡(luò)中確立了自己的合法性r,駱一禾也部分地借用了這一話語策略。具體來說,駱一禾借用魯迅的表述,將80年代指認為與五四同樣充滿緊迫感的、方生方死的大時代,“中國文明在尋找新的合金,意圖煥發(fā)新的精神活火”s。由此,駱一禾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tǒng)的激烈批判,事實上“闡揚的是對于文字、語言的精神看待的態(tài)度”t,而作為新文化運動重要標志的新詩之所以確立,則“是由于它隸屬于白話文運動而成為偉大的開端。也就是說,新詩由一個偉大的文化運動(也是救亡運動)作為標志而立極”u。顯然,五四這一中國現(xiàn)代歷史的“起點”,在此種表述中被高度詩歌化、美學(xué)化了,而“隸屬于”這一行動的新詩所攜帶的能量,則不僅是“藝術(shù)”的,同時也是“政治”的,即“它替代自己的批判對象而成為新的政治理想的化身”v。與其說,這種生命本體論式的歷史觀與詩歌觀,超越了將文學(xué)與政治相對立的理解方式,將純粹的審美原則擴大到社會與歷史中去,并以此完成了對民族精神的重塑和對世界的整體把握,進而重新想象、設(shè)計中國的未來,毋寧說,這種與激進的美學(xué)理念相伴生的“歷史感”,通過“詩歌——中國——新人”的同構(gòu)而試圖作用于“普遍”的個人生命及其感性w,進而召喚著那些漂浮于特定時空中、攜帶著烏托邦沖動的個體。這種美學(xué)化、審美式的解放方案中或許攜帶著80年代“詩化哲學(xué)”的身影x,暴露出駱一禾作為“新啟蒙”知識分子的重要側(cè)面,同時,這一“內(nèi)面的人”與文學(xué)(詩歌/審美)和“中國”的同構(gòu),也清晰地展現(xiàn)出了駱一禾的詩及詩論作為典型的現(xiàn)代文學(xué)的特征y。
因此,正如上所述,與其說駱一禾所召喚的是中國革命,不如說是對整體性的民族啟蒙的想象(兩者也正是在塑造新人、改造民族的層面保有歷史邏輯上的契合),而詩人、詩歌則在其中被賦予了結(jié)構(gòu)性的重要位置。但問題在于,駱一禾將革命重新命名為對民族的啟蒙,一方面遮蔽了革命和民族的復(fù)雜性,簡化了革命對革命者/革命知識分子與民眾、社會在不斷變動的歷史語境中彼此糾纏的張力,也抹去了革命在這一過程中對新的倫理關(guān)系、社會組織的探索與困境;另一方面,其將革命書寫為對民族和人民的啟蒙,認為民族、人民和“我”都始終處于持續(xù)生成的狀態(tài),但卻并沒有回應(yīng)這種生成的條件、路徑和方式究竟是什么,而是將之描繪為想象性的烏托邦,也因此,這一想象在理論層面充滿了不穩(wěn)定性。所以,駱一禾才需要塑造一個絕對、本質(zhì)的關(guān)于“生命”的神話,來支撐這一論述,即其所謂“情感本體論的生命哲學(xué)”z。
二、“生命詩學(xué)”與神話式的啟蒙主體
駱一禾將自己的思想體系稱為“情感本體論的生命哲學(xué)”,而一個關(guān)于此的簡單描述是:借用弗洛伊德對人類意識結(jié)構(gòu)的分析與榮格對“原型”的相關(guān)論述,駱一禾提出:在生命的整體構(gòu)造當中,“自我”不是一個“孤立的定點”,而是“‘本我——自我——超我’及‘潛意識——前意識——意識’雙重序列整一結(jié)構(gòu)里的一項動勢”,因此,歷史由無數(shù)生命實體構(gòu)成,而每一實體都存在著展現(xiàn)“全體意識”的潛能,即同時含有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處于一種潛在的“集成狀態(tài)”,并催動自我的“不斷成長和發(fā)現(xiàn)”。進而,駱一禾提出了“博大生命”的命題:“指那些說出了大文化風(fēng)格中主導(dǎo)精神的導(dǎo)師的總和”。也就是說,作為“復(fù)合體”的“博大生命”仍需經(jīng)由個體來完成,而個體的不斷成長則是孕育“博大生命”的唯一途徑。具體到駱一禾在其詩學(xué)思考中提出的“詩歌共時體”概念,或許也可以說,這是一種生命本體論的詩學(xué),即不同于一般線性文學(xué)史觀中的代際更替圖景,駱一禾認為詩人是“置身于具有不同創(chuàng)造力型態(tài)的,世世代代合唱的詩歌共時體之中的”。而組成這一“共時體”的,則是每一個真正的詩人所創(chuàng)造的獨特的“詩歌心象”,即詩人將相同的詞匯轉(zhuǎn)變?yōu)椤安煌恼Z流和語境”和“有構(gòu)造的詩歌語言”時,展現(xiàn)出的各不相同的藝術(shù)思維和對生命的感知。也就是說,文字和語言本身并無意義,而“詩必然完成在語言創(chuàng)造中”,只有通過“生命自明”/加速燃燒的生命的力量將語言置于詩歌的上下文中,“把經(jīng)歷、感觸、印象、幻想、夢境和語詞經(jīng)沉思渴想凝聚,獲得詩境與世界觀的匯通”,語言方能重建與存在的聯(lián)系而顯現(xiàn)出自己,詩人亦由此完成自己對詩和生命的獨特貢獻,并在其間“生長著他的精神大勢和遼闊胸懷”。
顯然,與其說這是一種自成一脈的詩學(xué)表述,不如說是80年代流行的諸多理論語言的一次集中展示,而其間李澤厚的“主體性”哲學(xué)的身影尤為明顯,只是將其由馬克思和康德而延伸出的關(guān)于“實踐”與“積淀”的表述,改造為了弗洛伊德與榮格的精神分析理論。當然,也正如李澤厚將“人類總體—個體”這一對稱結(jié)構(gòu)的焦點移至“個體”,認為個體的“現(xiàn)實性早于和優(yōu)于”群體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的普遍性,從而將這一理論啟蒙化;駱一禾同樣將精神分析理論對人的意識結(jié)構(gòu)的分析,轉(zhuǎn)換為了“個人”所具有的呈現(xiàn)生命“集成狀態(tài)”的巨大潛能,同時也將《傳統(tǒng)與個人才能》中艾略特對“傳統(tǒng)”的理想秩序的強調(diào),轉(zhuǎn)換為只有“個人”發(fā)揮自己內(nèi)在的生命力才有望加入的、有著各不相同的創(chuàng)造力型態(tài)的“詩歌共時體”,進而將上述理論啟蒙化,在一個先驗性的主體結(jié)構(gòu)中,為個人話語預(yù)留了一個相當關(guān)鍵的功能性空位,并借此完成了關(guān)于“人”的本質(zhì)論述,將這一具有完整主體性的個人放置于一個完滿的想象性關(guān)系當中。
由此可見,駱一禾的詩學(xué)體系所關(guān)切的并不僅僅是詩學(xué)問題,而是有著回答“何為‘人’/‘人’何為”這一問題的沖動。在駱一禾的論述中,這一體系是對現(xiàn)代理性及其造就的原子式個人和后現(xiàn)代式碎片的超越:現(xiàn)代社會主客體的拆分使人脫離了“他的基本狀態(tài)”,自我中心主義則進一步使內(nèi)心由一個“世界”坍縮為“角落”,進而使人失去生命力,具體到詩歌層面,則是以比喻和意象的拼貼代替了真正的創(chuàng)造力;而生命的運動則是另一種狀態(tài),其間蘊含著以創(chuàng)造力為基點、超越現(xiàn)代主義思路展開寫作的可能,并最終決定新詩的命運,當然也將刷新我們感受世界的方式,由此而“伴生一種特殊的世界觀”,并塑造新人。
在此,“生命”既是意義的起源和動力,也是歸結(jié)。這當然可以說是啟蒙的加速度所帶來的必然思路,然而,這種加速度如何與相對穩(wěn)定的日常倫理對接,如何落實在切身的主體建設(shè)過程中,而不是單純強調(diào)主體生成的潛能?駱一禾的“生命哲學(xué)”并未回答這樣的追問,而是通過對一系列概念的辨析,悄然繞開了這一對20世紀中國革命構(gòu)成過重大考驗的問題。
譬如其將“文化”區(qū)分為兩種面向:一是精神覺醒的生命歷程,它的活動構(gòu)成文化的“根性”,不同的文化乃是生命活動的不同途徑;一是“習(xí)俗、知識”等文化形式,僅僅是文化的外殼和“僵死的制度”。通過這種區(qū)分,駱一禾將生命從文化中剝離出來,賦予其本體論的意義,由此得出結(jié)論:“文化之死并不注定生命之死,否則就將文化與生命這種命運的、人文的東西變成了邏輯的、自然遺傳的東西。”從這種生命本體論的觀點出發(fā),駱一禾又將傳統(tǒng)文化明確區(qū)分為:“本土生命”/“本土精神”和“傳統(tǒng)文化”兩類,前者蘊有創(chuàng)造力,而將前者歸入后者則是傳統(tǒng)文化的持有者即傳統(tǒng)文人們被統(tǒng)治者奴化的邏輯。再譬如其區(qū)分“日常”與“現(xiàn)實”,而“現(xiàn)實”之所以不等于/大于消磨自我的“日常”,也正在于個人生命得以與其構(gòu)成一體兩面、互相參與和生成的狀態(tài),而如果說駱一禾由此經(jīng)驗著“非現(xiàn)實的日常”或想象著真正的現(xiàn)實、歷史,那么,這種區(qū)分也并非單純的理論問題,而是直接關(guān)涉駱一禾對“何為現(xiàn)實”的想象和文化訴求;因此,在其對群體性的“人”展開書寫時,也就將之區(qū)分為“庸眾”和“人民”兩副面孔,而“現(xiàn)代意識”的來源也從外部的啟蒙轉(zhuǎn)向了內(nèi)部的覺醒。
顯然,這已經(jīng)不是“啟蒙—被啟蒙”的單向關(guān)系所能完全涵蓋的一種生命意識。如果聯(lián)系20世紀中國革命對新文化運動的超克來看,不同于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單向輸出與改造,前者是在革命知識分子和中國社會之間積極尋求一種良性的辯證關(guān)系,在這一過程中,知識分子必須深度介入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具體結(jié)構(gòu)和現(xiàn)實經(jīng)驗,并召喚出其中大多數(shù)個體和群體的革命性,同時也會在不斷的探索和纏斗中,校準自我的身心狀態(tài),磨合出在特定語境中具有相對合理性的實踐方式。可以說,這是一種雙向的啟蒙和改造,也正是這種辯證關(guān)系形塑了中國革命的獨特性。但是,駱一禾對革命的啟蒙面向的強調(diào),對這一點并沒有充分的關(guān)注,而是如上文所述,在啟蒙的思路中迅速將革命人格化、美學(xué)化了。
這種思路無疑過濾掉了對革命經(jīng)驗中諸多含混、幽微的歷史遺產(chǎn)與債務(wù)的省思,當然,這也和駱一禾對“民族新生”的整體性構(gòu)想有關(guān)。在這一構(gòu)想中,與其說“生命”作為駱一禾的詩學(xué)體系當中釋放批判能量、構(gòu)造烏托邦的原點而存在,不如說構(gòu)成了一種特定的認知裝置,并由此過于籠統(tǒng)地剔除了其辨析出的兩極之間廣大的灰色地帶。也正因此,歷史才能被化約為不斷循環(huán)的“死局”,而這種化約在以循環(huán)論的敘述帶來某種歷史縱深和洞察力同時,事實上也預(yù)設(shè)了對歷史和現(xiàn)實的結(jié)論,進而受制于此,封閉了對歷史細節(jié)的進一步考察與體認,更難以使駱一禾對塑造這一認知裝置的歷史語境和文學(xué)機制產(chǎn)生充分的反思,也無助于對80年代何以呈現(xiàn)為如此面貌展開細致、切實的剖析。
進一步說,駱一禾經(jīng)由這一特定的認知裝置,將“立人”的要義聚焦在“生命”的生長、壯大之上,并由此講述了一個關(guān)于“新人”和“生命”的神話,試圖以此超越現(xiàn)代理性個人的局限,但悖謬之處在于,這一神話本身即是現(xiàn)代的發(fā)明。也就是說,在駱一禾的思想脈絡(luò)中,存在一個真正、理想和絕對的現(xiàn)代,作為歷史的遠景和終極目的,經(jīng)由詩歌及其所謂的“詩歌共時體”,被轉(zhuǎn)化為了強烈的當下感性經(jīng)驗。依循這樣的思路,主體可以經(jīng)由對人類文明成果的總結(jié)和匯入,直接完成自身的建構(gòu),而無需從自己的現(xiàn)實經(jīng)驗和具體處境出發(fā),在反復(fù)磨礪中校對自身與現(xiàn)實的結(jié)構(gòu)性關(guān)系。
在今天看來,這種高度美學(xué)化的思路當然并不如其自述的那樣有充分的真理性,反而攜帶著在舊的價值觀念退場、新的社會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的歷史過渡期,基于主體的不穩(wěn)定狀態(tài)的“有限”合理性,但在彼時的認知結(jié)構(gòu)所帶來的特定視域和對焦方式中,詩歌/詩人的建設(shè)性意義及其批判對象的不理想都被放大乃至絕對化了。無疑,這種神話式的敘事乃是基于整個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劇烈變動,那么必須追問的就是,當這一啟蒙神話、生命神話被還原到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其間真正的剩余物究竟是什么?
三、“中國視野”與“非政治的政治”
事實上,在駱一禾寫于1981年的一首詩中,有一個意味深長的表述,即“別離開這塊九百六十萬平方的土地”和“晨昏交替的時分”“來猜測我們”,因為“這是我們的民族艱難造就英雄的混沌”,此時“一個新的社會剛剛被自然懷孕”,“每一個人……就是我們的整體”,而其間的抒情主體則是“用血液和體溫”“織補”“殘山剩水”的“我們這一代”。這種將民族國家與個人身體同構(gòu),經(jīng)由全稱代詞的使用呼喚關(guān)于“祖國”的集體認同的修辭方式和使命感、代際意識、個人的主體意識,固然都是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經(jīng)典話語,但更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其與新啟蒙知識分子的一個極為有趣的錯位:“我們這一代”的使命乃是“織補殘山剩水”,而非告別“廢墟”、邁向“新生”;同時,“織補”所聯(lián)系的實踐中的主體狀態(tài)和具體社會構(gòu)造中的身心體驗,也有別于“情感本體論的生命哲學(xué)”中高度神話式的“生命”。如果聯(lián)系其對“五四”和“長征”的修辭化表述,似乎可以梳理出一個有趣的歷史脈絡(luò),即“‘我們’織補殘山剩水——‘中國文明’尋找新的合金——‘中國’新生”,其間的主語從“我們”到“中國”的微妙轉(zhuǎn)變,或許也暗示出,隨著80年代歷史脈絡(luò)的推進,對部分知識分子而言,整體性的啟蒙沖動逐漸代替了切實、精微的實踐和改造方案。
簡言之,這種歷史體認的邏輯在于,無論是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織補”,還是以“長征”所標志的“新生”,都意味著一個堅實的主體位置已然存在,而“尋找新的合金”的命名,卻將五四與80年代的中國主體標示為“未完成狀態(tài)”。如果說“五四——長征”由此而存在某種連續(xù)性的話,那么在這樣的邏輯中,80年代被命名為五四,則意味著如《長征》一詩所表露的,對于后革命時代的到來和冷戰(zhàn)的終結(jié)、“第三世界”的退場,駱一禾有著明確和不無痛切的體認,而當這一體認與在80年代末消費主義帶來的震驚體驗合圍,將80年代命名為“五四”,也就包含著直面“告別革命”的現(xiàn)實經(jīng)驗和“朝向未來”進而重新打開革命所攜帶的烏托邦激情這一雙重面向,而由于80年代末在世界范圍內(nèi)促使革命發(fā)生的歷史結(jié)構(gòu)已然消失/被壓抑,作為另類現(xiàn)代性方案的革命在這里不得不作為幽靈而借助一個高度本質(zhì)化和美學(xué)化的“現(xiàn)代意識”回返。當然,這一回返能夠成立的前提依然在于,革命與現(xiàn)代共享著某種對于“新人”進而是新的“民族——國家”的想象,也可以說,這一想象正是縫合“革命中國”與“現(xiàn)代中國”之縫隙的入口之一,上文所涉及的駱一禾的一系列表述,未嘗不可以在這樣的邏輯中理解。這意味著80年代歷史轉(zhuǎn)折中的知識分子所攜帶的不僅僅是以西方/現(xiàn)代為參照系的、對于更理想的生活圖景和社會結(jié)構(gòu)的想象,更是“民族——國家”在國際形勢和地緣政治變動中的某種整體性訴求,換言之,80年代的社會能量并不是一種抽象、無背景地朝向自由和開放,而是烏托邦式的個人解放沖動和國家社會的轉(zhuǎn)軌相耦合的定向迸發(fā),而在這一過程當中,知識分子的主體意識作為一種結(jié)構(gòu)性的因素,其存在與民族國家本身息息相關(guān)。
具體到駱一禾這里,其在“情感本體論的生命哲學(xué)”中,正如上文所述,事實上以抽象的“生命/精神”之名懸置了作為具體行為方式和歷史經(jīng)驗的傳統(tǒng),進而既反對傳統(tǒng)中國的神話,同時也通過對現(xiàn)代西方的自我中心主義和后現(xiàn)代的碎片化的批判取消了“前現(xiàn)代——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的歷史進化論的合法性,并由此抽空了“現(xiàn)代”本身的歷史邏輯和內(nèi)容,將塑造新人的所謂“現(xiàn)代意識”絕對化,或曰將解放的目標寄托于某種“絕對的現(xiàn)代”/“現(xiàn)代的神話”,并在基于此而組織對于現(xiàn)實的批判能量時,懸置了層疊于現(xiàn)實經(jīng)驗細節(jié)中的含混與復(fù)雜。這里蘊含著卡爾·曼海姆所批判的某種極端和片面傾向,即認為“只有在烏托邦中和革命中才有真正的生活,制度性的秩序總是不斷衰落的烏托邦和革命所遺留的邪惡殘余。”而由于上述缺陷的存在,這一邏輯事實上無法回答“現(xiàn)代之后怎么辦”的問題。
如果可以借用“純文學(xué)”的命名,將該邏輯指認為“純現(xiàn)代”的話,那么,抵達“純現(xiàn)代”烏托邦的路徑,在這一脈絡(luò)中正是由某種自足、完滿的“純文學(xué)”或曰審美想象所造就的。已經(jīng)有論者指出,海子、駱一禾的美學(xué)理想和劉小楓的“詩化哲學(xué)”淵源頗深,但正如賀桂梅在將“詩化哲學(xué)”指認為“純文學(xué)”的合法性得以建構(gòu)的知識譜系之一時所說,“這種‘非政治化’的訴求本身即與現(xiàn)實世界處在一種緊張的‘張力關(guān)系’當中,而其政治性也因此強烈地表現(xiàn)出來。”對于駱一禾而言,或許這種“非政治的政治”更富意味的地方在于,除了以詩歌想象浪漫主義的主體形象/以浪漫主義的主體形象想象詩歌,他也同時以這樣的方式想象著中國乃至世界。
進而,如果說80年代確實存在關(guān)于“落后的中國”的敘述,并帶來了某種處于歷史和未來之間的焦慮的話,在上文論述的基礎(chǔ)之上,駱一禾對于進化論歷史觀的批判和對“共時體”詩學(xué)的強調(diào),就有著另一重意味,即“克服歷史的時間差”從而走向、參與世界的一次想象。但反諷之處在于,這一由不同的“創(chuàng)造力型態(tài)”構(gòu)成的、“世界詩歌”意義上的共時、多元的存在,事實上是有核心的,換言之,其內(nèi)部是有秩序/等級的,而處于這一秩序頂點的是但丁、歌德、莎士比亞等文藝復(fù)興和啟蒙時代的西方文學(xué)大師,固然可以由此而指認駱一禾的文學(xué)資源,但更為重要的是,判定這種秩序/等級的理由和標準在于,這一“共時體”所指涉的從來不是僅僅作為一種文體的詩歌,而是與詩歌同構(gòu)的生命/精神世界,即其所謂“在這個層面里自我的價值隆起絕非自我中心主義、唯我論的隆起”,而是“生命自身”/“生命構(gòu)造”,是海德格爾意義上的“存在”和雅斯貝爾斯意義上的“大全”/本原。由此當然可以引出對駱一禾詩學(xué)的某種存在主義解讀。但如果由此重審駱一禾的“共時體”詩學(xué),更值得注意之處就在于,這其實是一種以“多元”“共時”為名的一元、本質(zhì)化論述,而所謂“走向世界”,在此并非“平行移動”,而是意識到自己身處“共時體”當中而使自己的精神世界不斷生長。其內(nèi)在邏輯或許正是張旭東在討論80年代現(xiàn)代派美學(xué)成就的歷史特性時所指出的“雙重的摹仿”,即“在空間維度上,具體講在形式創(chuàng)新和審美游戲上,它摹仿了一個更‘現(xiàn)代’更‘世界’的藝術(shù)建制和哲學(xué)建制,但在自身‘政治無意識’的表達和敘述上,也就是說,在時間維度上,80年代文藝和文化思想討論卻在象征和‘自律性’層面摹仿了新中國前30年歷史運動和社會運動的創(chuàng)造性和內(nèi)在韻律”,也就是說,在這一由審美話語開啟的內(nèi)部自律空間中,所填充的依然是民族、國家、文化甚至文明等集體意識和集體經(jīng)驗,而這一話語的操持者也往往“不假思索地把個人探索的主體性等同于集體行動的主體性”,由此,在駱一禾的表述中,這一不斷發(fā)揚感性血肉的生命力同時也是創(chuàng)造歷史的主體感知,得以以詩歌/審美為媒介,將革命中國的宏大敘事與主體意識“解碼”并“再編碼”至一種以“現(xiàn)代”為名的意識形態(tài)之中,“配合完成了現(xiàn)代化國家和全社會的期待和目標。”
當然,也正是由于民族國家話語的始終在場,這種作為“非政治的政治”的審美想象,并不僅僅是所謂“內(nèi)面的發(fā)現(xiàn)”的產(chǎn)物,正如姜濤所說,“新詩、新文學(xué)的起點”也從一開始就和“魯迅思考的民族‘心聲’問題、晚清以降仁人志士對于‘心之力’的強調(diào),以及五四新文學(xué)對于情感的普遍性、真摯性的理解聯(lián)系在一起……具有某種整體感和社會性,和20世紀的‘時代精神’有很強的內(nèi)在同構(gòu)和共鳴”,這當然和民族危亡的現(xiàn)實境遇和歷史體認直接相關(guān),而由于80年代將自身建構(gòu)為另一個五四,也就內(nèi)在地繼承了這一感知。這或許也是駱一禾再次提請革命資源的原因之一,而革命精神所攜帶的“不斷尋求‘遠方’的精神動力、為了崇高事業(yè)‘獻身’的激情、對于更廣大人群的關(guān)切等”面向,和被革命塑造的“中國道路”“中國形象”,既被駱一禾詩歌中的抒情主體所繼承,也間或是對“‘純文學(xué)’的知識譜系”的梳理與批判并不能完全涵蓋的、80年代中國同時也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內(nèi)在精神結(jié)構(gòu)之一種。
注釋:
a有論者指出:“如果考慮到80年代的中國詩壇對‘現(xiàn)代主義’一邊倒的熱潮這重背景,駱一禾、海子的詩學(xué)理念和文學(xué)史觀念在當代中國文學(xué)的語境下頗有“逆流而動”的意味。駱一禾、海子都提倡浪漫主義并質(zhì)疑當時流行的現(xiàn)代主義詩學(xué),這是80年代中國作家較早地從文學(xué)本身——而不是意識形態(tài)——角度反抗現(xiàn)代主義的主張之一。”李章斌:《“新浪漫主義”的短暫重現(xiàn)——簡談駱一禾、海子的浪漫主義詩學(xué)與文學(xué)史觀》,載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論叢》2021年第1期,第1頁;“毋庸諱言,駱一禾、海子的詩歌趣味迥異于當時乃至而今的文學(xué)風(fēng)尚,他們的寫作也與習(xí)見的現(xiàn)代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的立場,直接構(gòu)成一種對峙。似乎可以說,他們所要掀起的是一場‘新浪漫主義’運動,這樣說也大致不差。”姜濤:《在山巔上萬物盡收眼底——重讀駱一禾的詩論》,載于《新詩評論》2009年第2輯,第59頁,收入姜濤:《巴枯寧的手》,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頁;另收入陳東東編《星核的兒子:駱一禾紀念詩文集》,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21年版,第386頁。
b如王東東經(jīng)由對駱一禾詩學(xué)的存在主義闡釋,認為“為民族生存甚至民族精神提供一幅終極意義上的形而上圖景,而這一點也契合了1980年代的啟蒙和浪漫的思想潮流。”王東東:《“與聞于世界之創(chuàng)造”:駱一禾詩學(xué)建構(gòu)的存在主義路徑》,載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叢刊》2021年第11期,第137頁。
c如冷霜引用駱一禾寫于1987年的《長征》一詩,指出“后革命”語境下20世紀五六十年代詩歌與80年代以來詩歌在認識與研究上的“斷裂”,而近年來,雖然駱一禾“詩歌中的文明視野,他的詩歌觀與浪漫主義詩學(xué)之間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被越來越多地討論,但他的另一些面向”,在這種“斷裂”論的遮蔽下卻難以被充分挖掘。此外,駱一禾在詩中“對中國革命的強烈肯定和贊頌”與“新啟蒙”思潮的距離,和他在詩歌觀念上與“第三代詩歌”主潮的距離之間,或許也存在某種相關(guān)性。冷霜進而認為,駱一禾“在1980年代后期詩歌中展現(xiàn)出來的宏大的文明想象與他從革命傳統(tǒng)順承而來的世界眼光之間的關(guān)系,他對浪漫主義詩學(xué)的傾心與20世紀五六十年代詩歌藝術(shù)資源的革命能量之間的關(guān)系,也都值得進一步探討”。參見冷霜:《“后革命”語境與當代詩歌研究的“斷裂”》,載于《漢語言文學(xué)研究》2022年第1期,第26頁。
d西川:《答馬鈴薯兄弟問:學(xué)會欣賞思想之美》,收入《大河拐大彎:一種探求可能性的詩歌思想》,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2年版,第242—243頁。
e駱一禾:《長征》,收入張玞編《駱一禾詩全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第297—303頁。本文下引詩句如無標注,均出自該詩。
f目前對駱一禾詩歌文本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從其詩歌的部分核心意象、重要主題或經(jīng)典作品入手展開細讀與分析、討論其詩歌理想,如何清:《駱一禾詩歌意象問題探尋》,載于《名作欣賞》2022年第15期,第49—51頁;鐘世華:《文學(xué)精神與歷史理性——以駱一禾詩中“黃昏”色彩的分析為中心》,載于《當代文壇》2021年第5期,第166—171頁;胡書慶:《碧綠的十字:駱一禾詩歌的闡釋》,商務(wù)印書館2015年版;等,但此類研究集中于麥地、黃昏、水等意象或愛、犧牲等主題,論者的注意力也往往被其兩部長詩和《槳,有一個圣者》《黃昏》《壯烈風(fēng)景》等代表性的短詩吸引,重復(fù)性過高。經(jīng)由詩歌理念分析其詩人形象,如雷前虎:《駱一禾:客死人間的圣徒詩人》,載于《名作欣賞》2019年第2期,第145—146頁。而由于駱一禾在詩歌與詩論中有著大量的自我闡釋,此類研究也多易于滑向?qū)︸樢缓逃^點的復(fù)述。對駱一禾詩歌不同版本的考證,如于慈江:《駱一禾〈先鋒〉〈為美而想〉二詩的版本及其他》,載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叢刊》2021年第1期,第204—211頁,但除比較不同版本間的異同并作出相應(yīng)的簡要分析外,并未提供更有價值的研究思路和觀點。
gr賀桂梅:《“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第2版)》,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21年版,第7頁,第21頁。
h[德]彼得·比格爾:《先鋒派理論》,高建平譯,商務(wù)印書館2002年版,第89頁。
i毛澤東在《講話》中亦曾強調(diào)革命作為“普遍的啟蒙運動”的意義,而“文藝”則在其間扮演著“普及”“提高”乃至塑造新人的重要使命。詳細論述參見張旭東:《“革命機器”與“普遍的啟蒙”——〈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歷史語境與政治哲學(xué)內(nèi)涵再思考》,載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叢刊》2018年第4期,第3—17頁;收入張旭東:《批判的文學(xué)史——現(xiàn)代性與形式自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273—292頁。
jmz駱一禾:《美神》,收入張玞編《駱一禾詩全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第833頁,第832頁,第833頁,第832—846頁,第836—842頁。
k參見駱一禾:《火光》,收入張玞編《駱一禾詩全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第847—854頁。
l賀桂梅:《時間的疊印:作為思想者的現(xiàn)當代作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1年版,第203頁。
n駱一禾:《致閻月君》,收入陳東東編《春之祭:駱一禾詩文選》,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20年版,第560頁。
opq“十月的詩”引言,載于《十月》1987年第4期。
s駱一禾:《水上的弦子》,收入張玞編《駱一禾詩全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第829頁。需要補充的是,“中國”的位置在此由“被啟蒙”轉(zhuǎn)變?yōu)橹鲃印皩ふ摇薄;蛟S可以說,這一轉(zhuǎn)變也在不經(jīng)意間標示出駱一禾在歷史的變動中確認“中國”主體的努力。
tu駱一禾:《論昌耀》,收入陳東東編《春之祭:駱一禾詩文選》,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20年版,第447頁,第462頁,第453頁,第453頁,第453頁。
v賀桂梅:《“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文化研究(第2版)》,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21年版,第365頁。與此相參照的是,駱一禾強調(diào)詩歌的文明價值,并認為其應(yīng)該也能夠如古希臘史詩、神話或希伯來神話般為文明的發(fā)展提供奠基性的價值準則與力量,參見駱一禾:《致閻月君》,收入陳東東編《春之祭:駱一禾詩文選》,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20年版,第560頁。
w這一點從駱一禾對魯迅的評價中也能看出。林賢治就曾提及駱一禾“強調(diào)魯迅哲學(xué)的獨創(chuàng)性、現(xiàn)代性,人格的深度,因而是中國情感本體論哲學(xué)的思想者,而不是邏各斯理性哲學(xué)的思想者”,而駱一禾做出這種判斷的“著眼點在中國。”參見林賢治:《悼一禾》,收入陳東東編《星核的兒子:駱一禾紀念詩文集》,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21年版,第189頁。
x詳細論述參見賀桂梅:《“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文化研究(第2版)》,第五章“‘文學(xué)性’的知識譜系——‘純文學(xué)思潮’”第一部分“美學(xué)譜系:詩化哲學(xué)”,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21年版,第340—348頁。
y參見[日]柄谷行人:《日本現(xiàn)代文學(xué)的起源》,趙京華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版;另參見賀桂梅:《書寫“中國氣派”:當代文學(xué)與民族形式建構(gòu)》,結(jié)語“當代文學(xué)難題與中國經(jīng)驗的歷史自覺”第三部分“從‘中國’思考當代文學(xué)”,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20年版,第516—526頁。
轉(zhuǎn)引自張玞:《大生命——論〈屋宇〉和〈飛行〉》,收入陳東東編《星核的兒子:駱一禾紀念詩文集》,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21年版,第49頁。
“十月的詩”引言,載于《十月》1987年第1期。
本段觀點參見駱一禾:《美神》《火光》,收入張玞編《駱一禾詩全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第832—854頁。
參見李澤厚:《康德哲學(xué)與建立主體性論綱》,收入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哲學(xué)研究所編《論康德黑格爾哲學(xué) 紀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頁。
參見[英]T·S·艾略特:《傳統(tǒng)與個人才能》,卞之琳譯,收入陸建德編《傳統(tǒng)與個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論文》,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頁。
參見駱一禾:《一封新發(fā)現(xiàn)的駱一禾的遺信》,載于《廣西文學(xué)》2010年第5期。
即駱一禾詩《殘忍論定:告別——訪萊蒙托夫》,在對混亂的庸俗市井和“弄臣世界”展開批判時所寫“現(xiàn)實不再出現(xiàn)/現(xiàn)實已被日常圍殲……這不是現(xiàn)實主義而是日常主義”。該詩收入張玞編《駱一禾詩全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第496—501頁。
此處也可以參照竹內(nèi)好對歷史的理解:“歷史并不是被作為結(jié)果來理解的”,而是“以可能性的狀態(tài)存在于主體內(nèi)部……對于主體來說歷史就是每一個現(xiàn)在,如果主體放棄了判斷、決定以及行動,也就失去了他的歷史”,由此,竹內(nèi)好得以“超克”進化論視野中以先進與否衡量歷史與歷史人物的標準,而是將主體與歷史同構(gòu),“以介入歷史的深度,和是否具有真正的主體性來衡量歷史人物”,同時將歷史產(chǎn)生的時刻指認為“主體為了自我形成而拼搏的一個個瞬間”。參見唐宏峰:《作為方法的竹內(nèi)好——以〈何謂近代〉和〈近代的超克〉為中心》,載于《中國圖書評論》2007年第3期,第88頁;另參見孫歌:《在零和一百之間(代譯序)》,收入孫歌編《近代的超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5年版,第46頁。
前者參見駱一禾:《市井狹邪——論一種性格及其慣性思維》《殘忍論定:告別——訪萊蒙托夫》,收入張玞編《駱一禾詩全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第303—310頁、第496—501頁。后者如《長征》中所書寫的“農(nóng)民”。
參見賀照田:《啟蒙與革命的雙重變奏》,載于《讀書》2016年第2期,第13—24頁。
駱一禾曾在詩中將80年代中后期的北京市井生活,與由軍閥、庸眾、“黑幕小說、通俗演義”等構(gòu)成的晚清和“黑暗”民國,以及明王朝由盛而衰的1587年(即萬歷十五年)同構(gòu)。參見駱一禾:《市井狹邪——論一種性格及其慣性思維》,《殘忍論定:告別——訪萊蒙托夫》,收入張玞編《駱一禾詩全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第303—310頁、第496—501頁。
駱一禾:《致后人》,收入張玞編《駱一禾詩全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第13—14頁。
[德]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tài)與烏托邦——知識社會學(xué)導(dǎo)論》,李步樓、尚偉、祁阿紅、朱泱譯,商務(wù)印書館2014年版,第240頁。
參見王東東:《追尋美神:1980年代中國的新浪漫主義與審美教化——以駱一禾、海子為中心》,載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叢刊》2023年第1期。
賀桂梅:《“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第2版)》,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21年版,第365頁。
洪子誠:《1954年的一份書目——中國當代文學(xué)中的世界文學(xué)》,載于《小說評論》2022年第2期,第10頁;收入洪子誠:《當代文學(xué)中的世界文學(xué)》,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22年版,第13頁。
參見駱一禾:《一封新發(fā)現(xiàn)的駱一禾的遺信》,載于《廣西文學(xué)》2010年第5期。
駱一禾:《火光》,收入張玞編《駱一禾詩全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第851頁。
“雅斯貝爾斯借謝林‘與聞于世界之創(chuàng)造’(Mitwissenschaft mit der Sch?pfung)的雋語來論述進入大全或本原的努力:‘在我們的根源里我們曾經(jīng)參與或知道萬物的本原,而在我們的世界這個窄狹范圍里我們就忘記了。我們從事哲學(xué)思維活動,就在于喚醒我們的回憶,從而讓我們返回本原。’”引自王東東:《“與聞于世界之創(chuàng)造”——駱一禾詩學(xué)建構(gòu)的存在主義路徑》,載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叢刊》2021年第11期。
參見駱一禾:《火光》,收入張玞編《駱一禾詩全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第847—850頁。
張旭東:《文藝文化思想領(lǐng)域40年回顧(1979——2019)》,收入張旭東:《批判的文學(xué)史——現(xiàn)代性與形式自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20—321頁。
姜濤:《怎樣重新領(lǐng)會“革命詩歌”的傳統(tǒng)》,載于《漢語言文學(xué)研究》2022年第1期。
這一點從其詩中強烈的自我主體與犧牲意識、“居天下之正 行天下之志 處天下之危”的主體位置與“生為弱者”“為我成為一個赤子/也是一個與我無關(guān)的人”的自我想象、“修遠”使命的提出等方面,可以清晰地辨認出來。相關(guān)詩作/詩句參見駱一禾:《世界的血·第四章:曙光三女神》《生為弱者》《漫游時代》《修遠》,收入張玞編《駱一禾詩全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第591頁,第115—116頁,第526頁,第483—487頁。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xué)文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