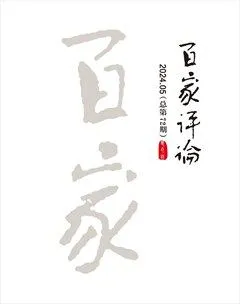新世紀西部小說的女性書寫
內容提要:新世紀西部小說的女性書寫取得重要發展。西部小說打破了女性作為映襯男性群像的創作局限,細致呈現女性與空間、女性與自我、女性與他者、女性與日常生活的復雜關系,展現了西部女性由私人領域進入公共文化場域的行為實踐和嶄新面貌。尤其西部作家對少數民族女性自我覺醒和觀念變化的書寫,豐富了西部文學的女性話語體系。
關鍵詞:新世紀 西部小說 女性書寫 公共場域
盧卡奇認為:“小說是成熟男性的藝術形式”,即“小說的精神態度是男性的成熟,其素材的典型結構是離散、是內在性和冒險的分離”a。盧卡奇的論述強調了小說的雄性特質卻忽略了小說的柔美特征。西部小說也一樣,讀者對它產生強烈的刻板印象,即他們普遍認為西部小說具有陽剛、雄壯的特點而忽略其柔美、溫情的內容。進入新世紀,西部作家在女性書寫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績,打破讀者對西部小說的刻板印象,也重構了西部小說的審美風貌。新世紀西部小說關于性別關系問題的書寫發生重要的轉變,譬如其在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審美表達等層面重構并豐富了西部文學的女性話語體系。
一、西部小說的刻板印象與雄性氣質
西部的自然環境影響小說的審美風格。自20世紀80年代伊始,西部小說便以豪邁和陽剛的風格享譽文壇,譬如小說中的流浪漢、屠戶、獵人、老兵、土匪等人物體現西部的文化氣質,也奠定了西部小說的整體藝術風格。事實上,西部曠遠、嚴酷、荒涼的自然環境影響作家的審美感受。相應地,小說的故事主人公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下頑強生活,他們身上張揚著原始生命力,殘酷的環境也造就了他們堅韌和剛強的品格。紅柯早年生活在新疆,新疆的自然風物完全融入其小說創作,因此紅柯小說的男主人公總是展現英雄氣質:“所有的人都聽見群山上空滾動的吼聲,雄獅團長跑遍了八百公里的塔爾哈山和巴兒魯山,他給那些喪失斗志的人以勇氣,他的聲音令人振奮”b。紅柯習慣性采用“雄獅”“戰馬”“蒼狼”“火焰”等一系列詞語形容男性,展現男性在西部自然環境的鍛造下所形成得剛烈、韌性的品質。同時,他們縱情奔跑在西部的草原、森林、群山、沙漠之間,以一種自由灑脫的方式生活。郭雪波的《大漠魂》中的老雙陽和干兒子狗蛋克服困難,不畏懼沙塵暴,在沙漠深處種出了紅靡子,而老雙陽對抗惡劣自然環境的行為正是雄性氣概的顯現。雪漠的《獵原》中孟八爺智斗狼群和獵人,在嚴酷的自然環境中堅守初心,他的生存意志和生命韌性在黃土高原上熠熠生輝。一定意義上,西部作家塑造了大量具有征服性特征的男性人物形象,而這些人物性格的形成受到西部的沙漠戈壁、森林草原、雪山湖泊、暴雪沙塵的影響。
西部小說在兩性關系中著重凸顯雄性氣質。西部小說集中描寫男性英勇、威武的一面,卻呈現出女性軟弱、柔情的一面。這種兩性關系的對比中,作家們有意識地凸顯雄性氣質而弱化女性力量。在紅柯的作品中男性像險峻的高山、奔騰的河流、翱翔的雄鷹,他們身上洋溢著蓬勃的生命力、昂揚的斗志和野蠻的干勁。例如,《古爾圖荒原》中在新疆奮勇開墾凍結的土地的丈夫,《西去的騎手》中馬仲英所率領的跨黃河、過沙漠的英勇騎兵隊伍,《大河》中彪悍能干的父親自由地穿梭于森林和山澗之間。同樣,這些小說作品中的女性是柔弱、渺小和被動的存在,女性的懦弱襯托出男性的雄性特征。紅柯的《大河》中,湖南籍女兵在阿爾泰意外懷孕,她受到老金的照顧并順利渡過生活難關。老金的彪悍、粗獷襯托出女兵的單薄和柔弱。雪漠的《大漠祭》中,老順的女兒蘭蘭以換親的方式嫁給白福,她總是遭到丈夫的毒打,婚姻生活使其感到絕望而痛苦;瑩兒同樣以換親的方式嫁給老順有陽痿問題的二兒子憨頭,他愛上丈夫的弟弟靈官,因為靈官的逃避感情和離家出走,她獨自忍受情感折磨而痛苦地生活。郭雪波的《霜天苦蕎紅》中,瀚海科爾沁沙地自然環境惡劣,村民種植的苞谷沒有收成,鄉村的女性被迫靠出賣勞力維持家庭的生計。一方面這些女性的性格軟弱使其無法逃離自己所處的生活絕境,一方面她們的被動性使其無法選擇自己的理想生活和情感歸屬。受到西部傳統文化的影響,西部作家有意識地塑造具有陽剛特征的男性形象,并通過柔弱和悲慘的女性襯托男性主人公,以此呈現了一種凸顯男性氣質卻失衡的兩性關系。
在傳統的性別關系結構中,父權制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且男性逐漸成為一種“支配和壓抑女性的性別角色”c。西部小說中的父親或哥哥等男性總是決定女性的人生和命運。例如,《大漠祭》中的父親不顧及女兒的感受而決定利用女兒為兒子換親。《馬蘭花開》中的父親為了緩解拮據的生活而匆匆嫁了大女兒馬蘭。《紫青稞》中的大姐桑吉受到傳統思想的束縛,無奈地踏上進城為孩子尋父的道路。二姐達吉過繼給阿叔次仁,為了讓阿叔有一個體面的上門女婿,她聽從其安排接受了普拉的感情。事實上,男性性別身份的確立反映社會大眾對性別想象和性別觀念的認同。改革開放以來,西部和東部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方面的巨大差異使得西部作家普遍產生文化焦慮,他們積極主動地參與自我性別身份的建構,以豐富的實踐活動應對男性的性別危機,進而以此彰顯西部文化在社會性別機制方面的影響。西部小說從社會語境和兩性關系的層面呈現了西部的男性文化氣質,深刻反映了西部在不同社會歷史文化語境下的性別文化。
西部小說過度刻畫男性角色往往導致女性的失聲或消失。具體來說,西部小說內部存在一種顯見的父權文化,這構成壓抑和主導女性的主要因素。在具體的閱讀過程中,讀者們往往會記得紅柯筆下英勇的軍墾戰士、郭雪波筆下機敏的獵人、雪漠筆下跋扈的父輩、董立勃筆下囂張的基層干事、李學輝筆下乖張的緊皮手等等,而這些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往往是沉默的,她們或失聲或沒有存在感,這也說明女性在西部的歷史發展中被遮蔽的問題。關于新疆兵團建設的書寫中,紅柯、董立勃等作家著重呈現男性在新疆建設過程中克服惡劣自然環境而英勇獻身集體事業的行動及表現。關于西部大開發的書寫中,賈平凹、雪漠、劉亮程、郭雪波等作家重點展現村長、書記、隊長、村民等男性角色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發揮的作用而忽視了女性的貢獻。關于少數民族地區改革發展的書寫中,葉爾克西、梅卓、馬金蓮、亮炯·薩朗等作家也強調少數民族男性的率先覺醒以及他們推動西部偏遠地區改革發展的歷程。作家們普遍忽視女性的生存境遇和生命訴求,實則忽略了現代化發展進程與女性命運的內在關聯。正因為如此,西部小說的刻板印象是雄性的,其中女性的聲音被忽視了,故而小說溫柔、細膩的主題內容和情感表達也不為讀者所注意。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文化的多元化,西部作家們也逐漸作出改變,他們也聽到了屬于女性的聲音,譬如一些西部作家立足現實生活和壯闊歷史的女性書寫,既展現了不同女性的風采,又以女性視角審視民族歷史的發展進程,從而使得西部小說的女性敘事呈現多重意蘊。
二、女性的浮出與性別視角的建立
西部作家開始注意到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女性意識的覺醒。他們通過對女性生活遭際和命運軌跡的書寫,反思了改革開放以來西部女性思想觀念的變化以及自我主體性的建構。谷運龍的《燦若桃花》中,喪夫的小姝不畏懼長輩的阻攔和世俗的眼光,克服重重困難嫁給自己的初戀地寶,自信坦然地開啟新的生活。《春蘭》中幺姑娘不滿意家里的定親對象,進城打工時與廚房工作的同事自由戀愛。同樣,春蘭的訂親對象秋生進城讀書,她拒絕母親介紹得其他結婚對象,決定進城去尋找自己的幸福。春蘭和幺姑娘作為被羌族傳統文化束縛的女性,反對包辦婚姻、走出羌寨是她們自主性的選擇,這種反叛與出逃主題的書寫具有思想啟蒙的意味。《日近長安遠》中,農村女孩甄寶珠反復找“商品糧”d未果的情況下,嫁給了農村小伙秋生,寶珠決定同丈夫進城打工。她既吃苦耐勞又聰明伶俐,從賣襪子、開飯館到停車收費,賺了不少錢,改善了原本貧困的生活。西部作家將女性的精神蛻變和時代背景結合在一起,表現女性意識的覺醒使得西部女性迸發的生命活力。現代化帶來豐富的物質成果的同時也改變了西部的文化傳統、情感結構和心理模式,處于失落狀態的西部女性接受現代觀念啟蒙,擺脫外在的文化精神束縛。她們通過調整個人與社會以及個人與他者的復雜關系,獲得一種新的自我認同,并憑借頑強的信念尋找到更加可靠的精神寄托和生活方向。
新世紀西部小說也展現了女性在追逐自我過程中遭遇的自我淪陷問題。小說《日近長安遠》中,羅錦衣原本是個普通的鄉村女性,她通過跟孟建設交往,成功地轉為民辦老師,但她又不甘于一輩子當一個普通的鄉村老師,再次通過交易成為一名縣城的老師。羅錦衣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她借助付良才的力量,一步步地從縣城進入城市,由普通的民辦老師成為城市一所設計院的院長。她懂得察言觀色和拉攏關系,并通過外貌的收拾打扮,不斷地包裝自己。隨著羅錦衣人老珠黃,付良才選擇了年輕的盧雙麗。故事的結局便是羅錦衣依靠男性得到的一切卻同樣毀于男性。作家這樣的處理具有一定的戲劇性,但是也說明了羅錦衣憑借交易換來的一切終究是泡沫。王華的《花城》中花村的女性苕花、金錢草等女性進入城市當打工妹,從事搞傳銷、賣保健品、賣化妝品等工作,她們為了在城市謀生不惜出賣自己e。苕花為了在城市中生存下去,甚至嫁給年齡較大的城市男人。這些女性覺得花村的生活無聊,她們想要體驗城市刺激的生活,然而城市中某些不良風氣洗刷掉了她們身上的純真和善良,苕花、金錢草等人在城市也前途渺茫。這些進城的鄉村女性企圖通過逃離家庭來釋放個性和追求自我,但她們往往囿于性別身份最終陷入困境。西部小說展現女性走出鄉村進入城市所面臨的精神困境和“越軌危機”f,進而說明女性依靠性別紅利獲得的生存資源和社會資源終究會使得自己陷入深淵。
同時,新世紀西部小說展現女性在自我覺醒過程中的內心矛盾和情感沖突。盡管她們的思想有所覺醒,但是仍舊受到男性的觀念主導或影響,故而她們思想和生活總是處于矛盾沖突之中。小說《紫青稞》中,普村的藏族女孩達吉過繼給叔叔次仁后進城生活。她進入城市積極適應新生活,學著售賣農副產品,從賣牛奶到賣奶渣、奶酪、油酥再到開酒館,達吉實現了經濟獨立。但是,達吉為了讓阿叔有一個體面的上門女婿,她聽從叔叔的安排接受了自己原本不喜歡普拉。尼瑪潘多的小說反映了已然實現經濟獨立的女性,她們的精神仍舊未能獨立,她們習慣性地接受長輩的安排,以致其長期處于情感壓抑和精神孤獨的狀態。小說《野麥垛的春好》中,西部偏遠山村的春好自幼跟同村的張生相好,兩家也決定換親,即春好嫁給梅子的哥哥張生,梅子嫁給春好的哥哥跟風。然而梅子因不滿跟風不思進取,喜歡上其他人,導致兩家的換親沒有成功。春好因為哥哥跟云的惡劣行跡又被迫為其換親,嫁給自己不愛的郝家樹,她的生活沒有了指望。后來春好跟同村的東拴有了感情,被鄰居撞破,東拴意外判刑,春好無奈只能進城尋找出路。進城后的春好為生活所迫,從事不光彩的行當,自此她變成家里的搖錢樹。盡管生活艱難,但春好對陌生人也充滿善意,如照顧打工少年小秦和其他的乞討者。春好對生活充滿信心,她從未想過放棄自己。在小說的最后,春好和失去雙腿的張生走到了一起。季梁棟寫出了西部女性的樸實和善良,她們總是以柔弱的身軀應對殘酷的現實生活。這群女性無法在逃離家庭之后建立屬于自己的獨立精神空間,因為她們總是在回歸家庭和尋找自我之間反復徘徊。
進入新世紀,西部女性經歷了多種文化的洗禮和熏陶,她們面對感情變得更加地主動,體現了鮮明的現代精神與時代色彩。不能忽視的是,“女性對于自我的覺醒與拯救中必然伴隨著種種苦難的歷程”g。小說《拉薩紅塵》中,瑪雅穿梭于不同的男性之間尋找精神伴侶,并以此來反抗愛情的易逝以及麻木的婚姻生活。瓊吉白瑪總是陷入愛情或是婚姻的艱難抉擇中,她遵從內心的情感需要而不惜違背婚姻法則和道德倫理的約束。藏族女性重視自己的情感需求和內心感受,她們也敢于打破傳統文化的束縛而去追求理想生活,但是她們對于自己的生存處境、精神需求以及行為表現依舊充滿困惑。這說明少數民族女性的自我意識有所覺醒,而這種覺醒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小說《月焰》書寫兩代藏族女性的命運軌跡和情感糾葛。母親瓊芨白姆出生在藏族的貴族家庭,西藏解放的時候,瓊芨白姆離開家庭去尋找劉軍長,之后她學會漢語被推薦上大學。在上學的過程中,瓊芨白姆跟自己的同學巴頓談戀愛,在巴頓返回拉薩之后她又跟自己的老師雷產生感情,此后她嫁給巴頓,兩人又迅速離婚。跟洛桑結婚多年后,瓊芨白姆選擇跟洛桑離婚,爾后她同丹竹仁波切的感情也無疾而終。女兒茜瑪跟母親瓊芨白姆一樣,她也無法正視自己的感情,總是游離在不同的情人之間。在新世紀階段,西部小說對女性的呈現體現了日常生活中女性意識的外化,即女性通過彰顯自我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來確證自我的“性別角色”h和社會特征,例如她們習慣性地表述“我要怎么樣”。西部作家在書寫女性的過程中,不自覺地分析女性與空間、女性與自我、女性與日常生活的關系,從而揭示女性主人公在放縱、頹廢、傾聽以及覺醒過程中對自我的發現和安頓。
三、走向公共文化場域
新世紀西部小說關于女性的書寫取得重要的發展。在西部作家筆下的女性群體,“面對公認的差異和區分,她們承諾認識上的合作并尋求公共性”i。作家們開始關注長期被男性所遮蔽的女性聲音,書寫女性在現實生活和情感問題中的困境,呈現女性豐盈的內心世界。在西部小說中,女性不僅自我意識覺醒,而且她們積極走入公共文化場域,展現自己的精神風采和職業能力。盡管傳統文化觀念影響著女性群體的生活和選擇,但進入新世紀階段,女性群體的思想和觀念發生變化,她們普遍擁有了更多的選擇權。西部小說中女性明顯的變化表現為,她們日漸從私人領域進入公眾領域,譬如有意識的通過架空父權體現女性的自主意識和獨立精神。南茜·弗雷澤認為:“公共領域是一種不受限制地理性討論公共事務的理想”j。女性走向公共場域,即女性走出家庭,進入社會公共空間場域。譬如政府機構、商業領域、文化傳媒等領域都有女性活動的身影。女性有自由地表達自己和選擇生活的權利,她們在公共領域的地位和表現值得被尊重。
西部小說展現了女性逐漸走出做家務、照顧兒女的私人領域而相繼成為醫生、老師、廠長等公共文化場域的代表人物。她們打破了人生只能由男性決定的觀念,找回了自己丟失的話語權。阿舍的《阿娜河畔》中,新疆某兵團農場的石昭美喜歡來自支邊家庭的明中啟,但是明中啟喜歡上海的支邊青年婁文君,后來石昭美與明中啟因為誤會而結婚。婚后的石昭美沒有被家庭困住而是積極提升自己,逐漸成長為一名優秀的醫生。她經常深入基層,救治兵團的病人。正是在基層工作中,石昭美走出情感困境,也找到自己的職業理想和生活追求。馬金蓮的小說《馬蘭花開》中,因為父親嗜好賭博,馬蘭高中輟學,用自己的彩禮換得弟弟妹妹的學費。她嫁入李家妥善地處理了婆媳關系、妯娌關系,當李家的大家庭分崩離析后,她興辦養雞場,逐漸成為在家庭中擁有話語權的人。小說中的馬蘭是一個聰明、善良、勤勞的女性,她既能操持家務、照顧老人和小孩,也能積極謀求出路。貧困的生活并沒有壓垮她,反而激勵她尋找脫貧致富的道路。她頂住來自家里公公、丈夫乃至小叔子的壓力而興辦養雞場,增加了家庭的收入,從而改善了家庭的經濟情況。馬蘭也是西部小說中具有成長意義的女性形象。她憑借自己的能力獲得了家庭話語權,從私人領域走向公共領域,施展了自身的才能,也贏得家庭話語權。盡管西部小說中存在一種過于理想化的性別關系,但是這種對于現實問題的回避恰恰揭示出阻礙女性發展的文化根源是復雜的,它不僅存在于單一的男女關系中,“也存在于家族集團男性成員與女性成員之間,以及更廣泛的社會領域中的作為階層的男女關系之間”k。因此,新世紀西部小說的時代意義在讓女性進入公共文化場域,改變自己困窘的生活局面,進而追求理想或創造新的生活。
新世紀西部小說在歷史長河中描摹女性的身影,反映她們在民族和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貢獻和創造力,尤其展現了少數民族女性在現實生活和社會轉型過程中的風采。具體來說,西部小說從思想觀念、行為表現、文化取向等多個方面展現西部女性進入公共領域的變化。肖勤的小說《好花紅》寫貴州黔北大婁山的故事。主人公花紅的父親是獵人,母親曾因落難嫁給父親但是不愛他。母親與隔壁山里的年輕獵戶相好而死在父親的槍下。花紅自幼跟父親學得一手好槍法,在父親失蹤、新婚丈夫苦根失聯的情況下,花紅加入革命隊伍,并憑借過硬的本領出入于槍林彈雨之中,爾后成長為一名部隊指導員。花紅為了讓手上沾染老百姓鮮血的苦根繩之以法,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花紅選擇犧牲個人的情感維護群眾和集體的利益,體現現代女性的精神自主和理性決絕。王華的《大婁山》中的婁婁是碧痕村的駐村第一書記,她為了營救被騙入傳銷組織的貧困青年,因為意外的車禍而喪生。婁婁活在碧痕村每一位村民的心里,她為脫貧致富所興建的苗繡作坊沒有停止運作,這也說明婁婁的精神影響著每一位村民和鄉村干部。《紫青稞》中的阿佳天加是一個男性化打扮的女村長,“只有村長阿佳天加男人般的身材,浸透了陽光和青稞酒的黑紅臉膛能一眼認出來……誰都知道村長生就一副男人性格,大大咧咧”l。普村阿媽曲宗家的老屋子被洪水沖垮,阿佳天加不畏懼藏族的“忌諱”,將即將撒手人寰的阿媽曲宗接到自己家暫住。阿佳天加的出現,是對藏族傳統權威文化的解構。她既可以勝任原本男性負責的村長一職,又展現出超越男性的氣魄和擔當。女性鄉村干部在當下社會發展中具有重要意義,尤其少數民族女性進入公共文化場域,她們發揮自己的能力在鄉村基層做出一番事業,展現了新時代少數民族女性獨特的精神面貌。
新世紀西部小說展現了女性進入公共領域的過程。“公共領域”對于女性群體來說,是永遠敞開的。在這個場域中,她們擁有了發掘自我潛能的機會和條件,同時她們在公共領域的表現也值得期待。賈平凹的《帶燈》塑造了給鄉村政治場域帶來一絲明亮的基層鄉村女干部帶燈的形象。帶燈是櫻鎮綜治辦的負責人,平日主要處理群眾上訪的日常事務。帶燈是一個機智、聰明、能干的基層工作者,她機智應對村民的上訪問題,妥善處理村民之間的矛盾和紛爭。盡管帶燈身處綜治辦這樣一個復雜的機構,但她憑借自己的聰明智慧團結了一批基層群眾,將各項工作穩步推進。在具體工作過程中,女性基層干部竭心盡力地為人民群眾解決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問題,她們也在公共領域展現了自身的卓越才能。同樣,尼瑪潘多的《在高原》中,藏族姑娘白瑪措吉畢業之后,沒有留在城市,而是回到自己的故鄉。白瑪措吉回到塔金后成為一名鄉鎮干部,但是在工作的過程中她面臨著重重的困難,她的很多改革思路和策略得不到周圍人的響應。白瑪措吉的一腔工作熱情慢慢變得冷淡,她開始重新理解和認識自己的工作。小說的結尾,白瑪措吉帶著遺憾離開塔金走向了拉薩。在公共文化領域,西部小說中的女性基層工作者重視如何改善鄉村基層管理以及如何調整鄉民與基層組織之間的關系等問題。不能忽視,帶燈和白瑪措吉的故事結局也反映女性在公共領域遭遇的客觀難題,這亦說明女性在公共領域的發展和成長之路任重而道遠。
新世紀西部小說展現女性在公共領域的表現不只是為了強調女性的覺醒和改變。在更深層次的方面,女性在公共領域的發展也顯示出她們在思想和行為表現上的智性精神,即一種充滿正義感和生命赤誠的文化追求。例如,紅柯的小說《太陽深處的火焰》中,新疆女孩吳麗梅具有純粹的人文理想和知識追求。吳麗梅從渭北大學畢業后,沒有選擇留在繁華的城市,而是去到新疆偏遠的大漠腹地塔里木軍墾大學,從事有建設性意義的科研工作,諸如她常帶著學術團隊考察塔里木河下游的太陽墓地。吳麗梅最終獻身學術事業,一場沙塵暴將她的生命永遠定格在大漠深處。吳麗梅是新疆大漠和紅柳文化的象征,即吳雪麗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和拼搏精神。紅柯將吳麗梅比作是“太陽”,“因為吳麗梅有生命活力、有信仰追求、有生活期待,她正像是一團火,太陽深處的火焰最終熔化人心的黑暗”m。與吳梅麗不同,她曾經的戀人徐濟云渾身流露著“平庸之惡”n。徐濟云在各種場合都穿著吳麗梅織的羊毛衫,他要從吳麗梅的身上汲取那股“火”的力量。唯利是圖者利用一己之私撲滅學術圈和知識圈的火。徐濟云深刻地知道吳麗梅離開他,離開渭北的原因是她厭惡知識分子圈子的污濁。小說中徐濟云作為被現代物質文明腐蝕的個體,他所尋覓的救贖資源來自新疆姑娘吳梅麗。吳梅麗身上的自信、開朗、善良、正直等品質洗滌了徐濟云內心的污濁,讓其獲得暫時的內心安寧。在公共文化場域,女性身上所體現的智性精神,代表一種非主流的生活方式,這也反映了女性個體獨立睿智的精神品質和文化訴求。
在西部小說創作題材上,涵蓋了從私人到公共的各種議題,既涉及家庭內部的情感關系、個體對自我身份、社會關系的探索以及對社會現狀的反思。在傳統文化視閾下,西部女性一方面遭受著天災人禍、疾病和死亡等帶來的傷痛;一方面又遭遇著欺騙、不公和誤解所帶來的心理創傷。盡管身處逆境或飽受挫折,女性依然挑起家庭重擔,成為家庭的頂梁柱。女性的沉默背后是她們沒有話語權和選擇權。及至當下,西部作家們“努力撼動著公共與私人的邊界,開辟出告別革命之后政治的新空間。正如所見,這些作家的作品體現出女性突破歷史給定的角色,以主體之姿進行思考與創作的生命力”o。在新世紀的創作過程中,馬金蓮、肖勤、王華、阿舍、尼瑪潘多等作家打破傳統文化的束縛,強調普遍意義上的女性公共空間場域的重要性,呼吁建立女性表達自身和彰顯自己的公共文化空間。同時,西部作家也強調充分地尊重女性的訴求和主張,關注女性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領域的職業選擇和工作成績,彰顯她們在歷史進程和社會發展過程中的表現和作用,由此也呈現西部作家在建構女性形象、推廣性別文化以及發展少數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多重探索。
進入新世紀,西部小說的女性書寫打破了女性作為映襯男性雄性特質的窠臼。西部小說中的女性作為一群鮮活的生命存在,她們有自己的生活追求和情感需要,敢于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并且她們進入到公共文化場域后能在各行各業綻放自己的光彩。尤其西部作家對于少數民族女性自我覺醒和觀念蛻變的書寫,豐富和重構了西部文學的女性意識和女性話語體系。總之,新世紀西部小說展現了女性的性別自醒、性別反思以及性別經驗的超越,體現對女性的精神訴求和文化主張的尊重,從而將性別平等與自足逐漸外化為一種樸素的日常生活書寫。
注釋:
a盧卡奇:《盧卡奇早期文選》,張亮、吳勇立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頁。
b紅柯:《古爾圖荒原》,大眾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頁。
c詹俊峰:《瑞文·康奈爾的男性理論探索》,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10頁。
d周瑄璞:《日近長安遠》,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11頁。
e王華:《花城》,《當代·長篇小說選刊》2016年第6期。
f薩拉·艾哈邁德:《過一種女性主義生活》,范語晨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86頁。
g田泥:《走出塔的女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頁。
h露西·德拉普:《女性主義全球史》,朱云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55頁。
i米蘭達·弗里克等編:《政治哲學中的女性主義——女性的差異》,選自《女性主義哲學指南》,肖巍、宋建麗、馬曉燕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頁。
j南茜·弗雷澤:《正義的中斷:對“后社會主義”狀況的批判性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頁。
k上野千鶴子:《父權制與資本主義》,鄒韻、薛梅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47頁。
l尼瑪潘多:《紫青稞》,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68頁。
m紅柯:《太陽深處的火焰》,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401頁。
n漢娜·阿倫特:《反抗“平庸之惡”》,陳聯營譯,上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4頁。
o汪瀟灝:《共域與私域之間——21世紀拉美女性導演作品觀察》,《當代電影》2023年第5期。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