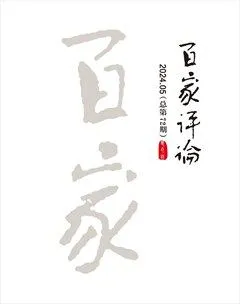闖入者、現(xiàn)代性幽靈與自我教育
內(nèi)容提要:楊怡芬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海上繁花》以1942年發(fā)生于舟山群島的“里斯本丸”號(hào)沉船事件為基底,牽涉意外的“闖入者”與舟山漁民之間微妙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海上繁花》映照的是現(xiàn)代性幽靈盤旋于戰(zhàn)爭(zhēng)時(shí)代所產(chǎn)生的人性錯(cuò)位與價(jià)值悖論。而小說(shuō)相關(guān)具有背反性的細(xì)部,也為觀照20世紀(jì)世界文明史進(jìn)程提供了饒有意味的視角路徑。
關(guān)鍵詞:現(xiàn)代性 現(xiàn)代文明 工具理性 歷史觀
一
2019年末,微信公眾號(hào)“明州世相”刊發(fā)了一篇題為《14位英國(guó)老人在舟山尋找父親,揭開(kāi)一場(chǎng)77年前的沉船慘案》的紀(jì)實(shí)文章。該文對(duì)1942年10月發(fā)生于舟山群島東極諸島海域的“里斯本丸”號(hào)沉船事件,以及77年后“里斯本丸”號(hào)沉船事件遇難者子女相聚舟山紀(jì)念先輩等細(xì)節(jié)有著頗為審慎的記錄。文中詳述了1942年滿載1834名英軍戰(zhàn)俘的日本貨輪“里斯本丸”號(hào)自香港出發(fā),在前往日本戰(zhàn)俘營(yíng)的途中,被美國(guó)潛艇“鱸魚(yú)”發(fā)出的魚(yú)雷擊中。就在“里斯本丸”號(hào)即將沉沒(méi)之際,附近的舟山漁民劃船前來(lái)營(yíng)救落水的英國(guó)戰(zhàn)俘。關(guān)于舟山漁民自發(fā)救人的義舉,作者龔晶晶所示的一句話是值得注意的:“這是很多東極漁民這輩子第一次見(jiàn)到白種人。”a至于舟山漁民在“這輩子第一次見(jiàn)到白種人”后究竟作何感想,他們同意外的“闖入者”之間拋開(kāi)“拯救/被拯救”的關(guān)系又是怎樣形成互動(dòng)的,作者對(duì)此并未作過(guò)多的縱深書寫。
這個(gè)引人遐想的話題,在2023年借虛構(gòu)的時(shí)空布景得到了接續(xù)。是年,浙江舟山籍作家楊怡芬同樣以1942年“里斯本丸”號(hào)沉船事件為創(chuàng)作題材來(lái)源,出版了長(zhǎng)篇小說(shuō)《海上繁花》。相較2019年龔晶晶的紀(jì)實(shí)文章里對(duì)舟山漁民初次見(jiàn)到白種人的有意渲染,小說(shuō)《海上繁花》涉及該部分的書寫似略有些引而不發(fā)的意味。只是寫到舟山漁民在日軍上島搜捕英國(guó)戰(zhàn)俘的過(guò)程中,如何將三名“白種人”掩藏于幽僻山洞之時(shí),小說(shuō)借舟山少年阿卷的視角有如此敘寫:“伊恩他們的手腕上,現(xiàn)在是光光的,但他們一定曾經(jīng)有過(guò)手表吧?那么,他們的時(shí)間,被日本人搶走了;他們和這世界的連接,也被日本人砍斷了。阿卷尋思著這些,可不好意思把它們說(shuō)出口。某一天,他的時(shí)間也會(huì)和外面的世界連接在一起嗎?這樣想著,阿卷都呆了。”b盡管客觀地說(shuō),這段心理波動(dòng)多少脫離了一個(gè)舟山少年從其身份角色出發(fā)理應(yīng)具有的話語(yǔ)邏輯、思維結(jié)構(gòu)與姿態(tài)立場(chǎng),更如同是作者不得不化身為少年阿卷而實(shí)現(xiàn)的“敘事任務(wù)”,但以“光光”的手腕與被剝奪的手表為引,可注意到阿卷在面對(duì)陌生的“白種人”及其潛在的“聯(lián)系”與“沖擊”時(shí),需要得到讀者正視的“回應(yīng)”。
上述所征引的這段源自舟山少年的心理活動(dòng),實(shí)則也鉚接了被舟山漁民救下的英國(guó)戰(zhàn)俘三人,從舟山一路輾轉(zhuǎn)躲避最終抵達(dá)重慶期間的顯豁的敘事主題,即如何找回“他們的時(shí)間”。“他們的時(shí)間”關(guān)涉現(xiàn)代性視閾下一套以語(yǔ)言、地域、歷史、意識(shí)形態(tài)等價(jià)值要素為區(qū)分依據(jù)的“階層”觀念。小說(shuō)開(kāi)篇言及伊恩一家在香港生活時(shí)期,尹恩的兒子喬就困惑于“階層”的設(shè)置與編織,比如他與家中作為女仆的安妮便有著不可輕易逾越的“階層”壁壘:“這是英國(guó)人特別在乎的,他們是純正的英國(guó)人,之后是葡萄牙人、歐亞混血,再是有錢的華人,最后是沒(méi)錢的華人,那就是像安妮這樣為他們服務(wù)的用人們。”c1941年12月24日,即時(shí)任香港總督楊慕琦在香港九龍半島酒店簽下投降書的前夜,英國(guó)男孩喬與香港女孩安妮之間未遂的性愛(ài)就是強(qiáng)悍的“階層論”的注腳。即使作者似乎有意將這場(chǎng)未完成的情愛(ài)關(guān)系,暗示為喬基于道德責(zé)任而不能“毀掉這么好的安妮”,但安妮在意亂情迷之間脫口而出的“少爺”及喬隨后的反應(yīng)仍然表明,這依舊不過(guò)是喬所屬的“階層”面對(duì)他們俯視的“階層”,在實(shí)質(zhì)性接觸當(dāng)中本能的排他傾向。
一切的轉(zhuǎn)折點(diǎn),是1941年12月25日香港的淪陷,以及伊恩、喬等原本握有文明優(yōu)越感的“純正的英國(guó)人”旋即淪為階下囚的實(shí)情。但理應(yīng)指出,即便是在經(jīng)歷了此后“地獄航船”的浩劫,即便是面對(duì)拋開(kāi)個(gè)人安危救下他們的舟山漁民,縱然伊恩等人心存感激,不過(guò)這并未使伊恩等人徹底擺脫對(duì)舟山漁民的“他者”判定。由始至終,“伊恩們”和舟山島民,包括承擔(dān)護(hù)送任務(wù)的各路仁人志士之間保持著微妙的緊張感。茲舉一例,他們?cè)诟爸貞c途中放棄了購(gòu)買御寒的棉長(zhǎng)袍,而是執(zhí)意要到重慶后找尋裁縫訂做“全毛的西裝”與“呢子大衣”。迥異而又堅(jiān)定的服裝款式的選擇的背后,是具有明晰邊界感的階層意識(shí)與受到“現(xiàn)代”洗禮的價(jià)值取向。而伊恩等人與所處環(huán)境的緊張感是在何時(shí)松弛的,又是何時(shí)逐漸消散的呢?是三人隨護(hù)送部隊(duì)行至云和時(shí)終于買到了“走得很準(zhǔn)”d的黃銅外殼懷表,是他們獲悉國(guó)民政府已聯(lián)系到祖國(guó)的外交部,這時(shí)作者楊怡芬試圖強(qiáng)調(diào),他們感覺(jué)重新“歸入文明社會(huì)的秩序里”,而這“失而復(fù)得的歸屬感,讓伊恩激動(dòng)”e。
由此引申出的一個(gè)議題是:令伊恩等人念茲在茲的究竟是怎樣的“文明社會(huì)”?可以看到,一方面,這是基于崛起的科學(xué)技術(shù)與明晰的工具理性意識(shí)而形成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形態(tài),是一種有別于他們的“舟山恩人”的日常生活模式及規(guī)范準(zhǔn)則,但“伊恩們”顯然沒(méi)有認(rèn)識(shí)到,正是令他們具有歸屬感、令他們不自覺(jué)生出傲慢與偏見(jiàn)的現(xiàn)代文明及其塑造的科技幽靈,一度以惡魔般的設(shè)計(jì)將他們推向“里斯本丸”號(hào)這艘地獄航船,推向了近乎絕望的生存境地。由之,當(dāng)霍布斯鮑姆指出20世紀(jì)是“科學(xué)改變了世界以及人類對(duì)世界的認(rèn)識(shí)的時(shí)代”f,這首先昭示了作為現(xiàn)代理性文明的忠誠(chéng)的產(chǎn)物,科學(xué)技術(shù)改造、甚至是標(biāo)準(zhǔn)化了趨于全球化時(shí)代背景下不同國(guó)族群體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地域”與“地域”不再是因地理與歷史互相隔絕的“孤島”。此外霍氏也意在表明,我們現(xiàn)在所熟稔的各類具有致命殺傷性的武器的研發(fā)與廣泛運(yùn)用,同樣也是現(xiàn)代性浪潮“改變了世界以及人類對(duì)世界的認(rèn)識(shí)”的充滿曖昧性的根源。不斷更新?lián)Q代的武器級(jí)別,使得加害者與殺戮者在面對(duì)借助武器間接完成的血腥行徑時(shí),并不會(huì)產(chǎn)生真切的道德負(fù)罪感,因?yàn)閭εc殺戮在現(xiàn)代科技幽靈的加持下顯得異常的輕易,也因輕易而無(wú)休無(wú)止。這也是霍布斯鮑姆談到的:“戰(zhàn)爭(zhēng)變得愈加殘忍的另外一個(gè)原因,是因?yàn)閼?zhàn)爭(zhēng)本身的非人化。血淋淋的殺人行動(dòng),如今變成一個(gè)按鈕或開(kāi)關(guān)即可解決的遙遠(yuǎn)事件。”g
二
《海上繁花》有一個(gè)耐人尋味的細(xì)節(jié):個(gè)人與家庭遭受重創(chuàng)的伊恩,在生還后由重慶回到英國(guó)倫敦,“二戰(zhàn)”結(jié)束后又因工作安排重返香港。伊恩一直記掛著生活在偏遠(yuǎn)島嶼的恩人,而他向阿卷一家報(bào)恩的方式,是資助阿卷來(lái)香港接受被他們的“階層”所認(rèn)同的現(xiàn)代教育機(jī)制,即讓阿卷進(jìn)入到自己的“文明社會(huì)”。很顯然,這種“進(jìn)入”(或謂之曰“召喚”),也是試圖讓阿卷格式化自身的“他者”因子。伊恩最終由于阿卷沒(méi)有如約而至產(chǎn)生焦慮,然而女兒敏妮卻揭橥了父親的這種焦慮實(shí)質(zhì)上“是否含了某種優(yōu)越感”h,或者說(shuō)是在一種文明與文明遭遇過(guò)程中沒(méi)有達(dá)成的“征服/被征服”關(guān)系。伊恩未能深層次考慮過(guò)的問(wèn)題在于,恰恰是阿卷與他父母、鄰人在現(xiàn)代性共識(shí)之外的“異見(jiàn)”,令他們即使面臨潛在的殺身之禍也要救援英軍戰(zhàn)俘。當(dāng)伊恩惘然于舟山漁民竟會(huì)由于“救人一命,天上一星”的理由救下自己,其實(shí)他們的困惑之處也源因這種“毫不利己”的異域觀念,有別于“伊恩們”理性、準(zhǔn)確、功利的“現(xiàn)代性算法”。當(dāng)然,他們也必然難以理解“星”之于舟山漁民的特殊內(nèi)義。“星”除去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呼應(yīng)的古老而神秘的符號(hào)意義外,對(duì)于經(jīng)年累月以出海捕魚(yú)為生的舟山漁民而言,“星”又有著預(yù)示氣象變遷、護(hù)佑漁民平安的具體的現(xiàn)實(shí)指向。因此“救人一命,天上一星”,隱含著舟山漁民對(duì)“自然”在時(shí)、空維度的崇拜行為與縱深追尋,同樣地,舟山漁民關(guān)乎“星”的獨(dú)特的自然崇拜,也是“伊恩們”所屬現(xiàn)代文明框架體系之外的“盲區(qū)”。
這處充滿悖論性的細(xì)部,是觀照《海上繁花》牽涉的物質(zhì)掠奪、殖民侵略、襲擊屠殺等內(nèi)容,包括小說(shuō)“進(jìn)行時(shí)”敘述者張明需要“尋找明媚的事物來(lái)對(duì)抗”的那些“黑暗面”,緣何會(huì)在20世紀(jì)如此頻繁發(fā)生的一個(gè)重要的觀察視角。與之相關(guān)的是,《海上繁花》里“文明社會(huì)”的遵循者與布道者,同時(shí)也是“文明社會(huì)”受害者的“伊恩們”,事后針對(duì)1942年“里斯本丸”號(hào)沉船事件、針對(duì)20世紀(jì)動(dòng)蕩時(shí)局所顯現(xiàn)的某類偏狹而又具有典型性的論見(jiàn)。“里斯本丸”號(hào)幸存者約翰幾十年后回舟山故地重游,他在無(wú)意間聽(tīng)到香織用日語(yǔ)接聽(tīng)電話后,聯(lián)想到了在被俘期間兇神惡煞的日本守衛(wèi),以及日本守衛(wèi)在日常對(duì)待家人的具有明顯反差的“溫柔和暖意”。約翰對(duì)此的自我回應(yīng)是“這都是因?yàn)閼?zhàn)爭(zhēng)”。但如此論斷實(shí)則也回避了更為核心的追問(wèn):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戰(zhàn)爭(zhēng)的發(fā)生?日本守衛(wèi)的背反的人性是否僅因戰(zhàn)爭(zhēng)這一“特殊性”條件所致?小說(shuō)另一處細(xì)節(jié)同樣需要提及。“二戰(zhàn)”結(jié)束后,被運(yùn)送至日本戰(zhàn)俘營(yíng)做苦力的英國(guó)軍官得以獲救。此時(shí)戰(zhàn)俘群體內(nèi)部的主事人有意告誡同伴“戰(zhàn)俘營(yíng)、集中營(yíng)甚至地獄航船的事,還是藏在心底最好,大家往前看往前走,別回頭”i。此言既意在表明落魄的英國(guó)戰(zhàn)俘怎樣擺脫滲入骨髓的創(chuàng)傷記憶,也暗合了英國(guó)戰(zhàn)俘無(wú)法充分形成邏輯自洽的事實(shí)——為何他們恪守的現(xiàn)代性價(jià)值理念,最終卻令自己“傷痕累累”,并正逐漸摧毀他們對(duì)于現(xiàn)代文明社會(huì)的虔誠(chéng)的信仰。
齊格蒙特·鮑曼的《現(xiàn)代性與大屠殺》,就對(duì)《海上繁花》里二戰(zhàn)幸存者的恐懼、沮喪與疑慮進(jìn)行過(guò)理論層面的創(chuàng)造性闡發(fā)。他認(rèn)為,恰是趨于成熟的現(xiàn)代社會(huì)形態(tài)與被復(fù)魅的“現(xiàn)代性”,催生了20世紀(jì)的一系列人間慘劇:“大屠殺如同一扇窗戶,透過(guò)它可以看到那些由理性行為中徹底的現(xiàn)代藝術(shù)所引致的過(guò)程的產(chǎn)生,可以看到一旦這些過(guò)程為實(shí)現(xiàn)現(xiàn)代權(quán)力欲圖達(dá)到的目標(biāo)而被利用的時(shí)候,現(xiàn)代權(quán)力的新的潛力和新的視野就有可能變成現(xiàn)實(shí)。”j如上文借霍布斯鮑姆之言所述,西方工具理性意識(shí)主導(dǎo)下的社會(huì)達(dá)爾文主義與令人眼花繚亂的科技升級(jí),使侵略、戰(zhàn)爭(zhēng)、屠殺等駭人現(xiàn)象被施以“協(xié)調(diào)”“合理”的形式外殼與邏輯支撐,齊格蒙特·鮑曼的《現(xiàn)代性與大屠殺》也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現(xiàn)代邏輯演進(jìn)必將會(huì)在某個(gè)特定的歷史節(jié)點(diǎn)產(chǎn)生大屠殺,而大屠殺是現(xiàn)代文明理念進(jìn)行所謂的“篩選”“優(yōu)化”的主要的“途徑”與“技術(shù)”。頗具意味的是,小說(shuō)里對(duì)現(xiàn)代性語(yǔ)境下推崇的“文明”真正形成超越性反思的個(gè)體,卻是“二戰(zhàn)”期間被迫應(yīng)征入伍、在“里斯本丸”號(hào)上目睹人間慘劇的日本青年荒木。面對(duì)令同伴欣喜若狂的侵略行為,荒木反而有感于“什么叫文明呢?難道文明就是借著‘解放’之名,讓那些國(guó)家的人做出犧牲?那些被殺的人,真的是‘犧牲’,就如獻(xiàn)祭儀式上的豬羊”k。現(xiàn)代文明的強(qiáng)力規(guī)訓(xùn),令“血淋淋的歷史”演變?yōu)椤艾F(xiàn)代社會(huì)的權(quán)力的‘正常’運(yùn)轉(zhuǎn)”的必然結(jié)果。l但這種種又無(wú)疑背離了現(xiàn)代文明一度自我標(biāo)榜的正義、自由、平等等道德旗幟,最終演繹為對(duì)現(xiàn)代文明信仰者的反噬。
從這個(gè)角度講,《海上繁花》映照的是現(xiàn)代性幽靈盤旋于戰(zhàn)爭(zhēng)時(shí)代所產(chǎn)生的意味深長(zhǎng)的人性錯(cuò)位與價(jià)值悖論。應(yīng)指出,小說(shuō)里形形色色人物在多年后回憶自己所經(jīng)歷的“個(gè)人史”時(shí),往往會(huì)將殘酷往事歸咎于戰(zhàn)爭(zhēng)與戰(zhàn)爭(zhēng)當(dāng)中“人”毫無(wú)征兆的突變。而日本船員荒木有關(guān)“文明”一詞的審視與質(zhì)疑,不經(jīng)意間勘破了1942年“里斯本丸”號(hào)事件及其前后所發(fā)生的變故的根源——20世紀(jì)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大規(guī)模的掠奪、傷害、侵略,一定程度而言皆是基于現(xiàn)代性意志的權(quán)力“變現(xiàn)”。在權(quán)力“變現(xiàn)”的訴求下,長(zhǎng)期以來(lái)被現(xiàn)代文明渲染、夸飾,及以此同域外的“野蠻文明”形成涇渭分明的現(xiàn)代性、啟蒙、民主等核心概念,最終為契合某種“殘酷的邏輯”而走向詞義的背反面。這也就局部闡明了小說(shuō)《海上繁花》里飽受摧殘的英國(guó)戰(zhàn)俘為何對(duì)戰(zhàn)爭(zhēng)的解讀與反思,只能停留于表征的層面,因?yàn)橐坏┳鞒龈鼮樯钊氲钠饰觯耙炼鱾儭本筒坏貌恢泵嬗勺约候\(chéng)信仰的文明開(kāi)啟的“潘多拉魔盒”——依照《海上繁花》的一種富于深意的說(shuō)法,即“伊恩們”最終發(fā)現(xiàn)唯有否定、甚或消解“他們的時(shí)間”,才能讓一切的痛苦與罪惡得到合理的解釋。
三
以英國(guó)戰(zhàn)俘為例,關(guān)于楊怡芬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海上繁花》,似乎其內(nèi)的諸多人物都有意識(shí)要將內(nèi)心的另一個(gè)不愿觸及的“自己”抽離開(kāi)去:小說(shuō)敘述者張明作為舟山漁民的后代,在查閱了大量“里斯本丸”號(hào)沉船事件的史實(shí)檔案,以及逐漸了解到自己生活的海域曾遭遇的人性的至暗時(shí)刻,為了抵御來(lái)自歷史幽微處的沉重壓迫而試圖撇去的那一層“黑暗”的自己;張明的異國(guó)戀人香織試圖剝離掉自己因“日本人”身份而包含的歷史遺賬與民族恩怨;敏妮想要抹去其在上海淪陷期間為了保全性命而出賣肉體的不堪記憶。事實(shí)上,小說(shuō)另有一個(gè)人物同樣希冀形成“現(xiàn)實(shí)的自己”與“想象的自己”的分離,他就是成年后依舊生活在群島一隅的阿卷。這個(gè)協(xié)助救下伊恩等英國(guó)戰(zhàn)俘的“小恩人”,長(zhǎng)久以來(lái)都受困于伊恩以報(bào)恩為名設(shè)下的漫長(zhǎng)的“現(xiàn)代性的誘惑”。也正是如此,“從少年到青年,阿卷一直想象有另一個(gè)自己在香港求學(xué)”m,“另一個(gè)自己”成了阿卷人生難以抵達(dá)的欲望鏡像。可以認(rèn)為,阿卷在某些時(shí)刻的悵然若失多來(lái)源于這“被壓抑的現(xiàn)代性”,源于成年后的自己未能同年少時(shí)所預(yù)設(shè)的“外面的世界”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勾連。然而恰是這種潛在而未能實(shí)現(xiàn)的分離,以及阿卷父母在面對(duì)伊恩的報(bào)恩請(qǐng)求直言的“我們有我們的生活”n,構(gòu)成了“伊恩們”在試圖履行“文明使命”時(shí)無(wú)法一馬平川的“塊壘”。需要指出,舟山漁民的高貴之處,不僅在于他們冒著可能會(huì)被日軍屠戮的危險(xiǎn),救下伊恩等從“里斯本丸”號(hào)跌落海中的英國(guó)俘虜,更是由于他們?cè)诿鎸?duì)曾經(jīng)的被救助者,以及被救助者以“報(bào)恩”之名的“現(xiàn)代性的誘惑”時(shí),選擇了拒絕,選擇了另一種不主動(dòng)襲仿的人生結(jié)構(gòu)與日常情態(tài)。“我們的生活”不是空洞無(wú)力的語(yǔ)法表達(dá),不是被“伊恩們”這些所謂“文明優(yōu)越者”刻意忽視的景觀標(biāo)本,而是具有無(wú)限張力的寂靜之聲。作為一種文明傳統(tǒng)的樸素原型,“我們有我們的生活”重新定義了被現(xiàn)代性任意“加速”或“減速”、“增容”或“壓縮”的時(shí)間概念與空間概念的來(lái)處。
舟山漁民強(qiáng)調(diào)“我們有我們的生活”及其延伸開(kāi)來(lái)的豐盈而堅(jiān)定的信念立場(chǎng),指涉為現(xiàn)代文明單向度演進(jìn)坦途中,無(wú)法輕易馴服的存在對(duì)象。而另一層使現(xiàn)代文明及其追隨者時(shí)時(shí)陷入進(jìn)退維谷境地的來(lái)源,是個(gè)體穿過(guò)歷史裂縫、瞥見(jiàn)現(xiàn)實(shí)與未來(lái)的書寫行為。這在小說(shuō)《海上繁花》里指向兩個(gè)方面:其一是敘述者張明以小說(shuō)樣式完成的對(duì)1942年“里斯本丸”號(hào)沉船事件的梳理與追溯;其二是作者楊怡芬跨越“歷史”與“當(dāng)下”、“現(xiàn)實(shí)”與“虛構(gòu)”界限而完成的《海上繁花》。通過(guò)書寫行為,后來(lái)者以特定的縫隙路徑回到了擬真的歷史場(chǎng)景,但他們并非僅以此成為歷史碎片的搜尋者與還原者,這也是《海上繁花》更為核心的意義所在——所有的聲音匯聚于今,成為“當(dāng)下”這個(gè)愈發(fā)被現(xiàn)代性幽靈掌控的“算法時(shí)代”的質(zhì)疑者與破局者。舟山青年張明對(duì)1940年代“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歷史鉤沉與文學(xué)創(chuàng)作,看似是偶然的個(gè)體行為,但卻裹挾著歷史必然性的沉重回響。此外,張明的書寫行為,也是反思國(guó)內(nèi)眾多小說(shuō)創(chuàng)作中異常普遍的“教育功能”及其以“正/反”為要旨的觀念批判,并且代之以“人”何以為“人”的終極追問(wèn)。如張明小說(shuō)楔子部分涉及的那個(gè)“面目模糊”的“香織”,香織本人就有如此感慨:“至于那個(gè)在楔子里不停出現(xiàn)的‘香織’,阿明君一會(huì)兒以為‘香織’會(huì)是愛(ài)麗絲,一會(huì)兒以為‘香織’會(huì)是敏妮,他始終沒(méi)有寫出是個(gè)怎么樣的女人,對(duì)吧?”,香織意在指出“不確定,才是目前最真實(shí)的。阿明還是把我當(dāng)一個(gè)鮮活的女人在愛(ài),而不是一種觀念。”o從這個(gè)角度而言,虛構(gòu)的小說(shuō)家張明與現(xiàn)實(shí)的小說(shuō)家楊怡芬以“里斯本丸”號(hào)沉船事件為主線的書寫創(chuàng)作,并非基于一套陳舊的道德教化立場(chǎng),相反,小說(shuō)內(nèi)外的兩位作者的深層次目標(biāo)都是為了重新思考“我”與“她”、“我們”與“他們”在新的時(shí)代語(yǔ)境下的情感結(jié)構(gòu)與維系紐帶——此處的“我”與“她”、抑或“我們”與“他們”,隱顯作者試圖超越某種片面性、對(duì)立性的民族情感與價(jià)值判斷的理念寄托。
盡管《海上繁花》被作者賦予的一個(gè)明晰的主題,是如何尋找“明媚的事物”對(duì)抗“黑暗吞噬”。楊怡芬在2023年的某次小說(shuō)分享會(huì)上坦言,《海上繁花》之所以穿插張明與香織的跨國(guó)戀情,很大程度上源于“明艷色彩”的敘事訴求。p但這并不意味著關(guān)乎此部分內(nèi)容的解讀,僅僅纏繞于兩性情愛(ài)層面。這段貫穿小說(shuō)始終的“舟山愛(ài)情故事”,實(shí)則是改革開(kāi)放時(shí)代的青年如何厘定歷史、現(xiàn)實(shí)與未來(lái)的向度,如何看待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性的位置,又是如何“到世界中去”的特殊隱喻。尤其是當(dāng)他們之中的部分青年借由歷史碎片深刻地感受到了那種壓垮魂靈的悲痛與沉重,包括悲痛與沉重是如何附著于自己身上且成為無(wú)法克服的精神障礙,也就意味著青年業(yè)已無(wú)法收縮于狹隘的一己之歡,同時(shí)也意味著新時(shí)代的青年群體不應(yīng)再將歷史維度發(fā)生的恩怨情仇全然標(biāo)簽化、符號(hào)化。
在此基礎(chǔ)之上,小說(shuō)觸及20世紀(jì)三代人迥異的歷史觀與現(xiàn)實(shí)觀。《海上繁花》以張明前往日本大阪,在香織家人的見(jiàn)證下向戀人求婚收尾。但有意思的是,香織的奶奶與母親在此期間的關(guān)注點(diǎn)各有不同。香織奶奶在意的是“她”和“她們”是否都會(huì)被張明寫進(jìn)小說(shuō),而香織母親更加在意張明向香織求婚的戒指好看與否,這其實(shí)也是“向后看”與“向前看”這兩種顯豁觀念的映照與對(duì)峙。而張明面對(duì)香織奶奶拋出的問(wèn)題,回應(yīng)以“只是寫進(jìn)了小說(shuō)的楔子部分。楔子嘛,就只要盡到楔子的本分就可以了”q,這是一類新世代青年對(duì)待歷史、當(dāng)下與未來(lái)之間關(guān)系時(shí)的態(tài)度。無(wú)關(guān)“解密”,僅為“呈現(xiàn)”。應(yīng)看到,《海上繁花》“楔子”部分的張明、香織,以及張明和香織背后牽涉的家庭、地域、國(guó)族,事實(shí)上都是歷史在特定階段的“引言人”,而過(guò)往歷史則似是長(zhǎng)久以來(lái)隱于舟山海域深處的“里斯本丸”號(hào),其沉默不言相關(guān)聯(lián)的是另一種需要得到重視的眾聲喧嘩。“引言人”所要做的不是將“自我”傳奇化或是走失于歷史敘事的迷宮幻象,而是借自己之所見(jiàn),或者如楊怡芬自言的“找到一個(gè)聲音,找到敘述的基調(diào)”r,將后來(lái)者的情感與思考引向那片寬廣的海域與那片海域擁有的人性之光。
因之,張明創(chuàng)作的那些有關(guān)1940年代“里斯本丸”號(hào)沉船題材的小說(shuō),首先達(dá)成的是張明指向內(nèi)部的“自我教育”(這顯然也是作者楊怡芬的“自我教育”)。而張明完成小說(shuō)后關(guān)乎某些人物形象、某些文明理念、某些敘述基調(diào)的自我懷疑與在此基礎(chǔ)上的自我生長(zhǎng),都是旨在充分表明對(duì)一種既定的價(jià)值立場(chǎng)、情感結(jié)構(gòu)的審視與重塑。“懷疑性”與“生長(zhǎng)性”是張明與香織,包括這個(gè)世代更多青年“到世界中去”與作為“世界中”的“行動(dòng)者”的必要前提。他們聯(lián)系與對(duì)照的,是半個(gè)多世紀(jì)前居于海島的少年阿卷在“這輩子第一次見(jiàn)到白種人”時(shí),曾憧憬地將自己的地域時(shí)間與“外面的世界連接在一起”。但對(duì)“張明們”來(lái)說(shuō),他們已然不再必須因“和外面的世界連接在一起”淪為現(xiàn)代意志的獻(xiàn)祭品,他們完全可以憑借自己的“聲音”講述何謂“一命”,何謂“一星”。面對(duì)蔓延全球的現(xiàn)代性魅影的“召喚”,“反召喚”恰恰成了張明、香織,包括小說(shuō)《海上繁花》之外的青年讀者們面向世界、進(jìn)入世界的應(yīng)有之義,一種新的意義層面的“我們有我們的生活”由此展開(kāi)。
注釋:
a龔晶晶:《14位英國(guó)老人在舟山尋找父親,揭開(kāi)一場(chǎng)77年前的沉船慘案》,“明州世相”2019年11月28日。
bcdehikmnoq楊怡芬:《海上繁花》,北京出版集團(tuán)、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138頁(yè),第31頁(yè),第193頁(yè),第209頁(yè),第239—240頁(yè),第297頁(yè),第49頁(yè),第279頁(yè),第301頁(yè),第321頁(yè),第321頁(yè)。
fg[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極端的年代:1914—1991》,鄭明萱譯,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639頁(yè),第59頁(yè)。
jl[英]齊格蒙特·鮑曼:《現(xiàn)代性與大屠殺》,楊渝東、史建華譯,彭剛校,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97頁(yè),第197頁(yè)。
pr楊怡芬、何玉新:《打撈沉于海底的二戰(zhàn)記憶》,《天津日?qǐng)?bào)》2023年11月7日。
(作者單位:浙江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人文與傳播學(xué)院)
[基金項(xiàng)目:國(guó)家社會(huì)科學(xué)基金重大項(xiàng)目“社會(huì)主義文學(xué)經(jīng)驗(yàn)和改革開(kāi)放時(shí)代的中國(guó)文學(xué)研究”(項(xiàng)目批準(zhǔn)號(hào):19ZDA277)、浙江省哲社科規(guī)劃課題“改革開(kāi)放時(shí)代中國(guó)小說(shuō)的知識(shí)分子書寫研究”(項(xiàng)目批準(zhǔn)號(hào):24NDJC316YB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