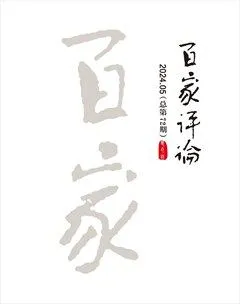地方經(jīng)驗(yàn)與記憶的詩(shī)學(xué)
內(nèi)容提要:老四是活躍于新世紀(jì)詩(shī)壇的80后詩(shī)人,他善于書寫“自我”與生存世界的多重關(guān)系,致力于深層生命經(jīng)驗(yàn)的開鑿與書寫。老四詩(shī)歌有強(qiáng)烈的“在地性”,這一方面體現(xiàn)為他對(duì)沂蒙故鄉(xiāng)和生活地濟(jì)南的地域經(jīng)驗(yàn)書寫,更體現(xiàn)為他在漂泊行旅過程中的文化體驗(yàn)與精神地理建構(gòu)。他對(duì)地方經(jīng)驗(yàn)的呈現(xiàn)與審視,實(shí)現(xiàn)了從“文化地理”向“精神地理”的詩(shī)學(xué)轉(zhuǎn)化。老四對(duì)文化傳統(tǒng)的高度自覺與詩(shī)學(xué)實(shí)踐,構(gòu)筑了宏闊而又堅(jiān)固的精神底座,召喚著詩(shī)歌審美的多元建構(gòu)。
關(guān)鍵詞:老四 詩(shī)歌 自我 地方經(jīng)驗(yàn) 文化傳統(tǒng)
老四是活躍于新世紀(jì)詩(shī)壇的80后詩(shī)人,他在大學(xué)期間開始寫詩(shī),2006年在《山東文學(xué)》發(fā)表處女作,2013年參加《人民文學(xué)》第二屆“新浪潮”詩(shī)會(huì),2019年成為山東省作協(xié)第五批簽約作家。2013年到2014年間,是老四詩(shī)歌創(chuàng)作的轉(zhuǎn)折期和成熟期,他逐漸脫離80后青春寫作的集體合唱,開始在詩(shī)歌中發(fā)出自己獨(dú)特的聲音。閱讀老四的詩(shī)集如《自白書》(文學(xué)魯軍新銳叢書,山東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沂蒙筆記》(張煒工作室文叢之一,即將出版),會(huì)發(fā)現(xiàn)其中的一些詩(shī)歌文本仍不乏80后詩(shī)歌中普遍存在的青春書寫與感傷氣息,但更多是一種具有審美辨識(shí)度的詩(shī)歌聲音呈現(xiàn)。這種獨(dú)特的詩(shī)歌面貌既與他的語(yǔ)調(diào)和修辭相關(guān),更是其生命經(jīng)驗(yàn)的獨(dú)特體現(xiàn),標(biāo)志著一個(gè)詩(shī)人建立了獨(dú)屬性的詩(shī)性語(yǔ)言與詩(shī)藝機(jī)制。老四善于書寫“自我”與生存世界的多重關(guān)系,致力于深層生命經(jīng)驗(yàn)的開鑿與書寫。老四詩(shī)歌有強(qiáng)烈的“在地性”,這一方面體現(xiàn)為他對(duì)沂蒙故鄉(xiāng)和生活地濟(jì)南的地域經(jīng)驗(yàn)書寫,更體現(xiàn)為他在漂泊行旅過程中的文化體驗(yàn)與精神地理建構(gòu)。老四詩(shī)歌中的抒情主體,孤獨(dú)而又敏銳,封閉而又敞開,不停地出走而又歸來(lái),始終葆有一種詩(shī)性的張力。近年來(lái),隨著詩(shī)歌心智的愈發(fā)成熟和文化心理的持續(xù)覺醒,他愈發(fā)倚重地方經(jīng)驗(yàn)與文化傳統(tǒng),在對(duì)齊魯大地上的山川河流、歷史文化和生存景觀的深度開鑿中敞開詩(shī)歌經(jīng)驗(yàn),嘗試著從個(gè)體經(jīng)驗(yàn)書寫到文化記憶書寫的范式轉(zhuǎn)型。
一、“一個(gè)人”及其精神鏡像
老四詩(shī)歌的抒情基點(diǎn),最初來(lái)自對(duì)“一個(gè)人”之生命與情感狀態(tài)的詩(shī)性體悟。“一個(gè)人”是老四早期詩(shī)歌反復(fù)出現(xiàn)的主體稱謂和生活狀態(tài),這在某種意義上構(gòu)成其詩(shī)意發(fā)生的起點(diǎn)。他在《一個(gè)人》中以“詠嘆調(diào)”的方式書寫這種情境:
“在文字里持刀遠(yuǎn)行/這么多年我只是一個(gè)人/一個(gè)人坐公交車,車上空無(wú)一人/一個(gè)人上班,單位空無(wú)一人/一個(gè)人赴酒局,宴席上空無(wú)一人/一個(gè)人在人山人海,人山人海里空無(wú)一人”
某種意義上,這首詩(shī)可以看作是一個(gè)詩(shī)人的宣言。在中國(guó)文化中,“以筆為刀”有著漫長(zhǎng)且深刻的精神傳統(tǒng),“在文字里持刀遠(yuǎn)行”暗示了某種抉擇與無(wú)畏。老四自覺加入“持刀遠(yuǎn)行”的歷史隊(duì)伍,這暗含了對(duì)寫作這一道路之孤獨(dú)、困厄、艱難的體認(rèn)與了悟。“一個(gè)人”意味著某種孤獨(dú)狀態(tài),但這不是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孤獨(dú),而是文學(xué)世界與精神維度的孤獨(dú),這種孤獨(dú)包蘊(yùn)著一種內(nèi)心的堅(jiān)定與無(wú)畏,這種孤獨(dú)甚至是一種刻意的選擇與追求。“一個(gè)人”在深層上是一種精神的高峰體驗(yàn),正是這種心靈與精神上的孤獨(dú)感催發(fā)“詩(shī)人的誕生”。《一個(gè)人》與其說(shuō)是書寫孤獨(dú)體驗(yàn),毋寧說(shuō)是表達(dá)現(xiàn)實(shí)生活與精神生活的碰撞、交融。詩(shī)歌最后的四行,每一行的前半句可看作是寫實(shí),是真實(shí)的生活狀態(tài),后半句則是一種虛構(gòu),具有多重隱喻意涵。這首詩(shī)意味著一種詩(shī)歌創(chuàng)作的狀態(tài)和詩(shī)意燃燒的時(shí)刻,這種句式同時(shí)預(yù)示著老四詩(shī)歌經(jīng)驗(yàn)的敞開,他后來(lái)的詩(shī)歌較多是“空無(wú)一人”狀態(tài)下的精神產(chǎn)物。
“一個(gè)人”意味著某種“獨(dú)處”的精神狀態(tài),老四曾在一篇?jiǎng)?chuàng)作談中引用他心儀的葡萄牙詩(shī)人佩索阿的話,“成為詩(shī)人不是我的野心,而是我獨(dú)處的方式。”他的《水上行》是對(duì)這種獨(dú)處方式的再次確認(rèn):“我愛獨(dú)處/一個(gè)人守著一條河/一個(gè)人和天下所有人戀愛/一個(gè)人懷揣懼怕/一個(gè)人在河上,每一滴水里/安置我的一段孽債”。老四一方面反復(fù)地書寫這一個(gè)孤獨(dú)的內(nèi)心自我,另一方面又不斷地制造出眾多的自我鏡像。與“一個(gè)人”的精神探尋相對(duì),老四詩(shī)歌中的“我”經(jīng)常會(huì)投射出多元鏡像:眾多不同的“我”同時(shí)出現(xiàn),與“我”互為鏡像,與“我”展開對(duì)話,在略顯荒誕的情境中表達(dá)某種悖謬化的生存體驗(yàn)。不斷重臨自我的生命起點(diǎn),在時(shí)間的深處遙望自己,拉開時(shí)間距離審視自我,是老四詩(shī)歌的顯豁主題。他的《自白書》將敘述的起點(diǎn)回溯至“我”從母親子宮降生的時(shí)刻:“人生中第一個(gè)黎明和黃昏/他將愛上青草、汶河,在河邊的菜園里/度過童年,抵達(dá)并不久遠(yuǎn)的中年/他將愛上荒蕪、寂寞,在孤獨(dú)的一生中/治療傷口,最終沿著過去的村道/回歸宿命中的來(lái)處和去處”。不斷重臨生命的起點(diǎn),究其實(shí)是一種精神還鄉(xiāng)。《自白書》寥寥數(shù)筆完成了對(duì)自我人生歷程的悲劇性體認(rèn),是回憶錄,更是啟示錄。對(duì)老四而言,詩(shī)歌是回憶的藝術(shù),是不斷激活個(gè)體精神史的藝術(shù)。他總是在某個(gè)時(shí)刻陷入對(duì)自我的記憶,將之描述為《謀殺時(shí)間的旅程》:“山那邊的一所學(xué)校/多年前我曾在校園里/我看到了無(wú)數(shù)個(gè)我/在樓宇和廣場(chǎng)的縫隙/像螞蟻一樣/奔跑、焦慮、絕望乃至痛哭。”不管是對(duì)“人生中第一個(gè)黎明和黃昏”的凝視,抑或是“多年前我曾在校園里”的場(chǎng)景再現(xiàn),都是此刻之我的一種精神鏡像,這種回望與凝視具有一種“變形”的情感與詩(shī)學(xué)功效,暗含著一種悲劇性的內(nèi)審意識(shí)。現(xiàn)實(shí)之“我”與“我”之鏡像的對(duì)話幾乎每時(shí)每刻都在發(fā)生,就如現(xiàn)代詩(shī)人戴望舒在《我的記憶》中所描述的,“它的拜訪是沒有一定的/在任何時(shí)間,在任何地點(diǎn)”。于是,在《海陽(yáng)至濟(jì)南過濰坊》的車中,詩(shī)人看到,“車窗外,我看到了一個(gè)我/他不是我,是這個(gè)世界的一根稻草”。這是一種由速度而起的精神幻象,高速運(yùn)轉(zhuǎn)的現(xiàn)代交通隱喻了移動(dòng)、飄零的封閉性生存空間,將我們迅速地拋入遙遠(yuǎn)而陌生的世界。德國(guó)社會(huì)學(xué)家羅薩指出,隨著不斷的社會(huì)加速,我們“被拋入世界的方式發(fā)生了轉(zhuǎn)變,而且人類在世界當(dāng)中移動(dòng)與確立自身方向的方式也發(fā)生了轉(zhuǎn)變。”a老四的詩(shī)折射出我們生存背景的模糊與破碎,生存世界因此增添了更多的不確定性。
老四所虛構(gòu)的自我鏡像,在他的詩(shī)歌中不僅僅是“我”在不同時(shí)間與空間中的滋生與繁衍,他還虛擬了其他鏡像化的人物,譬如“兒子”“付小芳”等。在《我可能還有一個(gè)兒子》中,詩(shī)人由自己現(xiàn)實(shí)中的兒子展開想象:“我需要另一個(gè)兒子,作為我兒子的鏡子/作為我的鏡子,作為人間的鏡子//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自己/看到了時(shí)間轉(zhuǎn)化為空間的整個(gè)過程”。在中國(guó)人樸素的倫理觀念中,兒子是血脈和基因的延續(xù),是父親的“新我”,擔(dān)負(fù)著實(shí)現(xiàn)甚至突破父輩人生成就的殷切期待。而在這首詩(shī)中,老四旨在書寫不同生命之間的相互折射、相互印證。“付小芳”是老四詩(shī)歌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人物,從某種意義上說(shuō),付小芳這一書寫對(duì)象,同樣是其自我的某種鏡像,是“我”的情感成長(zhǎng)與心智轉(zhuǎn)型的參照物。付小芳被幻化為各種角色,如《再憶付小芳》中的姐姐:“姐,我用整個(gè)童年、少年虛構(gòu)了你/今日添一件花衣裳,明日增一抹腮紅/眼睛用林黛玉的,嘴巴用紅山子/額頭是一朵喇叭花,尾巴是我牽著你的那只小手/我如何制造你,就如何制造我的過去/如同后來(lái)的二十年把你填進(jìn)記憶的傷疤”。在對(duì)付小芳的“虛構(gòu)”與“制造”中,抒情主體的童年經(jīng)驗(yàn)、情感歷程得以更豐富地敞開。在詩(shī)學(xué)意義上,付小芳的真實(shí)與否、身份歸屬已經(jīng)不再重要,作為“我”的精神鏡像,她的身份愈是多變,“我”的情感世界就愈發(fā)豐富。她因此成為“我”的個(gè)體經(jīng)驗(yàn)與故鄉(xiāng)記憶的凝聚:“你終于成了最圣潔的女人/是所有女人的集合/我的故鄉(xiāng),所有女人聚在你身上”(《付小芳前傳及生之過往》)。這是一種化主觀為客觀、將整體不斷抽離的詩(shī)歌過程,“姐,在我虛擬你的過程中/你也抽走了我身上的許多部件”。在不斷地抽取中,抒情主體的記憶被持續(xù)填充。
二、故鄉(xiāng)記憶中的“精神地理”
從詩(shī)歌寫作之初,老四的詩(shī)歌就有鮮明的地方指向,新世紀(jì)以來(lái)的“臨沂詩(shī)群”構(gòu)成老四詩(shī)歌寫作的背景與“起點(diǎn)”。作為新世紀(jì)山東詩(shī)歌的重要群體,“臨沂詩(shī)群”的獨(dú)異貢獻(xiàn)在于對(duì)地域文化的書寫。《詩(shī)刊》2003年第2期首開“群落展示”專輯,第一期推出臨沂詩(shī)群,標(biāo)志著其作為代表性地域詩(shī)群的正式出場(chǎng)。江非、邰筐和軒轅軾軻被稱為臨沂詩(shī)群的“三駕馬車”,江非以“平墩湖”為基質(zhì)的鄉(xiāng)土經(jīng)驗(yàn)建構(gòu)、邰筐對(duì)臨沂城的浮世繪書寫、軒轅軾軻的解構(gòu)性口語(yǔ)探索等成為新世紀(jì)詩(shī)歌的重要現(xiàn)象。另外如辰水、尤克利、白瑪、朱慶和等以各自的創(chuàng)作展示了臨沂詩(shī)群的豐厚實(shí)績(jī)和多元取向。老四是這個(gè)群體的后起之秀,是地域詩(shī)學(xué)的開拓者。縱觀老四的詩(shī)歌寫作,他始終堅(jiān)守一種“在地性”的詩(shī)歌原則,致力于對(duì)故鄉(xiāng)地理風(fēng)物與情感記憶的書寫,其中建立在河流、親情與鄉(xiāng)愁基礎(chǔ)上的情感勘探,尤為值得重視。
老四曾在創(chuàng)作談中談及張承志《北方的河》對(duì)于他的影響,“河流”是老四故鄉(xiāng)書寫的重要精神空間,是他詩(shī)歌的核心意象,呈現(xiàn)出豐富的象征意蘊(yùn)。老四的詩(shī)集中有多首以“汶河”命名的同題詩(shī),另外還有《黃河行》《河之洲》這樣的小長(zhǎng)詩(shī)。在面對(duì)故鄉(xiāng)時(shí),老四是在與汶河的對(duì)話中喚醒自身的精神記憶,汶河的流淌繪制出個(gè)體精神的地圖,譬如其中的一首《汶河》:
“只有汶河是幸運(yùn)的,它沒有長(zhǎng)成/綿長(zhǎng)的黃河,也沒有揮刀自宮/只把一條細(xì)流完整地送給我的童年/而我也不過是它的一場(chǎng)游戲/它總是把我吞沒/然后又輕輕地吐出來(lái),吐給/遙遠(yuǎn)的天空,以及命運(yùn)”
“吞沒”與“吐出”隱喻著“我”與故鄉(xiāng)之間循環(huán)往復(fù)的“離”“返”關(guān)系。出走,構(gòu)成80后一代人的共同命運(yùn),而返回,則成為80后一代人共同的精神趨向。從汶河到黃河,意味著詩(shī)人從蒙陰到濟(jì)南的生存環(huán)境變遷,也是其精神地理變遷的線索。在《河之洲》這首長(zhǎng)詩(shī)中,老四以河流為線索書寫個(gè)人史,完成了某種關(guān)于河流的總體性詩(shī)學(xué)建構(gòu):“我看見世界上所有的男孩/在同一條河里走來(lái)走去/世界上所有的農(nóng)民也在河里/所有的遠(yuǎn)方和過去,水滴破碎的聲音/與等待有關(guān)的一場(chǎng)夢(mèng)/在靜止的河里,在黃河的所有面孔中/融為一體,不可分割”。《河之洲》既是個(gè)體精神地理的建構(gòu),同時(shí)也呼應(yīng)著我們這個(gè)民族的生存根基,老四的河流書寫最終匯入關(guān)于黃河的總體性經(jīng)驗(yàn)之中。
老四詩(shī)歌中的河流,既包括“汶河”“黃河”等具有鮮明地理標(biāo)識(shí)的河流,他對(duì)那些無(wú)名的河流更感興趣,在他這里,河流史即心靈史,河流構(gòu)成他觀照故鄉(xiāng)的重要入口和鏡像。如《河流史》:“我常常以河流為興奮的起源/沒有誰(shuí)能描繪這么多綠色的小蛇/在丘陵的縫隙里,苦苦掙扎的/像每一座村莊里走出的女子/灰黃的頭發(fā),干癟的乳房”。這些籍籍無(wú)名的河流,流淌著那些無(wú)名村莊中的無(wú)名女子的命運(yùn),由此,河流史也是苦難史,河流成為詩(shī)人老四難以抹去的精神胎記。江弱水說(shuō),“僅三十年來(lái)我們經(jīng)歷著人類歷史上空前規(guī)模與速度的經(jīng)濟(jì)與社會(huì)發(fā)展,從一個(gè)農(nóng)業(yè)社會(huì)一下子進(jìn)入到現(xiàn)代社會(huì),這種急遽的變動(dòng)使人們心理不適,鄉(xiāng)愁成了鎮(zhèn)痛劑和麻醉劑,讓人緩釋焦慮。這一高速發(fā)展的物質(zhì)文明改寫了我們的城市,也使得鄉(xiāng)村失血,鄉(xiāng)土失色。”b老四在無(wú)名河流和灰黃、干癟女子之間的詩(shī)歌比興,恰是對(duì)現(xiàn)代化“加速”語(yǔ)境中鄉(xiāng)村境遇的詩(shī)意撫摸。他反復(fù)書寫汶河,其實(shí)是在撫摸自己的童年和命運(yùn);他不厭其煩地勘探故鄉(xiāng)河流的地理,其實(shí)是在建構(gòu)故鄉(xiāng)與自我的精神流向圖。
多年前,著名詩(shī)人于堅(jiān)有一首題為《故鄉(xiāng)》的詩(shī):“從未離開 "我已不認(rèn)識(shí)故鄉(xiāng)/穿過這新生之城 "就像流亡者歸來(lái)/就像幽靈回到祠堂”。如果說(shuō)于堅(jiān)那一代人是留守的一代,80后則是離開的一代,但這種對(duì)于故鄉(xiāng)的悖論化感受卻驚人的相似。如其在《山中的日子或故鄉(xiāng)》中所寫:
“你善于總結(jié),下午開車在這片山區(qū)行走/小溪、桃林、山崮,洞府中的/鐘乳石寄托了億萬(wàn)年的變遷與視而不見/常遇見墓地,或消失的墓地/你的祖先已風(fēng)化成無(wú)處不在的風(fēng)化本身/一個(gè)念頭讓你停下車對(duì)著/溪水里升起的山崖發(fā)呆:/我身在故鄉(xiāng),卻無(wú)可救藥思念故鄉(xiāng)”
這種“身在故鄉(xiāng)”卻又“思念故鄉(xiāng)”的悖論化感受,暗示了故鄉(xiāng)的歷史巨變,以及這一過程中持續(xù)的精神缺失。《孟王村》是為殘留的村莊立像:“從城市刮來(lái)的風(fēng),風(fēng)里的媳婦們/從更遠(yuǎn)處的村莊朝貢來(lái)的水果和蔬菜/從他們體內(nèi)排泄的鋁合金、碳氧化合物//五分鐘,我們?cè)诖迩f里亂闖,闖著闖著/就走出去了,進(jìn)了另一個(gè)村莊/那么多殘留的老農(nóng)立在路邊,成了活的化石”。這只是一次迷路過程中的“誤闖”,甚至整首詩(shī)也只是某種速寫式的畫像,但其暗含的反思與批判意識(shí)卻相當(dāng)濃郁。“媳婦”與“老農(nóng)”分享著當(dāng)下村莊生活的兩端,一端與城市保持密切的聯(lián)系,“風(fēng)”構(gòu)成隱喻化的時(shí)代書寫;一端則是農(nóng)村的封閉與保守,“化石”強(qiáng)化了“風(fēng)”的剝蝕以及他們無(wú)效而倔強(qiáng)的抵抗。
對(duì)于詩(shī)人老四而言,“親情”是其書寫鄉(xiāng)愁的重要方式。老四詩(shī)集中,對(duì)母親、父親、兄弟和兒子的記憶與書寫,觸目皆是。他在《自白書》中深情回憶“母親”這一身份的生成時(shí)刻,“勞累了一夜的母親,在這個(gè)早晨陷入/持久的睡眠,這是她第一次/以母親的身份,迎接寂靜的光環(huán)”。他在《父親列傳》中追憶父親的日常,“他常偷偷起床,趕著一群蔬菜去往/縣城的集市/凌晨三點(diǎn)或四點(diǎn),總有一些陽(yáng)光/在他的額頭散開”。童年時(shí)代父母雙親的日常生活與情感,往往成為背井離鄉(xiāng)的成年人鄉(xiāng)愁的集聚點(diǎn)。老四對(duì)這些不經(jīng)意瞬間的書寫,以鄉(xiāng)愁之光照亮了暗黑的記憶隧道。沿著親情的線索上溯,老四對(duì)故鄉(xiāng)的精神地理勘探指向?qū)λ劳黾捌湎笳魑锏臅鴮憽W鳛樯媸澜缗c死亡世界的情感觸媒,墳?zāi)辜仁潜狈洁l(xiāng)間常見的地理景觀,同時(shí)成為精神尋根的重要意象。老四的《姥姥的墳》《火葬場(chǎng)》《墓碑》《祖墳》等詩(shī)歌是在對(duì)“死亡”的審視中尋找“我”與故鄉(xiāng)之間的精神紐帶。老四對(duì)故鄉(xiāng)的情感投射,時(shí)常會(huì)聚焦于作為永恒的故鄉(xiāng)之根的墳?zāi)梗缙湓凇赌贡分械慕?jīng)驗(yàn)書寫:“無(wú)碑的墳頭在山坡上兀自/錯(cuò)亂著,不記準(zhǔn)方位和參照物/會(huì)很容易拜錯(cuò)了祖宗”。某種意義上,墓碑才是真正永恒的故鄉(xiāng)。這種無(wú)名的“錯(cuò)亂”狀態(tài),對(duì)于有鄉(xiāng)村生活經(jīng)驗(yàn)的人來(lái)說(shuō)是無(wú)比真實(shí)的,它構(gòu)成傳統(tǒng)意義上的鄉(xiāng)村正在消失的深層隱喻。
老四對(duì)“茶棚村”、沂蒙、濟(jì)南乃至齊魯大地的地方經(jīng)驗(yàn)書寫,在某種意義上已經(jīng)超越“地域經(jīng)驗(yàn)”“地域文化”的所指,而致力于一種“精神地理”的詩(shī)學(xué)建構(gòu)。用詩(shī)人沈葦?shù)脑捳f(shuō),“是一種與地域有關(guān)并超越地域的文學(xué)精神”:“一片土地上的精神地理由那片土地上的人來(lái)呈現(xiàn)。精神地理是與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相呼應(yīng)的概念,卻是超越并提升二者的。我們對(duì)自然、地貌、風(fēng)光、風(fēng)土等關(guān)注較多,對(duì)人,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人、此在的人、人的命運(yùn)、人的掙扎、人的悲劇等則關(guān)注較少。也就是說(shuō),我們常常只留意、只看到一個(gè)地方風(fēng)情和風(fēng)景的表象,看不到人的內(nèi)心。”c老四以故鄉(xiāng)的山川河流、人事流轉(zhuǎn)為基礎(chǔ)所建構(gòu)的詩(shī)歌地理,恰是一種個(gè)人化的“精神地理”,這“不僅是一種地理氣象,更是人的一種精神狀態(tài),是人和地理融合后的一種氣質(zhì)與個(gè)性。”他以自己不懈的精神探索,推動(dòng)了對(duì)地域經(jīng)驗(yàn)的深層勘探,實(shí)現(xiàn)了從“文化地理”向“精神地理”的詩(shī)學(xué)轉(zhuǎn)化。
三、從“個(gè)人史”到“地方志”:詩(shī)學(xué)路徑的轉(zhuǎn)換
在即將出版的詩(shī)集《沂蒙筆記》中,老四將其中的第四輯命名為“地方志”,如果加上前面的“地理書”,讀者會(huì)深切地意識(shí)到他對(duì)地域經(jīng)驗(yàn)的沉迷。從早年對(duì)個(gè)體經(jīng)驗(yàn)的書寫,到近年來(lái)對(duì)地域文化的關(guān)注,老四詩(shī)學(xué)路徑的轉(zhuǎn)換軌跡得以呈現(xiàn)。不妨說(shuō),老四試圖在他的詩(shī)歌中完成從“個(gè)人史”到“地方志”的詩(shī)學(xué)轉(zhuǎn)化。他的前期詩(shī)歌從“一個(gè)人”的孤獨(dú)體驗(yàn)出發(fā),在不斷深入的生命記憶中展開個(gè)人史的講述,個(gè)人史意味著生活史、生命史、情感史和心靈史,在這個(gè)過程中,詩(shī)人調(diào)校著他的詩(shī)學(xué)鏡頭,對(duì)自我的生命歷程進(jìn)行反復(fù)質(zhì)詢與確認(rèn),探測(cè)著自我意識(shí)的諸多可能。但老四沒有遁入空洞玄想或繁復(fù)修辭的詩(shī)歌陷阱,而是堅(jiān)持用口語(yǔ)和樸素的敘事呈現(xiàn)詩(shī)意。他的詩(shī)歌是基于日常生活的基礎(chǔ)之上,母親、父親、兒子、朋友等時(shí)常出現(xiàn)在他的詩(shī)歌中,我們亦可以從詩(shī)歌文本中梳理他的生活史。在此過程中,老四培植了自己的冥想意識(shí)和凝視能力,他經(jīng)常在生活的某個(gè)瞬間陷入冥想,在喧囂的世界中洞見“不同的自己”。如《兒子和祖先在蔬菜大棚相遇》:“后來(lái)天黑了,我什么都看不見了/趴在草氈子上睡著了。父親把我抱下來(lái)/像抱著他的祖先,我們用他的腿走回村莊/星星和田野馱著我們,如同馱著之前的無(wú)數(shù)個(gè)我們”。這是詩(shī)人對(duì)童年經(jīng)驗(yàn)的一種超現(xiàn)實(shí)想象,詩(shī)意的轉(zhuǎn)化與升華了無(wú)痕跡,連接起故鄉(xiāng)的大地和祖先的魂靈,具有一種強(qiáng)烈的文化認(rèn)同感和精神感染力。老四維護(hù)著這種詩(shī)藝的巧妙平衡,彰顯其獨(dú)特的詩(shī)藝策略。
老四對(duì)“個(gè)人史”的精神探尋中,一種來(lái)自歷史深處的文化靈魂不斷閃現(xiàn),這似乎預(yù)言了他后來(lái)對(duì)地域經(jīng)驗(yàn)和文化傳統(tǒng)的執(zhí)著探尋。老四有一些詩(shī)歌可稱為“行旅詩(shī)”,它們多以“訪……”“……道上”等進(jìn)行命名,他在齊魯大地上的行走,訴諸一種精神地理的詩(shī)學(xué)。詩(shī)人徒步翻越蒙山,書寫內(nèi)心的猶豫與矛盾:“把這個(gè)下午塞進(jìn)那個(gè)永恒的初秋/竟有一股懺悔:既辜負(fù)了一座山的挽留/又辜負(fù)了一輛車的速度/我這一生,總是用腳背著/越來(lái)越重的身體,蝸行在飄蕩的風(fēng)里”(《蒙山道上》)。這種矛盾恰恰構(gòu)成我們時(shí)代的生存隱喻,“當(dāng)所有的物件被裹挾到時(shí)代運(yùn)轉(zhuǎn)的高速公路上,詩(shī)歌卻遵照自身內(nèi)在律令的脅迫,以漫長(zhǎng)的心智辯駁、延緩乃至拒斥時(shí)代的加速度。”d詩(shī)人的“懺悔”,是現(xiàn)代人矛盾心理的一種折射,我們既無(wú)法像古人那樣隱居山間,也不愿被現(xiàn)代化的速度裹挾。
老四直面齊魯文化的精神遺跡,他對(duì)山東大地上的歷史遺跡與文化傳統(tǒng)有自覺的對(duì)話意識(shí),這從其詩(shī)集目錄中與之相關(guān)的題目即可粗略得知,他在詩(shī)歌中對(duì)齊國(guó)、魯國(guó)等地域歷史文化展開反復(fù)書寫與對(duì)話。他自稱是東夷人的后代,行走在齊、魯文化之間,探訪齊魯大地上的歷史先賢,為齊魯大地上的山川河流立傳。老四詩(shī)歌的“地方志”書寫,并不是個(gè)體經(jīng)驗(yàn)的完全放逐,而是在更深廣的歷史文化空間中燭照個(gè)體經(jīng)驗(yàn)。《魯南行》在對(duì)“魯?shù)亍睔v史地理的書寫中貫穿了濃郁的歷史憑吊意識(shí),“那些山間的草木,隨時(shí)化為人形/而我準(zhǔn)備著化身一株草/從《論語(yǔ)》《詩(shī)三百》里/流浪而來(lái)的夫子,總是在/第一時(shí)間踏步在我的身側(cè)”,《齊長(zhǎng)城曰》《報(bào)蒲先生書》等通過歷史遺跡或文化逸聞遁入歷史的深處,探尋“我”與歷史文化的深層精神聯(lián)系。老四詩(shī)歌的“地方志”書寫還指向近代的歷史人物與事跡,譬如對(duì)陳克若、“紅嫂”的書寫:“紅嫂不是一個(gè)人,而是許多人的總和/也不是一代人,而是這片山區(qū)/一代又一代女人的集合/比如在更北邊的影視城/村莊以石頭的名義,和山融為一體/電視劇中,紅嫂恢復(fù)年輕時(shí)的模樣/我們的祖母,或祖母的祖母/用永恒不變的愛,承載山區(qū)的/一種樣貌。”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紅嫂’現(xiàn)象是齊魯大地奉獻(xiàn)給20世紀(jì)中國(guó)文化史的一個(gè)豐富的文化現(xiàn)象。”e“紅嫂”不僅是革命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的一種現(xiàn)象,更是一種地域文化精神的傳承,內(nèi)蘊(yùn)著一種文化特質(zhì)。老四對(duì)文化傳統(tǒng)的書寫始終保持一種對(duì)話性,貫穿并高揚(yáng)著詩(shī)人的精神主體性,這實(shí)際上已經(jīng)超越了“地方志”而演化為一種“文化詩(shī)學(xué)”。
老四對(duì)文化傳統(tǒng)的自覺面對(duì)與深度書寫,凸顯了一種詩(shī)歌書寫的“歷史意識(shí)”,如艾略特所言,“我們可以說(shuō)這種意識(shí)對(duì)于任何人想在二十五歲以上還要繼續(xù)作詩(shī)人的差不多是不可缺少的;歷史的意識(shí)又含有一種領(lǐng)悟,不但要理解過去的過去性,而且還要理解過去的現(xiàn)存性;歷史的意識(shí)不但使人寫作時(shí)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還要感到從荷馬以來(lái)歐洲整個(gè)的文學(xué)及其本國(guó)整個(gè)的文學(xué)有一個(gè)同時(shí)的存在,組成一個(gè)同時(shí)的局面。這個(gè)歷史的意識(shí)是對(duì)于永久的意識(shí),也是對(duì)于暫時(shí)的意識(shí),也是對(duì)于永久和暫時(shí)的合起來(lái)的意識(shí)。就是這個(gè)意識(shí)使一個(gè)作家成為傳統(tǒng)的。同時(shí)也就是這個(gè)意識(shí)使一個(gè)作家最銳敏地意識(shí)到自己在時(shí)間中的地位,自己和當(dāng)代的關(guān)系。”f艾略特《傳統(tǒng)與個(gè)人才能》中的這段話,可以作為理解老四詩(shī)學(xué)路徑轉(zhuǎn)換的樞紐。老四以個(gè)體精神史和地域經(jīng)驗(yàn)為基礎(chǔ),在一種整體性的詩(shī)學(xué)視野中審視歷史與文化,建構(gòu)了一個(gè)與不同時(shí)代的“文化亡靈”“精神遺跡”展開對(duì)話的共時(shí)性詩(shī)歌空間,顯示了開闊的文化視野和穩(wěn)健的詩(shī)學(xué)姿態(tài)。對(duì)于一個(gè)青年詩(shī)人而言,這份文化與詩(shī)學(xué)上的自覺是非常難得的。詩(shī)人只有不斷激活本土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在歷史中照見未來(lái),在不斷地對(duì)話中夯實(shí)、加固自己的文化意識(shí),才可能真正理解傳統(tǒng),融入傳統(tǒng),成為這個(gè)傳統(tǒng)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注釋:
a羅薩:《新異化的誕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3頁(yè)。
b江弱水:《詩(shī)的八堂課》,商務(wù)印書館2017年版,第166—167頁(yè)。
c沈葦:《亞洲腹地:我們的精神地理》,《名作欣賞》2016年第4期。
d張?zhí)抑蓿骸稖嫉郎稀罚蹲x書》2003年第2期。
e魏建、賈振勇:《齊魯文化與山東新文學(xué)》,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頁(yè)。
f趙毅衡編選:《“新批評(píng)”文集》,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頁(yè)。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xué)詩(shī)學(xué)高等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