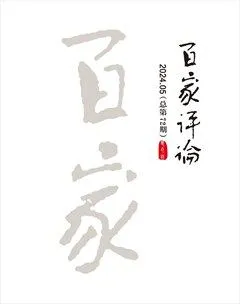共和國文學中的山東經驗
內容提要:新中國成立以來,山東文學參與了共和國文學發展的每一個重要時刻,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近年來,山東作家也在諸多體裁領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他們一方面積極在時代文學主潮中爭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也在關注宏大主題和重點題材領域的同時始終堅守自身的創作特色與個性,力避在創作者高度聚集的領域中迷失自己,在延續山東文學輝煌的同時也展現了獨特的風姿。這背后既有作家自身的努力,也離不開文學制度的保障和助力。
關鍵詞:山東文學 創作個性 文學制度
新中國成立以來,山東文學參與了共和國文學發展的每一個重要時刻,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不可或缺的一個板塊,其發展歷程不僅折射出了社會歷史的深刻變遷,也為人民生活提供了豐富的精神滋養。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山東文學緊貼時代脈搏,高揚現實主義旗幟,努力發掘現實生活中的典型人物與典型事跡,為文壇貢獻出了一系列謳歌英雄、反映人民斗爭生活的佳作。七十多年來,山東文學不僅在藝術上勇攀高峰,也在思想和情感上深刻地影響了廣大讀者。2019年,為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全面展現新中國文學創作成就,學習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單位聯合推出了“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叢書。其中收錄的由山東作家創作的作品就有劉知俠的《鐵道游擊隊》、曲波的《林海雪原》、馮德英的《苦菜花》、郭澄清的《大刀記》、張煒的《九月寓言》、莫言的《紅高粱家族》、楊志軍的《藏獒》等等。這些作品或回顧抗戰烽火、真實再現山東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而可歌可泣的奮斗歷程,或將目光延伸至廣闊的原野、探索知識分子的精神理想,或以“獒性”呼喚人性、書寫另類的啟蒙,不僅展現了山東文學的獨特風姿,也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重要收獲。
當然,山東文學對共和國文學發展的貢獻絕不止于上述作品,也絕不止于一種文體。按當代文學史的分期來說,在文學史的每一個階段,山東作家都貢獻出了數量眾多的“入史”佳作。“十七年”文學史上,楊朔的詩化散文成為這一時期美文創作中耀眼的存在,其獨出心裁的“拐彎藝術”雖然在后來引起了一些爭議,但卻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引來眾多的模仿者。峻青的散文“風格親切自然、質直雄勁,充滿了時代的氣息和作者對生活、對人民的深摯情感”a,其散文代表作《秋色賦》成為膾炙人口的名篇。除此之外,楊朔的長篇《三千里江山》、峻青的短篇小說集《黎明的河邊》、王愿堅的小說集《黨費》等等,也都是這一時期革命歷史題材創作中的名作,它們或細膩描繪戰爭年代的人性光輝,或深刻反映人民生活的希望,共同構建了一個個生動鮮活的歷史場景,成為紅色經典文學脈絡中的重要一環,被許多文學史家遴選入史并專章討論。而這一時期蕭平的兒童文學創作也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兒童文學園地中占有重要位置,其作品中所構建的純凈、溫情而又略帶憂傷的兒童世界,在當時的兒童文學創作中具有很高的辨識度,其關注社會人生、反思批判現實的非兒童題材作品也體現出知識分子強烈的責任感與憂患意識。
新時期以來,“文學魯軍”異軍突起,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等領域遍地開花,佳作頻出,成為備受文壇矚目的現象。小說領域老中青三代作家同臺競技,百花齊放。“不但涌現了張煒等一大批被譽為‘魯軍’的年輕作家,而且五六十年代已經成名的中、老作家如劉知俠、馮德英、李心田、王希堅、李向春等也煥發青春,創作出了顯示著觀念更新的新作;不但有鄉土、地域小說家,也有都市題材小說家;不但有‘純文學小說家,也有通俗小說家……”b張煒、莫言、王潤滋、左建明、尤鳳偉、李貫通、矯健、李存葆、劉玉堂、畢四海、馬瑞芳、劉玉民、趙德發、苗長水、張宏森、劉海棲等人的創作都各具特色,備受文壇關注。
張煒的《古船》以膠東古鎮洼貍鎮1940年代的土地改革到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期間這四十年的歷史作為背景,將社會政治風云激蕩的大事件同洼貍鎮上家族的興衰交織在一起,并且通過一艘“古船”的出土,追溯源流、貫通古今,對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做了深入的思考,同時也對新的歷史條件下經濟改革與現代化的走向問題進行了探索。作品中所貫穿的豐厚的文化底蘊、宏闊的文化視野,深沉的人道主義憂思以及悲天憫人的超越情懷,使得這部小說內蘊極為深厚,具備了一種撼人心魄的藝術感染力,被一些文學史家認為是“當代最優秀的長篇小說之一”。c莫言的《紅高粱家族》等作品深刻剖析了高密東北鄉這一地域背景下農民的生存狀態與歷史變遷,展現了鄉土社會的沉浮圖景,作品不僅在國內文學界引起了廣泛反響,更在國際文壇上贏得了廣泛贊譽,標志著中國當代文學在探索民族性與世界性融合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一步。軍旅作家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環》巧妙地將軍旅生活與社會現實緊密相連,為新時期軍旅文學創作開辟了新的路徑。尤鳳偉的《泥鰍》聚焦于城市底層農民工的生存狀態,體現了對城市邊緣群體的關懷。劉玉堂則以獨特的農人視角和幽默詼諧的筆觸,在《鄉村溫柔》等作品中構建了一個充滿鄉土氣息而又不失現代感的故事世界,被譽為“沂蒙靈手”。劉玉民的長篇小說《騷動之秋》曾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作品生動地講述了商品經濟大潮對鄉村生活和人與人之間關系所帶來的巨大沖擊,并塑造了性格極具張力的農民企業家岳鵬程這一時代新人形象。其他如王潤滋的《賣蟹》、矯健的《老人倉》、苗長水的《冬天與夏天的區別》、左建明的《陰影》《榆王》、李貫通的《天缺一角》、趙德發的《通腿兒》等作品,也各自以其獨特的視角和深刻的主題,成為文壇矚目的對象。在詩歌散文領域,孔孚的山水詩和耿林莽的散文詩、桑恒昌的本色詩學與詩歌創作,馬瑞芳、張煒的文化散文均在文壇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報告文學領域,李延國的《廢墟上站起來的年輕人》《在這片國土上》《中國農民大趨勢》,王兆山的《一篇小雜文與一位大教授的命運演繹》,賈魯生的《丐幫漂流記》《陽間、陰間》以及與王光明合作的《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彭雁華的《蒙山沂水》、郭慎娟的《知識的罪與罰》、李存葆與王光明合作的《沂蒙九章》等等,也都是享譽全國的名篇佳作,為新時期以來報告文學的繁榮貢獻了魯軍力量。在新時期山東文學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一系列齊魯文學地標在中國文學版圖上逐漸凸顯出來,諸如莫言筆下的高密東北鄉,張煒所描繪的膠東半島,劉玉堂的沂蒙山區……這些承載著深厚文化血脈的山東地域標簽成為了展現人性深度與社會變遷的文學高地。
新世紀以來,山東文學同樣保持了良好的發展勢頭,為文藝界貢獻出了一批優秀的作品。張煒的《你在高原》、莫言的《蛙》、楊志軍的《雪山大地》先后獲得茅盾文學獎。王光明、鐵流、徐錦庚、黃發有、許晨、夏立君、路也等也相繼獲得魯迅文學獎。而在“五個一”工程獎、徐遲報告文學獎、老舍文學獎、曹禺戲劇文學獎等全國性重要文學獎項評選中,山東作家也屢屢上榜,展示了新世紀山東作家的創作實力。近年來,山東作家也繼續密切關注著時代主題,深入思考如何用“中國經驗”講好“中國故事”,探索更好地傳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精神,同時也關注個體如何在時代洪流中經歷命運的起伏跌宕,深入剖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人與社會相互塑造以及人與自我心靈對話的錯綜復雜關系。在此基礎上,他們在作品里進一步探尋個體如何在這些關系中尋找平衡與成長,以應對日新月異的社會變革和不斷變化的自然環境從而塑造更加充實和有意義的人生,在一些創作者高度聚集的題材領域中展現出了自己獨特的風姿、續寫著山東文學的輝煌。
一、文學與生態
隨著現代化進程和社會轉型的不斷加快,生態問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守護綠水青山,尋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態理念已經成為新的時代共識。在此過程中,越來越多的作家也開始關注生態命題,生態文學已然成為新世紀以來中國文學創作領域的重要現象。眾多的山東作家也積極介入生態文學創作,貢獻出了不少佳作。張煒的長篇小說《河灣》入選2023年生態環境部、中國作家協會聯合發布的“首批生態文學推薦書目”。這部作品延續了張煒對自然生態的贊頌,生動體現了主人公傅亦銜對現代的反思和對與自然和諧共處的追尋,內中不僅呼吁人們回歸到自然,重新建立與自然的連接,同時也倡導人們在精神層面上反對世俗,尋找真我,體現出了對精神世界的探索和追問。當然,還有許多作家以獨特視角介入了這類創作。李恒昌的長篇小說《大河赤子》巧妙地將張五魁一家人的命運與黃河流域的生態環境緊密相連,通過他們不遺余力地保護象征著村莊歷史的百年大槐樹,以及積極參與守衛黃河入海口的行動,深刻反映了人類與自然環境的依存關系以及對生態保護的責任擔當。楊志軍的兒童文學作品《三江源的扎西德勒》以孩童純真的視角探索三江源的自然奇觀,回憶家庭參與野生動物保護的溫馨故事,緊扣了當代生態保護的時代主題。陳認真的《群羊的轉場》、尚長文的《老楊的世界》也同樣以生態保護為重要主題,分別獲得第四屆全國“大鵬生態文學獎”一、三等獎。立足于現實主義,山東文學創作緊貼時代,深入挖掘生態問題的根源,以文字為媒介,揭示人類與自然之間復雜而微妙的關系,從而呈現出一幅幅真實而深刻的生態圖景。這種對現實及時而又富有深度的關注,使得山東文學作品具有了強烈的時代感和現實意義。
但是,單純書寫生態又容易陷入一種題材和主題的重復,容易流于一種淺層的生態理念灌輸。于是,一些山東作家另辟蹊徑,將生態書寫與其他重大時代命題相結合,使得作品具有了多重內涵和豐富的解讀空間。如楊志軍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雪山大地》即是如此。《雪山大地》不僅可以作為生態文學的文本來加以解讀,同時也切中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脫貧攻堅這一主題,深刻展現了以父親、母親為代表的漢族家庭和以角巴、桑杰為代表的藏族家庭之間歷經三代人的深厚民族情誼以及他們在生死相依中攜手推動沁多草原實現共同富裕與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飽含深情地描摹出極端自然條件下堅韌不拔、奮發向前、無私奉獻的人物群像。從生態文學的角度來說,雪山大地這一自然生態在作品中幾乎被強調到了本體的層面,它既是人類的養育者,也是人類的歸宿。作品中父親之所以能夠得到藏族人的認可,是因為他與藏族人一樣朝拜了雪山大地。小說中幾乎所有人在遭遇困厄時都會念到“雪山大地”,這一行為既是對自身生存環境的一種敬畏,也是一種樸素的生態信仰。在作品中,人與自然是和諧統一的,人類保護自然,自然才能夠給予人類生命以足夠的養料。正是意識到了這一點,在牛羊數量的增長對于草料的需求已逐漸超過草場的承載能力之際,以父親強巴為代表的先覺者開始意識到背后隱藏的巨大危機,并開始著手治理草原沙化,力圖讓草原重新覆蓋綠色,開啟了長達十年的牧民搬遷工程,限制人類活動對草原生態的破壞。作品中的許多情節都頗具象征意味,居住著被隔離的麻風病人的生別離山深處卻有著能夠有效緩解麻風病的苦味“王子茶”,可以讓那些麻風病人能夠延長幾十年的生命,這其實也象征了大自然給予人類的庇護,從另一個側面寫了人與自然的相互依存、和諧統一。結合雪域高原獨特的地域文化環境,作品中對自然生態的尊崇甚至可以上升到自然神性的角度加以闡釋。
而在生態主題之外,小說也以沁多草原為背景,深情書寫了在黨和政府的堅強領導下,青藏高原從奴隸制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巨大歷史變遷過程,并著重寫了變革中所面臨的諸多挑戰:經濟發展困難、牧民受教育程度低、舊頭人的余威尚存、不平等的奴隸思想并未完全根除、“以物易物”的傳統交易觀念也依然根深蒂固等,這一道道難題橫亙在沁多草原邁向現代化的道路上。為了解決這些難題,父親到野馬灘蹲點,在草原建起了第一所牧民學校,還創建了第一個貿易公司,建起了牧民新城,為雪原奉獻了一生;母親苗醫生不懼生死,為救治療麻風病患者而不幸感染麻風病去世,為雪山大地的醫療事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原頭人角巴不僅全力支持新政府,主動改部落制為公社,還為緩解饑荒無私獻上牛羊,號召牧人把孩子送去學校,為保育院、麻風病醫療所提供食物,全力支持草原的發展事業;讀了博士的才讓、“我”、妻子梅朵、央金等人都放棄了在城市的事業或是自己的愛好,回到草原并將生命投入到草原建設之中……在他們的不懈努力下,沁多草原逐漸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奴隸思想被平等思想取代,“以物易物”的交易觀念也逐漸被現代市場經濟所取代,義務教育進入草原,草原上的牧民們開始享受現代城市的便利……作者用大量生動的細節和鮮活飽滿的人物形象真實再現了沁多草原人們所經歷的歷史性變革,在生態文學通常所具有的共時性向度之外,也在歷時性向度上做了重要的開拓,使得作品具有了濃重的史詩意味。而不拘泥于生態文學的單一向度,同時在作品中回應并掘進多重時代命題,也是《雪山大地》在眾多同類作品中成功“突圍”的原因之一。
二、現實,怎樣看與怎樣寫?
近年來,一些山東作家也聚焦于現實生活,成功捕捉并展現當代社會的種種問題,通過對社會現象和人物命運的深入挖掘,引申出對社會發展現實的深刻思考。同時,他們也關注人物的生存困境,以豐富的情感表達和深刻的人性洞察給予讀者持久的溫暖和啟示。趙德發的《經山海》描繪了以吳小蒿為代表的鄉鎮干部如何將個人經歷融入鄉村振興的過程,刻畫了女性在多重社會角色間的選擇與掙扎。作品還敏銳地捕捉到了鄉村短視頻領域為迎合網絡流量而出現的低俗化傾向等熱點問題,并呼吁建立更加健康、理性的鄉村文化傳播生態。王方晨的《花局》聚焦于虛構的“花局”,深刻剖析了官場腐敗的亂象以及小人物個體意志被集體意志裹挾的現實問題。阿占的中篇小說《后海》,筆觸聚焦于青島這座城市的地理變遷與社會發展,生動展現了青島跨越百年的工業發展歷程。吳丹的長篇小說《鯨落果園》作為“非傳統的石油題材小說”則觀照著工業生產之外的工人心理與工人生活。總之,眾多的山東作家緊緊注視并思考著變革中的社會現實,及時將之付諸筆端,展現出了濃烈的“在場”熱情。
2023年問世的王方晨的《大地之上》是一部充溢著鄉土氣息和人文關懷的長篇小說。《大地之上》是鄉土題材,但主角卻是城鎮化后被架空的“農民”。“大地上沒有我的一棵莊稼。”d這是子在川會長的感慨,卻深刻揭示了對于農民來說,作物以生命的形態表達了人與自然的相互依賴。圍繞香莊搬遷這一線索,作品關注的就是這些失去土地而“一無所有”的被架空的農民的角色。內中所塑造的郭二毛、江玉枝、張福慶、趙國瑞等眾多鄉村世界中的人物形象都頗具代表性,他們的生活展現出的是社會變革過程中真實的鄉村生活風貌。
根據庫茨涅茲和克拉克的理論,經濟學界普遍認為城市化主要特點是第二、三產業的增長以及農村人口向城鎮的轉移。e農民作為農村社會的基本單元,在鄉土社會變遷中其身份和角色的轉變被視為社會轉型的微觀反映。這樣的角色轉變也催生了農村社會結構、道德倫理原則和生活方式的巨大轉變。城鎮化過程中,鄉村人該何去何從?《大地之上》對“離開故土”這一命題進行了多元化的探討。作品通過三個頗具代表性的女性形象,探討了農民離開故土“出走”之后的路徑選擇。一點紅、金蘭、二毛,她們各自代表了三類不同的出走農民。一點紅是“想出走”卻無法出走的農民;金蘭是具有反思意識、能夠在社會變遷中迅速把握機遇轉型并確定自己新身份的農民;而二毛,則不僅是香莊無法生育的婦女,更是鄉村與城市、傳統與現代沖突的象征。她的“不能生育”不僅是一個生理特征,更是一種隱喻,暗示著鄉村在現代文明沖擊下的困境和無力。作者通過不同角色的命運軌跡形象地展示了農村生活從傳統到現代的全方位轉向和社會關系對個體身份認同的深刻影響,為觀照鄉土社會變遷、理解中國社會發展路徑提供了新的視角。
鳳歧和宗利華都有長期從事紀檢、警察工作的經歷,積累了豐富的寫作素材。二人共同創作的《天下人心》將視野聚焦于社會關注度極高的“反腐”領域。以往的反腐小說中,辦案人員往往會被刻畫為無畏的戰士形象,然而《天下人心》在凸顯辦案人員堅定“戰士”面孔的同時,也用大量筆墨書寫了他們作為普通人的一面。辦案人員葉音的心理健康問題、張浩的病情及其家庭困境、燕飛的死、朱克艱的病等情節,看似瑣碎,但卻凸顯了人物形象的立體與真實。他們有歡樂有悲傷,有執著有掙扎,甚至齊九天、凌云、武來、孫岱、張兵、莊嚴、郎永軍、顧世言等貪官也都各有特點,人性的復雜和矛盾被生動準確地展示了出來。
另外,《天下人心》也富有古代“傳奇”色彩,作品不僅采用了傳統的章回體小說敘事框架,實現了情節的起承轉合與首尾呼應,更融入了許多具有傳奇色彩的情節,增強了可讀性。在張兵被誘殺的情節里,郎子君假扮“黑白無常”來增加恐嚇張兵的效果,而郎子君在被顧世言逼迫自殺時,吟唱著《哀溺文》跳崖,顧世言卻做賊心虛仿佛見到了郎子君的鬼魂,甚至仿佛還聽到郎子君大喊“要你命的人來也”……這些情節設置,增強了藝術感染力,也使得作品具有了濃厚的“傳奇”韻味。除此之外,“大團圓”式的結尾,將大量人物形象匯聚在一處,也給人以戲劇謝幕式的視覺沖擊。可以說,發掘傳統文化資源并實現其創造性轉化,也是這部小說取得成功的關鍵性要素之一。總之,在追求“在場”、密切關注現實的同時,山東作家們也在題材、主題、敘事技巧等方面不斷尋求創新,并積累了一系列成功的文學經驗。
三、時代變革中的非虛構
非虛構作品、報告文學、紀實文學以其真實、客觀的特性,成為記錄時代變遷和社會發展的重要載體,也推動了文學界對現實主義的再度審視與重新開掘。盡管學界對這些概念的界定尚存爭議,但這三者在密切文學與現實生活的關聯方面所具有的優勢則早已是共識。
近年來,山東作家積極深入生活,獲取了豐厚的現實滋養,用手中的筆生動地描繪了山鄉巨變的壯麗畫卷。在這些作品中,讀者不僅看到了山鄉面貌的煥然一新,看到了改革開放的巨大力量,也看到了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如何在時代的洪流中積極尋求自身的定位和人生價值的實現。文學是人學,一直以來,報告文學的主體也都是人。但近些年來一批以城市或大江大河為主體的報告文學作品卻成為文壇值得關注的一種現象,山東作家在這方面也貢獻出了不少優秀之作。張中海的《黃河傳》獲第九屆“徐遲報告文學獎”長篇獎,作品從黃河這一中華民族的母親河的地理成因切入,深入挖掘了黃河所承載的厚重民族歷史文化。通過講述黃河歷史上多次斷流的經歷,巧妙地引出了黃河流域人民世代相傳的深刻共識——“河潤邦昌”。王秀梅的《渤海傳》以渤海區域真實的地理空間和歷史時間為坐標,以“一峽三灣”與“黃渤海分界線”所形成的閉合結構為敘述整體共同構筑成一個空間,其中既滲透著作者對家鄉的熱愛,也隨處體現著以作者為代表的黃河子民對這片地域新風貌的認同感。朵拉圖和逄春階的《家住黃河灘》、孟中文的《大河平野》從獨特的視角記錄了黃河灘區民眾群體在脫貧攻堅與遷建歷程中共享的艱辛奮斗記憶。鐵流的《靠山》和厲彥林的《沂蒙壯歌》則以非虛構手法,分別展現了沂蒙革命老區歷史與當下延續“黨群同心、軍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與共”的沂蒙精神。通過書寫帶有獨特區域記憶與集體想象的歷史文化,這些作品具有了獨特的身份標識。
以《黃海傳》為例,這部出版于2023年的作品是新時代海洋文學的優秀之作。作品深入探討了黃海的歷史變遷、文化脈絡、科技進步等議題,內中既融入了作者基于豐厚的科學素養而形成的對海洋的深刻認知,也凝聚了作者對海洋歷史文化的理解與贊嘆。全書由“亙古滄溟”,“藍海帆影”,“風云激蕩”和“巨變種種”四個部分構成。雖然在形式上有點類似于古代的方志,但卻遠非傳統方志所能概括。它不僅是對一個區域的物產、地理、人文等方面的記述,更包含了對整個黃海區域以及那些生活、勞動、戰斗、繁衍在黃海周邊的人們的詳盡描繪。作品不僅關注黃海的海洋生物、地貌、氣候等自然現象,也深度探究了黃海作為文化載體所承載的廣泛的社會、歷史、民俗、宗教等指向。在作者筆下,黃海不僅是一個生態系統,更是一個生動活潑的具有地域特點的人文區域,例如由于有著制鹽的傳統,日照濤雒鹽場周邊有許多個叫“廒頭”“灶子”的村莊,獨特的歷史資源和鹽場環境給這些村子刻下了難以磨滅的烙印,或許這才是為黃海作傳的真正意義所在——通過歷史與未來的交織找到人們對這片歷史文化底蘊深厚的海洋區域的原生歸屬感。
如果說《黃海傳》是一部由沿海漁民共同鑄造的海洋文化傳記,那么2023年出版的李桂華的《看云起——中國“菜籃子”的共富樣本》就是有關特定地域發展的城市文化傳記。不同于《黃海傳》注重歷史的長度,《看云起》選擇了歷史的一個截面——改革開放以來為解決“三農”問題,壽光人是如何以勇于爭先、積極進取的精神發展出“壽光模式”的。作品圍繞王伯祥為代表的一批有遠見的干部,抓住中央推進農村改革的機遇,努力發展蔬菜產業、打造“壽光模式”展開敘述,深情敘寫了他們引進冬暖式大棚、開發無公害蔬菜、建設高科技示范園、舉辦國際蔬菜博覽會,以及研發國產蔬菜種子、建設雙王城水庫與生態經濟園、創辦大學為社會發展提供人才保障、執著探索工農業協調發展的復興之路等偉大創舉,同時也歌頌了壽光人將這些經驗無私向全國推廣,為鄉村振興國家戰略提供壽光智慧的廣闊胸懷。在鄉村振興的道路上,涌現出了許多著名的鄉村典型,比如華西村、南山村等等,但許多鄉村典型的發展模式都與自身獨特的經濟文化資源緊緊捆綁在一起,難以推廣和復制。而壽光模式的推廣和復制卻已經在許多省份落地生根,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在邁向現代化、走向民族復興的路途中,這是一種無價的智慧。作品深入淺出地講述了壽光模式的發展脈絡與經驗教訓,飽含深情地謳歌了在壽光模式生成過程中涌現出來的一大批先進人物,審美價值與認識價值并重,是一部在現實土壤里生長出來的優秀作品。
總的來說,作家們在以非虛構的方式書寫現實時,都展現出深邃的歷史眼光和廣闊的文學視野,他們準確地捕捉到了歷史的流變,用豐富的細節描寫助力作品豐盈,同時也不約而同地扣住了一些備受關注的時代命題進行了深入的探索。“有非虛構,但少文學”是當下非虛構文學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但從山東作家的創作實踐來看,絕大部分作品在追求真實和藝術的平衡方面都做得比較成功,這些探索也是非虛構文體實踐所取得的新成就。
四、網絡文學的新面貌
網絡作家已成為山東文學創作隊伍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隨著山東省網絡作家協會的組建和陸續開展活動,網絡作家有了正式的溝通交流平臺,許多網絡作家在繼續深耕自身創作領域的同時,也將目光投射到廣闊的現實生活中。過去、現在、未來,玄幻與寫實,類型化與藝術探索,傳統文化與跨文化多向并進,開拓出了網絡文學創作的新生面,取得了眾多可喜成就。
風御九秋的《參天》通過主人公在亂世中的成長與抉擇,展現了人性的復雜與堅韌,以其深沉的歷史底蘊和細膩的敘事手法在眾多類型化作品中脫穎而出;言歸正傳的《這個人仙太過正經》以輕松幽默的風格和獨特的仙俠設定贏得了眾多讀者的喜愛;清閑丫頭的《仵作娘子》以獨特的女性視角和探案元素,為網絡文學注入了新的活力;傲天無痕的《九天玄帝訣》則以其宏大的世界觀和精彩的戰斗場面,吸引了大量喜歡熱血玄幻題材的讀者;小歲夕的《賽博時代的魔女》作為賽博朋克小說,利用科技改造人類身體的設定將人放在高科技的控制之下,卻又制造了魔女這類非人類生命體產物,加深了讀者對科技與人類關系這一主題的全面理解;草廬煮咖啡的《數字基石》以網絡文學特有的敘事手法和風格,描繪了陳天明帶領華泰軟件公司突破國外CAD軟件壁壘的歷程。作品巧妙融合了網絡文學的代入感與行業敘事的嚴謹性,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起科普教育、文化傳播的功能,呈現了一種網絡文學創新敘事的探索。
2023年7月,黑山老鬼的《從紅月開始》獲頒第二屆“天馬文學獎”。《從紅月開始》重新開掘了“心理”主題。這部“玄幻”小說詳細描繪了紅月亮事件后,末世降臨,人們普遍遭受精神污染,變得抑郁、自閉、自虐或者發狂。但也有人因為“紅月亮”獲得了特殊能力,主角陸辛就是其中之一。小說圍繞破解精神污染的主線,展開了一系列故事,比如“紅玫瑰”事件、人形果實樹事件、開心小鎮事件、人臉縫合怪事件等,這些精神污染的怪物其實都是基于人類負面情緒而產生的,隱喻著困擾現代人的心理健康問題,如抑郁癥、自閉癥、強迫癥、精神分裂等。《從紅月開始》看似玄幻,實則是對精神疾病的一次深入探討。作品在構建恐怖懸疑氛圍時,并未拘泥于傳統的鬼怪或血腥描繪,而是在人們日常熟悉的空間中加入不同尋常的“精神壓力”元素。這些元素精準地對應了讀者內心的焦慮,會自然而然地引發讀者的聯想與共鳴。
比如作品中寫到了現代打工人熟悉的一個場景——咖啡館,并將其塑造成了一個精神污染怪物的據點,進入這個咖啡館的被污染者大部分都會因為抑郁而自殺。另外,對工廠內部不合理的工作時間安排問題,作品也有所觸及,這同樣有現實生活的映照。其中,039號特殊污染源揭示的就是工廠的企業家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迫使工人們晝夜不停地勞作,即便在工傷的情況下也不得停歇。這種極端的工作模式不僅嚴重侵犯了工人們的合法權益,更對工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極大的損害。作品通過這一情節的描繪深刻揭示了一些企業對工人權益的漠視與剝奪,引發了對現代工業生產中勞動者權益保護問題的深刻思考。
從主題層面來說,小說還表達了對科技發展的隱憂和對如何用理性和人性創造更好的世界的回答。《從紅月開始》共享了洛夫克拉夫特的克蘇魯設定,因此它也共享了“理性”與“瘋狂”的質詢。作品中,科學家們偶然發現地球有一位無意識的“神”,它會在地球的文明發展到一定高度時“回收”文明,再重新創建文明,因此創建了研究所開始研發“創世硬盤”,并試圖給“神”注入意識從而擺脫輪回,結果造成了紅月亮爆發。然而還有兩類人在試圖拯救世界,一類是試圖造就“諾亞方舟”逃避災難,一類是試圖祭祀整個世界以結束末世。他們都是人類試圖以“理性掌控一切”的代表。只有陸辛基于對人性的認識一步步成長,最終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并最終戰勝了“神”。由此,作品中揭示出,如果一味強調人類能夠掌控一切,崇信理性主義,就容易陷入與黑臺桌組織相類似的不將人當人的境地。因此,人類永遠不應該忘記人性中最純粹的愛與善……這樣的思考是相當深刻的,顯示出作品對于現代人精神困境的思索已經抵達了相當深入的層面。
實際上,除了仙俠等傳統元素的主流輸出之外,類似《從紅月開始》對“克蘇魯”這類海外元素的創造性改造,也是中國網絡文學能夠跨文化傳播、走紅世界的重要原因。以克蘇魯風格的網文為例,其之所以能風靡全球,深受讀者喜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克蘇魯神話所蘊含的深厚文化內涵。這種文化語境不僅為作品提供了獨特的敘事背景與世界觀,更使得讀者即便在跨文化背景下也能輕松理解并產生共鳴。《從紅月開始》的創作實踐不僅促進了不同文化背景讀者之間的深度交流與互動,也為網絡文學創作走出類型化的低水平重復,向思想和主題的縱深掘進,以及全球化語境下網絡文學的創新與發展提供了重要啟示。
五、文學批評與創作的雙向互動
最后應當指出的是,山東文學創作所取得的豐碩成果,也離不開評論界的支持。新時期以來,山東文學批評界始終與創作界保持了良好的互動,從宋遂良、吳開晉、孔范今、陳寶云、袁忠岳、任孚先到譚好哲、李掖平、吳義勤、王光東、張清華、施戰軍、黃發有,以及更年輕一代的孫書文、馬兵、叢新強、張麗軍、張艷梅、劉永春、趙坤、房偉等,都積極介入了所屬時代的文學現場,為山東文學發展,也為繁榮當代文學批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近年來,山東文壇批評家與作家雙向互動、彼此溫暖、共同成長的健康發展態勢也得以繼續保持下來,這首先是與批評家隊伍的建設分不開的。批評不僅是一種職業,批評家也是講述“中國故事”、總結“中國經驗”的重要力量之一。基于此,山東文學界以《百家評論》等期刊為陣地,以簽約文藝評論家制度為依托,以泰山文藝獎等文藝界評獎為抓手,在培養批評人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顯著的成效。通過這樣的體系化建設,山東文藝界不僅能夠及時發現和推廣優秀的文藝作品,也能夠為文藝創作提供更加全面、深入的指導和支持。同時,文學批評也從價值觀念、理論方法以及審美思維等方面進行自我審視與反思,逐漸解開中國文本的復雜結構,進而不斷拓展文學批評的影響力和作用范圍。
2015年,山東率先實施“簽約文藝評論家”制度。這一創新舉措標志著山東在文藝評論人才培養方面邁出了關鍵性的步伐。迄今為止,簽約文學評論家已有三批。制度化的運作在鼓勵青年評論家自由探索的同時,也確保始終有一批評論家對山東文學保持持續的關注。這有助于形成一個更加緊密的文藝評論與創作共生體系,把作者與評論家緊密連接起來,讓評論家既能在創作的早期階段即介入其中,提出有價值創作建議,助力文學作品的發展和完善,也能在作品完成后及時提供深度的解讀和批評,擴大作品的影響并助力其經典化。這種聯系機制的轉變,使得評論家與作家的聯系更加緊密,批評與創作的互動更加健康,批評家與作家實現了抱團取暖和共同成長。時至今日,劉玉棟、東紫、常芳、艾瑪等一批70后山東作家已成為當代文壇的中堅力量,王玉玨、魏思孝、錢幸、周燊、紫藤晴兒、王韻、祝紅蕾等一批青年作家也已經在各自的創作領域嶄露頭角并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而在文學創作“新魯軍”崛起的過程中,山東文學批評家陣營發揮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
回首七十余年的歷程,在共和國文學發展的每一個階段,山東文學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一部當代文學史的百花園中,齊魯花叢是分外絢爛而奪目的。而近年來山東文學在各種文體領域所取得的成績也都可圈可點。如果考察其特點與共性,那就是作家們的創作視點始終聚焦于變革中的社會現實,在關注宏大主題和重點題材領域的同時始終堅守著自身的創作特色與個性,力避在創作者高度聚集的題材領域中迷失自己。或許這就是他們在文壇上建構出自身醒目的文學面孔的“制勝法寶”。當然,這其中既有個體的努力,也離不開文學制度的保障和助力。
注釋:
ab喬力、李少群主編:《山東文學通史(20世紀)》,山東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335頁,第528頁。
c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13頁。
d王方晨:《大地之上》,山東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第8頁。
e丁守海:《概念辨析:城市化、城鎮化與新型城鎮化》,《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5月30日。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