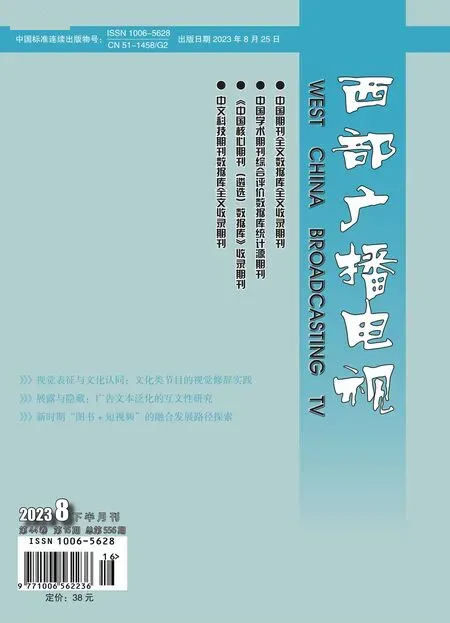北美華文文學改編電影中女性形象的視覺修辭策略
周 林
(作者單位:吉林大學文學院)
自電影媒介誕生之初,其獨特的敘述方式便與文學中相似的敘述審美特質形成了緊密的聯系[1]。因此,現代文學的經典作品往往成為影視改編的首選。近期,北美華文文學受到廣泛關注,其影視改編也逐漸成為熱議的焦點。根據饒芃子和楊匡漢在《海外華文文學教程》中的定義,北美華文文學是指由北美華人用漢語或中文創作的文學,它是北美華人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北美華文文學的影視改編,主要是指其作品從文學形式轉化為電影或電視劇等多種媒介。隨著文學改編在國內影視市場的日益發展,北美華文作品的電影改編已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文化現象。在這些改編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始終是核心議題[2]。電影語言和修辭手法在北美移民華人的獨特視角下,為觀眾展現了背后的文化內涵,實現了女性形象的影像書寫與其時代特質的表達。這些女性形象的精神內涵不僅反映了個體的生活體驗,更是對社會變革的期盼,對傳統文化框架的挑戰,以及對更廣泛精神自由的探索。
1 視覺修辭:修辭學的視覺轉向
古希臘學者主張,辭格是通過言語的運用實現勸說,旨在傳播與說服。許多深入的視覺修辭學觀點均源于文學修辭的“視覺轉向”。在20 世紀60 年代,伴隨廣告、電影、電視等視覺媒體的崛起,由伯克引領的新修辭學流派將修辭學視為一種傳播行為,其研究范圍已超越言語和文學,轉向象征性行動,涵蓋文字符號與影像符號的表述。巴爾特認為,影視文本中的圖像符號為一種信息載體。隨著社會進步,視覺文化逐漸盛行,科技的持續進步使圖像及其他視覺符號在信息傳播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其傳遞的信息更為豐富,傳播速度也超越文字。陳汝東認為,“視覺修辭是一種以語言、圖像以及音像綜合符號為媒介,以取得最佳的視覺效果為目的的人類傳播行為”[3],并強調視覺修辭的三個核心方面:語言文字的可視化修辭、以圖像為媒介的修辭行為,以及以圖像主導、其他元素(如文字、音響)輔助的綜合修辭行為。基于此,劉濤提出視覺修辭即通過圖像化手段進行勸服性話語生產的符號實踐[4]。在北美華文文學作品改編為電影的過程中,女性形象既需要展現多元的社會價值觀,又要強調其在劇情中的關鍵作用。但實際改編中,女性角色的塑造常受到話語轉換和導演風格的制約。其主體性的塑造與視覺修辭的構建密不可分,通過對女性角色的細致設計,結合色彩、光線等技術手段,為女性形象注入更深層的意義。
實質上,視覺修辭是修辭學的可視化展現,旨在傳達其背后的深層觀念。它將視像系統看作一個完整的符號體系,探討其在視覺語言中的修辭效果,并研究如何在特定的環境中應用特定的修辭策略,以構建和傳播語義。中國近年來的電影作品,如《金陵十三釵》《歸來》《芳華》《山楂樹之戀》和《唐山大地震》,都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幫助人們從修辭的角度深入分析和理解其中的女性形象。對于這些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它們不僅僅是簡單的角色塑造,每一個形象都富有象征意義,都蘊含著深層的文化信息和藝術審美。例如,《金陵十三釵》反映了戰爭背景下女性的堅韌和勇氣,同時也呈現了女性的柔情和無奈。這種雙重性的修辭策略,使得觀眾在欣賞影片的同時,能夠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感受女性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的處境和情感。同樣地,在《歸來》中,女性形象則展現了家庭和社會背景下的責任與擔當,以及對過去的懷念和對未來的期望。這種對比和交織,使得修辭策略更加復雜,為觀眾提供了更豐富的視覺和思考空間。而在《芳華》和《山楂樹之戀》中,女性形象更加集中地展現了青春的美好與遺憾,以及時間流逝中的記憶和情感。這種時間與情感的修辭策略,使得觀眾在感受影片的美感的同時,也更加深入地思考了青春、時間和情感的關系。在《唐山大地震》中,女性形象則成為地震災難中的象征,代表了家庭、愛與犧牲。這種強烈的修辭策略,使得觀眾在感受到震撼的同時,也對家庭、愛和犧牲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和體悟。
因此,通過對這些影片中的女性形象進行修辭分析,人們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感受到電影所要傳達的深層意義,同時也更加準確地解讀北美海外華文文學影視化中的女性形象的深層含義。這種深度的修辭分析,不僅增強了電影的藝術魅力,也為觀眾提供了更多的思考和感悟空間。
2 視覺轉喻后的凝視客體
視覺轉喻的核心思想在于圖像指代,其強調利用某一視覺元素指代與之相關聯的其他事物。視覺轉喻的關鍵特性為“同域指代”[5],意味著喻體與本體在認知結構上有相同之處。這可以視為一種借代,其中一個事物代表另一個事物,它們在意義維度上有密切的聯系。視覺轉喻方法中,常常將部分作為整體來呈現,這是常用的修辭策略。從意義建構的視角來看,語言使用者需依賴特定的視像系統符號來展現整體概念。簡而言之,視覺轉喻的建構主要是為了將難以直接觀察的抽象觀念,通過視像系統符號具體化。北美海外華文文學的改編電影利用視覺轉喻修辭進行了藝術轉化,旨在具象化和場景化地呈現,同時通過視覺轉喻的結合和創作,突出角色的女性特質。
視覺表征必須依賴特定介質,此介質的形式對信息呈現至關重要。媒體是簡單的傳播工具,能夠通過隱晦的話語權力建構文本意義。在觀察的影視系統內部,皆受物質框架的限制——即媒體邊界與時間限制。因此,創作者視角必然受所述“邊界意識”影響。視像的本質語言,在視角、取景、視野及其動態變化的多重影響下,導致視像系統的斷層與不連續性。觀眾需在這些斷層中構建并想象完整現實圖景。例如,小說《金陵十三釵》中的情節通過“鮮血”這一共通意義空間緊密連接,實現了血腥轉喻,將婦女的個體經歷融入民族和國家災難敘述。相對之下,電影版本將女性的自我犧牲和救贖主題,改編為英雄救美情節,并強調了女性角色的華麗旗袍和優美肢體語言。此種改編中斷了文學的血腥轉喻,轉而強調東方女性美麗印象,將女主角定位為“奇觀”的話語范疇,使女性成為男性“凝視”的對象,這也引起了許多批評。視像的斷層與不連續性,不僅體現在藝術作品的演繹上,更體現在影視改編過程中。視覺修辭通過具象的視覺符號,如姿態、歌聲等,將女性角色塑造成被凝視的對象,這在北美的華文文學作品改編電影中尤為常見。
由此,視覺表征不僅是信息呈現的途徑,更是一種文化和社會現象的反映。通過介質的選擇和使用,視覺表征揭示了信息呈現的復雜性和不連續性,而這種復雜性與不連續性在文學與電影的改編中得到了生動的展現。從單一的視覺表現到社會文化的廣泛影響,視覺表征的研究為人們理解現實世界提供了新的視野和深入的思考。
3 視覺隱喻下的主體覺醒
視覺隱喻是一種借助于人們普遍認同、植根于集體記憶的視像符號來替代抽象、復雜觀念的修辭手法。具體來說,在相近的視像符號系統互動中,通過聯想的方式構建抽象概念。其基礎原理為轉義生成,即在視覺修辭的意義機制中,視覺隱喻依托于由視覺元素構成的轉喻結構,并在圖像文本的聚合軸上落實隱喻意義的產生[6]。因而,視覺隱喻的生成需基于視覺轉喻,通過意象符號的構建來實施,強調不僅要深入探討視像系統中符號背后的深層含義,還要運用它們之間的內在邏輯以更深刻地傳達圖像所表達的意義。
視覺隱喻產生的核心原則是實現視像呈現與隱含意義之間的轉換,如通過影片中有意義的符號外延與鏡頭語言的有序性來理解和把握其背后的含義。視覺隱喻修辭涉及在視覺中運用抽象概念和圖像來表現情感或概念,進而生成意義,深化觀眾對作者意圖的理解,提升視覺體驗。與視覺轉喻不同的是,視覺轉喻將視像系統的符號直接與修辭者的意義空間聯系,而視覺隱喻則需將視像系統置于類似于修辭者意義空間的邏輯結構中,并通過觀眾的聯想和體驗來實現隱喻背后的意義交流。從視覺知覺的角度出發,觀眾是否能產生聯想是形成視覺隱喻空間的基礎。例如,通過視覺隱喻的修辭手法,北美海外華文文學改編電影反映了女性角色的內在意識覺醒,通過呈現女性形象的視像系統,成功實現了女性主體意識覺醒這一隱喻意義的構建。
在電影的語言修辭中,鏡頭的使用方式為角色賦予了豐富的意義層次。一方面,通過不同鏡頭組合的時間排列,電影的結構被劃分為起始、發展和高潮;另一方面,鏡頭的長度及其變化為電影帶來特定的韻律。更重要的是,這些鏡頭語言不僅重現了影片中的明確內容,而且深化了對潛在意義的探尋,為觀眾提供了進一步的聯想空間。
電影《芳華》改編自嚴歌苓的同名小說,以青春與時代為雙重話語架構,對軍隊文工團中的年輕人的命運進行了隱喻性的表達。影片中,何小萍偷取林丁丁的軍裝并在攝影館留影,這不僅為何小萍創造了一個“他者”的影像,更成為她在軍隊中的存在證明。此舉旨在獲取他人的認可,并試圖建立完整的自我認同。但是,何小萍的真正主體性是在沂蒙頌舞臺劇中被激活的。此時的鏡頭焦點在何小萍身上,形成了羅蘭·巴特描述的“刺點”,突顯了畫面中的某一細節,使觀眾能夠輕易與其建立情感連接[7]。
電影《歸來》聚焦于家庭和愛情的價值,通過細節展現主人公馮婉瑜和陸焉識的情感歷程。電影中,當馮婉瑜失去記憶時,陸焉識以琴聲重燃她的回憶,而馮婉瑜則以觸摸來傳遞深厚的情感。此外,電影采用了大量長鏡頭對兩位主人公進行特寫,刻畫他們的情感變化,同時也展現了兩人在畫面中的平等地位。
總的來說,電影中的視覺修辭不僅提供了豐富的視覺體驗,還為觀眾打開了聯想的空間,使其能夠從電影中獲得更深層次的感受和思考。這在北美華文文學改編的電影中尤為明顯,其中對女性形象的隱喻修辭不僅展現了女性的形象,還挖掘了其更深層次的象征意義。
4 視覺象征里的宏觀話語
在《詩經》中,“比”與“興”構成了一種復雜的修辭策略,而象征與此二者呈現出相似的修辭效果。在視覺話語的表征系統中,意象的創造是一種主流的視覺修辭方法[8]。所謂的意象,指的是意念與形象的融合。它采用視覺系統中的具體符號來表示與之關聯的宏觀抽象概念。然而,必須指出,象征體與其所代表的意義空間并不是同步呈現的。從意義空間的產生機制來看,由于該空間并不直接對應現實中的特定事物,而是僅作為概念上的存在,此種存在通常通過視覺隱喻來形成。在文學描述中,這種存在常被稱作“意象”。為了理解這種象征的意義空間,受眾需要依賴于某一具體事物所暗示的象征體。這種暗示與視覺隱喻背后的話語結構形成鮮明對比,因為象征所指向的是一個更廣泛的認知范疇,這種認知范疇常常基于文化層面的觀念結構,并促使受眾在集體記憶和行為認知中產生情感共鳴,進而與象征的意義空間建立連接。北美海外華文文學改編電影運用了大量視覺象征策略,旨在突出人的基本情感與傳統的哲學思想,并對這些概念進行解讀與再現,通過修辭策略對女性形象的構建,使觀眾在思維和價值觀上與電影作品產生共鳴。
在影視作品中,恰當地運用視覺象征修辭策略可以將特定社會和文化背景下的抽象概念轉化為具有象征意義的視像系統。這種系統通過直觀的視覺傳播方式為受眾展現,其間的符號交互賦予作品更深的內涵。例如,《山楂樹之戀》中,靜秋的象征意義基于隱喻構建。影片將“青春愛情”隱喻為少女靜秋的形象,進而實現“純凈之愛”的符號化表達。具體地,影片中的靜秋形象與小說中的描述有所不同,更加突顯其青澀的氣質,使受眾更易聯想到青春戀愛。此外,電影強調了戀愛中的復雜心理和初戀經歷,為受眾展現了一種純真的愛情,創造了一個象征“純凈愛情”的視像空間。
張翎的《余震》中,女主角“小燈”的痛苦回憶與唐山大地震及其母親的拋棄有關。這部作品采用非線性敘事,展現了小燈的知覺和意識如何瞬間跨越過去與現在。敘事邏輯以“小燈”為主線,背后揭示了她內心“破碎”的話語框架。而電影《唐山大地震》則將焦點從小說的“創傷難愈”轉向“災后重建”。電影采用順時敘事,象征家庭和國家的重建,以及個體與國家的認同。此外,電影采用了并行敘事,展現了家庭成員間的關系,進一步強化了家國同構的象征意義。
由此可見,北美海外華文文學作品的電影改編中,女性形象更為豐富。這些形象不僅承載了文化底蘊和時代變遷的精神價值,還展現了她們的信念、智慧和冒險精神,使得角色更加生動、多樣,更接近現實生活,使觀眾感受到民族與時代的精神內涵。
5 結語
在當代社會,人類價值觀念日益多元,對于女性話語的自我表達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在這一文化背景下,海外華文文學作品所改編的電影,開始深入探索和關注女性的自我表達。盡管這些改編影片在女性形象的刻畫上進行了新時代的價值探索,但仍然受到了部分刻板印象和消費文化的制約,導致其中的女性修辭有時呈現出物化的趨勢。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推出更多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的優秀作品”[9]。這要求改編者在進行修辭時,既要重視藝術的完整性和表現,又要深入考慮所處的社會和文化環境,確保改編作品與原著在意義上達到和諧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