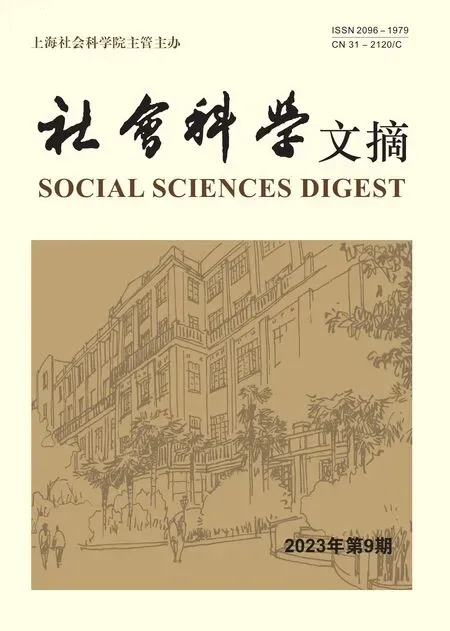中西哲學的始點與道路之辨
——從丁耘和吳飛的論爭說起
文/蔡祥元
道和存在是中西哲學引導詞,它們都跟自然有關,源自古人對自然現象(包括人生現象在內)的觀察,并用來標識自然的本源。他們所面對的對象是一致的,都是自然現象,也有相似的思想動機,均要把握自然現象背后形而上的原因,但最后卻發展出兩套有根本差異的思想體系。對于這種差異,自近代中西哲學碰撞以來,有諸多不同角度的展開。總體而言,這些差異基本上著眼于中西哲學既成形態展開,對其差異根源的追溯不多。如果能著眼于早期哲學家如何分別從自然現象的觀察中提煉出道和存在,并以此比較提煉方式的差別,對于理解中西哲理差異將大有裨益。
丁耘與吳飛近期的一組討論就是著眼于這個視角展開的。在我看來,雙方的爭論涉及中西哲理的始點與思維方式兩個方面。在第一個方面,丁耘、吳飛都有明確把握(雖然觀點不同),第二個方面雙方也均有提及,但未展開,甚至有不同程度的誤解。就中西哲理差異而言,后一方面可能是更重要的,它關乎的是思想道路的不同。
丁耘、吳飛有關中西哲學的始點之爭
亞里士多德把古希臘自泰勒斯以來對自然本源的追問具體化為原因,并提出了四因說。丁耘就是著眼于四因說展開的。他首先概述了牟宗三與海德格爾對四因說的解讀,表明他們對亞里士多德有不同程度的發揮,但有一個共同點,也即“全都強調動力因、淡化目的因”。該文的直接意圖就是通過對四因說的溯源,對此觀點進行糾偏,突顯出“目的因”在亞里士多德思想體系中的獨特地位。他認為,亞里士多德在《物理學》和《形而上學》有關宇宙或自然自身的構想中,動力因和目的因是合一的;而制作技藝不同,動力因與目的因是分開的。這種合一的思路不能來自制作活動,只能來自實踐。這是亞里士多德對世界終極原因的思考,它超出了柏拉圖制作模式。目的、動力、形式這三種原因的合體,就是經亞里士多德加工過的“努斯”概念,它是自然的第一本體與宇宙的終極原因。由于“努斯”一詞本身也有“思想”“心思”的意思,這樣一來,此終極原因就表現為一種宇宙的“大心”。宇宙之“大心”不僅僅只是思維活動(心之思),同時還包括了心之所思(善),是心體與性體的合一。丁耘對海德格爾觀點的批評是為了會通中西哲理的起源。雖然儒家義理學中沒有出現由系詞而來的存在問題,但是,亞里士多德四因背后這一“大心”的思想訴求,在中國哲學語境中不能說沒有端倪。他認為牟宗三“即活動即存有”的心性觀與亞里士多德的“大心”是可以比擬的。
吳飛很好地看到了丁耘的思想動機,也即,通過融合動力因和目的因,在亞里士多德的形上學與宋明心性論之間建立一種思想關聯。但是,在吳飛看來,丁耘的這一做法有意無意地模糊了制造與生生之間可能存在的根本差異。他沒有看到,儒家之生生取喻于男女生育現象,而亞里士多德的生成論則取喻于制造現象,兩者之間有著根本的區別。與丁耘不同,吳飛明確主張,生生與制造之間有著根本的差異,它們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哲學思維模式。在制作模式中,形式被認為是永恒不變的,質料處于流變的不定之中,由此導致形式與質料的二元區分。此區分在構成西方形而上學基本框架的同時也構成其思想的困境所在,導致形而上學的二元論兩難以及倫理學上善惡的截然對立。與之相對,取喻于男女交合生育現象的“生生之道”,在生育的過程中,不存在形式與質料的二分,生育是生生原則(陰陽相感相交)自然而然的結果,在陰陽之間也不存在善惡高下之別。
吳飛、丁耘有關中西哲理道路之別的論述及其問題
生育和制造現象雖然扮演了中西哲理始點的角色,但是,此差異并不直接就決定了中西哲理的整體區別,這里還需要考慮它們對待始點的態度或方法之別。如吳飛所總結指出的,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也直接關注過生育現象。同時,《周易》也直接關注諸多的“制作”現象。就思想體系而言,思想之始點固然重要,但如何從始點開辟出思想體系的“道路”同樣重要。對于思想道路的差別,丁耘和吳飛均有所涉及,但都未能展開,且有不同程度的誤解。
吳飛在追溯生育現象對于中國哲學的始點地位的過程中,也同時論及了中國古代哲人如何從生育現象中提煉出“生生之道”。他首先對“生”與“生生”作了語詞使用上的區別。也即,“生”指涉的是日常生活中生育、生成現象;而在《易傳》語境下“生生”,針對的是一種形而上的哲學概念,所謂“生生之謂易”。因此,從“生”到“生生”,有一個思想上的跨越。這個跨越關涉的就是思想道路。對于此跨越,吳飛用“推想”和“抽象”來刻畫其特征。這只能說是對“思想道路”的一個泛泛論述,并未觸及道路的關鍵。
丁耘把亞里士多德探求始因的方法稱為“邏各斯道路”,把儒家義理的思想方法特質稱為“現象學道路”,以此表明雙方思想道路的差別。遺憾的是,從丁耘對儒家義理展開方式的論述來看,他也并沒有完全將儒家義理的“現象學道路”的特色充分展現出來。他主要在語詞層面做了一些區分和指點,表明《周易》哪些相關語詞“直接描述”作為本體的“永恒運動”。比如,他認為天地是乾坤的“形”“象”“用”,而乾坤則是天地的“元”“體”。在這個意義上,乾坤就是天地之道,天地有形有象,是形而下者,而乾坤則是形而上者。但是,這種意義上的“直接描述”就可以解讀為“現象學道路”嗎?這種做法在我看來暗中預設了本體是直接自身呈現出來的,所以我們可以“直接描述”它。但是,儒家乃至一般中國古代義理的思想關鍵恰恰就在于:這樣一種本體的直接呈現到底意味著什么?它是如何可能的?在我看來,這將關乎中西哲理的本質性區別。
取象與定義
那么,中西哲理的道路之別到底何在?
我們先看亞里士多德是如何從制造現象提煉出四因的。四因中最核心的是形式因,其他幾種原因都是相對形式因展開的。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形式”決定了“物之所是”,它直接來自柏拉圖的“型相”。無論是“形式”還是“型相”,都是在“是什么”這一引導性問題框架下發展出來的,也用來回答“物之所是”。亞里士多德將這一方式稱之為“定義”。
正因為古希臘哲學家追問自然本源的方式以定義視域為引導,使得他們最終沒有提煉出“生生之道”,也即并沒有因此走向基于生成現象的形而上學。在面對自然現象的時候,古希臘哲人也直接關注了生成乃至生育現象。亞里士多德在總結“自然”一詞的基本涵義時就指出,該詞無論在日常使用還是在詞源上,都跟產生有密切關系。他甚至直接關注過生育現象乃至人類的生育現象。但是,他認為生命的生育現象中并沒有真正的生成,因為貓只能由貓生成,狗只能由狗生成,在這個自然的生育活動中,貓和狗都已經事先存在了,這里不涉及貓和狗的原初生成。對亞里士多德而言,作為“物之所是”的形式是不能被自然生成的。
為什么基于定義的思想方式無法展開生成現象呢?這是因為存在與生成在內涵上具有不相容性。從時間角度我們對此可以獲得一個直觀的理解。生成是一個時間中發生的過程,有時間的跨度。而定義是依托系詞展開的,典型的定義形式是:S is p。不難看出,定義的語法形式是現在時。一個基于時間延展的生成現象的“本質”是無法在現在中被給出的。另一方面,這一基于定義的思維方式又暗中決定了一種以現在為核心的時間觀。根據亞里士多德對時間的定義,時間是一種被數的數,而現在-點就是它的基本單位。這一對時間的定義反過來又進一步阻礙了對生成變化的思考。
那么,中國古人如何能夠從生成、生育現象中提煉出形而上的“生生之道”呢?這跟中國古代哲學的思維方式有根本關系。作為“六經之首”的《周易》是這一思維方式的代表。根據《易傳》的總結,我們把它稱為取象。《易傳》就是著眼于“象”來解讀《周易》整體的思想方法。易卦與天地萬物是以象為紐帶相互關聯起來的,彖、爻辭以及由之而來的吉兇悔吝,都是基于象而言的。《周易》之所以可以“彌綸”天地之道,涉及如下兩個環節:一方面,天地之道可以通過象來呈現自身,“見乃謂之象”;另一方面,圣人通過觀摩天地萬物的變化,通過象來展現此變化之道,卦或八卦就是圣人用來展現此變化之象的。
現在的問題是,取象所取的“象”跟事物是何種關系?我們如何能透過它把握背后的“天地之道”?
首先,“象之為物”來源于具有類似系辭特征的“像”。“A像a”說的并不是“A是a”,但它又不能等同于“A不是a”。由此我們首先可以確定,象不同于“物之所是”。其次,象不能簡單等同于或混同于形象或表象。形象著眼于具體事物而言的,《周易》中的象雖然也以具體事物為出發點,但不局限于具體事物,而是通過它代表一類“實情”,“以類萬物之情”。這個意義上的象跟本質也有相似之處,都具有某種程度的普遍性。卦象所關涉的“類”又不能理解為西方哲學種屬框架下的種類。種類之“類”是由某種共同本質或共相所支配,它基于一般與個別的區分,比如馬的“型相”貫穿所有個別的馬。但《周易》中的取類與之不同,同一卦象可以由不同種類的事物來代表。另外,還需要注意取象跟西方哲學修辭學語境中象征也有區別。現代漢語語境中“象征”源自西方的修辭學,它跟比喻、擬人等一起,通常被認為是修辭表達的一種。和比喻一樣,象征也具有一個通過某物(符號或感性物)來再現某個他物的結構。而中國哲學語境中的取象則沒有設定這樣一個前提條件。
可以說,象既不是具體事物的形象,也不是某一事物的本質或一類事物的共相,還不是“理念世界”的“象征”。那它是什么呢?“象之為物”這個問題很難正面回答。它不同于確定意義上的“實體”,也就不能以“是什么”的方式給予回答。與實體性相對,象具有構成性的特征,也就是說,它需要在一種結構關系中被“構成”。比如,當天作為乾的時候,它需要與地、雷、木、水、火、山、澤等八類自然物一起構成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等八個卦象。與實體的超時間或非時間性相比,象的構成性特征又直接表現為象的時間性。陰陽是構成卦象的兩個基本要素。而陰陽這兩個詞本身在詞源上就具有明顯的時間性特征,陰指的是水之南,山之北,陽則相反,水之北,山之南,而山、水之陰陽是以日光照射引起的。因此,陰陽雖然取象于男女,但在八卦中,陰陽的關系與差別都是通過時間來體現的。
所以,象不是事物的理念或共相,也不是理念的象征——它們都關涉某個對象(自然對象或觀念對象)——而是“變化”之象。著眼于取象與定義這兩種思維方式的區別,我們才能更全面領會陰陽跟四因的差異。陰陽并不是對男女生育現象的定義,也因此,它不僅適用男女生育,同樣可以用于動物雌雄交配現象,乃至更一般地用于日夜、天地等等。可以說,它相對于男女交合生育現象有一個“超出”,但這種“超出”不是抽象的。從現象中抽象出來的“本質”跟現象之間有一個根本的斷裂,也因此,本質自身構成一個獨立的“思想世界”。但取象不同,此“陰陽之象”不脫離男女交配生育現象而存在,它可以在此過程中被“直觀到”。
結語
最后我們結合中西哲理始點與道路的關系,對中西本源觀的差異做一整體性總結。前面已經指出,中西古代哲人面對自然變化都試圖把握變化背后的終極原因,這就是本源。太極和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實體指涉的都是這個意義上的本源。從字面乃至內容上看,雙方有不少的相似之處。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實體是不動的推動者,而太極同樣具有不動的特征。太極之動具有“周而復始”“反復其道”的特征,而亞里士多德則認為無限存在的運動只能是圓周運動。著眼于取象與定義這兩種思維方式的特點,就可以看到,這些相似性只是表面的,即便在這里,雙方也有關鍵的區別:
首先,太極中的循環往復更多是一種時間現象,而亞里士多德的圓周運動則是著眼于空間性的位移運動。雖然都是“周”,“周而復始”之“周”跟“圓周”之“周”關涉的是兩種不同的“周”。“周而復始”之“周”中包含了原本的差異,里面有“生生之象”。太極中這種“往來反復”中的“生意”在空間化的圓周運動中是體現不出來的。
其次,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實體是一種理性推論的結果。他注意到,事物的運動需要推動者,而推動者本身的運動還需要進一步的推動者。如此推論得出的第一實體,在康德看來只不過是一種先驗理念,是純粹理性從自己的推理本性出發得出來的一個概念,它超出所有“有條件者”(經驗世界),成為絕對的無條件者。但是,太極/陰陽卻不是通過這種推論的方式提取出來的。它是在男女、雌雄的交合生育現象中直接被“觀”到,因此,太極/陰陽并不是通過理性推理建構出來的先驗理念,它是圣人通過“觀”天地萬物的變化“看”到的。“太極/陰陽”無所不在,天地、日月、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乃至山水等自然萬物中都可以觀到“太極”。
太極圖和圓周可以用來展示中西本源觀的整體差異。圓周是“空洞”的,它代表的是一種“先驗理念”,里面沒有可被直觀的內容。太極圖不同,它里面有“象”,也即陰陽相生之象,這種象是可以在經驗世界中被“直觀”到的。關于此種“觀”如何可能,它跟西方傳統哲學中的理智直觀以及跟現象學視域中的諸種“直觀”是何種關系,筆者將在其他論文中再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