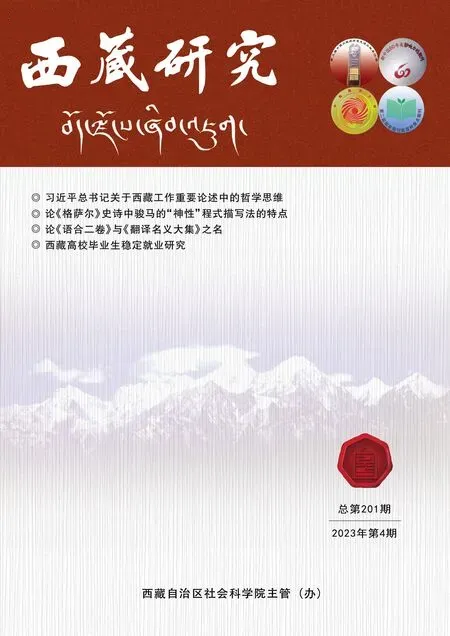堡子坪白馬人麻晝儀式的文化闡釋*
權新宇
一、問題的提出
彭兆榮指出,在過去一百年里,人類學儀式研究大致沿著兩種進路演進:一是對儀式與古典神話進行探討,其學理依據主要是人類學古典進化論,以泰勒、斯賓塞和弗雷澤等早期人類學家為主要代表;二是對作為社會行為的儀式進行探討,這種進路力圖揭示儀式在社會結構和社會組織中的作用與功能,涂爾干、利奇、維克多·特納、瑪麗·道格拉斯等學者秉承了這一學術傳統。隨后而來的結構功能學派、象征文化學派等均從不同角度對儀式進行了闡釋,使得人類學儀式研究成為從內涵到外延都不易框定的話語包容。(1)彭兆榮:《人類學儀式研究述評》,《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第88頁。
堡子坪村寨隸屬甘肅省文縣石雞壩鄉薛堡寨行政村。該村位于縣城西南35公里處,白水江中游,東連石坊鄉,南鄰鐵樓鄉,西與四川省九寨溝縣草地鄉接壤,北靠馬營鄉。該村與薛堡寨相鄰,村前險峻深谷,村后高山密林。海拔高度約1610米,高寒陰濕,自古旱災頻繁,易遭冰雹、地震等自然災害。耕地多為山坡旱地,主要種植玉米、小麥、洋芋等耐高寒抗旱農作物;飼養豬、牛、羊、驢和騾等家畜。該村住戶現有48戶,其中白馬藏族43戶,漢族5戶,漢藏常住人口共計220人。白馬人有尤、尚、楊、毛四大姓氏。尤姓最多,其次是尚姓、楊姓,毛姓最少。四大姓互婚,本姓不互婚,也不與異族通婚,最近五六年也有個別人與漢族通婚,語言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藏語支北部方言。(2)孫宏開:《再論西南民族走廊地區的語言及其相關問題》,《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3年第6期,第32頁。
從人文地理版圖來看,堡子坪白馬人居住于藏彝走廊東北端,這里自古民族種類繁多且支系復雜。諸多族群在這里長期接觸與交融,形成了鮮明的“漢、藏”兩大文化圈,并留存有古老的文化遺存,堡子坪“麻晝”(mbba1nrzzro2)即為例證。因其角色似十二生肖,故當地漢族俗稱其為“十二相”,但當地白馬人認為是白馬藏語方言漢語音譯,“麻”(mbba1)為“丑陋”之意,“晝”(nrzzro2)為“跳、舞動”之意。
從已有研究來看,國內學者(3)儺舞說代表性作者參見于一:《白馬藏族“十二相”考略》,載《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6期,第92頁;余永紅:《隴南白馬藏族“十二相”的文化淵源》,載《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11年第5期,第124頁。多言其為儺舞。尤其是近十多年來,伴隨著“麻晝”身份向“非遺”轉變,無論是在甘肅文縣還是四川省九寨溝縣及平武縣舉辦的白馬人文化旅游節廣告及大型電子屏幕滾動式解說詞中,亦是在白馬村寨人及學界學術成果中,此種觀點極具代表性。毋庸置疑,堡子坪白馬人“麻晝”與古儺不無關系,但據筆者實地訪談得知,堡子坪白馬人“麻晝”與古儺只是“形似”而非“神似”。換句話說,儺文化特征只是“麻晝”的一個文化面向而非全貌。與儺舞說不同,拉先認為,白馬藏族聚居區的“巴”舞屬于苯教忿怒神尊一系中的宗教神舞。“巴”舞面具,源自苯教二十七位瓦姆忿怒女相神中的“賽瑪九尊”和“結姆九尊”。(4)拉先:《白馬藏族“巴”舞研究》,《西藏大學學報》2019年第4期,第66—67頁。
盡管儺舞說和苯教忿怒神尊說,均從不同側面揭示了漢、藏兩大文化在堡子坪白馬人“麻晝”儀式形成過程中留下的歷史印記,但作為從歷史煙雨中走來、生存于漢藏兩大文化圈并傳承至今的“麻晝”,其儀式背后不可能只隱藏著儺和苯教文化面向,反而“麻晝”儀式投射的恰是多元宗教信仰層累的文化圖式。然而,國內鮮有學者探討堡子坪白馬人“麻晝”儀式背后投射的多元宗教信仰圖式。基于此考量,本文擬在深描堡子坪“麻晝”儀式角色與時空維度、儀式過程與結構的基礎上,進一步揭示“麻晝”儀式投射的宗教信仰之于白馬人的社會意義。(5)文中未注明資料均為課題組2019年正月十五至十七日期間在文縣石雞壩鄉薛堡寨、堡子坪等田野考察所得。
二、麻晝儀式角色設置與展演的時空維度
雖然堡子坪“麻晝”和流傳于四川省九寨溝縣碟子坪、溝里、陽山及英格等村寨的“亻芻舞”(又稱“咒偶”)為同一文化事項,但在角色與展演時空維度設置等方面,“麻晝”有自己的鮮明特色。
(一)角色設置
薛堡寨YMQ老人說,“以前(民主改革),麻晝面具數比現在要多,有30多個。但大多已毀于‘破四舊’和‘文革’期間,現在的這些面具,也是改革開放后依據健在老人的記憶復原的。”(6)時間:2019年正月十四日下午;受訪人:楊茂清,男,白馬人,薛堡寨人,92歲,勒貝,農民;地點:楊茂清家中。當下,堡子坪白馬人在都剛山神前、村委會院子和家戶跳“麻晝”時,獅、牛、虎、龍、雞、豬面具出場參與請神、送神,娛神娛人挨家挨戶入室驅鬼逐疫;2012年佛光寺建成后,在佛光寺祭祀菩薩時,獅、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相出場敬請眾菩薩,但請眾菩薩參與村子里驅鬼逐疫、祈福納吉儀式時,出場角色又變為獅、牛、虎、龍、雞、豬面具。對此差異,BDS的解釋是:
以前,寨子里也跳過十二相入室驅鬼逐疫,但跳完后,寨子往往不順利。因此,在都剛山神、觀音樓、場壩及挨家跳時,僅出場獅、牛、虎、龍、雞、豬相;2012年佛光寺建成后,在佛光寺祭祀菩薩時,出場獅、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相。(7)時間:2019年正月十五日下午;受訪人:班代壽,男,白馬人,堡子坪人,44歲,勒貝,“嘛夠池”、“刀頭”扮演者,農民;地點:班代壽家中。
表面上看,村子里跳的六相與佛光寺跳的十二相(見圖1)并無二致,但實際上二者有著本質不同:在都剛山神前、觀音樓與村落出場的六相(見圖2),除自身外,實際上還代表著另外不出場的6個動物:

圖1:佛光寺麻晝十二相/筆者(2019)

圖2:村落和都剛山神前跳的麻晝六相/筆者(2019)
第一相名為獅頭,實為獅(頭)+鼠(眼)組合;第二相名為牛頭,實為牛(頭)+馬(面)組合;第三相名為虎頭,實為虎(頭)+狗(耳)組合;第四相名為龍頭,實為龍(頭)+蛇(眼)組合;第五相名為雞頭,實為雞(嘴)+鳳(頭)組合;第六相名為豬頭,實為豬(頭)+象(嘴)組合。
通過如此組合,實際上村子里出場了獅、牛、虎、龍、雞、豬、鼠、馬、狗、蛇、鳳、象等角色,只是前六相顯性出場,而后六相隱性出場,但佛光寺跳的十二相僅代表自身并不代表其他動物。然而,九寨溝縣白馬人跳的“亻芻舞”出場角色多為單數,如5、7、9和11不等,也無一相代替兩相的規定。出場面具數與村落家族數量有關,即村子里有多少個家族就出場多少個“亻芻舞”面具,每個面具代表一個家族。
拋開當地人對“麻晝”六相與十二相差異的地方性闡釋,單從當下村子里參與驅鬼逐疫的六相特征來看,其組合特征鮮明。這無疑再現了《山海經》所表達的華夏先民造神的原初思維。如《山海經·南山經》言:“凡《南次二經》之首,柜山距漆吳之山約有七千二百里,兩山之間又有十七座山,其山之神,多為龍身,長著鳥首。”(8)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年,第13頁。《山海經·東山經》也言:“又南五百里,曰石垔山,南臨石垔水,東望湖澤,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音如獆狗,其名曰峳峳。見則其國多狡客。有鳥焉,其狀如鳧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絜鉤,見則其國多疫。”(9)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第100頁。由此可見,參與入室驅鬼逐疫的六相應該為“麻晝”的原生形態,而佛光寺祭祀眾菩薩的十二相應為“麻晝”的次生形態。換句話說,六相是白馬人對華夏先民造神思維的繼承與堅守,而佛光寺十二相無疑是當地人面對漢傳佛教再度輸入所作的調適抑或能動性再造物。
(二)時空維度
雖然堡子坪麻晝儀式遵循著傳統的時空架構,但隨著堡子坪白馬人農業生計方式變遷及佛光寺修建,麻晝儀式的時空維度也得到了重構。
1.儀式時間
正月十六日下午,筆者在堡子坪村委會院子公共火塘旁隨機訪談了正在烤火的YXM,據YXM講:“聽老一輩講,往前,春耕開始(農歷四月十八日左右)、秋收后的十月十五日、農歷正月期間村子里都會跳‘麻晝’。現在僅在正月十五、十六兩天跳。”當問及附近九寨溝白馬人寨子,在結婚、喬遷等喜慶日子也跳“麻晝”,堡子坪不跳“麻晝”的原因時?YXM說:“他們那邊(九寨溝)幾個村寨跳‘咒偶’所佩戴的面具是新面具,沒有被開光,不代表神靈,可以在其他日子跳。我們正月跳的面具為舊面具,舊面具代表著神靈,在規定的日子之外跳,神不答應,會給村子里帶來災禍。”(10)時間:2019年正月十六日下午;受訪人:尤新民,男,白馬人,堡子坪人,50歲,勒貝,“麻晝”、“獅頭”扮演者,農民;地點:村委會院子公共火塘邊。
YXM字里行間無疑投射出堡子坪白馬人跳“麻晝”所遵循的時間原則:一是堡子坪白馬人跳“麻晝”的時間節點隨農事而變動,如“四月十八”春耕下種開始,祈求眾神保佑未來農業豐產;“十月十五”秋收后為豐收而酬神;二是堡子坪白馬人賦予跳“麻晝”的時間(自然時間)以神性(社會時間),如“在規定的日子之外跳,神不答應”。
2.儀式空間
在當地老人“碎片化”記憶中,20世紀50年代前,每年農歷四月十八日春耕開始,白馬人都要在田邊跳“麻晝”,祈求眾神護佑農作物豐產;約農歷十月中旬全年農事基本結束,人們聚集場壩跳“麻晝”酬神慶祝豐收;農歷正月十五日挨家挨戶入戶跳“麻晝”驅鬼逐疫、祈福納吉。“文革”期間,像諸多民間文化一樣,跳“麻晝”儀式被迫中斷,80年代初恢復。但現在農歷四月十八日在田邊和農歷十月中旬在場壩已不再跳“麻晝”。2012年佛光寺建成前,一般在都剛神山前請神、觀音樓前敬觀音樓宗神和菩薩、自西向東挨家入戶驅鬼逐疫、村子場壩跳十二大陣娛神娛人,最后在都剛神山前送神;2012年佛光寺建成后,請神改為在佛光寺進行,同時村委會院子取代了傳統村落公共空間場壩,成為跳十二大陣娛神娛人的儀式空間,其他儀式空間并沒有發生明顯變化。
從共時性角度來看,“麻晝”展演時空維度已發生了些許變化。儀式時空變遷的主要原因,除當地老人所言的“破四舊”和“文革”使得“麻晝”傳承中斷之外,生計方式變遷也是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原因。長久以來,白馬人生計方式如《龍安府志·武備志·土司志》所言:“該地土俱系深山……刀耕火種,番民男婦務農為主。一歲之供全賴乎蕎,多荒少熟……荒則采蕨根作面為食。”(11)鄧存水等:《龍安府志·武備志·土司志》,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本,第185—187頁。遲至20世紀70年代中期,白馬人的農業生計方式均未發生太大變化。改革開放后,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市場經濟發展,尤其是近20年來工業化和城鎮化加速推進,白馬人村寨像大多數村落一樣“空心化”現象日趨凸顯,多數村民只是名義上的農民,外出務工已成為青壯年人群主要謀生手段。在農業生計方式日漸式微情境下,之前與農時節令密切相關的農歷四月十八日于田間地頭、農歷十月中旬在場壩跳“麻晝”,祈求眾神護佑莊稼豐收與酬謝眾神已失去了原初意義。此外,2008年“5·12”大地震文縣受災,災后重建使多數白馬人村寨首次通電,村寨公路修建也極大地方便了村民出行。2012年漢傳佛教再度傳入堡子坪,雖然漢傳佛教早在當地人認為的清光緒年間已滲入堡子坪,但2012年之前觀音樓并不是“麻晝”請神和送神空間。2012年佛光寺建成后,白馬人家多裝有誦讀佛經的電子設備,誦讀之聲數小時不絕于耳。在白馬人家屋廳房“神柜”之上,漢傳佛教菩薩掛像與“家神”案、祖先神案共掛于一處。如此情境下,佛光寺成為了“麻晝”請神空間。可以說,佛光寺成為新的請神空間無疑是堡子坪白馬人主動接納漢傳佛教的能動再造,而村落里面和都崗神山前跳六相無疑是堡子坪白馬人對傳統的堅守。
三、麻晝儀式過程與結構
在特定的時空架構內,隨著儀式空間轉換和展演內容變化,堡子坪“麻晝”儀式過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四個環節,即敬請佛光寺菩薩、觀音樓宗神,挨家入戶驅鬼逐疫,場壩娛神娛人,送麻晝與眾神歸山,其儀式結構也發生著相應變化。以下是筆者在2019年正月十五至十六日現場記錄的“麻晝”儀式展演過程。
(一)麻晝儀式過程
隨著麻晝儀式時空維度的變遷,在堅守傳統的同時,隨著展演內容變遷增添了新的儀式展演環節。
1.請神
正月十五日上午11時40分,佛光寺高音喇叭傳來:“請跳‘麻晝’的村民速到佛光寺,年度跳‘麻晝’行將開始。”。“麻晝”扮演者及眾村民聽到廣播后,陸續到達佛光寺。“麻晝”扮演者裝扮好各自角色,在獅頭率領下,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依次為序列隊,在佛光寺院子里按順時針方向,表演十二種動物使出渾身解數解除獵人套索等情節,跳完后,在三眼銃四聲巨響中,獅頭手持佛頭法器率眾神入寺,手持佛頭法器的豬頭斷后,在神龕前按順時針方向跳圈祭拜阿彌陀佛、觀世音、大勢至、文殊等眾菩薩。拜完后,十二相卸妝。其中,“池哥”和“池母”裝扮者返回家中,敬家神和祖先神并裝扮各自角色。按照傳統,“池哥”老大須在一戶尤姓老房子(據說該房屋修建于清光緒年間)中裝扮,裝扮完后去請“池哥”老二,請來后二人又去請“池哥”老三,最后請“池哥”老四。隨后“池哥”老大、老二和老三去請各自的“媳婦”。“媳婦”到場后,和“池哥”一起跳幾圈,即沿著山路跳向佛光寺,到寺后與獅、牛、虎、龍、雞、豬一起入寺,請眾菩薩參與驅鬼逐疫。請上眾菩薩后,在兩位手持刀劍的“池哥”開路與另外兩位“池哥”、三位“池母”、“護駕”下,手持龍頭法器的獅頭率牛、虎、龍、雞、豬頭依次沿著山路跳向村子。隨行婦女高唱“瑪知麻咪薩廉叨,阿彌陀佛”,而男人則一路高喊“嗷、嗷、嗷”相應和。行至觀音樓前,獅頭率牛、虎、龍、雞、豬頭祭拜觀音樓宗神。祭拜完后繼續跳向村委會院子。跳到村委會院子后,“池哥”、“池母”及眾人退場,六相開始圍繞村委會院子按逆時針方向跳幾圈十二大陣舞步。
2.驅邪逐鬼
正月十五日晚上6時,“麻晝”6人、“池哥”4人、“池母”3人、“甘晝”2人和“麻根”2人組成祭祀隊伍去觀音樓敬神,然后在寨子中心固定地點跳一遍各種祭祀舞蹈。隨后在眾人所唱《瑪知》歌聲中,祭祀隊伍去村組干部、教師、醫生、傳承師傅和有威望人家里入戶驅邪,對于其他人家只去“麻晝”和“池哥晝”。按照傳統規定,從寨子西面第一戶人家開始入戶驅邪。每到一家,“池哥”面向主人家廳房“神柜”(12)“神柜”是放置在白馬人家廳房后背墻前的一個長方形木質柜子,其上多擺放香爐等神圣物品。平日白馬人多在“神柜”前焚香及紙錢祭祀祖先和家神。之上所掛祖先神與“家神”案,雙手平握象征刀劍的木棍,雙腳離地跳三下,三拜家神和祖先神。主家給“池哥”豬肉一塊、饃頭兩個、香蠟紙若干。跳出廳房時,“池哥”在火塘轉三圈,用五色糧食撒出門外驅邪、驅鬼,同時用木棍敲廳房門框邊三下驅趕鬼疫。隨后“池哥”和“池母”再跳到該家廚房,“池母”三拜灶神,并敲打驅趕鬼邪。敲打完畢后,主人家點燃燒紙扔出門外,以示鬼疫已被趕走,隨后端出酒菜,唱酒歌感謝“池哥”和“池母”,“池哥”老大祝福該家百事順利、萬事吉祥。小伙子吼三聲,放炮。隨后,“池哥”和“池母”再去第二家,如此這般,村子里所有家戶都要跳到。在寨子東面“麻晝”、“池哥晝”、“甘晝”、“嘛夠池”在此一起送瘟神,送走瘟神,驅鬼儀式才算結束。
3.娛神娛人
正月十六日下午1時,獅、牛、虎、龍、雞、豬六相在村委會院子里開始跳十二大陣:第一大陣,“狹晝”(“拜山神舞”);第二大陣,“腰晝”(“牛舞”);第三大陣,“搭晝”(“虎舞”);第四大陣,“安晝”(“兔舞”);第五大陣,“搓晝”(“龍舞”);第六大陣“山尼”(“蛇舞”);第七大陣,“報杰蘭木”(“馬舞”);第八大陣,“占晝”(“羊舞”);第九大陣,“世晝”(“猴舞”);第十大陣,“寫晝”(“雞舞”);第十一大陣,“雷杰瓦扎”(“狗舞”);第十二大陣,“帕晝”(“豬舞”)。十二大陣均跳六小路,共計七十二小路。雖然在村委會院子里僅出場獅、牛、虎、龍、雞、豬六相,但還跳了兔、蛇、馬、羊、猴、雞、狗等動物動作,以取悅山神、水神等神靈,祈求眾神護佑山寨安康、五谷豐登。在這期間,村民也跳藏式鍋莊、集體舞,還表演現代歌曲獨唱等來增添節日氣氛。
4.送神
正月十六日晚上6時,在村子里跳的六相,從村委活動中心院子出發沿著山路跳向都剛神山,送眾“麻晝”歸山。在都剛神山前六相繼續跳祭拜山神舞步,期間班姓“勒貝”(13)類似漢族師家或端公,主要從事傳老爺(即跳神)、安神、驅鬼、治病、招魂、消災、避邪等活動。此外,白馬人神職人員還有沙巴尼和貝木。沙巴尼類似漢族陰陽先生,主要從事安葬亡人;貝木主要從事算卦、降魔驅邪。搭建祭祀堆。兩位村民宰殺山羊,并把羊血、耳朵、腿和背部羊毛放在祭祀推上倒酒點燃、燒香磕頭,尤姓“勒貝”率領眾男人跪在都剛山神前,念送神咒:
老爺神好好聽神咒,凡人有請必有感應……請上元一品四府天官、中元品謝罪地官、三元品三官大地是廟神……高廟宗神、菩花天宗、南斗六郎、北斗七星、九耀星神、二十八宿……州里州城隍,縣里縣城隍。藏園門前有玉皇,東門外頭鐵腳黑池、南門外頭五眼山海爺……南山貴子大娘、西天山里金花三娘娘……東海岸上觀世音、中央岸上觀世音;東海岸上八大金剛……中海岸上八大金剛;沿河八寨八廟宗神,半溝金海龍王、李家山郎母主郎、郎藏山黑爺、阿尼則搜比定;岷堡溝觀音大寺、黃門店上掌印都崗;磨上寨子洋湯老爺;半山里玉海龍王、石灰梁山青巖龍王、九天圣母、薛堡寨洋湯老爺、照鷹嘴上山神都崗、博達峰黑池龍王,沙坎溝池沙龍王、籠窗溝白馬龍王、豐都龍王;橋頭下八海龍王、橋梁土地、盤古龍王、山神都崗、阿尼業山入定那;龍門店上行兵、尤氏走馬將軍、尤氏跟馬將軍、尤氏走馬都崗、業入朵蓋。今天給當方山神、宗神念神經,當方神靈你要聽,當方神靈要顯靈,保佑山寨吉祥平安。(14)2019年正月十六日晚上7時,尤新民在都剛神山前念送。原文為白馬語,班代壽譯為漢語。為便于閱讀,筆者在引用時作了適當變動。
請求大家吼三聲,口舌是非帶出寨外,吉祥如意請進門,祈盼從今以后百事順利,風調雨順,山寨安康,五谷豐登,六畜興旺。三災八難趕出寨外,神靈保佑全村老的長命百歲,小的一長成人。隨著眾人三聲“噢、偉”,炮手鳴放三眼銃三響,麻相卸裝,儀式至此結束。隨后眾人開始分食烤羊肉,在場的人人有份。在當地人眼中,吃了祭祀過都剛山神的羊肉,一年內不得病,筆者也有幸吃了兩塊羊肉。
(二)麻晝儀式結構
就儀式結構而言,堡子坪“麻晝”儀式大致也對應著范·杰內普眼中的分離、聚合和閾限后三個階段,但堡子坪“麻晝”儀式結構與范氏理論尚有些許差異,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正月十五和十六日是堡子坪白馬人跳“麻晝”的日子,其余日子因為“神不答應”而不能跳及村落里、都崗神山前均不能出場十二相等規定,維系了“麻晝”儀式結構長久以來的穩定性,而獅頭手持佛頭法器無疑是白馬人對漢傳佛教的調適。第二,在“麻晝”儀式過程中,并非所有儀式參與主體都發生了角色轉換。如在儀式三個階段中,大多數普通村民身份并沒有發生明顯改變,身份發生改變的只有6或12個“演員”和念誦神咒的“勒貝”。在整個儀式過程中,相對于“勒貝”來說,普通村民始終不能夠通神。儀式前后普通村民身份并未經歷兩種截然不同的轉換:即從“日常”到“神圣”,再從“神圣”回歸到“日常”。在普通村民身上,特納所言的“閾限”期間“反結構”、“交融”狀態事實上非常模糊。第三,“麻晝”儀式發生的原動力并非來自儀式本身的內部結構性張力,而是來自于白馬人鬼神信仰以及樸素的生存認知。這種動力源作為一種意識模式深植于村民的心理結構之中,又與靠山吃山、靠天吃飯的生存環境及生計方式密不可分。第四,“麻晝”儀式中的祭品通過儀式賦予的象征和祭詞實現了向鬼神供奉。通過祭品表達人與神的交易互惠,實現了神圣與世俗互構。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麻晝”儀式“主演”六相或十二相,還是作為“配角”的“池哥”及“池母”,均為青壯年男性裝扮。挨家入室驅鬼逐疫和都剛山神前送神均禁絕女性在場,女性僅在佛光寺請神和村委會院子娛神娛人環節在場伴唱《瑪知》歌。表面上看,“麻晝”是力量型舞蹈且跳的時間長,需要身強力壯的男性跳,實際上,這與白馬人的傳統社會結構有關。白馬人家庭社會角色分工一般是“男主外、女主內”。像跳“麻晝”這樣的“男主外”,無疑是男人身份與地位的體現。
四、麻晝儀式投射的宗教信仰
“麻晝”儀式中的請神、挨家入室驅鬼逐邪和送眾神歸山等環節均充滿了顯圣意味,這表明“麻晝”是堡子坪白馬人宗教信仰的外顯形式。從儀式角色、祭祀空間和祭祀咒語來看,麻晝儀式投射的宗教信仰,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原生宗教信仰,如山神、水神、動物神及鬼神信仰;二是外來宗教信仰,如道教、苯教和漢傳佛教。
(一)原生宗教
堡子坪原生宗教植根于白馬人的文化傳統中,與村民的生計方式及宗教信仰密切相關。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鬼神信仰為主的原生宗教不僅存在于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也在“麻晝”儀式中反復展演。
1.自然神
送神空間都剛山,其實是堡子坪村后的一座山,但村民視其為神山,并在山頂為其搭建簡陋神廟一座。和大多數白馬人村廟一樣,都剛山神廟也非都剛山神獨居,而是眾神居所。廟內后背墻前立長約10公分、寬約70公分的木板一塊,當地人稱該木板為神案(見圖3)。神案自上而下依次畫有都剛山神、小兒喇嘛、走馬將軍、業脈告來具、入地郎君、引兵土地、豐都龍王、八爺、葉師投肉、四元枷銬(15)“四元枷銬”是半路結為弟兄,斬妖除邪的四位神祇,分別為張遠大、李遠白、董四貴、稀文聶。等地方神靈。當地人說,都崗山神為神鷹化身,每年農歷九月十五日均在此舉辦廟會、傳神、祭祀都崗山神。2012年之前,每年農歷正月十五日上午,在此請眾神參與驅鬼逐疫、祈福納吉儀式,正月十六日晚上在此酬謝眾神。屆時要唱《白馬山寨的神鷹》酒歌:

圖3:堡子坪都剛山神案/筆者(2019)
白馬山寨的神鷹喲,你是白馬兒女向往的神鷹。……白馬山寨的神鷹喲,你是薛堡寨人心中的神鷹。你有神奇無比的本領,能把世間的邪惡戰勝。你有一顆救世的心靈,庇護著勤勞善良的白馬人……(16)邱雷生、蒲向明:《隴南白馬人民俗文化研究(故事卷)》,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15—316頁。
從“麻晝”送神咒來看,參與堡子坪“麻晝”儀式的自然神與都剛山神廟供奉的自然神并無二致,如天神、土地神、風神、雷神、火神、水神等。盡管“龍”并非現實中的動物,而是華夏先民想象出的神獸,但作為水神的龍王普遍為白馬人所供奉,如豐都龍王、白馬龍王、盤古龍王、蓋古龍王、小兒龍王、黑池龍王、血池龍王、赤沙龍王、趕山龍王、青巖龍王、八海龍王及清水龍王等。過去,每逢久旱,白馬人在“貝木”的率領下,全村成年男子都要去神山跳神祈求眾龍王降雨。如此眾多的“龍王”無疑是白馬人“靠天吃飯”生計環境的現實寫照。
2.鬼、祖先與“家神”
在村子里訪談時,村民與古人一樣多認為,“鬼”多指“人死曰鬼”,(17)阮元校:《十三經注疏(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588頁。且有善惡之分。能福佑眾生,保佑四季平安、五谷豐登者為善鬼,如祖先神;未善終者靈魂所化為惡鬼,專與人作祟及制造疫病。針對鬼神制造疫病,白馬人發明了相應的驅鬼技術。如《南坪鄉土志》卷上《風俗》云:“白馬藏人,三年內備羊只,必請師人跳神,執單面羊皮鼓,跳躍堂中作商羊舞,口唱番語,傳禍福,多有靈驗。鄉人有病不服藥,多禱鬼神打羊皮鼓祈福解病。”(18)馬秉忠、徐步蟾編著:《南坪鄉土志》卷上《風俗》,民國四年(1915),南坪縣志辦公室付印,1983年,第29頁。正月十五日下午,在村委會院子公共火塘邊烤火時,當地人MKT告訴筆者:“之前(民主改革前)得病之后,一般請巫醫以土法治療。若久病不好,就找‘勒貝’、‘沙巴尼’、‘貝木’跳神,問神到底是啥子(什么)鬼在害人,然后畫符驅鬼,消災治病。”(19)時間:2019年正月十五日下午;受訪人:毛客他,男,白馬人,堡子坪人,61歲,沙巴尼,農民;地點:村委會院子公共火塘邊。
除平日里村民個人驅鬼治病之外,每年農歷正月十五日晚上,無論是獸類獅、虎還是牛、豬、雞等尋常動物及想象的“龍”,均以“假面”方式被幻化為“異型神獸”,在手持牦牛尾和木棍(象征刀劍)的“池哥”(白馬人眼中的“方相氏”)率領下,自西向東挨家入戶驅鬼逐疫。這種集體驅鬼逐疫儀式,無疑是白馬人鬼神信仰的當下注解。
堡子坪白馬人家供奉晚近逝去的人為“先人爺”。不同于漢族家庭,白馬人家譜神案(見圖4)為布面畫案,長約2米、寬約1米,其上畫有先祖全身或半身像,并畫一牌位,按照字輩序將家族逝去的老人寫在牌位內,之后老人去世后按照字輩序陸續填進空牌位。家譜一般存放在族長家,過春節時請出,供族人供奉祭拜。堡子坪白馬人也供奉“家神”,如金海龍王、郎母桌郎、華化波秀、波秀秀東、黑爺、掌印都剛、九天神、母青岸龍王、珍珠娘娘、瑜海龍王、楊湯龍王、小寺喇嘛、熊山都剛、黑池白馬、雜嘎保咒、白馬龍王、豐都爺、八海龍王、隊以古主、財神大吉、盤古龍王、毛神都剛和楊喇嘛等地方神靈。每家供奉的“家神”大致相同,但也略有差異。如班柏柳家的“家神”案(見圖5)左上方畫的是上天童子,右下方畫的是入地郎君,左邊畫的是青筆上張;“家神”案中心右邊畫的是紅筆構肖土地爺;“家神”案最底部畫的是四元伽考等神祇。此外還有尤氏走馬將軍、尤氏跟馬將軍、尤氏走馬都剛等“行神”。(20)文縣和九寨溝縣白馬人神職人員供奉的“行業神”。“行神”畫在“家神”案上,“行神”騎馬,馬腿向前騰飛。馬口張開則表明該神職人員有弟子;馬口閉著,則表明該神職人員已無弟子。如有法事,神職人員要焚香,請上“行神”一同前往做法。九寨溝縣白馬人村寨也有單獨畫的“行神”案。同一家族供奉相同的神靈,“家神”案一般多供奉在家族長子家中。平日用紅布包裹卷起立于“神柜”之上,不視外人。臘月三十日請出祖先神案和“家神”案并掛在“神柜”之上焚香祭祀。農歷正月十五日晚上“麻晝”入室驅邪時,“池哥”要雙腳離地跳三下,敬該家祖先神和“家神”。

圖4:白馬人家譜神案/筆者(2019)
(二)外來宗教
堡子坪白馬人在與其他族群交往、交流中,吸納外來文化元素,使得“麻晝”祭祀儀式呈現出典型的多元宗教混融特質。
1.佛教
據《馬氏族譜》記載,清雍正七年(1729),時任文縣知縣郭時政倡議修建岷堡溝文樓,得到白馬人響應。文樓建成后,縣令郭時政宣布圣諭,土司裁革。(21)馬繼賓撰:《馬氏族譜》記載,“清雍正七年(1729),文縣令郭時政拿銖票傳喚各族,糧冊尚強,土司裁革。”另見邱正保等主編:《隴南白馬人民俗文化研究》(調查資料卷),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9頁。作為改土歸流歷史見證的文樓,上下兩層,一層為行人通道,二層供奉漢傳佛教菩薩數尊。當地人說:“一直以來,文樓即供奉菩薩數尊。”這表明,作為文化教化的漢傳佛教至遲在清雍正年間已滲入岷堡溝。盡管堡子坪觀音樓修建時間(清光緒年間)晚于岷堡溝文樓,但從建筑風格及供奉的菩薩造像來看,觀音樓無疑是岷堡溝文樓的濃縮版。堡子坪觀音樓也分上、下兩層,一層為行人通道,二層供奉漢傳佛教菩薩一尊。正月十五日“麻晝”祭祀隊伍通過一樓時,要在此祭拜觀音樓宗神,唱《觀音樓宗神》酒歌:
觀音樓神啊,你是一個吉祥的神,你是白馬人心中尊貴的神,你給白馬人帶來歡樂吉祥,你保佑著隔河兩岸的百姓,你保佑著家家牛羊肥壯,你保佑著莊稼五谷豐登。觀音樓神啊,你是一個幸福的神,你是白馬人心中愛戴的神,你給白馬人帶來幸福安康,你保佑隔河兩岸的太平,你保佑著我們出行平安,你保佑我們一路順風……(22)邱雷生、蒲向明:《隴南白馬人民俗文化研究(故事卷)》,第328—329頁。
如果說觀音樓是在清中央政府強化邊陲治理情境下,堡子坪白馬人對佛教的有限吸納,那么2012年村民集資在村北山梁上建佛光寺,則是堡子坪白馬人對佛教的主動選擇。佛光寺內,現供奉阿彌陀佛、觀世音、大勢至菩薩等,其信眾多為村中老年婦女。寺院無固定神職人員,平日打掃寺院、許愿和還愿等日常事務多由村中毛姓男子義務承擔。從蘭州請來的眾菩薩入住堡子坪引發“麻晝”儀式發生了三點變化:一是佛光寺建成前,村子里只跳六相,不跳十二相,佛光寺建成后,在佛光寺跳十二相;二是佛光寺建成前,請神和送神均在都剛神山,佛光寺建成后,請神空間變為佛光寺,送神在都剛神山前進行;三是在佛光寺建成前,獅頭手持龍頭法器,佛光寺建成后,在佛光寺請眾菩薩時,獅頭手持佛頭法器。由此可見,隨著儀式主體對外來佛教的主動接納,“麻晝”儀式也隨之得以再造,進而演化為一種新的“文本”。
2.苯教與道教
盡管學界對白馬人是否信仰苯教或藏傳佛教存在較大爭議,但筆者實地觀察到的卻是:雖然在白馬人居住區域或村寨并不存在苯教和藏傳佛教寺院,但苯教已在白馬人居住區留下了些許印記。如白馬河“四山班家”所供奉的“阿尼澤叟畢記”山神,流傳在薛堡寨、堡子坪和九寨溝縣白馬人村寨的“阿尼嘎薩”傳說即為明證。從詞源來看,白馬語中并無“阿尼”一詞,但在藏語里面,“阿尼”(A nyes 或A myes)卻為常見詞,且多為“祖輩、祖父”之意。隨著時空轉換,“格薩爾”一詞在流傳中出現了諸多地方變音,如堡子坪“阿尼嘎薩”之類的稱呼。堡子坪白馬人說,他們跳的“池哥晝”中的四個“池哥”代表“阿尼嘎薩”四兄弟,三個“池母”代表皇上的三女兒和皇宮里的兩個女子。(23)古元章、張金生、邱雷生等:《隴南白馬人民俗文化圖錄》,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4頁。此外,與王含章、阿旺嘉措提到“瑪哈”(dmag)(24)王含章、阿旺嘉措:《迭部藏族的民俗宗教“垛”(gto)及其文化內涵分析》,《宗教學研究》2018年第1期,第136頁。相比,堡子坪白馬人送“麻晝”歸山后跳的“麻夠池”,無論是“刀頭”反穿羊皮襖,臉部涂墨,還是兩隊人馬戰前練兵、交戰、攻城等方面都極為相似。都剛山神案上所畫的小兒喇嘛及“麻晝”儀式中所請或送的眾喇嘛,不是苯教寺院或藏傳佛教寺院專職修行的僧人,而是神職人員或生前有“特異功能”、死后出現“特異現象”的人,但喇嘛稱謂可能借自苯教或藏傳佛教對僧人的稱謂。“麻晝”伴唱歌詞“瑪知麻咪薩廉叨”(ma55dz53ma55mei53sa55lie31nd55)也能說明這一點。有學者認為,該伴唱詞應為苯教八字真言“阿喇追木耶撒勒杜”(Om-na-dei-mye-sa-hdu)(25)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實地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89年,第37頁。的變音;受苯教影響,堡子坪白馬人按逆時針方向轉圈跳“麻晝”。實際上流傳在九寨溝縣馬家鄉白馬人村寨的一首“魯歌”這樣唱道:“土地高神得了病。阿拉魯唱‘魯歌’,土地高神沒好轉。桑吉切來跳神,土地高神病未好。雍仲苯來念經,土地高神病痊愈。”另外一首“魯歌”回答了“阿拉魯”、“桑吉切”和“雍仲苯”的來源:“阿拉魯自何地來?阿拉魯自這(本地)來。桑吉切自何地來?桑吉切自北方來。雍仲苯自何地來?雍仲苯自衛藏來。”(26)楊冬燕:《(白馬)藏族信仰習俗現狀調查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第62、70頁。這兩首“魯歌”無疑是苯教在這一區域留下的底層記憶。
此外,在請神咒中,還請來了天官、地官、九耀星神、玉皇、九天圣母、菩花天宗,南斗六郎、北斗七星、八大金剛、二十八宿、城隍、金花三娘娘等道教神祇。如此道教神祇多出現在“勒貝”、“沙巴尼”和“貝木”咒語中,如神職人員《護身咒》:
東方青帝將軍護我身,南方赤帝將軍護我身,西方白帝將軍護我身,北方黑帝將軍護我身,中央黃帝將軍護我身,五帝將軍護我身,鐵牛肚里去藏身。若有鬼神不服者,口誦一聲遠離身。若我今使鐵扇金龍鎖四門。龍神至感大都來護身。七金剛八菩薩,九天王盡隨身。謹請南斗六良,北斗七星,今請奉請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27)任躍章:《中國白馬人文化書系信仰卷(下冊)》,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13頁。
綜上所述,“麻晝”儀式投射的原生宗教信仰和外來宗教信仰表明兩個基本事實:一方面說明藏彝走廊東北端自古族群種類繁多且支系復雜,諸多族群長時間接觸與共生,使得這一空間的族群文化呈現出融攝特質;另一方面也凸顯了白馬人宗教信仰的包容性及鮮明的生存價值取向。無論是以都剛山神、龍王為代表的自然神及以祖先為代表的人格神,還是外來的道教、苯教和佛教眾菩薩均為村民解決日常生活中“難題”之策略。雖然理論上眾菩薩關照的是信眾的“終極意義”,但在堡子坪村落情境中,也無妨村民去佛光寺“許愿”和“還愿”。這說明眾菩薩解決的依然是村民日常生活中的現實問題,而非單純的“終極關懷”。堡子坪白馬人正月十五至十六日兩天跳“麻晝”,更是以自然神和鬼神及外來的眾菩薩、苯教和道教諸神為基點,在特定時空架構中,通過一系列媒介(如法器和咒語)將諸神加以符號化和象征化,以眾神之名驅逐侵害人們心中的鬼邪,旨在落實來年村寨風調雨順、五谷豐登、人畜興旺等現實性訴求。同時,在年復一年的儀式操演中,堡子坪白馬人精神世界與自身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得到追溯性表述。
五、結語
愛彌兒·涂爾干(Emile Durkheim)指出,宗教由信仰和儀式兩個重要部分組成。(28)愛彌兒·涂爾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東、汲喆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52頁。據此審視作為宗教具象的“麻晝”,也由信仰和儀式兩部分組成。堡子坪白馬人長久信奉的“萬物有靈”宗教觀念與鬼神信仰,構成“麻晝”建構的信仰原點。“萬物有靈”觀念使得原本作為自然物的山、水和動物等在堡子坪白馬人眼中皆為神靈;而從歷史中走來的鬼神信仰卻使得村民普遍“心中有鬼”且對惡鬼作祟、制造病疫等深信不疑。如果說,以“萬物有靈”和鬼神信仰為代表的本土宗教信仰形塑了堡子坪白馬人“麻晝”的原生儀式,那么苯教、道教和漢傳佛教等外來的宗教信仰無疑塑造了“麻晝”的次生形態。如果把觀音樓看成是“改土歸流”情境下“華夏邊緣”對“王朝”教化的某種“回應”,那么其所供奉的觀音菩薩則表明堡子坪白馬人對外來漢傳佛教的有限接受。這種有限接受,可能導致豬頭手持佛頭法器的出現,但卻沒有改變對獅頭法器的使用,也沒有改變在都剛神山前請神和送神的傳統。然而,2012年全村集資修建的佛光寺卻導致“麻晝”儀式由原生形態向次生形態改變。佛光寺首次取代都剛山神成為請神空間,且創造性出現十二相請佛光寺眾菩薩儀式環節,也使獅頭手持法器由龍頭變為佛頭。伴唱詞《瑪知》歌詞中“瑪知麻咪薩廉叨”與神咒中提到的眾喇嘛“南斗六郎”、“北斗七星”等神靈,無疑是苯教和道教促使“麻晝”儀式由原生形態向次生形態演化的另一種動力。由此可見,“麻晝”儀式也不是一成不變,而是隨著信仰變遷而發生相應變化。在信仰變動中,“麻晝”儀式得以不斷重構,進而被形塑成一個新的文本。
在堡子坪白馬人“麻晝”儀式展演中,還能照見其建構的另一個原點,即半農半牧的鄉土背景。都剛山神廟內供奉的豐都龍王和“麻晝”中的“龍”,即為堡子坪白馬人農業生計方式的寫照。但隨著現代化、工業化全速推進,農業生計方式日漸變遷,外出務工等已成為大多數白馬人的首選生計方式。生計方式變遷情境下,鄉土社會孕育的“麻晝”回不到過去。即便“麻晝”離堡子坪鄉土社會漸行漸遠,但尚能預見的是,作為白馬人表達自我和族群追溯自身文化的表述方式——“麻晝”仍然會在傳統儀式框架內展演下去。展演動力借用彼得·貝格爾在《神圣的帷幕——宗教社會學理論之要素》中所言,即“麻晝”是堡子坪白馬人追求意義的本能之下所創造的屬于他們的世界。(29)彼得·貝格爾:《神圣的帷幕——宗教社會學理論之要素》,高師寧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頁。也如馬林諾夫斯基所言:“所有的巫術和儀式等,都是為了滿足人們的需求。”(30)馬林諾夫斯基:《巫術與宗教的作用》,金澤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第91頁。“麻晝”這一極具意義的行為“文本”滿足的無疑是堡子坪白馬人的現實生存訴求。在年復一年的儀式操演中,追求意義的本能與生存需要,不僅使白馬人編制的“意義之網”(31)Geertz,Clifford,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Baaic Books,1973,p.5.得以建構,也為“麻晝”存在與傳承下去提供了不竭動力。
(致謝:本文田野資料的獲得,得到班代壽老師及家人的幫助,誠摯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