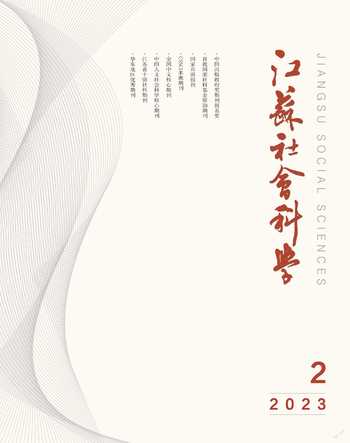朱子學傳播的民間化路向
內容提要 理學通俗化文獻在朱熹等理學家的積極推動下,經歷了從形成、發展到成熟的歷史演變過程,在宋元時期形成了一定的社會影響。以三種重點文獻為論述中心:一是從奠定理學通俗化理念的《小學》入手,它主要彌補了朱子四書學的理論漏洞從而完善整個理學體系;二是從儒家經典與詩歌互動的《訓蒙絕句》展開,它賦予儒家典籍豐富的情感與審美要素以拓展儒家經典閱讀的普及面;三是以仿蒙求體的《性理字訓》為中心,它使抽象艱澀的性理概念通俗易懂并發揮出理學工具書的功用。在此基礎上,考察諸類文獻與理學理論發展的關系、相關衍生文獻的類型、民間實際流傳情況以及在東亞國家(朝鮮與日本)的歷史影響,從而爬梳出一條長期為人忽略的朱子學民間傳播的歷史發展脈絡。
關鍵詞 朱子學 理學 通俗化 《小學》 《訓蒙絕句》 《性理字訓》
許至,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程端禮(1271—1345)為朱熹(1130—1200)的二傳弟子,他一生致力于地方教育,歷任建平縣、建德縣教諭,臺州路、衢州路教授等學官,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程氏根據《朱子讀書法》的教育理念并結合自身教學實踐編著了《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下簡稱《日程》)一書。此書初成于元延祐二年(1315),歷經二十年,至元統三年(1335)最終刊刻于甬東家塾。雖然《日程》初衷是服務于家塾子弟,但是由于其融教育目的、內容、計劃、方法為一體,具有可操作性,并符合儒家道德教育理念,故受到元代國子監的大力表彰,被刊刻并推廣至全國各類官私學校,甚至在明清亦頗具影響力。《日程》規定了學生在各個年齡段的必讀書目,其中八歲前后應閱讀的書籍如下:
八歲未入學之前,讀《性理字訓》。日讀《字訓綱》三五段,此乃朱子以孫芝老能言,作《性理絕句》百首,教之之意,以此代世俗《蒙求》《千字文》最佳。又以朱子《童子須知》貼壁,于飯后,使之說記一段。[1]
八歲入學之后,讀《小學》正文……師授說平日已讀書不必多。先說《小學》書。畢,次《大學》。畢,次《論語》……[1]
頗為有趣的是,元代學者熊大年(生卒年不詳)曾頒刻朱熹《小學》并在書后附錄了自編的《養蒙大訓》,此書共匯集了宋代理學家的10本啟蒙著作,基本包含了程端禮規定的5本書籍。筆者將相關的書籍列出:朱熹《小學》《訓蒙絕句》《童蒙須知》,程端蒙《性理字訓》《毓蒙明訓》,陳淳《啟蒙初誦》《訓蒙雅言》《小學詩禮》,王柏《伊洛精義》,胡寅《敘古千文》,饒魯《訓蒙理詩》,程若庸《增廣性理字訓》[2]。《日程》與《養蒙大訓》匯集的書目有幾點值得關注:其一,從諸書的編著者而言,大部分是朱熹一脈的理學家,包括程端蒙、陳淳、王柏、饒魯、胡寅、程若庸等,其中朱熹編著數量與類型最多,其后學對各類啟蒙書均有延續,可見在朱子學的啟蒙、通俗化領域皆有傳承與創新。其二,由于諸書編著的初衷是啟蒙,它們比較符合低齡化讀者的需求,特別是形式上而言,大部分篇幅相對短小,語言簡約,然而內容上符合蒙童的掃灑涓潔應對的“事”卻不多,更偏向道德教化之“理”以及理學知識。故而,筆者認為諸書雖設為啟蒙,但它們的啟蒙對象并非以年齡為界限,而是以儒家道德修養功夫高低為標準,諸書的受眾不限于蒙童,而是一切理學初學者和道德修養上的后進者。
一、《小學》:理學通俗化理念的成型及其傳播
《小學》正式刊定于宋淳熙十四年(1187),由朱熹發凡起例,其弟子劉清之(1133—1189)具體分類、搜集、編定。內容上分為內篇與外篇,內篇分為立教、明倫、敬身、稽古,每一目分別摘錄儒家典籍原文;外篇分為嘉言與善行,采輯漢代至宋代名賢的言行事跡,多出自史籍與北宋諸子之書。由此可知,《小學》實際是一本經史匯編本,內容并不具有原創性,但符合正統的儒家道德教育理念,其摘錄的條目以立教、明倫、敬身為大綱(其中明倫與敬身摘輯條數占全書的90%)。朱熹完成此書已到晚年,作為社會精英圈中的學者,他何以要編著一本道德啟蒙書?此書又與其正統的學術思想有何關聯呢?筆者根據朱熹《小學題辭》《題小學》《大學章句序》以及其關于小學教育理論的論述,歸納了以下兩個原因。
其一,朱熹是為了彌補小學教育理念及讀物的缺失,根本目的是實現理學道德教化的全面覆蓋,特別是覆蓋低齡化群體。朱熹堅信古代通行《小學》與《大學》二書,然《小學》焚于秦火。由于《小學》與小學教育的缺失,世人在童蒙時未養正,道德教育起點就存在缺陷,人性固有之善性不復存在,才導致“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豗”[3]這種局面。倘若要去除人性中的私欲,與其成人后費力剝除,不如在童蒙時將其扼殺,讓人從根基處抑制私欲并始終保持固有的善性,為將來打造圣賢柸璞打下基礎。于是朱熹主動扛起續古者小學之教的旗幟,確立小學教育理念,編定《小學》,將道德教化的年齡提前,當然啟蒙道德教化的理論基礎、架構核心都涵攝于他構建的成人道德修養理論體系中。
其二,從學術史角度而言,《小學》的產生是為了彌補朱熹《四書》體系中的理論漏洞。宋淳熙四年(1177),朱熹發現其構建的四書理論體系存在致命弱點,他提倡“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的觀點,即敬知雙修、誠明兩進皆要“主敬”,但問題是《大學》的道德進修次序是由格物致知再到正心、誠意、修身等“主敬”環節,這樣“敬”的安置就存在割裂。于是朱熹將小學納入道德修養理論體系中,與大學形成先后次序,并將“敬”納入灑掃應對進退中,如此“敬”得到了銜接,理論漏洞得以修復。朱熹門人曹叔遠(1159—1234)曾質疑“敬當不得小學”,但朱熹反駁道:“某看來,小學卻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1]筆者認為朱熹及其后學編著通俗化文獻俱是從這兩方面出發。
上述兩個原因使《小學》在實際的社會流傳中,不僅充當道德啟蒙的閱讀教材,而且與朱熹整體思想旨歸融合并成為學術著作。早在宋淳熙二年(1175)朱熹與呂祖謙(1137—1181)就共同編著了被稱為“四書之階梯”的《近思錄》,后此書與《小學》綁定成為四書及理學研習的預備書籍。朱熹本人對《小學》的編著與實踐推廣都十分重視。據唐紀宇考證,早在宋乾道六年(1170)朱熹就曾與林用中(生卒年不詳)討論將“涵養”“敬”與小學教育相結合的打算,在與胡實(1136—1173)、吳翌(1129—1177)通信中對小學與大學的道德教育次序也進行了討論。宋淳熙九年(1182)始,朱熹與劉清之對此書編著的商定、討論、修改、定刊前后可考的有6封書信;淳熙十四年(1187)《小學》刊定之后,朱熹主動贈送陳淳(1159—1223)、應仁仲(生卒年不詳)、宋之源(?—1221)等人,請他們探討此書[2]。宋紹熙元年(1190)朱熹任福建漳州知州,在巡視地方學校時親自為學生講授《小學》并進行宣傳。由上可知,朱熹小學理念的建構與《小學》的編寫,是他對啟蒙教育及學術理論完善的深思熟慮之結果。
由于《小學》兼具啟蒙與學術性質,其目標群體則顯得比較模糊,在實際的閱讀與傳播過程中,它似乎成了一本男女老少皆宜的民間性讀物。試舉幾例:
君(按:孫棕)以成童之年受學康齋吳聘,君時已治經,康齋復令熟讀朱子《小學》,且教之靜坐澄心。[3]
奉元韓從善擇教人,雖中歲后必使自《小學》入。[4]
有史六丈者……慕先生(按:賀欽)之德,遂來求學。先生仍以前輩待之,每來輒為解說《小學》……[5]
以上所舉并非個例,“成童”“中歲”“六丈者”等群體顯然超出了小學教育范圍,它甚至成為終身研讀與揣摩的作品。“徐氏世家……于朱子《小學書》未嘗釋手,每語諸子曰:‘此豈獨教幼學,汝曹當終身佩服……”[6]事實上,《小學》閱讀群體的全面擴充得到了朱熹本人的認可,當其門人游倪(生卒年不詳)問他,若年齡超過童蒙范圍,是否可以跳過《小學》直接讀《大學》,朱熹回答:“授《大學》甚好,也須把《小學》書看,只消旬日功夫。”[7]可見,《小學》啟蒙對象是以儒家道德修養功夫的高低為標準,凡初學者、后進者,不論年齡大小皆須閱讀《小學》,故而此書成為全年齡階段的理學道德教育讀物并被納入四書體系建構中。
然而,《小學》作為一本道德啟蒙書,被從事一線教學的塾師們指出諸多問題,主要有兩點:其一,其所采輯部分內容涉及“大人之事”,如胎教、保傅之教,君臣、夫婦之則,這已經脫離稚童學習與生活階段所需。其二,就其編著體例而言,總字數達10萬余字,《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下稱“三百千”)總計不過0.25萬余字,可見其閱讀或授讀任務十分繁重。內容的艱深與超長的篇幅是《小學》作為道德啟蒙讀物不可忽視的問題。朱熹另著有《童蒙須知》,此須知從衣服冠履、語言步趨、灑掃涓潔、讀書寫字、雜細事宜五個方面規定了小學階段所應施行的事,語言簡易通俗、篇幅短小,或許是對《小學》存在問題的有效彌補,二書也時常同時出現。
然而,《小學》的上述問題并沒有影響它的實際傳播力,自南宋成書后,它在元、明、清的傳播范圍與影響力,是任何一本啟蒙或通俗類讀物都無法企及的。主要表現在三方面:其一,最高統治者(萬歷、康熙、雍正、乾隆)、歷代官方教育機構、各級行政官員、知名儒者對《小學》大力表彰、刊刻、頒布;東宮、宗室小學、國子監小學、地方官辦小學、私塾的學生皆有閱讀《小學》之證。其二,《小學》成為官方學校指定的教科書,甚至在康雍乾時期有八十余年成為“童生”入學考試和復試的指定官方命題參考書。當《小學》與一般讀書人命運攸關的科舉考試相掛鉤時,其在民間的傳播范圍及其效果可想而知。其三,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后世對《小學》的各類改編本有近90種,從時代分布上來看,宋代2本、元代16本、明代31本、清代37本;從分類形式上看,主要有注解類、概要類、詩歌類、考證類、續寫類等。
在朱熹所有的正統著述中《小學》并不起眼,然而朱熹后學也進行了不遺余力的推廣與傳承,這也直接影響了此書在歷史通俗化讀物中的知名度。一方面,朱熹后學對《小學》進行大力贊揚與宣傳,如陳宓、魏了翁、真德秀等學者為《小學》作序并在各地刊刻頒布,以擴大它的實際影響力。另一方面,朱子后學效仿《小學》《童蒙須知》體例,編寫相關理學啟蒙類讀物。陳淳對朱熹小學理念傳承及教材編寫最為得力,他著有《小學詩禮》《訓蒙雅言》《啟蒙初誦》《訓兒童八首》等道德教育類小作,也編著了相對通俗的學術著作《北溪字義》。其他還有如程端蒙與董銖《程董二先生學則》、劉清之《訓蒙新書》《戒子通錄》、真德秀《教子齋規》、李宗思《尊幼儀訓》、胡一桂《人倫事鑒》和王應麟《蒙訓》《三字經》等。由于朱熹及其門人多在書院、精舍和蒙館中教書,故而從理論上而言諸類通俗化文獻在讀書人中得到一定的流傳。在朱熹之前鮮有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學者重視童蒙教育領域,或許受之影響,南宋不少知名學者也加入編寫隊伍,如呂祖謙《少儀外傳》、孫應符《幼學須知》、王日休《訓蒙法》、史浩《童丱須知》、林同《孝詩》、俞觀能《孝弟類鑒》、邵笥《賡韻孝悌蒙求》、徐伯益《訓女蒙求》和楊簡《蒙訓》等。
《小學》在整個東亞文化圈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據蔡雁彬考證,大約在元代中葉、高麗朝后期《小學》傳入朝鮮,在五百余年間倍受尊崇,主要體現在:一是被司譯院用作漢語學習與考試的教材,同時作為科舉考試的“小科”復試依據,也是成均館錄名時的考核之書;二是成為官方的部學到鄉校的重要學習教材;三是發揮化民成俗的政教作用;四是作為學者修己治人的讀本;五是根據《小學》續寫或進行“類小學”讀物編寫,如俞彥鏶《大東小學》、樸在馨《海東續小學》與金亨在《大東小學》等[1]。日本學者白井順曾考察明代的《小學》注解本如陳選《小學句讀》《小學增注》、程愈《小學集說》、何士信《小學集成》、吳訥《小學集解》等在朝鮮與日本的流傳與使用[2]。由此可知,《小學》作為朱子學或理學通俗化的產物,承載了傳統的儒家道德理念。相較于一般的儒家典籍與諸子著述,對非漢語母語的儒學研習者而言,《小學》是權威性的入門書籍,這使其在東亞國家的傳播更具有效性。
二、《訓蒙絕句》:儒家經典的詩歌化詮釋及其民間傳播
束景南認為《小學》《童蒙須知》與《訓蒙絕句》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小學教育體系[3]。《訓蒙絕句》是一本詩集,但與傳統詩歌不同,朱熹提煉四書中關鍵詞作為詩題,并以七言絕句對詩題進行解讀,共計98首。此書的詩題分為兩類:一類是具有四書特色的命題,如《戒慎恐懼》《鳶飛魚躍》《芻豢悅口》《萬物皆備》等49題56首;一類是抽象的理學范疇,如《天》《心》《意》《仁》《致知》《中庸》《命》《性》等30題42首。朱熹編著此書的原因是他對當時社會流行的啟蒙讀物(以識字與掌故類為主)不甚滿意,在他的教育視野中儒家經典更符合啟發蒙童,以更好地打造圣賢坯模。然而,大儒們的經典詮釋文本晦澀深奧,并不符合初學者的智識和閱讀需求。如何使儒家經典閱讀通俗化?如何幫助初學者有效地理解儒家經典呢?對此,朱熹進行了一系列的嘗試與探索。
宋紹興三十二年(1162),朱熹編著了《論語要義》,此書的特點是義理解釋詳細,訓詁考證簡略。宋隆興元年(1163),他對《論語要義》進行刪減并編寫了《論語訓蒙口義》,此書由簡易的訓詁、音讀、章句含義構成,相較前書更加淺顯易懂。現今二書不存,甚為可惜。隆興二年(1164)朱熹又編著了《訓蒙絕句》,此書只保留了義理并將其韻律化,最大限度地使四書通俗化。由三年間三書的連續編寫這一行動可證朱熹在不停地探索將儒學經典通俗化,將理學思想傳播向低齡化、文化層次相對較低的人群下移。
相較于《小學》和《童蒙須知》,《訓蒙絕句》的學術化、知識化、理學化傾向尤為明顯,它本質上是朱熹四書學思想的一種詩化凝練。試以儒家的重要概念“仁”為例:“心無私滓與天同,物我乾坤一本中。隨分而施無不愛,方知仁體蓋言公。”[1]朱熹將“仁”置于“愛”“天理”以及“公”與“私”的關系中進行探討。四句要點分別如下:①心原初狀態未受任何私欲之熏染,人只有除盡哪怕纖毫的私欲才能成仁。②人心不夾雜絲毫私欲之后,才可能實現天地人萬物同一。③愛雖然存在等差,但也未忽略對他人與社會之愛,如“民胞物與”般,天地之間充滿愛。④人完全剝去私欲,天地萬物一體,仁才能最終彰顯無偏無私的“公”,即仁之體為“公”。“以公為仁”的觀點本是程頤對仁的邏輯分解,朱熹繼承并發展了這個觀點。他在正統的學術著作中亦有論述,如:
“仁者人”也,合天下之公,非私于一己者也。蓋無公天下之誠心,而任小己之私意,則違道遠矣。然“仁者人也”,愛有差等,則“親親為大”。[2]
蓋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于其所當愛者反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為一體,而無所不愛矣。[3]
由上對比可知,詩歌化的“仁”呈現的學術立場、專業用語及思想內涵毫無疑問屬于傳統理學著述話語與學術體系,不過《訓蒙絕句》因受詩歌字數與詩體韻腳的限制,呈現出一種凝練的形態。整體而言,詩化的“四書”解釋將龐雜冗蔓、佶屈聱牙的理學思想化繁為簡,類似“道學韻語類”。
《訓蒙絕句》對理學的通俗化還體現在以下幾方面:其一,全文夾雜各種口語化的表達,如“所謂不思并不勉”(《大而化之》)[4],“更無一點閑思想”(《浴沂》),“試把工夫橫豎看”(《居敬》)等直白淺顯、通俗易解的詩句。其二,利用比喻、擬人等修辭手法,如“用猶枝葉體猶根”(《體用》),“不察予心重似雞”(《求放心》),“祇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鑒看”(《克己》)生動形象地解說了深奧艱澀的理學思想。其三,利用詩歌詠物嘆情特點賦予道德教化靈動的氛圍感,如“心隨身上門常閉,課罷苔封候夕暉”(《為己為人》)呈現了朱熹反思當時士子為學目的后產生的一種無奈之感;“捱得一番難境界,便添脊骨一番堅”(《任重》)表現了朱熹對后學任重道遠的殷切期待與真情鼓勵。
朱子門人徐經孫(1192—1273)對此書的訓蒙性質并不贊同,他認為這是朱熹不敢自謂盡道的自謙之辭。清人王文清(生卒年不詳)稱此書:“童子習之,則可以解經義,涉群書,而不迷所往;成人貫之,則然夜之行燭,可以證己見之是非,辨歸宗之疑似,誠為學之階梯,抑亦斯文之桴筏孔。”[1]由此可知,《訓蒙絕句》打破了小學與大學的學習屏障,一面可教授于孩童,促使其浸潤于陰陽造化、仁義道德性命、圣賢傳心之旨中,以打造圣賢坯模;另一面成年人也可閱讀,并與所舊學貫通,檢驗其是非,不失為錦上添花。綜上所論,《訓蒙絕句》在實際的閱讀中,與《小學》相同,呈現出一種全民閱讀的特征。
《訓蒙絕句》中的詩歌與宋元之際流行的理學詩十分相似,理學詩受邵雍的大力推崇,經周敦頤、張載、程顥相承,到朱熹成為最大的推動者。理學詩與詠物嘆事、陶冶情操的傳統詩歌不同,它們主要是討論格物致知之理,闡發性命義理,情感與審美要素雖存在,但不是主流。換言之,理學詩的旨趣并不在文學審美情趣,而是借凝練的詩歌廣泛地宣揚學術觀點并進行思想道德教化。
理學通俗化的根本目的是保證學派的長足發展,使理學的受眾面更加廣泛。《訓蒙絕句》編著的另一個原因或許是朱熹為正統理學的學術地位作辯護,這與張九成(1092—1159)《論語絕句》直接相關。此書形式上與《訓蒙絕句》十分相似,前置一段《論語》原文,后設一首七言絕句進行解讀,它的解讀重點并不在《論語》的微言大義,更似一種對孔子及其門人的言行的評注,主觀情感注入較多。“陽儒陰釋”是朱熹給張九成思想貼的標簽,在理學家的排斥之下,張九成保存下來的著作甚少。朱熹曾閱讀此書并評價:“讀《論語詩》,三復感嘆。今日學者不沒于利欲之途,即流于釋氏之徑,往往視此為迂闊卑近,亦無怪其迷于入德之方也。”[2]筆者認為,朱熹在學術領域主戰場中對張九成流于禪氏進行痛批,并試圖扭轉當時社會禪學對儒學的影響,即使在通俗類讀物中也要搶占市場先機,故而仿照《論語絕句》編寫了《訓蒙絕句》,從而為理學思想掃清異端障礙,保證理學正統地位的穩固性。
與《小學》相同,朱熹門人后學亦跟隨其腳步以詩歌闡釋或詠嘆儒家典籍。如陳淳《閑居雜詠三十二首》、徐僑《讀〈詩〉紀詠》、許衡《大學詩》、劉因《讀論語》、陳普《四書詠》《毛詩詠》、方回《易吟》等。明人譚寶煥(生卒年不詳)雖不為朱熹后學,但他在明正德七年(1512)著有《性理吟》兩卷,前卷為《訓蒙絕句》原文(但只有92首),后卷為自創的七言律詩49首,譚氏自序中表明自己是“效顰東家”。后卷每首詩前都有“朱子曰”,即朱熹對某一命題的基本觀點,然后譚氏再賦詩一首,詩猶如注。雖然譚氏詩作是復述朱熹觀點,并沒有學術創新,但它對朱子學的民間化傳播發揮了一定作用。
譚寶煥的《性理吟》對朱子學的影響并不止于此。據白井順考證,《性理吟》在其后的流傳中“朱子曰”不知因何被省略,因此二書被合成150首并題為《朱子性理吟》流傳。它流傳到東亞的朝鮮與日本,朝鮮大儒李滉(1501—1570)曾閱讀此書并進行考察認為其內容相當淺薄,措辭拙劣,懷疑是偽作;樸齊仁(1536—1618)曾極力推薦太子閱讀《訓蒙絕句》;后朝鮮學者(未知名)將《性理吟》按性理學分類,并加入胡居仁的注釋。在日本,清順治十四年(1657)朱子學研究者山崎闇齋(1618—1682)出版了《朱子訓蒙詩》并為其作跋;清咸豐二年(1852)楠木碩水(1832—1916)手抄《朱子性理吟》并供門人研習[3]。由上所論,《訓蒙絕句》《性理吟》受到漢語圈外的日本與朝鮮儒學圈的重視,并以他們的方式閱讀,亦可證朱子學的普及范圍之廣。
三、《性理字訓》:理學范疇通俗化闡釋及其民間普及
宋代學者常將哲學范疇稱為“字”,對“字”的解釋則稱為“字義”或“字訓”。對哲學范疇及推理致思其實早分散在哲學論著中,但并未有學者單獨將其凝練出來并進行集合釋義。前述《訓蒙絕句》中一類詩題就是理學概念,朱熹從四書中凝練了約30個。程端蒙的《性理字訓》(又稱《小學字訓》)以朱熹理學思想為源頭,提煉了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意義的理學范疇30個。具體如下:
命、性、心、情、才、志、仁、義、禮、智、道、德、誠、信、忠、恕、中、和、敬、一、孝、悌、天理、人欲、誼(義)、利、善、惡、公、私
《性理字訓》言簡意賅,全文不過500余字。由于難以確定此書的具體成書時間,其與《訓蒙絕句》孰是源頭無法下定論,但至少能說明朱子一脈是最早將理學概念作為統編主線并對其進行解釋的群體。師徒二人對此書的編寫還有交流,宋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閱讀《性理字訓》后寫信于程端蒙并褒揚此書,這一年正好是《小學》正式序定刊印的時間。程端蒙的另一著作《程董二先生學則》與朱熹的《童蒙須知》十分相似,這種巧合可以說明在理學通俗化著作的編寫領域朱門之間具有一定的默契,甚至可以說是一種特意的安排,即得到朱熹的授意,當然這種授意是以正統的理學思想傳播為前提。我們分別以程端蒙和朱熹對“仁義禮智”的解釋為例:
為木之神,在人則愛之理,其發則惻隱之情,是之謂仁。為金之神,在人則宜之理,其發則羞惡之情,是之謂義。為火之神,在人則恭之理,其發則辭遜之情,是之謂禮。為水之神,在人則別之理,其發則是非之情,是之謂智。[1]
蓋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為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為恭敬。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為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為是非。[2]
二者相較,可以說程端蒙的“字義”基本是對朱熹觀點的復述,語詞的表達、闡釋的順序幾乎完全一樣,實乃恪守師傳,不失尺寸。縱觀30個范疇,程端蒙將朱熹已下過定義的重要的理學概念進行集合,在已有的名詞解釋基礎上進行形式上的變動,使用明顯的下定義句式“是之謂”進行統一,或進行增添、刪減、調序,也有一些自我總結。
《四庫全書》褒揚《性理字訓》創造了仿蒙求體。蒙求體是中國傳統通俗化讀物重要體裁之一,原出自唐代李瀚專門為孩童編寫的歷史掌故課本《蒙求》一書,此書采用四字韻文,每四字為一句,上下兩句構成對偶。程端蒙將歷史掌故轉換成理學概念,相關聯的“字義”對偶,并以“是之謂”統一結尾。朱熹稱此書是“大《爾雅》”,《爾雅》是中國第一部詞典,《性理字訓》也可稱得上是一部理學微型詞典。然而,“大”一詞頗有意味,從著述篇幅而言,《爾雅》必然勝出,可見“大”并非指此。清人汪師韓(1707—1774)曾解釋,“朱子以‘大《爾雅》稱之,惟所釋乃仁義道德之字”[3],“仁義道德”乃是儒學所信奉的重要價值,在朱熹看來《性理字訓》更勝一籌,故而以“大”稱之。
宋末程若庸(生卒年不詳)為朱熹的再傳弟子,他對《性理字訓》進行了增補與修改,并著成《增廣性理字訓》,后此書代替《性理字訓》流傳于世。《增廣性理字訓》的特點主要表現在:其一,它將范疇分成造化、性情、學力、善惡、成德、治道6個類型,并將30個范疇增至182個[4],以使理學范疇體系更加完整和豐富;其二,將《性理字訓》中四言、五言、七言統一調整成四言,使全文更加規整;其三,在保持原有范疇解釋的基礎上進行補充,使闡釋更為充實與準確。
《性理字訓》對理學家饒魯(1193—1264)與王柏(1197—1274)也產生了影響,二人分別著有《訓蒙理詩》與《伊洛精義》。前者歸納了如天地、日月、四時、八節、五行、人物、人倫7個基本儒學范疇;以五言為一句,八句為一組,語言生動有趣。后書提煉了55個常用理學概念,其中與《性理字訓》相一致的有18個,并加入了如狂、狷、自暴、自棄、殘、賊等并不常用的概念;形式上采用四言一句,四句為一組,其闡釋觀點多來自二程。與程端蒙一樣,王、饒二人均受聘于各大書院,對普通學子而言,厘清與理解性理范疇的含義對研習理學具有指導意義,這也呈展了程朱理學在民間傳播的樣態。
這類以“是之謂”“是曰”“謂之”句式結尾的明顯下定義的理學范疇詮釋集合體,由于受字數、對偶、韻律等限制,對理學概念內涵的理解容易產生不完善、不全面的問題。陳淳的《北溪字義》則規避了義理解釋不到位的問題,這也是字義體文獻從啟蒙教育層面向學術研究領域的轉向。《北溪字義》共選取了26個范疇,具體如下:
命、性、心、情、才、志、意、仁義禮智信、忠信、忠恕、一貫、誠、敬、恭敬、道、理、德、太極、中和、中庸、禮樂、經權、義利、鬼神、佛老、太極
它與《性理字訓》重合的概念達到17個,特別是命、性、心、情、才5個范疇在書中出現的位置與先后順序都一致,這很難說是巧合,很難否認二書之間的相承關系。朱熹、程端蒙、饒魯、王柏、程若庸著書的初衷是將理學思想通俗化,發揮啟蒙初學者的功效,故而行文簡明扼要,直白淺顯,篇幅短小。《北溪字義》則采用一般敘述體,篇幅較大,但是與艱澀深奧、部帙繁復的理學論著比較,這部陳淳晚年的講學稿還是相當通俗易解的。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概念詮釋整體架構筋骨分明、層層推進。以“仁義禮智信”為例,①“分別看”,對“五常”即“仁義禮智信”逐一闡釋;②“橫觀”,從五者橫向關系進行比較;③“豎觀”,從五者先后次序推進解釋;④“錯而言之”,從五者縱橫交錯關系展開論述。從四個層次剖析,概念的解釋呈現出限界分明、脈絡互通,故而每一個字義的解釋都像一篇小論文。二是使用技術性的解釋條件,比如每段段首開明宗義,概述本段大意;或使用具有“引導性”的詞句作提示;或以簡短明確下定義方式“曰”“則謂之”“是之謂”提醒。三是巧妙運用如比喻、擬人、排比、設問等修辭手法,即使是敘述體,仍使抽象嚴肅的理學概念、靜態理論闡釋顯得自然生動。四是使用與日常生活相近的例子解釋概念。比如對氣稟清明但賦質不純粹的“不賢者”如此形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里面,亦透底清澈。但泉脈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烹茶則酸澀,是有惡味夾雜了。”[1]陳淳將人之氣稟的清濁與泉脈汲取過程中的清濁結合起來,此種闡釋風格在文中比比皆是,甚是形象生動。
《北溪字義》對理學范疇的闡釋,其論證的嚴密性、義理的深刻性、邏輯的清晰性都遠甚于前書,當然文中的觀點未脫離于朱熹的理學范圍框架,故而陳榮捷稱之為“一部朱子思想的最佳結晶,也是新儒家哲學名詞的最佳詮釋”[2]。朱熹后學陳普(1244—1315)直言受《性理字訓》與《北溪字義》之影響,并編有相同體例的《字義》。此書編排了153個范疇,基本涵蓋了前書所涉及的概念,也有如降衷、秉彝、浚哲、謀、惹良、誠之、密、軌必等罕見的詞條;其句式長短不一,篇幅不均,下定義的方式繁多。陳普作為朱子一脈的理學家,其義理解釋仍以朱熹思想為中心。
雖然字義體文獻并不在當時理學研究的主流范疇之中,但后世學者對它們進行了各類注解與增補,可見這類理學通俗類讀本并沒有斷續。如宋代黃季清《訓蒙詩注》、郭元源《朱子性理吟注》、董玠《性理字訓注》、沈毅齋《增廣性理字訓注》、戴亨《北溪字義辨正》;元代金若洙《性理字訓集義》、李季札《字訓續編》、陳櫟《小學字訓注》;明代佚名《北溪先生性理字義節要》《北溪先生字義詳解》;清代金友理《朱子性理吟注釋》、方博《朱子性理吟集說》、鄭儀孫《箋注性理字訓》、黃叔璥《廣字義》;民國張元勛《訓蒙詩集解》、鮑心增《北溪字義啟蒙》等。值得一提的是,這些作者之間具有明顯的師承關系,且多為朱熹一脈。
《小學》《訓蒙絕句》曾在海外傳播并產生一定的影響,《北溪字義》亦影響過東亞的朝鮮與日本,這也再次證明了理學通俗化讀物的傳播力度。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朝鮮翻刻了《北溪字義》;林羅山(1583—1657)將此書翻譯成日文,于明天啟元年(1621)首次出版,后崇禎元年(1628)、崇禎五年(1632)對此書的日文版進行重版,這三次出版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北溪字義》對非漢語民族初學者的指導作用。清順治十年(1653)林羅山編著了《性理字義諺解》一書,于順治十六年(1659)出版,此書是日本學者對《北溪字義》的一種通俗化注解,后產生一系列相似的讀物,如淺見絅齋(1652—1711)《性理字義講義》、若林強齋(1679—1732)《性理字義師說》等書。陳普的《字義》亦有1671年和1694年的和刻本,當然,它在日本的影響力無法與《北溪字義》在日本的影響力相比。
四、結語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兩個結論:其一,從通俗教育與傳播領域而言,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家在中國傳統啟蒙道德教育史上的貢獻是巨大的。在《小學》成書之前,啟蒙著作的數量與種類極少,在朱熹的推動與實踐下,宋代開創了多種啟蒙教育類型并形成了完整的教材體系,其后的元明清不過是踵事增華。據筆者粗略統計與歸納,宋代理學家的通俗化文獻類型可分為道德類、理學類、經學類、歷史類、識字類、文章類、韻對類、博物類等8大類50余本。當然這類通俗類讀物根本上是程朱理學在學術領域向下攻占的一種策略,這種“向下”可分為年齡的下降與階層的下移兩個層次。在啟蒙教育理念的推動下,經過朱熹及其后學的不懈努力,這類理學通俗化讀物在民間廣泛流傳,并成為全民性的讀物,甚至傳播到海外。其二,從理學理論體系完善與學派思想傳播層面而言,朱熹確定小學教育理念、小學與大學分野及其教育設計,編著《小學》《訓蒙絕句》《童蒙須知》等書,無論是彌補四書理論體系中“致知”與“敬”的抵牾,還是保證以“存天理、去人欲”為基礎的道德修養論的完整性,抑或是對佛道等異端思想的抵抗而爭取更多理學信徒,根本上都是從理學思想體系完整構建出發。這也解釋了朱子后學紛紛加入這一隊伍的原因:本質上還是為了保證理學社會地位的正統性與穩固性。
關注一流的儒學人物與鴻文巨冊是學術研究史中一般的歷史敘事圖景,然而在深邃精致的哲思所繪出的濃墨重彩的畫作中,尚有一些為人忽略的墨點、線條,抑或是空白,理學通俗化文獻大概就屬于這類。從諸文獻的編著者、著述內容、體例與特征等方面可知它們之間具有明顯的傳承關系,這是一條研究朱子學和理學的蜿蜒曲折的蹊徑。本文旨在盡微薄之力將朱子學、理學和儒學發展史中不為人注意而湮沒于歷史中的這一股潛流引導出來,希冀能為中國哲學的世俗化、通俗化研究提供一種特別的視域。
〔責任編輯:史拴拴〕
本文為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儒家經典通俗化詮釋文獻的整理與研究”(22ZXC005)的階段性成果。
[1]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1頁。
[1]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2—3頁。
[2]其中朱熹《孝經刊誤》明顯不具有通俗化性質,故不列出。參見熊大年:《養蒙大訓》,《叢書集成續編》第61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99—233頁。
[3]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250冊,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41頁。
[1]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七,王星賢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6頁。
[2]唐紀宇:《事與理——朱子〈小學〉概說》,《中國哲學史》2019年第1期。
[3]楊廉:《楊文恪公文集》卷六十,明刻本,第14b頁。
[4]文德翼:《求是堂文集》卷十六,明末刻本,第32b頁。
[5]賀欽:《醫閭集》卷一,民國四明叢書本,第1b—2a頁。
[6]楊士奇:《東里續集》卷三〇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配清文津閣四庫全書本,第14b頁。
[7]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一一八,王星賢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855頁。
[1]蔡雁彬:《朱子〈小學〉流衍海東考》,《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
[2]白井順:《朱熹〈小學〉傳播的一側面——以程愈〈小學集說〉為中心》,《歷史文獻研究》總第36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2—59頁。
[3]束景南:《朱子大傳:“性”的救贖之路》(增訂版),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616頁。
[1]朱杰人、嚴佐之等編:《朱子全書》第2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頁。
[2]朱杰人、嚴佐之等編:《朱子全書外編》第1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頁。
[3]朱杰人、嚴佐之等編:《朱子全書》第2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3—1414頁。
[4]以下詩均出自《訓蒙絕句》,不一一注明。
[1]王文清:《朱子性理吟引言》,轉引自朱漢民、鄧洪波:《岳麓書院史》,湖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67頁。
[2]朱杰人、嚴佐之等編:《朱子全書》第2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31頁。
[3]白井順:《朱子學的傳播與普及——〈朱子訓蒙絕句〉如何被閱讀》,《人文論叢》2006年第00期。
[1]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280冊,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頁。
[2]朱杰人、嚴佐之等編:《朱子全書》第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12頁。
[3]汪師韓:《韓門綴學卷一·五雅》,清乾隆刻上湖遺集本,第32b頁。
[4]明代朱熹后學朱升(1299—1370)增補一條“善”,共計183個概念。
[1]陳淳:《北溪字義》,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頁。
[2]陳榮捷:《朱學論集》附錄二,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