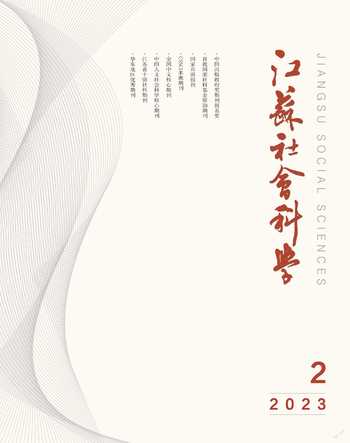網絡民俗研究的理論邏輯和“概念性框架”
徐國源 曹志偉
內容提要 數字化傳播時代,人們的日常生活、習俗環境被互聯網影響和重塑。互聯網中勃勃新生的大量新型民俗事象,反映出傳統民俗在現代社會生活語境中發生了深刻衍變。這類在網上生產、傳播的新民俗,雖保留了傳統民俗的“種”的基因,但也反映出因社會生活內容更新、數字化傳播所帶來的諸多衍變,且已蛻變為棲居網絡空間的“新民俗”。基于數字化時代“民俗”出現的變化,民俗學研究既要關注數字化時代社會正經歷的“再習俗化”過程,聚焦網絡民俗的“元問題”并作出整體性觀照,展開網絡民俗的多學科、系統性研究;同時也要積極跟進互聯網時代生活數字化帶來的民俗學概念性框架的新議題,拓展原有的研究方向和內容,推動民俗研究理論范式創新和現代民俗學學科建設。
關鍵詞 網絡民俗 數字傳播 民俗學
徐國源,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曹志偉,南京財經大學新聞學院講師
數字化時代,人們的日常生活、習俗環境被互聯網影響和重塑,社會正經歷著一場深刻的“再習俗化”過程。傳統的民俗文化如節慶、祭祀、展演等,除在當下的社會生活中傳承外,還轉移到了互聯網空間,且生成了大量帶有網絡專屬特征的民俗新形式,如:網絡民俗藝術、網絡民間文學、網絡節慶與祭祀、網絡崇拜與信仰等。網絡民俗,也可稱為“在線民俗”,它依托數字化傳播平臺不斷產生并迅速傳播,使傳統民俗真正處于“活”的狀態,同時也為人們提供了虛擬空間民俗文化實踐、體驗和消費的新路徑。基于數字化時代民俗文化傳承、生產和傳播出現的新變化,需要拓展互聯網時代民俗學的研究視域,調整民俗研究的范式和方向,關注互聯網時代民俗學產生的新議題,分析探討網絡民俗的新特征、新形態和新機制。
一、拓展數字時代的民俗學研究領域
依托互聯網生成的大量新型民俗事象,目前一般稱之為“網絡民俗”。這類在網上生產、傳播的新民俗,雖保留了傳統民俗的“種”的基因,但也反映出因社會生活內容更新、數字化傳播所帶來的諸多衍變,且已蛻變為棲居網絡空間的“新民俗”。基于數字化時代民俗出現的變化,當代民俗學研究理應有所回應,將“網絡民俗”作為重要研究內容。
國外民俗學、文化人類學界已然形成關于“網絡民俗”的系統性討論。20世紀中后期,美國民俗學家阿蘭·鄧迪斯就注意到,21世紀是互聯網統治的時代,人們將紛紛從現實空間“奔向”網絡世界,并斷言“任何一種文化藝術倘若不與網絡聯系在一起,都會逐漸走向衰敗”。他還清楚地表明“工業化事實創造了新民俗”,例如,計算機民俗[1]。鄧迪斯的這一觀點對民俗學研究有著重要的啟示,也引發了西方民俗學者開始轉向網絡民俗的研究。美國學者特雷弗·布蘭克于2009年出版的《民俗與互聯網》及于2014年出版的《民俗學和互聯網研究的概念性框架》,就專門針對新興數字技術時代的互聯網民俗進行了理論化闡釋,旨在“將網絡確立為民間研究的合法領域”[2]。布蘭克于2012年出版的《數字時代的民俗文化》,還明確將互聯網視作民俗學家重要的分析領域,并為數字化的民俗研究設定了相關研究議程。2010年以后,美國、英國、俄羅斯等國家的許多民俗學者開始轉向互聯網民俗研究,將研究視角從傳統的民間故事、傳說、風俗習慣等延伸到了與當下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網絡虛擬世界,步入了數字時代的“后民俗學”[3]研究。
國內對于“網絡民俗”雖尚未形成系統性的討論,但一些前輩民俗學者在其民俗學論著中的一些觀點對認識“網絡民俗”有較大啟示。如鐘敬文認為:“民俗學的研究是現代學,它研究的資料主要是從現代社會中采集來的。”[4]他提出民俗學的性質是“現代的”,要盡可能建立“現代式科學”[5],指明了民俗研究與現代社會發展的關聯性。烏丙安則在《民俗學原理》一書中提出:“全社會變革帶動了整個習俗環境的變革……俗民個體不得不在不同程度上接受這種改變了的習俗形式,從而導致了一場大范圍的俗民再習俗化。”他進而指出這種“再習俗化”過程將會產生新的民俗[6]。鐘敬文等雖沒有專門討論互聯網時代的“網絡民俗”問題,但已揭示民俗的“變動性”和民俗研究的“現代性”。另一位民俗學者高丙中在其《民俗文化與民俗生活》一書中,則通過對“民”和“俗”意義的溯源提出:隨著新生活、新群體、新媒介的出現,一方面,過去以“農民”為主體的傳統民俗觀要有所改寫,農民其實只是一種類型的“民”,還有城市市民之“民”以及都市化時代的“新市民”,后者已極大地擴展了“民”的范疇;另一方面,“俗”的內容也在變化,民俗之“俗”的外延“已經擴展到全部的社會生活、文化領域了”,且已從舊時代以農村為主的舊風俗形態轉變為新都市、新工業化時代的“新民俗”(西方一般稱為“后民俗”)[7]。據此,高丙中提出:“工業化事實創造了新民俗……例如,我們現在就增加了沖浪的民俗、摩托車騎手的民俗和計算機設計者的民俗(計算機民俗)。”[8]上述國內學者都敏銳地注意到了現代社會生活更新所帶來的“民俗”衍變,并作出了頗具前瞻性的學術提示,這對今天的網絡民俗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啟示。
進入21世紀以后,特別是隨著數字化傳播媒介不斷發展,網上以“民俗”“民間文化”“新民俗”“非遺”等冠名的民俗現象大量涌現,基于此,一些學者也開始將“網絡民俗”納入研究視野,倡導展開網絡(數字)民俗、“后民俗學”研究。代表性的論文如黃永林的《民俗學的當代性建構》和李向振的《拓展互聯網時代民俗學研究視域》,兩者都指明互聯網是民俗學家開展民俗志研究的獨特領域,網絡民俗研究有助于民俗學成為“現代學”的學科特點。孫文剛在《網絡民俗:民俗學科的新生長點》中更清晰地闡明:網絡民俗成為愈來愈多的當代人(尤其是廣大網民)的一種模式化的民俗生活,如從昔日面對面的游戲、談話到今天網絡虛擬空間中的游戲、網聊等娛樂方式的改變;從古時的“烽火傳訊”“鴻雁傳書”“魚傳尺素”到現代的寄書信、發短信、打電話、E-mail、QQ聊天、飛信、微博、微信等日常通信方式的改變,實質性地反映出傳統的民俗生活在現代社會語境中的演變,反映出網絡時代人們民俗生活的一種變化[1]。自2010年以來,越來越多的民俗學研究者開始關注和研究網絡新民俗事象,一些其他學科的研究者也有意識地向“網絡民俗”聚焦,楊秀芝的《“互聯網+”視野下的民俗文化活態化研究》[2]、程名的《網絡傳播的社群化特征與網絡民俗的建立》[3]、彭小琴的《民俗藝術的新媒體傳播路徑》[4]等,就分別從不同學科背景、理論視角關注傳統民俗的傳播語境轉換和歷史承變,揭示出網絡民俗研究的多元認知維度和新的研究路徑。
不可否認,國內學者對網絡民俗的研究雖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但總體而言我國的網絡民俗研究還是一個尚待開發的學術領域,真正涉足此研究的民俗學專家不多,尤其是深耕此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較少。更有意味的是,“網絡民俗”一詞其實也并非由民俗學者提出,而是由從事傳播研究、文化研究的學者首倡并加以命名。從民俗學發展角度看,此種相對“冷寂”的研究狀況,與西方國家“后民俗”研究日趨主流、煌煌勃興形成鮮明比照,確實引人深思。
國內有影響的民俗學者較為疏離“網絡民俗”研究,其中原因大概有三:首先,從學術范式看,歷來從事傳統民俗學研究的學者較多致力于民俗學科的原生問題研究(是什么、為什么、能什么),主觀上較為輕視對“當下”“活態”的傳承和傳播問題;其次,從學術觀念上看,他們一向較為關注傳統民俗學領域內的學術命題,對“舊”民俗有眷戀,與“新”民俗則保持距離,因而對現代生活中、網絡空間上傳播的“異質”的新民俗現象保持著警惕,或將“脫范”的網絡民俗歸為“大眾文化”現象,而不將其歸為“民俗”;最后,乃學術趣味使然,一些民俗學者對網絡新媒介不太留意,甚至對網絡傳播還不太熟悉,更遑論其中已十分斐然的民俗現象。
由于上述種種原因,至少到目前為止,國內最優秀的民俗學者加入“網絡民俗”研究陣營中的人較少,反而是一些傳播學者、文化研究學者“跨界”進入了新民俗研究領域。但這種“跨界研究”也帶來了相當大的問題。第一,網絡民俗首先還是“民俗”,“網絡”只是傳播媒介問題,如果缺少對民俗“原問題”的精深耕耘,就無法從根本上探討網絡民俗的基本屬性,一些學科性的問題也很難回答;第二,其他學科學者的跨界研究由于對傳統民俗存在一定隔膜,難免從民俗“表象”看問題,以致出現誤讀、誤解之缺憾;第三,從更深的方面看,“跨界”的研究往往從外視角看問題,缺少內視角的民俗學科意識,難以在民俗學學科發展的層面上建構更科學、更具體系化的民俗研究的理論體系。總體而言,到目前為止的網絡民俗研究并不令人樂觀,真正有價值、高質量的研究成果也不突出,更遑論具有原創性、體系化的理論專著力作了。
在“網絡棲居”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方式的今天,網絡民俗以其充滿活力的實踐重構了傳統民俗學的版圖格局。新的問題域與風俗場要求民俗學進行理論建構與創新,以實現民俗研究與民俗實踐的同頻共振。網絡民俗是民俗在數字媒介時代的新形態,一定程度上重構和改造了傳統民俗。“確立網絡民俗研究,對于我們認識、理解、把握網絡民俗和民俗之間的聯系會通提供了一個切入點,也為我們在民俗學領域更加深入地走進微觀文化研究和民俗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契機。”[1]
網絡民俗的研究無疑具有多方面的價值。從學科建設方面看,一方面,由于互聯網已成為民俗生產的重要因素,許多新的、創造性的混合文化表達已具有了“民俗”性質,也擴展了民俗學本身的內涵,因此民俗學需要拓展原有的研究方向、范式和內容,研究互聯網時代民俗學產生的新議題。另一方面,互聯網以其充滿活力的傳播實踐重構了傳統民俗學的版圖,學術研究需要聚焦網絡民俗的“元問題”并作出整體性觀照,形成網絡民俗研究的問題域,展開網絡民俗的多學科、系統性研究;同時,新的文化場和問題域要求學科之間破除壁壘,對網絡民俗展開跨界交叉的多學科綜合研究,為數字化時代的民俗學理論建設、學科發展提供新思路、新方案。
從學術研究與現實互動的角度看,網絡民俗研究將加深人們對互聯網時代民俗文化的認知,而衍生的思想觀點將回應民俗文化適應社會發展的時代訴求,拓展民俗文化的現實服務功能,所論述的問題也將能推動民俗文化資源觀的形成,直接或間接地助力現實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為政府文化政策和文化傳承創新提供理論指導。
二、網絡民俗研究的“概念性框架”
數字化傳播時代,“網上棲居”已生成了一種新的社會關系和生活模式,也使各種民俗現象依托網絡平臺不斷產生并迅速傳播。毋庸置疑,網絡空間正經歷著一場“再習俗化”過程。從宏觀的視角進行考察,傳統社會中人之“習俗化”與三個方面的因素緊密相關:第一,習俗化與人的本能有關;第二,習俗化與人的自然成長有關;第三,習俗化與人的社會化有關。而在以網絡空間為代表的多元傳播環境下的“再習俗化”,則是在原習俗化基礎上的社會性延伸或者補充,也可以說是一種繼續并擴大習俗養成的活動。特別是在新的生活數字化環境下,人們所經歷的網絡空間的再習俗化還具體表現出三個特征:第一,習俗環境變革中的再習俗化;第二,異文化環境中的再習俗化;第三,個人自覺的再習俗化。如此來看網絡民俗,也許它已經是經過多次延伸、補充、再造的“再習俗化”的民俗了。
當代民俗學研究應注意到網絡空間的“再習俗化”進程,以及建基于數字傳播時代人們的民俗生活經驗的衍變。這些新的因素不僅更新了“鄉土”“俗民”“習俗”等原有的意義,且生成了許多與傳統民俗文化不同的“異質性”及表征。2014年5月,美國猶他州州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該校波茨坦分校英語與傳播系助理教授特雷弗·布蘭克編寫的新書《民俗學和互聯網研究的概念性框架》。布蘭克在書中表示:“傳統主義者總是認為民俗學領域的田野調查只能在田間地頭進行,因此常常忽略數字化,認為數字化僅存在于技術和大眾媒體領域,無法在網絡空間內開展田野調查;但實際上,互聯網不只是言論和觀點的傳播平臺,而已發展成為民間文化、風俗習慣不斷演變和創新的平臺。”[2]該書試圖構建一個互聯網民俗研究的理論框架,開拓了民俗學研究的新領域。
網絡民俗,包含了網絡民間文學、網絡崇拜與信仰、網絡祝福與祭祀、網絡游戲娛樂等諸多復雜事象,是一種新型民俗文化。作為廣大網民傳承、享用、創造的一種生活文化,它既屬于廣義民俗的一部分,又是民俗發展中出現的一種新的民俗形態。作為學術的回應,網絡民俗研究既要分析考察網絡民俗“是什么”“變了什么”“傳了什么”等民俗學科問題,還需探討這種新的民俗形態何以可能、網絡空間如何“再習俗化”、其產生有著怎樣的文化背景和現實依據、如何評估網絡民俗價值等跨學科問題。
鑒于互聯網時代民俗文化出現的新變化,民俗學需要調整既有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向,不斷跟蹤研究數字化傳播時代網絡中的新民俗現象,同時,也要重視網絡環境下日常生活方式衍變所生成的新民俗特征,以便更好地研究互聯網時代民俗學產生的新議題。例如:作為“新知識”的網絡民俗所包含的三個關鍵因素,即新的生產(傳播)主體——網民、新的傳播媒介——網絡、新的民俗內容——新民俗[1]。同時,還要探究數字化傳播時代“民俗”范疇的要素到底發生了哪些變化,具體包括:從“俗民”到“網民”身份如何演化?習俗的生產傳播環境究竟發生了哪些更替?從生活媒介到數字媒介的衍變又帶來了怎樣的社會慣習革新?這些問題都需要運用到社會學邏輯,借助多學科理論加以探討和回答。
近20年,國內外網絡民俗相關研究取得了較多成果,為網絡民俗的深層認知、理論建構和新研究領域拓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礎。比如,在“認識論”方面,學界對網絡民俗已初步形成了共識:首先,網絡民俗不只是字面上“網絡”和“民俗”的簡單累加,還關涉對民俗學和網絡傳媒的復雜關系的認識;新的民俗“現象”,反映出互聯網時代網民對傳統民俗的現代、后現代“改造”。其次,網絡民俗是一種不斷變化、擴容的新型民俗文化,是傳統民俗形式的“更新換代”。最后,民俗學需建構“現代學”的學科特點,同時介入當代網絡社會文化建設的現實需要之中。
由此“認識論”,我們大致可形成網絡民俗研究的總體學術思路,即通過對互聯網傳播結構的分析,描繪出技術嵌入社會系統的過程,將民俗實踐活動放置回社會文化的整體性語境中予以觀照,考察網絡民俗之于民俗研究領域的影響和意義。同時,還需帶著鮮明的問題意識,透過對大量網絡民俗事象的深度分析,生成網絡民俗研究的問題域和理論話語,形成多維度的學術思考,如:如何解釋數字空間的社群化、再習俗化?民俗的地方性、空間性如何改變?怎么看互聯網帶來的民俗生態與社會生活轉型?傳統的禮俗互動還存在嗎?如何建立民俗文化與社會發展議題之間的學理聯系?等等。在此眾多問題的引導下,我們大致可形成數字化時代網絡民俗研究的“概念性框架”。
(1)網絡空間的社群化。互聯網技術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棲居”于網絡,形成網絡俗民社群,他們的社會慣習也隨之更新。在網絡構建的空間里,俗民擺脫了千百年來地緣的束縛、權力制度的支配與習俗慣制的約束,參與空間也從露天舞臺轉向了電腦、手機。這種網絡空間的社群化涉及諸多需討論的問題,如虛擬、鏈接與俗民人際關系如何重構?匿名、即時的鏈接傳播生成了怎樣的俗民群體的聚合?網絡社群化如何帶來新民俗生產?等等。
(2)網絡空間的“再習俗化”。正如詹姆斯·凱瑞所指出的那樣,網絡媒介傳播已經成為“將人們以共同體或共同體的形式聚集到一起的神圣典禮,它的最高境界是建構并維系一個有秩序、有意義、能夠用來支配和容納人類行為的文化世界”[2]。如此來看,網絡媒介之于民俗意義的建構,就不再局限于民俗文化元素的高度仿真和再現,而已置換為網絡虛擬空間的“再習俗化”。在人媒融合的新環境下,網民們可以在“圍觀”與“參與”之間靈活轉換,完成民俗的轉生和衍生,創造出許多新的民俗模式、民俗形態和符號。因此就有必要追問,“習俗”的形成條件為何?網絡空間如何再習俗化?網絡民俗的生成邏輯是什么?等等。
(3)網絡傳播與民俗的傳承、變異及重構。進入21世紀,隨著互聯網日漸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發生在網絡虛擬空間中的民俗傳承和傳播有了很大變化,以至如何解釋和界定“民”和“俗”也成了新的問題。不過歷史地看,每一時代的民俗其實都有過因為傳統生產生活方式變化,隨之形成新的民俗傳統的情形。如此來看,網絡民俗的出現,既顯示出“傳統”之于新技術環境的適應性,同時也反映出民俗與時偕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網絡民俗作為廣大網民創造、享用、傳承的一種生活文化,既屬于廣義民俗的一部分,也是民俗發展中出現的一種新的民俗形態。當代民俗學者應以動態的視角去看待和研究這一新技術時代的網絡新民俗,深入探究在數字化傳播環境酵化作用下逐漸生根的網絡民俗與傳統民俗的關系,進行如下問題的討論:媒介技術的賦形如何生成網絡新民俗?傳統民俗在網絡傳播中如何傳承、變異和重構?網絡民俗特征、功能及意義為何?等等。
(4)傳統民俗觸網與“互聯網+型”民俗。農耕時代,民俗文化主要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在相應族群內部傳播,具有地域性、封閉性較為明顯的特征。在如今5G技術主導的新媒體時代,越來越多的民俗文化已借助高速發展的傳播技術,沖破了地域界限,突破了族群內部傳播束縛,異常鮮活地呈現于大眾視野。這種“互聯網+民俗”的傳播形態不僅拓展了傳播途徑,更重要的是它更新了民俗生產的傳播機制,民俗文化因此出現了與傳播共享的“互聯網+型”民俗。其中也有許多“傳播”問題值得探討,如:傳統民俗如何實現網絡“活態”傳播?“互聯網+民俗”的傳播形態為何?如何評估“互聯網+民俗”與民俗文化資源觀?等等。
(5)習俗的虛擬化與“轉生型”民俗。網絡民俗實踐活動是整體性社會文化語境演化的伴生物,它對傳統民俗事象既有傳承,也因媒介、傳播、語境等新“變量”而出現了變異和重構。如此,就需要討論為適應現代生活習尚、由社會生活空間向虛擬空間轉移的“轉生型”新民俗,重點需要討論的問題包括:“轉生型”網絡民俗事象的類型、特征為何?“轉生型”網絡民俗的生產機制是什么?網絡如何展示新民俗生活?
(6)網民衍生創造與“再生型”新民俗。民俗與生活關系緊密,既有歷史淵源,又有現實基礎,人類社會任何一個時期都在萌生形成新的習俗。網絡媒介不僅塑造傳統民俗事象,同時也在“仿真”性的民俗活動參與中通過移植、復制、延展、創新等方式,在傳統民俗的“模因”中融入現代生活元素,運用民俗性象征符號進行民俗文化重構,從而使其成為當代生活消費文化。需要討論的問題包括“再生型”網絡新民俗及其特征、“再生型”新民俗與原有民俗比較分析、“再生型”網絡民俗的生產機制、網絡新民俗與民俗重構議題等。
(7)“鄧迪斯之問”與網絡民俗的理論框架建構。互聯網是民俗學者開展民俗志研究的獨特領域,也是傳統民俗學在“后民俗”時代研究范式、學科概念和理論敘述創新發展的新空間。如此,就需從民俗學發展角度回應“鄧迪斯之問”:網絡能否扮演民俗傳承和社會傳承的角色?民俗學發展該往何處走?網絡民俗學研究方法為何?[1]在回應、闡釋“鄧迪思之問”的基礎上,建構出互聯網民俗研究的理論框架。
(8)互聯網傳播與民俗文化傳承、保護和利用。網絡改變了當代民俗文化傳承發展的軌跡,也帶來了民俗理論范疇的新變,呼喚著當代中國民俗研究方向和范式的調整和改變。這需要我們在更宏闊的視野上重新審視互聯網時代民俗文化的傳承保護問題,積極展開如何推動民俗文化適應社會發展的理論思考,如:民俗的現實意義與應用價值為何?民俗文化資源觀與文化創新如何再認識?如何解釋民俗的禮俗意義與價值引導?等等。
上述“概念性框架”,特別強調了網絡民俗之于傳統民俗在生產傳播主體、空間(數字空間與生活空間)、機制模式上的傳承和重構,同時也內含著網絡民俗研究的學理邏輯和問題意識。民俗學者應該認識到,網絡民俗研究的重要性其實并不亞于傳統意義上的民俗志研究,它面向人類所置身的現代、后現代,植根于當下社會的民俗生活和經驗,是一個大有可為的研究領域。
三、建立“現代式科學”的網絡民俗研究
20世紀90年代,民俗學家鐘敬文先生就提出了“民俗學研究的目的,要盡可能建立現代式科學”的觀點。鐘先生的論見,既包含著對民俗研究向“現代式科學”邁進的深切關注,也提示傳統民俗研究亟待在理論、內容、方法上拓展更新,推動學科向“現代性”“科學性”方向發展。
網絡民俗以其充滿活力的生產傳播實踐重構了時下的文化傳播版圖,新的文化場與問題域要求學科之間破除壁壘,進行跨界交叉的綜合研究和理論建構創新。首先,需要建立網絡民俗研究的問題域和話語體系,拓展傳統民俗學理論維度。在這方面,國外網絡民俗研究似已形成了較為明確的“問題域”和研究方向。例如,一些西方學者注意到,虛擬環境不僅適合一般文化生產,也適合民俗生產,互聯網已經成為民俗學生產的主要因素,許多新的、創造性的和混合的文化表達,具有明確的民俗學性質,且已出現在生成的事實語境和文本之中。因此,網絡民俗研究要“根據特定的參數討論虛擬環境的民俗化,而不是民俗的虛擬化,還應揭示通過數字通信技術產生的文化環境和背景是如何變成一個經驗領域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又如何幾乎等同于口頭環境”[1]。國外的民俗學研究提示我們,民俗學研究既要深耕民俗學科原生問題,也應重視“當下”“活態”的傳播問題,從而在民俗學科發展的層面上建構更科學、體系化的民俗研究的理論體系。
其次,應建構全新的網絡民俗志的學科理論和方法。網絡民俗研究屬于綜合性的學術研究,除了運用一般網絡民俗事象(文本)的分析闡釋、多學科的理論方法外,還特別強調民俗學者須轉變研究思路,結合數字化時代的網絡民俗研究的特點,在方法論上有所突破和創新。
(1)用好“網絡民俗志”研究方法。民俗學家鐘敬文先生很早就提及“民俗志”的概念,認為“民俗志是關于民俗事象的記錄”。網絡民俗志則把城鄉地域空間轉移到網絡世界,擴展傳統民俗志研究的視角,試圖建立切合互聯網時代的民俗田野調查和研究方法。具體而言,網絡民俗志擁有三個基本面向:“一是作為文本類型,即基于網絡田野調查所獲取的資料對某種特定民俗文化事象的文字記錄;二是作為研究方法,即研究者在具體研究中應充分認識網絡田野的獨特價值和學術意義,轉變傳統民俗志中只是依靠田野實地調查的研究傾向;三是作為研究理念,即研究者通過關注互聯網對傳統民俗文化傳承時空及文化分層等影響的分析,重新認識網絡時代民俗事象的存在樣態,同時對新出現的網絡民俗事象進行體裁學方面的研究。”[2]這一研究思路,為網絡民俗志研究提供了理念和方法論的指導。
(2)更加重視網絡空間的“田野作業”。俄羅斯學者馬蒙諾娃·娜塔莉亞·瓦西里耶夫娜等指出:“與傳統民俗學相比,虛擬民俗學在保留傳統民俗學文本的所有基本特征的同時,也獲得了以新的數字格式傳播的前所未有的新形式:作者集體性、匿名性、變異性。在虛擬世界中,民間藝術以迷你視頻、筆記、贈品、帖子、散列標簽、生活黑客、城市傳奇、故事、笑話、捕捉短語、歌曲、軼事、諺語、格言、行話等形式存在,具有自己獨特的社會和信息環境、使命和目標受眾。”[1]顯而易見,網絡中傳播的民俗事象、文本類型已出現了重大更新,亟須建立一套適應互聯網場域的“振木鐸徇于路”的調查方法。例如,通過網絡“走訪”、訪談進行“網絡田野作業”,借助互聯網直接與民俗文化傳承者進行交流和對話,采集真正有價值的原始資料,進而探究互聯網帶來的民俗文化與社會生活轉型等問題。在此方面,如何通過海量數字文本發掘具有典型性的“網絡民俗”是其中的一個難點,同時也對學者的專業技術和治學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熟練運用“現代技術”展開研究。網絡民俗的基本特征是非線性、超文本性和多元性,即中介的網絡傳播實踐。除了傳統民俗學中所知的語言體裁外,還形成了復合化的符號文本。土耳其學者古魯姆·厄洛在《虛擬環境作為數字通信技術中介的民俗體驗領域》一文中指出:“虛擬環境是一個能夠為民俗生產提供充分條件的因素。在這種背景下,馴化的虛擬環境已經進化出一個新的民俗體驗領域,使原始甚至真實的民俗表演和制作的出現成為可能。這種情況下,直接引起民俗學研究興趣的方面是溝通和互動技術。”[2]基于網絡民俗本身具有的“新技術”特征,民俗學研究自然也應結合這一特點,做出研究的技術路線、分析方法的調整。例如學者對網絡傳說的研究,如今就有專門的城市傳說網站和數據庫,專家和非專家都可以訪問。互聯網已經成了一個大型的檔案館,一個民俗保管員,這為研究網絡傳說開辟了新的途徑。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現代技術不是民俗學的敵人,而是傳播民俗學的關鍵因素[3]。
四、結語
民俗是中華文化的瑰寶,它以最淳樸的生活形態承載著民眾的道德追求、精神信仰和審美情趣。數字化傳播時代,互聯網的“沖擊波”不僅革新了俗民社群的生活方式,更重構了俗民之間的組織關系,使民俗生產活動在保持內核和突破邊界的基礎上實現了自我更新。生活方式、俗民群體和民俗事象的更新預示著民俗研究正處于研究范式轉型的前夜。人媒融合的數字生活及網絡民俗的勃興,呼喚著當代民俗研究應關注社會正經歷的“再習俗化”過程,聚焦數字化時代民俗研究的新課題——網絡民俗。
在網絡民俗研究的概念性框架中,“鄉土”“俗民”“習俗”等傳統概念的原有意義得以更新,新的生產(傳播)主體、傳播媒介、民俗內容不斷涌現,民俗學并非像鄧迪斯擔憂的那樣“令人感到郁悶不安”[4],在現代社會中它仍充滿活力地延續著。“現代式科學”的網絡民俗研究是未來民俗研究拓展的必然方向,也同樣需要傳播學、文化學、民俗學學者不斷探索,推動民俗學研究向“現代性”“科學性”發展,形成學科壁壘破除、理論建構創新的民俗研究新局面。
〔責任編輯:清果〕
本文為蘇州大學“網絡民俗研究團隊”項目和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中國當代民謠的網絡傳播研究”(2020SJA0249)的階段性成果。
[1]Dundes Alan, "Folkloris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US, 2005, 118(470), pp.385-408.
[2]Blank Trevor J., Towar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Folklore and the Internet, Logan: U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4,p.9.
[3]Inna Golovakha- hicks, "Demonology in contemporary Ukraine: Folklore or postfolklore?",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2006, 43(3), pp.219-240.
[4]楊哲:《鐘敬文生平·思想及著作》,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頁。
[5]鐘敬文:《民俗學概論》,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頁。
[6]烏丙安:《民俗學原理》,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頁。
[7][8]高丙中:《民俗文化與民俗生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73頁,第25—26頁。
[1]孫文剛:《網絡民俗:民俗學科的新生長點》,《民間文化論壇》2013年第5期。
[2]楊秀芝:《“互聯網+”視野下的民俗文化活態化研究》,《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
[3]程名:《網絡傳播的社群化特征與網絡民俗的建立——以天涯虛擬社區為例》,《東南傳播》2012年第9期。
[4]彭小琴:《民俗藝術的新媒體傳播路徑》,《傳媒》2015年第23期。
[1]程丹陽:《網絡民間文學:民間文學的新形態》,《江西社會科學》2017年6期。
[2]Blank Trevor J., Towar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Folklore and the Internet, Logan: U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0.
[1]孫文剛:《網絡民俗:民俗學科的新生長點》,《民間文化論壇》2013年第5期。
[2]詹姆斯·W.凱瑞:《作為文化的傳播——“媒介與社會”論文集》,丁末譯,華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7頁。
[1]Dundes Alan, "Folkloris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US, 2005, 118(470), pp.385-408.
[1]Gulum Erol, "Virtual Enviroment as a Digit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Mediated Folkloric Experience Sphere", Milli Folklor, 2018,30(119), pp.127-139.
[2]李向振:《拓展互聯網時代民俗學研究視域》,《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8月31日。
[1]Mamonova Natalya Vasilyevna, Yukhmina Elena Alexandrovna, "Instagram Network Folklore in the light of the Linguosynergetics", European Proceedings of Social and Behavioural Sciences, 2018, 9(4), pp.146-152.
[2]Gulum Erol, "Virtual Enviroment as a Digit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Mediated Folkloric Experience Sphere", Milli Folklor, 2018, 30(119), pp.127-139.
[3]Voichici Oana, "Folklore and the Internet: the Life of Urban Legends in the Digital World", inSandu Antonio, Frunza Ana, Ciulei Tomita, Gorghiu Laura (eds.),Multidimensional Education &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thical Values, Pianoro(Bologna): Medimond Publishing Company, 2016, pp.551-557.
[4]Dundes Alan, "Folkloris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US, 2005, 118(470), pp.385-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