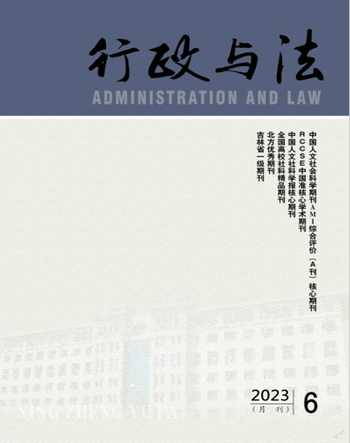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的法教義學闡釋
凌萍萍 陸杰
摘? ? ? 要:在刑法家長主義與積極刑法觀的引導之下,《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設了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這一罪名,本罪的設置表明我國刑法對未成年女性性權利的保護從僅論證“壓制反抗”的角度拓展到論證“壓制反抗”與“職責保護義務”并存的整體性保護模式。本文以本罪的復合法益保護為紐帶,將“注意規定說”與“法條競合說”作為研究本罪及其與強奸罪間關系的中心,強調刑法對未成年女性性自由權的提示性與重復性保護,以及倡導回歸性侵類犯罪同意模式的立法核心,明確本罪交叉類型法條競合的具體適用,以期指導司法實踐從而實現對未成年女性性權利的全方位保護。
關? 鍵? 詞:性自由權;注意規定;照護職責;交叉類型法條競合;行為犯
中圖分類號:D924.34? ? ? ? 文獻標識碼:A? ? ? ? 文章編號:1007-8207(2023)06-0095-13
收稿日期:2023-05-14
作者簡介:凌萍萍,南京信息工程大學法政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刑法學、犯罪學;陸杰,南京信息工程大學法政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刑法學、犯罪學。
基金項目:本文系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個人信息法律保護體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FXD004;江蘇省研究生實踐創新計劃項目“個人信息公法保護路徑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SJCX22_0378。
資料顯示,2018年到2022年間,檢察機關共起訴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9萬人,年均上升3.6%。其中,起訴強奸、猥褻兒童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13.1萬人。[1]由此可見,性侵犯罪已成為侵害未成年人最突出的犯罪類型。值得注意的是,《江蘇法院少年審判工作情況暨少年司法保護典型案例》報告的性侵被害地點統計數據顯示,發生在被害人家中的占比為24%,發生在學校及培訓機構的占比為5%,發生在醫療或體檢機構的占比為3.48%;被告人和被害人關系數據統計顯示,師生關系、親屬關系、臨時監護關系等較為親密的熟人關系占比14.5%。[2]在熟人尤其是對未成年人負有照護職責的人員性侵高發的背景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簡稱《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二十七條規定了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將未成年女性的性權利保護力度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問題的提出:刑法教義學視角的確立
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的設立標志著我國對未成年女性性自由權的保護進一步強化,相較于傳統的性犯罪而言,本罪名呈現出兩個不同角度的變化:一是責任判斷對象的變化。在傳統的性犯罪中,針對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女性強調的是違背被害人的意愿,而不考慮行為主體責任中存在的意志缺陷;而在本罪名中則強調行為主體在特定領域內責任標準的提高,責任是構成要件該當的和違法行為中所表現出的法益意識的可非難的缺陷。該缺陷既可能是很重要的,也可能是很輕微的,此處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意志形成時動機價值的高低;成為責任判斷對象的是違法行為以及行為中被現實化的被法律所否認的心理。[3]本罪為行為主體設置了特定的義務前提,主體義務的確定為其刑事責任的嚴格化提供了必要的依據。二是被害人同意范圍的變化。我國性犯罪“被害人同意”的界限一直沿用“幼女”這一特定群體的認定標準。將性行為的認知同意權限定在14周歲,換言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將我國性犯罪中性自由決定權的自主同意條件設置為14周歲以上。在傳統性犯罪的認定中,已滿14周歲且在知情同意下的性行為被推定為合法。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認定的重點內容是對被害人在特定情形下的認知同意權限的修正。
基于刑法規范用語的有限性與抽象性的特征,有必要對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進行契合刑法教義學的深層次分析,以增強本罪于司法的可操作性。首先,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是否具有立法上的正當性基礎決定本罪是否應單獨設置,因而有必要對其正當性基礎進行契合政策精神和立法背景的解讀。其次,因為保護法益的界定直接決定著對犯罪構成要件的實質解釋,故對本罪的刑法教義學分析亦需要明確其保護法益。再次,對于本罪入罪模式的理解的主要爭議集中在立法推定說、法律擬制說和注意規定說之間,該爭議牽涉到本罪與強奸罪間關系的認定,因而直接影響到案件的罪名認定等司法適用問題,故有必要對其加以厘清并提供相應的論證支持。最后,明確提出本罪與強奸罪交叉類型法條競合的具體適用規則,回歸教義學服務于司法實踐的宗旨。
二、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的立法正當性證成
(一)積極刑法觀的引導
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通過之前,學界就存在是否有必要單獨設立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的爭論。當前,我國刑事法網劃定的總體趨勢是適度的犯罪化,適度的犯罪化是一種理性的犯罪化,而非情緒的犯罪化。因此,在確立刑法的調控范圍時,要適應社會的情勢,根據規制犯罪的需要來決定是否予以犯罪化。[4]刑法作為其他一切法律的保障法,要做到在法網規制上實現從“不嚴”到“嚴”的轉變,嚴密整體法網,完成維護秩序、保護法益的任務。《刑法修正案(十一)》在積極主義刑法觀的影響下,其犯罪化程度可謂歷來十一部《刑法修正案》之最。由于近年來監護人、看護人等具有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其照護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頻發,引起社會各界對此廣泛關注,但當前我國刑事法網中除猥褻兒童罪以外基本不存在獨立于普通性犯罪的條文,導致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在范圍以及結構上對普通性犯罪尤其是強奸罪條款的依賴過于嚴重。而適度的犯罪化首先須考量的是在已有常見犯罪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分解、細化,[5]在強奸罪中添加新的構成要件要素進而析出本罪,有利于改善原本單一的性犯罪結構。自此,從二罪法定刑設置的整體來看,立法者設置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旨在規范具有特殊身份的主體對其保護對象之間發生的“自愿”性行為,形成了我國性犯罪設置的階梯式立法模式,將被害人主觀意愿作為犯罪構造的規范性要求,對性犯罪的“自愿性被害”與“被迫性被害”進行了明確的劃分,在刑罰領域中實現了兩種不同意愿之下行為的不同要求。綜上,積極刑法觀助力于性犯罪預防體系完善的進路為:在既有強奸罪條款的基礎上,通過增添構成要件要素、擴充行為方式、將個人法益擴展到個人法益與超個人法益并存的復合法益構造實現了刑事規制范圍的進一步擴張。
(二)刑法家長主義對自由決定權的限制
刑法家長主義主張國家在某些領域為了公民自身的利益可以不顧其意志而限制其自由或自治。[6]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之所以單獨設置,總體上可以理解為刑法家長主義在立法中對未成年女性性自由權進行限制的體現。根據限制程度的不同,家長主義有兩種劃分。硬家長主義認為為保護某人免受自愿選擇的損害,刑事立法即使違背某人意愿也是必要的。如強奸罪就存在通過否定被害人性同意能力的角度來為未成年女性提供相應保護的條款即奸淫幼女條款,該條款否認14周歲以下的女性具有性自由決定權。與此相對應,軟家長主義認為完整地處分其性權益的自由決定權應當只授予那些“擁有成熟的判斷能力”的理性人。所以即便是家長主義最堅決的反對者也意識到軟家長主義可以合法地保護人們免受他們自己行為的傷害。不難發現,兩種家長主義的共性在于對被害人自由處分自身權利的決定權即自由決定權進行限制。世界上沒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在意思自治原則被奉為圭臬的私法領域中,尚且存在公序良俗等原則對私法主體的約束,作為強調個人服從國家強制力的公法,刑法對其調整主體的權利處分行為進行適當干涉的正當性更毋庸多言。
一般而言,在刑法上,被害人行使自由決定權的對象范圍僅限于個人法益,但個人法益又存在人身法益、財產法益的劃分。就個人財產法益而言,被害人對其享有自由決定權,刑法一概不加以干涉。就人身法益而言,部分身體健康權、自由以及性自由權利等人身權利、民主權利都是權利人可以承諾的利益,對于這部分利益的單純放棄,可以直接導致刑法保護的缺失。[7]也就是說,被害人對該部分法益的承諾放棄需受到一定的限制。對性自由權利自由決定的限制主要體現在對承諾程度的限制以及善良風俗的限制。對承諾能力的考察需要考慮兩個因素:一是辨識能力,二是意思能力。所謂辨識能力是指被害人對于承諾所涉及利益的種類、性質、效用的認識能力,這種認識需要達到的程度根據不同類型的利益種類有所不同。所謂意思能力是指被害人能夠將自己處置合理利益的意志有效表示的能力。如當涉及到未成年人缺乏關鍵的判斷和理解后果的能力,甚至包括有能力的成年人,由于他們缺乏信息來源以至于不知道他們具體在做什么。[8]《刑法》中奸淫幼女,猥褻兒童罪中幼女和兒童的年齡規定均為14周歲,14周歲之下的幼女和兒童對于性交和猥褻行為無承諾能力。實際上,刑法已經間接將處分性利益的被害人年齡限定在14周歲。但是對于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女性,一般來說,其辨識能力已經初步具備,性自由權必須受到一定程度限制的依據在于其在被看護的特殊場合下,負有照護職責人員較易利用被害人對其人身依附、依靠、信任等關系而形成的權威地位與信息優勢侵蝕被害人的意思能力,從而使被害人作出有瑕疵的、非實質的意思表示而同意發生性關系,進而遭受性侵犯。鑒于此,刑法通過扮演“家長”的角色以否定被害人存在瑕疵的表面意思以維護未成年女性的合法性權益。概言之,被照護人的年齡因素與被照護的特殊身份因素決定了本罪是軟家長主義介入刑法的體現。
此外,在具體的自由決定過程中,以下原因會產生影響:一是利益的性質。根據利益性質的不同,完整的自由決定權所需達到的精準度也存在差異,涉及人身方面的利益對于其承諾方式的要求必須要嚴格。自然人擁有的利益本身并不是一個單純的平面結構,而是存在著位階差異,就被害人而言,其利益的屬性也存在本質區別。被害人承諾能力由于利益階層和種類的不同,呈現出不同層次的要求。性權利是一項典型的人身利益,具有人格權與身體權雙重屬性,該復雜屬性決定其權利的行使相較于財產權以及某些相對不重要的身體權利而言,其外圍領域范圍內的行使必須受到嚴格的法律控制。有學者提出“性行為領域理論”將性行為劃分為不同的領域進行討論。在個人核心領域,婚內性行為、同性戀的性行為需要充分地尊重個人的性自由權,法律不加以干涉;對于個人外圍的性行為,如聚眾淫亂,不管是否存在同意,均構成犯罪。此次《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了另外一種領域即新型性行為領域的刑法規制。[9]因此,本罪與聚眾淫亂罪一樣,都是刑法對個人在其外圍領域范圍行使性自由權的限制。二是權利人與行為人之間的關系。承諾人與行為人之間的關系往往對被害人行使自由決定權的效力產生極大的影響,任何人與周圍的群體之間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關系,各類不同的關系以及不同的親密程度直接導致行為方式的不同。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而“照護職責”這一紐帶顯然將特殊職責人員與被照護的未成年女性捆綁得愈加緊密。無論照護人員基于法律義務還是道德義務,從一般人角度而言,照護人與被照護人之間都處于較為親密的關系,被照護人無論是行使何種利益之自由決定權,都會或多或少地受到照護人的影響或是干涉。三是特定情境因素。這里的特定情境是指在某種對處分利益的權利有著直接或者緊急影響的狀態。當被害人的利益陷入價值的矛盾沖突狀態時,被害人的精神狀態將隨之受到較為嚴重的影響。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較易利用自身經濟、身份上的優勢地位于某些特定情境下,對被害人或施以恫嚇或加以利誘,從而可能導致被害人基于對自身妥協所能獲得之利益或保全之利益的考量,而情愿作出犧牲其性利益的舉措。因此,刑法不存在一個與道德完全無涉的刑法家長主義的概念,刑法與道德的關系可從刑法通過保護底線規范來維系社會的角度加以理解。刑法通過捍衛包括一些基礎性的道德倫理在內的底線規范,發揮維系社會共同體的功能。[10]性權利是一項典型的人身利益,人格權與身體權的雙重屬性決定其與社會倫理密不可分。因此,對于性自由決定權的限度判斷需要考慮該權利處分帶來的后果即對于權利人自身以及社會帶來的危害或者潛在危害。這里的潛在危害是指由于被害人的承諾而導致利害關系人或者是社會的不利益狀態。本罪應以善良風俗為界限對權利人行使自由決定權進行限制,實質上就是強調在性權利行使的問題上,被害人不得觸犯到一般大眾的道德倫理觀念。在性權利承諾的場合下,既需要考察被害人所承諾利益本身的合理性,還需要考察行為人的行為是否符合一般的社會相當性,也就是符合善良風俗的一般理念。概言之,本罪是在個人性自由權與家長主義交織融合下,基于完善性犯罪規制體系的考量而產生。基于此理解,下文將對本罪背后深層次的法益構造與具體教義學問題展開分析。
三、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的法益構造
無論根據結果無價值的法益侵害說還是二元行為無價值的規范違反說,犯罪均被認為是侵害法益之行為。[11]據上文所述與學界通說,性自由權是性犯罪的共同法益。根據本罪立法精神以及政策引導下的規范保護目的之考量,本罪應為刑法對于負有照護職責的人員違反照護義務背后的倫理關系的一種規制,故將本罪的保護法益理解為復合法益更為妥當,其主要法益是未成年女性的性自由權,次要法益是照護職責所形成的倫理關系。
本罪的性自由權類型需要進一步討論。筆者認為性自由權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一是絕對意義上的性自由權,保護所有婦女對自身性權利的自由決定權,強調的是主觀意愿的自由,而并不考慮導致其自愿的動機。二是推定的性自由權,這是需要結合婦女的特定狀態而設置的權利。刑法理論認為,只有婦女具有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時,才具備對自身刑法權利的同意能力,權利人同意理論要求法益所有者只有在真實自愿的情形下實現權利的放棄才能實現刑法的出罪功能;換言之,只有當婦女在刑法中對自身性自由權的表示被確認為有效時,刑法才能認可此種性行為的非罪化。當婦女的年齡、精神狀態或者其他被刑法明確為不能完整、真實表達自身意愿時,即使其作出放棄性自由權的表示,也會被認為是無效的,如我國刑法設置的幼女、精神病婦女與他人自愿發生性行為的情形等。三是未成年女性在特定狀態下的待定性自由權。此種性自由權的保護取決于刑法對該部分權利的保護態度以及司法實踐的現實需求。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女性相對幼女這一群體而言已經具備一定的自由決定權,但對于涉及身體重大利益的權利的有效承諾權仍需進一步斟酌。這個階段的未成年女性在一般的狀態下可以較為明確地判斷其權利的性質以及權利的行使可能帶來的后果,但是當其處于特定的狀態下時,其權利的行使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擾。如當監護主體、看護主體、教育主體等特定人群對其進行性誘騙、性引誘等行為時,這部分特定群體所具有的職責義務往往會使得未成年少女對其行為的認知產生一定程度的偏差,同時,也正是基于此種照護職責,行為人與未成年少女之間的密切程度也使得其更容易實施危害行為。因此,基于照護職責產生的特殊領域內的未成年少女的性自由權應當在刑法中進行例外性考慮。
不可忽略的是,照護職責所產生的倫理關系也是本罪保護法益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有學者基于結果無價值的立場質疑本罪將某種倫理禁忌納入刑法的規制會混淆法律與道德的界限,從而導致立法科學性存在疑問。[12]張明楷教授認為,不可否認的是“舊行為無價值論”將行為規范等同于社會倫理道德規范,但是其行為違反倫理的觀點已被淘汰,當前最有影響力的二元行為無價值論所指的規范是與倫理道德無關的、保護法益所需遵守的行為規范。[13]誠然,一元行為無價值所指的規范違反指的是倫理道德規范的違反,是受到以自然犯為其規制主流的古典刑法的影響,因此,舊規范違反說的法益觀其實是將法益等同于倫理道德,從而難免遭受混淆了道德失范與刑事違法之間界域的批判。隨著自然犯時代的落幕以及法定犯時代的降臨,目前的二元行為無價值已經意識到模糊不清地援用倫理道德標準不足以限定刑法可罰之不法的界域。隨著刑法現代化轉型的進程,法益仍無法做到與倫理道德徹底劃清界限。由于法益概念的抽象性與模糊性,刑罰保護范圍得到了無限度的擴張。[14]此后的結果無價值者注意到了這一弊端,所以將倫理道德斥之于刑法體系之外,但卻實際上導致了法益體系失去了法治國基礎的利益根基。因此,包括社會倫理與道德在內的感情法益雖是一種相對精神化但卻是超個人法益范疇內不可或缺的類型。不能否認的是,法益概念的過度精神化的確是當代刑法值得警惕的一個問題。法益概念緣何成為時代的寵兒最為重要的原因是實現了刑法排斥倫理道德的功能。所以當時的結果無價值論者認為法益概念的首要功能就在于禁止國家單純為保護某種倫理道德而動用刑罰,因而對性犯罪體系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廢除了單純違背性風俗的罪名,從而將可罰的性犯罪限定在了對性的自由決定權和青少年身心健康加以保護的范圍之內。[15]“立法的方式無外乎確認與制定,確認是對既有道德倫理的認同和法律保護。”[16]眾所周知,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而刑法則是法律的底線,是一切法律的保障法。根據這種當然推理,感情法益無疑是刑法的保護客體,只不過并非所有的倫理道德感情均需由刑法加以保護。新自然法學派代表人物富勒提出在道德價值的等級體系中,存有兩個層級:第一層為“義務道德”,它設立了一些基本規范,沒有這種規范,人們就不可能組成一個有秩序的社會;第二層為“愿望道德”,它是善的生活的道德、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實現人之力量的道德,是以人類所能達致的最高境界作為出發點。[17]包括刑法在內的法律作為社會的規范,它不是以圣人、英雄為標準的,而是以一般人、普通人為標準的。[18]“義務道德”與“愿望道德”間的界限必須涇渭分明以區分罪與非罪。另外,發生在負有照護職責人員與其照護的未成年女性間的性行為,由于負有照護職責人員嚴重違反其職責所要求的義務道德而弱化了該行為的社會相當性,因此刑法為保護此種義務背后的倫理道德關系進而介入具有相當程度的必要性與正當性。所謂的社會相當性理論最早由德國刑法學家韋爾策爾提出,即以符合義務的注意而為之行為,且該行為屬于歷史形成的社會共同生活秩序范圍內的行為。[19]在借鑒、整合結果無價值論的法益侵害說的基礎上,日本學者大谷實進一步提出違反刑法規范所代表的社會倫理的、應當受到刑罰懲罰的侵害法益的行為是犯罪。[20]應當將對社會基本倫理秩序的違反視作不法判斷的重要因素,將刑法對法益的保護限定在社會相當性的范圍內,只要行為人的行為脫離社會相當性的,就應認定其具有法益侵害性從而具有實質的違法性。因此,違反“義務道德”的行為已經挑戰了刑法的倫理道德底線,由于嚴重脫離社會相當性可以認為其在社會危害性上達到了嚴重性的程度,應當由刑法加以規制。
另外,法益是一個規范性概念,其界定仍需回歸到教義學領域中加以考量。對刑法教義學而言,適格的感情法益可以補強個人法益釋法作用的不足,充分地解釋罪名的構成要件。若將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的保護法益僅界定為單一的性自由權則會削弱了法益的解釋功能,無法為本罪的教義學研究提供有力的闡述。并且如果根據性侵犯罪的保護法益是性自由權和身心健康的二元法益通說,其中的身心健康法益過于籠統與模糊,亦無法為本罪的教義學分析提供有力的闡述,甚至可能誤導司法實踐的展開。本罪相較之于強奸罪,其犯罪主體為特殊主體只能是負有照護職責的人員,負有照顧職責的行為人與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女性發生了性行為,一般就推定行為人利用了其職責關系而入罪,并且在此基礎上不允許被告人提出反證而證明其并沒有利用職責關系而出罪。通過對本罪進行教義學考察,可發現特殊職責形成的倫理道德之法益對于本罪的行為方式、犯罪主體的確定是不可或缺的。此外,通過規范保護目的亦能得出同樣的結論。“法益既是一個事實概念,又是一個規范概念。”[21]因為法益是經由立法從客觀的生活利益轉化而來的產物,它是一個實在的客觀產物;另外,法益又是規范保護目的的一種表征,其實際內涵又取決于對罪名規范保護目的的解讀。本罪的規范保護目的不同于強奸罪之處在于,它禁止的是特定關系人之間的性行為,意在通過維護一種古老的倫理禁忌不被打破來保障未成年女性的身心健康。因此,本罪的法益應包含倫理道德這一超個人法益以明示其與強奸罪的構造差異。
但有學者認為從本罪于刑法分則的體系定位看來,將本罪的保護法益理解為負有照護職責人員職責義務背后的“性倫理道德”這樣的社會法益的舉措將面臨與體系解釋的應然結論相抵牾的批判,進而提出應將本罪的保護法益僅界定為我國性犯罪的共同法益即單一的性自由權。[22]此種批判恐怕難以成立。誠然,本罪的確規定在刑法分則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一章中,但這只能說明此章罪名的保護法益為包含性自由在內的公民人身權利或者民主權利,但這并不意味著此章內所有罪名的保護法益只能是單一法益,其亦可能是復合法益。如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的保護法益既包括公民的身體健康及生理機能完整的權利也包括國家的醫療管理秩序;再如刑訊逼供罪的保護法益既包括公民的身體健康也包括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秩序。因此,本罪保護法益為復合法益的特殊屬性與其在刑法分則的體系地位無涉。主要法益揭示了某個犯罪所侵害的而為刑法所保護的諸多復合法益中的主導方面,故而決定了該具體犯罪的性質。[23]因此,罪名的主要法益是刑法分則的劃分依據,本罪位于“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一章的體系地位只能說明本罪的主要法益為性自由權,并不能作為排除其他法益存在的根據。
四、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的入罪模式判斷
刑法的壓制功能與預防功能的并存并非是簡單、機械的組合,不同的法益保護領域與特定規范對象體現了刑法功能的不同側重,但是無論是何種功能的體現,都應當符合刑法的合理性入罪。如何順利實現照護職責主體與未成年少女之間特定行為的定性需要從理論上落實其行為入罪與定罪合理性的必要性論證。就目前的理論研究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種學說:立法推定說、法律擬制說以及注意規定說。
(一)立法推定說之辨析
有學者認為,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屬于立法上的事實推定。[24]立法推定指立法者采取演繹推理的方式證明假定的事實并明文規定,當無證據將其推翻時,即認定其為真實的。法律推定的結論直接來源于法律規定而非證據,故推定的事實屬于免證事實。本罪中推定的構成要件要素為“利用職責關系”。因此只要負有照顧職責的行為人與14-16周歲的未成年女性發生了性行為,一般情況下就推定行為人利用了其職責關系(不需要司法機關積極證明)而入罪,但是在此基礎上允許提出反證,證明行為人并沒有利用職責關系進而出罪。值得肯定的是,立法推定說的適用為行為人提供了自證的空間,亦即通過立法推定的方式授予作為被告的行為人以反駁權。不可否認,此種舉證責任的倒置能夠有效地節約司法資源。但立法推定作為“舶來品”來源于英美法系,更具體地說,是在證據法的框架內被廣泛地應用。[25]因此立法推定說的適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司法實務的需求,但由于該說與憲法的比例原則以及刑事程序法上的無罪推定原則存在著一定的沖突,學界對其適用予以限制已達成共識。除此之外,本學說所忽略的另一個問題則是該行為入罪的刑法目的,相較于沒有特定責任的社會一般人而言,行為的可罰性在于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存在的特定關系以及行為人所具備的特定責任。當行為人與被害人建立特定的責任關系時,已經明確的是:特定責任人與相對人之間的保護義務已經形成,此種保護義務應當包含基礎性保護義務(針對相對人的未成年屬性做出的一般意義上的保護)以及特殊保護義務,特殊保護義務是基于此種具有便利性的照護職責可能對未成年人帶來的潛在風險(這里稱之為潛在風險主要是指即使在未成年人作出權利放棄的承諾時,其權利依然存在被侵害的風險),而未成年人對于此種潛在風險的判斷能力尚沒有完全形成。因此,只要存在潛在風險,無論未成年人是否有權利放棄的意思表示,具有照護職責的行為人都不應當實施任何可能侵犯這些權利的行為。綜上,本罪不宜適用立法推定說。
此外,根據本罪行為犯的犯罪類型亦能有效證否該說。有學者認為在行為人與未成年女性確實情投意合產生戀愛關系進而發生性關系的場合下,只要不將本罪的法益理解為諸如設立照護職責人員的交往紅線這樣的社會利益,就應該認為本罪保護法益并未受到侵犯,可以認為是有效反證了抽象危險的不存在從而在構成要件層面出罪,也可以是在違法性層面以沒有實質的法益侵害為由出罪。[26]根據法條表述,行為人利用照護職責與未成年女性發生性關系只是本罪的行為方式之一。只要行為人負有監護、收養、看護等特殊職責,且與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女性發生了性關系,本罪就已成立。換言之,本罪應屬于行為犯,不屬于抽象危險犯。在德國,抽象危險犯都是行為犯,均是違反行為規范的結果。[27]結果無價值論者認為抽象危險犯同具體危險犯一樣具有實存危險,只是這種危險較為緩和。由于這種緩和的抽象危險并無法律上的直接規定,只能憑個人主觀評斷。抽象危險犯的處罰根據在于其產生的抽象危險,這種抽象危險不同于具體的危險,具體危險犯的成立需要有客觀的案件事實積極證明即由控方舉證證明,而抽象危險犯中抽象危險是否存在不是不需要證據證明,而是控方將證明責任轉嫁給被告,即前文所論及的允許反證的立法推定的入罪模式,因此,抽象危險犯與具體危險犯的差異只在于證明該危險是否存在的責任人不同而已。而行為犯與抽象危險犯最易混淆之處在于行為犯與抽象危險犯均可能由于行為人的行為該當犯罪的構成要件而成立。但是抽象危險犯可以通過允許被告人反證自己行為的無危險性從而在構成要件該當性層面出罪,而行為犯由于行為本身該當犯罪構成要件就存在對法益的實際危險而不允許反證。所以在刑事司法中,是否允許反證成立成為二者分野的界碑。[28]究其根本,認為本罪的入罪模式應當屬于允許反證的立法推定實際上是建立在本罪抽象危險犯之犯罪類型的基礎之上的,即認為行為人與被害人發生性關系,立法者就推定其利用了照護職責所形成的身份優勢,從而便具有侵犯被害人性自由權的抽象危險。但是,本罪實行行為的可罰性在于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存在的特定關系以及行為人所具備的特定責任。當行為人與被害人建立特定的責任關系時,特定責任人對相對人的保護義務就已經形成,當他們間發生性關系時就已經對被害人的性自由權以及社會倫理關系產生了實害,而并非僅僅是一種蓋然性的抽象危險。因此,本罪屬于行為犯,并不存在被告人可以提出反證進而出罪的問題。對本罪的犯罪類型的理解應同強奸罪保持一致,不應理解為抽象危險犯,故本罪的入罪模式不適用立法推定說。在司法實踐中,一旦行為主體實施了法條所規定的危害行為即與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少女發生性關系,即使被害人是出于自愿的,也不能在違法性階層出罪。
(二)法律擬制說之檢討
有學者認為應當采用法律擬制的概念。[29]此說有待商榷。首先,學界對于法律擬制的正當性仍存有較大疑問。批判者認為法律擬制存在缺乏擬制的正當理由、損害刑法的嚴謹性與權威性、違背罪刑法定原則、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犯罪構成理論等諸多缺陷。因此,即便法律擬制廣泛存在于我國刑法分則之中,具備實定法基礎,但鑒于其上述的諸多弊病,對罪名擬制之情形的認定需要格外慎重。教義學對罪名的刑法擬制的考察應當從罪名條款的明文規定以及司法實踐中的實際操作狀況的雙重視角加以剖析。除刑法明文規定的比較明顯的法律擬制以及實質上并不違背罪刑法定原則的法律擬制以外,不宜擴大法律擬制的認定范圍,并且需要在不明顯違背罪刑法定原則的前提下,盡可能地將有關罪名解釋為注意規定。[30]
其次,若適用該說,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便應當理解為強奸罪的特殊規定,如此則會完全割裂本罪與強奸罪的關系。根據此說的立場,假如負有照護職責人員利用未成年人對其信賴關系或者自身優勢地位與其照護的已滿16周歲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發生性關系,則會容易導致裁判人員認為該行為是基于未成年人的性同意,屬于自愿發生性關系從而否定強奸罪的成立。由于傳統觀點認為強奸罪的實行行為必須具備能使被害人不敢反抗、不知反抗或者不能抗拒的強制性質。但筆者認為對強奸罪立法核心的理解應當由“強制模式”向“同意模式”進行轉變。對強奸罪條款的理解應著眼于“性同意”而非“暴力”。將“婦女的不同意”作為強奸罪入罪標準顯然更具科學性。超越強奸必須為“強制性”的這一狹隘概念,開拓一個新的視野:把注意力集中在性的自由是人格自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將強奸定義為侵害性自由權的行為。[31]我國學界中越來越多的學者亦主張順應強奸罪的發展趨勢,改革現行立法模式,接納以“不同意”為基礎的立法模式,將“未經被害人同意”作為強奸罪的入罪本質。[32]因此,只要行為人在未取得被害婦女同意的情況下與其發生性關系,就應當以強奸罪論處。根據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條款,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之間的未成年女性在被監護、收養、看護等場合中,其照護人所占據的權威地位與擁有的信息優勢極大地削弱了被害人的性同意能力,由于“權力關系下無自愿”以及類型性思維下通過對強奸罪本質特征的詮釋,被害人的性同意被類型性地認定為無效,在犯罪構成要件上無需被害人同意,即被害人無判斷能力,故不允許反證,即使有被害人承諾也無效,這也是本罪最為關鍵的立法技術。基于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該立法技術被廣泛應用于侵犯未成年合法權益的犯罪。典型的如奸淫幼女犯罪,即使得到被害人同意,也不影響罪名成立;再者,拐賣兒童的行為,即使得到兒童的同意,仍然構成拐賣兒童罪。
(三)注意規定說之宣示
注意規定是指在《刑法》已經對某一問題作出基本規定的前提下,為避免司法工作人員忽略或產生誤解,而將其單獨列出以提醒司法工作人員注意的規定。[33]提示客觀構成要件的注意規定并未更改刑法對行為要素的一般要求。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第二款規定:利用職權、從屬關系,以脅迫手段奸淫現役軍人妻子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的規定即按照強奸罪定罪處理。該條款的行為仍為未經被害婦女同意而強行與其發生性關系的強奸行為,即使立法者不作此重復性提示,也應以強奸罪定罪處罰。有學者認為利用職責關系屬于一種隱性強制手段,使得該行為與普通強奸罪具有相似的行為構造,為本行為的入罪提供了行為構成要件該當性上的依據,是本罪入刑的核心理由。[34]但強奸罪的立法核心應為性同意,其法理本質為未經被害人同意的“性權利的侵犯”,只要能評價為一方對另一方的性侵犯,即可認定為強奸的實行行為。因此,筆者主張應從強奸行為的本質特征出發,結合強奸罪的立法精神,運用刑法解釋學來辨析本罪與強奸罪之間的法律屬性的不同。對強奸罪條款中“其他手段”這一兜底條款的解釋范圍不應當過于狹窄,應當在立足于強奸罪保護婦女性同意權的立法宗旨的基礎之上,擴大其涵射范圍。負有照護職責人員利用未成年人對其信賴關系或者自身優勢地位的行為完全可以認定為“其他手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發布的《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第二十一條規定:“對已滿14周歲的未成年女性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利用其優勢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無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而與其發生性關系的,以強奸罪定罪處罰。”該司法解釋亦可佐證本說的立場,其中“迫使”根據文義進行解釋,其不法程度顯然低于“暴力”與“脅迫”,可歸于“其他手段”的涵射范圍之內。而這里的“迫使”所包含的內容也可以進行擴張性的實質解釋,行為人基于優勢地位給被害人可能造成的威脅并非現實的人身威脅,而是間接的后續性風險的存在或者是正常生活秩序的破壞,只要違背照護職責人所應當具有的基礎性義務的行為或者是基于未成年人的思維而可能出現的非常規性生活改變時,都可以理解為“迫使”。另外,該司法解釋第二十七條規定: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偶爾與幼女發生性關系,情節輕微、未造成嚴重后果的,不認為是犯罪。該條款一直被認定為強奸罪的典型出罪性事由,而究其根本,出罪的法理依據在于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的特定平等性關系。當行為人與被害人處于合理的平等地位時,被害人不具有明顯的弱勢,其對自身性權利刑法保護的“放棄”并非基于特定的約束和壓迫,刑法對該種行為規范的重心也并不在行為的“被迫性”上,而是基于對幼女特殊的嚴格保護上,因此,當行為本身未對幼女造成實質性傷害時,刑法為其保留了一定的出罪可能性。
據此,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的設置在行為方式上同強奸罪有重合之處,換言之,二者構成要件存在著交叉與重合,本罪與強奸罪是一種交叉類型的法條競合關系。因此,本罪可以局部地被認定為是針對《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一款的注意規定,它是對強奸罪條款的重申,即使不設置該注意規定,根據強奸罪條款,利用未成年人對其信賴關系或者自身優勢地位與其發生性關系的負有照護職責人員也應當以強奸罪定罪處罰。本罪注意規定說的適用能夠最大程度還原強奸罪“同意模式”的立法核心,該入罪模式既認可了未成年人享有一定的性自由權,又能最大限度地保護其性權益免受侵害。因此,刑法設置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的目的在于提示司法工作人員此次新增的犯罪類型在很大程度上本就是強奸罪本條的應有之義。我國今后立法的發展方向之一是類型性。[35]顯然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的部分犯罪類型無論是從其保護法益還是構成要件出發,都可以進行類型化處理,進而歸于強奸罪條款來規范,但在刑法家長主義與積極刑法觀的介入與引導之下,確有必要將未成年少女性權利的保護從僅論證“壓制反抗”的角度拓展到論證“壓制反抗”與“職責保護義務”并存的整體性保護模式進而獨立成罪。
【參考文獻】
[1]五年來檢察機關起訴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9萬人[EB/OL].最高人民檢察院網,https://www.spp.gov.cn/spp/zdgz/202303/t20230301_604971.shtml.
[2]江蘇法院少年審判工作情況暨少年司法保護典型案例發布[EB/OL].新華報業網,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0615380762724972&wfr=spider&for=pc.
[3][19][27](德)漢斯·海因里希·耶賽克.德國刑法教科書[M]徐久生,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572,345,359.
[4]付立慶.論積極主義刑法觀[J].政法論壇,2019(1):100-111.
[5]周光權.刑法總論[M].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21:18.
[6](日)曾根威彥.刑法學基礎[M].黎宏,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4.
[7]凌萍萍.被害人承諾研究[D].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43.
[8]Fateh-Moghadam B,Gutmann T.Governing[through]Autonomy.The Moral and Legal Limits of“Soft Paternalism”[J].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2014,17(3).
[9][29]項佳航,楊安寶.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理解與適用[EB/OL].悄悄法律人,https://mp.weixin.qq.com/s/_WxNAmMLzTNn7jUltavbwA.
[10]車浩.自我決定權與刑法家長主義[J].中國法學,2012(1):89-105.
[11]陸杰.電信網絡詐騙與其關聯犯罪的罪數分析[J].上海公安學院學報,2022(6):43-53.
[12][22][26]付立慶.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的保護法益與犯罪類型[J].清華法學,2021(4):72-86.
[13]張明楷.行為功利主義違法觀[J].中國法學,2011(5):113-127.
[14]樸普錫「フランツ·フォン·リストにおける法益概念の刑事政策的含意」,立命館法學1號(2018年)58龘參照.
[15]陳璇.法益概念與刑事立法正當性檢驗[J].比較法研究,2020(3):64-65.
[16]田宏杰.立法擴張與司法限縮:刑法謙抑性的展開[J].中國法學,2020(1):166-183.
[17](美)朗·富勒.法律的道德性[M].鄭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7.
[18]張明楷.刑法格言的展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397.
[20]馬克昌.比較刑法原理[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92.
[21]田宏杰.行政犯治理與現代刑法的政治使命[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2(1):111-119.
[23]張小虎.刑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104-105.
[24][34]周詳,孟竹.隱性強制與倫理禁忌:“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的理據[J].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97-108.
[25]Ullman-Margalit E.On Presumption[J].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1983,80(3).
[28]江嵐,趙燦.抽象危險犯與行為犯之界限——以“抽象危險”的認定為路徑[J].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2):120-123.
[30]周銘川.論刑法擬制的本質、正當性及應有類型[J].交大法學,2021(1):160-163.
[31]Schulhofer S J.Taking Sexual Autonomy Seriously:Rape Law and beyond[J].Law and Philosophy,1992,11.
[32]何洋.強奸罪解構與應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206.
[33]張明楷.刑法學(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587.
[35]張明楷.刑事立法的發展方向[J].中國法學,2006(4):18-37.
(責任編輯:劉? 涵)
Abstract:Under the guidance of paternalism of criminal law and the positive view of criminal law,the crime of sexual assault committed by the personnel responsible for care has been added to amendment(XI).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crime indicates that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young women in Chinese criminal law has been expand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rely demonstrating“repression and resistance”to a holistic protection mode of demonstrating the coexistence of“repression and resistance”and“duty protection obligation”.This article takes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mpound legal interests as a link.The“provision for attention theory”and“legal concurrence theory”are regarded as the center of studying this crim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rape.It emphasizes the prompting and repetitive protection of the criminal law to the juvenile women's right ofsexual freedom,and advocates for returning to the core of legislation of sexual criminal consent mode.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cross type of overlap of articles of law should be clarified,so as to guide judicial practice and achieve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of women's sexual right.
Key words:sexual freedom;note provisions;care obligations;cross type of overlap of articles of law;behavioral off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