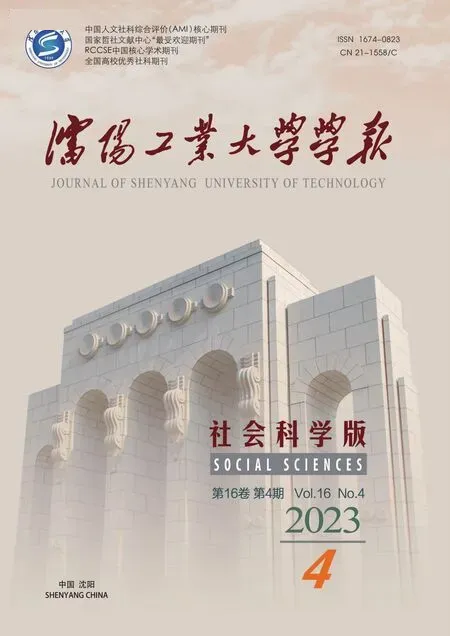母題、情感與命運: 全人類共同價值視域下中國民族題材電影研究
趙麗芳, 張寶譽
(中央民族大學 a. 新聞與傳播學院; b. 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院, 北京 100081)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呼吁:“世界各國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1]此12字價值觀念體現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厚度,站在人類歷史進程的戰略高度,凝聚人類不同文明的價值共識[2]。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為世界和人類向何處去的問題呈上中國答卷[3]。同時,全人類共同價值具備“隱匿性”和“顯性化”特征。隱匿性意指其并不是某種先驗存在,而是扎根于全人類實踐活動、潛藏于全人類日常生活中[4];顯性化則在于其被準確闡釋和傳播之需[5]。


一、全人類共同母題:災難、家園與尋找
胡適在研究歌謠時首譯母題(motif),認為這些用方言誦唱的口頭文化是大同小異的,大同即為母題,小異是在不同地方流傳過程中附加上的“本地風光”。盡管各時各地的故事主題有所不同,但講述故事的口頭藝術(母題)并不受不同文明的限制和束縛,它在任一世紀和地方都觀照基本的個人和社會需要[9]。立足于五四運動引發思想變革的社會背景,中國學者將“母題”概念引入,意圖從民族文化敘事中探求母題的特性與共性,并闡釋其如何表征人類的所思所愿[10]。而電影同樣處于文化無意識的層面,捕捉著難以注意卻一再顯示的現象[11]。電影的敘事母題也是不可再分的最基本內容單元,表征個人、國家和世界的基本價值觀念。因此,對全球化和現代化背景下全球電影相似母題的研究,能夠揭示特定時期社會大眾心態的銀幕投射,反映這一階段全人類的共有需求。
1. 自然生態“災難”母題
“哪里有焦慮,哪里就有電影的母題。”[12]敘事原型在時空維度上的變化具有動態特征,但敘事母題作為其深度模式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表征具有普遍意義的人性困境和歷史經驗。人類社會難免面臨天災和人禍,而“災難”母題則記錄其對人造成的傷痛記憶,承載人對這些現象的文化解釋。在全球化和現代化背景之下,“災難”母題聚焦于資本邏輯文明形態下的現代性之困——其進步發展是以自然生態為代價的,凸顯的是物質力量與人類的世界歷史,將民族國家確立為現代化主體力量,卻因“物的依賴關系”無法形成“真正的共同體”[13]。
“現代性”概念的內涵具有時代烙印,存在一條“數學—啟蒙理性—工業化—反工業化”的變化脈絡:其在17世紀笛卡爾時代的核心是數學;再從18世紀啟蒙運動、理性精神的同義語,關注人權,到代指19世紀的工業化運動;直至20世紀站至技術與科技的對面,表明對工業化后果的抗議[14]。中國民族題材電影《遠去的牧歌》《季風中的馬》《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等關注的生態問題是現代化、工業化的惡劣后果;美國的災難影片《全球風暴》《后天》《2012》同樣表現出相似的生態危機。“生態不是一個地域性的問題,它只是通過地域表現出來,其實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產生的。”[15]全人類共同面臨自然生態的破壞問題,遭遇隨之而來的生活方式變動,這不是某一個體、地域、國家或民族能解決的,由此暗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行為主體的共同需求。
“災難”母題承載的是傷痛記憶:《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中的傷痛是“遠離城鎮的地方,水草才會長得豐茂”;《季風中的馬》中的傷痛是草原沙化、賣馬進城后的鄉愁;《2012》中的傷痛是世界末日之際人類掙扎求生的百態……不同電影呈現出災難程度和形式的差異,但災難的成因始終相同,直指工業化、現代化、全球化的負面影響。自然生態“災難”母題映射當下全人類共同存有的發展焦慮,而焦慮的解決路徑與全人類共同價值中的“發展”觀念相合。后者包含推進創新發展、謀求共同發展和實現可持續發展三方面含義,要求各國打破狹隘利己的思維定式,創新合作共贏的發展理念,以更具韌性的發展作為解決全球問題的“金鑰匙”[14]。
2. 文化身份“尋找”母題
“家園”也是雙重背景下民族題材電影重點表現的母題,涉及家園環境的改變、精神家園的迷失兩方面。前者主要惋嘆家園生態環境的破壞,聯系著上述自然生態“災難”母題;后者觀照人類的精神家園。全球化、現代化、工業化提升生產力,變革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進而推動人對自我身份認知的變化、與他者交流方式的改變。由此,“家園”母題又關聯著“尋找”母題,呈現為人對記憶中“家園”“家人”和“自我”的尋找。
甘姆森(GAMSON)以“詮釋包裹”(interpretive packages)理論分析框架的話語呈現策略,“詮釋包裹”即話語的物化形態,其將話語理解為一個個包裹,便于完整闡釋某一議題的意義體系[16]。“詮釋包裹”可進一步分為框架和推理裝置,框架裝置直顯于句中,包含隱喻、例證、描述等符號策略,提示讀者如何思考議題中的元素;推理裝置則隱含在句子中,包括原因、后果、解決策略和道德呼吁等,啟示讀者如何處理議題中的相關元素。可見,框架的勸服性理解通過語言的策略性使用達成。上述“災難”“家園”“尋找”母題間也存在著如此的邏輯隱線,三者之間是層層包裹、相互滲透的——自然生態“災難”引發了人與既往“家園”的離散,現代社會的流動性加劇了精神“家園”的迷失,使得“尋找”成為現代人一生的課題。
萬瑪才旦的公路電影是此觀點的典型樣本——“災難”是導火索,使得個體與“家園”解綁,“尋找”看似是接續而來的行為過程,卻在公路場景的反復展演中成為行為的最終意義。萬瑪才旦電影在西方類型化影片視域下,具備公路片特征,“路”成其最大視覺符號,各異文明文化的博弈、不同生活方式的對抗、個人身份選擇的可能性等都在路途中發生[17]。《尋找智美更登》中貫穿著公路旅行,并且在尋找“智美更登”角色的途末,“導演”坦言自己也失去了對這一傳統藏戲角色的把控;《老狗》中的公路既是找尋農業文明代表符號“老狗”的展演場景,也是呈現父子交通工具差異、表征新舊文化觀念矛盾的載體;《塔洛》結尾處未知盡頭的道路,則表征“塔洛”個人身份認知的迷失。
亦如鮑曼所言:“現代社會的真正問題不是如何建構身份,而是如何保持它。”[18]“尋找”是貫穿于萬瑪才旦公路電影始末的,此類“尋找”母題也呈現于伊朗導演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的“村莊三部曲”中——“路表達了人們尋找必需品,尋找永遠不安的靈魂,尋找永不結束的探索。”[19]同樣,美國的公路電影“捕捉到了美國夢、緊張和焦慮”[17]。萬瑪才旦電影、阿巴斯的三部曲、美國公路電影共構全球公路電影類型片,共同映射全球化、現代化背景下個人身份的危機和尋找。未來不確定文化的走向以及如何參與整個過程的焦慮,都是全人類需要直面的問題。
二、全人類共有情感:基于人性產生聯結
上述民族題材電影重點表現對敘事母題的總結,主要從電影的內容文本出發,挖掘其反映的全人類共處生存境況、表述的共有所思所愿;進一步基于受眾的接受心理,探究敘事母題背后的動員邏輯,挖掘共同體成員形成語義互通的原因和影響。人類認知世界的方式存在范疇化特征,即以原型作為我們認知的起點,基于其預設的范疇去認識現實世界[20]。相較于母題溯源于民俗學,“原型”概念源自心理學,蘊含著特定群體固有的情感體驗和認知方式,由社會輸入的價值觀念、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等提供[21]。質言之,人性層面的共通情感可作為原型,是人際交往互動的核心動因,民族題材電影的傳播則可視為導演與受眾、共同體成員間“情感能量”互動的動態進程[22]。
1. 人性中的共通點
中國民族題材電影《臍帶》講述了蒙古族音樂人“阿魯斯”重返草原,照顧患有阿爾茨海默病母親的故事。為防止母親走失,兒子用一根粗繩連在二人的腰間。形似臍帶的粗繩由此產生了“逆位”的母子關系——孕育生命階段的臍帶是母子連心的樞紐,而贍養母親階段的臍帶則是象征后輩孝順、代指親情連接的粗繩。質言之,“臍帶”承載著人性中的多重共通點,成為電影情感傳播的重要符號:一是如前所述,表征親情關系;二是暗指命運生死。剪斷臍帶是新生命的降臨,而割斷麻繩則是對生命的告別。《臍帶》結尾選擇以浪漫的方式訴說死亡議題,在沉靜的湖水旁、溫暖的篝火邊、悠揚的歌聲里,兒子選擇割斷麻繩,尊重母親走向死亡的選擇。沉重的死亡議題在此種視聽氛圍中抹去悲愴基調,使觀影者學會安然訴說離別、坦然面對生死。關于疾病的呈現,導演喬思雪并不以剖析痛苦為目的,而是表明阿爾茨海默病患者也許忘記所有,但依然能感受到情感。正如母親最后向兒子輕聲道,她覺得很幸福。
《臍帶》的導火索是小兒子不滿大兒子對母親的照顧,毅然決定帶母親重回記憶中的草原家園。因此,其起因依然是傳統與現代、城市與鄉村等二元化對立。但是民族題材電影中對二元化差異關系的呈現并不凸顯意識形態的對抗,而是以開放性、包容性、更積極進取的精神狀態直面矛盾與問題,并試圖從人性和生活角度去找尋不同文化中的共通點[23]。萬瑪才旦電影同樣以人性中共同關注的議題為主要呈現對象。在導演萬瑪才旦看來,傳統與現代的沖突是個體矛盾與關系分化的起因,但并不是人物的行動邏輯,因此電影深入挖掘日常生活中個體的內心需要與精神動因。以《塔洛》為例,對于放羊人“塔洛”而言,他選擇賣掉羊群、走向城市的真正驅動力并不是二代身份證、城市KTV或美麗發廊女人等現代事物的誘惑力;他剪掉小辮子、參加演唱會、愈加開放的性觀念也并不意味其與舊生活的決裂。塔洛個人行為的驅動力并不是在藏文化與現代化之間作出選擇,而是自我在內心博弈后決定孤注一擲、追求情感的勇氣。這種基于人性的共有情感更易引起觀眾共鳴,由此,觀眾代入地思考影片人物的困惑,參與到同導演、其他共同體成員的互動中。
2. 由情感達成團結
綜上所述,民族題材電影聚焦于普通人物的生命故事,關注人性層面的共通情感。民族題材是外殼,而共通情感是電影的內核。在這些情感原型的作用下,導演與受眾能跨越地域、民族、國家等藩籬,實現個人情感與原型情感的共振,由此將個體體驗的情感和意義納入集體共享的情感和意義中[21]。這種對人類共有情感、日常生活、生命故事以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關注無疑與全人類共同價值相契合。后者的豐富內涵同樣是以人為出發點進行闡釋的:“和平與發展”關乎人的生存發展權,“公平與正義”關乎人的尊嚴,“民主與自由”關乎個人的福祉[2]。
相較于“作為儀式的傳播”,情感這一非理性因素的參與和凸顯將民族題材電影的傳播還原至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交往溝通的狀態。傳播并非人類純粹理性的產物,柯林斯(COLLINS)將“相互關注”(mutual focus of attention)與“情感連帶”(rhythmic emotion entrainment)視為傳播儀式中極為重要的“過程性事件”[22]。互動儀式的成功需前述二者的相互強化——每個個體的注意力集中于同一客體,借言行將自我聚焦點向他人示意,當個體感知到自我言行被他人覺察時,便會強化表達、形成良性反饋,并在循環往復的過程中將“群體團結”推至高點[22]。柯林斯進一步將本文所述的情感原型視為“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y),認為其推動參與者間“共同關注”“情感連帶”的產生。更重要的是情感能量不限于主觀體驗,還賦予人力量、發動行動,由此達成共意共情群體的聯結[24]。
高度“相互關注”、密切“情感連帶”將導向成功的互動儀式,反之,低度“相互關注”、疏離“節奏連帶”則行至失敗。其中,個體正面或負面的情感體驗產生關鍵影響,正面情緒利于高群體團結的形成。這同樣是新時代影視創作呼喚溫暖現實主義的應有之義。相較于抽離尖銳問題、留下表象真實的懸空現實主義和觸碰復雜矛盾但沉湎消極狀態的灰暗現實主義,溫暖現實主義的民族題材電影能從人性角度找尋到共通點、挖掘到更具建設性的力量[23]。
三、全人類共同命運:出走、回歸與新方向
盡管民族題材電影存在地域化、民族化特征,但各國民族題材電影均表現出相似的自然生態“災難”母題和文化身份“尋找”母題,傳播基于人性層面的人類共通情感經驗,并以這些共通情感達成跨地域、跨民族、跨國家的傳播。這表明在全球化、現代化背景下,人類的共同命運既是出發點,也是當下進程中的目的地——相似母題、共通情感揭示全人類潛在聯系,同時我們所面臨的共同困境又要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民族題材電影從隱匿的共同聯結出發,又再次回歸至強調命運與共的訴求,并在這一過程中為“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指明方向。
1. “出走回歸”式電影情節
“回歸”情節接續著“出走”的受挫,包括主動回歸與被動回歸,前者是歷經他者文化洗禮后,重拾或加深對文化之根的認同;后者則是在加劇迷茫、撕裂身份后,重回安全家園的需求。同時,“回歸”也可分為行動與精神層面,這兩類時常相互交融。在美國華裔導演朱浩偉執導的電影《身在高地(In the Heights)》中,“回歸”家鄉多米尼加共和國是男主角“Usnavi”的夢想,但最終回歸行動的失敗正在于精神回歸的成功。男主經營的小店是紐約華盛頓高地拉丁裔社區的“燈塔”,電影依然將重要意義的闡釋落于真摯溫暖的情感。法國電影導演費利普·彌勒執導的電影《夜鶯》講述了多個人物出走與回歸的故事,但所有人物的共同歸因都指向溫暖情感:爺爺“志根”的返鄉是兌現與亡妻的諾言;兒子(父親)“崇義”的返鄉促其重新理解親情;孫女“任幸”的返鄉重喚童真與善良。在此,“回歸”不單是對傳統文化的重新認同,也是在共通情感中得以實現精神的救贖,是自我精神家園的重建。
2. 重返價值共識、指明未來方向
然而,“差異”的呈現是以“共同”為旨歸的。霍爾在“延異”思想的啟發下,拒絕將黑人視為西方分類體系中的他者,也質疑黑人的自我他者化。這與全人類共同價值對中心國家和文明沖突的挑戰不謀而合。當前西方中心主義者推行的國際體系由以美國為中心的少數國家設置國際議題、主導規則秩序,認為不同文明有高下、優劣之分,使“其他現存文明卷入到波及全球的西方化浪潮之中”[26]。這顯然與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的現實境況不符,但部分西方國家依然固守強權至上的“零和博弈”思維、落入文明沖突論的窠臼[7]。
中國民族題材電影呈現的相似母題、傳播的共有情感、蘊藏的共同命運提供了異于西方“普世價值”的時代答卷。西方“普世價值”立足于唯心主義世界觀,推崇個人主義價值論[27]。而中國民族題材電影既可將全人類共同價值作為傳播策略,也可被視為全人類共同價值的載體——全人類共同價值推促著中國民族題材電影國際傳播的實踐升維,以相似母題和共通情感轉化對立語境,以共同命運融匯差異語境[8]。由此,中國民族題材電影成為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有力載體,促成“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28]的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