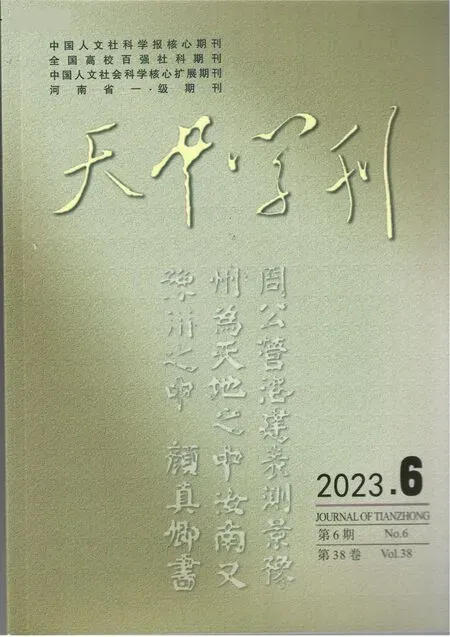新時期中國史學的本土化實踐——劉澤華“陰陽組合結構”說的形成及意義
任芮欣
新時期中國史學的本土化實踐——劉澤華“陰陽組合結構”說的形成及意義
任芮欣
(重慶工商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重慶 400067)
“陰陽組合結構”說是劉澤華在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提出的一項重要理論。該理論經歷了早期醞釀、初步論證和理論定型等發展階段,旨在揭示中國傳統思想命題的相反相成特質及其背后的政治思維。從理論淵源來看,學界關于中國傳統思想“混沌”性特征的研究、對中國傳統哲學“調和”與“中庸”式思維方式的認識,以及馬克思主義學說中矛盾的法則等,都對“陰陽組合結構”說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方法論意義上,“陰陽組合結構”說是對思想史研究中抽象繼承法的反思,是對馬克思主義史學批判繼承法的發展,是新時期中國本土化史學的代表性理論之一。
劉澤華;陰陽組合結構;政治思想史;史學本土化
在20世紀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劉澤華及劉澤華學派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存在。其中,“陰陽組合結構”說是劉澤華提出的分析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理論。所謂“陰陽組合結構”說,是指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沒有一個確定的理論原點,每一個思想命題都有另一個命題進行補充,兩個命題相反相成、不可分割,且無法相互轉化,例如君本和民本、尊君和罪君、天人合一和天王合一、道高于君和君道同體等。劉澤華認為,這種陰陽組合結構式的政治思維,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具有廣泛的實用性,為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的穩定和自我調節提供了保障。可以說,“陰陽組合結構”說是劉澤華用理論化方式對中國傳統政治思維的概括,是劉澤華在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術貢獻。有學者稱這一理論是一個“重大的學術發現”[1]9。目前學界對這一理論的考察主要集中于對其內涵的發掘,對其形成過程、理論淵源及方法論意義等尚缺乏深入探討。基于此,本文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對“陰陽組合結構”說的形成過程、理論淵源及方法論意義進行考察。
一、“陰陽組合結構”說的形成
“陰陽組合結構”說是劉澤華對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結構性現象的理論概括。它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過了一個演變發展過程。大體而言,該學說的形成經歷了早期醞釀、初步論證、理論定型三個階段。
首先,早期醞釀階段。在這一時期,劉澤華在先秦政治思想研究中,已經關注到傳統政治思想中不同命題之間相反相成的結構性特點,此時他多采用“統一體”“辯證統一”等方式進行概括。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指出,孔子的思想是一種“邊際平衡”思想,該思想的特點是在矛盾面前努力使雙方不發生根本性變化,從而達到一種平衡狀態。在考察先秦時期的君、民關系思想時,他指出:在先秦思想家的思想體系中,君、民并非對立關系,而是相互補充的統一體,“這種以君為中軸的君民關系論,是貫穿各種具體文化思想內容的主要線索”[2]167。他認為,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君主專制主義的理論與“立君為民”的相關理論相互矛盾,但其實兩者是辯證統一的關系。“立君為民”的理論為君主專制主義理論提供了理論上的自我調節功能,也可以在精神上給予普通人以滿足。在考察先秦時代的進諫、納諫思想與君主專制主義的關系后,他指出:進諫、納諫實質上與君主專制制度并不矛盾,而是“君主專制制度的一種補充”[3]59。可以看出,在20世紀80年代初,劉澤華對先秦政治思想中相關命題的結構性現象已有自覺考察與認識,并關注到了不同政治思想命題之間相反相成的關系,這些研究成果為他之后對這一現象進行理論性概括奠定了基礎。
其次,初步論證階段。1986年,劉澤華在《王權主義的剛柔結構與政治意識》中首次對這一問題進行詳細論述,認為王權主義體系的內在構成是一種剛柔結合的二元結構。這種“剛柔結構”具有以下關鍵點。第一,王權主義的“剛”,即其絕對性。這種絕對性體現在:王是溝通天人的中樞;王擁有統屬社會一切的巨大權力;王是認識的最高權威和終極裁決者。第二,王權主義的“柔”。為了防止王權最終走向極端化,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又蘊含著一系列對王權進行限制和調節的思想理論,如天譴說、從道說、圣人和尊師說、社稷和尚公說、納諫說,等等。這些思想為限制王權提供了理論依據。第三,王權主義的“剛柔結構”。上述兩個方面共同構成了王權主義體系中的“剛柔結構”。關于這種二元結構的特點,劉澤華強調,“柔”是對“剛”的補充。王權的絕對性是最大的前提,調節王權的理論機制是對王權絕對性的補充。“剛性原則決定著君主政治的基本方向,柔性理論則根據具體情況不斷地積極地進行自我調節,以保證君主政治正常運行”[4]34,正是這種剛柔二元結構使王權主義體系具備了良好的應變性和強大的自我調節能力,從而獲得了頑強的生命力。在此之后,劉澤華在論著中又以陰陽結構、陰陽組合命題、主輔組合命題等來指稱這種二元結構,直到將這一概念最終確定為“陰陽組合結構”。
再次,理論定型階段。2000年前后是劉澤華史學研究體系中概念和命題定型的重要時期,也是劉澤華王權主義理論最終形成的關鍵時期。在這一時期,劉澤華對陰陽組合結構的相關理論進行了詳盡闡述。其中,《傳統思維方式與行為軌跡》和《傳統政治思維的陰陽組合結構》是他晚年集中闡述該理論的重要文章。劉澤華強調,“陰陽組合結構”是中國傳統政治思維方式的一個最基本特點。他用舉例子的方式列舉了一系列的陰陽組合命題,如君本與民本、尊君與罪君、王體道與道高于君、王有天下與天下為公等。他指出,這些命題均處于陰陽組合結構之中,即每一個命題都無法單獨存在,在邏輯上無法自成系統,需要成對存在,互相依存;每一對命題之間均存在主輔關系,前者是主,后者為輔。只有在這種陰陽組合結構中考察中國傳統政治思想,才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在《傳統政治思維的陰陽組合結構》中,劉澤華進一步系統論述了他對這種二元結構的認識。第一,這種陰陽組合結構模式在古代政治思維中普遍存在。他在文中列舉了大量具體的陰陽組合命題,并對其中一些進行了詳細闡釋,如“天人合一與天王合一”“圣人與圣王”“道高于君與君道同體”“天下為公與王有天下”“尊君與罪君”“正統與革命”等[5]33。古人在闡述推導自己的思想理論時,并不是從某一個理論原點出發,而是在這種組合結構中進行推演。第二,這種陰陽組合結構的“陰”與“陽”不能分割,也無法相互轉化。談到“陽”,一定離不開“陰”;談到“陰”,也不能離開“陽”。此外,與矛盾雙方對立統一、可以相互轉化不同,這一組合中的陰陽兩方面無法互相轉化。在陰陽組合結構中,“陰”“陽”位置絕對固定,不能出現錯位。第三,這種陰陽組合結構的思維方式具有巨大容量,可以將不同的概念和命題包容于統一的思想體系之中,在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傳入之前,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一直囿于陰陽組合結構的思維方式之內。也正是由于這種巨大容量,使得中國古代君主專制擁有了強大的適應能力和應變能力而長期延續不輟。
綜上所述,劉澤華是一位具有高度理論自覺的學者。“陰陽組合結構”說經歷了一個從提出到逐步完善的完整過程。它來自于劉澤華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實踐,是劉澤華從具體研究實踐中發掘出的一種中國傳統政治思維方式。其后,經過劉澤華及其合作者的理論升華,“陰陽組合結構”說的理論內涵逐漸清晰和豐富,并被應用于中國政治思想史相關問題的考察,成為分析中國政治思想史的一種有效工具。
二、“陰陽組合結構”說的理論淵源
任何一種學說的形成都建立在一定的學術基礎之上,而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劉澤華的“陰陽組合結構”說也不例外,其有著較為明確的理論淵源。他既繼承了學界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主要特征的相關研究成果,又吸收了馬克思學說中矛盾的法則等理論因素,并結合自身研究實踐,最終提出了“陰陽組合結構”說。
首先,關于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混沌”性特征。在中國思想史研究中,部分學者曾指出,中國傳統思想的一大特點是“渾淪”或“混沌”,即學理上缺乏嚴密邏輯,不注重學理推衍,各種思想、概念、范疇的運用也缺少嚴密界定與規范。張岱年在《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將中國千年來文化傳統的基本精神概括為四點,即天人合一、以人為本、剛健有為、以和為貴;而中國文化的主要缺陷則表現為:等級觀念、渾淪思維、近效取向、家族本位[6]386。在此,張岱年將“渾淪思維”列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缺陷之一。中國傳統思想在思維方式上的這一特點,在學界得到了較為廣泛的認同。李澤厚也指出,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化在一般情況下缺少嚴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論探討,“毋寧更欣賞和滿足于模糊籠統的全局性的整體思維和直觀把握中,去追求和獲得某種非邏輯、非純思辨、非形式分析所能得到的真理和領悟”[7]323。劉澤華認為類似觀點具有一定合理性,他指出,中國古代思想各種理論命題相互交織,難以在學理上理清理論原點,但相關研究不應僅停留在“混沌”層面,這一問題還有深入分析的空間。在此基礎上,劉澤華提出,中國古代政治思想有其內在理路,即陰陽組合結構。與此前學界常見的“渾淪”“混沌”說相比,“陰陽組合結構”說更加清晰地展現了中國傳統思想內部的結構性特征,是對相關研究的一大推進。
其次,關于中國傳統思想的“中和”“調和”性特征。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中和”“中庸”或“調和”式精神,在學界受到了較多關注,相關論述屢見不鮮。梁漱溟在論及中國形而上學的大意時認為,“調和”是中國形而上學的中心意思,在中國的形而上學思想中,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都處于一種相反相成的調和關系之中,在這個宇宙中,絕對的、極端的或不調和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凡是現出來的東西都是相對、雙、中庸、平衡、調和”[8],這是具有中國式思想的人們所共有的思維特征。馮友蘭認為,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存在著內外的對立、本末的對立、粗與精的對立、動與靜的對立、體與用的對立等,但是這些對立在中國古代超世間的哲學中不再成其為對立,這些對立不是被取消了,而是被統一起來。至于如何將這些對立進行統一,便是中國哲學力求解決的一大問題,“始終有勢力底各家哲學,都求解決如何統一高明與中庸的問題”[9]。李澤厚認為,中國古代的辯證法是一種處理人生的辯證法、互補的辯證法,而非屬于精確概念的辯證法和否定的辯證法,“它的重點在揭示對立項雙方的補充、滲透和運動推移以取得事物或系統的動態平衡和相對穩定,而不在強調概念或事物的斗爭成毀或不可相容”[7]321。劉澤華提出“陰陽組合結構”說,最初即是關注到了傳統政治思想命題中的對立統一關系。他揭示了孔子邊際平衡式守舊思想的本質,分析了君本與民本思想的辯證統一,認為在傳統政治思想理論中,君與民是一個調和的統一體。他所提出的“陰陽組合結構”政治思維,反映了事物對立與統一的基本面,是中庸、執兩用中思想的具體化,是中國傳統思想中“極高明而道中庸”思維方式的體現。可以說,劉澤華提出的“陰陽組合結構”,深刻闡釋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的中庸、調和式思維模式。
再次,關于馬克思主義學說中的矛盾法則。“陰陽組合結構”說的理論與矛盾的對立統一原則既有學理淵源,又存在一定區別。劉澤華的學術研究,強調對歷史進行辯證分析,注重在矛盾中陳述歷史。面對批評者稱其為“全盤否定論者”“歷史虛無主義”的聲音,劉澤華多次表示:“我遵循馬克思說的,在矛盾中敘述歷史,因此給我戴上上述兩頂帽子未必合適。”[10]20可以說,提出“陰陽組合結構”說的理論,是劉澤華在矛盾中陳述歷史的一種嘗試。劉澤華這種在矛盾中陳述歷史的思想,來自于馬克思的提法,是對馬克思這一說法的具體化、實踐化。經考證,“在矛盾中陳述歷史”出自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一封信。1853年9月3日,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件中寫道:“真理通過論戰而確立,歷史事實從相互矛盾的論斷中得出。”[11]這句話是馬克思用以回應1853年9月3日《晨報》上一篇題為《應該怎樣寫歷史》的文章的聲明內容。劉澤華將馬克思的這一陳述進行了進一步闡發,結合唯物辯證法的基本法則,將其提煉為一種學術研究的重要方法,并通過“陰陽組合結構”說的理論使這一分析方法在政治思想史研究領域得到具體應用。“歷史事實從相互矛盾的論斷中得出”,即要在矛盾的分析過程中把握歷史事實。
矛盾的法則也就是對立統一的法則,這是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法則。矛盾的法則提示人們要在矛盾的辯證統一過程中認識事物的本質。矛盾雙方不能孤立存在,而是互為存在條件,共處于一個統一體中,并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陰陽組合結構”說吸收了在矛盾的辯證統一過程中把握事物本質這一方法論,強調在陰陽組合結構關系中把握傳統政治思想本質。“陰陽組合結構”說的理論,從傳統政治思想各個命題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出發,將各種命題歸入不同的組合關系中。這些組合結構中的命題相反相成、互相依存,存在著一種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以尊君與罪君這對陰陽組合命題為例,劉澤華認為,尊君的理論與罪君的理論相互聯系而存在,談論尊君離不開對罪君的論述,闡釋罪君也需要對尊君進行討論,因此,劉澤華強調要將二者作為一個統一組合結構進行考察。但是,陰陽組合結構關系與矛盾的對立統一關系也有一定區別,與矛盾雙方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不同,陰陽組合結構關系中的各命題無法相互轉化,即對立統一包含著對立面的轉化,但陰陽之間不能轉化,這也是劉澤華稱此種關系為陰陽組合結構而非對立統一的原因。
總而言之,“陰陽組合結構”說與學界已有的相關研究成果具有理論上的淵源。劉澤華的理論,一方面繼承和吸收了學界已有成果,另一方面又在其基礎上進行了發展。“陰陽組合結構”說不止步于對傳統政治思維的現象性描述,而是進行了理論概括和闡釋,使之升華為一種適用于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研究的理論工具。
三、“陰陽組合結構”說的方法論意義
劉澤華的“陰陽組合結構”說揭示了中國傳統思想命題的組合性特征,分析了組合命題之間的主輔關系,“打開了傳統政治思想的文化密碼,呈現出其基本屬性和內在結構”[12]138,為研究傳統政治思想提供了全新視角,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首先,“陰陽組合結構”說強調將傳統思想命題置于相互依存、相反相成的結構關系中進行分析考察,從而避免了就傳統政治思想的某一個命題進行無限制的發揮和抽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中國思想史研究中抽象繼承法的一種糾偏。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的抽象繼承相關問題,最早由馮友蘭于1956年11月在中國人民大學的演講中明確提出。馮友蘭認為,當下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對中國古代哲學的否定意見占據多數,導致中國古代哲學中可繼承的遺產變少,如果要全面了解中國哲學史中的哲學命題,需要從兩個意義方面對這些命題進行把握,一是哲學命題的抽象意義,二是哲學命題的具體意義,“只有這樣做,才可以看出哲學史中可以繼承的思想還是很不少的”[13]106。此后在《再論中國哲學遺產底繼承問題》中,他又用了“一般意義”和“特殊意義”進行表述。馮友蘭這一關于古代哲學的繼承方法論述被人命名為“抽象繼承法”。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學術風氣的轉變,抽象繼承法逐漸受到重視。20世紀90年代后,針對日益興盛的國學熱與傳統文化熱潮,有學者對抽象繼承法提出了反思,指出了抽象繼承法的缺陷,認為抽象繼承法不是對傳統的繼承,而是將現代精神附著在傳統命題之上。
劉澤華在學術研究中對抽象繼承法持謹慎懷疑態度,認為不能脫離具體歷史事實而孤立地討論傳統思想命題。在劉澤華看來,任何傳統文化都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不是超時空的產物;傳統文化中的任何命題都從屬于某一思想體系,與思想體系中的其他話語同在,不可脫離思想體系來討論思想命題。因此,面對傳統文化,首先要做歷史的考察,認識其真實歷史面貌;其次要在思想體系的整體中對其進行分析,而不是脫離歷史語境,對某些命題進行抽象發揮。例如,在對古代進諫、納諫的民主性問題的研究中,劉澤華及其合作者強調要把這類現象納入具體的歷史環境進行綜合研究,而不是脫離具體歷史語境,對其進行抽象討論。而“陰陽組合結構”理論是劉澤華反思抽象繼承法的一個有效工具。“陰陽組合結構”說揭示了傳統政治思想命題的具體歷史屬性和本來面貌,發掘了傳統政治思想命題的結構性特征,將傳統政治思想命題置于思想體系中進行考察。傳統政治思想命題一主一輔、一陰一陽結構特征的發現與提出,徹底打破了部分學者高舉抽象繼承法對某一傳統政治思想命題進行無限抽象研究的神話。
其次,“陰陽組合結構”說既繼承了批判繼承法的批判性,又反思了其對傳統思想文化采取的精華與糟粕二分法,主張將傳統思想文化命題置于相反相成的結構關系中進行綜合考察,是對批判繼承法的揚棄和發展。最早明確提出用批判繼承方式對待傳統文化繼承問題的是毛澤東。1940年,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指出應該吸收一切當下社會可以利用的文化,吸收過程不是不加分別地兼收并蓄,而是需要區分文化的精華與糟粕,批判地繼承文化傳統,吸收利用其中屬于文化精華的部分。這種把傳統文化二分為精華與糟粕、進行批判繼承的方法,成為學界長期以來對待傳統文化的主流,甚至在某些時期出現了極端教條化的傾向。由于批判繼承法并未明確如何進行批判、如何區分精華與糟粕等問題,造成了一定時期內學界過分強調對傳統文化的批判,而忽視了對傳統文化的繼承。
劉澤華認為,從邏輯上看,精華與糟粕的價值二分法并無不可,但在具體實踐中卻難以操作:“二分法無疑是一種極其高明的思維方式,有快刀斬亂麻之效果。但也有一刀切之弊。從純邏輯上看,二分法固無不可,但對實際問題實行二分法則是十分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強分必亂。”[14]168如何更好地使用二分法,是需要深入考慮的問題。劉澤華提出的“陰陽組合結構”理論,在方法論層面上對批判繼承法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一方面,它繼承了批判繼承法的批判性,對傳統政治思想進行了全面分析考察。這一理論對傳統政治思想命題之間的結構性關系進行了揭示,發掘了傳統政治思想的內部結構特征。這種在矛盾中陳述歷史的分析方法,可以展現傳統政治思想的結構特征和陰陽雙面屬性,既抓住了傳統政治思想的專制主義本質特征,又展現了傳統政治思想內部的自我調節機制,從而實現了對傳統政治思想的全方位分析考察,為批判繼承提供了穩固可靠的事實基礎。另一方面,它又完善了批判繼承法對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二分法。劉澤華認為,對傳統思想文化的精華與糟粕二分方法,并不能夠完全解決如何處理傳統文化的問題:第一,區分精華與糟粕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但判斷標準因人而異;第二,即使能夠做出精華與糟粕二分的認識,但精華也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精華,籠統地講繼承與弘揚,也存在一定問題。“陰陽組合結構”理論強調傳統政治思想的陰陽結構關系,在這種結構關系中,陰陽命題之間相輔相成、不可分割,雙方同屬于一個統一的結構體。這種結構分析法不同于傳統的精華與糟粕二分法,它對傳統政治思想命題作了系統性考察,避免了二分法的孤立與片面,有利于在綜合結構層面全面系統地把握傳統文化原貌。
再次,“陰陽組合結構”說是新時期中國史學本土化趨向的代表,對于推動中國思想史研究具有不可輕視的理論價值。近代以來,在歐風美雨的洗禮之下,中國傳統思想研究始終受到西學觀念和方法的影響。毫無疑問,西方學說在中國傳統思想研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既拓展了審視傳統思想的可能性空間,也貢獻了解讀傳統思想的有效性方法。但是,西學的形成基于歐洲的歷史經驗和現實,在闡釋中國思想時是否完全適用依然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正如部分學者所指出,“用西方模式來籠罩中國經驗,用西方觀點來加工中國材料,用西方的話語來描述、歸納中國文明和思想的特征,用西方程序來對中國的歷史重新編碼”[15]157,往往存在削足適履的問題。然而,像這樣對西學具有高度警覺的學者畢竟屬于少數,大多數學者不僅沒有學術自覺,反而主動去擁抱西學、臣服西學。
自五四時期以來輸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當然也是西學的一部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并不僅僅是將唯物史觀的理論與方法運用到中國歷史研究中,更是將唯物史觀與中國的歷史經驗、文化基礎相結合,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劉澤華的“陰陽組合結構”說其實就是將唯物史觀與中國歷史經驗進行結合的有益嘗試。他受到了唯物史觀的啟示,尤其是矛盾學說的影響,揭示了中國傳統政治思想潛藏的矛盾性結構。同時,他強調中國傳統思想中的矛盾性命題之間是組合關系,是不能轉化的,這也是“陰陽組合結構”說和矛盾說的差異所在。他指出:“這里用了‘陰陽組合結構’,而不用對立統一,是有用意的。在上述組合關系中有對立統一的因素,但與對立統一又有原則的不同,對立統一包含著對立面的轉化,但陰陽之間不能轉化。”[16]從這段表述中可以注意到,劉澤華使用的概念工具并非西學的對立統一,而是中國傳統思想范疇的陰和陽;其凸顯的是對立面的組合關系,而不是西學中的對立統一關系。對立面的組合恰恰就是基于中國歷史文化和傳統思想的“中庸”思維。可以看出,劉澤華的“陰陽組合結構”說并不是將馬克思主義的矛盾學說簡單運用到中國思想史的研究中,而是基于中國歷史實際提煉出的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論學說。從概念的使用到命題的提出,“陰陽組合結構”說都表現出顯著的本土化色彩。可以說,“陰陽組合結構”說是新時期中國本土化史學的代表性理論之一。
總之,劉澤華的“陰陽組合結構”說揭示了中國傳統政治思維的二元結構體系,將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的不同概念與命題放入這種結構關系中進行重新考察,可以更加清晰地認識傳統政治思想的本質與核心。它的應用既可以使原本處于“混沌”狀態的傳統政治思想有理可循,又可以避免對傳統政治思想“一葉障目”式的片面性認識。“陰陽組合結構”說是劉澤華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理論成就,其既為解釋中國傳統政治思想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分析工具,也為王權主義理論的完善與證成提供了有利條件,是新時期本土化史學的代表性理論之一。
[1] 李振宏.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權主義學派[J].文史哲,2013(4):5–28.
[2] 劉澤華,王連升.論先秦人性說與君主專制主義理論[G]//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1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139–167.
[3] 劉澤華,王連升.先秦時代的諫議理論與君主專制主義[J].南開學報,1982(1):58–66.
[4] 劉澤華.王權主義的剛柔結構與政治意識[M]//中國政治思想史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3–38.
[5] 劉澤華.傳統政治思維的陰陽組合結構[J].南開學報,2006(5):33–35.
[6] 張岱年.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M]//張岱年全集:第7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378–387.
[7]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M].北京:三聯書店,2008.
[8]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134.
[9] 馮友蘭.新原道:中國哲學之精神[M].北京:三聯書店,2007:4–5.
[10] 劉澤華.《中國的王權主義》修訂本序[M]//劉澤華全集·序跋與回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14–20.
[11]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49.
[12] 寧騰飛.劉澤華史學方法論的構建[J].史學理論研究,2022(2):133–144.
[13] 馮友蘭.中國哲學遺產底繼承問題[M]//馮友蘭文集:第10卷哲學論文集.長春:長春出版社,2008:102–106.
[14] 劉澤華.簡說精華與糟粕[M]//劉澤華全集·隨筆與評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166–168.
[15] 王學典.從西方話語中拯救中國歷史:“本土化”史學的回歸[M]//把中國“中國化”:人文社會科學的近期走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156–165.
[16] 劉澤華.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M].北京:三聯書店,2017:351.
K061
A
1006–5261(2023)06–0132–07
2023-07-03
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22CZS066)
任芮欣(1993― ),女,四川綿陽人,講師,博士。
〔責任編輯 姬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