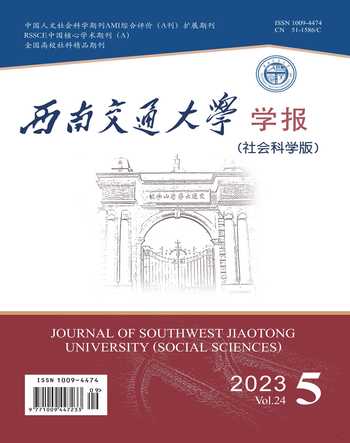“游戲三昧”的禪學內涵與詩學意義
摘 要: 禪宗“游戲三昧”指禪定后精神上達到自由無礙的境界,具有無分別、圓滿自足的美學意蘊。由于“游戲三昧”的禪風符合詩人追求心靈自由的審美理想,所以進入詩學理論,進而影響了詩人的創作態度,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構思上,“游戲三昧”促使詩人突破拘執,達到揮灑自如的境界;創作風格上,“游戲三昧”推動詩人形成自然無跡、渾然天成的詩風;表達上,“游戲三昧”促使詩歌語言逐漸幽默化和通俗化。由于“游戲三昧”的大自在境界與“不可湊泊”的詩境是相通的,“游戲三昧”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喻指詩歌奧妙訣竅的重要詩學范疇。
關鍵詞: 禪宗;“游戲三昧”;心靈自由;詩學意義;詩歌范疇
收稿日期: 2022-09-26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歷代釋家文論文獻集成與綜合研究”(22AZW011)
作者簡介: 王 悅,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E-mail:937779614@qq.com;張 勇,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佛教詩學研究。
在禪學上,“游戲三昧”是表達自由的重要范疇,指心無掛礙、隨性自在。由于中國禪宗的自由精神深入人心,“游戲三昧”之說也逐漸擴展至其他方面,特別是詩學領域。元好問云:“筆端游戲三昧,物外平生往還”〔1〕(《巨然秋山為鄧州相公賦》)。蘇軾稱贊釋道潛的贈詩“超然真游戲三昧”〔2〕(《與參寥子二十一首》)。陳巖肖、張表臣等人在其詩話中也都以“游戲三昧”評價過蘇軾作品的通達無礙陳巖肖《庚溪詩話》(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上冊),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73頁):“東坡謫居齊安,時以文筆游戲三昧”;張表臣《珊瑚鉤詩話》((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50頁):“時出險怪,蓋游戲三昧,間一作之也”。】。當然,也有僧人加入到文學創作和批評活動中,并將對“游戲三昧”的理解融入詩學中,提出了一些獨特的創作觀,如惠洪提出“游戲翰墨”說陳自力《釋惠洪研究》(中華書局2005年版),張勇、樊亭亭《惠洪詩論四題》(《中國詩學研究》2019年第1期)等都指出惠洪“游戲翰墨”說源于禪宗的“游戲三昧”。】,道潛說“興來即揮毫,游戲三昧前”〔3〕(《過玉師室觀霅川范生梅花》)。可見,“游戲三昧”思想已進入詩學語境并產生了重要影響。
目前,學術界對“游戲三昧”的考察主要集中在哲學領域,既有對“游戲三昧”的系統討論〔4〕,也有對“游戲三昧”與參禪規范之關系的探究〔5〕。周裕鍇先生較早關注到“游戲三昧”與詩學之關系,他以蘇軾、黃庭堅二人為例討論了宋代文人士大夫將“游戲三昧”從人生態度轉化為藝術創作態度的表現與影響〔6〕。禪宗“游戲三昧”對文藝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張培峰認為其在宋代文評中“是一種極高的藝術境界和藝術享受”〔7〕。而禪學的“游戲三昧”與文學的會通之處便是自在與法度〔8〕。“游戲三昧”是詩禪相通的一個重要基點,因此,在借鑒前輩成果基礎上,本文擬探究“游戲三昧”的理論內涵與美學意蘊,嘗試理清這一范疇進入古代詩學理論的軌跡,為進一步探究詩禪關系做一些補充。
一、“游戲三昧”的理論淵源與禪學內涵
(一)“游戲三昧”的理論淵源
中國禪宗“游戲三昧”思想的形成與佛教“游戲”思想和莊子“逍遙游”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游戲三昧”原本是佛家用語,在早期的漢譯經典中以及注經中,“游戲”一詞就常出現。《大智度論》有云:“戲名自在;如師子在鹿中自在無畏,故名為戲。”〔9〕慧遠云:“于此神通歷涉名游,出入無礙,如戲相似,故復名戲。”〔10〕“游”有教化、點化之意;“戲”在佛教中表示自由無礙。“三昧”,又譯為“三摩地”“三摩提”,即般若三昧。《大智度論》釋“三昧”為“善心一處住不動”〔9〕,指排除一切雜念、內心平靜的狀態。
在佛學中,“游戲三昧”的意思是佛菩薩通過“游戲”的方式專注正定而自在無礙地度化眾生。此時,“游戲三昧”常與“神通”一詞一起出現。鳩摩羅什所譯的《妙法蓮華經》中有“神通游戲三昧”〔11〕。《楞伽經》云:“諸菩薩摩訶薩無量三昧自在之力,神通游戲。”〔12〕僧肇在《注維摩詰經》中也說:“游通化人,以之自娛。”〔13〕可見,“游戲三昧”是菩薩的神通力之一。
在佛教傳入中國后不斷本土化的過程中,“游戲三昧”也吸收了道家的自由思想。“游”是莊子的重要思想,莊子將“逍遙”和“游”聯系在一起,表示超越現實、無拘無束、精神上的絕對自由。“逍遙游”指向心性自由,《人間世》有“乘物以游心”〔14〕,《德充符》說“游心乎德之和”〔14〕,《莊子·田子方》有“吾游心于物之初”〔14〕。可見,“逍遙游”的主體是心靈,莊子之“游”是一種愉悅的境界。莊子借老聃的話“得至美而游乎至樂,謂之至人”〔14〕(《莊子·田子方》),表現出“游”的最高境界是“至美”“至樂”。莊子認為大美無美,也就是說,“逍遙游”的至境是“游”于“無”之中,即“無為”。這是超功利的,是精神上的自適與自足。如何達到這種境界呢?莊子提出心齋、坐忘的修養功夫,即去除內心雜念、虛靜澄明,正如《山木》中所說的“虛己以游世”〔14〕,“虛己”而順乎大道,方能游向超然之境。
與老莊一樣,禪宗的最終目的也是解脫。禪宗在描述解脫的境界時,與莊子之“游”相似:
夫道人之至游矣,履虛極,守妙明;飲真醇,住清白,斷崖放足,空劫轉身……入諸世間,真契游戲三昧,斯可謂至游矣。〔15〕
禪宗將這種超脫自然的境界稱為“游戲三昧”。不過,莊子“逍遙游”傾向的是遨游于方外,是“游乎塵垢之外”(《齊物論》)〔14〕,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逍遙游》)〔14〕。而禪宗“游戲三昧”卻是“入諸世間”,慧能說:“于一切時中,行、住、坐、臥,常行直心”〔16〕,高峰原妙也說:“雖在塵中,游戲三昧”〔17〕。馬祖道一更是提出了“平常心是道”,認為禪道就在行住坐臥、應機接物之中,自然而然就是真正的無拘無縛。如此,禪宗便將把“游”導向了日常生活。
(二)“游戲三昧”的禪學內涵
宗寶本《壇經·頓漸品》謂:
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來自由,無滯無礙;應用隨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戲三昧,是名見性。〔18〕
這里的“游戲三昧”形容的不是菩薩,而是“見性之人”,指參禪者于當下識得自性本心,剎那間解粘去縛,達到“游戲三昧”境界。禪宗并不標榜“神通”,《五燈會元》卷第九中有一則公案:
有梵師從空而至,師曰:“近離甚處?”曰:“西天”。師曰:“幾時離彼?”曰:“今早”。師曰:“何太遲生!”曰:“游山玩水”。師曰:“神通游戲則不無,阇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19〕
禪宗強調“自性即佛”,重視自我的內在修行和自性的顯現。南泉普愿禪師“頓然忘筌,得游戲三昧”〔19〕,楊岐方會禪師“天縱神悟,善入游戲三昧”〔20〕。禪家以“游戲三昧”形容禪師頓悟開解的狀態,逐漸消解了“神通”,完成了其由形容佛向形容人的轉變。由此,禪宗“游戲三昧”是指隨緣而禪、證悟入道后,精神上達到自在無礙、圓滿自足又不失正定的境界。
宋代圓悟克勤則以“大機大用”表示“游戲三昧”。在克勤看來,“趙州吃茶”“雪峰輥毬”“禾山打鼓”“德山棒”“臨際喝”等這些游戲之姿的開示方式,“千差萬別會歸一源,可以與人解粘去縛”〔21〕,都是引導參禪者開悟自證的方便之舉,是“大機大用”。所謂“機”指禪機,“用”則是“真如”的顯現,“大機大用”是通過禪機而直指本心、體悟真如,是“不滯名相,不墮理性言說,放出活卓卓地”〔21〕。《碧巖錄》引了一則桐峰庵主與僧人的對答,僧人問桐峰庵主遇大蟲該如何,桐峰作“虎聲”來回應,而僧人“作怕勢”,僧又說桐峰是老賊,桐峰當仁不讓。克勤解釋二人的來往為“見機而作”,又引五祖的“神通游戲三昧,慧炬三昧,莊嚴王三昧”〔22〕來形容。禪機對應“游戲”,“用”對應“三昧”,如此,“大機大用”便與“游戲三昧”相通了。百丈懷海與黃檗希運的“戲”更為克勤贊嘆:
百丈一日問黃檗云:“什么處來?”檗云:“山下采菌子來。”丈云:“還見大蟲么?”檗便作虎聲。丈于腰下取斧作斫勢。檗約住便掌。丈至晚上堂云:“大雄山下有一虎,汝等諸人出入切須好看,老僧今日親遭一口。”〔22〕
同樣是機鋒敏捷,黃檗作“虎聲”來回應百丈的問題,百丈“作斫勢”接住了黃檗的“戲”,黃檗也隨機應變,便要打。而最后百丈的話,其實是對黃檗之語作了肯定。克勤認為兩人的戲有放有收,既“捋虎須”,又“收虎尾”。可見,在克勤這里,“游戲三昧”需要臨機應變,自由抒發,收放自如。
經臨濟一脈的發展,“游戲三昧”的內涵更加豐富寬泛。《無門關》引“趙州狗子”公案,學僧問“狗子是否有佛性”,趙州只答一個“無”字。佛門講“眾生皆有佛性”,而趙州卻說“無”。實際上,這里的“無”并非與“有”相對,而是不涉及“有無”的“無”。一個“無”字,直接將思路截斷,不再執著于追問有無佛性,由此證悟眾生平等,顯得更為透脫自在。如此,我們便能理解《無門關》中的“逢佛殺佛,逢祖殺祖。于生死岸頭,得大自在。向六道四生中,游戲三昧。”〔23〕“逢佛殺佛,逢祖殺祖”的用意是為了破除執著,指參禪者需要目空一切、違背常規,打破祖師設下的關口,才能真正大徹大悟。這是一種“絕后再蘇”的體驗,也是“游戲三昧”的境界,宗杲稱其為“臨機縱奪,殺活自由”〔24〕。
(三)“游戲三昧”的美學內涵
“游戲三昧”的立足點是無滯無礙,其本征特征便是自由。大悲妙云禪師有云:“生死去來,游戲三昧,天上人間,自由自在,明月清風,了無執礙”〔25〕。“游戲三昧”的狀態是純粹的,指不黏著而達到精神上的愉悅。這與西方美學中的“游戲”不謀而合。康德將審美自由稱為“游戲沖動”,朱光潛解讀時也說游戲“標志著活動的自由和生命力的暢通”〔26〕。席勒指出,“只有當人是完全意義上的人,他才游戲;只有當人游戲時,他才完全是人”〔27〕。游戲的狀態是人最本真的狀態,“游戲”的過程中需要虛空專一的審美心胸,方能達到真正的自由之境,宏智正覺有言:“虛通之門,游戲之徑”〔15〕,奇然智禪師亦云:“不生奇特之想,不起拘滯之情,游戲三昧,自然現前,不二門中,自由自在”〔28〕。當主體處在游戲之中時,無有掛礙,縱橫瀟灑,才能超越一切時空、因果和世間種種束縛,自證真如,進入大自由、大自在境界。從這一維度來看,“游戲三昧”的內涵與這種美學特質恰好契合。
“游戲三昧”具有無分別、絕對待的特性,是心性上的圓滿自足。禪門重視內心的自足,即證悟本心的真性,這就需要泯滅分別心。真凈克文謂:“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凈戒。趁出淫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29〕,“豬頭”“淫坊”“酒”和“凈戒”看似矛盾,實際上本無分別,佛法就在日常生活中,人的本心具足佛性,一切現成。黃檗希運就多次指出這樣的境界“本自具足”〔30〕“圓明遍照”“直下便是,圓滿具足,更無所欠”〔30〕,宏智正覺亦云:“本來具足,圓陀陀地”〔15〕。在“三昧”基礎上入不二法門,游戲世間,如此,便能實現生命的自在圓成之美。
綜上,中國禪宗的“游戲三昧”源于佛教的“游戲”,同時融合了莊子“逍遙游”思想。禪宗強調在現實生活中證悟入道,逐漸消解了佛教中的“神通”,并將莊子出世間的“游”引入日常生活中,“游戲三昧”成為一種隨緣運用的一行般若。禪者以“三昧”為基礎,自在拈弄,仿若游戲,無拘無束。這樣的游戲是純粹的、超功利的,其審美本質即是自由,具有無分別、圓滿自足的美學意蘊。
二、“游戲三昧”:從人生態度到創作心態
(一)“游戲三昧”的人生態度
禪宗“游戲三昧”的自由自足為文人士大夫提供了一種隨緣任性的人生態度。較早使用“游戲三昧”這一范疇的文人是王維,他在論畫時說:“手親筆硯之余,有時游戲三昧。歲月遙永,頗探幽微,妙悟者不在多言”〔31〕。“游戲三昧”不僅是繪畫之道,也可以看作是王維的人生態度。王維繼承了禪宗的“無念、無住、無相”,其詩云:“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31〕(《酬張少府》)。所以,當詩人至“水窮處”時,能夠愜意地“坐看云起時”。其實,早在魏晉時期,《維摩詰經》中恣意狂放的維摩詰形象對想要擺脫“世教”桎梏的文人名士就有著特別的意義。維摩詰游戲人間,“入諸淫舍”“入諸酒肆”,“在欲而行禪”,可謂是“火中生蓮華”,“辯才無礙,游戲神通”,這為文人調和出世與入世的矛盾做出了示范。《世說新語·言語》中劉尹問竺法深“何以游朱門”,竺法深回答:“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32〕。此回答頗具維摩意趣,即如果內心無染無著,那么“朱門”“蓬戶”便無分別。
到了宋人這里,“游戲三昧”的人生態度更為普遍和強烈。蘇軾屢次遭貶,經歷坎坷,對禪宗“游戲三昧”思想體會尤其深刻。他有詩云:“人間本兒戲,顛倒略似茲。惟有醉時真,空洞了無疑。”〔33〕(《和陶飲酒二十首》)人生如夢如幻,不如將此當作一場游戲。《戲答佛印》中有句:“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豬待子瞻”〔33〕,“破戒”的自在更加明顯。東坡所說的“游戲”“兒戲”并不是普通意義上的玩世不恭,更多的是與佛教相聯系,是一種解縛之后的愉悅自在。“游戲三昧”的心態在黃山谷的詩中也隨處可見,如“出門一笑大江橫”〔34〕(《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會心,為之作詠》)的會心通達,“胸次九流清似鏡,人間萬事醉如泥”〔34〕(《戲效禪月作遠公詠》)的灑脫無羈。黃山谷有一首《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
巴俗深留客,吳儂但憶歸。直知難共語,不是故相違。東縣聞銅臭,江陵換祫衣。丁寧巫峽雨,慎莫暗朝暉。〔34〕
黃庭堅曾因元祐黨禍而被貶入蜀,居蜀地八年之久。這首詩寫于出川東歸、途徑巫山縣之時。巫峽一帶天氣晴雨不定、變幻莫測,正如同人生的反復無常。他卻以“戲”為標題,用幽默輕松的口吻將這些苦難說了出來。
可見,禪宗“游戲三昧”已成為詩人的安身立命之道,詩人以隨緣自適的“游戲”心態超越功利得失,擺脫現實苦悶,獲得自我解縛的愉悅,從而達到了廣闊而自由的生命境界。
(二)“游戲三昧”對傳統創作態度的沖擊
“游戲三昧”對詩人的人生態度和審美情趣有著深刻影響,在其創作心理上也會有所表現。中唐時期,禪宗大興,皎然有大量以“戲題”“戲贈”“戲作”等為標題的詩歌,可見其作詩目的是“戲”。他的詩大多輕松放曠,不少詩句中含有“狂”和“笑”字,如“才子會須狂”〔35〕(《戲呈薛彝》),“笑看風吹樹”〔35〕(《出游》),“笑向閑云似我閑”〔35〕(《戲題松樹》),“大笑放清狂”〔35〕(《戲作》)等。皎然所作的聯句更顯肆意狂放,如《水堂送諸文士戲贈潘丞聯句》“雅韻雖暫歡,禪心肯拋卻”〔36〕,《七言樂語聯句》“苦河既濟真僧喜(李崿),新知滿座笑相視(顏真卿)。戍客歸來見妻子(皎然),學生放假偷向市(張薦)”〔35〕。這樣的聯唱詩是友人之間的唱和娛樂、玩笑調侃,如果以“溫柔敦厚”的詩教標準來衡量,很難說是“有用”。皎然在《詩式》中提出“詩有五格”,把“不用事”奉為第一格,認為詩是詩人情感的自然流露,作詩不宜過于斟酌字句、競用僻典,這應當源于皎然隨緣自適的“游戲”心態。
后來的權德輿等人循此思路進一步推進了詩歌的游戲化,蔣寅先生指出:“正因為權德輿集團與浙西文士集團的這種血緣關系,兩者之間形成了實際上的承傳關系,浙西聯唱詩會中的游戲傾向作為基因最終在權德輿等人的臺閣酬贈中得到發育,演化成風行一時的游戲詩風”〔37〕。權德輿與皎然、陸羽等人有較為深入的交往,難免會受到“游戲”為詩的影響。其詩《離合詩贈張監閣老》便具有濃郁的“游戲”色彩,既表達出對友人的不舍之情,同時每個首字去掉部首組合起來又是“思張公”的意思。此外,他還做過很多如藥名詩、卦名詩、星名詩等一系列“游戲”意味十足的創作嘗試。
宋代文人在詩歌創作上更是將“游戲”之心發揮到了極致。蘇軾多次明確表示“游戲三昧”的詩歌創作態度,在《戲和程正輔一字韻》的自跋中曰:“此詩幸勿示人,人不知吾儕游戲三昧,或以為詬病也。”〔33〕在《聞辯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以詩戲問》中說:“借禪以為詼”〔33〕,可見,蘇軾是有意識地借“游戲三昧”為詩法。他曾評價黃庭堅“以真實相出游戲法”〔2〕(《跋魯直為王晉卿小書爾雅》)。禪家主張在日常生活中高度入定而又以游戲心態對待世間萬物,隨緣乘化,如此便能進入覺悟的境界。“真如”是不能言明的玄妙,禪師往往以“大好燈籠”“庭前柏樹子”等不合理路的回答來說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明顯答非所問。這給了詩人一個啟示:要獲得“真實相”,無需苦心經營,而要在深通詩歌創作的奧妙、規律的同時,以“游戲”的方式進入詩境。
實際上,與蘇軾類似,宋代許多文人已經有意識地以“游戲”的態度對待詩歌創作。謝逸有詩云:“吾人共閑燕,翰墨相娛嬉”〔38〕(《與諸友分韻詠古碑探得羅池廟記以池字為韻》),“賦詩非不工,聊以助游戲”〔38〕(《游西塔寺分韻得異字》)。鄒浩也說:“從來游戲常三昧,出語縱橫無忌諱”〔39〕(《代書寄清老》)。這些都表達了作詩要隨意而發、“游戲”為之的觀點。
綜上可知,“游戲三昧”既是一種人生態度,又進而內化為詩人的創作態度。在儒家傳統的文藝觀念中,詩歌常常被賦予“載道”的作用。隨著詩人接受禪宗思想,“游戲三昧”突破了傳統創作理念,無所拘執的創作態度使得創作主體的自身價值得到凸顯,其豐富的情感得以展現。
三、“游戲三昧”對詩學理論的影響
禪宗“游戲三昧”的人生態度被引入詩歌創作后,對詩學理論也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構思、風格、表達等方面都有明顯表現。
(一)詩歌構思:揮灑自如、不可湊泊
“游戲三昧”的高妙之處就在于否定了對外境的執著,剎那間明心見性,獲得心靈上的解脫。作詩和參禪都講求真心妙悟,所以“游戲三昧”思想直接影響了詩歌創作的構思方式。詩人即興抒寫、了無掛礙,由此獲得精神愉悅,達到一種自由的狀態。
詩僧惠洪提出“游戲翰墨”說,即以認真但不執著的游戲態度進行創作,從而進入圓融無礙的境界。他多次表示詩歌是隨緣而作,“非有意于工詩文,夙習洗濯不去,臨高望遠,未能忘情,時時戲為語言”〔40〕(《題自詩》),“于文字未嘗有意,遇事而作,多適然耳”〔40〕(《題珠上人所蓄詩卷》)。
那么,創作時應該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態呢?從惠洪對黃庭堅的評價中可以窺見一二:
山谷在星渚,賦道士快軒詩,點筆立成,其略曰:“吟詩作賦北窗里,萬言不及一杯水,愿得青天化為一張紙。”想見其高韻,氣摩云霄,獨立萬象之表,筆端三昧,游戲自在。”〔41〕
這是說創作構思時也當如“游戲”一般,無心牽掛、自在灑落、不拘一格。惠洪還明確將“游戲翰墨”與“作大佛事”并舉,從本質上貫通了詩學與禪學:
東坡居士,游戲翰墨,作大佛事,如春形容藻飾萬象。……游戲翰墨,撾雷翻云。偶寄逸想,幻此沙門。〔40〕
“游戲三昧”促使詩人創作時心無掛礙,揮灑自如;而詩人妙觀逸想,以“游戲”的態度對待詩歌創作,無滯無礙,便能進入正定三昧的境界。由此,“游戲翰墨”便進入了佛事體系,也為禪僧參與詩學活動賦予了合理性。
此后,金人李純甫兩次提到“游戲三昧”與翰墨文章的關系:“道冠儒履皆有大解脫門;翰墨文章亦為游戲三昧”〔42〕(《重修面壁庵碑》),“翰墨文章,亦游戲三昧;道冠儒履,皆菩薩道場”〔42〕(《程伊川異端害教論辯》),意思是:作詩為文也可以使人獲得解脫,進入“游戲三昧”的大自在狀態。李純甫認為“關鍵不落詩人詩”“字字皆以心為師”〔43〕(《為蟬解嘲》),詩歌是真情真性的顯露,這種“惟意所適”恰是參禪悟道的境界。屏山之論無疑是對金代詩壇詩禪又一次深刻會通的精辟總結。
“詩禪一體”的觀念在釋英的《白云集》也可以見到,趙孟若在為《白云集》所作的《序》中說:“詩禪從三昧出,不可思議。拈花微笑,夢草清吟,曷常有二哉。……涉此地后有此詩,有此詩即悟此禪。”〔44〕“拈花微笑”是佛家公案,“夢草清吟”化用了謝靈運“池塘生春草”句的典故。趙孟若將“三昧”作為詩禪互通的關鍵,認為通過詩思和禪悟都可以進入“三昧”狀態,達到從心所欲、任心自在的境界,如釋英所說,“一點梅花髓,三千世界香”〔44〕(《夜坐讀珦禪師潛山詩集》)。詩論家們從構思這一維度將“游戲三昧”之境與詩境溝通起來,“游戲三昧”的空靈無礙也促進了隨意拈筆、揮灑自如的創作理念的形成。
(二)創作風格:自然天成、渾然無跡
“游戲三昧”是參禪悟道的理想境界,禪宗證得“游戲三昧”,即達到無著無住的自由境界;詩人悟得“詩家三昧”,也會進入自然渾成的境界,達到詩歌創作的極佳狀態。在這一點上,詩與禪是相通的。而要達到這種境界,就須回歸自性的“真”,即無有掛礙,不受形式規則的束縛。在此,“游戲三昧”任運隨適、自然而然的思想給了詩論家們很多啟發。
陸游在禪宗“游戲三昧”的基礎上提出了“詩家三昧”,強調詩歌創作應自由自在、自然渾成。他在《九月一日夜讀詩稿有感走筆作歌》中講述了自己學詩開悟的過程:起初“學詩未有得”,自南鄭從軍后,生活發生變化,其詩境也發生了轉變,不再“乞人殘余”,而是“詩家三昧忽見前,屈賈在眼元歷歷。天機云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45〕。結合陸游的《示子遹》和《文章》來看,陸游原本寫詩傾向“欲工藻繪”,沒有領悟到“工夫在詩外”。悟得“詩家三昧”后,發現“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45〕,認識到文章不應囿于語言技巧,無需刻意雕琢,只須信手而作。
比陸游稍早一些的王庭珪也反對斧鑿的痕跡,其詩云:“好詩渾厚如金玉,妙質勿令斤斧侵。要識筆端三昧力,夜深山水自成音”〔39〕(《彭青老好談禪喜作詩西寧詩有謀身之語借其語激之》),明確強調詩的渾成和自然。沈作喆在《寓簡》中云:“東坡表啟樂語中間有全句對,皆得于自然,游戲三昧,非用意巧求也。”〔46〕張元幹評蘇養直的詩時也說:“平生得禪家自在三昧,片言只字,無一點塵埃。”〔47〕禪宗“游戲三昧”的介入強化了中國詩學對于自然渾厚風格的追求,詩人以“游戲”之心進行創作,不刻意雕琢修飾,便會營造出一種自然清淡、渾然無跡的詩境。
(三)詩句表達:戲謔詼諧、通俗活潑
“游戲三昧”的自在性還表現為突破語言技巧的束縛,形成一種戲謔詼諧、通俗活潑的語言形態。吹萬禪師云:“最初參尋,雖借語言入,又不可執泥語言也。”〔48〕這是禪家基本的語言觀,禪師常常以不合常規的方法說禪,用諸如“屎里蛆兒”“干屎橛”等污穢之詞回答“什么是佛”的問題,看似荒唐,實際上是“游戲”說法、寓莊于諧,啟示弟子莫要執著掛礙,因為佛性就在日常生活中。慧日文雅的《禪本草》、湛堂文準的《炮炙論》都是寓禪理于文字游戲中。圓悟克勤開悟時作詩云:“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里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只許佳人獨自知”〔19〕,詩中情境顯然不符合戒規,卻在插科打諢、幽默戲謔的表達中破除了語言束縛。
禪宗“打諢而出”的表達方法被詩人借用并轉化為詩法。宋代黃庭堅作詩便擅用這種“寓莊于諧”的方式,如《戲贈世弼用前韻》云:“盜跖人肝常自飽,首陽薇蕨向來饑。誰能著意知許事,且為元長食蛤蜊”〔34〕。“食蛤蜊”與禪宗常說的“吃茶去”相似,深得禪機鋒妙,看似無意,實則表達出了詩人自由瀟灑的心性。江西詩派李商老的“風廊謔談僧,蒲團尋老衲”〔49〕邏輯顛倒,透露出詩人輕松幽默的心態和活潑的筆意。韓駒更是將“游戲”筆法運用得出神入化,《次韻黑氈歌》將物擬作人,不直接寫黑氈,而稱其為黝奴,頗具趣味性;《分寧大竹取為酒樽,短頸寬大,腹可容二升而漆其外,戲為短歌》《題大姑山》等詩也都是其“游戲”文字的表現。幽默戲謔的表達使得詩歌語言愈加通俗活潑,不僅增加了語言材料,也拓展了審美想象空間。
明代王世貞論詩講求不避俗語,并借“游戲三昧”傳達出這一觀念:
昨歐楨伯訪海上云:某謂于鱗近過一國尉園亭賦詩,落句云:“司馬相如字長卿”,鄙不成語乃爾,定虛得名耳!此正是游戲三昧,似稚非稚,似拙非拙,似巧非巧,不損大家,特此法無勞模擬耳。〔50〕
在王世貞看來,李于鱗此詩看似淺俗,實際上是深諳為詩之道而以游戲出之。胡應麟講求游戲文字、不避俗語,“其游戲三昧,則有巧語,有諢語,有俗語,有經語,有史語,有幻語。此正弇州大處,然律以開元軌轍,不無泛瀾。”〔51〕他將唐、明并論,認為明中葉詩壇并不遜于盛唐詩壇,原因就在于明中葉詩壇風格多樣,不拘格律,境界大開。清代趙翼說:“文人無所用心,游戲筆墨,東坡口吃詩亦同此伎……固不必議其纖巧,近于兒戲也。”〔52〕可以看出,詩論家將“游戲三昧”引入詩學的同時,也接受了“游戲三昧”帶來的語言俚俗化。
到了清代,葉燮《原詩》云:“詩家總持三昧之門也”〔53〕,結合上下文來看,這里并不是要論述詩禪關系。再如,翁方綱的《七言詩三昧舉隅》、王漁洋的《唐賢三昧集》等都以“三昧”為書名,這里的“三昧”表示的是詩歌的真決。可見,“游戲三昧”已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喻指詩歌奧妙訣竅的重要詩學范疇。
四、結語
中國禪宗主張“游戲三昧”,追求“去執”后心靈上的絕對自由和圓滿自足,具有特別的審美意蘊。“游戲三昧”不僅影響了文人的心態和生活,也為文人以游戲翰墨的方式實現人生超越提供了理論支持。就構思而言,“游戲三昧”的愉悅自由境界和詩歌構思的自如境界是相通的,“游戲三昧”要求詩人不受拘執、信手拈弄,從而達到揮灑自如的境界,受此影響,詩人進行構思時,對世間萬物的觀察也變得隨意自適,形成了“隨意拈筆”的創作理念;在風格方面,“游戲三昧”強調隨緣自適,促使詩人形成自然天成、渾然無跡的詩風;在表達方面,“游戲三昧”啟發詩人擺脫語言文字的牽絆,筆意靈活暢快,幽默詼諧,詩歌語言由此逐漸幽默化和通俗化。
那么,“游戲三昧”是否代表毫無規范,將創作視為兒戲呢?實際上,“游戲三昧”是自由與法度的統一。禪師追求的是自性的開顯,“游戲”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方式。《祖堂集》謂:“自性清凈,謂之戒體”〔54〕。洪州禪在承繼“游戲三昧”的同時,也講“律即是法,不離于禪”〔19〕。這說明禪家并不是不講律制,而是將戒律內化于心法中,“自性”本身便是一種自律。呂澂先生指出,“禪家如此一門深入而透徹全體,并不比片面估值,動轍凝滯,由此便有了‘直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這說明禪家生活原是嚴肅、謹慎,并沒有放任的意思”〔55〕。
真正禪者的游戲自得是在正定的基礎上呈現出天真活潑的生命情趣,“三昧”是“游戲”的內在規范,專注才能得自在。惠洪在提出“游戲翰墨”說的同時,便關注到“游戲三昧,互為賓主”〔40〕(《題珠上人所蓄詩卷》)。“游戲”與“三昧”相輔相成,“游戲”是獲得審美快感的方式,是活力的顯現;“三昧”是“游戲”的基礎,只有修養深厚、精神專注,才可能獲得充分的創作自由。禪宗“游戲三昧”為詩人創作提供了重要啟示。詩人始終在積極尋求詩歌創作中“法度”與“自由”的平衡,所謂任運自適、隨心所欲,并不是要違背藝術內在規律,而是指不過分拘泥語言、形式等外在的束縛。
不過,詩人如果離開禪的文化背景,沒有把握好“游戲三昧”與藝術規則的關系,過度“游戲”,則很有可能“玩物喪志”,使得詩作失去生命本真之嚴肅和藝術本真之嚴肅,產生狂蕩之流弊。因此,藝術家在自在揮灑的同時,也要遵守一定的藝術規律。
總的來說,禪學中“游戲三昧”的參禪理念在詩禪交互的背景下進入詩歌創作和詩學理論后,深刻影響了詩人的審美追求以及創作理念,融合禪家“游戲三昧”理念的中國詩學因此自逸通達,透露出活潑的生命力,也成為詩人創作臻于自由之境的重要方法。
參考文獻:〔1〕
元好問.狄寶心,校注.元好問詩編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1:534.
〔2〕蘇 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6:1865,2195.
〔3〕釋道潛,著.孫海燕,點校.參寥子詩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280.
〔4〕吳汝鈞.游戲三昧:禪的實踐與終極關懷〔M〕.臺北:學生書局,1993:160.
〔5〕龔 雋.略論禪風中的“游戲三昧”與自性戒〔J〕.佛學研究,2013,(22):25-37.
〔6〕周裕鍇.文字禪與宋代詩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83.
〔7〕張培峰.佛教心境論與藝術本源思想〔J〕.蘭州學刊,2015,(7):50.
〔8〕陳星宇.禪學與文學意趣的會通——“游戲三昧”與蘇軾詩歌〔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14,(3):64-68.
〔9〕龍 樹,造.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C〕∥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5冊).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1990:110,110.
〔10〕慧 遠.維摩義記〔C〕∥大正新修大藏經(第38冊).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1990:440.
〔11〕鳩摩羅什,譯.妙蓮法華經〔C〕∥大正新修大藏經(第9冊).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1990:55.
〔12〕求那跋陀羅,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C〕∥大正新修大藏經(第16冊).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1990:480.
〔13〕僧 肇,撰.注維摩詰經〔C〕∥大正新修大藏經(第38冊).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1990:371.
〔14〕陳鼓應,注譯.莊子今注今譯〔M〕.北京:中華書局,1983:136,160,576,576,539,94,18.
〔15〕宏智禪師廣錄〔C〕∥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8冊).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1990:98,100,17.
〔16〕慧 能,著.郭 朋,校釋.壇經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2021:33.
〔17〕高峰原妙禪師禪要〔C〕∥卍新纂續藏經(第70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705.
〔18〕宗 寶,編.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8冊).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1990:358.
〔19〕釋普濟,著.蘇淵雷,點校.五燈會元〔M〕.北京:中華書局:1984:532-533,136,1254,166.
〔20〕釋惠洪,著.呂有祥,點校.禪林僧寶傳〔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196.
〔21〕圓悟佛果禪師語錄〔C〕∥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7冊).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1990:777,777.
〔22〕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C〕∥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8冊).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1990:210,211.
〔23〕宗 紹,編.無門關〔C〕∥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8冊).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1990:292.
〔24〕蘊 聞,編.大慧普覺禪師語錄〔C〕∥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7冊).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1990:922.
〔25〕大悲妙云禪師語錄〔C〕∥嘉興大藏經(第38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450.
〔26〕朱光潛.西方美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375.
〔27〕席勒,著.審美教育書簡(第十五封信)〔M〕.馮 至,范大燦,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80.
〔28〕奇然智禪師語錄〔C〕∥嘉興大藏經(第36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564.
〔29〕賾 藏,主集.蕭萐父,呂有祥,點校.古尊宿語錄〔M〕.北京:中華書局,1994:861.
〔30〕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C〕∥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8冊).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1990:379,380.
〔31〕王 維,撰.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489-490,120.
〔32〕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M〕.北京:中華書局,2011:97.
〔33〕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2:1888,2654,2167,824.
〔34〕黃庭堅,著.劉 琳,李勇先,王蓉貴,點校.黃庭堅全集〔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114,273,132,1181.
〔35〕釋皎然,撰.杼山集〔C〕∥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71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795,801,828,829,868.
〔36〕彭定求,編.全唐詩〔M〕.北京:中華書局,1960:8881.
〔37〕蔣 寅.大歷詩人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1995:425.
〔38〕上官濤,校勘.《溪堂集》《竹友集》校勘〔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1:18,18.
〔39〕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21冊卷1236)〔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3971,16849.
〔40〕釋惠洪,著.釋廓門貫徹,注.張伯偉,等,點校.注石門文字禪〔M〕.北京:中華書局,2012:1520,1522,1187-1188,1685.
〔41〕釋惠洪.冷齋夜話〔C〕∥張伯偉,編校.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48.
〔42〕閻鳳梧,主編.全遼金文〔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2617,2622.
〔43〕薛瑞兆,郭明志,編纂.全金詩〔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159.
〔44〕釋 英.白云集〔C〕∥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2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666,669.
〔45〕陸 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803,4469.
〔46〕沈作喆.寓簡〔C〕∥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4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137.
〔47〕張元幹.蘆川歸來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77.
〔48〕吹萬禪師語錄〔C〕∥嘉興大藏經(第29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509.
〔49〕李 彭.日涉園集〔C〕∥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22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622.
〔50〕王世貞.藝苑卮語〔C〕∥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1063.
〔51〕胡應麟.詩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61-362.
〔52〕趙 翼.甌北詩話〔C〕∥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343.
〔53〕葉 燮.原詩〔C〕∥王夫之,等,撰.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610.
〔54〕靜筠二禪師,編撰.孫昌武,等,點校.祖堂集〔M〕.北京:中華書局,2007:196.
〔55〕呂 瀓.中國佛學源流略講〔M〕.北京:中華書局,1979:378.
The Zen Connotation and Poetic Significance
of “Playing in the Joyous Samadhi”
WANG Yue, ZHANG Yong
Abstract: “Playing in the joyous Samadhi” in Zen refers to the spiritual attainment of being free and unhindered after meditation, with the aesthetic implication of no differentiation and full self-satisfaction. Consistent with poets’ aesthetic ideal of pursuing spiritual freedom, the Zen Buddhism style of “playing in the joyous Samadhi” was adopted as the theory of poetics and thus influenced poets’ creative attitudes in three aspects. On poetic conception, it motivates poets to break through restraints. On poetic style, it promotes poets to be natural and traceless. On the expression, the language of poems is gradually humorous and popularized. The great freedom of “playing in the joyous Samadhi” is similar to the poetic realm of the unpredictable. On this basis, “playing in the joyous Samadhi”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n important poetic category signifying the secrets of poetry.
Key words: Zen; “playing in the joyous Samadhi”; spiritual freedom; poetic significance; poetic category
(責任編輯:武麗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