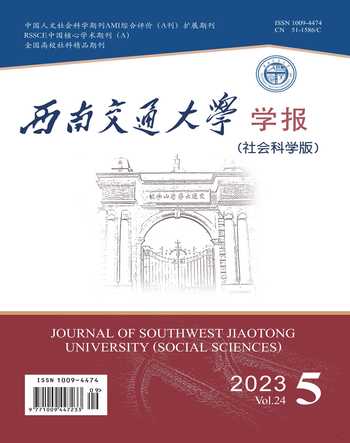從黑格爾到阿甘本:辯證法的虛無主義問題及其解決路徑
摘 要: 黑格爾辯證法工作的出發點是解決哲學二元論中蘊含的“虛空”和虛無化問題,完成主體意識對“虛空”自為的生成性轉化。但阿爾都塞認為這種轉化以“無主體進程”的本體論形式保留了虛無,并可以在霍布斯的國家主權機器及其去主體化的主體程序中找到相應的政治實踐形式。阿甘本據此挖掘出辯證法內含的行動法則與暴力機制,指出它帶來了自由行動的困境,而解決辦法唯有開啟有關“自我—觸感”和非專有之愛的共同體經驗。黑格爾到阿甘本這條思想脈絡的發展,顯示了黑格爾的“絕對者”概念對海德格爾及其后來的虛無主義批判的決定性影響,他們共同的解決路徑是建立新型的行動共同體。
關鍵詞: 辯證法;虛無主義;黑格爾;阿爾都塞;阿甘本;權力機器;自我—觸感;絕對者
收稿日期: 2022-09-19
基金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德勒茲與法國當代文論研究”(22BZWB030)
作者簡介: 陳 琦,復旦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當代法國哲學研究,E-mail:18395395950@163.com。
海德格爾曾提出,虛無主義作為西方形而上學的歷史性階段,是在黑格爾處發展至頂峰。虛無主義的典型癥候是世俗與神學、虛無與合法化的不可區分,而黑格爾辯證法恰恰是對意識經驗科學與絕對有神論的混淆。“‘上帝死了’……唯獨沒有‘不存在上帝’的意思”〔1〕,“自在的上帝”經歷漫長的意識勞作過程轉化為可觸及的“自為的上帝”,于是絕對精神就作為一種存在的神學取代了上帝,它確證存在者之存在于主體面前的絕對顯現,并要擔保主體對世界對自身的解蔽能力。海德格爾說這種擔保正是虛無主義問題的根源所在,因為它使沒有根基成為一種新的根基——它意味著通過對自我不斷的抽離和挖空來重新占有自身,意味著一個對否定性進行肯定化生產的無限循環、辯證搖擺的過程:一方面設定了一個可支配、現成在手(Zuhandenes)的全面內在化的世界;另一方面,設定世界的意識機器因只在于維系自身運轉的絕對可行性,所以注定淪為除自身以外別無他物實在的虛無的籌劃、協商和計算。而這正是法國哲學所謂“去政治化”的政治虛無主義時代現況的先聲,旨在響應海德格爾的呼吁,即當前政治實踐如要克服虛無化,需要重新審視黑格爾主義的影響。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有阿爾都塞和阿甘本,他們指出黑格爾哲學起初恰恰是要克服二元論所帶來的西方哲學的“虛空”。
一、黑格爾的虛無主義批判與辯證法的生成性轉化
黑格爾早在其青年神學論階段就對虛無主義的問題做過初步論述。他提出猶太教的道德律令是康德二元論的同謀,因它制造了生命體內外的對立和分裂,限制了生命力量的發展和統一。他也針對猶太教的法律法規及其懲罰手段做了剖析,指出這種法規是否定生命的異己客體、是至高無上的強權,它通過對懲罰措施的簡單重復建構偶然性的正義;另一方面,犯人接受懲罰即他剝奪了別人什么東西他也將遭受同等苦難,這種懲罰非但不能使他與他者、與法規、與自我對生命精神的背叛達成和解,反而進一步加劇了分裂,“那個異己的力量……這個敵對的存在一經懲罰了他便不復對他起作用……因為犯法者永遠把自己看作犯法者……他的這種現實與他對于法律的意識是互相矛盾的”〔2〕。而后在《精神現象學》中他重提了這種強權邏輯,說這是一種主奴意識的暴力循環,是一種普遍倫理精神的毀滅,致使倫理共同體分崩離析成諸多為他的、被動的、“空”的個別性。“空”即是對虛無狀態的描述,黑格爾也將其命名為“法權狀態”,他在原子論那里找到了始作俑者。
黑格爾認為近代原子論和康德“物自體”共同的問題在于它們理論的根基處都存在一種“空”,而辯證法的工作正是要填滿這種“空”。“空”是現成直觀的自在之在,是完全外在于實體、只為實體運動提供環境條件而并不能推動實體運動的“純粹空間”。這種觀點是相對古代原子論的曲解甚至倒退,因為古代哲學家恰恰認識到虛空是萬物運動的推動者,只不過這種認識尚且粗淺:“他們誠然已經知道推動者是否定的東西,但還沒有了解它就是自身(Selbst)……看起來似乎是在實體之外進行的……事實上就是實體的行動,實體因此表明它自己本質上就是主體”〔3〕。黑格爾說虛空是主體意識發展過程的必經環節,是通過對自身的否定、排斥而自我制造的虛空,是個體最初的直接規定性;在否定性運動將直接規定性不斷外化并發展為規定性一般的同時,個體有限的意識行動也發展為無限的“行動一般”,并將其建立為自身的普遍性實存。這意味著作為推動力的虛空是主體或實體的自為之力,既是否定性的斥力也是建構性的引力,建構了個體對自身而言絕對的確定的“一”,并同時將自身展開為無限的“多”的共同體。所以黑格爾反對原子論,因為它導致實體運動受控于偶然決定論,喪失了意識與對象、主體與實體之間統一的可能性。辯證法對虛空的填滿實際是對二元論的填滿,通過虛空自身對自身的轉化,將消極分裂的自在之“空”轉化為積極能動的生成之“空”,是一種自我填滿、自我充盈和自我實現。
阿甘本曾評價說黑格爾在這里使用的實際是一種時間的延遲機制,這種時間機制的雛形最早由亞里士多德提出,阿甘本也將其概括為“時間化裝置”或“語言學裝置”:“它將存在劃分成本質和實存,并將時間導入存在,這種裝置是語言的工作。它將存在者主觀化為主體(hypokeimenon),這是言說自行實現并讓裝置運轉起來的根基”〔4〕。亞里士多德借由對行動概念的界定,即行動是對人倫理本性的“現實化”或實現(entelecheia),給出了“主體化=現實化”的理論雛形。該等式設定了意識對象是有待實現的可意識之物、是主體實在化進程的一個環節,它將康德意義上被動的既定存在物轉化為能動的自我行動。這種行動在亞里士多德那里既是人的政治行動也是他的言說行動,言說是為聲音錨定一個指稱對象或開啟一段話語情境的“命名”時刻,而“命名”實際是一種語言的預設結構、一種否定性的時間結構,它默認言說行動因為時間間隔永遠無法切中實在對象,它永遠在言說“已經不是”的東西。到了黑格爾那里,這種時間間隔就被定義為虛空,它可以通過否定之否定的揚棄運動轉化為生成性的歷史時間,并且只在終結的時刻才真正開啟。
“借助時間的方式,實在被等同于本質。也就是說,存在與實在之間的同一性關系是一個歷史—政治任務”。〔4〕正如亞里士多德的行動論建構了人如何行動以及何以為人的古典政治秩序,辯證法的轉化工作也不外如是,“為了要使自己的潛在性成為現實性,意識必須行動”〔3〕,它強制性地規定了人必須行動,潛能即是為了在行動中耗盡自身,且行動的瞬間注定落入這個生成性的裝置。這正是后來阿爾都塞進行黑格爾批判時的關鍵切入點,他指出黑格爾的初心是完成對“虛空”的生成性轉化,但實際的情況是虛空只是被轉化而未被消除、分裂被延遲而未被終結,于是虛空和分裂意味的死亡與暴力就不可能結束,且否定性、內在性的轉化反而讓人無路可逃。這種結構后來被阿爾都塞用來描述霍布斯的國家主權機器。
二、阿爾都塞論霍布斯主權機器與辯證法的虛無化傾向
后期阿爾都塞在霍布斯主權國家機器中發現了可對他前期提出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進行修正的權力構成形式。它不是封閉的“雙重鏡像”系統,要求承認或臣服于特定的大他者或“大主體”(Sujet),而是一套“去主體化”的主體化程序。這套程序最終幫他錨定了虛無主義的總問題。
居伊·德波曾用“景觀社會”的概念來概括現代性的典型癥候。他提出“分裂就是景觀的全部”〔5〕,這是說當下社會的再生產不是對產品或生產資料的再生產,而是對景觀的再生產;人已失去對產品的占有使用權,不再作為傳統意義上的生產者而是消費者。因此人唯有通過消費即自我分裂和掏空的方式使自身作為景觀展示的一部分,而無法從生產環節中獲得自己特定的主體性身份,所以景觀社會下的主體是純粹分裂、去主體化的主體。阿爾都塞在霍布斯那也發現了這種主體,“給定的本質向自己的對立面轉變,主體生產出了一種與自身相對立的秩序”〔6〕,其中個人不是被一個具體的主體化程序所控制,而是同時受到兩股對立勢力或兩種假設的可能性的拉扯。程序是預防性和調節性的,是為了在兩個對立的可能性之間取得辯證平衡,它的運作或許沒有確定的結果,因其目的只在于為自身持續的辯證運動做擔保。這恰好對應了早期阿爾都塞在黑格爾辯證法思想中發現的虛無主義傾向。
阿爾都塞說黑格爾的邏輯學是一種“過程”的哲學,主體的絕對性只在它展開自身、顯現自身的整個過程的絕對性當中實現,換言之,拋開整個過程它什么也不是,所以辯證法實際是一種“無主體的進程”:“這個主體就是辯證法……否定之否定的運動。無主體的異化過程(或辯證法)只不過是被黑格爾認可的唯一主體”〔7〕。“無主體的進程”誠然是對超驗性主體及其意向性結構所意味的自我特權的瓦解,早期阿爾都塞將其視為對傳統主體哲學的顛覆。然而通過研究霍布斯國家問題,他發現現代國家機器恰恰是“無主體進程”的翻版,這臺機器的卓越之處在于它反起源、反發生學和演繹學,它首先承認人理性的孱弱無力也即主體和主權合法性基礎的不確定性——其中自然法不是真正的法則、不做定性,不要求對現實經驗的絕對切中,它是以“假言命令”(impératif hypothétique)的形式對可能性及其實現條件進行計算的功能機制,而可能性就包括計算失敗的風險的可能性。因此它意味著無論理性如何搖擺、內戰是否發生,人最終都無法逃脫立約行動的必然命運。相應地,社會契約保障的也不是統一國家理性而是實現自身的可能性條件,這導致現代國家主權淪為一種光學幻象,“主權者是演員(Persona)……這個人的統一性創造了被代表者的統一性”〔6〕,不存在統一的政治實體而唯有統一的代表權;社會契約僅在建立的一瞬間有效,人民即主權者處在不穩定的自然狀態內,用霍布斯的話說,“議會一組成,人民就解散”〔8〕。因此主權機器所征用的即是作為“無主體進程”的辯證法,它的運作機制是一種語言的預設、表象游戲,無法真正切中現實,去主體化也去實體化。
阿爾都塞曾分析說這源于辯證法對人行動法則的規定。行動被黑格爾定性為一種“勞作”,而“勞作”的目標是為人類最初的罪行做贖還,這個罪行就是亞當夏娃吃下可以打開心眼的禁果并自此開啟人類認識活動的歷史事件。但阿爾都塞認為不是吃下禁果使人犯罪,真正的罪行發生在人伸出手的那一刻——伸手試圖觸及蘋果的動作預設了知識的可觸及性,即德里達《觸感》(Le toucher)中所謂的“在沒有對它有所觸及的情況下要求著觸及”〔9〕。黑格爾意義上的行動昭示著處在西方形而上學根基的“觸感中心主義”(haptocentric metaphysics),它首先規定了對象和認識的分離,意味著人行動與自身存在之親密性在最初的喪失——“既定物一旦成為被認識的對象,就會把自己顯現為與自身相分離并且與自身相不同的東西……這個世界進入了分裂的狀態”〔7〕。意識的漫長“勞作”無外乎是重復伸手摘取蘋果,重復分裂與和解,以及對觸及活動及可觸及法則的強調。因此人與其生命分裂的罪行既無法從猶太教法律的懲罰活動中得到解脫,也無法在辯證法的內在性循環中得到真正的寬恕——循環保障的不是最終的和解而是這個循環的運行本身,而運行需要分裂的罪行作為支撐。阿甘本在黑格爾與阿爾都塞對原罪論的洞見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辯證法虛無化導向司法暴力機制,其中行動被建構為一臺自動運轉的“人類學機器”并帶來了“自主=自由”的假象,而要逃脫這臺機器的控制,唯有開啟全新的生命觸感活動。
三、阿甘本對虛無主義的解決:行動機器的司法困境與“自我—觸感”的突圍
(一)辯證法的行動機器與虛無主義暴力——以奧斯維辛集中營事件為例
阿甘本依然是在亞里士多德那里發現了行動法則作為“人類學機器”的初級形態。亞里士多德將人類活動區分為以外在產品為目的的“制作”和以實現自身為內在目的的“行動”,而它們最終都作為一種“勞作/功效”(ergon)活動達成一致。阿甘本說“功效”是古希臘的一種權力裝置,“一種分而治之(divide et imopera)的方式,讓生命體成為結合了一系列功能性能力和層面的等級制關系體”〔10〕,它把行動區分成現實與潛能、靈魂與身體、主人與奴隸、屬人與非屬人兩極,通過建構其間的生產轉化關系實現整個人類生產生活系統的自動化運作。“自動”是兼有自動和被動兩種屬性、從屬和統治兩種正義、以己之動而為他物運動的活動,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好的公民不僅要學會統治、也要學會服從,這與柏拉圖從自我規訓到規訓他人的“治理術”一脈相承。行動中的人是“自主”的,但“自主”不是做自己的主人,唯有落入行動的法則系統,人才有可能掌握主動權,這發生在目的實現、潛能“現實化”并耗盡其他一切可能性的一刻。也就是說,“功效”設定了一臺必須持續運作的行動機器,行動的過程即是對普遍倫理規定進行生產和還原的過程,它給出了人類何謂的倫理學答案。
這臺人類學機器奠定了傳統共同體主義的內在性原則。個人的意識、實踐和社會的政治、技術、經濟同處在一個內循環的生產機制之下,完全透明且高度功能化,個人以對自我主體性的生產、分裂和規訓來供社會整體的對他的使用和分配。今天內在主義和功效論是法國哲學思考的關鍵難題,而阿甘本認為它的肇因是亞里士多德的行動論和黑格爾悲劇論的改造。黑格爾說悲劇藝術是絕對倫理精神在具體生命存在中的實踐形式,悲劇行動經歷了自我揚棄、迂回與調停的漫長過程。《詩學》所強調的悲劇結構必備的“結”與“解”,被他描述為人類行動必然面臨的沖突與和解,這導致:一方面,行動的主體注定是有過錯(Schuld)的主體,行動就是為了犯錯;另一方面,行動作為意識活動的外化和顯現,“在作出決定和發出動作中對自己的內心生活始終是自覺的”〔11〕,所以人必須要為自己的行動擔責,這形成了一套“行動—意愿—歸責”無盡輪回的裝置系統,造成了現代意義上的自由難題。行動的“原罪論”激發了這樣一重吊詭的司法困境——既然人類必然有罪,那么他的罪行也就無所謂是否無辜了,“現在古希臘的悲劇人物……使決斷成為不可能了。因他不能掌控自己的行動,無辜的罪行(innocent guilt)是一個享有影響力的面具”〔12〕,黑格爾為實現倫理精神合法性而構建的行動機器反過來拋棄了自身的合法性,使得人人都成了潛在的受害者和施暴者。這無疑也讓正確認識奧斯維辛集中營事件此類重大歷史暴行成了難題。
阿甘本認為奧斯維辛集中營事件是一種將行動的悲劇范式推演到極致的“緊急狀態”(Befehlsnotstand),一個完全懸置法規卻同時發揮至高法力的“例外”之地。在這個地帶,主體與去主體化、行動的善與惡、無辜與罪過甚至生與死本身都已失去區分的意義——集中營是生產尸體的工廠,“死亡的辯證法”讓純粹的死亡不再可能,人是隨時可生可死也是非生非死的“赤裸生命”。于是不僅用以審判奧斯維辛的法規是失效的,言說它的證詞和見證行動也成為不可能,它完全超出了人類語言表達能力、認知符號框架的極限,“奧斯維辛的絕境即是歷史知識的絕境:事實與真相之間,證明與理解之間的不一致”〔12〕。集中營內極端駭人的存在超出了存在物對它的指涉能力,中斷了存在與被言說的存在物之間的語言學聯系和辯證法邏輯,顯示了歷史不可言說、不可傳遞的虛無內核,以及意識在時間維度中自我展開的不可能。因此阿甘本指出,認識和言說奧斯維辛是一種絕境,但它也開啟了全新的經驗,“當我們消除了語言的預設性力量,我們才有可能讓沉默的事物呈現出來”〔4〕,它讓集中營內被當作生產條件的不可見的死去的生命重新顯現,并讓他們重新回歸到自身的“純粹死亡”,意味著“言說不可言說之物”與“見證不可見證之物”的解放行動。這一經驗即是阿甘本所謂的“羞恥”。
(二)“自我—觸感”,赤裸生命的“羞恥”經驗
“羞恥”是存在于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極端情境下的特殊體驗,“將死之人不能在他的死亡中找到除了羞恥以外其他的意義……而唯有羞恥使人存活”〔12〕,阿甘本在這里采用了法國作家安泰爾姆(Robert Antelme)所書寫的一幅帶有奇異味道的“羞恥”場景——一位被當眾執行死刑的意大利年輕人在被德國軍官從一行囚犯中叫出來并站在施暴者面前的那一刻面露“紅暈”。阿甘本說年輕人瞬間的“羞恥”是列維納斯所謂的存在論意義上的赤裸體驗,它是一種突然闖入的生命沖動,無法預料無法逃避,帶著錯亂的情緒而抵達理性意志和人類知識的極限,通往巴塔耶所謂的“非知裸露”的迷狂——正如“裸體”對自身全然的裸露一樣,它恢復了人與存在之間原初的親密性,“裸體是羞恥的,因它是我們存在和存在終極親密性的顯現……親密性是存在對我們自身而言的……羞恥所發現的正是存在對其自身的發現”〔13〕。年輕人此刻站在囚犯和殺人犯之外一個不確定的位置,遭遇雙重排斥而淪為一個不可言說、不可見證但可被任意凌辱屠殺的“赤裸生命”;與此同時,他也處于“蓄勢待發”的短暫一瞬,一個將要成為但尚未成為被生產的尸體的時刻,此刻他身上涌現的是一種極度匱乏的需要、無自我的自我主義和無人稱的主體——人同自我的關系發生了變化,自我沒有落入一個預設的認知框架或辯證法程序,而是變成了與自身無限分離的未知者和陌異者。
阿甘本認為“羞恥”不僅是異質性的赤裸體驗,也是一種觸感體驗。啟發他的是源自斯賓諾莎而后由德里達、米歇爾·亨利等人發展的“自我—觸及/觸感”(auto-affection)。德里達說我們需要解除可觸及法則對觸感行動的限制,讓行動重新向潛在的非—觸即不可接觸性敞開。他將這種顛覆性的觸感模型命名為“自—觸及你”(se toucher toi):“自—觸及你既非單子式的……亦非雙重、對稱或相互的關系”〔9〕,“你”不是對“我”而言自明著的、映射著的對象,也不是與“我”相對立、為了回歸“我”而需要否定掉的“他”,而是觸感全然未知、永不可抵達的東西。因此“自—觸及你”意味著觸感內核的全然外露,是對接觸的中斷性、匱乏性與純粹死亡的暴露,它不再按照權力生產系統的預設返回自我之在場性,而是“可不接觸”、是轉而走向陌異的遠方的“自—觸”。這種全新的觸感模式被阿甘本挪用,他同時征引了米歇爾·亨利對內在性生命的定義,最終將其命名為“自我—觸感”。
“自我—觸感”指向這樣一種特殊行動,在它發生的時刻,施動者與被動者、現實與潛能、行動與功效進入不可區分的地帶,是亨利意義上無主體、無指示、無意向性的生命的內在性經驗,是生命對自身全然質料化的使用。“質料化”是說生命將自身作為純粹的質料和潛能,它如其所是的存在,圍繞自身打轉而不再等待靈魂賦予其形式化的未來,意味著一種無形式的、自指的運動,用斯多葛學派的一個說法來表達,就是“存在自己做著體操”〔14〕。正如舞者突然停滯的舞步,這一刻舞臺上所展示的不再是主體與行動的關系,唯余趨向離散的舞者與純粹姿勢,一個內蘊著保存著無限潛能、無時間的、非生成的、行動的純粹“占位”(localizzato),“內在自我是舞臺而感官是觀眾,所有的分隔消失后……感官如實的品嘗驚異的滋味”〔15〕。生命的“質料化”即“自我—觸感”的體驗尋求的是溢出從亞里士多德到黑格爾對認識和言說行動的觸感法則的設定,它最終開啟的是身體感覺經驗“非功效”(inoperative/ argos)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式的觸感在德里達那里是跳動的心、身體和愛,順著這個思路,阿甘本最終回歸了海德格爾的“本有”(Ereignis)思想,“不僅是知識的光和遮蔽,而首先是對遮蔽和不透明的開放……在愛中,專有和非專有的辯證走到了它的盡頭……愛是我們無法主宰、永不可觸及卻永遠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東西”〔14〕,“本有”意味著愛之盡頭的非專有性,意味著對專有之物的自由使用,即專有性和非專有性之二分的失效,而開啟它的場所恰恰是黑格爾辯證法的盡頭,即“絕對者”的時刻。
四、結論:虛無主義的未來,絕對異化的“專有者”與共同體
阿甘本曾說海德格爾的“本有”與黑格爾的“絕對者”概念旨在思考一種回歸自身而可免除分裂的東西,即思想作為一種“專有者”(L’ appropriazione)的存在。只不過對黑格爾來說,這種無可分割是主體意識的無可分割,是意識自身無條件的確定性和自明性。海德格爾認為這是黑格爾失敗的部分,因為他使自行發生、撤回、保存的物的經驗和真理在經歷對認識條件和認識工具反復的考驗之下,扭曲為主體對認識對象絕對占有的權力意志。所以海德格爾說需要重新安放黑格爾“絕對者”概念的位置——“絕對者”恰恰是在它整個“勞作”、“觸及”過程全然終結的地方真正開啟,也唯有在終結時刻也即在無他者、無時間性的時刻,它才抵達自身并拋棄所有,包括對自我和他者的反復占有。這是一個絕對異化、絕對專有的時刻,它在抓住專有的時刻就拋棄對專有的執著了。阿甘本認為這個“專有者”就是連接黑格爾與海德格爾思想的界檻,他也將其描述為浸入激情的愛河而徹底狂亂的時刻,狂亂使人避免落入生產和再生產系統的無盡輪回,是虛無主義的行動機器的不起“功效”、非“現實化”。它也是阿甘本所謂“羞恥”和“自我—觸感”意味的異質性的生命經驗。這是黑格爾為現代虛無主義問題所留下的最為關鍵的思想資源——辯證法在終結時刻的自我獻身解除了它對強權和虛空的眷戀,而為人們自由使用自身生命開辟了活路。
我們可以看到,現代虛無主義的政治呈現出“一切皆為政治”的“去政治化”盛況。政治向日常生活全面推進、絕對敞開并絕對赤裸,但在門戶大開的同時卻不允許任何人真正進入甚至改寫它,現代社會是喪失了自身實在的景觀式的、博物館式的社會。對此,學者埃斯波西托曾指出,需要重新提出一種“非政治”的范疇去抵抗現代“去政治化”和“超政治化”相互抵牾的兩難境地。“非政治”不是“反政治”的意思,它和政治共享一個場所,要做的是消解政治借由主權機器與權力生產、再生產系統所設立的規定與邊界,以還原政治純粹而無可分的存在。既然虛無主義時代帶來了傳統歷史國家論的終結,與其中諸種界限、范疇本身的相互侵越轉化、不可區分,那么批判工作的立足點不應該是對這些概念進行溯源和求真,而是阻斷計算、轉化,即阻斷辯證法的再生產邏輯、時間性的生成邏輯和專有性的財產邏輯對人類活動的控制,從而讓無限運轉的權力機器得以停歇甚至倒轉。因此,虛無主義政治的未來召喚的是一種非功效、純粹否定、絕對異化的共同體,“從這一角度看,共產主義標志著死亡的毀滅,即死亡他異性效能的終結,因為它使生命完全內在于自身之中”〔16〕。這種共同體的模型已在法國哲學諸學者那里給出了異彩紛呈的答案,而阿甘本所做的是將它定位到絕對受益的起點,即“異化”、“絕對者”或“專有者”,它們正是黑格爾虛無主義批判工作中最為卓越的理論成果。
參考文獻:〔1〕
海德格爾.林中路〔M〕.孫周興,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186.
〔2〕黑格爾.黑格爾早期神學著作〔M〕.賀 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323.
〔3〕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上卷)〔M〕.賀 麟,王玖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24,265.
〔4〕Giorgio Agamben. L’ uso dei corpi〔M〕. Vicenza: Neri Pozza Editore,2014: 170,176,175.
〔5〕Guy Debord.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M〕. Ken Knabb(trans.). London: Rebel Press,2005:13.
〔6〕阿爾都塞. 政治與歷史:從馬基雅維利到馬克思〔M〕.吳子楓,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8: 328,476.
〔7〕阿爾都塞. 黑格爾的幽靈:政治哲學論文集I〔M〕.唐正東,吳 靜,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 363,72.
〔8〕Thomas Hobbes.De Cive (Latin Version)〔M〕.Howard Warrender(eds.).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3: 154.
〔9〕德里達. 解構與思想的未來〔M〕.夏可君,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427,445-446.
〔10〕Giorgio Agamben. The Open: Man and Animal〔M〕. Kevin Attell(trans.).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14.
〔11〕黑格爾. 美學(第三卷 下冊)〔M〕.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256.
〔12〕Giorgio Agamben. 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M〕. Daniel Heller-Roazen(trans.). NY:Zone Books, 1999: 97,18,104.
〔13〕Emmanuel Levinas. De l’évasion〔M〕. Montpellier: Fata Morgana,1982: 87.
〔14〕Giorgio Agamben. Potentialities: Collected Essays in Philosophy〔M〕. Daniel Heller-Roazen (trans.).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235,203-204.
〔15〕Giorgio Agamben. Karman: Breve Trattato Sull’ Azione, La Colpa e Il Gesto〔M〕. Turin: Bollati Boringhieri, 2017: 130.
〔16〕埃斯波西托. 非政治的范疇〔M〕.張 凱,譯.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21:367.
From Hegel to Agamben:
The Problem of Nihilism in Dialectics and Its Solving Route
CHEN Qi
Abstract:G. W. F. Hegel started his dialectics work from solving the “emptiness” and nihilism contained in philosophical dualism, completing the gener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itself to “emptiness”. But L. P. Althusser believed that this transformation retained nihilism through “subjectless process”, reflected in the political practice of Hobbes’ state sovereign machine with its de-subjective subject procedure. Accordingly, Agamben pointed out its laws of action and mechanisms of violence, arguing that dialectics brough the dilemma of free action and the only solution was to open up the community experience of “auto-affection” and non-exclusive love. The development of ideas from Hegel to Agamben shows the decisive influence of Hegel’s “absolute” idea on the nihilistic critical work of Heidegger and after him with a new model of community.
Key words: dialectics; nihilism; G. W. F. Hegel; L. P. Althusser; G. Agamben; power machine; auto-affection; absolute
(責任編輯:武麗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