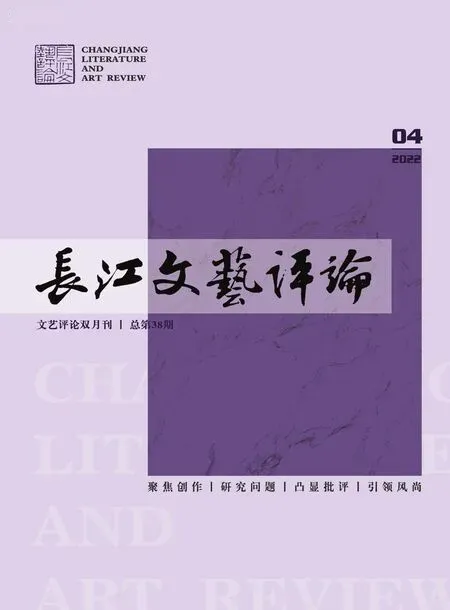重構經典復歸童真
——評梅杰《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綱要)》
◆蔣士美
中國現(xiàn)代兒童文學的濫觴,通常被認為源于“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早在1920年,周作人便在《兒童的文學》一文中表達出對于中國兒童文學之匱乏的強烈擔憂,并就此問題嘗試性地提出了諸多可行性建議。實際上,周作人開啟了中國“兒童文學”當從民間口頭文學、逸聞故事以及古代神話中汲取創(chuàng)作靈感的先河。只是相比于完全的“二度創(chuàng)作”,周作人的提議更著重于強調對于兒童文學的“深度發(fā)掘”“收集整理”和針對兒童的心理及認知特點對收集而來的諸多民間材料進行“重新編訂”的方面。《兒童的文學》可視為促進中國兒童文學誕生的里程碑式著作,作者在書中所傳達出的“兒童本位論”也成為了橫跨中國兒童文學三個歷史高峰期(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及八十年代)的中心議題之一。而由此論所引發(fā)的關于“兒童文學本質”的討論,也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學術界爭論不休的焦點。郭沫若曾高屋建瓴式地指出“兒童文學”不僅需要具備基本的藝術和美學價值,更重要的是必須符合“兒童文學之本質”。至于這個“兒童文學之本質”所指為何,魏壽鏞、周侯于、吳研因等教育家在杜威“兒童中心主義”的影響下,提出“兒童文學”在語言的表述上和情節(jié)的編纂上必須符合兒童的審美心理,符合兒童心理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不得出現(xiàn)“情感失度”等過分煽情的組成要素,以保證“藝術價值與兒童本位”二者之并重。正是由于老一輩教育家、作家及學者為中國兒童文學的奠基所作出的艱辛努力,才造就了上個世紀我國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的三個黃金時代,涌現(xiàn)出了諸如葉圣陶、豐子愷、鄭振鐸、冰心等高質高產的兒童文學作家。與此同時,他們也是一批真正具備時代及社會責任感,一心為兒童寫作的精神引路人。
反觀當代尤其是進入新千年之后的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相較于“黃金時代”的作品,其內容大有自“兒童本位”向“商業(yè)本位”逐漸演進的態(tài)勢。相當數(shù)量的兒童文學“制造者”高舉“文學創(chuàng)意”的旗幟卻在為金錢而寫作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漸漸失掉了一個作家應該具有的良知和道德約束感。與此相伴生的,還有盲目市場化帶來的對于兒童文學作品“經典”之標準的消解,一大批優(yōu)秀的兒童文學作品在市場商業(yè)競爭的漩渦中敗下陣來,淪為了“商業(yè)化寫作”潮流的犧牲品。過去由老一輩教育家“審一以定和”般建構出的“經典”體系,被后來居上的諸多充滿了西方價值觀的作品凌駕其上。“童心”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以創(chuàng)造“快餐式文化”為目標的“新兒童文學”。然而,教育市場資本化的趨勢并不能阻擋讀者群體對于“經典”作品的渴望,對于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及出版領域的種種亂象,群眾抵制兒童文學“毒”作品的呼聲日益高漲。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青年學者梅杰新近出版的《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綱要)》(以下簡稱《綱要》)可謂是扛鼎之作,此書藉由梳理史料之機,以全新的“兒童本位論”為中心,重新定位了當代兒童文學須在承繼“經典”的根底之上,繼續(xù)為“童心”寫作的創(chuàng)作初衷。并在以史帶論的前提下,在堅持兒童本位論的基礎上,逐步建構出一套極富生命力的“泛兒童文學”理論,為當代“商業(yè)化寫作模式”向“新兒童本位”的轉向與復歸提供了堅實完備的理論依據(jù)。
一、在“經典懷舊”中尋找兒童文學的未來
什么是經典?經典可以被認作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某個特定歷史時期中精神文明的集中(代表性)體現(xiàn)。在文學創(chuàng)作尤其是兒童文學的相關創(chuàng)作中,任何一部歷久彌新的文學作品必定首先具備了成為“經典”的充要條件。而在這“充要條件”背后,兒童文學受眾的特殊性決定了作品本身的“經典”與否不僅需要滿足大眾普適性的審美判斷,更重要的是其核心表達必須符合“兒童心理”對于作品形式與內容的審美期待。兒童與成人有著截然不同的觀照世界的方式,近代著名兒童心理學家皮亞杰曾指出,兒童心理發(fā)展可大致歸納為四個階段:感知運動階段(0至2歲)、前運算階段(2至7歲)、具體運算階段(7至12歲)以及形式運算階段(12歲以后)。同成人相對穩(wěn)定的認知結構相比,兒童對于外界事物的體認缺乏一種恒常的、模式化的認知方式,這就導致其在日常的與外在客體的認識活動中很難形成某種動態(tài)穩(wěn)定的“心理圖式”。作為存續(xù)于人腦之中的一種經驗性的存在,“心理圖式”可說是形成“客體恒常性”即所謂“安全感”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在學界看來,兒童文學受眾群體的年齡范圍一般被認為介于3至17歲之間,受到兒童發(fā)展心理學及認知心理學相關論點的影響,國內出版界通常將兒童文學細分為數(shù)個領域,即嬰兒文學、幼年文學、童年文學和少年文學。但這種劃分實際上只是抓住了兒童認知特點中那些被人為劃定的特征性表象,而忽略了各年齡段兒童心理需要構建“客體恒常性”的普遍訴求。這些具有強烈傾向性的簡單劃分直接影響了兒童文學的創(chuàng)作,導致很多“機械唯物主義”式的作品不斷從市場中涌現(xiàn)出來。這些“商業(yè)化寫作”模式下的“文學快消品”事實上已然背離了其遵循兒童認知發(fā)展規(guī)律的初衷,用實質上的“靜止觀”替代了表面化的“發(fā)展論”,淪為了資本主導下的市場細分的產物。如此粗制濫造、唯利是圖的商業(yè)產品,不僅與“經典”無緣,其本身還會起到“劣幣驅逐良幣”的負面效果,不斷混淆視聽,消解“經典”形象在普羅大眾心目中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與經典消亡伴行的,是一個民族乃至一個國家之民眾對于自身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逐漸疏離和淡漠。就兒童文學在當代的創(chuàng)作與承繼而言,經典存續(xù)的意義不僅僅是為當下日漸迷離的寫作風向指引正確的航路,更重要的是以經典作品中流露出的真摯“童心”喚醒金錢導向社會下人們沉睡已久的良知,重新激發(fā)民眾人性之中向善的一面。梅杰在“中國兒童文學大視野叢書”總序中就“市場意識”與“經典意識”二者的兩相契合作出了極為精到的解讀。他指出,市場與經典之間的關系并不具有先天存在的不可調和性,無論是所謂“唯市場論”,還是“唯經典論”都不能推動中國兒童文學經典的承繼發(fā)展和新生優(yōu)秀兒童文學作品的良性傳播。對于市場與經典兩者關系的正確認知,一定是隨著歷史的進程而不斷得以更新和發(fā)展的,而這些“新的理論”“新的認識”必將在“新的時代”帶來經典的重新塑造。誠然,文學史上關于何為“經典”的論爭自文學誕生以來就從未停止,梅杰在擇選經典兒童文學作品并在此基礎上重構中國兒童文學史的過程中,對于“經典”的再判斷,他選擇了一條飽含個人灼見的兼容并蓄之路。他所提出的“大視野”之框架,不僅貫徹在“中國兒童文學大視野叢書”的整體出版思路之中,更成為了他創(chuàng)作《綱要》一書的底層邏輯。
既為“綱要”,就是要本著拋磚引玉、直切心源的初衷去為痼疾纏身的文史界“應病與藥”。梅杰在《綱要》一開篇即借數(shù)位歷史學者之言論為重塑“經典”之“大視野”的整體邏輯構架進行先導性鋪陳。他以思想家梅光迪“歷史是人類求不變價值的記錄”之觀點作為核心,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在對史料的深度和廣度進行翔實發(fā)掘的基礎上,以個人化立場言說歷史可以更好地揭示歷史本真實相的中心議題,完成了從以往觀念固化的“歷史性經典”向“個人化經典”的轉變。而此處所言之“個人化的經典”并不是意在推崇個體對歷史經典的主觀隨意性解讀,而是在對各家言說以“兼容并蓄”之態(tài)度進行整體觀照的前提下,避開文史界一以貫之的對于“經典”以及“經典”作品的主流化言說,另辟蹊徑地通過史論結合、以史帶論的方式為讀者展現(xiàn)出一個多維化的立體圖景,引導并啟發(fā)讀者參與其中成為擁有獨立意識的“歷史敘述者”。《綱要》對文史界傳統(tǒng)語境中“經典”概念的解構價值在于,它不僅為中國兒童文學史的寫作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更動搖了一直以來統(tǒng)攝學界的一些具有鮮明歷史傾向性的主流論點。它將歷史敘述的話語權從“勝利者”的講壇上逐漸剝離開來,重新交還到了歷史的主體——人民的手中,并在其實際的論證過程中貫徹了伽達默爾“消解二元論”的歷史觀,獨創(chuàng)性地在“接著講”的基礎上“另起爐灶”,走出了一條極富個人魅力的“文學革命”道路。
《綱要》以扎實的史料作為支撐此書所提“新論”之根基,將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中與兒童文學相關的一些因時代論爭而藉藉無名,且為史學家所忽略的人物作品一一擇取出來,使他們的作品和言論得以借助全新的歷史視野重新發(fā)聲。這種“再發(fā)聲”的過程本身就是重塑“經典”的過程,而《綱要》所秉持的“經典懷舊”,亦是在梅杰對歷史上優(yōu)秀經典兒童文學作品再三地“顧盼回眸”之后所新得的“經典化”構想。“經典”既是歷史的,也是“當代”的,它是由歷史瞬間中無數(shù)個“當代”的片段組合而來,而附著在每一條片段上的“當代”時間點都會將當時流行的思想觀點有意無意地加諸于對“歷史”或“經典”的評判上。秉承此說,梅杰在行文中以平實且極具個人化風格的語言,將兒童文學發(fā)展的階段看成是一個有機的融合體,摒棄簡單以時間脈絡來劃分史料的傳統(tǒng),將其整合為史前、孕育、誕生、發(fā)展、挫折、新生、斷裂、重建等幾大行進段落。這種劃分方式,單就其形式而言,也是一種對于傳統(tǒng)“經典”的反叛。梅杰的這一舉措,意在從形式到內容由外及內地顛覆主流“經典”的話語權,以一種全然的“陌生感”包覆讀者的洞察力,剔除其頭腦中先驗式存在的諸種“審美期待”,使之在接受過程中惶惶然不知其所始,惶惶然不知其所終。而這些苦苦尋覓、四處求索的閱讀體驗,正是《綱要》所要帶給眾多讀者的精神禮物,這份禮物既是用來打破窠臼的武器,也是重新定義“經典”之濫觴的源頭活水,是全書“經典懷舊”之宗旨的外在表現(xiàn)。
二、在泛化的“童心”中完成對心靈力量的復歸
古有李贄“童心說”,今有梅杰所倡之“泛兒童文學論”,兩者雖相隔數(shù)百年,但其核心思想卻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泛兒童文學”之“泛”是將原先局限在歷史逼仄角落之中的狹隘的“兒童文學”大而化之,使其演變成為具有相當普適性的全新的審美評判標準。在梅杰看來,中國兒童文學與所謂“成人文學”之間的關系,并不像許多學人所言那般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它們二者間存在著一條天然共生的“臍帶”。而這條臍帶其實就是李贄“童心說”在現(xiàn)當代兒童文學語境之中的延伸。誠然,梅杰對于“當代文學”的說法持有懷疑態(tài)度,這點在《綱要》中所附的《總序》及緒論中都有頗為詳盡的論講,這里不再贅述。“泛兒童文學論”究其本質,就是西方舶來之“兒童本位說”的升維泛化,但它不以狹義的“兒童”為中心,而是乘著“大視野”的東風,對人類的共同情感及人性之本進行了深度思考。“兒童本位論”自其堅定的支持者周作人力倡以來,兒童文學似乎成為了獨立于現(xiàn)當代文學領域之外的一支“小眾”文學品類。實際上,自杜威“兒童中心論”漂洋過海成為領銜中國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乃至教育界頗為推崇的主導性理論之后,“兒童”就被人為地與“成人”割裂開來,“兒童”這一概念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都只是作為“成人”的附庸。許多知名作家如巴金、老舍等就是由于無法正確處理“成人”與“兒童”之間的“溝壑”,以至于在實際創(chuàng)作中過于偏重“文學化”。在梅杰看來,兒童文學的創(chuàng)作決計不可如此這般“戴著鐐銬跳舞”,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將寫作對象乃至作者期待中的受眾群體進行概念化地分割只會使成品顯得十分刻意,使人讀之難分軒輊,并不能從其中品評出獨到的韻味來。
“泛兒童文學論”的提出就是為了推翻這些將創(chuàng)作者禁錮在思維怪圈之中的種種陳詞濫調,破除一切從西方輸入的,裝扮著權威外衣的“主義”和“公理”。兒童之所以被稱之為兒童,并不完全是因由其自身的生理(或心理)特點而被劃歸為一類具有特殊意義的群體,這種經過經驗化地(或說是“科學地”)簡單歸納而出的“定理”,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完全是西方近代科學一廂情愿的結果。筆者認為,梅杰所言之“泛兒童文學論”的最大價值,就是它不僅讓兒童文學之創(chuàng)作脫離了原先由許多所謂“不可抗力因素”所鋪設的預定軌道,摒除了以往文史界經過長期認知固化而形成的諸多“創(chuàng)作公式”的消極影響,更重要的是它實際上泛化了“兒童文學”中“兒童”一詞所蘊含的原生語義以及它原本所指代的一個特殊群體。從這個意義上說,“泛兒童文學論”掀起的不僅是一場別開生面的“兒童文學革命”,它更可能成為一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學解放運動”的先聲。
“泛兒童文學”之“泛”,既是消解,也是重建,更是復歸。它消解的是自文學誕生之初便橫亙于世間的萬千偏見與“概念地獄”的枷鎖,重建的是經過市場經濟洗禮之后為人所淡忘的“經典”,復歸的是在長期由概念分化的世界中人們蒙塵已久的“童心”和“童真”。一言以蔽之,作為現(xiàn)實世界社會關系和人類情感的異化或投射,文學之所以被冠之以“文學”的名號,就是因為它自人類結繩記事之始就擔負著記載人類最為真摯質樸情感的使命。真摯的情感蘊含著人類本性之中對于生活的熱愛、祈盼和向往,它不拘泥于任何形式,不受制于任何理念的束縛或干擾,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在物質貧瘠的時代,或者按照一些人類學家的說法,即是在人類混沌初開的“童年”時期,對于自己在自然界中的見聞與經歷,他們更傾向于采用繪畫的方式進行直觀具象的表達,而用以描述更為抽象或繁復事由的文字,則是在生產力及社會關系漸次成形之后產生的。文字的出現(xiàn)使人類得以更加自如地表達自己的思維和想法,隨著社會分工的不斷細化,生產資料來源的不斷豐富,語言文字變得愈發(fā)精煉和富于美感,建構在現(xiàn)實社會之上的一個全新的“概念世界”也由此慢慢浮現(xiàn)。我們在此并不否認概念化之于社會發(fā)展帶來的種種便利,但它本身亦是一把雙刃劍———概念化的存續(xù)一方面使社會個體之間的交流變得簡明高效,另一方面卻讓參與交流的主客體之間增加了“文本誤讀”的可能性。從這個層面上講,“誤讀”的產生可以看作是人類社會“自然進化”的產物。但這里的問題是,如果在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的語境中來探討這一語言文字不斷概念化的“進化史”,我們不禁要發(fā)問:到底是“兒童”成就了文學,還是文學成就了“兒童”?
梅杰在《綱要》中明確指出,“泛兒童文學”是聯(lián)結兒童文學閱讀和成人文學閱讀之間的橋梁,而這個橋梁的出現(xiàn),恰恰是因為所謂“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之間,存在著有悖于“應然狀態(tài)”即理想狀態(tài)的模糊地帶。其實在筆者看來,這一觀點中所直指的“模糊性”,恰恰可以回答上文所提及之“兒童”與“文學”之間的關系問題,也即是梅杰在全書中反復提及的“兒童的”與“文學的”二者之間的矛盾(梅杰指出多位文學大師因為處理不好二者關系,在兒童文學門檻前敗下陣來)。“兒童”之所以為“兒童”,“文學”之所以為“文學”,實際上根本不存在所謂的邊界和范圍。梅杰理論體系的立根之本,其中最為關鍵的所在,就是牢牢把握住了這片由概念所化的“模糊地帶”。私以為,將“泛兒童文學”比擬為橋梁,實為自謙之語,只因在概念世界風云詭譎的時時變幻中,能夠以永恒態(tài)維系自身形相的“概念”或“論說”,只可能存在于“應然狀態(tài)”里。“泛兒童文學”之“泛”,在承繼前文所述之“泛化”的含義之后,它的真實面貌實是在闡釋及描摹與“應然狀態(tài)”相對之概念世界的“本然狀態(tài)”。在“本然狀態(tài)”中,概念與概念之間的聯(lián)結是不斷變化、不斷重組、不斷消亡的,所以無論理論統(tǒng)攝下的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應當如何,在實際書寫文本的過程中,作家的“邊界意識”在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并不會成為其創(chuàng)作思維的主導。
當然,這一泛指“絕大多數(shù)”的情況,是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一個遵循內心寫作的、富有“童心”的作家所應當秉持的最基本原則,也就是說在“生就的兒童文學作家”那里,哪怕缺乏邊界意識,也絲毫不會影響他在事實上已經抵達兒童本位,并進入兒童的心靈世界。借用美國哲學家桑塔亞納對于藝術起源的見解,他認為“藝術是本能沖動的理性顯現(xiàn)”,但就文本寫作中“童心”的闡發(fā)而言,“本能沖動”(更準確來說是“本真沖動”)的部分是一定要大于理性的。“泛兒童文學論”中所蘊含的“童心”正是桑塔亞納所言“本能沖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是這份“童心”中包孕了東方特有的智慧,它摒除了“本能”之中獸性的部分,而還之以“真”、賦之以“善”、歸之以“美”,使“兒童”與“成人”間的溝壑彌合在“泛兒童文學論”復歸“童心”的柔光中。雖然梅杰自謙式地指出,“泛兒童文學論”,“不是給兒童文學作家提供某種創(chuàng)作理念,而是一種兒童文學應用方法”,但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分明看到,一些成功的“泛兒童文學”文本的真實存在,必然會對作家的創(chuàng)作產生啟發(fā)。梅杰《綱要》一書的寫作,正在是兒童本位論與泛兒童文學論的雙重視野下,以審美的(兒童本位堅守)和歷史的(泛兒童文學視野)原則,對百年中國兒童文學進行了個人化的經典重塑,必將給當下兒童文學的創(chuàng)作、研究和出版,帶來極大的觀念震蕩,這或許是《綱要》一書最大的現(xiàn)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