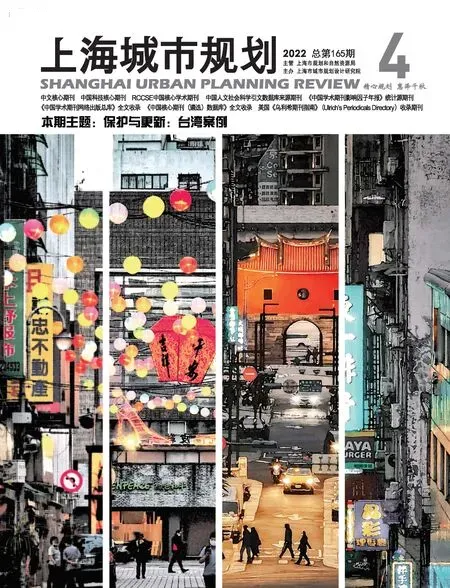超越真實與想象:一個臺灣“非典型”文化遺產的空間探析*
羅 晶 LUO Jing
0 引言
都市更新中的文化遺產保存,從早期作為對現代性與工業技術理性的質疑與抵抗,發展至1980年代以來作為旅游目的地的“文化策略”[1],與被用來創造全球城市借以維系其全球經濟控制中心地位所需要的“生活風格”[2],再及至當下社區營造被引入遺產保存的公共行動領域,其建構的論述既擺脫了“遺產保護”與“資本積累”的二元對立,也在努力躲避鄉愁式保存的陷阱,而試圖通過吸納多方社會—空間行動者(social-spatial actors)的參與,形成共同探索、選擇與協商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根據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文資法》”)指定的臺北市近500個古跡、歷史建筑、紀念建筑與聚落建筑群中,西門紅樓、臺北之家、大稻埕迪化街[3-5]等作為成功的案例,經常出現于學界與公眾視野中。綜其優勢,主要為政府持有、委外經營,亦有部分民間公益團體駐扎推進社區營造,并作為公共建筑吸引了大量的參觀消費人流,形成良性循環。
然而無法忽視的是,尚有一批具有歷史價值的文化遺產,因其自身典型性不足或保存現狀不佳,不足以進入官方的民族文化敘事;或因其規模較小,又是私有產權,不利于旅游開發,遂被排除于塑造與找尋“城市文化風格”的公眾視野;再退一步,這些建筑又囿于指定文化遺產的相應規定,不能進入徹底的資本化運作或城市拆除式更新。于是,這部分文化遺產成為卡在公共與私人領域之間的“傳統建筑孤島”。
艋舺謝宅就是這樣一個“非典型”的臺北市定古跡。它所在的萬華區,古稱“艋舺”,是臺北最早被福建移民開墾的地區,與府城臺南、鹿港并稱“一府、二鹿、三艋舺”,分庭抗禮,是早先北臺灣最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可以說是臺北市的發祥地。艋舺在乾隆年間開展港口經濟后即出現“郊商”①郊,亦稱郊行或行郊,是一種商業同業公會類型的組織。郊源自中國商人的商業結盟,但并非中國各地都有,歷史上的類似機制有會館、公所、公會、幫等名詞,成為“郊”者僅清代華南沿海的商賈,尤其以臺灣最盛。,亦稱船頭行,為商業同業公會組織,很快發展成為地方社會的核心組織。始建于清嘉慶年間的謝宅,即是北郊(主要為福建安溪人)建發船行的大本營。
然而時遷景移,昔日繁華成為過去歷史,艋舺現如今是臺北市最老舊的城區,也是都市更新最為活躍的陣地。距謝宅一個街區之遙便是電影《艋舺》的拍攝地、文化古跡清水巖祖師廟,緊鄰在側的是臺北歷史街區保存的重要案例貴陽街。
艋舺卻與它們形成了鮮明對比。老宅主體被鐵皮嚴嚴實實地包起,屋頂不見天日,只有一小段側山墻與廂房暴露于外。磚壁與木板墻上長著青苔,沿街卷閘門緊閉,門外空間也沒有設置亭仔腳②基于亞熱帶氣候多烈日與暴雨的特性,市街中沿街立面出檐下多設有公用通路,慣稱“亭仔腳”。與周邊街區連接起來。城市肌理驟然斷裂于此(見圖1-圖2)。

圖1 艋舺謝宅沿街外觀Fig.1 Street facade of Xie-Mansion

圖2 艋舺謝宅鳥瞰Fig.2 Aerial view of Xie-Mansion
顯然,這樣的謝宅與文化遺產的全球化敘事相去甚遠。因此,它避免了像許多知名的文化遺產一般在精英和大眾的“凝視”下異化,產生奇觀式歷史保護與真實地方的矛盾——它遭遇著與之相反的困境,在最為貼近本地社會網絡與日常生活的層面走向與文化遺產制度的初衷相悖的方向。用列斐伏爾“整體論”的空間觀來看,它逃逸了文化遺產空間生產中的抽象空間,提醒人們面對現實中由真實與想象共同構成的差異空間[6-7]。本文從這一視角出發,對艋舺謝宅的案例中多方行動者的不同認知,以及地方的多重內涵進行觀察與討論,試圖更加清晰地認知遺產可持續保護的概念和方向。
1 文化遺產的空間生產
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概念三元組”[6]及其后續演繹引申,尤其是索亞描繪的通往真實與想象空間的旅程,是本文在面對文化遺產保存中出現謝宅這樣的“非典型”時重要的批判路徑。“文化遺產”的稱謂將有歷史價值的建造物從周邊環境中區分出來,歸屬于特定的政府部門,指定特定管理者,制定特別的規定,本質上是當代社會及其生產方式下的一種“空間分類”。它對應的是專門領域的“分工”,是文化部門與建筑、城市規劃等學界的專家學者在當下對于地方歷史的想象和知識生產。例如,《文資法》在第一條即開宗明義,是為“保存及活用文化資產”;并在之后的條款中規定了臺灣文化資產的定義,以及文化資產的指定方式。可見,“文化資產/遺產”是被框定的一套完整的、有著明確邊界的系統,這個系統具有明確的目的,并經常與意識形態關聯。
列斐伏爾認為,如“文化遺產”這樣的知識化的空間類型,生產出的不過是關于空間的“話語”,并提醒道,這其中存在著支配性的“霸權”,“通過‘人的中介’(如政策、政治領袖,以及知識分子和專家)對‘知識’進行的操縱,進而操縱整個社會。因此‘空間’在這一過程中主動地服務于一種系統的建立,這個系統即是那個被看作是關閉的、整體的、系統性、沒有矛盾和差異的社會[7]128”。基于對上述“系統論”的空間的反對,列斐伏爾提出“空間生產概念三元組”:一方面,空間是在3個層面上同時出現的——感知的(perceived)、構想的(conceived)與生活的(lived);另一方面,與之平行的現象學構型為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空間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再現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 or spaces of representations)(見圖3)。被指定的文化遺產,即屬于空間再現,指那些被構想出來的、理想型的并且占據支配地位的符號或象征。所謂“感知的”,也就是“空間實踐”,包括生產和再生產,對應于每個社會形態中的特定位置和整體空間;所謂“生活的”,也就是“再現空間”,是透過相關意象和象征而呈現出的直接的、活生生的空間,也是“棲居者”和“使用者”的空間。列斐伏爾特別提出,空間再現的一個共同特征便是構想它們的人都會幻覺地認為“構想的”與“感知的”“生活的”是完全相符的[7]131。這一警惕構成本文的理論出發點。

圖3 列斐伏爾的兩種空間概念三元組Fig.3 Two conceptual-spatial-triad of Lefebvre
索亞更進一步討論了空間三元組中的一種二元張力,以“想象”與“真實”指稱“空間再現”和“空間實踐”,并將“兼具真實與想象”(real-and-imagined)的第三空間(thirdspace)對應到“再現空間”。展開來說,索亞的第一空間(firstspace)是物質性的空間,是真實的、具體的空間,是特定的社會形態下制圖與規劃分區的空間;第二空間(secondspace)是構想的精神空間,是通過想象尋求對空間的改變和占據,它覆蓋著物理的空間,象征性地利用這些客體,并試圖成為真實的空間,使得空間的物質形式僅僅通過人類活動被間接理解。索亞主張打開非此即彼的封閉邏輯,將第三空間作為一種他者,從而保持“兩兼其外”(both/and other)的開放性[8]60-61。他“格外強調要破除支配和被支配、抽象和具體、視覺和身體、物質與想象的二元對立,邁向‘真實與想象兼具’的再現空間[9]7”(見圖4)。本文對謝宅的討論正是基于這一空間辯證法的二元張力分析,試圖從超越真實與想象的第三空間視角對文化遺產進行空間分析,以審視謝宅現狀的根源。

圖4 索亞對空間生產的本體論—認識論演繹Fig.4 Soja's ontological-epistemological deduction of production of space
本文對于文化遺產現狀剖析的另一個重要依據,是地方感的概念及其構成維度。自1970年代以段義孚為代表的人本主義地理學者將“地方”引入人文地理學研究以來,地方感逐漸成為一個重要的概念,并形成完善的研究體系。地方感所體現的是人在情感上與地方之間的一種深切的連結,是一種經過文化與社會特征改造的特殊的人地關系[10]。面對全球化、日益增強的流動性與城市對于現代建設的追逐,新的人地關系使得城市更新對于地方感的塑造日益重視。從某個角度來說,社區營造便是關于地方感的營造,它使得社區中的文化遺產不再只是一個傳統的物,而是社區精神與公共歷史的情感承載。本文從地方依戀和地方認同維度探究謝宅空間。地方依戀指的是人與特定地方建立起的一種他們希望長久保持的聯結關系,而地方認同則被定義為人的身份認同的一部分,人們通過與地方的互動而認為自己歸屬于一個特定的地方[11]。
本文借用民族志的方法,通過關鍵人物深度訪談和文獻回顧,結合建筑學的空間調查,對艋舺謝宅的文化遺產保護現狀進行深描。下文將先從建筑的“真實”物理空間和《文資法》及檔案記錄下的“想象”開始,逐漸超越二者展開呈現謝宅社會空間的全貌。
2 謝宅的真實與想象
今日謝宅的存在,借用索亞[12]描述洛杉磯歷史發源地“天使圣母的城鎮”所用的比喻,如同多次書寫的羊皮紙(palimpsest)一樣,承載著多重的歷史記憶。它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傳統”建筑,留傳至今的絕不是清時北郊歐陽長庚所建之物;相反地,它濃縮了時代變遷下兩個家族的生計使用與文化傳承,在臺北歷史進程中一再地被寫作、刮去與重寫。
歐陽長庚由福建晉江移民臺灣,所建原為一幢泉州式的三落兩進帶左右護龍(廂房)的大厝,但與泉州傳統三落大厝又略有不同,第一落為兩層高的磚木混合構造。第一落門廳做船頭行之用,第二落為公媽廳③“公媽廳”是從祠堂分支出來的放置祖先牌位的地方。一般隨著一個姓氏的發展,族人數會不斷增多,分支也會不斷增加,為了祭祀的方便,同一分支的人一般共用一個“公媽廳”,放置祖先牌位,每年過年及特定節日都會祭拜。,第三落為船頭行的船工居所。至日本對臺灣的侵占和殖民統治時期,第一落門廳被拆除,原船頭行行址上建起了二層日本殖民風格建筑。1945年,歐陽家已十分沒落,房產被抵押給銀行,在廈門經商的謝溪圳從歐陽的孫輩手中買下此宅,并許諾:“我會好好將這棟厝留下,不會讓它拆掉消失,讓你對得起歐陽祖先。[13]”
今日謝宅建筑主體的第二落及廂房基本保存了最初的樣貌,為閩南式硬山雙坡屋面,側面采用五行中的“火”字山墻,墻上設有青釉花磚的通氣窗。墻基及墻腰用花崗巖石條疊砌,以上為50 cm厚的紅磚墻,飾面以牡蠣粉、細沙與紅糖攪拌涂抹粉光(見圖5-圖6)。建筑基本格局為三開間,“四房合一廳”,舊時戶主住于房中。將民居中最重要的公媽廳盡最大努力保留完整,也符合建筑布局的主次關系。

圖5 謝宅的第二落現狀及其后進的四層公寓Fig.5 The second hall and the four-story-apartment behind

圖6 謝宅第二落山墻Fig.6 The gable of the second hall of Xie-Mansion
建筑的第三落在謝溪圳買下后被整修為月光浴室,至1970年月光浴室由于燒鍋爐屢屢接到罰單而被迫拆除,改建成四層公寓樓房,直至今日依然作為出租公寓經營,租金為謝宅現在的主要收入。后文將涉及的現在的謝宅屋主之一謝東昇,也住于公寓一層,并經營著一家雜貨店“月光商店”以維持生計(見圖7)。

圖7 謝東昇經營的“月光商店”的一面墻Fig.7 A wall of "Moonlight Store" run by Dong-Sheng Xie
謝宅的第一落,則反映了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對城市道路系統與基礎設施的現代化改造。日本政府在臺建立了貫穿的、均質的交通系統與土地行政分區,這意味著拓寬的道路穿透了艋舺原本密布的城市肌理。西昌街與長沙街的變更迫使謝宅第一落建筑被拆除后退重建,新建的兩層樓改用西洋式日本折衷風格,臨街按照日本制定的《臺灣家屋建筑規則》設置亭仔腳,梁作拱弧狀,外墻以洗石子飾面,屋頂是變異的五波面西式三角桁架(見圖8)。新建日式建筑在郊行沒落后作為商店開設,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短暫租借給同窗張家來開設“月記醫院”。1952年,謝家請建筑師進行局部整修,保留外觀不變,內部功能調整為店鋪及旅社,開始經營“星光旅社”直至1999年結束營業。

圖8 1985年(上)與2015年(下)的長沙街對比Fig.8 Comparison of 1985 and 2015 Chang-Sha Street
從1999年開始,謝宅被指定為臺北市定古跡。古跡的范圍僅包含第一落與第二落及之間廂房——第三落原址上的四層出租公寓,以及北側廂房外的加建均不在保護范圍之內。臺灣文化事務主管部門記錄的謝宅評定基準為“具歷史、文化、藝術價值”,指定/登錄理由為:①為臺北市僅存之清中葉郊行遺構,雖只剩第二進廳堂,但仍具有艋舺商業歷史價值。②第一進內廳近代改建為旅社,內部為日式風格,亦具有時代特色。③第二進為閩南式傳統建筑,用料巨大,木雕精美,深具藝術價值。該古跡的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所有權屬為私有,土地所有人及管理人均為謝從世、謝東昇、謝宏富等12人。
《文資法》優先于一般性規定——這意味著建筑物一經指定為“文化遺產”,它就被“凍結”了,其新建、增建、改建、修建等行為均受到約束限制;同時也意味著,那些不那么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價值”的、也即未進入指定范圍之內的部分,則需要遵從城市規劃法規、建筑法規、土地法規等一般性規定。在謝宅的案例中,被指定為“文化遺產”的建筑部分受到《文資法》的約束,而第一落與第二落所坐落的土地,甚至緊密附著于廂房的加建部分,都是可以改變、拆除、再開發的。因此,一旦成為“文化遺產”,便是進入一個更高層面的系統,其下還覆蓋了其他層疊的、支配性的、抽象的知識系統,以及不同的行動者對這一真實空間的想象與認知。下文基于“第三空間”視角,從地方感的依戀和認同兩個層面進行分類和論述。
3 地方依戀層面的一致與矛盾
艋舺謝宅的古跡指定過程進展得非常順利。1998年10月,臺灣古跡保存的積極推動者、臺北市榮譽市民、加拿大人史康迪(Curtis Smith)發現了這棟古宅,第二天即帶領相關當局官員及專業攝影師登門采訪。他積極推動古跡認定工作,至1999年1月,僅僅3個月時間,謝宅即被當局核定并公告。類似的專家學者幫助推動的情形基本貫穿于那之后的謝宅保護過程。例如,在古跡認定2年后的2001年,古跡所有人謝溪圳去世,《文資法》雖減免了房屋稅與地價稅,但由于之前從未發生過古跡繼承問題,謝家繼承人還是面臨被征收3 200萬臺幣的遺產稅。據謝東昇口述,減免遺產稅的過程主要依靠夏鑄九和李乾朗兩位學者的陳情和推動,最終于2003年出爐《文資法》修正草案《艋舺謝宅條款》,謝家正式免繳遺產稅。
我們可以說,參與政府古跡指定與保存工作的專家學者、甚至關注萬華城市更新的網絡社區作為外來力量,對于謝宅作為一個臺灣傳統建筑的情感與認知,并不輸于謝東昇這位謝宅的“守護者”。相較之下,反而是謝家的幾位繼承人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分歧。從媒體報道[14-16]、法院判決書等資料來看,主要矛盾集中在謝溪圳的大房太太與二房太太之間。二房謝秀玉之子謝東昇,自幼時便與母親住在月光浴室二層,繼承父親遺愿極力保存;大房謝林阿儀之子與孫輩謝從世、謝宏富等,則對保存極力反對,并公開表示謝宅的處置應由所有繼承人全數同意,不可執意“將祖產交出去”。而如若放棄文化資產的保護與限制,則謝宅所屬土地又能恢復市場價值,大概可以連同周邊鄰里迅速地進入城市更新的浪潮之中,顯著提高容積率,翻新生活環境。
因此,謝宅疏于修復保護的現狀,最直接的原因自然是經費不足,但在不同行動者的視角下,背后深層原因卻反映了文化遺產在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間的尷尬局面。在謝東昇的論述和地方文史工作者[13]273,[17-18]的出版記載中,“公共部門的不作為”是保存失敗的關鍵原因。公權力只提供了若有似無的保護,例如在謝宅因道路施工導致的地基下陷幾近倒塌時緊急搭建了臨時圍擋與支撐,再如放置了幾個噴著“文化局”字樣的滅火器。除此以外并無撥款幫助修繕,再加上經年累月繁復的公文往返與周旋,將謝東昇置于老屋翻新和古跡維護皆不得的兩難境地。但事實上,根據《文資法》規定,謝宅作為私有文化遺產,其保存修復責任本就落于所有人與管理人本身,亦即矛盾重重的謝家繼承人群體中。這一情形并不罕見,一份臺北市文化遺產保存失敗案例的調查報告顯示,臺北市有一大批文化遺產面臨著與謝宅類似的處境,其失敗原因歸根于家族繼承人之間的意見矛盾造成的拖延、部分繼承人消極參與、自籌資金不足等[19]。在謝宅這個案例中,甚至還發生了數次被人惡意縱火的局部急性損毀事件,謝東昇及學者們判斷極有可能是鄰里或家族為求土地能擺脫地上建筑物遺產指定的束縛,恢復其市場價值而為。
既然成為公共的古跡后,其“空間再現”是一個靜態的、完美的、可以被預設的終極狀態,且這一狀態需要真實空間實踐中的私人權益的讓渡。那么,縱然各行動者對此“地方”都有著公共記憶與情感、有延續傳統的認知、甚至有家族生活與生計的依賴,這個地方依然是被“捐”為了不屬于與這個建筑最為相關的行動者們的“公共財產”。謝宅的私產身份未能獲得“公共”的接管,卻又成為鄰里與家族其他方的絆腳石,因而尤顯孤立無援。
4 地方認同層面的孤獨
在公共記憶方面,謝宅保護尚有許多同盟:家族中謝東昇一脈的保護派、幫助推動保護工作的專家學者、文化局關心此事的官員、萬華都市更新中活躍的古跡保護工作者、網絡上的關注者等。但是在地方認同的層面,亦即文化遺產所牽涉的家族、社區乃至保持關注的周邊人們是否發展出自身對于此地的歸屬感,現狀的謝宅給出的答案卻更加不盡人意。
在這一點上,謝東昇及其家人在敘事中表達出自身與謝宅之間極其強烈的聯結關系。除了自身在老宅的居住歷史外,謝東昇的地方感還包含了對于宅邸保存下來的清朝時期豪華且精致的用料與工法、清時祖訓的宏大敘事,以及宅邸風水講究等的驕傲與認同。例如,在說到天井中所用石材時,謝東昇說:“這是泉州才有的石頭,我們從大陸過來船運,要幾十年甚至幾代才可以建造這個房子”——此為對老宅歷史的夸大;在領著筆者參觀第一落日據時期改建的騎樓時,謝東昇指著外柱的斷面反駁了專家的鑒定:“這全都是中空的,空氣都往上爬,所以說完全是隔熱的。專家說是偷工減料,當然不是!”——此為對專家講述的對謝宅不利的建筑知識的反駁……在經年累月的知識積累與親身體驗中,謝東昇構建了一套關于謝宅的令人驕傲的敘事系統。不難發現,其中加入了許多夸大甚至虛構的部分。時間線索在細節中被打碎和模糊化,日據時期的印記被刻意忽略,盡可能地向清朝時期歷史靠攏,甚至還包含了與學者代表的“知識”的對抗、對外人定義的否定等。列斐伏爾認為,再現空間具有“想象”的特質,“想象”尋求對這個空間進行改變和占據。在這個案例中,屋主在再現空間的層面上,形成了自己的圖像與符號系統,構建了地方對于自身的意義。
可惜的是,對于其他的行動者來說,這一層面的意義是缺失的。文化局于2001年委派學者制作的《臺北市定古跡艋舺謝宅調查與再利用規劃》,是為客觀詳實記錄“真實”的謝宅現狀,并不包含任何非物質部分的記錄與解讀。并且,該報告所記錄的建筑物現狀也存有疏漏差錯,部分歷史記載亦與當地地方志及口述史有所出入。在社區推動地方文化保存行動中,謝宅也被排除在萬華歷史的整體敘事外。大體的原因在于,它既不屬于區域內貴陽街或青草巷這樣的街區式歷史文化遺產,不具有群體性的日常生活空間敘事的體量;又不具有宗教或商業等公共屬性,無法被納入艋舺社區博物館導覽路線,而作為私宅常年大門緊閉,喪失了傳統展示的趣味性與商業性。因此,不再有人講述謝宅的故事,它與人之間斷了聯結,失去了人為構建的意義,也可以說,喪失了“想象”。這樣的文化遺產只剩下物質空間這個空殼本身,它固然投射著曾經的社會關系,但卻不再是“活生生的”。
5 結論
索亞提出的第三空間在理論上是開放的,甚至可以說是模糊的。索亞特別指出了這一點:“我將第三空間定位理解和行為的一種他者方法,目的在于改變人類生活的空間性,它是一種獨特的批判性空間意識,正可適應空間性—歷史性—社會性重新平衡之三維辯證法中體現新范域、新意義。由此開始一個漫長的故事或者說旅程。[8]10”本文受到這一批判意識的啟發,針對具體的文保案例,展開一段深入的探索。實際上,本文的分析依然不是落在“真實”空間,就是落在“想象”空間,但索亞的視角提示我們注意到了兩種空間的多元層級,以及它們之間并不總是對立的關系——并非僅有《文資法》及其所代表的的文化遺產制度體系建構了謝宅的想象空間,社區對于謝宅作為區域傳統的認知,以及謝東昇本人將謝宅的傳統元素符號化與敘事化的行為,都展現了謝宅在想象空間層面可以具有的厚度;也并非僅有在測繪、丈量、顯示交換價值的土地圖紙或顯示建筑價值的調查報告中才是謝宅的真實空間,謝家投射于空間劃分與空間處置意見上的家族關系網、謝東昇堆疊成山的資料中展示的謝宅不同于官方記錄的歷史,同樣在現實中構成謝宅的真實空間。
謝宅是文化遺產保護中一個非典型的個案,卻也是一種遺產保護模式的原型。它離公有的、最具公共性的、最經典傳統的建筑遠,也就距離家族與個人、鄰里,以及不經典的日常生活近。如果文化遺產保護缺失了對真實與想象之間的厚度的關注,那么謝宅作為一個具有社會意義的建筑空間,便被簡化為一個兩極化的空殼,一極是這個房子的一磚一瓦本身,另一極是被貼上“文化遺產”標簽,成為“時間的異托邦”的終極完美狀態。前者是與“人”無關的,后者則是謝宅作為一個“非典型”的古跡,它所涉及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所無法達到的。
在空間知識系統的分類規則下,我們應當重新反思那個遙遠的終點是否適用于每一個遺產個體。許多具有歷史價值的建筑在面對私有的權屬、公益的價值與不完好的現狀時,或許可以放棄一躍而成為“文化遺產”,而是將重點放在“成為”文化遺產的過程上。這意味著始終關注所有的空間厚度,始終容納各個行動者的不同目的并建立協調引導,建立社會效益與資本的良性互助機制,甚至納入更多的行動者,如民間文保機構、信托機構等。在這個過程中,也將重塑遺產保護的公共領域,使“公共”與“私人”的范疇能夠被討論,即便是少數人的權益也能夠被協商。這些過程并不全指向知識性的文化遺產標簽,而是指向真正的永續保存。
筆者還要指出的是,地方感作為本文分析框架的一個基礎,在文化遺產保護中并不是新鮮概念。但具體地挖掘某個歷史建筑能夠塑造的地方感的不同維度和程度,以及評估地方感對于推動保護工作的效用,依然能夠對理解一個建筑遺產的社會空間有新的啟發。
最后,盡管謝宅的保護現狀不如人意,且結構性的矛盾似乎無法形成一致的推動力,但我們依然可以用“成為”遺產的過程性目光看待它——現實也正是如此,在本文寫作的過程中,新的《艋舺謝宅修復及再利用計劃》也在醞釀,謝宅的真實與想象空間依然在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