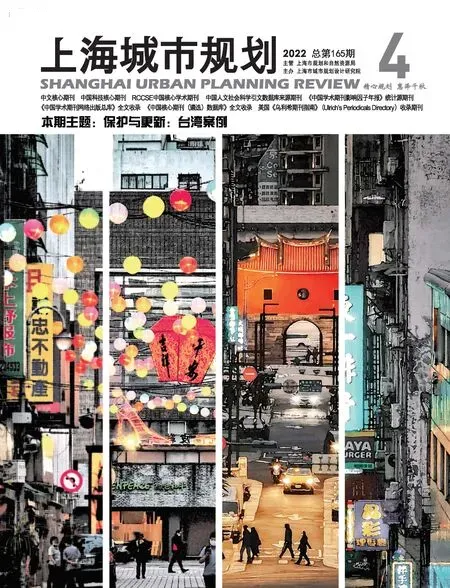臺灣地區產業文化資產轉型的批判性回顧
柯楨楠 吳一凡 KE Zhennan,WU Yifan
0 引言
自1995年集集車站保護運動開始,臺灣地區逐漸對產業文化資產存續加以重視。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原貌保護后,2006年臺灣地區行政管理機構下屬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建會”,其于2012年改制為臺灣文化事務主管部門)展開了《文化性資產再生事業計劃》,以推動其強調再利用的保護模式。至2012年《亞洲工業遺產臺北宣言》發布,臺灣地區已經有45項被登錄的產業文化資產。至2022年,名錄已達到49項,成為亞洲地區產業文化資產保存數量最大的地區,相關保護再利用實踐經驗的豐富程度不言而喻。根據社會價值及功能,臺灣地區產業文化再利用可以分為5大類別:文化產業類、經濟產業類、交通產業類、博物館類、非營利組織類[1]。由于文化創意產業和產業文化資產具有高度的相互適應性,以文創產業為導向的再利用模式成為越來越多產業文化資產復興的第一選擇[2]。
所謂文創產業,臺灣地區有關規定說明,指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的形成及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的潛力,并促進民眾美學素養,使人民生活環境提升之下列產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以下簡稱“文創園”)則是讓原本產業失去效用、停止生產或運作,或指定為古跡、歷史建筑物類型者成為文化創意產業的載體,在生產文化創意產品、創造產業經濟價值的同時,使產業文化資產得以更好地保存和活化再利用。在后工業時代轉型背景下,臺灣地區的文創園在發展上遇到明顯的困境,如激增的園區數量與不斷減少的進駐廠商的自相矛盾,參觀文創園區人數與進駐文創業者實際營收的差距懸殊,投入大筆預算而營業額卻不如預期等。本文旨在透過臺灣地區轟轟烈烈的產業文化資產轉型為文創園的表象,從價值認同、地方感的塑造和常民生活的回歸3個角度,探究其缺陷所在,并試圖討論一種轉變的可能性。
1 亦喜亦憂:產業文化資產轉型為文創產業的必然性
1.1 臺灣地區產業文化資產保護發展脈絡
Industrial heritage在臺灣地區的翻譯除了工業遺產之外,還有產業遺產、產業資產、產業文化資產等。目前臺灣地區有關規定均采用“產業文化資產”的通稱來表述曾經具有生產性質的建筑物、設備等人造物與人造環境遺存。在描述臺灣地區的此類遺產時,本文采用“產業文化資產”一詞。
回顧世界產業文化資產保護發展史,可以看到“工業考古學”一詞于19世紀末就在英國被提及,經過100年的發展,至2003年國際工業遺產保護委員會(TICCIH)在俄羅斯下塔吉爾通過的《下塔吉爾憲章》,宣告世界產業文化資產保護時代的全面來臨。2012年,TICCIH在臺北市舉行大會,這是TICCIH大會第一次在亞洲城市舉行,彰顯了該國際組織對于亞洲地區日益受到威脅的工業遺產的特殊關注。
20世紀初,日本在臺灣地區主導興建大量的工業廠區及鐵路系統,將其產品作為日本的物資補給。到20世紀后期,由于產業結構的更迭和轉型,這些工廠和鐵道逐漸被閑置甚至廢棄。自1990年為保護集集鐵路而成立促進委員會開始,產業文化資產的保護觀念逐步受到臺灣學界和民眾的認可和重視。隨后發生1995年臺灣交通大學爭取保存彰化扇形車庫、1997年藝術家推動臺北酒廠的保存等事件,臺灣地區的工業遺產在一次次民間發起的保護運動中,推動臺灣當局在組織機構和制定相關規定上逐步前行。該階段專注于靜態保護。至2003年,臺灣當局成立“產業文化資產調查小組”,并發行“產業文化資產清查操作參考手冊”,開始了全面清查階段。對于產業文化資產的再利用則始于2002年提出的5大創意園區計劃,2006年和2010年又分別頒布第一、二期《產業文化資產再生計劃》。臺灣地區的產業文化資產再利用在“歷史保存運動”“永續環境的關注”“產業結構改變”和“都市計劃的結合”4股力量的作用下成為勢在必行的舉措(見圖1)。
1.2 產業文化資產“跟風”轉型文創園
文化資產可視為一種“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3],產業文化資產則多了一層空間場域的資本屬性。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中,文化創意產業的概念來自為了落實文化資產保護、利用和推廣,將文化資產轉換為一種可操作的經濟模式。
臺灣地區的產業文化資產大量轉型為文創園有其必然性。自1995年“文建會”提出“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概念后,又于2002年由臺灣地區行政管理機構確立了文化創意產業這一發展項目,也是在同年,“文建會”正式設立華山文創園區,并在2006年定位為推動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旗艦基地。華山文創園的成功讓其他產業文化資產的轉型看到希望。2009年臺灣當局進一步推動5大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計劃,包括華山文創園區、臺中文創園區、花蓮文創園區、嘉義文創園區和臺南文創園區[4],這5大文創園區均由舊酒廠轉型而成。以此為發端,臺灣地區的工業遺存紛紛轉型為文創園,如制煙廠改造的臺北松山文創園區、碼頭改建的高雄駁二藝術特區等頗受關注者,當然也有既無規模支撐又喪失自我特色的盲目跟隨者。
根據臺灣文化事務主管部門的產業文化資產登錄情況,已登錄的49個產業文化資產中,改造為文創園的有18個,改造為博物館的有10個(見表1)。可以看到在產業文化資產的再利用中,文化創意產業成為一個主要的取向。
根據臺灣文化事務主管部門所發行的文創年報中的資料顯示,2002年至2008年,文創產業營收平均以每年7.58%的速度成長,從2009年開始,文創園的個數還在不斷增加,但是營收成長率僅剩下2.76%[5]。2014年到2021年,臺灣文化事務主管部門所屬園區在委外營運期間共計創造55.3億臺幣的收入,但是營運管理者投入了57.1億臺幣的支出,總體來看入不敷出,營運者急需相關營運協助[6]。如駁二藝術特區在臺灣當局的大力扶持和推廣下經歷了2009年前后的一波發展高峰后,參訪人數還是逐年減少,許多經營者都表示合約期滿后不會再續約。
雖然當下文旅市場的蕭條與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直接相關,但許多文創園在疫情前就已呈現頹勢。臺灣學者提出“創意文化園區是強心劑還是打錯針”的疑問[7]。這些工業遺存在“停產”后再一次面臨“休眠”,縱然有外部的不可抗力,但其內在結構性缺陷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
2 孰是孰非:轉型為文創產業的困境探析
2.1 不被認同的價值認知
產業文化資產的認知主體來源廣泛,不僅有技術史研究者、工程師、產業建筑師、保護人士,還有普通民眾。不同主體有不同的價值偏向。專業人士再如何熱情地評價這些建筑和設備的技術價值,也需要大眾有同樣的熱情才行。而一般民眾對文化資產的認知止于名勝古跡的觀光游玩,或藝文空間的消費取向,文化資產中的無形價值卻難深植于民眾心中。民眾看到“林百貨”①林百貨于1932年建成,是南臺灣第一家百貨公司,是日據時期臺南末廣町繁榮的象征,配備南臺灣第一座商用電梯,號稱臺南銀座。1945年太平洋戰爭后停用,1998年被定為市定古跡,2014年修繕完成,以臺南文創百貨店的形態而獲得新生。并不會聯想到“展現日據時期富裕階級的社會形態”,游覽松山文創園時也很難去體會“臺灣煙草制造業與太平洋戰爭的關聯”②松山煙廠是臺灣第一座專業的卷煙廠,建于1937年,日據時期是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松山煙草工場。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后,卷煙除供應臺灣市場所需,也外銷華中、華南及南洋地區,供不應求。1998年停止生產,2001年由臺北市政府指定為第99處市定古跡,2011年開放為松山文創園區。。
臺灣地區文化資產的價值認定原則取決于所謂“文化資產保護法”及相關規定。一般在產業文化資產的調查研究階段,多是針對其稀有性、特殊性、歷史文化等進行調查,局限于修復層面的探討,較少著墨在如何將保存教育和文化宣傳的思維植入后續活化再利用的規劃設計構想中。因此在產業文化資產的保存和活化過程中價值認知的差異就會導致諸多的矛盾和阻礙。
高雄煉油廠的產業文化資產資格認定過程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它作為臺灣地區第一個煉油工程,“遍布了20世紀不同時期的歷史痕跡,呈現不同時代的硬件技術典范,也是見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現場,是臺灣石油產業技術與環境教育的活教材”。以上均是官方和專家對其的評價,實際上周遭社區民眾對于重工業設施充滿了負面的觀感,并不愿意其作為工業遺產留存。目前暫時僅宏南宿舍群被登錄為文化資產,對其他設施和廠區還在進行文化資產調查和討論。除了普通民眾的不理解,在2015年宏南宿舍群被登錄為文化景觀時更是因為登錄范圍的擴大而遭到臺灣中油公司的強烈反對。臺灣中油公司在2016年甚至對此事提起行政訴訟,但是最后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還是宣判高雄市政府勝訴。
高雄煉油廠的文化資產資格的認定,交織著來自政府、地方、產業、社區等不同來源的價值認知和強烈訴求。但是最終的結果對于民眾而言或許仍然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精英式決定,信息不對等的情況依然存在。而這種信息不對等造成的沖突不僅發生在資格認定的過程中,在其后的活化再利用中也一樣存在。
2.2 千篇一律的地方感
《建筑的復雜性與矛盾性》中,文丘里認為復雜與矛盾背后都有一個整體性以及一種內在的秩序、美學標準或統一的概念[8]。產業文化資產保存和再利用的復雜與矛盾皆來自其有形、無形的價值中,只是當代的修復及活化再利用的規劃形態,多是透過法規的限制,以拆解的方式討論著那些看得見的東西的去留,而無法讓看不見的價值本身得以在既存的空間中展現出一個完整的架構以表現其原本豐富的意涵。
從多個臺灣產業文化資產的調查評估計劃和真實的設計開發案例中不難察覺,調查評估計劃時期待以靜態的殘跡保存方式來重現遺跡的真實。這種方式往往流于形式,是一種“被簡化的真實”。在實際的開發活化過程中,文創園模式借由商業型態導入,把所有東西湊在一起,使其呈現為一種缺乏組織的拼貼,或可稱其為“拼湊的再現”,喪失了屬于文化資產的整體性和獨特性。所以,雖然臺灣當局在設置5大文創園區時針對個別園區提出了定位,但營運至今,較難看出5大文創園區有何差異,都成為展覽、表演、餐飲以及提供文創商品販賣的復合式商場。在產業文化資產活化過程中,不注重產業原有的歷史紋理,新用途與原有產業斷裂,在看似真實的物質空間呈現的同時,“地方感”卻消失了。大量同質的文創園遍布臺灣,一樣的文化元素重復在每一個園區里,呈現的是一種囫圇的“地方感”,“五分車像葡式蛋撻、滑板車、桶仔雞一樣,只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那一列不斷兜圈子的臺糖小火車像是迪士尼樂園里的游樂設施一樣,除了搖晃的樂趣之外,我們還得到什么?”[9](見圖2)。

圖2 臺灣地區各文創園區重復出現的各種臺糖小火車Fig.2 The Taiwan Sugar Train that appears repeatedly in variou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s in Taiwan
2.3 被忽視的常民生活
工業設施在其生產、儲運等原有功能完結后,確保不會因為生產的再發展而破壞構成歷史的要素后才有可能進入遺產序列。也就是說,工業設施在失去其產業價值退出經濟循環后,再通過文創產業以其文化資產這項資本再次進入經濟循環,所謂“文化再生產”。產業文化資產轉型為文創園后,一方面它就成為或被期待成為一個文化生產的場域,另一方面各方角色同時對其產生不同的價值需求。政府的考量在于“政績”,投資者目的在于“獲利”,文創從業者的需求是“平臺”,而作為文創經濟的終端,普通民眾既是居民又是“消費者”,需要的是“生活”和“共鳴”。
臺灣地區產業文化資產的開發多采用BOT模式③BOT(Build興建,Operation營運,Transfer移轉):政府提供土地,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并營運,營運期滿,該建設所有權移轉給政府。除此之外還有BOO、OT、ROT等政府與企業合作開發的形式。,如華山文創園,即由政府主導和持有,民間機構投資并運營。這種模式雖然可以減輕政府的財政壓力,但是民間機構需要自負盈虧。在資本引導下,商品化的文化更容易失去其獨特性,并趨向士紳化,而政府也更希望文化的建構與生產能夠為其增加城市吸引力,所以通過政策引導在園區內設立大型場館或藝術中心,此舉僅對城市精英而非一般大眾有利。與此同時也引來了許多房地產開發、投機,由此造成地價飆漲、租金上浮,導致真正的文創業者或者藝術家無法負擔而無奈搬離。文創園已然成為炒地皮的工具,也就有了2014年在松山文創園區爆發的“假文創,真炒房”事件④松煙文創案起因于臺灣大哥大進駐松煙文創大樓,被外界質疑松煙是假文創,引發“假文創、真炒樓”的爭議。文化局要求運營方改善過度使用文創大樓的情形,但運營方反擊,認為市政府開的條件不合理,強硬建議市政府照價買回。臺北市都發局長林洲民直指財團是“無本、求暴利”,讓藝術家成為二等公民,再掀爭議。。
除了考慮政府、產業、藝術家的需求,不應遺忘這塊場域上生活的普通民眾,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無法離開此地的原產業員工或者是依賴原產業的服務人員。他們不能憑借原有經濟循環繼續生活,也很難進入新的文創產業的經濟循環中獲得收益,且不具備創意產品的消費能力。原有的社區功能被拋棄,在地人的需求被忽略,失去生活機能,也就失去“共鳴”,所謂新產業也就成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
3 出世入世:價值認同、地方感的塑造與常民生活的回歸
2012年《亞洲工業遺產臺北宣言》提出:“第五條:亞洲工業遺產是綜合性文化景觀的一部分,無論農村或城市,除了內置的環境,它強烈反映了人類與土地的互動,具有異地地形的特征;第六條:亞洲工業遺產與西方世界殖民國密切關聯,它反映建筑和技術及歷史美學、科學價值的完整性,應被保留;第七條:亞洲工業遺產的機械操作和必要的技術知識體現在當地居民的技術人員上,因此操作技術和相關的檔案和文件都應被保留下來;第十條:亞洲工業遺產與當地人民有著密切聯系,因而當地人民應該被鼓勵參與并與工業遺產密切互動。”[10]《亞洲工業遺產臺北宣言》不僅為臺灣地區的產業文化資產正名,增強產業文化資產的身份界定,也為在臺灣地區《文化資產保存法》中未能明確的保護活化行動提供綱領:如何體現人與地的關系,如何讓產業特征保留,如何讓當地居民進入文化資產的再生產。在眾多再利用案例中,都能看到臺灣地區在某些方面做了有意義的嘗試和努力。
3.1 強化民間參與,促進價值認同
與古代遺跡相比,產業文化資產的價值始終難以被大眾普遍認可。在歷史性上,它從生產機構轉化成遺存的時間距離當代過近,在藝術性上,又往往缺乏主流審美的共識。在《巨獸:工廠與現代世界的形成》中,作者提到一些歐美學者把對廢棄工廠的懷舊稱為“煙囪懷舊”或“戀廢墟癖”[11]。因此,工業遺存成為文化資產更需要多維度的認可,而不僅是某個民間團體的一腔熱情或是政府的獨裁專斷。因此,臺灣當局希望通過制定有關規定,一方面修正充滿威權及學者精英主義的文化資產認定過程,另一方面借由提升民眾對于文化資產的正確觀念來推動文化資產保存再利用的執行。
1982年頒布的《文化資產保存法》沒有給任何民眾文化資產的申請或提報權力。2000年,在其修訂的27條及27-1條指出:“各級主管機關得接受個人與團體之古跡指定、歷史建筑登錄之申請,并經法定程序審查之”。這個改變說明民眾有了文化參與權,但是在界定范疇、評估方式、登錄機制、操作管理方法及分級分區等實質工作上很多內涵是模糊而有待詮釋的。2016年的修正案對上述問題進行了補充,并再次強化保障文化資產保存普遍平等的參與權,并擴大民眾參與程序。
修正案公布實施時,時任臺灣文化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指出:“文化保存是觀念,文資法是底線,如果人人有文資觀念,其實根本不用有文資法。”所以此次的修正案中“文化資產保存教育”首次公告實施,增訂理由為:鑒于政府、機關人員及民眾缺乏文化資產的認識與保存觀念,亟需借由學校教育體系,使民眾得以自幼培養文化資產保存觀念,故增訂實施文化資產保存教育的規定[12]。其目的是提升文資觀念,但依賴的手段還是關相法律法規。
雖然當下執行的《文化資產保存法》還存在諸多各方詬病的問題,尚處于“查缺補漏”的狀態,但是文化資產政策由“威權”轉向自下而上的公眾參與,并重視民眾的文資觀念提升,可以讓原本不容易被認同的產業文化資產價值再詮釋的情況得到改善,不失為一種進步。
3.2 地方感的塑造
Dicks B[13]曾提及,文化遺產是現在社會里一種依附過去意識的文化重構,經過地方一連串的形塑后,文化遺產可以被視為建構過去的一種代表。有別于其他古跡或者歷史建筑等傳統單體建筑的保護形式,工業遺產通常是整個空間的保存方式,可以為過去產業歷史提供絕佳的實證場域,通過對場域物質和非物質的多角度闡釋,讓大眾了解其價值和意義,來建立公眾的集體想象,并推動地方感的建立[14]。
建構地方感就是要關照到遺產和所在場域的特殊性,并讓某些歷史記憶得以彰顯,將人與土地之間的情感強化在工業遺產這一標的物上。在臺灣橋頭仔糖廠轉型中,特別注重歷史記憶特殊性的塑造。一方面臺糖公司注重的是工廠本身的歷史、器物、廠房以及制糖技術方面的保存;另一方面當地的民間組織文史協會則進一步在地方文史和地方特色上尋求突破,并輔以藝術和影展的方式。最典型的就是“藝術村”和“金甘蔗影展”[15]。2001年糖廠成立藝術村,進駐的藝術家在當地的文化特質中尋找創作靈感。比如在田野上創造一只巨大的毛毛蟲裝置藝術,路過的人都會驚呼“有蟲誒!”“有蟲”的閩南語就是“有糖”,與糖廠意象契合,與閩南語系的人產生共鳴。藝術村開啟了藝術在地化的許多可能,當地居民也能在此接觸到多種藝術形式并參與其中。又如金甘蔗影展的命名直接來源于糖廠的生產資料,該在地影展提出“現地拍攝、現地后制、現地影展”的思維。通過影展這一活動,用影像的方式創造并宣傳在地的故事,也是基于一種文創產業構思(見圖3)。可以看到在文化的傳播上,不只是借助單調的歷史物件展示,而是通過一些活動來“炒作”,讓看不見的文化資產活化再利用,重現糖業文化并獲得收益,這種節慶化的模式在產業文化資產的地方意象建構中不失為一個可取的途徑。

圖3 金甘蔗影展活動現場Fig.3 Golden Cane Film Festival event site
3.3 常民生活的回歸
英國社會學家保羅·威利斯提出,文化生產的文化實踐,其功能在于洞察或“看透”他們的生存狀況,從而從他們的角度決斷出最有利的身份和行動,以及可提供的制約和條件[16]。在高雄煉油廠案例中,雖然在公共部門主導的維護計劃討論中,更傾向于將其作為展示產業的博物館保護起來[17]。但是在開發計劃還未明確時,宏南宿舍區已被頻繁提供為婚紗照、電影、電視劇、廣告的拍攝場地,園區內福利社的冰品、點心,以及宏南餐廳在持續對外營業。園區內的體育館、教室等也自行舉辦社區活動。在地社區用自己對這個“資產”的認知及需求,自發對空間進行再利用,讓他們獲得歸屬感的同時對產業文化資產產生認同。此舉也影響了后續的維護計劃,將社區居民的需求考慮在內。
上文提到的橋仔頭糖廠則將社區營造的力量在遺產保護與開發中發揮到極致。以社區民眾的需求為出發點,閑置的空間成為社區活動中心,廠區成為在地公園,將空間盡可能地還給這塊土地的民眾。而橋仔頭文史協會作為推動者還在此創辦了一個公共論壇——轉型月臺。文史協會定期邀請專家學者就一個地方上的公共性議題與民眾對談互動,近幾年又慢慢加入社區居民感興趣的活動,比如邀請臺灣環境資訊協會主任來談《環境信托作為棲地保育途徑的可能性》,臺灣云林科技大學講師來講《如何搶救臺灣糖業文化資產》等。該模式進一步將居民拉進場域中討論公共事務,成為當地居民了解此地社會議題的一個平臺,也有助于在地團體對文化資產營造的觀念進行宣傳。這些舉措從常民生活出發,卻不止步于還原日常生活,而是植入空間和文化藝術的力量,致力于提高民眾對身處土地的認識及提高常民的文化認識。
4 結論:復層意義下的產業文化資產身份建構
早期工業遺產被視為一般文物古跡,其維護只能依賴于相關政府部門的資金補助。文創園的出現讓產業文化資產可以與新型商業模式有機結合,使其可持續發展,同時又使文化得以再生。在這個層面上置入文創產業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但臺灣地區近30年的產業文化資產保護和再利用的經驗所呈現的種種問題也在向我們發問:為什么要保護?這些衰退的工業遺存的特色到底在哪里?如何避免產生“后工業問題”?只能做文創嗎?是為了文創而文創嗎?它能為地區帶來什么?為常民的生活提供什么?在政治、經濟、傳媒等權力場域控制下又如何進行身份重構?
Bourdieu P[18]在其《文化生產場》中指出,“在把文學和藝術作為‘存在著不同位置以及位置斗爭(position-taking)’的場域去理解時,我們要脫離開那種傳統的二元對立困境,即單純采用一種內部的(internal)只分析作品文本或其領域,或外部的(external)只分析作品生產和消費的社會條件的視角”。當工業停產后,作為文化資產進入再生產領域,那么就不再是單純的具有“自律性”的文化創作,不可避免地成為與權利、經濟場域勾連的“他律性”生產。所以,產業文化資產再利用的本身具有歷史面向,同時具有未來面向,既有文化屬性,又離不開經濟生產,它的發展矛盾又充滿張力。本文通過拆解臺灣地區產業文化資產轉型中的典型問題,反思以盈利為導向、盲目跟風的文創開發帶來的空間異化對文化資產價值的背離,地方紋理的斷裂,以及與常民生活的割裂,同時也在那些積極回應上述問題并探索在更具有“公共性”的永續發展道路的轉型案例中尋找鑰匙。
本文僅局限于臺灣地區產業文化資產轉型為文創園的普遍問題分析,在全球視野下,其他地區也有共通的問題,或者是卓有成效的轉型經驗,其背后深層次的動因有待進一步研究探索,以期找到產業文化資產轉型的更多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