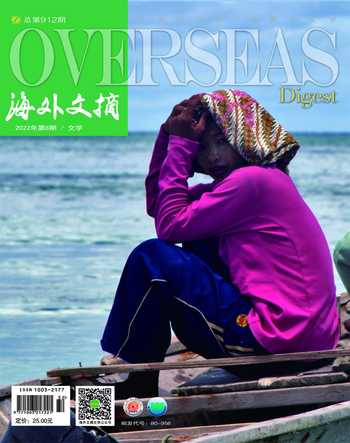補鍋強
2022-05-30 18:25:02黃康生
海外文摘·文學版
2022年8期
黃康生

小雨初晴的清晨,我還在睡夢里,就聽到了“補——鍋——嘞,補——鍋——嘞”的吆喝聲。那吆喝聲拖著長長的腔調,飄蕩在村子的上空。
我一骨碌從床上爬起來,然后三步并作兩步奔向打谷場。
補鍋強早已在打谷場支起風箱,架好爐子,生起炭火。“補鍋啰,生鐵補鍋!”補鍋強掄起鐵榔頭,噼里啪啦一陣亂打,將生鐵片砸碎,然后把碎片嵌進如小碗般大小的坩堝里……
突然,一條土狗從打谷場的草垛里躥出來,盯著補鍋強齜牙狂吠。補鍋強彎腰下蹲,拾起火鉗。土狗急促轉頭,一溜煙逃遠了。
“汪、汪、汪……”孩子們踩著土狗的叫聲從村頭村尾聚攏過來看熱鬧看稀奇。幾個頑皮搗蛋的小家伙圍著補鍋強打轉起哄:“補鍋嘞,補鍋嘞,補你爹的耳朵嘞!”
補鍋強板起臉,一臉嚴肅,濃黑的眉毛擰成了一個結。但這些搗蛋鬼仍不知趣地向補鍋強扮著鬼臉。補鍋強不由心頭火起,抓起火鉗啪啪亂舞。幾個搗蛋鬼哄的一聲,嚇得四處逃散。
“新鍋沒有舊鍋光,扔了舊鍋菜不香。”大人們紛紛放下手里的活計,提起穿孔、開裂、爛洞的鐵鍋來到打谷場。很快,打谷場便堆滿了大小不一的銹瘡鐵鍋。
村民們圍著補鍋強打哈哈,講價錢,談家長里短,生活瑣事。
村民們說,過日子離不開一口鐵鍋,鐵鍋燉煮著村子的酸甜苦辣,也暗藏著村子的生活密碼。
那年月,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一口大鐵鍋。村民如自立煙火,再窮也會買口新鐵鍋。鐵鍋通常用生鐵鑄成,用久了,鍋底就氧化生銹,一層層脫落,最后燒成破洞。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