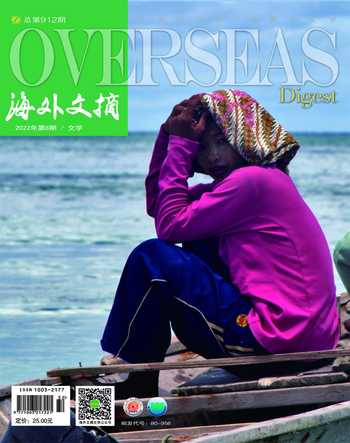我的干媽
2022-05-30 18:25:02張文龍
海外文摘·文學版
2022年8期
張文龍
我的干媽沒有生養一男半女,只抱養了兩個孩子:兒子是她的侄兒,女兒是我的幺妹。
干媽家與我家相隔20 分鐘遠近,同一個大隊。干爹是生產隊會計,人很高大,身子骨頗壯,講話膛音極重,如敲銅鑼。干媽的身子卻極瘦小,且患有暈病和氣管炎。干媽由于有病,不能參加集體活動,便在家做家務、種自留地。干媽給許多孩子做過保姆,卻是寄養在她家,最大的是帶到3 歲便被領走了。干媽依依不舍地送走一個又一個孩子,她多么渴望有個女兒呀!后來,我的幺妹抱給干媽喂養了,干媽自是歡天喜地,將她視若掌上明珠,寵愛至極。
干媽的家住在黃家灣,村頭的水井邊長著兩三棵古老的黃桷樹,現在算起來大約也有兩三百年的樹齡了吧!據干媽講,其中一棵黃桷樹成了妖,常常于夜間從樹里出來,專門勾引人家的少年郎,將他的血吸完至死。干媽嚴重警告我,千萬別對黃桷樹撒尿,否則那妖辨著人的尿氣,找上對它撒尿的孩子——最后吃掉他。那棵妖樹的身上牢牢地釘著好些顆耙釘,這是被害兒郎的父母們對妖樹的報復,證據確鑿,更令我們深信不疑。另一棵黃桷樹顯然不是一伙的,有一戶人家的廚房廈子正借它的半邊身子做基做墻,炊煙一道道裊裊婷婷地逗著黃桷樹的枝葉揮舞。環繞村莊的全是一年青水竹,冬天葉便掉了,村子的房舍便凸現出來,一目了然。春夏從村外又看不見村子,干媽村里多半人家搞副業,打籮筐、背篼和竹椅子等,生活過得殷實。……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