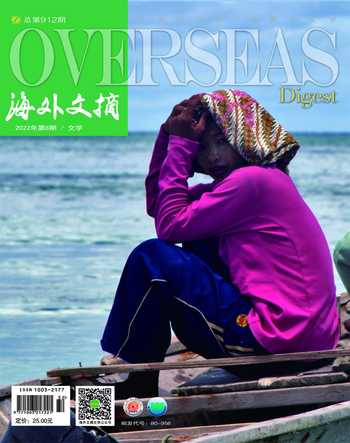你的一生要和誰相遇
2022-05-30 18:25:02李娜
海外文摘·文學版
2022年8期
李娜

一
他,身材魁梧,穿著洗得發白的中山裝,頭上戴著大檐帽,腰里別著水壺,提著馬鞭走過戈壁曠野。
大片羊群散落在房子四周,喝水、追逐、吃奶、嬉戲、咩咩叫,卻無人來管。我仿佛踏入一片黃熟的麥地,四顧茫然,不知該從哪里開始收割,又仿佛誤入他人花園的訪客,為踩壞一枝玫瑰而心懷愧疚。靜靜立著,試圖從羊群里找到熟悉的那只,抱著它撫摸柔軟的羊毛,把臉埋在它的脖子里,把額頭貼在它的額角,聽它奶聲奶氣、嬌憨綿軟的叫聲,然后滿足地喟嘆。好像在很久以前,我已經做了無數件這樣的事情。
生命是一片越走越窄的戈壁灘,年輕時腳程過萬,走到哪里都覺得天地狹窄,并且一定要去更遠處拼命折騰,以此證明自己有力挽狂瀾、氣吞山河的本事。中年時偏安一隅,像是忘記了年輕時的抱負一樣茍且生活,為不得已和無可奈何終日奔波,對青春、理想絕口不提,好像自打生下來就是中年人的模樣。老年時干脆哪里都不想去,囿于眼前這一小片地方茍延殘喘,喉嚨拉風箱一樣呼哧呼哧地響,卻吐不出一個有力的字眼。這是規律,也是進程,與出生在哪里、生活在哪里沒有關系。在某種意義上,都市與戈壁沒有區別。
他的鞋底越磨越薄,走過的地方越來越多,在甘肅乞討,在阿盟放牧,在錫林郭勒盟同場,在城里生活,每個階段都會遇到不同的人。他們在深夜把酒言歡,劣質烈酒一杯接一杯下了肚,彼此間的感情也越來越真摯。那時他還不懂推杯換盞、酒過三巡這兩個詞,只覺得一仰頭灌下去的動作無比痛快。……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