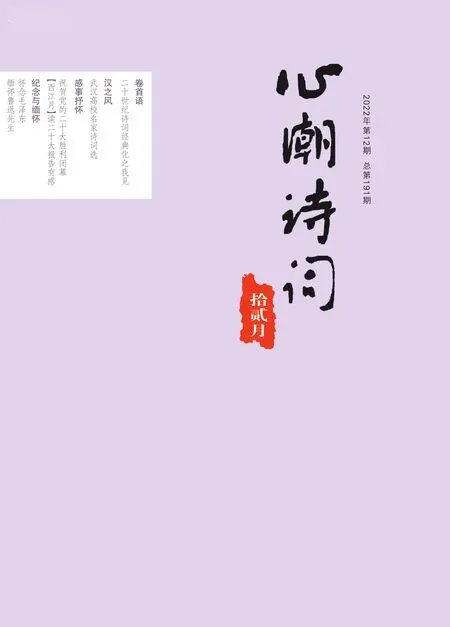我在北京的課讀生涯
施議對
1964 年9 月,我考上杭州大學研究生,在夏承燾先生門下學習宋詞。“文化大革命”中斷學業。1978年10月“重新報考”,入讀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在吳世昌先生門下繼續學習宋詞。1981 年7 月畢業,獲頒文學碩士學位。之后,在《文學評論》任編輯。1983 年10 月,攻讀博士學位,在吳世昌先生門下研習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方向為詩學與詞學。1986年7月,通過博士論文答辯,獲頒文學博士學位。完成博士學業,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一度與陳圣生、蔣寅合作,組建中國詩學研究組,創辦中國詩學研究叢書及《中國詩學》雜志。1991 年2 月,由北京移居香港。總的算起來,我在北京的課讀生涯,大略經歷十二年又四個月。
在京期間,碩士三年寄居北京師范大學西南樓,六人合居一室。讀書、寫作,相關事項待另撰專文記述。以下說說碩士畢業后,曾經居住的三個住所:東直門外西八間房、東城趙堂子胡同、望京麥子店。
第一個住所,東直門外西八間房。這是個簡易四合院。我和文學所幾位剛畢業的同事住在這里。我住北屋最邊上一個房間。由于入住不久,已接近生爐子季節,加上郊外冷得比較早,每當刮風下雨,爐子熱不起來,而床頭屋漏,便很難尋覓得到一個干燥地方,因此,我將自己的這一住處稱作“水深火不熱”齋。書齋名稱尚未正式啟用,但因劉再復的政協提案,卻已登上“政協簡報”。我的一闋小詞《沁園春·憶課讀生涯,仿南宋二劉體》記述當時情景。其曰:
亮馬橋邊,六公墳畔,西八間房。有一三一號,社科社研,書生課讀,牧女窺窗。土豆易燒,牛根難熟,夜半青燈鼠跳梁。弦歌地,道延安精神,今日發揚。風霜。春播冬藏。歷數載耕耘學士忙。喜論文答辯,通過全票,前程期待,老少同堂。金榜題名,峨冠高戴,不負辛勤拚此場。人才眾,愿無須媚外,土亦如洋。
詞上片說課讀生涯,為西八間房當日實錄;下片說論文答辯,為此后遷居趙堂子胡同時情事。移居港澳,曾撰一跋文加以說明。跋曰:
此為余十數年前之舊作也。上片寫于攻讀過程之中,下片乃后來所追補,故稱之為“憶”。北京東直門外西八間房131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地址。當時未有洋樓,所住簡易四合院,乃生產大隊舊物。與農舍接鄰,農家羊群常在院內奔走,故有“窺窗”之謂也。謹此說明。至其余種種,亦皆為其時其地之實際景況。施議對丙子夏日于濠上之赤豹書屋。
跋文作于1996 年夏,在澳門大學任教。跋文對于“窺窗”二字特別作了注釋。而土豆、牛根,用的則是蘇聯的典。至于延安精神,乃與西安精神相對應,表示發揚艱苦奮斗精神,屬于今典。煞拍土與洋,指的是國家自己培養的土博士和留洋歸來的洋博士,以為對于二者,應當平等看待,給予同等待遇。這首詞據實而言,隨性而發,謂效二劉(劉克莊、劉辰翁),亦恐墮入“辛學末流”。友人見此詞,贊曰:大俗大雅,微型離騷。未置可否?姑妄記之。
在西八間房,做成兩件事:一是將原有七萬余言的碩士論文《詞與音樂關系之研究》,增補修訂為三十萬言的專著《詞與音樂關系研究》;二是撰成《建國以來詞學研究述評》并刊登于《中國社會科學》1984 年第1 期。前者在吳世昌先生親自督教下進行,后者得到管叔(舒蕪)鼓動及指點。
第二個住所,東城區趙堂子胡同。這是個較為完整的四合院。前院、中院、后院,應有盡有。前院小庭園還有一棵高出屋頂的香椿樹。前院北屋,宋大媽一家三代居住,操一口地道京腔,負責院內文書收發及傳達。我和文學所幾位同事,包括社科院以外人士,分別在院內各個角落居住。計十七戶。我居前院西廂。起初名之為“未容膝齋”,只在為陳朗先生《西海詞》撰寫序文時用過,此后改其名曰:能遲軒。蓋取“詩到能遲轉是才”(袁枚句)之義。當其時,所居之所雖仍容不下膝,但各地詩友如施南池、虞愚、盛配、萬云駿、江樹峰、徐味、陳朗、楊牧云、焦同仁、丁芒、劉征、林從龍、徐培均、蔡厚示、林東海、周素子、林岫、林繼中、徐志剛、沈家莊、孫琴安、張國星諸輩以及日本友人藤田純子卻曾先后光臨做客。我的導師吳世昌先生也曾拄杖枉訪。數年間,廣卜詩鄰,與結詩緣,除了各地詩友,與臧克家先生每日的“見面禮”,亦成為這段時間詩書生涯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時,我的另一闋小詞《鷓鴣天·自嘲》亦曾作了記錄。其曰:
豈為虛名役此身。我生樂道且安貧。大鍋吃飯無愁米,小井看天自在春。居鬧市,亦閑人。書城坐擁味甘辛。會當磨取數升墨,洗卻毫端萬斛塵。
這首詞為應和香港友人而作,題稱自嘲,實則乃自夸。所謂“大鍋”與“小井”以及“無愁”與“自在”,似乎都在顯耀:你比我好,我比你優越。這應是當時鬧市閑居的一種心態。一時間,竟亦收到各地詩友不少應和之作。
某日,臧克家先生到訪,著《博士之家》一文,刊《光明日報》;隨即,劉征先生到訪,劉撰《博士之家詩話》,亦登《光明日報》。劉征“詩話”中附有詩云:
雜院深深博士家,一椽四口樂無涯。
用兼學憩炊餐睡,物列書床米菜花。
對客傾談人立鶴,遮燈夜讀字飛鴉。
連云廣廈長安路,聞道人才重有加。
劉征先生歌詩,據實以錄,如話家常,語語都在目前,但意旨卻并非都在目前。如長安路上的連云廣廈,突然間從鍋碗瓢盆中跳將出來,令人想入非非,就不同于一般實錄。所謂感發聯想,這應當也是詩人天性的一種體現。
1988年12月,即將搬離趙堂子胡同,遷往麥子店新居,臧克家先生有《施議對同志遷居送別》一詩,為賦別情。其曰:
博士我老友,呼號不稱名。
爾我見親昵,差距計年齡。
二人對面居,一天幾相逢。
今將喬遷去,依依動我情。
接奉手書墨寶,我亦依韻奉和。其云:
我生也有幸,合共詩人名。
聞道無先后,相交不紀齡。
硯田勤作業,陋巷感遭逢。
潭水深千尺,悠悠留別情。
我與臧克家先生,同住趙堂子胡同。我住14 號,臧住15 號。二人對面而居。臧克家先生《博士之家》寫道:“一天碰面的時候,何止一次兩次?往往街燈睜眼或明月當空,不期而遇于我的大門之前,敞開心胸,放言無忌。談詩論文,感嘆‘世風’,臧否人物,互看作品”;“日久天長,知面知心”。臨行之時,載笑載言,舞之蹈之;依依別情,親切動人。這是我居京期間,最為難忘的一段日子。對此,詩界朋友亦十分羨慕。
居住趙堂子胡同期間,我做了三件事:一、通過博士學位論文答辯,由碩士論文增補修訂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詞與音樂關系研究》被推舉為“近百年來詞學研究集成之作”;二、完成王國維《人間詞話》譯注工作;三、完成《當代詞綜》編纂工作。
第三個住所,望京麥子店。這個地方當時還沒通郵,沒有門牌號碼。原來覺得有點偏遠,現在已被淹沒在望京的樓群當中。1989 年元旦,由趙堂子胡同遷入。第二天,天降大雪。盛配先生頭戴一頂蓋耳朵的大棉帽,腳著一雙大棉鞋,突然出現在我的門前。我很驚訝,他也很驚訝。我問,怎么找得到這個地方?他說,按照我告訴他的路線找來的,但他不明白,怎么能斷定搬遷的這一天沒風雪?我告訴他,依據坊間流行的“春牛圖”,知道元旦這一天是個吉日,所以早在一個月之前就已與搬家公司約定好搬遷日子。盛配先生說,我送給他的大棉帽和大棉鞋,今天派上用場了。遷入新居,有了可以容身的處所,但還沒有書齋,也沒有書齋名稱。“麥子店新居”,這是盛配先生幫我記存下來的一個準書齋名稱。盛配先生《詞調詞律大典》(中國華僑出版社1998 年5 月版)卷首夏(承燾)序附言:門人施議對于序文曾“略予增益一二”。落款并署:“施議對。1989 年農歷元宵,于北京麥子店新居。”于是,我也就多了一處可以附庸風雅的憑借。
遷入麥子店新居,寫成《詞體結構論簡說》一文,并于1990 年6 月,應邀赴美國緬因參加國際詞學討論會。
大致而言,我在北京的課讀生涯,自1978年入讀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至麥子店,暫告一個段落;我的人生歷程,自不惑之年至知天命,亦告一段落。為此,我有《賀新郎·五十初度》一詞,記述這一進程。其曰:
五十君知未。是生朝、忽驚老大,問何滋味。鏡里烏絲烏難改,依舊明眸皓齒。總不信,匆匆如此。其奈詩書功名遠,算當初多少青春毀。空悵惘,帝都尾。人間能幾嘉時會。對樓前、紛紛行客,馬龍車水。惟有殷勤云端月,長照潮升潮退。鬧攘攘、蝸爭蠅計。格子搜爬猶情愿,縱斯文自古今涂地。天命在,豈應悔。
詩書功名、格子搜爬,縱斯文涂地,亦猶是矣。此所謂天命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