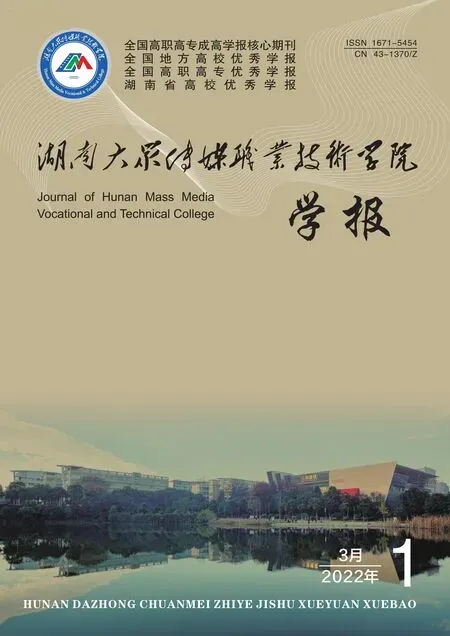慢一點·走出去·坐下來
——論音樂綜藝節目《時光音樂會》的三個創新維度
陶新艷
(湖南大眾傳媒職業技術學院 學報編輯部,湖南 長沙 410100)
2021年10月,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發布《廣播電視和網絡視聽“十四五”發展規劃》,提出要“把握‘公益、文化、原創’方向,深入推進廣播電視節目創新創優”[1],“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推出更多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原創節目,打造更多廣播電視節目品牌”[1]。同樣在10月,湖南衛視正式啟動新的頻道口號“青春中國”,“通過文化品格、時代精神和社會價值的升華,實現對青年群體更有力的價值引領”。[2]在全新口號的引領下,湖南衛視推出了《時光音樂會》《云上的小店》《今天你也辛苦了》等“小而美”的全新節目。
隨著廣播電視行業治理體系逐漸完善,我國的綜藝節目進入全面調整期。有別于“大投入、大制作、大明星”的節目制作思路,這些“小而美”的節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洋溢著自然、親切、溫馨的氣息。其中,2021年10月22日開播的音樂綜藝節目《時光音樂會》,以“你相信音樂能讓你回到過去嗎?”“如果可以回到過去,你會給哪一年的自己寫一封信?”這樣的提問作為出發點,為經典歌曲改編這一傳統節目類型賦予更自然的形態和更自在的靈魂。本文以《時光音樂會》為研究對象,從節目定位、節目形式、人物關系這3個維度來剖析其研發制作中獨辟蹊徑的創新之處。
一、節目定位:慢一點,用“信”串起“音樂+故事”
眾所周知,文學藝術起源于遠古人類的生產勞動。遠古人類在勞動過程中伴隨動作節奏而自然發出的勞動號子,便是音樂的雛形。作為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詩經》記載的300余首詩歌皆有曲調,盡管這些曲調沒有流傳下來。《詩經》中《風》這個部分,記載的是各地民歌,古人和著曲調唱出對美好事物的贊頌、對故土家人的思念、對壓迫欺凌的怨憤等豐富多樣的思想感情。孔子從個人修養和教化的角度,強調“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重要性。從荀子所說的“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可見音樂直抵人心、感人至深的作用,從而對人的性情、人的思想產生影響。
在我國音樂綜藝節目的發展歷程中,最早可以追溯到1984年中央電視臺舉辦的“青年歌手大獎賽”。進入新世紀,以《超級女聲》《中國好聲音》為代表的選秀類節目,為音樂綜藝節目打下了廣泛堅實的觀眾基礎。《我是歌手》首開明星競演類節目的先河,打造頂尖歌手之間的競技舞臺。《偶像練習生》《創造101》等偶像養成類節目,則在眾聲喧嘩中一步步偏離了正常的軌道。伴隨著音樂市場的細分化,樂隊、美聲、嘻哈、電音、搖滾、民謠、國風等豐富的音樂類型為垂直類節目百花齊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深耕圈層之外,跨界融合是另一種方向的探索,“音樂+競猜”“音樂+脫口秀”“音樂+旅行”等不同元素加入其中的“音樂+”綜藝新樣式日漸異彩紛呈。
《時光音樂會》這檔全新的節目定位于慢綜藝。所謂慢綜藝,是相對于內容以競技性和快節奏為主的快綜藝而言的。2017年,湖南衛視推出的節目《向往的生活》打開國內慢綜藝的大門。這種源自韓國的節目,以紀實的風格、舒緩的基調帶領觀眾逃離快節奏的工作、生活,在喧囂紛繁的日常中放下焦慮、放松心情。隨著近些年的發展,慢綜藝逐漸演變出生活類、民宿類、婚戀類、職場類、旅行類等分支。《時光音樂會》便屬于音樂慢綜藝。
在目前為數不多的音樂慢綜藝中,主要是“音樂+旅行”“音樂+文化”這兩種類型。《時光音樂會》則開辟“音樂+故事”的新賽道,創造性地以“信”的載體,用一首首歌曲的時間坐標,匯集不同歌手在不同年齡的音樂故事,再現屬于不同時代的集體記憶。
廖昌永用一首《東方之珠》深情回憶1997年香港回歸的歷史性時刻,渾厚的歌聲中躍動著一顆赤子之心;戴軍第一次在節目中道出《阿蓮》這首歌中原來藏著他對已故恩師難以言說的懷念;張杰追憶爺爺曾送他一個綠皮電動小火車,并對他寄予“獨占鰲頭”的殷切期望,他用不懈的努力讓爺爺《夢想成真》;許茹蕓自己創作的《突然想愛你》這首歌中,凝結著她對愛人砰然心動的瞬間;林志炫將一首《輸了你贏了世界又如何》,送給執著于音樂的自己,也送給“執著于自己所愛的朋友們”;鳳凰傳奇談笑風生地回顧起曾經受到的質疑和遇到的挫折,并約定“要一起唱到70歲”;郁可唯意外收到父親寫給她的第一封信,父親在信中為自己曾經簡單粗暴的教育方式道歉,女兒一邊讀信一邊回憶父親對她嚴厲管教的往事,泣不成聲,父女之間以“信”和解。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的步伐加快,人們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各方面的壓力越來越大。寫信、寄信、收信、讀信這樣的事情,似乎早已與數字化生活脫節。《時光音樂會》獨具匠心地借助“信”的形式,歌手在寫信、讀信的過程中觀照自身、相互傾訴,觀眾在聽信的過程中由此及彼、產生互動,營造出平等對話、貼心交流的節目氛圍。以“信”的載體,歌手們娓娓道來一個個短故事,短故事里牽引出長回憶,帶動觀眾回顧自己的往昔歲月,追憶往昔歲月里的溫暖點滴;以“信”的載體,歌手們娓娓道來一個個小故事,小故事里蘊含著大情感,從家國情懷到親情、友情、愛情,歌者情之所至,歌曲深入人心,觀眾為情所動;以“信”的載體,歌手們娓娓道來一個個老故事,老故事里生發出新共鳴,觀眾在沉浸式的體驗中與節目產生心理交集,獲得心靈治愈的效果。
“讓信帶我們回到過去,感受他們的音樂時光”,以“信”為媒,“音樂+故事”的《時光音樂會》串聯起時光里的故事與故事里的音樂,鏈接起節目中的歌手與節目外的觀眾,勾連起當時親身經歷的情緒與當下讀信聽信的情思,觀眾進而與節目中的故事、歌曲、情感實現強烈共振與積極共情,傳遞出昂揚向上的時代價值。
二、節目形式:走出去,去舞臺化的詩意空間
以往的音樂綜藝節目絕大多數在棚內錄制,尤其是演唱部分。隨著觀眾欣賞水平和審美要求越來越高,音樂綜藝節目本身對各種設備、演唱環境等方面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棚內音樂綜藝節目在制作上一再升級。幾千平方米的演播廳,由多組升降臺組成的舞臺結構,根據不同主題靈活切換的舞美設計,上千盞燈的炫目數控燈陣,幾百名觀眾的實時現場投票,不斷做加法的棚內音樂綜藝節目制作水準已經接近天花板,節目形式也難以突破。
戲劇理論中,在鏡框式的戲劇舞臺上,三面實體的墻構筑起三向度的空間實體,“三堵墻”的觀點由此而來。19世紀,寫實主義戲劇將“第四堵墻”的概念運用其中。所謂“第四堵墻”,是指在鏡框式舞臺臺口的一面無形之墻,這堵墻隱藏于表演者與觀看者之間。換言之,對觀看者來說這堵墻是透明的,對表演者來說這堵墻則是不透明的。表演者假想這“第四堵墻”橫亙在他們與觀看者之間,在接近真空的表演空間中完全投入角色,不受觀看者的影響。在“第四堵墻”參與構建的空間中,看與被看的結構關系得以固定,觀看主體、行動主體及其認同機制也得以建立。到了電視藝術領域,戲劇理論中關于“墻”的理論得到創造性地運用,運用于電視節目生產的諸多方面。
《時光音樂會》在節目形式上最大的創新之處在于走出去,打破“墻”的局限,最大程度地化繁為簡,用做減法的方式營造一個去舞臺化的詩意空間。“蘆葦深花里,漁歌一曲長”,第1期和第2期節目是名副其實的戶外音樂會,節目組選擇張家界一處民宿為拍攝地。鋪星空為幕,展青草為臺,幾位時光音樂人圍坐在呈半圓形排布的棕色草椅上。綠樹環繞,燈光點點,微風習習,蝴蝶撲翅,一派“川原秋色靜,蘆葦晚風鳴”的詩情畫意,有歌手不禁贊嘆像仙境一般。在這個置于天地之間的詩意空間,沒有墻,沒有舞臺,沒有觀眾,僅攝像機充當著“第四堵墻”,故事在歌手的歡聲笑語間恣意徜徉,歌聲在歌手與樂隊的默契配合中縱情流淌。
天氣轉涼,這給戶外錄制設備帶來難以克服的影響。從第3期開始,節目不得不進行空間轉移,轉移到民宿室內。透過攝像機這“第四堵墻”,遠景處的窗外依舊是蘆葦和綠葉,室內擺放著沙發、靠椅、圓茶幾,點綴著老式錄音機、老式放映機,歌手們三面合圍而坐,樂隊也就在室內,不大的空間里充盈著家庭派對的溫馨氣氛,也契合著節目的懷舊底色。從第7期節目開始,空間再次轉移,轉移到“時光森林”。雖然是棚內的“森林”,但視野開闊,目之所及皆是綠色,各種植物,深深淺淺,高低錯落,姿態各異。雖然是棚內的“森林”,但并不復雜,歌手們再次呈半圓形圍坐起來;不同的是,座位席前方搭建了一個木制的長方形小舞臺,稍遠處是一座木質小樓,歌手可以站到小樓上演唱,樂隊則在小樓下演奏。結合更有層次的舞美設計和更為多樣的場面調度,透過攝像機這“第四堵墻”,棚內的“時光森林”打造出更加多維的自然系視覺效果。
走出去,從戶外到室內再到棚內的空間轉換,《時光音樂會》旨在通過去舞臺化的手段,直接呈現或者藝術再現一個個返璞歸真的詩意空間,與“音樂+故事”的節目定位相輔相成。雖然沒有現場觀眾,沒有與觀眾的直接交流,節目中“被看”的這些歌手的自娛自樂,卻因身處詩意空間中的自由分享、自在演唱而顯得格外動人;“第四堵墻”之外的觀眾在“看”節目的過程中也很自然地被這種自由而帶動,被這份自在而感染,從而突破“第四堵墻”,潛移默化地構建起屬于《時光音樂會》的情感共同體。
三、人物關系:坐下來,以歌會友的時光家族
南宋王灼在《碧雞漫志》一書中言及“因所感發為歌”[3],“人莫不有其心,此歌曲所以起也”[3]。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音樂首先作用于人的感官,令人產生感官體驗,人們將這些感官體驗進行表達、分享、交流,而進一步領略真善美的藝術內涵,進一步密切關系、增強了解、增進感情。回到音樂的本質,回歸歌手的初心,《時光音樂會》中時光家族的人物關系由此構建。
在類型多樣的音樂綜藝節目中,歌手是核心人物。隨著節目類型的豐富和節目元素的增加,音樂綜藝節目中的歌手不再局限于自己的本份,而被賦予越來越多的標簽。在選秀類節目中,歌手是評委,多少帶有一種高高在上的意味;在競演類節目中,歌手是選手,彼此之間互相競爭;在養成類節目中,歌手是導師,充當著老師或前輩的角色;在跨界融合的“音樂+”節目中,歌手還附加著競猜者、旅行者、體驗者等身份。《時光音樂會》作為慢綜藝,節目環節簡單——回憶和分享,節目內容純粹——演唱和聊天,歌手在這里拋掉了其他標簽,安安穩穩地坐下來,回歸最本真的自己。
人物身份簡化了,人物關系隨之簡化。在歌手們組成的時光家族里,沒有比拼,沒有賽制,他們只以歌手的身份乘興而唱;沒有點評,沒有任務,他們只以歌手的身份傾訴聆聽;沒有劇本,沒有人設,他們只以歌手的身份以歌會友。
時光家族坐下來以歌會友,首先體現在《時光音樂會》創新設置的“莊主”這一頭銜及“輪流坐莊”的改編翻唱形式。整季14期節目中,有9期由作為常駐嘉賓的6組時光音樂人和3位時光好友“輪流坐莊”,成為“莊主”。“莊主”享有的特權,在于該期節目中的其他歌手將翻唱由“莊主”原唱(或創作)的歌曲。對于翻唱者來說,在“莊主”面前近距離地對其經典歌曲進行重新演繹,既忐忑又興奮。正如郁可唯所言,就像“在老師面前去完成作業”,并“想要得到老師認可的那種感覺”。而對于“莊主”來說,唱作人小柯表示“很緊張”,譚詠麟則非常期待“看到不同年代不同類型的歌手,怎么處理我的歌曲”。
《時光音樂會》中的時光音樂人,不僅年齡上從“50后”橫跨到“80后”,地域上覆蓋兩岸三地,樂壇資歷也差別不小。面對面地圍坐,不僅是一種形式上的平等,更將這種平等交流投射到歌手的心理層面,輻射到觀眾的心理層面。加之“輪流坐莊”的巧妙安排,讓回歸歌手這個唯一身份的時光音樂人,消弭了年齡、資歷、地域等方面的客觀差異,都能平等享受到做“莊主”帶來的滿足感和幸福感。
時光家族坐下來以歌會友,還體現還廣邀時光好友加入節目,并通過精心設計的節目主題,通過派對、K歌、年夜飯等別具一格的聚會形式展現歌手之間簡單卻不單調的人物關系。“時光金嗓風云會”這一期是原唱歌手與翻唱歌手的同臺合作,時光音樂人與7組時光金嗓歡聚一堂,現場多達二十幾人,營造出音樂派對的風格。“四十年華語金曲大會”這一期的現場則布置成KTV的樣子,歌手們點歌之后通過答題搶麥贏得演唱機會,贏得演唱機會之后也不用上臺,而是像在KTV里面一樣輕輕松松地坐著唱。臨近農歷新年的“時光年夜飯”這一期,歌手們圍坐在大大的方形飯桌前,各自用家鄉的過年菜和歡樂的歌曲送出美好的新年祝福,一派家人團聚的喜慶氣氛。
縱觀當前多元化的音樂綜藝節目市場,《時光音樂會》對于人物關系的簡化處理,未嘗不是一種創新。這個連主持人都省去的節目,舍棄了各種復雜的環節、流程、機制,把重點完全放在音樂本身,完全放在歌手本身,凸顯出時光家族坐下來以歌會友的簡單與純粹,與節目自身的調性相得益彰。
在國家廣播電視總局辦公廳公布的2021年第四季度廣播電視創新創優節目中,《時光音樂會》榜上有名。《時光音樂會》引林間冒出的一股細流,點滴匯聚起觀眾的心理共振與情感共鳴;如喧嘩鬧市的一股清流,悠然閃爍著洗盡鉛華、靈動脫俗的別致格調;用音樂流淌的一股暖流,不疾不徐地撫慰觀眾情緒、治愈觀眾心靈。受多重因素影響,雖然戶外音樂會的創意未能貫穿整季,雖然廣告植入有時略顯突兀,《時光音樂會》在節目定位、節目形式、人物關系等維度上別出心裁的探索還是卓有成效的,為音樂綜藝節目更好地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走出了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