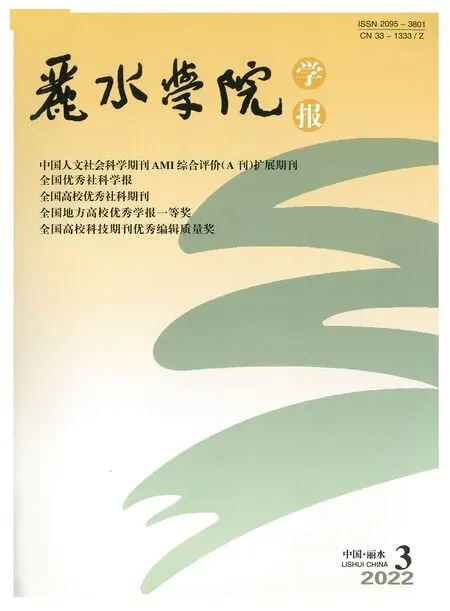博物館文化傳播的數字化應用分析
童嘉露
(閩南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福建 漳州 363000)
陳剛在《數字博物館概念、特征及其發展模式探析》一文中提到,數字博物館圍繞數字藏品的收集、保存、傳播和展示,以研究、教育、欣賞為目的,對實體博物館的服務時間和空間進行延伸和拓展,實現任何人(anyone)在任何時間(anytime)、任何地點(anywhere),獲得特定信息服務的目的[1]。簡言之,數字博物館即是集數字化、體驗式、信息管理等特點為一體的文化信息傳播平臺。
文化傳播的效果與傳播者自身的文化價值蘊含及傳播能力息息相關。長期以來,博物館保存的文化遺產與自然遺產數不勝數,是人類文化的微觀縮影,更是人類記憶的保存者。作為公共文化機構,博物館并非只是精英的殿堂,只需支付低廉的門票普通大眾也可從中獲取豐富的文化知識,享有平等獲取文化知識的權力。所以,博物館對于大眾來說是成本最低的文化接收神器。
博物館對于傳統文化的傳播具有一定的意義。首先,它以文物的形式保存了文化,延續了文化的生命。文化依托博物館文物符號向外擴散,在不同區域中流動與傳播,達到教化群眾的目的。其次,它促成了文化價值觀的構建,促進了大眾對傳統文化的情感認同,增強了民族凝聚力。再次,滿足大眾文化體驗與文化增值,賦予新的文化元素,衍生新的文化產品。因此,博物館不僅僅是展示文物的場所,更是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具有特殊的“媒介”屬性。
過去的博物館通常位居傳播者角色,以實物資料為基礎,利用陳列展覽、著書立說、解說員講解、文化沙龍等方式進行文化信息的傳遞,以單向流動的傳播模式為主,且受限于時空疆界,僅能被動傳播。博物館要實現文化傳播功能的極大化,就要將本地文化輻射到整個社會群體,最終達到全面的、無差別的文化擴散。隨著科技的發展,數字技術驅動文化傳播,信息得以突破時空限制,實現了多向性交流,并以此消除了用戶的經濟水平及地域差異,促成文化資源共享終極目標的實現。今日許多博物館開始積極利用現代數字技術,文化傳播手段變得更綠色、高效、經濟與便捷。數字化傳播方式的出現,無疑大大增強了博物館文化傳播的主動性與影響力。
一、數字時代博物館文化傳播的基礎建構
文化的傳播和擴散離不開大眾媒介,技術的發展使各種各樣的傳播媒介出現在大眾面前,要將文化推向大眾必須利用高效的傳播工具。美國傳播學者詹姆斯·凱瑞(James W.Carey)認為,傳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智力信息的傳遞,而是建構并維系一個有秩序、有意義、能夠用來支配和容納人類行為的文化世界[2]。博物館要突破以往的單向傳播閉環,實現從文化傳遞到文化傳播,必須利用文物資料構建人人可進入、可共享的數字文化世界,讓受眾在其中可以隨意獲取信息、交流感悟,最終形成一個文化共同體。而構建文化世界的第一步就是要建立出一個數字典藏平臺,而數字典藏平臺背后的各種信息技術支持即是文化傳播的基礎建構。
2003年10月17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頒發的《數字化遺產的典藏》(“Preservation of the Digital Heritage”)指出,凡文化、教育、科學、管理、技術、醫藥等創造性的數字文獻,包括文本、數據庫、靜態圖像、動態圖像、聽力文獻、圖表、軟件與網頁,都可以是數字化遺產[4]。數字化是實現信息共享的基礎,目前很多博物館都已將數字化形式的藏品載入信息系統,并將數據傳輸到各大網絡媒介,實現信息共享。世界上許多國家已經開始積極推進博物館數字化,例如美國國會圖書館制定的“國家數字信息基礎典藏計劃(NDIIPP)、IBM東京研究所日本民族學博物館的“全球數字博物館計劃”,為的就是保存人類文明,并使之延續。
完整的數字文化遺產可以反映人類歷史上的一切社會、文化、政治與經濟活動。數字文化典藏于媒介平臺中,數字媒介就成為了博物館數字文化傳播的載體,同時還催生了新的文化傳播方式。數字網絡空間允許全球各地的用戶進行訪問,具有開放共享的特點,具有公共空間的特征。數字典藏將藏品資料信息公布在網絡空間之中,任何人無論在任何地點都可以在網絡空間中進行信息的獲取和交流,不僅達到了全民共享的目的,還將文化傳播到了世界各地。
文化信息進入虛擬空間成為了連接人與人之間的紐帶,這個紐帶就代表了群體的身份符號和集體文化認同。人們在全球的信息賽博空間中被各種信息轟炸,同時也積極尋找存在感和文化認同,進而與其他受眾組建成具有共同特點、興趣、價值觀的社群,賽博空間中受眾間頻繁的互動交流構建成了一個集體文化共同體。博物館文化傳輸在這個虛擬空間中吸引了部分受眾的聚集,他們共同探討、分享同一種文化。也正是因為他們在網絡空間的分享與討論,使他們的身份從受眾轉變成了傳者,從而吸引到更多的受眾參與,如此循環使得屬于他們的集體文化雪球越滾越大。
詹姆斯·凱瑞將傳播視為文化,傳播不僅是信息的傳遞,更是維系社會關系和社會生活的儀式性活動。博物館構建數字空間不僅可廣泛提供文化信息,而且能讓受眾投身于文化世界中,共同參與生活,甚至重塑文化世界。
二、數字時代博物館文化傳播的數字化應用
(一)沉浸式體驗
在傳統的文物展覽中,陳列展覽是博物館文化傳播的基本方式,文物冰冷靜止地擺放在展示臺上難以引起受眾興趣,此時信息的傳播是單向的,受眾處于被動接收的地位。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VR)、增強現實(Augmented Reality)、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技術的應用改變了這種現狀,博物館文化傳播的方式從過去的單向傳播變為現在的沉浸式傳播,信息交流方式發生了巨變,沉浸式體驗成為了當下年輕人喜愛的信息接收方式。
虛擬現實是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結合相關科學技術,生成的與一定范圍真實環境在視、聽、觸等方面高度近似的數字化環境,用戶借助必要的裝備與數字化環境中的對象進行交互作用、相互影響,可以產生親臨對應真實環境的感受和體驗[4]。博物館利用虛擬現實技術開發3D數字影院,實現真假難辨的視覺效果,360°全息裝置演繹虛實結合,提供更多可視化信息,還有體感互動等都極具互動效果。這些數字展覽技術拉近了受眾與文物的距離,使受眾在互動中體驗文化內涵,具有直達人心的文化傳播效果。
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端門數字館”是于2015年成立的將古代建筑、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新興技術完美融合的全數字化展廳。大眾可以通過數字技術沉浸在故宮場景之中,在數字世界里了解歷史文化、觸摸故宮建筑,大眾如果有興趣,還可與皇帝漫步于宮中。2017年10月,在“端門數字館”內舉辦了“發現·養心殿——主題數字體驗展”,體驗展分為引言區、互動區、劇場區。引言區主要是通過“數字沙盤”及數字影片介紹養心殿文化;互動區利用AI、VR等高新技術與傳統文化結合,使大眾感受到真正的體驗式文化,游客可以在互動區中參加召見大臣、朱批奏折、親制御膳等體驗活動,“真實”體驗一次皇帝生活,全面細致地了解關于皇宮生活的知識。
VR虛擬現實、AR增強現實、AI人工智能賦予文化新力量,實現受眾身臨其境的沉浸式體驗、超越現實的感官體驗與“復活”歷史人物的再現體驗。文化與人類行為、生活方式息息相關,理解一種文化唯一的方式是持之以恒的體驗,如果無法讓受眾參與其中,則難以實現情感認同。數字技術的發展打破了歷史文化難以重現的壁壘,互動式體驗成為了文化傳播的重要方式,為受眾提供了全新的科技觀感。
(二)數字文創產品
在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5G等現代技術高速發展的背景下,各大博物館順應了數字經濟時代發展要求,打造了一系列“文化+科技”的數字產品。傳統博物館文創產品走向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轉型。
1.數字視聽作品帶動粉絲經濟
北京故宮博物院在蘋果App Store中出品了“每日故宮”“故宮展覽”“紫禁城祥瑞PRO”“紫禁城600”“皇帝的一天”“胤禛美人圖”“清代皇帝服飾”“韓熙載夜宴圖”“故宮陶瓷博物館”等十多款App。其中“胤禛美人圖”于2013年5月上線,上線兩周下載量便超過20萬,被評為“2013年度精選優秀App”。故宮App系列更加年輕化個性化,把枯燥嚴肅的游覽參觀變得有趣,各種交互、沉浸體驗使受眾身臨其境,獲取文化知識變得更加輕松、更加快速。資源轉化App應用契合了現代受眾碎片化閱讀的模式,可以使受眾隨時隨地了解故宮文化,把故宮博物院“裝”進口袋。
2016年7月,騰訊與故宮出品的《穿越故宮來看你》H5刷爆朋友圈,頁面瀏覽量(PV)高達300萬,皇帝置身于畫中,嘴里唱著Rap,宮女戴著現代VR眼鏡,利用社交媒體發送QQ表情,刷著朋友圈,這種魔性、鬼畜的視頻符合當下潮流,引起網友瘋狂評論轉載。從高貴嚴肅到親民活潑,故宮形象的數字化、年輕化轉型成功吸引了一大波流量粉絲。
2.立足IP打造爆款
近年來,中國國家博物館、蘇州博物館、三星堆博物館、大英博物館、敦煌研究院等紛紛入駐各大網上商城,其中各種文創產品的銷量不容小覷。各大博物館研發的文創產品品類廣泛,不僅包括珠寶、服飾、書畫、器物等系列,產品開發范圍還涉及各類首飾、鑰匙扣、文具、食品、化妝品等。各大博物館旗艦店等文創網店開始直播帶貨,參與購物營銷。博物院文創產品把具有代表性的歷史文化元素應用于現代日常生活品之中,既弘揚了傳統文化又融合了時尚理念,使文化輻射于大眾的日常生活中,潛移默化地強化了大眾的文化認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故宮淘寶打造了多款“網紅爆款”,使故宮成為新一代網紅。在故宮淘寶的微信公眾號,個性化、趣味化的“廣告文”點擊率達到“10萬+”,其營造的IP產品受到消費者熱捧。在2016年,故宮淘寶榮獲“淘寶十大原創IP”稱號。大英博物館研發的“最強IP”小黃鴨風靡全球,一經上線即被搶空。由此可見,產品的娛樂化和用戶的年輕化是驅動文創產品火爆的核心,在此基礎上利用數字媒介加以推廣,可在全球范圍內引起一股文化潮流。
(三)數字教育
博物館具有收藏功能、展示功能、娛樂功能,更為重要的是其承擔著社會教育功能。博物館是為大眾提供文化知識、開展愛國主義教育、進行社會科學研究的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承載著豐厚歷史文化資源的各大博物館吸引了普通民眾以及研究者的參觀、研究。
一些博物館根據受眾需求不斷創新文化傳播新形式,以紀錄片、綜藝節目的形式開展文化教育。例如中央電視臺綜藝頻道播出的《國家寶藏》節目,是一檔與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等九家國家級博物館共同合作的文博探索類節目。該節目通過影像化形式解讀中華文化,使受眾深刻感受傳統文化的魅力。中央電視臺紀錄頻道推出的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一經播出便受到了大眾的追捧,在豆瓣評分高達9.4分。紀錄片主要講述了故宮各類稀世珍寶的文物修復過程,使大眾從另一個視角了解到了不一樣的故宮文化,傳播手法年輕化、個性化,符合當下個性化的傳播潮流,吸引了大量受眾觀看。
三、博物館數字化傳播的作用與啟示
近年來博物館在數字化應用方面蓬勃發展,數字文創產品的推廣也掀起了一股“文博熱”,博物館的“科技+文化”融合模式展現了未來發展之路。博物館的數字化應用帶給我們諸多啟示,現歸納總結如下:
(一)實現多元文化碰撞
數字技術的應用實現了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博物館文化與大眾文化以及不同地區與國家文化之間的交流與碰撞。博物館作為一種文化符號,承載了豐富多彩的文化,是大眾了解歷史的現代窗口。博物館利用現代技術將各種文化遺產進行陳列、展示與傳播,生動活潑地再現了歷史優秀文化,實現了歷史文化與現代文明的接軌。同時,依靠互聯網技術,博物館的形象從嚴肅轉變為親民有趣,原本高高在上的精英文化演變成受眾喜聞樂見的大眾文化,實現了更好的傳播效果。更重要的是,數字博物館突破時空限制,將優秀的歷史文化“移植”到異國舞臺,將文化傳輸到世界各地,實現了文化的交流與傳播。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指出,世界的文化遺產是屬于全人類的,在尊重各國獨特的文化習俗與實用性的基礎上,應該允許全世界人類的無障礙訪問。因此,它于1992年發起了“世界記憶工程”,主要開展保護、收藏人類文化遺產與人類記憶等工作。數字時代的世界記憶保護與典藏是中國向世界文化輸出的機遇,現中國已有13項檔案入選《世界記憶名錄》。數字技術延長了文化的壽命,如果不注重文化傳播與文化記憶的延續,其生存狀態將會岌岌可危。我國應開展國家電子典藏計劃,將各民族的文化結晶收納、保存與傳播,展示我國的文明成果。
(二)構建文化世界
新媒介的發展承載海量信息資源,信息的碎片化、即時性分散了受眾注意力,一種流行文化可以迅速風靡全球也可以迅速被人拋到腦后。而要像好萊塢、迪士尼這樣的流行文化一樣永葆青春,必須建立堅不可摧的文化體系,形成獨有的文化價值觀,如此才能感染、同化更多的受眾。博物館就像一個文化王國,記載著一個個文明的興起與衰落,與其讓受眾感受零散的文化碎片,不如在博物館中建立起具有儀式表征的傳播場域,利用博物館獨有的意識力量喚起集體體驗。
詹姆斯·凱瑞(James W.Carey)提出的“傳播儀式觀”講述了一種儀式性傳播模式,與線性傳播模式不同,它強調信息的空間性擴散,與分享、參與、聯合、交往等概念密切相關,強調傳播在共同信念的表征和社會維系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5]。數字技術的應用使受眾仿佛進入另一個文化世界,這個文化世界賦予受眾新的身份,傳授新的文化價值,構建新的文化共同體,使傳者與受眾之間、受眾與受眾之間產生聯結感。在數字技術的加持下,歷史畫面的展覽、文化的虛擬形式不斷再現與重構文化記憶,維系群體的團結。作為承載集體文化的博物館,通過數字博物館的文化傳播構建文化社會,增強不同群體、不同階級、不同國家的文化信仰與凝聚力量。
(三)刺激文化產品消費
博物館可挖掘和應用的文化元素是不計其數的,但若只是簡單地機械復制藝術品,不加以創意推廣與傳播,則無法在琳瑯滿目的文創產品中脫穎而出。能夠掀起潮流的博物館文創產品,大多將新媒體技術與電商相結合,利用微信公眾號、微博的各種花式營銷使之成為“網紅”。例如圓明園推出的文創雪糕,將雪糕雕刻成景區的標志建筑,游客紛紛手持雪糕與相應景區元素拍照“打卡”,文博產品也因此成為了有趣、有品質的代名詞,實現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雙豐收。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文化產品的營銷推廣也存在過度娛樂化問題,比如一些惡搞表情包只是娛樂大眾,嘩眾取寵,并沒有文化教育功能,也有悖于文化傳播的目的。另外,大多數博物館掀起的文創產品消費潮流還局限于本土,傳播范圍非常有限。因此,可以借鑒知名IP小黃鴨的環球之旅巡展經驗,通過建造超大主題展廳以及開展場景體驗,打造“國際IP”。
(四)堅持人文傳播理念
現在,數字化傳播成為博物館文化重要的傳播策略之一,數字博物館力求消除信息接受不平等現象,意在通過互聯網技術縮小“數字鴻溝”,更好地發揮博物館教育功能。數字作品中呈現的歷史、文化、觀念,反映了超越時代的人文性特征,實現了博物館的教育功能。博物館利用通俗化的展示方式使受眾更好地了解傳統文化,破解“數字鴻溝”帶來的信息障礙。立足于市場與受眾導向,內容生產方式娛樂化,使博物館文化與娛樂文化結合,但也要避免“泛娛樂化”傾向,要注意數字產品帶來的即時消費性與娛樂至上思想對傳統文化內涵的瓦解。再有,受眾媒介素養的提升也影響著博物館文化傳播的力度,受眾需提高自身獲取信息的技能、知識與能力,從而更好地理解博物館文化。
面對文化傳播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困難,博物館應堅持“以人為本”理念,不陷入消費主義陷阱,積極促進流行文化的合理發展,構建和諧健康的文化傳播環境。
四、結語
數字技術被應用于博物館文化傳播之中,成為其重要的文化傳播手段。數字技術在延伸現實世界文化傳播的同時,還創造了一個虛擬的文化賽博空間。大眾在虛擬空間中實現互動與共享,極大提高了體驗感與參與感。在這個空間中新思想、新文化不斷碰撞,從而激發出更多文化創意,反哺真實世界的文化本體,真實與虛擬世界中的文化傳播相互促進、相輔相成,最終促成文化的進一步發展與創新。但若對科技力量過度強調而忽略了文化深層的意蘊,不免會“喧賓奪主”,使文物的歷史性與真實性被削弱。只有正確使用技術力量,科技才能為文化帶來變革性發展,文化也才能賦予冰冷的科技以內涵與智慧。對于中國而言,蘊藏豐富歷史文物的博物館,在數字時代無疑應積極善用現代數字技術,結合真實與虛擬賽博文化空間,讓文化傳播的范圍更加遼闊,并借由群眾的互動與共享達到文化創新的目的,使中華文化在世界上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