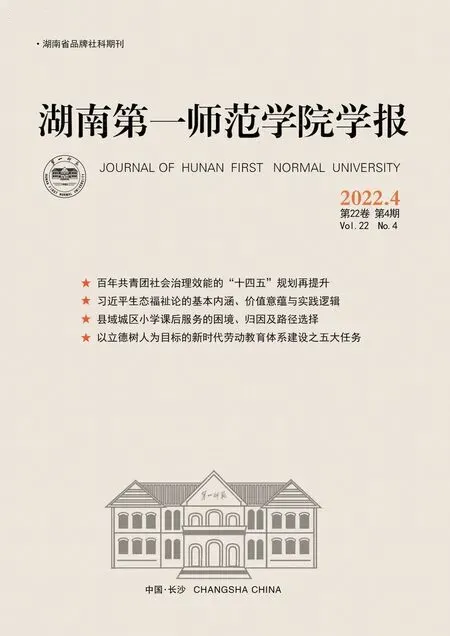民國東北的商租危機與輿論應對
許健柏
(湖南醫藥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南 懷化 418000)
商租權是近代日本在中國東三省所獨自攫取的條約特權,為其在華擴展勢力及攫取中國東三省土地發揮了重要作用。該特權源自1915 年5 月25 日中日簽訂的《關于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簡稱《滿蒙條約》)。歷史上,商租權既是滿蒙條約的核心利權,也是近代日本“滿蒙政策”的核心利益,它的演進深刻地影響著近代日本侵華的進程。商租權自產生以后,鑒于它牽涉的廣泛利益及造成的商租危機,備受國民關注。民國輿論界適時地回應民眾需求,及時地關注該特權,希望借公共輿論之利器,披露內幕、針砭時政、揭示危害。其中,民國輿論界不僅對商租權的實施進行及時報道,而且還提出了各類抵制的具體方略、建議等。當民國中央和地方政府主政官員在公共輿論界的督促下施行各類抵制措施時,新聞輿論界及時地進行跟進報道,大力加以宣傳。當地方主政官員抵制不力,商租造成社會危機之時,公共輿論界又對抵制措施不力,存在腐敗勾結外人等行為作出了嚴厲批判。民國新聞傳媒圍繞商租權的報道乃至批判,是在特殊環境下公共輿論參與抵制商租的重要內容,展示了民國時人借輿論界參與政治、抵御商租、挽我利權的愛國熱情。
針對民國抵制商租權實施的問題,學術界已有一定的成果。但這些成果多從政治、外交史視角進行研究,涉及的主體也多為民國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①。而對新聞輿論界參與抵制商租實施問題卻無專題研究,即便偶有涉及,也只是從抵制商租實施的某一區域或某一議題加以分析。為彌補以上不足,更向眾人清晰展示民國輿論界如何借公共輿論之利器去參與抵制商租,以及它們為此作出的不懈努力,擬對此做一探析。
一、民國東北商租危機的產生及增強
民國東北商租危機肇始于《滿蒙條約》的商租權條款,分別是第2 款:“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為建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為經營農業,得商租其需用地畝”[1]1101,以及該約附件6 換文:“本日畫押之關于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條約內第2 條所載‘商租’二字,須了解含有不過30 年之長期限及無條件而得續租之意”[1]1107。上述條款授予了日本在我國東北所謂“南滿洲”地區商租土地的特權。但是,緣于滿蒙條約是強迫簽訂,民國北京政府很早便確定抵制商租權的實施。例如《益世報》披露說:民國北京政府決定利用《滿蒙條約》延期3 個月實施的機會,秘密頒布了《商租地畝須知》14 則,對商租權的性質、實施范圍、商租期限和商租對象等作狹義解釋,并結合法律、訓令、口頭發布秘密命令等形式,開始抵制商租權的實施。《京報》跟進報道,披露中國的抵制讓日本極為不滿,曾多次要求交涉解決,卻始終未得解決,不甘心失敗的日本謀求強力推行,逐漸引發民國東北的土地商租危機。
民國東北的土地商租危機,是伴隨著日本商租土地進程的加深而愈趨激烈。1915 年8 月25 日,當日本決意趁《滿蒙條約》正式實施而大規模商租土地時,卻遭遇民國北京政府抵制,當時日本是不甘心的。據《京報》報道說:日本不甘心商租權實施受限,也決定利用商租權條款的疑義,借機解釋,擴大商租利權[2]。1921 年6 月,根據《京報》披露的日本“商租實施細則草案”來看,日本是希望將商租權解釋成土地所有權[2]。為達到這樣的目標,《晨報》深入披露說:日本已經制定中國東北土地開發計劃,擬投資設立滿蒙土地株式會社,“資本金為2千萬元”,并從國家預算“支出補助金2 百萬”,以支持南滿商租權的實施[3]。并且,日本是有堅定決心的,《清華周刊》引述日本國內消息說:商租土地問題“以前系因為中國方面極端反對,故迄未進入解決之機運,但東京政府方面現已決定具體辦法,無論有如何困難情形,定將進行徹底地解決”[4]80-81。
根據這樣的方案,日本人開始滲透到全東北地區向國人商租土地。而且,為了保證商租土地的成功率,日本人采用誘騙和強迫結合的手段,商租到大量的土地。據統計,從1915 年到1930 年,日本人利用各種非法手段,商租到中國東北土地的數量達上百萬畝[5]173-175。這只是日本個人商租到的土地數量,還沒包括日本機構商租到的土地數量。據日方材料披露,1926 年日本奉天總領事館統計商租到的土地居然達423500803 坪[6]19,引發東北嚴重的商租土地危機。《時事月報》評論說,照這樣的速度發展下去,“不出十年,(遼吉)兩省土地必十九入于日本人之手,則遼吉兩省,事實上即為日本之領土矣”[7]315。即使這樣,日本仍不滿意,大肆宣傳日本受中國欺壓,商租土地受到極大抵制,終于引發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后,民國東北的商租土地危機達到頂峰。日本拋棄曾經的顧忌,在偽滿的支持下,大肆商租土地。1932 年4 月,日本指使偽滿沈陽縣公署發布公告,“凡有土地,而無耕作力之農民,如欲將土地出租,可隨意租與外人經營之”。《華北日報》評論說:“此項布告,系基于滿洲國政府之訓令,各縣亦將有同樣布告發表,是則滿洲國土地完全開放于日人”[8]。1932 年12 月,《青島時報》更進一步披露說,“日本在偽國內居民之商租權,日人主張將中日條約第2 條規定范圍‘南滿’擴大,承認為全滿洲領土。自此承認后,由明春起,日人即可在滿自由營業,并因土地公益事業,租借需要之土地住宅,以便往滿移民”[9]。至此,《京報》痛呼:舊政權時代被橫暴軍閥所蹂躪的日本正當的條約權益,幾經星霜,在今日隨著日人經濟活動恢復,“而發揮其效力也”[10]。
在偽滿的支持下,東北新聞報集體痛呼:三千萬中國東北同胞將無立足之地。據媒體披露:日本近期唆使偽滿洲國明令公布商租權登記法,允許日朝人民有隨地租借土地之權。東北國人探知“該法之施行細則,現已由偽組織公布”“其以上各款,純為一種變相攫取我土地之陰謀,我東北同胞因受其脅迫利誘之結果,行見我東北膏腴之土地,將非吾有,而我三千萬同胞,均將無立足之地矣”[11]8。由于東北淪陷,傀儡偽滿政權通過各種手段滿足日本商租土地的需求,民國政府制定的商租土地抵制政策,已無抵制作用,大量日本人通過商租攫取到巨額東北土地。《東北通訊》由此痛呼,“日本獲得商租權,東北土地由此斷送”[12]。
二、民國輿論界對商租危機的及時報道
日本強制推行商租權后,導致中國東北地區危機日增。為警醒國人,鞭策政府提出有效對策,民國輿論界借公共輿論為利器,及時披露商租權與日本侵略的關系、中日協商商租細則的進程、揭露日本推行商租的卑劣手段及廣泛報道日本制造的商租危機等,涉及主要內容如下:
(一)揭示商租與侵略滿蒙關系的報道
1915 年5 月25 日,中日《滿蒙條約》簽訂后,民國輿論界開始研究《滿蒙條約》,揭示商租權與侵華的關系。《民國日報》指出:“日本視實行商租為徹底侵略東省之前提,吾人為自衛計,不能不群起抗議,誓死力爭。”[13]《申報》贊同此舉,認為“于日本滿蒙事業計劃有重大關系者”是商租權問題[14]。即使日本官方,也認同此說。日本拓殖省大臣松田在沈陽講話強調:“滿洲土地商租權問題,為重大問題之一”[15]。就如《大公報》揭示說:“東省外交,數十年之歷史里,外人勢力深入各方面,其接觸之多,范圍之廣,直為局外人所不能想象,大致日方最置重者第一為土地商租。”[16]上海《日日新聞》也報道稱:奉天地方日本駐滿各領事集議,所議各案中最重要的“滿洲土地商租問題”赫然在列[17]。《申報》更深入地揭示商租權在日本侵略滿蒙扮演的中軸角色,說:日本乘中日懸案未曾解決之時,已召集駐滿官憲回國開重要會議,討論侵略滿蒙的實行方法,其中“有下列四項中心議題”,而“商租權解決案”是侵略滿蒙關鍵的步驟[18]。對該關鍵步驟的落實,《申報》展開暢想:“以日本最近在東省積極推行之商租權而論,倘亦蒙我方允許,其危險實不可勝言,蓋帝國主義之侵略中國,向以保護僑民保護商業為名,東省僅有日本租借地,其經濟政治勢力,已隨木屐和服而無往弗至,若再允許其雜居,在日人侵略之入微,更不待言”[19]。所以,商租權在日本侵略滿蒙步驟中,扮演著中軸的角色。如民國學者王新命揭露說:滿蒙條約賦予日人的“南滿洲商租土地權、東蒙古合辦農業權、滿洲內地雜居權是三位一體的特權”,但商租權處于中樞統領的地位。民國時人陳紹禹在《申報》刊文,呼吁抵制商租,否則日本人“其居住所到之地,警察權、經濟權都要隨之喪失,日本人如果有居住營業自由,同地的中國人就要沒有自由,甚至不能立足”[20],商租權就是如此。總之,如《大公報》警示說:“擴張商租權問題,實為其全部計劃之骨干,此尤吾人所黨深切注意者也”[21]。
(二)披露商租土地實施細則談判進程的報道
除揭示商租權與侵略滿蒙的關系外,輿論界及時報道商租權在中國東北的實施進程,尤其對雙方懸而未決的實施細則談判予以高度關注,進行及時報道。因商租實施細則的未簽訂讓日本在東北商租土地遇阻,日本于1921、1924 年兩次由駐奉總領事向奉天當局提出,商議制定商租實施細則。《益世報》報道說:“日本方面以字面上發生疑義,致不能遂其野心之發展”,故“決議與中國交涉改正”[22]。隨后,《京報》《申報》《大公報》等報刊對中日雙方的交涉進程、細節等進行諸多報道。例如,《京報》刊文的《日本決定滿洲商租新案》所說:“日本外務省業已為詳細之調查,并參酌中國方面之希望,制成具體案”,該具體案“以四要點為基礎”[23],大致解決商租范圍、期限、“農工業意義”和“工業意義”的疑義[24]。但是,經巴黎和中國遞交廢除“二十一條”的提案后,中國方面認為商租條約已經失效,中方多次拒絕日本的交涉提議。如《申報》所言:“經我舉國反抗,及民八日本又自訂土地商租暫行規定,用強硬手段,要我當局即予施行,幸當局以主權所關,未予承認,民十六之際,彼又持此議,復遭駁斥。”[25]
最后,《東南日報》刊文說:“商租問題,中國政府雖曾受日本之交涉,然并無何等進展”[26]。此后,日本又多次修改方案,與華交涉卻始終未獲得突破,商租的細則交涉如《晨報》刊文所說:“東省商租交涉陷于停頓[27]”。此后,據《大公報》報道說:“日外務省催速解決滿洲大地商租權問題”,中國均以各種借口推諉緩辦[28]。中日商租實施細則交涉因中方的拒絕商定,讓日本苦不堪言。《大公報》揭露說:日本對“滿蒙已絕望,謂苦于人口與食糧問題,而受排斥之日本人,其在滿洲僅二十萬人,且因機關之不統一,土地商租之未確定,以致事業無從發展。”[29]“商租權問題至今無眉目,發展于滿蒙之望殆絕”[30]。
(三)揭露日本推行商租卑劣手段的報道
當日本實施商租土地受到中國抵制時,日本決意通過卑劣的手段誘迫中國人締結所謂商租契約,以不法手段完成東北土地的攫取。如《大公報》報道說:“前年中日締結新約,準日人在南滿一帶雜居及商租地畝之權利,于是日本商民咸勾串當地奸滑之徒,誘勸鄉愚將地契質押,盤取重利,及其結果則訂商租契約”。還舉例子證明說:“沈陽縣西鄉又發生商租巨大地畝案”,據《大公報》揭露說:該案緣由是當地平民因資金短缺,“初以地契作押,迨至本利不能如期歸還,(日人)則將該地契據為己有”,或“乘此時機逼令地主商租,且可以找得巨金,鄉民遂受其愚矣”[31]。
公共輿論界還深度揭露日人制造商租危機的行為,“一般日人利用當地奸民,勾串地主先將地契證據向日人抵押洋款,利重期短,迨期至不償,即逼令地主書立商租契約,甚至立契到手即迫各佃戶加租,先繳后種于是佃戶地主控案累累。日本官吏反謂各地方官阻礙商租,漠視條約,實則日人所租之地并非自行墾種,欲假其名以得土地權而已”。由此導致的后果是,“日人商租各案無一不有糾葛,反因此惹起交涉”[32]。相關類似的報道還有很多,據《大公報》報道,中日商租一節,已載在條約,惟奸民地痞,每貪小利私將房地出售于外人,亦有暗中典賣者,以致釀生糾葛,惹起外交[33]。1928 年10 月18 日,《申報》更是直接刊文警示國人,說:“日本侵滿之處心積慮,謀攫我商租鐵路等實權”[34]。
(四)廣泛報道商租制造的危機
日本強制推行商租權,以所謂重利誘迫中國平民租借土地,或提供以土地為抵押的貸款等手段,簽訂商租約章。當其中某一環節出現問題時,日本便乘機占有土地,大量的中國平民失去土地,引發生存危機。對此,報界也做了及時報道。
1917 年8 月25 日,《大公報》報道:日本取得商租權后不久,“日本商民咸勾串當地奸猾之徒,誘勸鄉愚將地契質押,盤取重利,及其結果則訂商租契約”[35]。大量商租契約的簽訂導致國人的土地被攫取,中日沖突頻發。如1917 年輿論界披露“果權商租案”。北京旗人果權在東北撫順縣有莊田400余畝,因家計艱窘,擬將土地售予原佃戶獲得金錢,但佃戶們要求減價。果權一怒之下將莊田全部商租與日人原口聞一,“原口派令日人多名前往索地耕種”,佃戶們生計受損紛紛呈訴衙門,“幾釀絕大風潮”。[36]《東北通訊》也報道日本人大肆商租,制造社會危機的惡性事件。據報道,日本瞄上東北的虎林縣、密山縣、樺川縣、寶清縣、勃利縣五縣,“因僻處邊境,居民稀少致地利未能開發,現在日人借偽政府之手獲得商租權,并以偽國政治力量,限令當地民眾,繳納地照,全數退出,為日人移民區域。”“所苦者我五縣同胞,均有被離故土之慘,實可痛也”。[37]
《大公報》總結說:“日人藉商租之名愚弄鄉民,盜賣國土之交涉,層見疊出,人民亦有不欲出賣被勢所迫而出此者”[38]。結果是大量的土地丟失,由此引發大量的國人生存危機事件。隨著日本人大量商租土地,中國社會震動,引發國人反日的情緒。《申報》報道當時的情形是,“商租尤為東省官民反對”。[39]公共輿論界也報道說:“日本已著手在滿蒙建筑六大鐵路,強迫實行土地商租權。東省已入危亡狀態”[40]。總之,東北土地“一落日人之手,日人即曲辭狡賴,認為賣給,不許我國農民贖回”,“遂使日人在我東北握有多量之土地,而使我國農民蒙受莫大之損失,我國權蒙受莫大之迫害”,最終“糾紛百出,懸案累累”。[41]
三、公共輿論界提出應對商租危機的具體策略
在民國特殊環境下,輿論界不僅對東北商租土地引發的危機進行及時報道,而且對如何應對這種危機積極獻言獻策,這主要體現于:
(一)主張否定商租條約
商租危機的緣起是滿蒙條約的簽訂,但是該約是強迫簽訂,所以自該約簽訂之時,輿論界廢棄之議便不絕于耳。1924 年12 月30 日,公共輿論界建議奉天省政府不得承認日本提出的商租權問題。如其所說:“近來聽說日本方面屢次向省府交涉商租一節,我們不僅認為二十一條有損國家權利,更應該認識到未經中國四億同胞承認有悖于世界各國之正義人道,違反公理。現在日本方面單獨提出商租問題,我們如果答應與其交涉,則等于間接承認了二十一條,則必將失落于國際信譽。蓋‘商租’二字,狹義解釋關系到南滿東蒙,廣義則攸關全中國之生死存亡。將來日本如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韙,或以利誘威脅等手段進行壓迫,則省府應毅然拒絕之”[42]340。1924 年8 月12 日,《申報》刊文,提出“商租問題之根本系由二十一條件協約而來,而二十一條乃為中國全國上下一致否認之,強迫條約至今無人不否認其效力不便”[43]。
1925 年1 月3 日,《申報》建議說:“省議會請省長對日本滿洲商租案,萬勿承認,以維主權”[44]。《申報》強調,“商租尤為東省官民反對”。其中,民國時人王永江講述反對的理由,說:“在奉反對商租問題,理由為商租與雜居關系密切”兩者相互配合,對華利權侵損嚴重。他認為,商租權屬非法的“二十一條”給予,理應撤廢,但現在撤廢“殊有增加糾紛之虞”,所以保守建議“商租案惟有保留不議一法”[45。]況且“日人在我東北本無購買土地權。民四雖曾于絕無理由之二十一條中提出土地商租權一條,但此亡國之條約,國絕未承認”[46]。
(二)主張出臺法律法規進行抵制
1915 年5 月當中日《滿蒙條約》簽訂,輿論界也興起抵制之議。《大公報》分析認為,“我國外交失敗于條約上者固多,失敗于條約以外者,尤遠過之”,“今請進而述調查所得之中日條約實行狀況”。[47]后來,當民國北京政府頒布《商租地畝須知》14 則等限制法令,令輿論界相當振奮。輿論界主張更進一步,直接出臺相關法律法規予以限制。如民國時人鄭君建議說:“即如商租、雜居制,雖屬條約所許,仍應以省政府力量予以嚴密限制”。[48]至于如何限制,《申報》建設:“今后我東北當局,亟應嚴格禁止國人私將田地租讓外人,并根據內政會議決議中,‘為妨止本國人民擅自租賣土地與韓人起見,應嚴定盜賣或擅租國土懲處條例,以資儆戒’之原則,擬定各種條例,嚴格執行”[46]。此后,東北地方當局響應輿論界呼聲,連續頒布多部嚴密的法律法規。
(三)主張全民參與抵制商租
此際,輿論界還在呼吁全民參與抵制商租實施。如1928 年6 月13 日,《申報》大力宣傳上海市宣傳部抵制商租的努力,“上海市宣傳部制定反日設計教育大綱,上海市黨部宣傳部在反日宣傳運動周內,擬請本市各小學實施反日設計教育,以反日資料聯絡各科教材”,其中設計反日教育大綱,主體內容是反對治外法權、土地商租、租界、以及其他的一切特權[49]。《對日新方針之確立與施行》建議“須全國一致,求國民了解,明于輕重取舍之義,使政府得以放手進行,更使外人知中國國民最后意旨,只能讓步至何種地步,逾此則惟有聽其破裂,長久對抗,不惜同歸于盡耳;須安撫東北人民,去除偽國阻力,使日本不致再以舊政權復活之說,恫嚇人民,而偽國取消,則善后交涉,更易著手;須喚起日本國民注意,使了解中國上下一致之真意,俾于從違之際,對最后的得失利害,有明了之判斷,不再為軍閥野心所誤,夸大宣傳所迷”[50]。1932年7 月1 日,《大公報》刊文《請看日本之滿洲移民計劃,如何抵制須待國人努力》,呼吁全民參與抵制商租權[51]。1928 年12 月13 日,據《大公報》報道,說:“黑龍江路權自在會,以日本此次對華要求,不僅路權一項,也如商租權、滿蒙雜居權等亦均列在交涉之內,如加大宣傳工作則日人將謂滿人心已死,益將強硬,因此學術聯合會,職教員聯合共同發起黑龍江反會”[52]。
(四)主張速定抵制商租的新方案
自1931 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扶持的偽滿洲國成立,促使中國抵制商租權的形勢改變。為適應新的形勢,輿論界亟呼民國政府擬定新方案。如1931 年12 月31 日,《大公報》呼吁“贊成宣布對日整個方針”,并且提出方案“商租問題,應與撤廢領判權問題同時解決,在領判權未取消前,維持九一八之原狀”[53]。但是,日本不理會中方提出維持“九一八”事件前現狀的要求,大肆商租土地。如輿論報道所說:“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商租土地技巧更顯奸狡,“先則改正商租辦法,遍及東北三省,近則議由偽國收買土地,放給鮮農,以避強占地畝恃強霸種之民族沖突,凡此種種,胥為實現融為一體之野心”。[54]針對此情況,輿論界要求“乘國際尚未承認偽國,東北秩序仍在擾攘之時,害取其輕,速定方案”[55]。因為“土地商租權問題等,任取一端嗎,皆關乎國命,應如何斟酌因應,亟宜逐案精研,預立方案”[56]。譬如“商租辦法,如何規定,盡可研究[57]”。
(五)主張展示抵制商租成效、增強國人信心
自民國北京政府訂定商租抵制方案以來,輿論界呼吁政府展示抵制商租的成效,借此鼓舞國人信心。如1926 年4 月16 日,《申報》報道:“日本進行東省土地商租交涉,日本政府以南滿方面日本特殊利權之一之商租權,自民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中日間訂立關于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條約,取得該項權利以來,迄今已間十年屢經日本政府向東三省政府折中交涉,終未實現,遂致該條約中規定之‘日本國臣民為于南滿洲建設各種商工業上之建筑物或為經營農業能商租必要之土地’條文及該條約附屬換文所定‘商租之文字附以三十年間之長期限且包含無條件得以行使之租借’等項明文規定,至今僅獲得文字上之權利”[58]。《大公報》也說:“二十一條件已規定商租權,后張作霖曾嚴厲限制之”[59]。在嚴厲限制下,《大公報》透露抵制商租的效果,說:“近據日方傳來消息,土地商租問題,似終無進步,日方已瀕絕望”[60]。中國政府的抵制措施使得日本實施商租權,遭遇極大阻力。
四、公共輿論界對政府抵制商租不力的批判
此際公共輿論界不僅對各地方所取得的各項成績進行宣傳表揚、寄予更高厚望;更對其中的缺陷、弊病提出了嚴厲批評。其最終目的仍在于借公共輿論之力,促使當局和國人更好地應對商租土地。此類批判如下:
(一)對中央政府應對方略無力的批判
如1923 年12 月10 日,《東報》報道說:“王正廷督辦赴日之目的,表面上稱為調查慘殺華人事件之真相,然據傳聞實為挽救北京政府之財政,因難起見,欲以解決商租問題為交換條件而向日本借款”。對于這樣的行為,《東報》批評說:“以上傳說無論有無然,如商租問題,乃二十一條件之一部分且系屬東三省范圍”,北京方面如敢這樣做,將是賣國政府無疑[61]。《大公報》總結說:“南滿區域之土地商租,被承認于袁世凱時代,大錯之一成,蓋在中央而不在地方。十數年來,吉會建筑之延宕,商租地畝之不能順利,毋寧謂中央失敗而地方補救之。直至今日東省外交難題集中于修路與租地兩大端,其禍根仍多由從前所謂中央政府者種之”[62]。1929 年1 月15 日,據《大公報》報道,說:“仍以滿蒙問題壓迫張學良,則尤為錯誤,因中國今日已非軍閥割據時代可比,東三省乃‘中華民國’完整的領土之一部,張學良只為奉命守土之公仆,舉凡鐵路問題,商租問題,自有負責之中央政府在。日本果欲提議交涉,只能向中央要求,不能在地方談判。此為東三省改制易旗后法律上當然之結果。世界茍有公理,此事不容否認。日本若不將此基本觀念,完全認清舊日做法,徹底改變。則中日交涉,斷無結果”[63]。
(二)對東北地方當局應對失措的批判
雖然東北地方當局根據中央政府的抵制商租指示,盡力抵制商租實施。但是,由于東北當局對抵制商租缺乏一套明確、系統而全面的方案,極大的影響了抵制效果。如《中央日報》批評說:“如此無方針,無定見,無組織,得過且過,勢必無事則虛驕,有事則顢頇,虛驕者臨變必張皇失措,顢頇者遇事必遷延放任,虛驕之極,足以召禍,顢頇之弊,足以誤事,虛驕與顢頇,東三省所由致亡”[64]。《大公報》也說:東省地方當局的抵制,到了后期抵制意志也不堅定,使得大量日本人在東省流動,“政府既漠視邊務,地方官亦未一一注意,遂任其自往自來矣”[65]商租土地開始泛濫。甚至,據《中央日報》透露:到了后期,在日本的壓力之下,東省地方當局打算讓步,奉天省長已經對日本駐奉總領事承諾交涉滿洲日本商租權問題,日本感慨“十數年來之懸案,漸有解決之曙光”[66]。
(三)對政府出現商租抵制漏洞的批判
民國政府在滿蒙條約談判過程中,沒有明確“南滿洲”和“東部內蒙古”的界限,這讓政府的商租抵制政策陷入困境。如《大公報》所言,南滿商租特權和東蒙合辦農業特權,兩處權利既不同,則何處為南滿,何處為東蒙,實為頭等第一應該解決之問題。然外交當局于此重大問題在談判時絕未注意,于是實行條約遂生困難。《大公報》還深刻揭露:“關于滿蒙條約,應以地域為綱領,彼則利在界限混淆,一逞其漫無限制之殖民政策,何者為南滿,何者為東蒙,始終與我政府無明確之規定,試問如何遵守”。[67]這樣的后果是,“屬于遼西范圍之奉天省錦縣地方有日人前往雜居,為地方官所干涉,當時即執此理由而日領迄不承認,遂無結果,至可嘆也”。至于所謂東蒙,“政府之意,似以東蒙各盟現已改縣治者為限,然日本迄無承認也”。這樣的條約漏洞,使得《大公報》慨嘆“余嘗言我國外交敗于條約上者固多,而失條約以外者尤遠”[65]。這樣的結果,使得南滿、東蒙的界限問題終成“彼我之間的懸案”[68]。
(四)對商租抵制效果的批判
公共輿論界雖然肯定政府抵制商租的努力,并對抵制商租的效果大肆宣揚,但囿于現實情況,國人商租土地給日本人的情況仍時常發生。如《大公報》報道說:為限制商租,民國政府要求國人向日本人商租土地需向當地政府備案,但“所有奉吉兩省均少有正式辦理者,而購地交涉與不法租地之糾葛,奉省時時有之”。[65]而且,情況還在加劇,《大公報》刊文曰:“東省自允準日人雜居訂立不動產商租條約后,中國無知人民貪圖厚利,假名商租盜賣國土之案,層見疊出,雖經官家查出,按律法辦,而一般利徒仍不知懼怕”[69]。甚至,《大公報》透露:“之后日人之勢力即侵入東省迨至庚子更為彌漫,日人所覬覦者為土地礦產兩項,迄乎雜居條約施行,日人藉商租之名,愚弄鄉民,盜賣國土之交涉,層見疊出,人民亦有不欲出賣被勢所迫而出此者”[38]導致被日本人商租到大量土地,釀成東三省人民的生存危機。
結語
土地是關乎生存的核心資源,對于任何國家、民族或個人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1915 年中日《滿蒙條約》的簽訂,令日本人有機會以“商租土地”名義,染指中國寶貴的土地資源。鑒于該特權的危害,民國政府與時人起而應對,提出諸多方略。民國輿論界更是借媒體輿論為手段,針砭時弊,指陳厲害,在民國政府抵制商租權的努力中發揮重要作用。它不僅對日人造成的商租危機進行跟蹤報道,而且對民國政府實施的抵制政策進行了及時報道與宣傳。為挽回利權,輿論界也積極向當局獻言獻策,提出了各類針對性的應對措施。當商租抵制取得成效時,輿論界進行大力宣傳表揚;而當日本無視中國的抵制,商租危機逐漸加深時,公共輿論界又對民國政府抵制不力的行為大加批判。但無論商租危機的日益增強,還是具體方略的提出,以及對民國政府官員的批判,均屬公共輿論界應對商租危機的重要內容,借此警醒執政當局和國人,固我土地,維我利權。
總之,《滿蒙條約》強迫出讓的商租權,既引發東北地區國民生存的土地危機,也催生了民國中央及地方政府抵制政策的施行,還喚起了社會各界尤其是媒體輿論的關注。民國輿論界對商租權的大量報道,既出于對重大新聞的追蹤,也出于愛國熱情,兩者結合呈現了時代傳媒與政治實踐的互動關系。在實際中,民國政府抵制商租權的實施進程與抵制的效果,與民國輿論界的關注報道很有關系,媒體的及時發聲,既警醒了國人也鞭策政府認真應對。民國政府抵制商租權措施的優劣,在媒體輿論的監督下得到檢驗和認知。這種認知又反過來促成新的公共輿論,對進一步督促民國政府和地方主政者去修正或調整其政策,以便更好地應對商租危機提供了必要的參考與借鑒。民國政府抵制商租的實施與公共輿論的及時發表這樣一種媒體與執政當局良性互動的過程,即顯示了政策實施下輿論的開放性與引導性,也對執政者實施執政活動很有益處。
注釋:
①王蕓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年;張忠紱:《中華民國外交史》,華文出版社,2012 年;馬振犢、唐啟華、蔣耘著:《北京政府時期的政治與外交》,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王海晨:《張作霖與“二十一條”交涉》,《歷史研究》,2002 年,第2 期王旭:《日本要求“土地商租權”與中國官民的抵制》,吉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