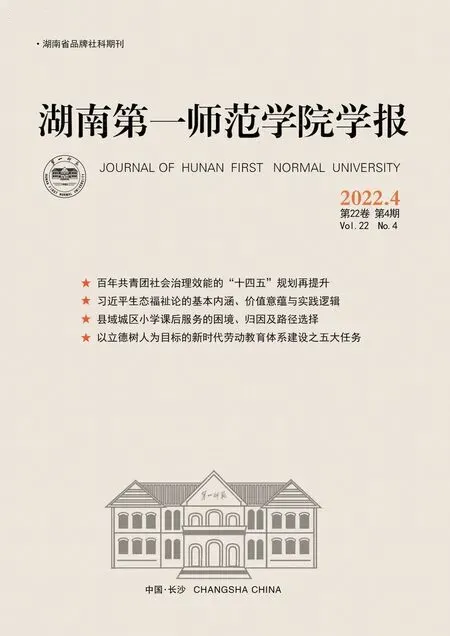日本古辭書“倭玉篇”考述
王安琪
(湖南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2)
“倭玉篇”①是日本中世時期出現的一系列按部首排列、以字形為檢索對象的字書的統稱。這些字書集中出現于《大廣益會玉篇》傳入日本之后,其編纂方式參考了《玉篇》,且多以“玉篇”命名,如“倭玉篇、和玉篇、玉篇略、玉篇要略集”等。其在內容上對《玉篇》有一定的繼承,是《玉篇》“日本化”的重要成果。
“倭玉篇”在流傳過程中形成了眾多類型和版本。據岡井慎吾《玉篇の研究》、川瀨一馬《古辭書の研究》、鈴木功真《倭玉篇の研究》等的搜集和考察,目前日本學界所認為的“倭玉篇”系列字書包括:
《倭/和②玉篇》(寫本28 種;刊本9 種,包括慶長版、夢梅本、古活字版等)
《玉篇要略集》(1 種)《新編訓點略玉篇》(3種)《玉篇略》(4 種)
キリシタン版《落葉集》附載《小玉篇》(1 種)
《類字韻》(2 種)《音訓篇立》(1 種)《拾篇目集》(1 種)
《元龜字叢》(1 種)《便蒙字義》(1 種)《篇目次第》(1 種)
近年來,隨著海外漢學研究的興起,跨文化漢字研究逐漸受到語言文字學界的重視,而日本漢字研究又是其中的重要課題。目前,國內關于日本漢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辭書的引書、輯佚研究,俗字、疑難字考釋研究,中日詞匯交流研究,等等。其中,前兩個方面的研究所關注的主要是日本鐮倉時代以前的文獻,第三項研究主要關注江戶時代以后的文獻,而對于鐮倉、江戶之間的室町時代卻鮮有問津。室町時代歷時兩百余年,連年戰亂使得日本的社會秩序被進一步破壞,僧侶階層取代貴族階層成為文化主體,文化階層下移,俗文化地位上升。與之前的奈良、平安時代相比,漢字的使用范圍進一步擴大,出現了大批文獻以及一些特殊的用字現象,是古日語向現代日語演變的重要階段。對這一時期日本的漢字使用情況進行研究,可以彌補現有研究的不足,使得漢字在日本的傳播史和接受史鏈條更加完整、連貫。
“倭玉篇”流行于室町時期,與《節用集》《下學集》并稱為“日本中世的三大俗字書”,在日語史和日本辭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時,“倭玉篇”是一種俗字書,針對的是漢學水平較低的人群,貼近大眾,而其影響力可以波及到江戶乃至明治時期,具有時間跨度長、使用頻率高、傳播范圍廣、流傳類型多等特點。作為室町時期日本漢字研究的切入點,“倭玉篇”無疑是最好的選擇。而國內學者對該文獻對該文獻關注較少,有時會在一些介紹性的文章中提到,而這些介紹大都比較簡略,甚至有違背事實之處。筆者拙文《“倭玉篇”系列字書的類型和版本》中對“倭玉篇”的版本及相關研究情況進行了較為全面的介紹,但受篇幅所限,對“倭玉篇”的成書背景、編纂者、體例以及其與《玉篇》的關系等問題均未做說明。本文擬對這些方面的情況做進一步的介紹,以便向學界同仁呈現“倭玉篇”的全貌。
一、“倭玉篇”的成書背景
“倭玉篇”出現于日本的中世時期,即鐮倉、室町時代,當時日本的社會文化有以下三個特點:
第一,日本的貴族階層沒落,權力中心轉移。從推古天皇開始,歷經飛鳥時代、奈良時代和平安時代,日本的權力核心是以天皇為中心的貴族階層。到了平安時代末期,日本出現了源氏和平氏兩大武士集團,兩個集團之間戰爭不斷。之后,源家擊敗平家,建立鐮倉幕府,確立了武家專政的鐮倉幕府政治體制,皇權受到嚴重沖擊。“當時事實上存在雙重權力,一方面是武家以鐮倉為中心行使實質上的權力,一方面是以天皇為象征在京都行使形式上的監護權。”[1]180鐮倉幕府末期,皇室公家勢力與武家勢力發生權力之爭,統治集團擁立了不同的天皇,日本進入南北朝時期。明德三年(1391 年),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消滅南朝,“樹立了將軍專制的權威,實現了全國統一,將政治權力中心移至京都室町”[1]216,日本進入室町時期。至此以后,日本天皇“名存實亡”,國家權力把持在將軍手中,以天皇為核心的貴族階層基本沒落。
第二,權力的更迭、戰爭的頻發給日本的舊有文化帶來了巨大的沖擊。這一時期,日本社會的標志性特點是“下克上”,即下層推翻上層——武士反叛掌權者,家臣反叛領主,庶出家族反叛嫡系家族,農民反叛地主,整個社會動蕩不安。“由下克上帶來的社會勢力的新陳代謝,在文化領域中也注定了貴族文化沒落和大眾文化上升的命運……順應社會勢力的交替,文化領域中也發生了大規模的新陳代謝。”[2]153-154這一時期,文字開始由貴族走向平民,俗文化日漸興盛。以“倭玉篇”為代表的俗字書就是為了滿足大眾的讀寫需求而出現的。
第三,僧侶階層成為文化主體,禪僧成為佛教傳播和漢學研究的主力。自佛教傳入日本以來,日本的知識階層就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一是以天皇為核心的貴族統治階層,二是僧侶階層。這兩個階層都是接受中國文化的主體,僧侶是佛教的接受和傳播者,而貴族則是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漢文化的接受和傳播者,兩個群體的文化訴求不同。隨著貴族階層的沒落和佛教的興盛,僧侶階層逐漸成為文化領域的主角。進入室町時代后,“雖然鐮倉時代的新佛教天臺宗、真言宗、禪宗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禪宗卻占據中心的統治地位”。[1]218而日本禪僧主張“禪儒不二”“禪儒結合”,以儒學作為“誘導人參禪的手段”和“實現參禪悟道的方法”,“他們的‘禪儒結合’,是將禪、儒作為體與用的關系,形成室町時代禪的特色”。[1]218-219在室町時期,禪僧既是佛教傳播的主體,同時也是漢學研究的主力。他們不僅留下了大量的漢詩、漢文作品,也留下了很多抄物,如《毛詩抄》《論語抄》等。
二、“倭玉篇”的編纂者
最早的“倭玉篇”是由誰編纂的現已無從考證。而且,“倭玉篇”在流傳過程中出現了數種類型,可知其間必有多人參與過改編。不過,據筆者考察,“倭玉篇”系列字書的編纂者應屬僧侶階層。理由有三:
第一,僧侶階層有編寫需求。“倭玉篇”系列字書是部首分類式字書,而“倭玉篇”之前的幾種部首分類式字書——《篆隸萬象名義》《新撰字鏡》《類聚名義抄》等的編者皆為僧侶。這是因為部首分類式字書主要是用來查字的,其目的是指導漢籍閱讀。僧侶為了研習佛法,勢必要閱讀大量漢文佛經,根據實際需求編寫適用的工具書合情合理。
第二,僧侶階層有編寫能力。如上文所述,“倭玉篇”系列字書出現的中世時期,僧侶代替貴族成為知識主體,這群人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具備編寫字書的能力。正如川瀨一馬在《古辭書の研究》中所說:“多數著作匿名,且編者多為禪僧,這是這個時代辭書的一個特色。”[3]557
第三,文獻證明。在現存的“倭玉篇”中,我們調查到七種著錄了抄寫者信息的版本,除了弘治二年寫本的抄寫者“主彌兵衛”外,其余皆為僧侶:
1.靜嘉堂文庫所藏的“傳紹益本”中有古筆極札③“高臺寺開山紹益長老真蹟元龜字叢 一冊”④,高臺寺位于京都市東山區下河原町,是臨濟宗建仁寺派的寺廟,屬于禪宗體系。
2.大東急記念文庫所藏《玉篇要略集》卷末有識語“旹大永四年閼逢 涒灘卯月二日三光末派劫嶽書旃 烏焉馬誤不少鳴呼慙愧”,“三光末派”據稱“是繼承了三光國師法系的紀州由良興國寺、泉州大雄寺或者云州云樹寺、京都妙光寺的僧侶(禪宗)的手跡形成的”[3]686,屬于禪宗體系。
3.同樣藏于大東急記念文庫的享祿本《玉篇略》下卷最后寫有“享祿壬辰菊月仲旬日 律野永林寺住謙長環沙彌上下卷書者也”,永林寺⑤是曹洞宗寺廟,屬于禪宗體系。
4.現藏于東京大學國語研究室的永祿本《類字韻》第五冊末尾有“永祿六年昭陽 大淵獻初商晦日天翁瑞”的識語,與全文筆跡相同,可知此書為天翁所抄,識語左側有“前永平天長二世天翁正安大和尚(花押)于時天正十年壬午四月十日置之”,說的是天翁在寫畢之后的十九年中,將此書作為日常使用的物資置于自己所居住的塔頭院。永平寺位于福井縣吉田郡永平寺町,是曹洞宗派寺廟,屬于禪宗體系。
5.現藏于宮內廳書陵部的賢秀寫本為慶長十年(1605 年)寫本,上卷末寫有“慶長拾稔乙巳蕤寶上旬書之畢天臺末流南山沙門賢秀法師位”,下卷末寫有“慶長拾稔乙巳蕤寶上旬書之畢/大倭州 多武峯 妙樂寺 平等院 於松岡 天臺末流/南山 沙門賢秀法師位 廿歲之時右三卷書之者也/表紙共束手致一細工以傳遐代云”,知此版本是由賢秀法師所抄,屬于天臺宗體系。
6.現藏于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的圓乘本為慶長二年(1597 年)寫本,各卷首有“圓乘”(圓)和“日氣”(小長角)兩枚朱印。“圓乘”,《佛教語大辭典》將其釋為“全心全意地教”(完全円滿な教え),《法華驗記 上·一五》:“若我出山,交雜人間,染著世習,還作惡業,被牽邪見,廢圓乘善”;天喜三年(1055 年),后朱雀天皇在京都市右京仁和寺附近修建了天臺宗寺廟——圓乘寺,后朱雀天皇逝世后,便葬于圓乘寺陵。該寺于長治二年(1105年)燒毀,而圓乘本《倭玉篇》抄寫于慶長二年,應與圓乘寺無關。日本有一個茶道流派名為“円乘坊派”,在安土桃山時代的茶僧(本能寺円乘坊住職)中,以利休的女婿古市宗円為中心;而本能寺于應永二十二年(1415 年)建于京都市中京區下本能寺町,屬于天臺宗寺廟。此“圓乘”或與本能寺圓乘坊有關,亦屬天臺宗體系。
以上六種《倭玉篇》皆為僧侶所抄,其中四種屬于禪宗體系,兩種屬于天臺宗體系。這應該不是偶然,可以推測,在“倭玉篇”尚未大量刊行的室町時期和江戶早期,“倭玉篇”主要是以抄本的形式在僧侶當中流傳的。
室町時代,“五山禪僧”群體是佛教傳播的主體,禪宗成為主流教派。這一時期,日本禪宗的特點是禪儒結合,僧人在研讀佛經的同時,也閱讀了大量的儒家經典。我們在對“倭玉篇”的考察過程中,并未發現其中對佛經用字有明顯的傾斜,結合當時禪僧的治學情況,這一點并不奇怪。
另外,室町時代的日本寺院還承擔了基礎教育的工作,僧侶們同時有著僧師的身份[1]223。當時的教科書以“往來物”為主,如《庭訓往來》《新撰類聚往來》《游學往來》《尺素往來》等。不過,僧侶們編纂一些通俗化的字書供學生使用也是很正常的。“倭玉篇”是否同時具有識字課本的性質,還需進一步考察。
三、“倭玉篇”的書名
“倭玉篇”這一書名是在什么時間出現的,尚無確切的答案。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倭玉篇》是長享三年(1489 年)的抄本,雖有題名為“和玉篇”的封皮,但有學者認為是后人所加。長享本卷上的封皮內側有一段文字,譯文如下:
此書上卷末寫有“長亨⑥三八月日”,這里的“長亨三年”即延德元年(八月二十一日改元)。現在是明治三十七年,距離當時已經四百一十五年了。
每卷都題有“和玉篇”,是否是其本名不得而知。“倭玉篇”這一名稱在《運步色葉集》的天文十七年(1548 年,引者注)的序文中可以見到,指的應該就是這種書。
由此可知,“倭玉篇”這一名稱出現的時間當不會晚于1548 年。
現存“倭玉篇”的古寫本書名各式各樣,除了“倭玉篇”“和玉篇”“和玉”之外,還有“篇目次第”“音訓篇立”“拾篇目集”“類字韻”等。對此,中田祝夫說道:“這樣的種種題寫在古寫本上的名稱,其中不是沒有后人由于輕率而誤寫的書名。總之,這些均作為正名而廣為普及是無法想象的。”[4]解說⑦另外,還有使用“倭玉篇/和玉篇”的書名、而該書并不屬于“倭玉篇”系列字書的情況,如《字鏡集》的“屋代本”,使用時要特別注意。
四、“倭玉篇”的編排方式和編纂體例
(一)編排方式
“倭玉篇”雖然種類眾多,但基本的編排方式均為部首分類式,即將漢字根據部首進行分類,再對部首進行排序。而部首的數量以及排列順序,不同種類之間差異很大,其中部首數量最多的是《新編訓點略玉篇》,最少的是圓乘本。鈴木功真在其博士論文《倭玉篇の研究》中,根據部首的排列順序,將“倭玉篇”分成五大類:“《大廣益會玉篇》的系統”“《世尊寺本字鏡》的系統”“意義分類的系統”“《龍龕手鑒》的系統”“《字鏡集》的系統”。這五大類彼此之間部首排列順序均不相同,而每大類中的版本之間的部首順序亦不完全相同。不同種類的《倭玉篇》的冊數也有不同,以上中下三冊的情況居多。各冊正文前通常有目錄,列出部首和部首編號。字頭呈豎排、分段的排列方式,每半葉的段數和行數各有不同。
(二)編纂體例
陸尊梧《日本古辭書與中國古辭書的淵源》一文中說:“它(《倭玉篇》,引者注)的體例是以漢字為字頭,先用漢字注出反切,再用片假名注出日語讀音,然后再加上日語注釋,偶爾也用漢語注。這些注釋,基本上就是把《大廣益會玉篇》的注釋用日語翻譯出來。”[5]74陸文的這段表述主要涉及兩個問題,一是注音,二是釋文。
據考察,“倭玉篇”系列字書的注音方式大體有兩種:一種是在字頭的右側用片假名注音,有時左右兩側皆有注音,如第四類本、慶長版等;另一種與漢字字書中的直音法類似,注音采用片假名或漢字,并在后面加一個“云”字,如延德本、《音訓篇立》等,這種注音方式可能受到了日本字書《字鏡》的影響。而在“倭玉篇”的諸多版本中,系統保留反切的基本沒有,多數版本中僅有少量的反切。例如,長享本《倭玉篇》共收單字字頭10304 個,詞頭46 個,其中保留反切的僅40 個;文琳《〈玉篇略〉反切用字特征初探——與中國古代字書注音關系之比較》一文中所考察的《玉篇略》是“倭玉篇”中反切保留較多的版本,與長享本的收字規模大致相當,其中也僅有389 個字頭下收錄了反切[6]10。因此,陸文中所說的“用片假名注出日語讀音”是諸多《倭玉篇》中普遍采用的體例,而“用漢字注出反切”就有違事實了。
“倭玉篇”系列字書中的釋文多為片假名,亦夾雜少量的漢字釋文。而陸文中所說的《倭玉篇》的假名注釋“基本上就是把《大廣益會玉篇》的注釋用日語翻譯出來”的說法與事實不符。菊田紀郎《倭玉篇三類·四類本の和訓》一文中對“倭玉篇”中的第三類本和第四類本“肉月部”中保留有“肉”字旁的字頭及其和訓做了考察,指出其中有的字音和釋義與《新撰字鏡》《類聚名義抄》《字鏡集》等有關,反映了“倭玉篇”音訓來源的復雜性[7]。
另外,岡田希雄在《和玉篇雜考》一文中指出,在《大日本古文書》、日本家族文書中位列第九的《吉川家文書別集》的“西禪永興兩寺舊藏文書貳”一條中收有吉田元長的自傳,其中第六十八章和一一八章中記載了另一種樣式的《和玉篇》。這種《和玉篇》字頭的上方為唐音,右側為漢音,左側為吳音,下方為日文讀法即和訓。和訓部分有三條豎線,一個字頭往往有幾個和訓。第六十八章作于天正年間(1573—1592 年),由此狀可知,該版本的《和玉篇》是吉田元長請周伯在《玉篇》的基礎上添加假名注釋而成的,周伯添加了漢音、吳音、唐音三種讀音,外加訓注。在現存的《倭玉篇》中,特意添加唐音的情況很少見。當時流傳的《聚分韻略》用黑色將唐音標注了出來,可知周伯在添加假名注釋時使用了《聚分韻略》的假名注。[8]1125-1126該版本目前未見著錄。
五、“倭玉篇”與《玉篇》的關系
對于這個問題,一些學者認為,“倭玉篇”是在前代的《字鏡集》等漢和辭書的基礎上簡化而成的,只是借鑒了《玉篇》的編排方式,并使用了其書名,如上文中提到的川瀨一馬[9]62-63。對于這種說法,山田忠雄等學者進行了反駁。其實,只要對內容稍加分析,就會發現,“倭玉篇”絕不僅僅只是借鑒了《玉篇》的編排方式和書名這么簡單。在有些版本的《倭玉篇》的釋文中明確指出該字頭《玉篇》未收,說明編纂者一定參考過《玉篇》。
以長享本《倭玉篇》為例,長享本中有12 個字頭的釋文明確指出該字《玉篇》未收:
?:ヲトトヒ(一昨日【前天】)⑧。玉篇無之。
榊:サカキ(榊)。玉篇無之。
杣:ソマ(杣【育林山,為采伐木材而種植樹木的山;育林山木材】)。玉篇無之。
楁:ヒヒラキ(柊【木名】)。玉篇無之。
?:クハタツ(企つ【企圖】)。無玉篇。
另外,“西”(“襾”之誤,筆者注,)字旁邊有一條批注,明確以《玉篇》為依據來說明長享本中的釋文有誤,如果長享本《倭玉篇》在編寫時沒有參考《玉篇》的話,應該不會在釋文中特意做此說明:
西[セイ]⑨:ニシ(西);イル(居る);アキ(秋)。(旁批:於嫁切。覆也。又許下切。漢《玉篇》如此,和點謬之。)
而且,批注中使用了“漢玉篇”的說法。明治七年八月由風月堂刊刻的《文選字引》的凡例中明確提到了“和玉”和“漢玉”,說明在日本人看來,“和玉篇”就是與中國《玉篇》相對的“日本《玉篇》”。如果說“倭玉篇”與《玉篇》之間沒有密切的關系,應該不會給人們留下這種印象。
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倭玉篇”就是“和譯的《玉篇》”。上文中提到的陸尊梧《日本古辭書與中國古辭書的淵源》一文中說:“……這些注釋,基本上就是把《大廣益會玉篇》的注釋用日語翻譯出來”[5]74,可知在其看來,如果不考慮編纂體例上的變化,那么“倭玉篇”基本上就可以看作《大廣益會玉篇》的日語翻譯本。日本學界也存在類似的說法。山田忠雄在《延德本倭玉編と音訓篇立·世尊寺本字鏡》一文最后說道:“《倭玉篇》中有非常浩瀚的一類是直接出自《大廣益會玉篇》的,在室町時期自然地形成一股潮流。其內容甚至只是將漢文注(反切和訓注)假名化,沒有增加其他的東西,亦可想象到相應地將其命名為‘假名玉篇’……兩種《倭玉篇》——可以稱作‘《大廣益會玉篇》直譯本’的一類和《音訓篇立》系列的一類,是《倭玉篇》中注文最詳細的,且注音的情況偏古式……”[10]319-320。山田忠雄認為《本朝書籍目錄》中所記載的“假名玉篇”可能就是將《玉篇》“假名化”了,另外可能出現過兩種類型的“倭玉篇”,其中一種就是“《大廣益會玉篇》直譯本”。
不過,就現存的“倭玉篇”來看,還沒有一種稱得上是“和譯的《玉篇》”或者“《大廣益會玉篇》直譯本”的,它們都對《玉篇》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主要體現在立部、收字、釋文等方面。以長享本《倭玉篇》為例,其對《玉篇》的改造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歸并部首,同時設立了新的部首,并改變了部首排列的順序。另外,一些單個字頭的歸部情況也與《玉篇》有所不同。
第二,收字量與《玉篇》不同。《玉篇》的收字量在兩萬以上,而長享本僅一萬出頭,在刪去大量字頭的同時,又根據其他材料增收了一些字頭。
第三,在釋文方面,有時確實能看出明顯的翻譯《玉篇》釋文的痕跡,但有時也會根據實際的使用情況對字頭做出新的解釋。如“刕”字,長享本中的注音為“シユウ”,釋文為“クニ(國)。州同”,而《玉篇》中的釋文則為“歷低切。姓氏。又力脂切。割也”⑩。長享本中的“刕”字無論在歸部、字形還是字頭順序上均與《玉篇》一致,可以認為是從《玉篇》中收錄而來的,但其讀音和釋義卻完全不一樣。長享本中稱此字是“州”的異體字。“刕”的這種用法,中國的字書中僅有宋代郭忠恕編寫的《佩觹》中有所提及:“三刀之夢為州”,注“王濬夢懸三刀于梁上,俄益一刀,后為益州牧”,典出《晉書·王濬傳》:“濬夜夢懸三刀于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而“刕”作“州”的用法在日本則較為普遍,如《三體詩法幻云抄》“西出陽關無故人”,注:“陽關,在沙刕”。可見,長享本中的“刕”字應出自《玉篇》,但釋文則根據實際情況做了調整。
綜上所述,“倭玉篇”在編纂過程中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參考了《玉篇》,同時也根據文字使用的實際情況對《玉篇》進行了改造,而這些繼承和改造都是《玉篇》“日本化”的具體體現。
結語
以上我們對日本中世時期出現的古辭書——“倭玉篇”系列字書的成書背景、編纂者、書名、編排方式和編纂體例以及其與《玉篇》的關系等進行了梳理。作為日本中世時期的代表性字書以及《玉篇》“日本化”的重要成果,“倭玉篇”在語言文字層面和文化交流層面都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值得引起學界更多關注。
注釋:
①由于“倭玉篇”是一類字書的統稱,因此文中在指稱這類字書時用引號,具體指稱某種版本時用書名號。
②日語中“倭”與“和”皆讀作“wa”,且在指稱日本時意義相同。“倭玉篇”系列字書中,有的書名是“倭玉篇”,有的是“和玉篇”,學界亦“倭”“和”皆用,因此如無特殊說明,本文對二者不做特別區分。
③極札:辨別古美術工藝品真偽的鑒定書。
④為盡可能呈現文獻原貌,本文在引用“倭玉篇”各版本的題跋、簽章和文獻正文時盡可能使用原文用字,未做繁簡轉換。
⑤永林寺:根據我們目前查到的資料,日本的京都、奈良(八峰山)和新潟都有永林寺。其中,奈良的永林寺開創于1532 年,而新潟的永林寺是五百多年前所建,未指明具體時間,京都的永林寺建寺時間亦不詳。享祿本《玉篇略》抄寫于享祿年間,是1528—1531 年間,從時間上推斷,奈良的永林寺似乎不合。不過,三處的永林寺均屬曹洞宗。
⑥“亨”為“享”之誤。
⑦對于不用“倭玉篇/和玉篇”的書名卻將其劃入“倭玉篇”系列字書的情況,岡井慎吾在《玉篇の研究》里有所提及,如塙氏溫故堂舊藏、現藏于內閣文庫的《篇目次第》:此書叫做“篇目次第”并不恰當,這一點在《國語學書目解題》中已有過論述。書中說:“此書稱為‘篇目次第’恐怕并非原來的書名。通檢其書,前面兩冊在紙的折痕處寫有‘玉篇’,第十一冊封面的外標題‘篇目次第’被劃掉,改為‘和玉篇’。其他的外標題處、紙的折痕處、小口書處皆為‘篇目次第’。大概此書原名‘和玉篇’或只是‘玉篇’,其卷首偏旁的目錄處‘篇目次第’的是后來寫上去的,被誤認為了書名。雖然如此,仍有一部分保留了原名‘和玉篇’或‘玉篇’的地方。”(第379 頁)
⑧圓括號中的漢字為對應片假名詞語的漢字表記,黑括號中為該詞的漢語意思,均為引者所加。下同。
⑨方括號中為該字的注音,通常位于字頭的右側。
⑩此處使用的《玉篇》版本為圓沙書院延祐本,屬于元刊本系列。據考察,長享本《倭玉篇》與元刊本《玉篇》關系密切。相關情況將另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