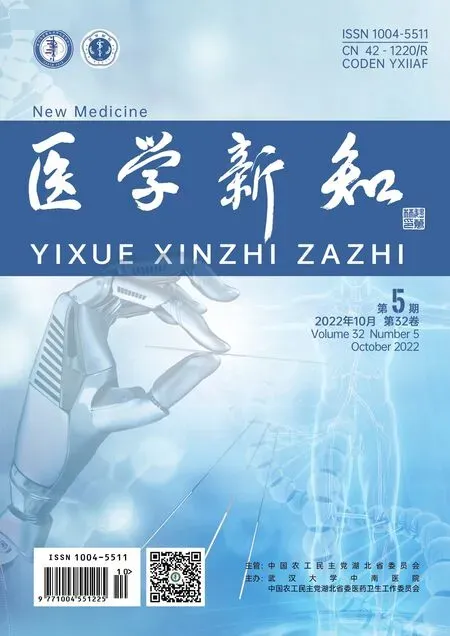克羅恩病早期診療的研究進展
陳 良,許春進,劉占舉
1. 同濟大學附屬第十人民醫院消化內科(上海 200072)
2. 商丘市第一人民醫院消化內科(河南商丘 476100)
炎癥性腸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發生在胃腸道原因不明的慢性非特異性疾病,包括克羅恩病(Crohn's disease, CD)和潰瘍性結腸炎(ulcerative colitis, UC),已成為我國常見的一種消化系統疾病,近年來就診人數呈逐年上升趨勢。由于該病病因和發病機制尚未完全闡明,因此治療缺乏特異性,傳統治療藥物如5-氨基水楊酸制劑、糖皮質激素和免疫抑制劑只能暫時控制和緩解癥狀,長期應用不良反應多,停藥后易復發[1-4]。生物制劑的問世為IBD的治療提供了新的手段,如抗腫瘤壞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單克隆抗體能夠控制IBD癥狀,提高患者生活質量,改善IBD的自然病程,但仍有1/3的IBD患者對抗TNF-α治療無應答,另有約1/3的IBD患者在抗TNF-α維持治療中失應答,臨床上約40%~55%的CD患者最終需手術治療[5-6]。近年來,多項研究指出早發現并及時干預在減緩或阻斷CD的疾病進展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可有效減少手術率、致殘率,對減輕患者以及社會負擔有重要意義[7-8]。因此,如何早期診斷并及時干預成為治療CD的關鍵。本文將對CD的早期診斷性生物標志物和靶向生物治療的研究進展進行介紹。
1 克羅恩病的早期診斷性生物標志物
內鏡和病理檢查仍然是目前CD診斷和監測的金標準。生物標志物是一種非侵入的快速檢測方法,可用于檢出早期病例、判斷疾病活動和預后,易被患者接受。目前,尚需研發具有足夠敏感度和特異性的非侵入性措施協助診斷CD,尤其是早期患者。傳統的生物標志物如C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紅細胞沉降率、白蛋白、血常規等特異性較低,且這些生物標志物在CD和UC患者之間的敏感性不同,與治療后疾病的活動度和黏膜愈合率相關性較差。因此,需要開發新的生物標志物,以更好地預測治療后早期應答,從而為患者提供更及時有效的治療。
1.1 糞鈣衛蛋白
糞鈣衛蛋白(fecal calprotectin,FC)作為IBD經典的生物標志物,其作用已被眾多研究證實。前期研究表明,FC濃度可預測CD患者使用阿達木單克隆抗體(adalimumab,ADA)治療失敗以及是否需要轉換治療,且FC對IBD活動性的預測價值優于CRP[9]。接受抗TNF-α治療的IBD患者中,FC水平與內鏡下評分高度相關[10-11]。FC水平在生物制劑以及其他藥物治療后降低可能預示著IBD患者疾病緩解和黏膜愈合[10]。進一步研究表明,在接受抗TNF-α治療的IBD患者中,治療前基線FC水平越高,治療后無應答率越高,臨床緩解率或黏膜愈合率越低[12-14]。
1.2 抗結核諾卡氏菌多肽抗體
結核分枝桿菌和諾卡氏菌通過入侵并感染宿主維持生存,而主要加速轉運蛋白家族(main accelerated transporter family,MFS)是參與細菌感染人類的最大次級活性轉運蛋白群之一[15-17]。通過對禽分枝桿菌副結核亞種(Mycobacterium avium subspecies paratuberculosis,MAP)以及諾卡氏菌的氨基酸序列分析顯示,MAP與諾卡氏菌具有同源性,并且在MAP的MFS中以及諾卡氏菌的侵襲蛋白中檢測出相同的氨基酸序列。這種多肽復合物被命名為抗結核諾卡氏菌多肽抗體(antiparatuberculosis-nocardia polypeptide anti body,anti-pTNP)。本研究團隊前期對中國9個IBD醫療中心CD患者外周血血清的研究結果顯示,CD患者血清中anti-pTNP水平高于UC患者和健康對照組,回腸CD患者anti-pTNP抗體陽性率顯著高于回結腸和結腸型CD患者,伴有肛周病變的患者anti-pTNP IgG水平顯著高于非肛周病變CD患者[18]。值得注意的是,anti-pTNP和肛周疾病是CD患者炎癥活動期的重要預測因素。anti-pTNP預測活動期CD患者的ROC曲線下面積為 0.918(95%CI:0.886~0.949)[18]。上述研究表明anti-pTNP可作為診斷CD的一種新的生物學標志物,特別是對于回腸末端病變、伴有狹窄和肛周疾病的CD患者。此外,包含anti-pTNP的預測模型顯示其可用于評估CD患者的疾病嚴重程度。
1.3 TNF-α
抗TNF-α治療可通過降低TNF-α的水平減輕IBD患者腸道炎癥,因此腸黏膜TNF-α的轉錄水平可用于評估抗TNF的療效。近期研究指出,UC腸黏膜TNF-α的轉錄水平與抗TNF-α治療之間具有顯著相關性;腸黏膜TNF-α轉錄水平與UC患者糞便FC、UC疾病活動指數評分以及Mayo內鏡評分等臨床參數具有良好的相關性[19]。進一步研究表明,英夫利西單抗(infliximab,IFX)治療應答IBD患者腸黏膜TNF-α轉錄水平顯著降低,腸黏膜TNF-α轉錄水平與疾病緩解和黏膜愈合率密切相關[20-21]。此外,黏膜組織TNF-α轉錄水平正常化預示IBD患者停用IFX治療后的長期臨床緩解[22]。
1.4 IL-17A
Th17細胞分泌的白細胞介素-17A(interleukin-17A,IL-17A)已被多項研究證實在評估IBD患者抗TNF 單抗療效中具有重要作用。既往研究表明UC患者腸黏膜組織內IL-17A轉錄水平越高,接收IFX治療的疾病緩解率越高[23]。在CD患者中腸黏膜IL-17A轉錄水平降低與ADA治療后內鏡下完全緩解密切相關[21]。此外,IL-17A水平正常可能預示CD患者長期臨床緩解[22]。
1.5 IL-7R
有研究報道,在免疫抑制劑、糖皮質激素以及抗TNF-α治療或抗α4β7單抗治療無應答的CD與UC患者腸黏膜組織中,IL-7受體(IL-7R)水平明顯升高,特別是在抗TNF-α治療無應答的IBD患者中尤為顯著。在人源化的小鼠模型中發現,阻斷IL-7R信號可減少T細胞的歸巢并減輕實驗性結腸炎癥,還可抑制UC患者效應性T細胞的體外增殖[24]。因此,在IBD的臨床治療中,IL-7R有望成為潛在的治療靶點以及預測治療效果的生物標志物。
1.6 腫瘤抑制素M及其受體
腫瘤抑制素 M(Oncostatin M,OSM)屬于IL-6超家族,主要由免疫細胞和基質細胞產生。最近研究指出OSM及OSM受體(OSMR)在IBD患者炎癥腸黏膜組織中高表達并與疾病炎癥程度呈正相關,在抗TNF-α治療失敗的患者中尤為明顯,在戈利木單抗治療的臨床試驗中也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25-26]。此外,TNF能夠促進人基質細胞中OSM相關的促炎趨化因子CXCL9和CCL2的表達,表明OSM與腸基質細胞的結合觸發了與其他信號的促炎協同作用[27]。因此,OSM可作為IBD患者抗TNF-α治療療效評價的生物標志物。
1.7 miRNAs
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s,miRNAs)是一類長度約為20~24個核苷酸的非編碼RNA。多項研究指出,miRNAs 在IBD的發生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本團隊研究證實,活動期IBD患者腸上皮細胞中表達miRNA-301A水平明顯升高,且miRNA-301A可通過降低靶基因BTG1在腸上皮細胞表達,進一步影響腸黏膜屏障,從而促進小鼠腸道炎癥發生及腫瘤形成[28]。另一項研究指出,活動期CD患者腸黏膜組織和血清中的miRNA-31、miRNA-200的表達水平均高于健康人群[29]。本團隊還發現miRNA-31A與腸黏膜屏障功能損傷、內鏡下嚴重程度存在明顯關聯,并發現miRNA-10A、miRNA-125A等均可能與IBD發病相關[30-32]。因此,miRNAs有望成為預測以及治療IBD的一個全新生物標志物。
1.8 蛋白質組學
由于IBD病因復雜、臨床表現不典型,因此該病的診斷需基于臨床表現、內鏡、組織學和影像學檢查結果綜合判斷,做出排他性診斷,而目前尚無診斷的金標準。蛋白質組學的出現,使IBD的研究有了進一步的發展[33]。Meuwis等報道了4種血清蛋白(血小板聚集因子4、結合珠蛋白a2、纖維蛋白肽A和髓樣相關蛋白8)與急性期炎癥密切相關,且是高靈敏性和特異性的IBD診斷生物標志物[34]。Zhang等報道血清蛋白質組學分析在鑒別IBD與腸結核方面具有重要價值[35]。Starr等研究提示,一組由5種蛋白質組成的生物標志物在鑒別兒童IBD方面具有重要價值,進一步研究表明一組由12種蛋白質組成的生物標志物可有效區分CD和UC[36]。此外,Drobin等研究已確定了13種血清蛋白與IBD患者的細胞信號轉導、免疫代謝調節和免疫細胞激活相關[37]。
在蛋白質組學中,炎癥相關蛋白質組譜的變化在預測IBD治療的應答與預后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價值。Medina等研究發現,在54例CD患者中,乙酰化調節的17種蛋白對抗TNF-α治療的應答具有預測價值,研究同時提出4種蛋白是抗TNF治療無應答的潛在生物標志物[38]。D'Haens等根據13種蛋白質(ANG1、ANG2、CRP、SAA1、IL-7、EMMPRIN、MMP1、MMP2、MMP3、MMP9、TGFA、CEACAM1和VCAM1)的血清水平,并結合內鏡下表現提出一種名為EHI的指數用以預測CD患者的疾病緩解情況,驗證結果進一步表明,該指數可準確預測CD患者的病情緩解情況,與FC對疾病的預測價值相比差異不大[39]。Pierre等對接受IFX治療的CD患者進行長期隨訪發現,通過分析患者血清的蛋白組學變化可預測CD患者的短期以及中長期預后,這可能有助于臨床醫生根據蛋白組學評估抗TNF-α治療的應答情況及預后[40]。
1.9 腸道菌群
隨著腸道微生態學的發展及研究的深入,多項研究認為腸道菌群參與了IBD的發生、發展過程。腸道菌群也是近年來IBD研究的熱點,其可通過多種途徑誘發和影響腸道炎癥反應。因此,對腸道菌群與IBD關系的研究有望為IBD治療和疾病預測帶來新突破。
Magnusson等研究報道,在接受抗TNF-α治療的IBD患者中,臨床應答和無應答患者的腸道菌群分布明顯不同,與無應答組相比,臨床應答組在基線時有較低的生態失調指數和較高的普拉梭菌豐度;研究進一步指出,在接受IFX或ADA誘導治療期間,應答組中的普拉梭菌豐度較基線期增加[41]。本團隊研究發現,經IFX治療后CD患兒腸道合成膽鹽水解酶的細菌增多,這可能與IFX治療后結合/非結合膽汁酸水平降低及其比率升高有關;此外,IFX治療的持續應答與高豐度的甲基桿菌屬、鞘氨醇單胞菌屬、鏈球菌屬和部分代謝產物(包括L-天冬氨酸、亞油酸和L-乳酸)的水平升高相關;該研究表明,部分腸道細菌豐度和代謝產物水平可能用于預測兒童CD患者的IFX應答情況,通過菌群測序可指導兒童CD患者如何選擇生物制劑治療[42]。Aden等研究表明,通過對糞便樣本的代謝組學分析顯示,代謝物交換與接受抗TNF-α治療的IBD患者臨床緩解顯著相關[43]。一項針對抗TNF-α治療的Meta分析指出,IBD患者的糞便或結腸活檢標本微生物群中大腸桿菌和腸球菌的豐度降低,而短鏈脂肪酸產生菌的豐度增加[44]。這些研究進一步揭示,抗TNF-α治療可以顯著影響IBD患者的腸道微生物組成和腸道炎癥,根據基線時菌群組成以及治療后細菌代謝產物的變化,可區分抗TNF-α治療應答者與無應答者,并預測IBD患者接受抗TNF-α治療的效果。
2 早期克羅恩病的生物制劑治療
生物制劑在IBD誘導和維持緩解、促進腸黏膜愈合、改善患者生活質量等方面效果顯著。與傳統的“升階梯”治療模式相比,目前越來越多的研究強調在CD早期階段盡早使用生物制劑可改善CD患者的癥狀和預后。
2.1 抗TNF-α單克隆抗體
Top-Down研究是最早評估早期CD患者應用生物制劑的研究[45]。該研究持續2年共納入了18個中心,旨在評估早期聯合免疫抑制劑(IFX和硫唑嘌呤)與傳統治療(糖皮質激素或硫唑嘌呤)對早期CD患者的療效。結果顯示,早期聯合治療組第26周無激素狀態下臨床緩解率顯著高于傳統治療組(60.0% vs. 35.9%,P=0.006),第52周時聯合治療組與傳統治療組無激素狀態下臨床緩解率無差異(61.5% vs. 42.2%,P=0.278);此外,在長期隨訪中(104周),聯合治療組73.2%的患者在腸鏡檢查中未發現潰瘍,傳統治療組為30.4%(P=0.003)[45]。
Colombel等通過對SONIC研究的事后分析,對未使用過免疫抑制劑以及生物制劑的早期CD患者作了進一步的探討,結果顯示在早期CD患者中,與IFX(25%~50%)或硫唑嘌呤(10%~30%)單藥治療相比,聯合治療獲得完全緩解的人群比例更高(63%~76.5%);隨訪18個月,接受聯合治療的早期CD患者中,80%以上達到完全緩解,60%以上達到完全緩解及內鏡下黏膜愈合,因此,SONIC研究表明早期生物制劑聯合免疫抑制劑治療可使患者提早獲益并且維持中長期無激素緩解[46]。在關于ADA的CHARM研究的事后分析中,將納入CHARM研究的人群根據病程長短分為3個亞組(<2年、2~5年、≥5年),研究同樣發現,病程越短(<2年),患者治療的臨床應答率越高[47-48]。針對ADA的安全性以及有效性的EXTED研究進一步指出,早期CD患者ADA治療更有可能達到內鏡下深度緩解[46,49]。
一些回顧性與觀察性研究也進一步證實了早期使用抗TNF-α的治療可使CD患者獲益。Mandel等研究表明,早期CD患者(診斷后3年內)使用抗TNF-α治療可顯著減少住院率(P=0.016)[50]。一項來自瑞士的隊列研究指出,在CD確診后2年內使用抗TNF-α藥物干預可降低腸腔狹窄的風險(P=0.018)[51]。此外,Ma等的回顧性研究表明,CD患者早期(確診后2年內)使用抗TNF-α治療可有效降低長期腸道手術率,該研究共納入190例CD患者,長期使用抗TNF-α治療并規律隨訪,中位隨訪時間為154.4周,延遲使用抗TNF-α治療的CD患者手術率(30.7%)是早期干預患者(5.7%)的5倍(P<0.001)[52]。
2.2 抗整合素單克隆抗體
目前用于治療CD的抗整合素單克隆抗體的代表性藥物主要有維得利珠單抗(Vedolizumab,VDZ)和那他珠單抗,但那他珠單抗相關的進行性多灶性白質腦病限制了其臨床應用[53]。在針對VDZ的GEMINI 2[54]和GEMINI 3[55]的臨床試驗中,未使用過抗TNF藥物的CD患者臨床緩解率及臨床應答率更高,間接說明了病程與臨床療效的相關性,但該問題在研究中未作進一步探討[56]。在一項真實世界研究中,VDZ治療后6個月,早期CD患者(病程<2年)無激素緩解與內鏡下黏膜愈合率更高[57]。目前關于VDZ與早期CD治療的臨床研究相對較少,需要更多的研究進一步探討。
2.3 抗白介素12/23單克隆抗體
烏司奴單抗(Ustekinumab,UST)是一種全人源IgG1k單克隆抗體,可結合IL-12/23的p40亞單位,目前已批準用于CD的誘導以及維持緩解治療[58]。目前UST主要作為抗TNF-α治療失敗后的二線用藥,因此其在早期CD的應用缺乏相關的臨床研究報道。在UNITI-2臨床試驗中未接受抗TNF治療的CD患者其臨床緩解率明顯優于UNITI-1試驗中曾接收過抗TNF治療的CD患者,通過分析兩組患者的基線特征發現,UNITI-2中患者的平均病程為(8.7±8.4)年,而UNITI-1中的平均病程為(12.7±9.2)年,雖然這些病人的病程已不再屬于早期CD的范疇,但也間接說明了病程越短,接受UST治療病人的臨床緩解率越高[58]。
3 結語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基礎和臨床研究都聚焦CD的早期診療,新的診斷標志物及藥物也在不斷開發問世,但在CD早期診療方面仍然存在不足。首先,需要發現高靈敏度的CD早期診斷生物標志物,進一步探索不同組合標志物之間聯合檢測的精準性,從而確定高效、無創、廉價的CD早期篩查方式;其次,目前尚缺乏亞洲人群的易感基因分析及流行病學報道,需要更多的基礎和臨床研究,以提高我國CD患者的早期篩檢率,做到及時干預,以預防長期并發癥;最后,在CD的早期治療方面,需要普及CD相關知識,提高醫護人員診療水平,減少CD的致殘率,減輕患者的疾病以及經濟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