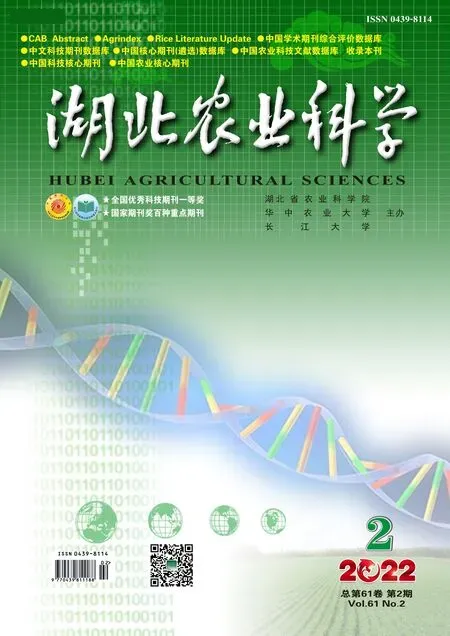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村直播課堂接受態度影響因素與模式分析
王真真
(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南京 211100)
《中國農村教育發展報告2017》數據顯示,農村小學數量占全國小學總數的85.02%,農村初中數量占全國初中總數的77.16%,鄉村教育依然是義務教育階段的主要對象。同時,農村基本公共教育依然明顯存在教學質量低、教育觀念落后、與城市教育資源差距大等問題[1]。《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中指出“優先發展農村教育事業,高度重視發展農村義務教育,推動建立以城帶鄉、整體推進、城鄉一體、均衡發展的義務教育發展機制。統籌配置城鄉師資,并向鄉村傾斜,建好建強鄉村教師隊伍”。并且明確提出“要在2035年基本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更加完善”。促進城鄉教育資源共享,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促進城鄉教育公平具有重要意義,也是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要步驟。
網絡直播課堂的含義中包括3個關鍵詞,一是以互聯網為媒介,二是同時不同地的時空特性,三是實時互動式的課堂師生關系。相較于傳統的面授課堂形式,網絡直播課堂具有其自身的特征與優勢。①突破時空限制[2]。從各地網絡直播課堂的實踐經驗中可以看出,通過網絡直播進行授課,授課教師不需要出現在教室,以互聯網和屏幕為助手,教育資源落后地區的孩子亦可以享受更高質量的教育資源。一方面,不需要支教老師深入山區,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各個教學點的學生遠距離上學。同時,對于一些昂貴的、難獲得的實驗器材、教學工具等,網絡直播課堂既避免了購買和運輸的問題,又給予了學生親眼觀看操作和參與討論的機會。②實時互動性。相較于網上慕課、網上視頻學習等網絡學習方式,直播課堂具有明顯的互動性強的優勢[3]。因為是直播式教學,老師和學生雖然所處空間不同,但所學習的知識一樣。在這樣的互動式課堂中,學生和老師更有參與感,更容易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課堂參與意愿,教學效果也更好。③資源共享性。網絡直播課堂可以成為共享教育資源的有效手段[4]。一方面,教育資源較為豐富的地方可以利用網絡直播課堂對優秀教師的教學成果進行推廣,對青年教師進行培訓等;另一方面,在促進城鄉教育公平方面,網絡直播課堂可以在保留現有教師編制的情況下,讓農村教學點與城市學生共享教育資源。
本研究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對影響農村網絡直播課堂接受態度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并提出政府與市場共建、校際合作幫扶的網絡直播課堂搭建模式,以期為鄉村教育振興提供思路和參考。
1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1 數據來源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湖北省12所小學的問卷數據,分別是紙坊第三小學、蘄春縣菩提小學、勞四小學、鄭店中心小學、東風小學、紙坊第一小學、紙坊第二小學、蘄州第一小學、蘄州第二小學、蘄州第三小學、蘄州實驗小學和蘄州第五小學,共收回有效問卷188份,填答問卷者主要為上述多所學校的在職教師、行政人員和學校負責人。在對問卷資料整理、篩選、核對以及有效問卷編碼后,利用SPSS 22.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處理與統計分析(取置信度95%)。
1.2 描述性統計
由表1可知,91.5%的樣本對網絡直播課堂持積極態度,8.5%的樣本持消極態度,說明網絡直播課堂在農村整體上是受歡迎的。雖然樣本在年齡方面分布比較平均,但是結合教齡發現,樣本教齡多分布于1~4年和15年以上,即農村教師以剛參加工作的青年教師和水平不高、年紀較大的中老年教師為主體,原因在于農村教師普遍存在“教而優則走”“教而優則仕”的情況,優質、骨干教師流失嚴重。學歷方面,絕大多數樣本為大專或本科畢業。相較于年級方面數據分布的平均性,樣本在科目方面的分布明顯不均勻,語文和數學老師明顯多于英語和其他科目,結合在調研過程中的觀察和訪問,農村教師在副科上的配置數量明顯少于語數外三大主科,一般是多個班級共用一個副科老師,甚至某些主科老師兼任副科老師,這顯示出農村學校對副科和素質培養課程的忽視。

表1 調查樣本基本情況
1.3 變量選取
因變量采取量化取值,當調查對象對網絡直播課堂呈積極態度(“是否贊同網絡直播課堂形式”一題中選擇“十分贊同”和“比較贊同”)時,取值為1;當調查對象對網絡直播課堂形式呈消極態度(同一題中選擇“不太贊同”或“反對”)時,取值為0。在結合已有研究的基礎上,選擇影響農村網絡直播課堂態度的個人因素和學校因素,共9個分變量,包括年齡、學歷、科目、年級、教齡、計算機操作熟練度、是否對網絡直播課堂有過了解或接觸、是否每間教室都配有計算機設備、是否組織培訓或開展過網絡直播課堂,并對分變量進行賦值(表2)。

表2 變量賦值情況
1.4 研究假設與χ2獨立性檢驗
本研究選擇χ2獨立性檢驗作為衡量影響因素與接受態度之間的測量工具(表3),此處選取其中最常用的Pearson Chi-Square(皮爾森卡方):

式中,χ2表示實際觀測值與理論值的偏離程度,count表示實際觀測值,ex pect ed count表示預測值。同時,常用Cramer’ sV對χ2獨立性檢驗的效應量進行測量:

式中,N是樣本數,k是類別最少的變量的水平數。同時約定小、中、大的效應量分別對應Cramer’ sV值為0.10、0.30和0.50[5]。
一般認為,當檢驗結果P<0.05時,拒絕原假設,即認為2個變量之間存在某種聯系。以年齡為例,原假設:年齡與接受態度之間沒有聯系。由表3可知,年齡與因變量之間的P=0.001<0.05,拒絕原假設,說明年齡與接受態度之間存在聯系,且Cramer’ sV值為0.352,即中度相關關系。

表3 χ2獨立性檢驗
選取P<0.05的變量,發現變量年齡、科目、年級、計算機操作熟練度、是否提前了解或接觸過網絡直播課堂以及學校是否組織開展過相關培訓6個變量與因變量接受態度存在聯系,其中年齡、科目、年級3個變量與因變量之間存在中度相關關系,其余變量與因變量之間僅有輕度相關關系。
2 結果與分析
篩取χ2檢驗中P<0.05即與因變量接受態度不相互獨立的,且Cramer’ sV>0.30即兩者的關系在中度相關及以上的變量,即年齡、科目、年級與農村直播課堂接受態度之間形成交叉關系。
2.1 年齡對農村直播課堂接受態度的影響
由表4可知,45~49歲的被調查對象中,態度消極的實際頻數為7,明顯高于3.5的期待頻數值;55~59歲這一部分選擇“不太贊同”和“反對”的有4人,也明顯高于0.9的期待值。可見,年紀大的人相較于中青年的教師表現出更加消極的態度,在授課方式的選擇上更加傳統和保守,對新事物的接受程度不如年輕教師。

表4 不同年齡對農村直播課堂接受態度情況
2.2 科目對農村直播課堂接受態度的影響
由表5可知,態度消極的樣本中,數學老師的實際頻數為16,明顯高于期待頻數7.1,且態度消極的樣本占比高達19.0%,也明顯高于其他科目,說明相較于其他科目,數學老師更傾向于現場互動和傳統的面授形式,認為網絡直播課堂不適用于數學科目的教學。

表5 不同科目對農村直播課堂接受態度情況
2.3 年級對農村直播課堂接受態度的影響
由表6可知,三年級的樣本選擇消極態度的頻數為8,明顯高于2.3的期待頻數;六年級教師中不支持或反對網絡直播課堂的樣本頻數為5,高于期待頻數3.1。相較于其他年級消極態度樣本所占的比例,三年級和六年級分別為29.6%和13.5%,遠高于其他組。在調研過程中訪談發現,三年級和六年級相較于其他年級,屬于轉折年級,三年級開始英語教學,教學形式更加正式,教學內容更加系統和復雜;六年級則處于小升初的關鍵年級。因此,教師在關鍵轉折年級更傾向于傳統的授課形式而不是網絡遠程課堂。

表6 不同年級對農村直播課堂接受態度情況
3 啟示與對策
3.1 啟示
直播課堂憑借獨有的實時互動性對于促進城鄉教育資源共享和提高農村基礎教育質量具有重要作用,調查結果顯示作為接收方的農村各學校對網絡直播課堂的進駐整體呈現出積極的態度,盡管客觀上教師配置在數量和質量上與城市學校存在較大差距,但是良好的計算機設備配備情況為直播課堂進駐農村學校提供了基礎條件。調查結果顯示,科目和年級與農村直播課堂接受態度之間呈現顯著相關的關系,因此,在直播課堂的安排上,一方面在以數學為代表的強調課堂互動的課程中減少直播課堂的安排,而在教師匱乏、不在升學考試范圍內的素質教育和興趣課堂中增加直播課堂的頻率;另一方面,在以三年級和六年級為代表的轉折性關鍵年級減少直播課堂的安排,而在一、二年級這樣升學壓力小、課程安排較松散的年級增加直播課堂入駐。同時,需要在課程安排上統一調度,讓直播課堂成為提升農村學校素質教育質量的有力助手。
盡管計算機配備為直播課堂提供了物質基礎,但教師的操作水平多限于日常的簡單操作,對計算機設備操作的有限性增加了學校對直播課堂入駐的顧慮,同時,提前了解或接觸過直播課堂的老師和參與過相關培訓的老師,對直播課堂的態度更為積極,因此,需要對教師進行有組織的培訓工作[6],不僅針對其對硬件設施的操作水平,還需提高對直播課堂的認知水平[7]。在訪談的過程中還發現一些數據無法呈現的問題,如教師愿意接受相關培訓的同時對費用表示擔憂,學校領導和教師個人傾向于政府出資;雖有少數學校和班級曾有過直播課堂的經歷,但是多以QQ視頻形式呈現,并沒有成熟規范的平臺,缺乏長效保障機制。
3.2 農村直播課堂城鄉協同模式
結合調研結果和需求方的現實條件,發現發揮直播課堂對于振興鄉村教育的獨特優勢,促進直播課堂進駐農村課堂,需要政府起到主導組織作用的同時,引入市場力量搭建專業直播課堂平臺,為受課方提供穩定的授課資源,統一調度,建立長效保障機制。基于上述結論,結合調研過程中訪談和觀察所得,本研究提出政府與市場共建、校際合作幫扶的網絡直播課堂搭建模式(圖1)。

圖1 直播課堂搭建模式
首先,政府應處于主導地位,由政府搭建連接城鄉學校之間的橋梁。相對于“一對多”“一對一”的課堂間關系具有更高的互動性和參與感,因此,建議由政府組織城鄉學校建立“一對一”幫扶關系。教育部門為每個師資力量落后的學校搭配一個師資力量相對雄厚的學校作為合作伙伴,共享教育資源。此外,基礎設施的配備,如多媒體、錄播室、攝影攝像設備、播放設備等,需要政府的財政支持[8]。對于授課方的教師和校方也要給予一定的補助。同時,由當地教育部門組織鄉村教師的集中培訓工作并承擔培訓費用。
其次,建議搭建穩定的直播平臺。直播平臺的建設需要引入市場的技術和運營經驗,如通過招標等政社合作形式,充分利用市場的技術優勢和已有直播平臺的運作經驗[9]。據了解,目前市場上的教學直播平臺包括騰訊會議、云朵課堂、伯索云課堂、YY教育等,目前多數教學直播課堂還處于剛剛投入使用的階段,用戶少且不成規模。有關部門可以與市場相關企業展開官方合作,將直播課堂建設的理念與現有直播平臺的優化相結合,共同建設穩定有效的官方教育直播平臺,為城鄉教育資源的直播共享提供科學平臺。
同時,課程的設置需要統一調度,以興趣課、實驗課為主。地方教育部門需要協調授課方和受課方現有的課程設置,在不影響雙方課程進度的情況下,一周開展1~2次直播課堂,課堂形式采用“一對一”形式,一位授課教師面對一個教室內的學生,課堂內容要包含課堂互動。如學校間建立官方資源共享幫扶關系后,授課方建設專門的直播教室或可移動的直播設備,每周1~2次為受課方提供遠程直播課程,主要以實驗課、興趣課為主要內容,老師只需要上課時去專門的直播教室即可,不影響正常的教學進度;而受課方通過教室內的多媒體設備接受授課內容并與教師進行互動,考慮到孩子的自律性和主動性問題,授課方教師可以在教室內維護秩序并幫助課前準備[10]。
4 小結
教育信息化是共享優質資源的最好載體,是推動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成本較低、便捷高效的途徑[11]。本研究通過對樣本的數據分析,發現變量年齡、科目、年級、計算機操作熟練度、是否提前了解或接觸過網絡直播課堂以及學校是否組織開展過相關培訓6個變量與因變量接受態度存在聯系,其中,教師年齡、科目和年級對網絡直播課堂的接受態度有較大影響。隨著后疫情時代的來臨,在線信息共享形式深入社會各行各業,直播課堂在促進城鄉教學資源共享的同時保障了實時互動性,為提高農村教育質量水平和振興鄉村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直播課堂政府主導、市場參與的城鄉協同模式有利于將城鄉教學資源連為一體,有助于實現農村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方式,對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和鄉村振興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