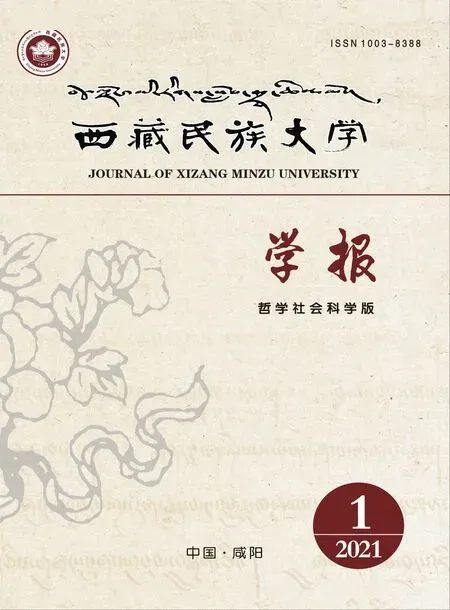傳播媒介與少數民族文化嬗變的歷史映射
——從媒介環境學視角探討蒙古族個案
李 亙,許加彪
(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陜西西安710063)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少數民族的文化嬗變只是中華民族宏大敘事的一個子部分。正如媒介域理論所揭示的,媒介使用與少數民族社會文化型態之間存在蝴蝶效應般的場域連鎖互動。法國著名傳播學者德布雷認為,媒介域指的是一個信息和人的傳遞和運輸環境,包括與其相對應的知識加工方法和擴散方法。[1](P261)媒介域作為信息傳遞的技術、社會聯系的機理、社會秩序的確立三者之間互動的場域,勾連了媒介使用和社會文化之間的內在邏輯。歷史上,民族間的傳播媒介大致相同,內蒙古自治區蒙古族的媒介使用,大致經歷了口語、文字、書籍、報紙、廣播、電視、網絡等發展型態,從媒介環境學的視角看,這些媒介催生和建構了不同的社會文化。
一、媒介環境學視角下媒介變遷和社會文化的建構
從宏大敘事的理論出發,社會文化發展的驅動可能是環境、政治、經濟、軍事、意識形態等因素,傳播學經驗-功能學派鮮有人關注媒介在其中發揮的關鍵作用。但傳播學媒介環境學派從自己的理論視角出發,建構了媒介技術與社會文化之間隱秘的勾連邏輯,從而彰顯了媒介技術的決定性力量。
美國歷史學家劉易斯·芒福德對技術所起的作用進行了人文主義的哲學反思。芒福德認為機械或機器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指具體的機械工具,二是指該機械工具運行后內生的觀念體系和制度體系。在使用印刷技術和紙張的過程中,思想失去了自由流動、四維時空以及自然的特性,帶上了抽象、絕對、程式化的特點。[2](P125)顯然,一項具體的技術設備不僅僅是生產力的體現,還帶來了人們思維和觀念的變遷。印刷機作為始生代技術時期的根本性發明之一,影響深遠。
加拿大學者伊尼斯在《帝國與傳播》《媒介的偏向》中闡釋了媒介和帝國之間微妙的長期效果,帝國空間上的擴張和時間上的維系形成了一種張力,媒介能夠回應和折射這種張力。媒介屬性具有兩大維度—空間維度和時間維度,這兩種媒介屬性對應了兩種人體器官—眼和耳,目之所及是空間,耳之所聞是時間。伊尼斯說,一種媒介經過長期使用之后,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它傳播的知識的特性,一種新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文明的產生。[3](P28)楔形文字、象形文字、字母表、羊皮紙、莎草紙、印刷機等與各個帝國形成了邏輯上的關聯。
傳播學著名學者麥克盧漢提出了“媒介即訊息”的神諭式觀點,把媒介視為人體的延伸,影響到人體的感知比率和感知模式。麥克盧漢認為,谷登堡革命所確定的印刷邏輯追求線條性、準確性和同一性,粉碎了以血親為形式的家族制,催生了民族主義、工業主義、普及教育等。麥克盧漢說,任何媒介對個人和社會的任何影響都介于產生了一種新的尺度;任何一種延伸,都是在事務中引進了一種新的尺度。[4](P33)媒介引發“人的尺度”的思想是媒介作用于社會制度的隱形機制。
文化學者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提出了“媒介即隱喻”的觀點,認為麥克盧漢的“媒介即訊息”會讓人把信息和隱喻混淆。波茲曼說,媒介更像是一種隱喻,用一種隱蔽但有力的暗示來定義現實世界,媒介—隱喻的關系為我們將這個世界進行著分類、排序、構建、放大、縮小、著色,并證明一切存在的理由。[5](P11)媒介即隱喻,表明媒介不是明言社會的信息,而是暗示社會的表征。
傳播學者梅羅維茨認為,電子媒介因其穿透時空的信息傳播力,改變了固有的社會場景區隔或社會情境設置,因此引發了人們社會行為的相應調整與社會運行的邏輯。梅羅維茨說,電視社會意義的重點不在于電視播放什么,而是其作為一種共享場所的存在。[6](P84)在梅羅維茨筆下,場景成為信息系統,媒介成為文化環境。
傳播學者保羅·萊文森作為波茲曼的弟子,著述頗豐,被稱作“數字時代的麥克盧漢”,認為媒介演化遵循“人性化趨勢”(Anthropotropic),即技術的發展會越來越人性化。萊文森說,媒介的存活概率與它和前技術時代信息傳播方式的近似度呈直接正相關,所有的媒介都朝著與現實世界漸趨同步的方向進化。[7](P118)媒介技術的“人性化趨勢”,說明技術是為人服務的,而不是技術主宰了人。
伊尼斯和麥克盧漢以一種獨到的方式從理論上歸納了媒體對社會的長效影響,強調了主流媒體類型和時空轉型之間的密切聯系,這種影響取決于媒介的形式以及可再生產性。[8](P22)總的來說,媒介環境學有三個深層次的理論假設:傳播媒介不是中性的、透明的和無價值標準的渠道;每一種媒介獨特的物質特性和符號特征都帶有一套偏向;傳播技術促成的各種心理的或感覺的、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結果,往往和傳播技術固有的偏向有關。[9](P53-55)
二、口語媒介:游牧生活中口耳相傳的人際傳播
我國的蒙古族源于額爾古納河東岸一帶,號稱“馬背上的民族”,最初是蒙古地區東北部的蒙兀室韋部落。傳統蒙古族居無定所,有別于漢族的安土重遷,這種游牧生活需要互助互愛,共同對抗不確定性的風險,形成了草原上的牧民熱情好客的豪爽性格。這種地域性的“部落”社交關系網,特別是集體的儀式活動,增強了游牧個體之間的集體認同感,有力維護了游牧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在蒙古各部落統一之前,蒙古雖有自己的語言,但并沒有書面的文字,信息傳播只有口耳相傳的形式,留存憑借人腦記憶或刻木為記。蒙古語屬于阿爾泰語的蒙古語族,分為內蒙古、衛拉特和巴爾虎不里亞特三種方言。
口語傳播形式一般不需借助其他輔助性媒介,易于人際間的信息傳遞和傳情達意,反饋迅速。但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口語傳播的距離和范圍有限,且不易保存。牧區大體上地廣人稀,周圍分散的牧戶多為熟人,其生產生活的信息傳播方式主要依賴于口耳相傳。與口傳文化發達相一致,蒙古族長調民歌、馬頭琴、呼麥成為蒙古族最典型的表現形式,都是借助于人的聽覺器官而產生的文化藝術瑰寶。同時,蒙古族創造了以口頭傳播為主要形式的民族民間文學和民間故事。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成為中國三大英雄史詩之一,總量10萬行左右,2006年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大約在13世紀,《江格爾》誕生于蒙古族聚居地,作為說唱敘事詩在衛拉特蒙古人中流傳。烏力格爾又叫“蒙古族琴書”,是蒙古族傳統民間說唱藝術形式之一,一人一琴說一故事,既可在蒙古包里,也可在草原馬旁,也可在劇場舞臺,題材來源廣泛。這些藝術演唱者不僅傳播民族的歷史知識和文化知識,也傳遞異鄉的社會生活,更是對現實生活發表隱形的權威意見,相當于一個流動的信息播報臺和生活指導站。牧民在閱聽中既享受到藝術熏陶,給枯燥的日常生活以慰藉,也通過情感共鳴獲得身份認同和社會認同。
口語傳播在蒙古族早期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不僅是維系牧戶部落群體的傳播紐帶,更是傳承歷史文明的重要途徑。游牧民族通過數代人的口耳相傳,如獨特的民族儀式、風俗習慣、居住風格、藝術風格等,逐漸凝結出集體記憶,進一步塑造和反哺了民族個性。口語傳播的作為傳播歷史長河中的基礎形態,是一種雙向的交談環境,信息沿社交關系網從一個人橫向傳遞給另一個人,而不是由一個非人的中心源縱向傳播。[10](P10)口語傳播的樣式與游牧生活的型態天然地糅合在一起,牧民草原社會有別于中原同心圓結構的鄉土社會,更像是一張縱橫交織的網狀結構,行走四方的江格爾齊如同網上的珠結,在他們的吟唱聲中,駿馬飛馳,肉香酒烈,養育了牧民豪爽的性格,也把一個個牧民編織成社會的一員。
在前現代社會,牧區時常可見牧民策馬急馳專程傳遞信息的情形,實際上就是利用人際傳播的功能。為了保證戰爭前沿與指揮中樞之間的快速聯絡,成吉思汗組建了號稱“箭速傳騎”的通信兵,建設了很多驛站。
三、文字媒介:傳統社會中從手抄到印刷的信息分層
13世紀初,以成吉思汗為首的蒙古部統一了蒙古各部后,建立了統一的蒙古貴族政權。公元1260年,忽必烈任大汗后,將統治中心由漠北的和林遷至燕京(后稱大都)。成吉思汗執政時期,蒙古人就借用了回鶻文字,成吉思汗命令畏兀兒人塔塔統阿以畏兀兒字書國言,這就是畏兀兒蒙古文,也叫回鶻蒙古文,蒙古族的文字書寫系統產生了。中國的蒙古族有兩種蒙古文字系統,內蒙古自治區、黑龍江等省的蒙古族使用13世紀創制的“胡德木文”,新疆的蒙古族則通用17世紀衛拉特高僧咱雅班第達創制的“托忒文”。
文字的神圣性,以及閱讀和書寫的技術門檻,造成了社會上對民眾表達和閱讀的區隔和分層。回鶻蒙古文很快普及,每一位蒙古貴族都力圖成為一個有知識的人,擁有私人的筆帖赤。[11](P13)在書面語言形成后,一些歷史著作悄然問世。如《蒙古秘史》(作者佚失)原書用回鶻蒙古文所著,記述了蒙古民族五百多年的演變史,成為蒙古族三大歷史著作之一,于1989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了世界經典名著。
因為有了書面文字,信息保存的時間維度有了革命性的變化,社會運行的語法規則變了。成吉思汗下令根據習慣法編成《大扎撒》,于是,蒙古法律體系從習慣法變為成文法,開啟了蒙古民族依法斷案的先河。古代著名的書面文獻《成吉思汗石銘文》是在石頭上用手抄體線條刻寫出來的。《飲膳正要》是元忽思慧于1330年用漢語撰成,體現出鮮明的元代蒙古族食養文化特色。
對于蒙古族來說,書的外延既包括印刷本,也包括手抄本。18世紀除了印刷多卷佛教經文外,還印刷出版了二百多種蒙古文書籍,既有北京印書館,還有察哈爾等寺院辦的印刷機構。雖然蒙古人掌握了印刷技術,但手抄書籍仍占據重要位置,直到20世紀20年代,手抄書籍被活字印刷所替代。[11](P99-109)經歷了7個世紀的蒙古書面語終于被新的書寫形式所取代。
內蒙古自治區的蒙古族生活在平均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原地區,以荒漠草原為主,牧場載畜能力較低,只能分散放牧,隨四季變化而放牧。蒙古族雖有文字,但解放前95%的人不識字,識字的人員主要是在蒙古族上層和富裕家庭。有學者考證,內蒙古卓索圖盟喀喇沁右旗札薩克郡王貢桑諾爾布創辦的《星期公報》是內蒙古最早的報紙。[12](P99-100)1905年,內蒙古昭烏達盟喀喇沁右旗王府創辦蒙漢文合璧的《嬰報》,這是我國境內第一張使用少數民族文字出版的報紙。1912年底,由內蒙古喀拉沁旗的巴達爾胡倡導在北京創辦了《蒙文大同報》,主旨為宣揚“五族共和”“五族大同”,即中華民族團結統一,具有十分鮮明的進步色彩。由蒙藏事務局出版發行的《蒙文白話報》1913年1月在北京創刊,文字通俗易懂,內容具有較強的新聞性。1925年5月20日,由北京蒙藏學校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蒙古黨支部主辦了《蒙古農民》,是我國第一種使用少數民族文字的馬列主義刊物,1926年被迫停刊。有學者統計,民國時期(1912-1949),內蒙古共創辦地方刊物259種,其中漢文刊物(包括蒙漢合鐾者)215種;共創辦地方報紙145種,其中漢文報紙(包括蒙漢合璧者)115種。[13]
蒙古文出現后,蒙古族的信息保存在時間維度上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手抄本書籍成為歷史深處的集體記憶,既有利于身份認同,但也造成了文化程度的社會區隔。再隨著印刷術的普及,報紙因其時效性成為社會動員的主要工具。內蒙古自治區的蒙古族感受到了來自媒介技術的巨大力量。
四、電子媒介:現代社會中情景融合的大眾娛樂
全自治區在解放前,旗縣沒有電話,只有王爺府有電報機。解放后普及了民族文化教育。1950年全區蒙古族人口為70多萬人,從事畜牧生產約占65%。在20世紀50年代實現了旗縣、蘇木(鄉鎮)有電話,并且籌辦了蒙語報紙和廣播電臺,20世紀60年代實現了嘎查(行政村)安裝電話。在此期間,全自治區實施了牧民定居、集體生產,牧場流動范圍縮小。隨著草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落實,牧區草場劃到牧戶,游牧范圍進一步縮小。
廣播設備價格低廉,收聽方便,憑借自身的無線電技術裹挾著打破空間維度的力量不期而至,打破了既有的傳播格局。廣播更因其便利性和伴侶性,出現后迅速獲得牧民的采納。內蒙古西部牧區相對地廣人稀,各家居住相對分散,無法實現村落社區的“大喇叭”集體性廣播,自備自用的個體化廣播較為通用。在內蒙古東部地區卻是另一番景象,該區域的牧民逐漸演變成“半牧半耕”的生產生活形態,出現了“大喇叭”的集體性廣播,能夠進行固定時段的統一收聽。
在民族語廣播發展史上,1950年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開辦了少數民族語言廣播節目,每天用蒙語和藏語播音一小時。1971年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重新調整為蒙、藏、維、哈、朝等五種民族語言。
全國各民族地區也在原有的基礎上紛紛建立了省(區)、地、縣三級廣播電臺(站),內蒙古自治區也是如此。1950年11月1日,內蒙古電臺蒙語廣播電臺開始播音,每天播音65分鐘,播出的節目也是簡單的翻譯稿件。20世紀60年代后,蒙語臺逐漸增加播出時長,內容由新聞擴展到藝術、翻譯的廣播劇等。為使牧區人民能夠收聽廣播,增設36個廣播差轉臺。2000年后,在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的呼應下,國家又推行“西新工程”,即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廣播電視覆蓋工程。受此惠及,蒙古語廣播每天播出時間延長至18小時15分鐘(包括轉播中央臺蒙語節目120分鐘)。2018年5月18日,內蒙古廣播電視臺蒙語廣播首次實現了24小時播出。截止到2017年,廣播在內蒙古自治區的覆蓋率達到了99.24%。[14](P399)
廣播成為盒形的“江格爾齊”。內蒙古廣播電視臺開播的《少兒天地》被譽為“蒙古族少年兒童的精神家園”,《農牧民之友》是一檔專門服務于基層廣大農牧民的專題類品牌欄目,《新聞透視》則是全國蒙古語廣播設立的第一檔評論性節目。蒙古語廣播不僅為牧區的蒙古族群眾提供信息傳遞的渠道,也是文娛活動的平臺。正如一首歌謠唱到:“蒙古包里的常客,炒米不吃茶不喝,放羊接羔吩咐到,又說新聞又唱歌。”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政府還組織了一些牧民集體的收聽行為,如收聽重大慶祝活動等。所以,廣播既有人際傳播的成分,也有組織傳播的成分,實現了社會情境的融合。
電視的出現昭示著圖像時代的降臨,電視作為訴諸于受眾聽覺與視覺雙重感官的傳播媒介,表情和特寫成為其關鍵的表達手段。內蒙古自治區的蒙古語電視節目于1976年10月2日開始播出,電視信號范圍只能覆蓋呼和浩特市中心;1979年5月1日采用PAL-D制式播出彩色電視節目;1983年蒙古語電視節目增加到每周播出兩次,每次3小時左右。[15]1997年1月1日蒙語衛星頻道正式開通,標志著蒙古語電視頻道的一個巨大發展。
電視機在普通牧戶普及則是20世紀90年代的事情。因為電網并不能完全覆蓋到偏遠地區的牧戶家中,該群體消費電視的前提條件是需要購置“風力發電機”等電氣設備。顯而易見,無論是購買電視,還是添置發電設備都意味著該戶牧民在當地的經濟條件居于上游水平。因此,電視不單是媒介技術的消費品,更是某種身份和財富的象征。早年間偏遠牧區的牧戶接受教育的方式、質量與城鎮人口存在一定差距,因而牧民的文化程度整體偏低。但電視因其無門檻的收視要求,很快成為一個全民狂歡的產品。
電視媒介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牧民的業余生活,電視劇的熱播、娛樂節目的追捧,一下子把外面的世界繪聲繪色地展現在自己的面前,即增長了知識,也獲得了愉悅。內蒙古蒙古語衛視曾經播出一檔名為《男兒三藝》的節目,該節目詳細記錄了內蒙古各地區蒙古族的那達慕盛況。特別是電視劇的播放,外面世界的生活方式潛移默化到自己的思維和現實中。例如,《開封城》《克拉戀人》《和媽媽一起談戀愛》等一系列網絡熱播劇的推出,雖受到蒙古語譯制工作的影響,播出時間略顯滯后,但仍為草原腹地的牧民帶來不一樣的觀感。熱播電視劇往往包含大量的流行文化和現代都市生活的場景。于是,牧民向往并積極追求外面世界的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也逐漸采納了現代生活設備的標志。在電視的隱性召喚下,牧民的生活型態逐漸向城鎮化過渡。電子媒介以無遠弗屆的媒介屬性悄悄改變了社會的型態,改寫了信息的疆界,也改寫了牧民的游牧生活。特別隨著摩托車等個性化交通工具的使用,牧民生活逐漸從游牧的流動性過渡到定居點的固定性,牧區的社會治理逐漸實現了科層化。
五、數字媒介:后現代社會中重回部落的虛擬世界
當下,正處于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介時代,即美國學者馬克·波斯特所提出的“第二媒介時代”,這一時代的核心是雙向交流和去中心化。[16](P22-23)保羅·萊文森進一步將互聯網出現之后的媒介進行更為細致的劃分,并提出:新新媒介使其用戶對新媒介有一定的控制權,用戶可以決定何時何地去獲取新媒介提供的文本、音頻和視聽。[17](P7)
近年來,新興網絡媒介開始涌入牧民的生活。截止到2017年,根據《2018內蒙古統計年鑒》農村牧區常住家庭平均每百戶耐用消費品年末擁有量一項顯示:移動電話平均236.92部/百戶,計算機平均24.20臺/百戶,其中接入互聯網的有16.78臺。[14](P213)由此可見,手機的使用在牧區已十分廣泛,絕大多數的牧民都能擁有一部智能手機。在使用過程中,牧民往往更鐘情于手機中的“微信”功能,用微信的語音功能聯系親友,而極少使用文字。這樣一個人際交往狀態,恰如重回部落時的情況,以口耳相傳作為主要的傳播方式。
相較過去的傳統媒體,數字新媒介在牧區采納的頻率越來越高,牧民不僅僅是單一的接受者,還有可能成為信息的生產者。“95后”蒙古族姑娘烏音嘎大學畢業后毅然返鄉,在短視頻平臺推出“草原印象錫林郭勒”,用手機、三腳架、加上簡單樸實的話語,展示草原的風土人情。其粉絲量累計達100萬,原創視頻超過400條,被播放和傳播上億次,部分視頻還在YouTube上播放。中國原生態草原景象也被傳播到世界更多地方。此外,有經濟能力的牧戶在自家草場上安裝監控攝像頭,用智能手機聯網隨時觀看監控畫面,并輔以遙控無人機監控自家的草場上的牲畜。部分牧戶家庭已實現寬帶入戶,一部智能手機加上家中的無線網絡可以享受媒介技術帶來的便利。譬如,牧民們使用智能手機觀看“快手”或“抖音”直播較為普遍,他們當中的大部分更愿意關注本地區或者附近村落的直播,所觀看的內容多以歌舞、搞笑為主。
牧民們逐漸習慣并接受互聯互通的網絡虛擬世界,與牧區之外的聯系日趨頻繁。網絡媒體的應用使得牧民獲取信息的速度和途徑等方面與城鎮人口相比差距在逐步縮小,但在普及率與城鎮地區仍存在較大差距。牧民使用互聯網更多的是將現實中的社交圈直接平移上來,以此滿足信息交流的實際需求。而較少開展匿名交友、聊天等行為。通常每個嘎查都會有村民微信群,如:牲畜交易群、獸醫群、日用品群、銀飾群、看病群等。其中,尤以牲畜交易群最具典型性。這是一種由本村的向導建立群,之后在群中向大家發布牛羊的供求信息,牧民如有出欄的牛羊便會及時響應,進而由向導帶領買主前往牧民家完成實地交易。
隨著牧民生活方式從游牧變為定居,再城鎮化,再到城市化,與這些生活方式變遷相對應的是媒介技術也相應地發生了變遷,或者說,媒介技術恰是牧民生活方式變遷的幕后推手。在數字媒介對于牧民生活的作用力充分展現后,牧民的自我認知和社會認同將會重構。
六、新時代少數民族信息傳播的建設策略
身處媒介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或后現代社會中,任何人都無法回避媒介變遷而導致的諸多問題。2019年7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赤峰博物館會見《格薩(斯)爾》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并說:“56個民族不斷地交流、交融,形成了多元文化的中華民族。我們是一個歷史悠久、文明沒有斷流的民族。”目前,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仍然欠佳,其獨特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形成了有關社會發展的語境。蒙古族不可避免地要面對媒介與社會發展這一問題,媒介變遷催生出牧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的變化。媒介變遷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只有抓住機遇,打造具有自己特色的少數民族傳播機制和體系,達到文化傳承、民族特色與國家認同的有機統一。
在新時代的當下,應該以縣級融媒體為基礎構筑立體的基層傳播信息網,大力培養從事數字時代少數民族工作專業人員,充分發揮大數據、智能化、數字化的信息技術革命技術,多層級協同創新,在民族化、區域化、國家化、全球化中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特色道路。
媒介技術既為社會的變遷開道,也為社會的發展開拓豐富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