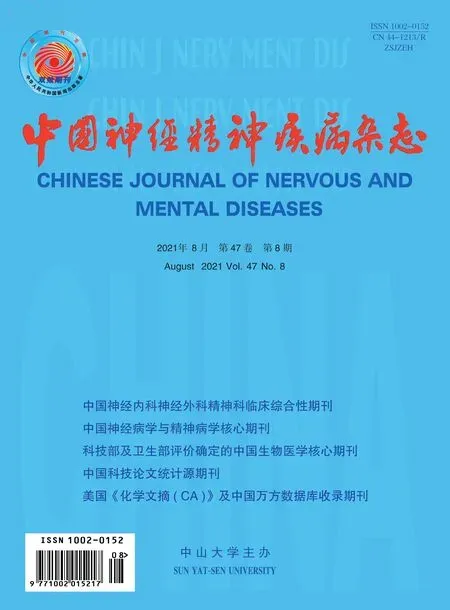呈典型雙峰腦炎表型的單純皰疹病毒腦炎繼發自身免疫性腦炎
高煜 王向波 閆鶴立 馬紅梅
單純皰疹病毒腦炎 (herpes simplex virus encephalitis,HSE)是病毒性腦炎中最常見的類型,超過 90%由單純皰疹病毒 1型 (herpes simplex virus type 1,HSV-1)感染引起。即使充分抗病毒治療,仍有患者緩解期臨床癥狀再度惡化,其中部分患者的癥狀惡化是由于病毒感染觸發免疫反應,繼發自身免疫性腦炎(autoimmune encephalitis,AE)所致[1-3],臨床上表現出“發病-緩解-再發”的雙相病程。成人HSE繼發AE的病例組報告較少,現總結分析我院7例HSE繼發AE的臨床資料,提高認識,分享診治經驗。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收集2017年3月至2020年9月北京豐臺右安門醫院連續收治的HSE繼發AE患者臨床資料。回顧性分析HSE和AE兩病程階段臨床表現、腦脊液檢查、AE相關抗體檢測、影像學表現,治療及預后。HSE的確診依據為腦脊液 (cerebrospinal fluid,CSF)二代基因測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檢出HSV基因序列,或CSF HSV-IgM陽性,或HSV-IgG陽性且滴度進行性升高。AE的診斷符合《中國自身免疫性腦炎診治專家共識》的 AE確診標準[4],腦脊液、血清AE相關抗體陽性。
1.2 抗體檢測 AE相關抗體檢測包括: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體(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NMDAR)抗體、抗γ-氨基丁酸A/B受體(γ-aminobutyric acid-A/B receptor,GABAA/BR)抗體、抗 α-氨基-3-羥基-5-甲基-4-異惡唑丙酸受體(α-amino-3-hydroxy-5-methyl-4-isoxazole-propionic acid receptor,AMPAR)抗體、抗富含亮氨酸膠質瘤失活1 蛋白 (leucine-rich glioma inactivated 1,LGI1)抗體、接觸蛋白相關蛋白-2(contactin-associated protein-like 2,CASPR-2)抗體。中樞神經系統脫鞘病相關抗體檢測包括:水通道蛋白-4(aquaporin-4,AQP4)抗體、髓鞘堿性蛋白(myelin basic protein,MBP)抗體、髓鞘少突膠質細胞糖蛋白(myelin oligodendrocyte glycoprotein,MOG)抗體。
1.3 治療與隨訪 治療包括阿昔洛韋抗病毒治療,糖皮質激素、靜注人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lin,IVIG)一線免疫治療,硫唑嘌呤長程免疫抑制治療,抗癲癇、精神癥狀的對癥治療及支持治療等。通過門診及電話隨訪了解病情轉歸,中位隨訪時間為5(范圍3~8)個月。采用Rankin量表(modified Rankin scale,mRS)評價預后,mRS≤2分為預后良好,≥3分為預后不良。
1.4 統計學方法 本研究為描述性研究,計量資料以中位數(范圍)表示,計數資料以例數或百分比表示。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共納入7例患者,男5例,女2例,中位發病年齡27(16~45)歲。7例均未發現AE相關腫瘤。
2.2 臨床癥狀與病程 7例均急性起病,臨床過程均呈現典型的“雙峰腦炎”表型,第一峰期為HSE期,第二峰期為AE期。①HSE期癥狀:發熱5例,頭痛4例,癲癇發作3例(強直-陣攣性發作),意識障礙3例(嗜睡),認知功能障礙2例,記憶力減退1例,視幻覺1例,語言障礙1例。②AE期癥狀:精神行為異常5例(躁動、胡言亂語、行為異常),認知功能障礙3例,癲癇發作3例(強直-陣攣發作2例,失神發作1例),記憶力減退2例,意識障礙1例(昏睡),語言障礙1例,肢體運動障礙1例。③HSE期與AE期間隔時間為27(18~55)d(表 1)。

表1 7例患者一般資料、臨床表現、病程、治療及預后
2.3 腦脊液檢查與抗體檢測 ①HSE期:7例腦脊液白細胞均升高[(29~152)個/mm3,正常值≤8 個/mm3],5 例蛋白升高[(52~105)mg/dL,正常值 8~43 mg/dL)]。3例腦脊液NGS檢出HSV-1基因序列,4例腦脊液HSV-IgM陽性。7例AE相關抗體均陰性。②AE 期:4例腦脊液白細胞升高[(12~34)個/mm3,正常值≤8個/mm3],1例蛋白升高(96 mg/dL,正常值8~43 mg/dL)。7例均行AE抗體檢測,腦脊液抗NMDAR抗體均陽性,其中4例同時血清抗NMDAR抗體陽性;1例合并腦脊液抗GABABR抗體陽性。4例行中樞神經系統脫鞘病相關抗體檢測,2例腦脊液MOG抗體陽性,其中1例同時血清MOG抗體陽性(表2)。
2.4 影像學檢查結果 ①HSE期:6例MRI發現異常信號,分布于顳葉6例,島葉1例,海馬1例,額葉2例;1例未見腦實質異常信號。②AE期:3例出現新發病灶,分布于基底節區、丘腦、腦室旁、胼胝體、額葉皮質、頂葉皮質(圖1),其中2例行增強掃描1例病灶強化;4例未見新發病灶(表2)。

圖1 單純皰疹病毒腦炎繼發自身免疫性腦炎患者的頭顱MRI A、B.例1 HSE期頭顱MRI可見左側顳葉內側病灶,FLAIR、DWI高信號。C~F.例1 AE期頭顱MRI可見基底節區、胼胝體、腦室旁、頂葉新發病灶,病灶部分強化。G.例3HSE頭顱MRI未見腦實質病灶。H.例3 AE期頭顱MRI可見左側額葉、顳葉皮層異常信號。

表2 7例患者兩個峰期影像學、腦脊液檢查及抗體檢測結果的比較
2.5 治療與轉歸 HSE期7例患者均接受了足量足療程阿昔洛韋抗病毒治療,1例聯合靜脈注射用免疫球蛋白。AE期6例接受糖皮質激素治療聯合IVIG,1例僅接受IVIG,1例序貫硫唑嘌呤長程免疫抑制治療。隨訪3~8個月7例患者均預后良好,7例AE期癥狀均較前緩解,1例遺留HSE期出現的記憶力減退,1例遺留HSE期出現的認知功能障礙(表1)。隨訪期復查MRI發現 AE期新出現的病灶消退,1例腦脊液抗NMDAR抗體在隨訪期持續陽性。
3 討論
始于中樞神經系統的感染,特別是病毒感染可以誘發AE。PRüSS等[5]證實30%的HSE患者病程中抗NMDAR抗體由陰性轉為陽性。ARMANGUE等[3]研究發現HSE發病后3個月內繼發AE的發生率為27%,其中64%為抗NMDAR腦炎。HSE繼發AE機制的研究多基于HSE繼發抗NMDAR腦炎。首先提出的假說是分子擬態,即HSV的病毒蛋白序列激發免疫反應,產生的抗體錯誤地與NMDAR上抗原決定簇發生反應。但目前尚未發現HSV與NMDAR有相同結構的抗原決定簇。隨后的研究發現不存在HSE與抗NMDAR腦炎之間的固定對應關系,其他類型病毒性腦炎也可繼發抗NMDAR腦炎[6-7],HSE可以繼發其他抗體類型的AE[3,8-10],故認為HSE繼發AE不是分子擬態的結果。目前認同度較高的機制是HSV易侵犯的部位與NMDAR高表達區域有一定重疊,病毒感染破壞邊緣系統等結構,導致NMDAR抗原決定簇暴露與修飾,成為自身免疫反應的靶點,啟動免疫應答。另一種可能的機制是HSV感染后T細胞、B細胞激活,分泌大量炎性細胞因子,透過血腦屏障引起中樞神經系統的免疫反應[11]。
HSE繼發AE多呈典型的雙相病程,即在HSE緩解過程中,距HSE癥狀首發2~16周出現AE癥狀[3]。本組病例均呈現典型的“雙峰腦炎”表型,病程的第一峰期為HSV侵犯顳葉、額葉和邊緣系統引起HSE,第二峰期為繼發的AE,AE相關抗體是該期的致病因子。AE期突出表現為新的或復發的神經系統癥狀,成年患者以精神行為異常、認知功能障礙最常見,癲癇發作次之,癥狀總體較經典AE輕[3]。與以往報告一致,本組AE期精神行為異常發生率71.4%,認知功能障礙、癲癇發作發生率均為42.9%。例7在AE期再發癲癇,發作形式由HSE期的強直-陣攣發作轉變為失神發作,提示恢復期癲癇發作形式的改變也提示繼發AE的可能。其他癥狀包括語言、運動障礙及記憶力減退,未見經典抗NMDAR腦炎常見的自主神經功能紊亂和中樞性通氣不足。
AE期腦脊液白細胞數、蛋白定量較HSE期下降,降至正常或輕度升高,腦脊液HSV基因測序、HSV-IgM轉為陰性[1,3],本組病例呈現相同趨勢,提示炎癥反應消退。AE期腦脊液顯著變化為AE相關抗體轉為陽性。目前觀察到最多的是抗NMDAR抗體陽性,本組NMDAR抗體陽性率100%,可能的原因是與其他受體或通道相比,NMDAR更為豐富。抗NMDAR抗體在HSE后1~4周開始合成[2]。動態觀察病例7發現抗NMDAR抗體轉為陽性發生于AE期癥狀出現之前,推測這種情況是因為免疫應答啟動數天,抗體到達足夠水平才會表現出相應癥狀。故HSE恢復期動態觀察AE抗體是必要的,以便及時發現繼發AE,指導后續治療。越來越多的病例研究發現AE期可合并多種神經元表面或突觸蛋白抗體陽性,屬于多重抗體陽性AE。該現象總體發生率低,機制不明,疊加的抗體可導致臨床表現的疊加或者變異[3,8,12]。例2 AE期腦脊液抗NMDAR抗體、抗GABABR抗體均陽性,提示這兩種類型AE共存,但患者只表現精神行為異常,無嚴重且難治的癲癇發作,不同于經典抗GABABR腦炎。抗NMDAR腦炎可合并MOG抗體陽性,其發生機制與少突膠質細胞膜表面有NMDAR有關,MOG抗體出現可能是繼發的免疫反應,也可能是兩者有共同免疫途徑異常[13]。這類病例可兼具抗NMDAR腦炎和中樞神經系統脫髓鞘病的臨床及影像特點[13-14]。例3、例5合并MOG抗體陽性,提示AE合并MOG抗體病,兼具兩者臨床特點,因為合并MOG抗體時預后可能更差,需要更積極的免疫治療[15],建議將MOG抗體檢查擴展到繼發AE患者中。此外,例3隨訪過程中發現雖癥狀緩解,但抗NMDAR抗體持續陽性,為預防復發經驗性給予長程免疫治療。抗體的持續存在是否為復發的預測因素,治療方案是否需要因此做出調整,有待進一步研究。
既往研究報告AE期MRI與HSE期相比,多無明顯變化,新發病灶少見[16]。但例1、例3、例5在AE期均出現新發病灶,分布于基底節、腦室旁、丘腦、胼胝體、額頂葉皮質,提示免疫反應發生于更廣范圍,而不局限于病毒直接侵犯的部位。例3新發皮質病變,符合MOG抗體陽性單側皮質腦炎的MRI表現,例5新發病灶為位于MOG抗體病常累及的丘腦,考慮這兩例新發病灶可能是MOG介導的免疫損傷所致。例1在AE期出現的偏癱不是抗NMDAR腦炎的典型癥狀,運動障礙與MRI發現的基底節、腦室旁病灶對應,病灶呈T2WI、FLAIR高信號,部分強化,具有脫髓鞘病灶的特點,不除外AE期疊加了MOG抗體病的可能,遺憾的是該患者未行相關抗體檢測。文獻報告82%AE期病灶強化[17],比例遠大于經典AE。本組2例AE期行增強掃描1例強化,這與病毒感染導致血腦屏障破壞有關。隨訪期間本組AE期的新發病灶均消退,可能原因是AE主要通過免疫機制引起相對可逆的神經系統損害,而不是HSV直接侵犯所致。
AE期對免疫治療反應良好[2,17],一旦排除HSE復燃,應盡早開始免疫治療。治療方案與經典AE一致。部分患者可遺留與HSV感染相關的后遺癥[17]。如例1,經免疫治療AE期新發癥狀完全緩解,新發病灶消失,但HSE期出現病變的顳葉明顯萎縮,隨訪期仍有記憶力減退。故患者的整體預后似乎更取決于HSE期病毒感染導致的損傷程度。
總之,HSE抗病毒治療有效的恢復期內再發精神行為異常、認知功能障礙、癲癇發作等癥狀時,應高度懷疑繼發AE的可能,應結合臨床表現、腦脊液檢查、相關抗體檢及MRI做出綜合判斷。繼發AE以抗NMDAR腦炎最常見,可合并抗GABABR抗體、MOG抗體陽性。頭顱MRI可見其他部位的新發病灶,新病灶的出現可能與MOG抗體介導的免疫損傷有關。成人繼發性AE對免疫治療反應良好,但患者可遺留可歸因于HSE的神經功能缺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