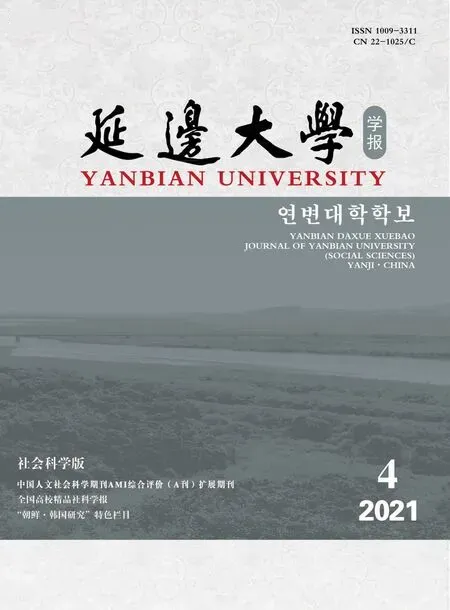蘇格拉底論美德的統一性與智者教育的本質
——柏拉圖《普羅泰戈拉》328e-334c解析
薛期燦 柴 琳
柏拉圖的對話《普羅泰戈拉》展示了哲人蘇格拉底與智者普羅泰戈拉就美德是否可教的問題進行直接交鋒的情景,為我們了解哲學與智術的區別提供了直接的材料。在對話情節上,《普羅泰戈拉》源于雅典青年希波克拉底想要在政治上出人頭地,急欲尋找這方面的老師學習政治技藝,而普羅泰戈拉公開承認他本人就是這方面的老師(319a)。于是希波克拉底找蘇格拉底帶他去見普羅泰戈拉。由于政治技藝的目的在于造就公民的美德,教人政治技藝意味著教人美德,因此,蘇格拉底向普羅泰戈拉提出質疑:美德是否可教?針對蘇格拉底的質疑,普羅泰戈拉發表長篇演說闡釋美德的可教性,并且證明在美德教育方面智者更勝一籌。
在聽完普羅泰戈拉的演說之后,蘇格拉底表示被說服了,只是還有一個小問題需要進一步考查,即美德在本質上是統一的還是多樣的。于是談話的主題從美德是否可教轉向對美德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與美德作為各不相同的部分的關系的討論。這促使我們去思考這樣的問題:一個擁有部分美德的人是否依然可以被稱為一個有美德的人?也就說,教人美德,是教人整個變好才算是教人美德,還是說教人部分變好就算是教人美德?美德到底是一還是多?本文將通過《普羅泰戈拉》328e-334c中蘇格拉底對美德統一性問題的考查來展示智者普羅泰戈拉在美德問題上的真實立場以及智者教育的本質,從而回答蘇格拉底是如何區別于智者并使哲學成為蘇格拉底式的。
一、正義與虔誠的統一性(328e-331e)
在針對蘇格拉底質疑美德是否可教而發表的長篇演說里,普羅泰戈拉提到了正義、虔誠、節制這三種政治美德(323a、324a),并把它們概括為一個東西本身(325a)。那么,這三種美德究竟是同一個東西的不同名稱,還是同一個東西的不同部分呢?普羅泰戈拉持第二種看法,即正義、虔誠、節制作為美德整體的各個部分互不相同,這種關系就像一張臉的眼、鼻、耳、嘴等各個部分一樣。基于這種關系,人們獲取美德的方式便是有人獲取一些部分,有人獲取另一些部分,因為一個人可能有勇敢但不正義、正義但不智慧的情形(329d-e)。這樣,按照普羅泰戈拉的說法,美德便有五種,除了正義、虔誠、節制這三種政治美德外,還包括勇敢與智慧這兩種個人美德,且各不相同。但是,各種具體美德的不同,是基于什么才不同的呢?蘇格拉底使用類比論證說,眼睛與耳朵之所以不同是因為它們能力不同:眼睛是用來看,耳朵是用來聽。同理,作為美德整體的部分不同于其他部分,也是因為美德的各個部分能力的不同。以能力論證模式為基礎,蘇格拉底首先考查正義與虔誠這兩種美德的關系。
蘇格拉底設計了一種微妙的提問方式來考查正義與虔誠這兩種美德。他編出一位無名的提問者向蘇格拉底和普羅泰戈拉提問,讓他們共同面對這個由蘇格拉底和普羅泰戈拉組成的小型理智共同體之外的人,就正義、虔誠這些重大問題向他們提問。蘇格拉底這個提問設計出于普羅泰戈拉將美德劃分為兩類:一類是政治美德,另一類是個人美德。作為個人美德,普羅泰戈拉是智慧且勇敢的,因為他自稱是智者(317b),并稱古代智者以詩歌等方式為掩飾來傳授智慧的做法不夠謹慎,沒能逃脫統治者的迫害,而他則公開自己的身份,并勇敢地承認自己在教人美德(316c-317c)。然而,普羅泰戈拉的做法也受到城邦的質疑,因為在城邦看來,作為政治美德,“正義與虔誠是由受諸神眷顧的智慧的先人奠定的”。(1)Lampert,Laurence,How Philosophy Became Socratic,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p.72.中譯見[美]朗佩特:《哲學如何成為蘇格拉底式的》,戴曉光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5年,第82頁。那么,在正義和虔誠這些重大問題上,你們這些智慧之人持什么樣的立場呢?通過設計一位無名的提問者,蘇格拉底代表這位無名者來考查普羅泰戈拉在美德問題上的真實立場。
蘇格拉底問,正義是不是指存在正義的事?因為,如果不是的話,正義有可能僅僅只是個名稱而已。他再問,正義的事情之所以正義,是不是因為自身正義所以才是正義的?因為,如果正義的事情之所以正義不是因為正義在起作用,那么正義這個美德與其他美德的界限也就消失了。正義區別于其他美德的地方就在于其特有的能力。在得到普羅泰戈拉肯定的回答后,蘇格拉底推論說,正義就是自身即正義的一類事情,或者說正義就是正義在其中發揮作用的一類事情。以相同的論證邏輯,蘇格拉底將其應用于虔誠:虔誠就是指存在著虔誠的事,虔誠的事之所以虔誠是因虔誠本身就是虔誠的,所以虔誠就是自身是虔誠的一類事情,或者說是虔誠在其中發揮作用的一類事情。
蘇格拉底這個論證的要點是要說明,一物之能力不同,其性質也不同。耳朵的能力是用來聽,眼睛的能力是用來看,各有各的功能,所以在性質上耳朵與眼睛也就不同。同樣,正義的性質是由正義的能力來界定的,虔誠的性質是由虔誠的能力來界定的,能力不同,性質也不同,所以,正義與虔誠不同,這種不同是完全的不同,即正義的事情就不是虔誠的事,虔誠的事情就不是正義的事,否則的話,正義和虔誠就只是同一個東西的不同名稱而已。(2)賽奈柯注意到蘇格拉底論證的不嚴密性,他舉例說,宣稱民主與經濟不相同,不等于經濟的就是不民主、民主的就是不經濟。蘇格拉底之所論證不嚴密,在賽奈柯看來,是為了逼迫普羅泰戈拉嚴肅對待對話。見劉小楓編:《誰來教育老師》,蔣鵬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5年,第250-251頁。但現實是,正義的事情也是虔誠的,虔誠的事情也是正義的,或者至少正義與虔誠是非常相似的。對神虔誠與對人正義在本質上并非完全不同。根據普羅泰戈拉解釋美德可教時所講的普羅米修斯神話,為了防止人類共同生活在一起互行不義,以至于人類滅亡,宙斯才派赫爾墨斯給人類送來正義與羞恥感這兩樣東西,作為維系城邦的秩序和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紐帶。正義是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美德,是為了避免人與人之間互相殘害,而虔誠則是維系人與神之間關系的美德。在普羅泰戈拉所講的普羅米修斯神話中,正義是由宙斯分發給人類的,人間正義的秩序是通過神來實現的,可見對人正義與對神虔誠其實是一回事,我們很難想象一個對人正義的人會做出不虔誠的事情,同樣也很難想象一個對神虔誠的人會假借神的名義對人行不義。當蘇格拉底問普羅泰戈拉如何看待論證的結果與現實的差距時,普羅泰戈拉回答說,正義和虔誠還是有一些不同的,不過,如果蘇格拉底你高興的話,就權當正義的就是虔誠的,虔誠的也是正義的(331c)。
普羅泰戈拉回答問題的方式顯得很敷衍。不同于普羅泰戈拉的長篇演說,蘇格拉底主張簡短問答,即由提問者和被提問者共同以簡短問答的方式完成談話的內容,同時被提問者所給出的回答必須代表本人的真實意愿,而非迎合提問者的意圖。以這樣的方式對談,是為了共同探究事物的本質、檢驗真理(348a)。于是,蘇格拉底堅持要求普羅泰戈拉將回答中的“如果”等字眼去掉。他說,對問題進行考查不是他自己一個人,而是兩個人共同進行的,所以,如果能將論證中的“如果你愿意”“如果你高興”等這些字眼去掉,那么問題就會得到最好的考查(331d)。蘇格拉底式簡短問答的談話方式最基本的前提是談話雙方都互相嚴肅地看待論證的結果,并將每一次自己的回答當成下一次回答的前提。蘇格拉底和普羅泰戈拉在談話方式和對待論證的態度上的區別,也顯示出普羅泰戈拉在對待自己所從事的教育事業的不嚴肅性。在來找普羅泰戈拉之前,蘇格拉底就警告希波克拉底,要是不知道什么對靈魂有益或有害,那么“一旦付了錢,把學識裝進靈魂里,獲得學識,離開時靈魂必然不是已經受到損害就是已經獲得裨益”(314b)。普羅泰戈拉對待論證的態度印證了蘇格拉底對希波克拉底的警告。
對于蘇格拉底所要求的論證的嚴肅性問題,普羅泰戈拉辯解說,一切對立的東西都有相似的地方,白之于黑有相似的地方,軟之于硬有相似的地方,正義與虔誠也有相似的地方,但我們不能說有相似就相同。他肯定了蘇格拉底的能力論證方式,一個東西不同于另一個東西是因為能力不同,所以性質不同。正義與虔誠不同,是因為正義與虔誠有不同的能力,但是,雖然正義與虔誠不同,它們并非沒有一點相似之處,不能因為它們有點相似就稱它們是相同的,同樣也不能因為它們有一點點不同就說它們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正義與虔誠不是一點點相同,也不是完全不同,那正義與虔誠到底是什么關系?對于蘇格拉底的追問,普羅泰戈拉顯得很不耐煩。于是,蘇格拉底就先暫停考查正義與虔誠的關系。
蘇格拉底為什么首先考查正義和虔誠這兩種美德呢?如果我們聯系到蘇格拉底被指控的罪名,即城邦對蘇格拉底的指控就在于說他不正義(敗壞青年)、不虔誠(不信神),那么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首先考查正義和虔誠這兩種美德的關系就有為自己的老師辯護的意圖。蘇格拉底的正義與其所選擇的生活方式有關。蘇格拉底所選擇的生活方式是哲學的生活方式。讓蘇格拉底走上一條獨特的哲學道路并最終被告上法庭的,源于蘇格拉底對智慧的困惑:自認無知的蘇格拉底竟被認為是最有智慧的。那么,什么是智慧呢?為此,蘇格拉底走上了一條獨特的考查智慧的道路。在這條路上,蘇格拉底獲得了對智慧的真正理解:別人以不知為知之,而他自己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換句話講,人的智慧是微不足道的,只有神才是智慧的。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放棄對智慧的追求,恰恰相反,智慧意味著保持對智慧的思與問。(3)[德]費格爾:《蘇格拉底》,楊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9頁。蘇格拉底自稱是城邦的牛虻便是最好的例證(《申辯》31a)。這樣看來,蘇格拉底式智慧便是其正義與虔誠的最好體現,即哲學的虔誠便是追問什么是正義。(4)[德]費格爾:《蘇格拉底》,楊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48頁。同時,蘇格拉底式智慧也體現了勇敢(自比為牛虻)與節制(自知其無知)這兩種美德的完美結合,也就是說,智慧要溫和,不能脫離節制,“哲學是勇敢與節制密切結合的最高形式”。(5)Strauss,Leo,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9,p.40.中譯見[美]施特勞斯:《什么是政治哲學》,李世祥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4年,第30頁。
通過設想一個無名提問者來提問的方式,蘇格拉底意在提醒智者普羅泰戈拉,從事美德教育的人自身美德的統一性的重要性,因為普羅泰戈拉對于自身的智慧及其從事美德教育的勇敢精神尤為看重,其目的是獲得個人智慧的聲譽而非探究真理,這就放棄了哲學的虔誠精神,從而顯得不正義。(6)Bartlett,Robert,Sophistr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Protagoras’Challenge to Socrat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6,p.44.當蘇格拉底通過考查顯示虔誠與正義在本質上是統一的時候,普羅泰戈拉開始顯得不耐煩。于是蘇格拉底便轉向考查節制這種美德,并與智慧聯系起來,考查它們的統一關系。
二、節制與智慧的統一性(332a-333b)
蘇格拉底以“相反者唯一”原則作為論證的原則來考查節制與智慧的統一關系。蘇格拉底首先向普羅泰戈拉確認,是否存在愚蠢這事,并且智慧是與之相對立的東西。在得到普羅泰戈拉的贊同之后,蘇格拉底開始考查節制這種美德。
由于能力論證模式得到了普羅泰戈拉的贊同,所以蘇格拉底繼續采用能力論證模式進行論證。一物之性質由一物之能力決定。節制之所以節制,是因為做事方式節制,也就是說,在做事的過程中節制在起作用,從而將事情做得既正確又有益。反過來講,如果將事情做得既正確又有益,那就是在做事的過程中節制在起作用,也就是做事節制。如果做事不正確、愚蠢,那就是做事不節制,也就是在做事的過程中節制不起作用。蘇格拉底再以強壯和虛弱、快速與緩慢作類比,得出他論證的第一個結論:一物之性質與一物之能力相對應。
在能力論證的基礎上,蘇格拉底引入“相反者唯一”原則作為論證的原則。他舉了三個例子:美,與之相對立的是丑;好,與之相對立的是壞;高音,與之相對立的是低音。蘇格拉底接下來問普羅泰戈拉,如果一個東西有一個與之相對立的東西,那么這個相對立的東西是不是只有唯一一個?普羅泰戈拉不假思索地給出了肯定的回答。現在,把這兩個論證原則結合起來:根據能力論證原則,即做事的方式或能力決定事物的性質,做事愚蠢所以是愚蠢的,做事節制所以是節制的,做事愚蠢與做事節制是相對立的,因此愚蠢與節制是相對立的。但是,普羅泰戈拉剛承認愚蠢與智慧是相對立的。根據“相反者唯一”的原則,可以得出智慧與節制是同一的,也就是說,實際上智慧與節制只是同一個東西的不同名稱而已。因此,蘇格拉底讓普羅泰戈拉做選擇:要么放棄“相反者唯一”這個論證原則,承認一個東西不只有一個東西與之相對立;要么放棄能力論證原則,否定美德的各個部分都有不同的能力。如果堅持“相反者唯一”的論證原則,就不得不承認節制和智慧是一回事,因為論證的結果顯示,愚蠢既與智慧相對立,也與節制相對立。可如果放棄能力論證原則,就和普羅泰戈拉一開始的說法自相矛盾。普羅泰戈拉開始的說法是,作為美德整體的各個部分,正義、節制、虔誠、智慧和勇敢各自擁有不同的能力,美德的各個部分互不相同,就像同一個臉部的眼、鼻、耳、嘴的關系一樣(329d)。
經過兩輪論證,蘇格拉底表明,正義與虔誠在本質上是一回事,作為智慧之人,普羅泰戈拉為了迎合民主政治,放棄哲學的虔誠,顯得不正義。同樣,智慧與節制也是統一的,智慧不能脫離節制,否則就不能把事情做得既對又有益。普羅泰戈拉勇敢地脫離古代智慧傳統,公開傳授智術,正在給哲學事業帶來前所未有的危險。現在,蘇格拉底只要把前面兩個論證合在一起,證明正義與節制的統一關系,就可表明正義、虔誠、智慧與節制這四種美德在本質上是統一的。
三、正義與節制的統一性(333c-334c)
在指出普羅泰戈拉自身美德的缺陷之后,蘇格拉底將進一步指出,普羅泰戈拉從事的智術教育所帶來的不義后果,即教人有節制地行不義,從而最終危害到城邦的穩定。
在考查節制這種美德的時候,普羅泰戈拉同意把事情做得既對又有益就是做事節制。蘇格拉底繼續問道,就做事不義本身而言,能否稱得上是節制,或者說看上去是節制的?如果普羅泰戈拉承認做事不義也可稱得上是做事節制,那么這無異于公開承認做事不義也可以把事情做得既對又有益。另外,當蘇格拉底問普羅泰戈拉美德是否是統一的時候,他否認了美德的統一性,并舉例說一個人可以勇敢但不正義、正義但不智慧(329e)。可是,蘇格拉底剛通過“相反者唯一”的論證原則迫使普羅泰戈拉承認智慧與節制在本質上沒有區別,如果一個人可以正義但不智慧,反過來講,是否意味著一個人可以智慧(節制)但不正義?或者,如蘇格拉底所問,做事不義也可以被稱得上是節制的?
普羅泰戈拉不能否定這個說法,因為這是蘇格拉底從他的回答中得出來的,但他又恥于公開承認,于是普羅泰戈拉便在自己的觀點與世人看法之間做了區分。他說,承認做事不義是節制的這個說法是可恥的,但許多普通大眾確實是這么說的,因為不義之行最終看起來像是很有節制。如果普羅泰戈拉公開承認做事不義也可以是節制的,那么這無異于承認人們行不義之事時,只要能瞞過民眾,那就是節制。為了回避蘇格拉底這個兩難的提問,普羅泰戈拉讓蘇格拉底先單獨跟大多數人的觀點作辯論,但蘇格拉底說,這倒無所謂,因為他關心的是論證本身而非論證者,因而在論證的過程中,不單是被提問者,連提問者本身也將受到平等的考查(333c)。蘇格拉底采用簡短問答的談話方式并非僅僅只是考查被提問者的觀點,而是連提問者本人也會受到平等的考查,從而蘇格拉底式簡短問答的談話方式就具有自我批判的特點,這并不是為了取得論辯上的勝利,而是為了考查事物的本質,即真理。

由于普羅泰戈拉否認正義與節制的統一性,因此,蘇格拉底將不義與節制聯系起來,并迫使普羅泰戈拉承認有些人做事不義也是節制的,或者說在做不義之事時也是明智的,明智的就是要考慮周全,考慮周全的目的是想把事情做成(做好),那么把事情做好就是對人有好處。我們把上述的推論加以簡化:做事不義→節制→明智→考慮周全→把事情做好→對人有利。普羅泰戈拉自稱教人善謀,就是教人要考慮周全,(9)朗佩特注意到了考慮周全與善謀的詞根關系,見Lampert,Laurence,How Philosophy Became Socratic,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p.77.中譯見[美]朗佩特:《哲學如何成為蘇格拉底式的》,戴曉光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5年,第87頁。[美]岡薩雷斯:《〈普羅泰戈拉〉中的德性:共同思索善》,劉小楓編:《誰來教育老師》,蔣鵬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5年,第84頁。另見Knut Agotnes,“Socrates’ Sophisticated Attack on Protagoras”,O.Pettersson,V.Songe-M?ller(eds.),Plato’s Protagoras:Essays on the Confronta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phistry,Gewerbestrasse: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7,pp.30-31;Bartlett,Robert,Sophistr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Protagoras’ Challenge to Socrat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6,p.50.因此,我們把考慮周全換成善謀,簡化后的蘇格拉底的遞推論證如下:做事不義→節制→明智→善謀→把事情做好→對人有利。教人善謀確實可以給人帶來好處,但是這里的人也可以是做事不義之人,因為行不義之事的人也可能通過習得善謀的技藝來給自己帶來好處。通過簡化我們可以看出,智者所從事的美德教育的本質就是將“實質的不正義與表面的正義結合起來”,(10)Strauss,Leo,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p.117.中譯見[美]施特勞斯:《自然權利與歷史》,彭剛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第117頁。也見[美]岡薩雷斯:《〈普羅泰戈拉〉中的德性:共同思索善》,劉小楓編:《誰來教育老師》,蔣鵬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5年,第83頁。即表面上教人善謀(政治技藝),實質上卻有可能教人有節制地行不義之事來給不義之人帶來好處,因此,當蘇格拉底指出普羅泰戈拉的教導所可能帶來的不義后果時,普羅泰戈拉生氣了。(11)岡薩雷斯把利用智慧和勇敢教人善謀可能被用于追求不義看成普羅泰戈拉最隱秘的秘密,并稱普羅泰戈拉的生氣表明,行不義時也算得上是節制是普羅泰戈拉的真實觀點,見[美]岡薩雷斯:《〈普羅泰戈拉〉中的德性:共同思索善》,劉小楓編:《誰來教育老師》,蔣鵬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5年,第79、83頁。
看到普羅泰戈拉生氣的樣子,蘇格拉底小心翼翼地換個說法問道:“你所指的好是指無人受益,還是說根本就沒有好這回事?”普羅泰戈拉否定了蘇格拉底的說法,好既非無人受益,也非一無好處。為了在辯論中取勝,普羅泰戈拉改變了蘇格拉底強加給他的論辯方式,發表了一通長篇演說為自己的關于好的相對主義立場作辯護:“我自己當然知道,許多東西對人并沒有益處——吃的、喝的、藥物以及別的數也數不過來的東西,但我也知道,有的東西對人有益處。還有一些則談不上對人有益或者有害,卻對馬有益;有些僅對牛有益,有些則對狗有益。還有一些對這些動物談不上有益或者有害,卻對樹木好;而且有些對樹根好,對嫩枝卻有害,比如畜糞,撒在所有的樹木的根上都好,可要是你想把它們撒在新苗和嫩枝上,就把它們全毀了。甚至還有橄欖油,對所有的植物都極為有害——而且是除了人以外的所有生物的毛發的大敵,卻呵護人的毛發甚至身體的其它地方。所以,一切的好實在復雜,而且五花八門。就拿這個橄欖油來說,在體外對這個人就是好東西,但在體內,同樣這個東西對人就極壞。由于這個原因,醫生全都禁止體弱者在想吃的東西中用橄欖油,除非極少一丁點兒,以祛除食物和佐料中讓鼻子感到的難聞味為限”(12)[古希臘]柏拉圖:《柏拉圖四書》,劉小楓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第99-100頁。(334a-d)。
普羅泰戈拉的這段演說,針對的是蘇格拉底的提問:做事不義對人有好處,還是做事不義無人能受益?如果做事不義對人有好處,那么到底是誰在受益?如果做事不義無人能受益,那么為什么做事不義還能是節制的呢,因為節制意味著把事情做得又對又有益?普羅泰戈拉肯定了做事不義也可以對人有好處,否定了做事不義對人毫無好處,只是這里的好處(益處)要相對來看。一個東西對甲有好處,不見得對乙有好處,因此,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普羅泰戈拉的長篇演說使其在美德問題上的相對主義立場顯露無遺。
四、美德的統一性與智者教育的本質
普羅泰戈拉在美德問題上的相對主義立場是蘇格拉底考查美德統一性問題的目的。普羅泰戈拉主張美德是相對的,必然否認美德的統一性。換句話講,如果美德是相對的,那么衡量美德的標準也將是變動的,這就觸及了城邦的政治基礎。
普羅泰戈拉的相對主義立場在《泰阿泰德》里有詳細的闡發。在《泰阿泰德》中,蘇格拉底通過助產泰阿泰德得出“知識即感覺”的說法后,認為泰阿泰德的這個說法與普羅泰戈拉的“人是萬物的尺度”說法很接近,按照這個說法,“人是‘是的東西’之所是的尺度,也是‘不是的東西’之所不是的尺度”。(13)[古希臘]柏拉圖:《泰阿泰德》,詹文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24頁。一陣風吹來,是冷是熱,衡量的尺度在人,人感覺到什么就是什么。同樣,一個東西對人好不好,衡量的尺度在于人而不在于事物本身。對甲好的東西,不一定對乙有好處;對乙不好的東西,不一定對甲有害。普羅泰戈拉在上述演說中所舉的畜糞和橄欖油的例子,說明看起來是不好的東西(畜糞)也有好處,看起來是好的東西(橄欖油)有時對人也有害。一切好都是相對的,做事不義有時也會對人有好處。普羅泰戈拉的相對主義立場表明,其教導的乃是習俗性的東西,探究自然的哲學在普羅泰戈拉那里最終變成迎合習俗(政治)的東西。(14)Strauss,Leo,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pp.116-117.中譯見[美]施特勞斯:《自然權利與歷史》,彭剛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第117-118頁。
普羅泰戈拉的演說贏得了在座者的一陣喝彩,可見在座的大部分人還是沒有能力區別普羅泰戈拉講辭中欺騙性的成分與真實的內容。在座的青年大部分如希波克拉底一樣,是沖著普羅泰戈拉的名聲而來,目的是學得一套演說的技巧,使自己在行事和說話方面變得厲害,以便在城邦的政治舞臺上出人頭地,然后為自己撈得好處(316c)。在來找普羅泰戈拉之前,蘇格拉底以天光未亮為由考查希波克拉底,結果顯示,希波克拉底對普羅泰戈拉教育的內容一無所知。于是,蘇格拉底向希波克拉底發出警告:在對普羅泰戈拉所教的東西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情況下,貿然將自己的靈魂托付給這類智者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因為一旦學得智者的教誨,靈魂便有可能受到永久性的傷害。蘇格拉底以醫生作類比說,靈魂的學習和身體的飲食不一樣,哪些東西對身體有益,哪些東西對身體有害,在食用之前我們可以請教醫生,甚至在誤食了有害的東西之后,我們還可以將其吐出。但是,靈魂的學習卻很不一樣,一旦學成,靈魂便要么受益要么受損,除非自己是靈魂的醫生,能夠辨別智者教誨中哪些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否則就不知道自己靈魂所托付的是好還是壞。蘇格拉底帶希波克拉底來找普羅泰戈拉,就是要來找尋靈魂的醫生,搞清楚智者教育的本質,辨別智者教誨中哪些教誨是有益的哪些教誨是有害的。蘇格拉底通過考查普羅泰戈拉對待美德的真實態度,揭露了普羅泰戈拉所教的智術(善謀或政治技藝)的本質及危害。教人善謀(政治技藝)有可能使人為了個人利益在行不義之事時顯得更節制更明智,從而對城邦的危害更大,特別是那些只關心個人利益而缺乏公益之心的人,一旦掌握這門技藝之后,便有可能在雅典的政治舞臺操弄雅典公民,藐視雅典法律,破壞雅典的政治穩定。(15)拉爾森提到,希波克拉底對政治無知的危害比普羅泰戈拉所教智術的危害來得更大。當然,希波克拉底與普羅泰戈拉智術的結合,也有可能為其通往僭政之路助力。見Larsen,Jens Kristian,“By What Is the Soul Nourished? On the Art of the Physician of Souls in Plato’s Protagoras”,O.Pettersson,V.Songe-M?ller(eds.),Plato’s Protagoras:Essays on the Confronta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phistry,Gewerbestrasse: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7,pp.79-97.
經過三輪的考查,蘇格拉底將普羅泰戈拉不義的偽裝一一揭開:首先,在考查正義與虔誠的關系時,蘇格拉底基于能力論證證明正義與虔誠的一致性——保持對哲學的虔誠便是智慧之人的正義。作為智者,普羅泰戈拉為了博取智慧的名聲,放棄了哲學的虔誠,公開在其著作中宣揚無神論,以人替代神作為真理的尺度,革新城邦的信仰,顯得既非虔誠也不正義。(16)[古羅馬]第歐根尼·拉爾修:《明哲言行錄》,徐開來、溥林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58頁。其次,在考查智慧與節制的關系時,蘇格拉底以“相反者唯一”為原則論證智慧與節制的一致性——智慧不能脫離節制。普羅泰戈拉否定整個古希臘智慧傳統,去掉詩歌的掩飾,公開搞智術教育,其行為并非勇敢,而是魯莽。最后,蘇格拉底考查正義與節制的關系——節制是為了城邦正義,而不是為了個人利益。普羅泰戈拉所教導的善謀就是教人在政治事務中更有能耐地行事和說話,然而,論證的結果顯示,普羅泰戈拉所教的有可能讓人有節制地行不義,從而讓不義之人看起來是正義的。這樣的技藝,一旦被道德品質低下的人所掌握,便有可能被用來為自己謀利,甚至為自己的僭政統治鋪平道路。
五、結語
通過考查普羅泰戈拉在美德問題上的真實立場,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與智者普羅泰戈拉區別開來:智者通過模糊美德的衡量標準,將美德相對主義化,從而否定美德的統一性,只顧追求個人智慧上的名聲,全然不顧其教育給城邦所帶來的危害,即表面上承諾教導青年美德,實際上卻僅僅只是在教導適用于民主政治下操弄民眾的言辭和政治技巧。哲學成了智術,美德教育反而是在敗壞青年。可以說,智者對城邦的衰落負有責任,這種責任的根源在于從事教育的智者自身道德品質的墮落,即從事教育者忽略自身美德的統一性,割裂政治美德與個人美德的關系,只在乎自身在智慧方面的勇敢與聲譽,而不顧其教育的政治后果。在《普羅泰戈拉》中,蘇格拉底試圖扭轉哲學的智術形象,將被智者相對主義化的美德標準重新歸一,這是蘇格拉底考查美德統一性問題的目的,也是哲人蘇格拉底區別于智者普羅泰戈拉的根本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