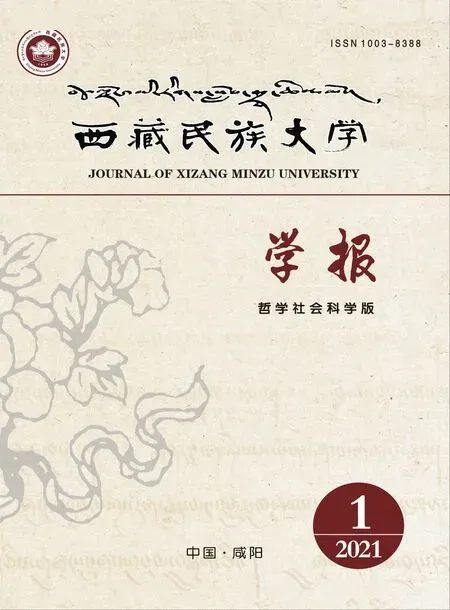國內《格薩爾》翻譯研究:現狀與展望(1986-2020)
崔紅葉,趙海靜
(1.西藏民族大學外語學院 陜西咸陽712082;2.西藏民族大學學報編輯部 陜西咸陽712082)
流傳于藏蒙地區的英雄史詩,藏族稱《格薩爾》,蒙古族稱《格斯爾》,本文通稱《格薩爾》。《格薩爾》史詩篇幅宏大,譯本眾多,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深受世界人民的歡迎。1986年王沂暖先生發表了第一篇《格薩爾》翻譯研究論文,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并開始對《格薩爾》翻譯展開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有鑒于此,本文嘗試對中國知網上發表的相關期刊論文進行梳理,總結《格薩爾》翻譯研究的成就,歸納其不足,并對未來研究進行展望,以期為《格薩爾》翻譯理論及實踐研究提供借鑒。
一、文獻來源與數據分析
(一)文獻來源
文獻資料來自中國知網總庫,采取高級檢索模式,文獻類別選擇期刊,使用四個檢索式進行檢索。檢索式A為篇名等于“格薩爾”或者“格斯爾”,同時,篇名等于“翻譯”或者“英譯”,精確匹配,獲得40篇期刊論文;檢索式B為篇名等于“格薩爾”或者“格斯爾”,同時,篇名等于“漢譯”或者“民譯”,精確匹配,獲得3篇期刊論文;檢索式C為篇名等于“格薩爾”或者“格斯爾”,同時,篇名等于“譯本”或者“譯介”,精確匹配,獲得8篇期刊論文;檢索式D為篇名等于“格薩爾”或“格斯爾”,同時,篇名等于“域外傳播”或者“走出去”,精確匹配,獲得2篇期刊論文;共獲得53篇期刊論文。去除1篇譯文,2篇綜述,1篇評介,1篇立項書,最終獲得48篇有效論文作為研究對象。
(二)數據分析
數據分析工具為Bicomb2書目共現分析系統,以《格薩爾》翻譯研究的48篇成果為對象,從研究動態、研究隊伍、載文期刊三個方面進行統計分析。
1、研究動態
《格薩爾》翻譯研究肇始于1986年,截止到2020年,累計34年的歷史。整體呈現出曲折中上升的趨勢,中間曾7次跌到零點,發文峰值出現在2016年(如圖1所示)。

圖1:1986-2020年《格薩爾》翻譯研究動態圖
三十余年來,《格薩爾》翻譯研究時斷時續,有效發文量只有48篇,年均發文量不足2篇,最高峰只有6篇。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時期:1986-2009年,萌芽期,研究成果零星出現;2010-2020年,發展期,研究成果有所增加。總體來看,《格薩爾》翻譯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學界關注度低,年度發文量不穩定,但已初步呈現出增長的態勢。
2、研究隊伍
全國共有23家單位的學者在《格薩爾》翻譯領域發表了相關研究成果。其中,西北民族大學、天津工業大學、西藏民族大學位列前三,共占比45%,是該領域研究成果的主要來源(如圖2所示)。聚焦學者的研究領域,可以發現,《格薩爾》翻譯研究者主要來自外語、藏學、文學三個領域,分別占比59%,21%和14%,涉及其他領域較少,僅占6%(如圖3所示)。
總體而言,西北民族大學是該領域的研究重鎮,涉及9位研究人員,既有開啟《格薩爾》翻譯研究的鼻祖王沂暖先生,又有寫出第一本《格薩爾》翻譯研究專著的扎西東珠;王治國是該領域研究的熱點人物,從天津工業大學到天津師范大學再到南開大學,每一步都與《格薩爾》翻譯研究息息相關;西藏民族大學、大連民族學院是該領域的研究新秀,以弋睿仙為代表的一批青年學者,以拉姆卓嘎為代表的一批青年學生,嘗試從多個角度探究這部活態史詩的翻譯及翻譯研究成果;可喜的是,國內權威研究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南開大學也關注了這一領域的研究,以王沂暖、降邊嘉措、王宏印為代表的老一輩專家學者也關注了《格薩爾》的翻譯問題。

圖2:作者單位分布圖

圖3:作者研究領域分布圖
3、載文期刊
研究發現,相關論文成果刊載于26種期刊之上。《民族翻譯》《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分別位列第一和第二。(如圖4所示)。

圖4:期刊論文分布圖
西北民族大學主辦了《西北民族大學學報》與《西北民族研究》兩種刊物,占據了《格薩爾》翻譯研究人才和翻譯研究平臺兩個制高點;《民族翻譯》成為該領域研究成果的重要刊載平臺;翻譯領軍刊物《中國翻譯》共刊發2篇《格薩爾》翻譯研究的論文,說明其已開始關注這一研究領域,顯示了《格薩爾》翻譯研究在學術界的重要性。
二、研究現狀及研究熱點
王克非[1]認為建立全能的翻譯學模式是不可能的,如將其分為三大類分別予以研究則比較可行。這三大類是:翻譯技巧研究、翻譯理論研究和翻譯文化研究。《格薩爾》翻譯研究可以采用這種研究分類方法。
(一)《格薩爾》翻譯技巧研究
“Studies on translating,可稱為翻譯技巧(或方法)研究,屬實用型研究,對于外語教學和翻譯能力的培養有直接的意義。”[1]此類研究是《格薩爾》翻譯研究的肇始,主要關注點為《格薩爾》專有名詞的翻譯研究、《格薩爾》文化意象的翻譯研究及《格薩爾》詩歌的翻譯研究。
1、《格薩爾》專有名詞的翻譯研究
專有名詞的翻譯研究屬于詞的翻譯研究。《格薩爾》專有名詞的翻譯研究始于馬進武[2],他提出《格薩爾》專有名詞翻譯的六條規范:按方言音譯,按藏語音譯,音意合譯,完全意譯,沿用歷史及更改書名。繼他之后,角巴東主[3]指出《格薩爾》專有名詞的曲解甚至誤譯問題,提出“音譯為主、沿用歷史”這兩條翻譯原則,同時發起編纂權威工具書和減少方言影響的倡議。洛珠加措[4]贊同《格薩爾》專有名詞翻譯沿用歷史譯名,同時提出在無歷史譯名的情況下,應該在權衡大眾接受度和學術界認可度的基礎上新創。崗·堅贊才讓[5]也關注了《格薩爾》名稱翻譯的問題,提出五種翻譯方法:書名分要素翻譯法、人名規范音譯法、非藝術地名音譯法、藝術地名意譯法、馬名意譯法。扎西東珠[6]對《格薩爾》專有名詞“以音譯為主、沿用歷史譯名、減少方言影響”的翻譯方法持肯定態度,同時提出藝術人名、建筑名、地名采用意譯或音意譯合璧法,馬名、武器名、曲調名和神佛名采用意譯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首次提出多義詞音譯法,即如果一個詞有多種意思,便要采用音譯法,而不能采用意譯法。
2、《格薩爾》文化意象的翻譯研究
文化意象的翻譯研究屬于詞組的翻譯研究。文化意象的翻譯研究最早見于王景遷等[7],主張翻譯《格薩爾》文化意象時,將不易導致誤解的文化詞歸化,易導致誤解的文化詞異化,學者異化,大眾歸化。臧學運[8]關注了《格薩爾》中反復出現的藏傳佛教文化意象,提出要精確、全面地把握以藏傳佛教為核心的藏族文化,避免文化誤讀。張寧[9]提議《格薩爾》文化意象翻譯應當有選擇地應用異化策略:精神文化歸化,物質文化異化。拉姆卓嘎等[10]嘗試將《格薩爾》文化意象翻譯體系化,提出直譯法、音譯法、音譯加注法屬于異化策略,意譯法和簡化法屬于歸化策略。
3、《格薩爾》詩歌的翻譯研究
詩歌的翻譯研究屬于語篇的翻譯研究。張積誠[11]討論了《格薩爾》詩歌翻譯的增減問題,提出以詩譯詩的原則和從詩韻、音節、節奏三方面進行“詩化加工”的操作技巧,奠定了詩歌翻譯研究的基礎。馬進武[2]提議《格薩爾》詩歌翻譯應當關注其“歌”的特點,即唱詞結構、音樂旋律和歌曲名稱。洛珠加措[4]支持《格薩爾》詩歌翻譯以詩譯詩,并提倡譯為現代詩。降邊嘉措[12]援引了郭沫若的話,建議《格薩爾》詩歌翻譯運用合作機制:譯者翻譯,詩人做詩化加工。
(二)《格薩爾》翻譯理論研究
“Studies on translation,可稱為翻譯理論研究,屬基礎性研究,它對于外語教學和翻譯能力的培養,有一定意義,但不像翻譯技巧研究那樣有直接的指導意義。”[1]此類研究在《格薩爾》翻譯研究中所占比重最大,涉及翻譯類別、翻譯原則、翻譯轉換機制、譯者素養、譯文接受及翻譯語境等。
1、《格薩爾》翻譯類別研究
最早討論翻譯類別的學者是崗·堅贊才讓[5],他從翻譯媒介的角度提出《格薩爾》翻譯的兩種類別:口譯和筆譯;扎西東珠[6]進一步提出《格薩爾》翻譯存在口譯、筆譯、口譯加筆譯這三種方式;鄭敏芳等[13]從加工程度將《格薩爾》翻譯中的筆譯細分為選譯、改譯、編譯、譯創等方式。王宏印等[14]以譯入語所在區域為標準,提出《格薩爾》翻譯存在域內和域外兩種方式,民譯和漢譯、外譯和英譯等途徑。
2、《格薩爾》翻譯原則研究
《格薩爾》翻譯原則基本遵循傳統的翻譯理論,但其在翻譯實踐過程中有自身的特點。何天慧[15]指出著名《格薩爾》翻譯家王沂暖教授遵從“信、達、雅”的翻譯原則,降邊嘉措[12]亦贊同此翻譯原則;馬進武[2]提出《格薩爾》翻譯三原則:忠實內容、語言易懂、保持風格;角巴東主[3]提出《格薩爾》翻譯應當準確理解、忠實表達、保持原文風格;崗·堅贊才讓[16]提出《格薩爾》翻譯的原則是忠實原文和保存文化特色;張積誠[11]提出《格薩爾》翻譯原則為忠實原著、領略用韻、再現音美;扎西東珠[6]提出《格薩爾》翻譯的三原則:名詞翻譯應當約定俗成,分別對待說唱本和規范本,遵從內容需要。
3、《格薩爾》翻譯轉換機制研究
翻譯轉換機制研究多為跨學科視角下的研究。楊艷華等[17]從修辭學的零度偏離理論出發,提倡《格薩爾》譯者運用語言正偏離、消滅語言負偏離的翻譯轉換機制,以提高漢譯英質量;李秀麗[18]從認知語言學隱喻概念理論出發,探析《格薩爾》翻譯的三種轉換機制:對等翻譯、蘊含翻譯和外延翻譯;邵璐[19]從篇章語言學出發,考察分析《格薩爾》翻譯轉換中的銜接性和信息性,反對過度強調市場而忽略原作本原性的做法。王治國提出《格薩爾》翻譯的漢譯中介模式[20]和九種翻譯轉換機制[21]。吳曉春[22]從文化審美表現論出發,考察了《格薩爾》文化信息的兩種翻譯轉換機制:對應和代償,指出代償中的闡釋法更能傳達蒙古族英雄史詩自身的文化和審美。邵璐等[23]從認知文體學理論出發,運用文體分析法考察《格薩爾》翻譯轉換中譯者的認知過程,指出翻譯過程的本質是譯者通過閱讀了解原作者認知機制后,對原文本進行的再創作。
4、《格薩爾》譯者素養研究
學界對譯者素養的興趣也很濃厚。崗·堅贊才讓[16]提出《格薩爾》譯者應該具備藏漢語言文字基礎、多方面知識和文學修養;賈曼[24]研究發現著名《格薩爾》譯者王沂暖具備四種素養:藏文理解力、漢語表達力和寫作能力、熟悉藏族世俗生活、了解佛教教義。
5、《格薩爾》譯文接受研究
譯文接受研究起步較早,近來頗受學者關注。崗·堅贊才讓[16]從文學的角度指出《格薩爾》譯文接受者在提高文化素養、開闊文化視野之后,接受心理和審美期待會隨之變化。王治國提出再創與創譯[25]、媒介融合[21]、深度描寫[26]有利于《格薩爾》譯文在海外的接受,落實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并提出應構建中華本土的史詩翻譯話語體系[27];宋婷等[28]指出歌劇及現代散體詩歌方式有利于《格薩爾》譯文的跨界傳播。
6、《格薩爾》翻譯語境研究
部分學者關注了雙語語境對《格薩爾》翻譯的制約作用。扎西東珠[29]提出雙語語境制約《格薩爾》譯文的產出;梁艷君等[30]提出《格薩爾》翻譯應再現言內外語境;劉彭愷[31]提出文化語境制約《格薩爾》譯者的策略選擇。
(三)《格薩爾》翻譯文化研究
“Studies on translation in a cultural context,即翻譯文化研究,它將翻譯史、翻譯與文化的相互作用研究包括在內,比過去提的翻譯史研究有更豐富的內涵,比較文學界常以這一角度看待歷史上的翻譯。”[1]此類研究在《格薩爾》翻譯研究中方興未艾,但研究成果集聚在梳理翻譯史方面,有關翻譯對文化的意義和作用的成果較少。

表1:《格薩爾》域內翻譯史
1、《格薩爾》翻譯史研究
《格薩爾》翻譯史研究表現為域內翻譯史和域外翻譯史兩條主線。域內翻譯史方面,學者們關注了《格薩爾》的漢譯史和蒙譯史,共梳理出17次漢譯活動和一次蒙譯活動(如表1所示)。
域外翻譯史方面,《格薩爾》英譯史的關注度最高。目前梳理出19次《格薩爾》外譯活動,包括9次英譯活動,6次俄譯活動,2次法譯活動和2次德譯活動(如表2所示)。
2、《格薩爾》翻譯的作用和意義
學界普遍認可《格薩爾》翻譯對文化有促進作用。洛珠加措[4]指出《格薩爾》翻譯是交流和溝通民族思想和情感的手段;崗·堅贊才讓指出《格薩爾》翻譯是思想的交流,[16]有利于史詩本身的繼承和保護。[5]扎西東珠提出,世界認可《格薩爾》是譯介的功勞。[6]降邊嘉措[12]提出翻譯可以讓《格薩爾》成為中華民族和全人類的精神財富和文化遺產。弋睿仙[36]提出《格薩爾》史詩英譯有益于格薩爾學乃至藏學研究的發展。降邊嘉措[37]提出《格薩爾》外譯有益于向全世界宣傳新中國的成就,宣傳優秀的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王宏印等[14]提出翻譯成就了《格薩爾》的千年傳唱、成功“申遺”和走向世界。
三、《格薩爾》翻譯研究展望
當前的《格薩爾》翻譯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然而,與《格薩爾》史詩的地位和翻譯現狀相比,該領域的研究尚存在以下七個問題。第一,研究規模亟待擴大。三十多年來,僅斷斷續續地發表了四十多篇《格薩爾》翻譯研究論文,相關研究曾多次跌回零點,甚至連續幾年內一直為零,即使是巔峰年份發文量也未突破個位數,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研究規模有待進一步擴大。第二,當前的《格薩爾》研究人員之間極少合作,跨民族、跨專業、跨單位的合作研究極為罕見,尚未形成研究團隊,極大地降低了生成高層次研究成果的可能性。第三,《格薩爾》翻譯研究的主要載文期刊影響力低。《格薩爾》的重要性得到了一致認可,然而,相關論文成果在發表方面卻很受局限。當前民族類刊物是最主要也是幾乎唯一的刊載平臺,翻譯類、外語類、綜合類刊物鮮少刊發相關研究成果,支持力度有待進一步加大。第四,《格薩爾》翻譯技巧研究缺乏大數據的檢驗。當前的《格薩爾》翻譯技巧研究僅是個別譯者研究有限譯本的結論,譯本研究集中在幾個經典譯本。相對于《格薩爾》眾多的譯本而言,當前研究涉及的譯本占比很小。當前的《格薩爾》翻譯技巧研究成果只得到了小范圍數據的支撐,缺乏大數據的檢驗和修訂,很難直接用于指導繁復的翻譯實踐。第五,《格薩爾》翻譯技巧研究和翻譯理論研究不充分。翻譯技巧研究局限于詞、詞組和語篇,翻譯理論研究局限于翻譯類別、翻譯原則、雙語轉換機制、譯者素養、譯文接受和翻譯語境,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均有待進一步拓展。第六,《格薩爾》翻譯文化研究不深入。當前的《格薩爾》翻譯史研究停留在介紹歷史事件不夠深入。第七,定量研究欠缺。當前的《格薩爾》翻譯研究側重主觀經驗和主觀闡釋,針對《格薩爾》翻譯數量特征、數量關系和數量變化的研究欠缺。

表2:《格薩爾》域外翻譯史
針對上述問題,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解決。第一,加大《格薩爾》翻譯研究人才培養力度,創新人才培養思路。學科的發展依賴于人才,《格薩爾》翻譯研究亦不例外。當前,能夠熟練運用藏、漢+外語的翻譯研究人才本就不多,了解《格薩爾》且對史詩感興趣的此類人才更是鳳毛麟角。針對如此窘境,民族地區的高校可以率先行動起來。在招生時,應向具備多種語言能力的考生傾斜,在課程設置方面,加大文學翻譯課程及語言課程的比例。第二,搭建《格薩爾》翻譯研究學術交流平臺,鼓勵協同創新。《格薩爾》翻譯學術交流平臺有利于同行交流,有利于研究團隊建設,有利于跨學科、跨單位、跨地區的合作與創新,有利于催生高水平的科研成果。第三,提升民族類刊物的影響力,鼓勵翻譯類、外語類、綜合類刊物刊發《格薩爾》翻譯研究成果。《格薩爾》翻譯研究迫切需要得到高層次、高水平的學術刊物的支持,讓更多的學者了解相關研究領域,鼓勵更多的學者轉換研究領域,快速擴充現有研究隊伍。提升民族類刊物的影響力是最直接的解決辦法,鼓勵高層次刊物發表相關文章可為有效的補充。第四,建設《格薩爾》翻譯語料庫,反復驗證、持續推進《格薩爾》翻譯技巧研究。建立大數據平臺,在檢驗中不斷完善當前的結論,促使翻譯技巧研究成果盡快應用于指導翻譯實踐。同時,電子化的語料資源,還可以用于術語整理和專門用途詞典編纂,為《格薩爾》翻譯實踐提供權威的資料以供參考。第五,拓寬《格薩爾》翻譯技巧和翻譯理論研究的對象。《格薩爾》翻譯技巧研究可以拓展到詞素翻譯研究、句子翻譯研究、語法翻譯研究和語用翻譯研究等方面;《格薩爾》翻譯理論研究,可以將翻譯研究的功能,翻譯與思維的關系,翻譯政策,機器翻譯及計算機輔助翻譯,翻譯單位等列為研究對象。第六,《格薩爾》翻譯史研究應該深入到中西文化交流的實際歷史場景。翻譯史研究不妨學習王沂暖教授的做法,通過譯原本比較進行譯本溯源;可以還原譯本傳播的歷史場景;可以調查讀者的閱讀接受等內容,也可以嘗試分析譯本制作的動機、譯者意識形態、譯入語文本所處的社會環境等超語言因素對譯本生成的影響,為當代中華文化的對外傳播提供思路與借鑒。第七,對《格薩爾》翻譯研究展開量化研究。運用調查、實驗、測量、統計等定量研究的方法系統地考察《格薩爾》翻譯研究的現狀,找出普遍性的規律、趨勢或分布情況,探索更客觀、更可靠、更具概括性的結論。
結語
本文回顧了三十余年來國內《格薩爾》翻譯研究的現狀,發現當前的《格薩爾》翻譯研究尚處于肇始階段,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仍有不足之處,需要社會各界攜手合作,共同將《格薩爾》翻譯研究推上一個新的臺階。隨著中國國家實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中華民族多元文化走出去面臨前所未有的戰略機遇。作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格薩爾》是中華民族多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當前,《格薩爾》的翻譯及翻譯研究對于增強中華文化自信心、提高中華民族文化“軟實力”和建立中國學術話語權等均有重大的意義。假以時日,隨著各項舉措的不斷落地實施,史詩翻譯研究必將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局面。史詩《格薩爾》翻譯研究前景可待,未來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