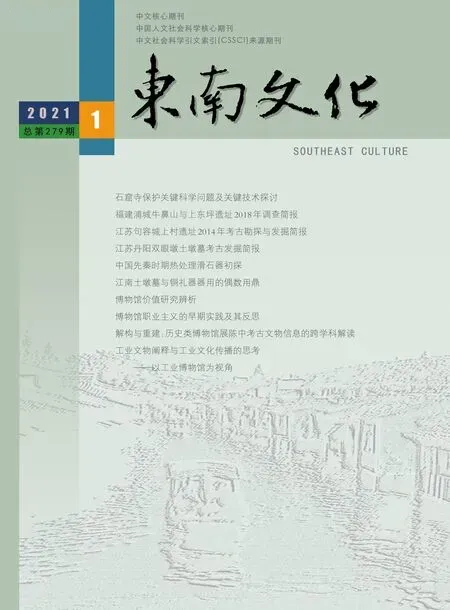江南土墩墓與銅禮器器用的偶數用鼎
楊 博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 北京 100101)
內容提要:江南地區土墩墓葬青銅禮器的器用禮俗,偶數用鼎是其中一個突出的表現。無論是墓葬整體器用組合的偶數用鼎,還是用鼎組合內部存在的偶數同形鼎,西周中期以降在寧鎮、皖南、江淮以及山東沿海地區均有所見,特別是偶數同形的用鼎禮俗至遲在春秋初期已成為上述地區有別于中原地區列鼎“周制”的顯著特色。墓葬青銅禮器用鼎亦揭示出春秋以后廣義之“周人”族群內部的諸侯國族在青銅器用文化層面的交融互攝,并最終凝聚成華夏族群的動態歷史過程。
一、問題緣起
廣泛分布于江蘇南部寧鎮地區及其鄰近的皖南和浙皖交界地區的土墩墓,是商周時期江南地區特有的墓葬形式[1]。它們多處在平原高地或丘陵山崗之上,封土成墩。一個土墩內或不止一墓,各墓亦見有疊壓打破關系[2]。有些墓主與隨葬品等葬物直接置于地面之上,有的有石床石槨。其上堆積的饅頭狀土墩,多數不加夯筑。土墩墓營建之前的原始地面上,多可見墓地建筑。它與吳越文化密切相關,已在考古學界形成廣泛的共識,也被順理成章地稱為“吳越土墩墓”[3]。墓中隨葬品多以原始瓷器、陶器為主,少數高等級墓葬中則見有銅禮器及殉人。特別是寧鎮、皖南地區所見青銅禮器,絕大多數出自土墩墓中,且在出土青銅禮器的土墩墓的區域內,多存在屬于同一時期的聚落遺址或者城址,而有些土墩墓密集分布區卻從未發現過隨葬青銅禮器的土墩墓葬,附近卻發現有小型遺址、戰堡或銅礦遺址。鄒厚本先生曾就此指出墓主身份地位與就近遺址性質之間存在聯系[4]。青銅禮器是商周貴族社會政治、倫理、宗教等一切禮儀制度的器用標志。不同等級身份的貴族在不同的禮儀場合所使用的青銅禮器,在種類、數量上是有差別的,有一整套青銅禮器的組合使用方式,即為“器用”。“事死如事生”,青銅器亦是商周貴族墓葬中最普遍和主要的隨葬器物,成為判定墓葬等級和墓主身份族群的重要標準[5]。
通過考察墓葬中的銅器樣式及其銘文風格,推究器用組合的差異,原是分析中原地區商周墓葬中禮制系統的有效途徑。長期以來,學界對皖南及寧鎮等江南地區出土銅器,特別是周代銅器的討論,正是遵循此種辦法。學界研究取得了相當的成果[6],例如主要依靠形制與紋飾差別,基本分為三種[7],即與中原、關中地區形制、紋飾相似,但帶有部分地方特征的融合型[8],中原型以及帶有明顯地方特征的地方型[9]。正如吳越地區土墩墓是對應國別與族屬而言的那樣,張敏先生又將之分為吳器、越器和干器[10];陸勤毅、宮希成等先生則分為中原、融合、吳越、徐舒、楚等數種[11]。筆者近年來關注以“青銅器區位分析”來討論隨葬青銅禮器的器用組合,主要考慮位置關系所能探究的“組合”中的器物來源,以及二者的相互關系,并兼及時代、等級、性別、地域等不同因素所造成的器用現象差異[12]。隨著近年來考古新發現的不斷增多,在學界研究基礎上,持上述問題視角進一步討論吳越地區土墩墓隨葬銅禮器的器用組合諸方面,是否有可能促進江南地區周代銅禮器器用的研究,是筆者接下來擬作初步嘗試的。
二、寧鎮、皖南地區土墩墓葬的銅禮器器用
整個東南地區的土墩墓群,隨葬青銅禮器的周代墓葬主要分布于寧鎮地區,如江蘇丹徒煙墩山[13]、母子墩[14]、磨盤墩[15],溧水烏山[16]、寬廣墩[17],儀征破山口[18],南京浦口長子墓[19],高淳下大路[20]等;贛西北地區,如上饒馬鞍山[21];閩北地區,如浦城管九等[22]。由目前所見材料,上述墓葬似可分為兩組討論,首先是隨葬器物種類較少或原始墓葬已被破壞、組合不全的一組。隨葬器物組合可見單獨水器,酒、水器,單獨食器,食、酒器等,亦可見食、酒、水器三類齊全的,如寬廣墩報道有銅匜1件,馬鞍山出土盤1,磨盤墩隨葬尊1、匜1,浦城管九報道有尊、盤、杯等。單獨食器的如浦口長子出土鼎1、鬲3。高淳下大路出土有鼎2、尊1;破山口所出器物據統計有食器鼎、鬲、甗,酒器尊、瓿及水器盉、盤等,則分別是食、酒與食、酒、水器的組合。
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煙墩山、母子墩與溧水烏山等寧鎮地區第二組保存較完整的西周時期墓葬。依據原始瓷豆,4座墓葬的年代均相當于中原地區西周前期[23]。4座墓葬的具體年代,所出銅器亦提供了線索。學界初步認為溧水烏山M1稍早,約在西周康王、昭王時[24]。M2所出卣略顯垂腹(圖一︰1),估計年代在穆王前后。煙墩山所出宜侯夨簋,銘文提到武王、成王,可能是康王時所作。墓中所出鼎有立耳且下腹傾垂的(圖一︰2),應不早于昭王時,墓葬年代似在昭、穆王時。母子墩墓所出方座簋(M1︰30)腹部所飾對稱垂冠大鳥紋(圖一︰3),已具有穆王時器的特點,其墓葬年代當不早于穆王。除溧水烏山M1單出一鼎之外,煙墩山、母子墩與溧水烏山M2隨葬銅禮器均涵蓋食、酒、水三大器類。溧水烏山M2所出方鼎、卣、盤組合較簡單,朱鳳瀚先生已指出其形制均屬與中原地區相似但紋飾帶有地方特征的融合型器物。煙墩山與母子墩所出涵蓋融合型、中原型與地方型,且以地方型器物為主,諸家均已多次指出,此不贅述[25]。

圖一// 寧鎮地區土墩墓隨葬青銅禮器舉例
單就器用區位而言,前述磨盤墩尊1、匜1,高淳下大路所出鼎2、尊1在墓葬中均可見相鄰置放的器用現象。母子墩所出銅器,除去在發掘前被挖去的雙獸首耳簋(M1︰1),墓葬中銅器群亦聚置一處,兩件鼎(M1︰27、28)與方座簋(M1︰30)、雷紋鬲(M1︰29)相鄰;提梁卣(M1︰25)與雙耳壺(M1︰26)、尊(M1︰31)與鳥腹尊(M1︰32)分別相鄰,體現出與中原地區相近的食器鼎、簋、鬲,酒器卣、壺等組合器相鄰的特色。有學者指出,母子墩墓將青銅容器與兵器、車馬器、陶瓷器整齊分置于墓葬內的不同位置,表明了人們對不同質地的器物以及不同形制的青銅器具有更加明確的區別[26]。
上述器物亦被學者分為三種類型討論,如提梁卣是融合型,雙耳壺是地方型,方座簋為中原型,雷紋鬲為地方型,兩件鼎則為融合型。但是墓葬情境中,不同類型的器物卻是作為組合器相鄰置用的。這是否意味著,墓主人或者說器用者并不關心器物的來源,而更關注的是器物本身所構建的禮制形式呢?
在此基礎上就兩座墓葬器用組合整體而言,學界早有注意其隨葬禮器特別是用鼎的偶數,如煙墩山及其附葬坑各隨葬4鼎,母子墩隨葬2鼎。楊寶成等先生即曾特別指出,從禮器組合看銅器群中多見鼎簋共出,一鼎一簋、二鼎二簋、四鼎四簋等鼎簋同比的器用現象顯著[27]。可以補充的是,母子墩的二鼎二簋前文已述,就器用區位而言當為二鼎一簋一鬲的器用組合,是否可析分為一鼎一簋與一鼎一鬲,似尚需確證。煙墩山墓葬惜未見到明確的器物位置關系,但是其隨葬融合型器物有一鼎、一簋,一盂、二盤;地方型器物有二“越式鼎”、一鬲,一尊、二盉;中原型器物為一鼎、一宜侯夨簋;就此而言,似亦可視作一鼎一簋的組合。
尤需注意的是煙墩山兩件形制相近的越式鼎(圖二︰1),這種兩件形制相近的鼎組合使用,使人聯想到前述高淳下大路的兩件鼎,形制均為立耳外撇、折沿、淺腹、蹄足(圖一︰4)。由此分析,寧鎮地區銅器墓葬的偶數用鼎似可分為兩端:其一,墓葬整體器用組合中用鼎的偶數;其二,整體偶數下同形鼎的偶數。我們知道,目前所見最早的列鼎是陜西寶雞竹園溝M1甲所見5件圓鼎,墓葬年代約在西周穆王時[28]。煙墩山墓葬在昭、穆王時的年代與之相近,但是偶數用鼎與竹園溝的列鼎間似存在不小的差異。

圖二// 煙墩山與屯溪土墩墓的“越式鼎”
皖南地區著名的“屯溪八墓”中,除M7、M8以外,均隨葬有青銅禮器。其中M4、M6隨葬尊1,M2、M5隨葬尊1、折腹平底盂1,為基本的食、酒器組合。學者多已指出以尊為主的器用形式,與寧鎮地區存在緊密聯系。M1所出鼎4、簋2、尊2、卣2、盤2、盂1等器物中,盆形腹扁柱足圓鼎(M1︰79、82)、尊(M1︰89)、卣(M1︰93、94)及盤(M1︰84、85)為融合型;盤形腹鼎(M1︰80、81)、圓鼓腹雷紋簋(M1︰96)、橢圓形簋(M1︰83)、折腹圈足盂(M1︰95)帶有顯著地方特色;粗體觚形尊(M1︰90)為中原型器物。就器用區位來說,發掘者已經注意到雙卣(M1︰93、94)一盂(M1︰95)縱列在北,兩尊(M1︰89、90)與之相鄰斜置于西,兩盤(M1︰84、85)縱放在南,兩件“五柱器”(M1︰91、92)在中間的擺放情況,細察亦可發現,四鼎(M1︰79—82)橫排在東,融合型的扁柱足圓鼎(M1︰82)與地方型鼓腹雷紋簋(M1︰96)相鄰[29]。以上首先可見與寧鎮地區相同的器用形式,即不同類型銅器共同組合使用,其次鼎簋、尊卣組合器相鄰的置用關系與中原地區相近。
M3隨葬銅器種類在“屯溪八墓”最多,兩件長方形腹,分別作矮柱足(M3︰9)及蹄足(M3︰5)的方鼎;淺腹、三足微外撇,近于“越式鼎”的圓鼎(M3︰11);兩件形制近同,均作圓鼓腹、三足中段以下外侈的圓鼎(M3︰012-1、012-2,圖二︰3、4);圓鼓腹、矮圈足,有雙半環獸耳(M3︰03、04、06、10、23)、附耳(M3︰05)或無耳(M3︰1、055)的簋8;方鑒2(M3︰20、011)以及上腹有鏤空紋飾之盤1(M3︰43)等均帶有顯著地方特色,其中兩件有蓋、雙半環耳的簋(M3︰10、23),其腹部形制與同墓所出無耳圓鼓腹簋形制近同,只是更為寬扁,故應為簋而非發掘報告所稱之“盒”[30]。中原型器物僅有下部光素的垂腹卣1(M3︰08);融合型器物有觶(M3︰44)、腹蓋飾有羽冠相糾的對稱大鳥紋的公卣(M3︰07)以及上腹部飾有夔龍紋的盉(M3︰6)等。仍先就器用區位而言,據發掘報告,有明確位置關系的第一組銅器方盤(M3︰7)置于圓盤(M3︰8)內,簋(M3︰10)置于方鼎(M3︰9)內[31],是亦可見組合器鼎簋等相鄰的器用現象。
由上述,“屯溪八墓”與寧鎮地區墓葬在器用組合、器用現象等方面均存在明顯的共同點,如隨葬銅器種類較少的墓葬中,尊比較重要。多種類禮器墓葬中,隨葬銅禮器作為整個器群組合使用,鼎簋、尊卣等組合器物常見聚置。偶數用鼎的現象普遍,且均存在墓葬整體偶數用鼎與形制相近的偶數組合用鼎兩種情況。
此外,在器用形制上,如屯溪M3所出短足方鼎(M3︰9,圖三︰2),中腹部紋飾的情形與溧水烏山M2所出方鼎風格近似(圖三︰1)。扁圓鼓腹,矮圈足、雙半環獸耳的簋(M3︰03、04、06)與江蘇丹徒司徒鄉磚瓦廠窖藏所出簋形制相同[32]。M1所出盆形腹鼎(M1︰82,圖三︰3),已呈垂腹,近于西周銅器三期即穆王時期形制,所出卣(M1︰93,圖三︰4)飾有對稱的垂冠大鳥紋,亦是穆王時期流行的紋飾風格。發掘簡報即曾認為這批銅器年代相當于中原地區西周中期至晚期[33]。發掘報告依據M3、M4、M7、M8所出劍及M4、M7所出戈之形制,將“屯溪八墓”年代斷在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朱鳳瀚先生已指出從形制特征看銅器仍有歸屬西周之可能,并提出“屯溪八墓”年代是否同一尚需再考[34]。

圖三// 溧水烏山與屯溪土墩墓隨葬青銅禮器舉例
學者近來注意到“屯溪八墓”陶、瓷器與青銅器共存,相較于青銅器的斷代而言,陶、瓷器使用時間更短,其年代相對也更接近于墓葬的埋藏年代。而在所有原始瓷產品中,豆又是出土數量最多的器類之一,形態亦較多樣,有明晰的地層依據,具有分期意義。通過對屯溪八墓隨葬原始瓷豆的觀察推斷,屯溪M3年代約為西周早期偏晚至西周中期,M1年代約為西周中晚期,M4、M6、M5、M7、M2及M8年代約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35]。若所論不誤,循此則寧鎮地區、皖南地區在西周時期墓葬銅禮器器用中,食、酒、水的器用組合,鼎簋、尊卣組合器相鄰等均與中原地區器用形式存在密切聯系;不同的是尊更常見,且在高等級墓葬中亦存在偶數用鼎的情況,其淵源與流變是下文將要著力探究的。
三、偶數用鼎的淵源及其流變
寧鎮、皖南地區以尊常見、偶數用鼎的器用禮俗,在江北地區亦有發現。學者曾指出,寧鎮及皖南沿江地區風格青銅器,既與當地以陶鬲為特征的湖熟文化有關,同時又與江淮地區的青銅文化息息相通[36]。皖南地區有不少青銅器在器型與紋飾方面與江北的群舒器相近,學者早已注意到二者之間傳播與影響的關系[37]。這里仍可以從墓葬器用禮俗來補充。
西周春秋時期,安徽樅陽地處群舒腹地。有趣的是上述兩種偶數用鼎的情況,在樅陽西周墓葬中均有發現。其一,墓葬用鼎整體為偶數。1996年樅陽官橋鎮前程村墓葬即出土素面鼎1(ZW00983)、竊曲紋鼎 1(ZW00982)、弦紋爵 1(ZW00981)、觚形尊1(ZW00984),其中素面鼎形制與山東濟陽劉臺子M3出土王季鼎相近,竊曲紋鼎的紋飾可與1964年張家坡西周墓地所出6號鼎相較,器物年代在西周中期至西周晚期。該墓即為鼎2、尊1、爵1的組合,偶數用鼎、鼎尊基本組合的器用禮俗顯明。
其二,同形鼎的偶數組合。1992年樅陽橫埠鎮官塘村墓葬出土重環紋鼎2(ZW00950、ZW00951),獸面紋尊1(ZW00952)。兩件重環紋鼎器型基本相同(圖四),與魯故城M48︰18、曲阜魯仲齊鼎相近,器身與莒縣西大莊所出3件列鼎近似,惟西大莊鼎的蹄足更為明顯。獸面紋尊(圖五︰1)形制近似屯溪M1︰90尊(圖五︰2),獸面紋、鳥紋與夔紋的組合亦近于葉家山M1︰019尊(圖五︰3),年代似應在西周早期。這種西周早期的尊與西周晚期的鼎組合的情況,在寧鎮、皖南地區常見,顯示出本地族群對青銅尊這一酒器的特殊偏愛。重要的是,該墓兩件同形鼎配一尊的組合,正合乎前文總結的偶數用鼎的第二種情形。

圖四// 樅陽橫埠鎮官塘村墓葬出土重環紋鼎1.ZW00950 2.ZW00951

圖五// 獸面紋尊比較
不惟西周,樅陽地區春秋早期墓葬中亦可見偶數用鼎的情形。1987年樅陽金社鄉楊市村來龍崗墓葬出土變形蟬紋鼎2(ZW00954、ZW00955,圖六),龍鋬匜1(ZW00953)。墓中所出鼓腹圜底三蹄足形制的鼎,為中原地區兩周之際常見的器型,裝飾凹點紋、變體蟬紋及腹部的扉棱,多具地方特色。春秋中期的安徽懷寧人形河所出云紋鼎,形制與其相同,下腹亦有變體蟬紋,惟上腹云紋與凹點紋不同。這種青銅鼎應是仿照中原西周晚期流行的器型,而在春秋早期發展成熟,在江淮地區形成地方特色,并可向南影響皖南、寧鎮等地區。龍鋬匜多出現在江北地區,形制深受中原地區影響,丹徒磨盤墩、棗莊東江春秋墓M2所出青銅匜,與之形制接近。由此,該墓年代應在春秋早期[38]。值得注意的是,該墓所出兩件變形蟬紋鼎不僅形制相近、大小紋飾均基本相同,屬于典型的偶數同形鼎。

圖六// 樅陽金社鄉楊市村來龍崗墓葬出土變形蟬紋鼎1.ZW00954 2.ZW00955
目前樅陽5座出土銅器墓葬中,除1987年湯家墩遺址出有方彝1、1985年浮山鎮會圣村出土雷紋鼎1以外,上述3座西周春秋時期墓葬,均使用偶數用鼎的器用禮俗。由樅陽3座墓葬聯系寧鎮、皖南地區所見,這種隨葬銅器中偶數用鼎的器用禮俗,早期墓葬中的用鼎數量若大于兩件,即4件以上時,一般會有兩件形制相近同;其發展趨勢似為形制不同的偶數,漸變為形制相同的偶數用鼎,以至于形制、紋飾、大小均近同的偶數用同形鼎。
樅陽所在的江淮地區地處淮夷腹地,淮夷與東夷聯系密切,因居住在淮水流域而得名。東夷是居住在東方的古老部族,其活動范圍大致從山東黃河下游地區直到江淮流域的近海地區。東夷、淮夷長期與中原王朝共存,文獻中“紂克東夷隕其身”的記述,眾所周知。學者研究發現,與夏代東夷族有關的岳石文化因素,在被稱作夏代淮夷文化的斗雞臺文化,特別是是斗雞臺二、三期,有較多發現[39],這顯然與來自魯南的東夷人群有關。進入商代,仍有相當數量的東夷向淮河流域遷徙。商周之際,因周公東征的討伐、魯公伯禽的逼迫,東夷人群繼續向南遷徙,分散到今天淮河流域。南遷之后的東夷、淮夷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再次糾合淮河流域大小族群,發動對周人的反叛[40]。金文中亦常見西周王朝對淮夷、南淮夷的征伐戰事,特別是西周中晚期淮夷實力強盛,對周王朝時叛時服,成為西周王朝的心腹大患[41]。
循著上述討論,目前所見山東地區西周時期銅器墓葬中,西周早期墓葬滕州前掌大M11隨葬鼎為偶數,8件鼎有方鼎2、大圓鼎1、小圓鼎1、扁足圓鼎2、分襠鼎2,其中兩件方鼎(M11︰82、92)形制、紋飾、大小近同;兩件分襠鼎(M11︰88、89)形制、紋飾近同,大小略有區別,一件通高22.4厘米,另一件22厘米;兩件扁足圓鼎(M11︰80、85)與分襠鼎情況相同,一件通高21厘米,另一件通高19.8厘米[42]。同形的偶數方鼎使用,商代即已盛行,馬承源先生指出偶數方鼎的器用似是常制,單個的反而可能是流散之器[43]。加之前掌大商代晚期墓葬M38所出鼎卻為3件,是故不能遽爾認定前掌大亦有偶數用鼎之禮俗,畢竟西周早期的用鼎禮俗未見確立用鼎數量之定規。
西周中期的山東高青陳莊墓地,M35隨葬銅器種類組合有銅鼎、簋、壺各兩件,盤、匜各一件;M36有銅盨、方壺各兩件[44]。盨、盤、匜均是西周厲王時期流行及確立的器物,故其墓葬年代在西周晚期前后,鼎、簋、盨等似亦為偶數同形。西周中晚期近海的煙臺、威海等地墓葬中可見偶數用鼎之情形。1969年煙臺上夼村紀國墓葬出土鼎2、壺2、匜1,?侯鼎與己華父鼎形制相同,紋飾、大小及銘文有差別[45]。1974年山東萊陽中荊鄉前河前村亦出土紀國銅器,有鼎2、甗1、壺2與盤、匜各1。弦紋鼎與重環紋鼎同樣形制相同,紋飾、大小有差[46]。上述墓葬年代均在西周晚期。1965年山東黃縣歸城曹家村南西周中期偏晚墓葬M1出土鼎2、甗1、爵1、尊1、卣1、壺1,兩件鼎皆垂腹柱足方唇,腹部一深一淺[47]。另一座西周中晚期之際的墓葬是1977年威海環翠區田村鎮西河北村M1,有鼎2、甗1、壺1、鐃1,兩件鼎形制相同[48]。
由上述,目前似尚不能明確山東沿海地區周代墓葬中偶數用鼎的禮俗中存在偶數同形鼎的情況。前掌大、高青陳莊以及煙臺等地紀國墓地的族屬似均與東夷贏姓、偃姓族群無涉,惟高青陳莊等地所見情形值得留意。高青陳莊遺址與齊國貴族有關,若偶數用鼎為東夷、淮夷族群之顯著特征,《史記·齊太公世家》曾明記:“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如此則姜姓的齊國、紀國在器用禮俗中是否“因其俗,簡其禮”,即受到偶數用鼎的影響,值得進一步探究。
時代陵替,若把目光放在春秋早期,中原地區如三門峽虢國墓地、天馬—曲村晉國墓地所見,自西周晚期列鼎制度已然明確,而上述樅陽地區所見偶數同形用鼎的禮俗并非單一,似已在皖南、皖北乃至江淮到山東沿海地區的東夷、淮夷族群中得到較大范圍的普及。
山東地區的偶數同形鼎主要見于東夷族群的郳(小邾)國、邿國、萊國、鄅國等。2002年6月發掘山東棗莊東江村東南高土臺墓葬,保存完好的M2、M3墓葬中所出器物以同形為最常見現象,M2即有平蓋竊曲紋鼎4,與郳慶鬲4、簠4組成四鼎四鬲四簠的組合[49]。邿國墓地1995年發現于濟南長清仙人臺遺址,共發現6座墓葬,均為西北向長方形豎穴土坑墓。簡報主要介紹了M3與M6,其中M3年代屬于春秋初期,墓室面積約11.9平方米,隨葬器物在槨室北部二層臺的邊箱內,為食器二鼎二簠組合,兩鼎大小相次,形制、紋飾一致。同屬春秋早期的M6亦用八鼎八簋等量偶數數量配比組合[50]。1963年山東泰安肥城小王莊出土一組青銅器,器用組合為竊曲紋鼎2、睽士父鬲2、象首紋簠2、陳侯壺2、魚龍紋盤1、象首紋匜1;此外尚有穿帶小壺形器1、勺2[51]。其中簠、匜的形制似已晚到春秋早期偏晚,同樣使用二鼎二鬲二簠偶數同形的器用禮俗。1976年山東日照崮河崖春秋早期萊國墓葬M1,器用組合為鼎4、鬲4、壺2、蓋盆2、盤1、匜1。墓中所出龍紋盤(M1︰13)形制、紋飾與儀征破山口龍紋盤相近,反映出東夷與吳越的器用文化淵源。上述4鼎中,兩件帶鈕平蓋大鼎、兩件鼓腹小鼎,兩兩形制、大小近同[52],四鬲兩壺兩盆均為同形器,是亦為二大鼎二小鼎四鬲兩壺兩蓋盆的偶數同形的器用形式。臨沂鳳凰嶺春秋晚期鄅國墓葬,墓室中有殉人且在器物坑內隨葬的6件銅鼎,亦是形制相近,大小相同[53]。
皖南地區1979年的繁昌縣城關湯家山山頂墓,器物組合為鼎6、盤形簋1、甗1、盤1、管狀流罐形腹盉1[54],盤形簋在吳國中心區域或鄰近的江蘇丹陽、無錫等地區常見;而管狀流罐形腹盉則屬皖南地區獨有之風格。6件鼎中分別有兩件方鼎(圖七︰1)、兩件立耳淺半球形腹圓鼎(圖七︰2)、兩件附耳罐形腹鼎(圖七︰3),為偶數用鼎。

圖七// 繁昌縣城關湯家山山頂墓隨葬偶數鼎
肥西縣紅衛鄉柿樹崗村小八里出土的一組銅器,亦可見此種器用禮俗的延續。墓葬組合為鼎2、簋1、甗形盉1、盤1、匜1及四環小方盒1[55],同出瓦紋蓋圓鼓腹簋,小雙半環耳,年代可能早到春秋中期偏早,兩件鼎偶數同形(圖八)。甗形盉形近于河南光山寶相寺上官崗磚瓦廠黃君孟夫婦合葬墓出土之甗形盉G2︰A6(圖九),年代約在春秋中期偏早。春秋初期的黃君孟夫婦合葬墓,G1即黃君墓出鼎2、豆2、壺2、罍2、盤1、匜1,G2即黃夫人孟姬墓出鼎2(圖一〇)、鬲2、豆2、壺2、罍2、盉2、甗形盉1、罐1、盤1、匜1等[56],黃君墓所出兩件銅鼎亦為偶數同形的用鼎形式。黃、羕與樊同為嬴姓,均是淮水流域的淮夷小國,亦普見偶數同形的用鼎情況。1964年,河南桐柏縣月河鎮左莊村發現一組春秋早期銅器,組合為鼎、罍、盤、匜各一。其中罍、盤、匜有銘文,作器者為羕伯庸。此外,1993—1994、2001—2002在左莊村北發掘東周墓葬26座,出土大量羕伯器物[57]。特別是春秋初期的M4與M22,均隨葬有偶數同形鼎,兩座墓葬的4件鼎形制、大小基本相同(圖一一),惟M4︰6、7鼎耳部飾虺龍紋,M22︰3、4鼎耳部飾重環紋,腹部均飾蟠虺紋、凸弦紋各一周。1978年,河南信陽平橋發現了春秋早期晚段的樊君夔及其夫人龍贏的同穴合葬墓,樊君夔隨葬銅立耳無蓋鼎2、簠2,壺2,盤1、匜1[58],兩件立耳無蓋鼎形制相同,亦同屬偶數用鼎的情況。

圖八// 肥西縣紅衛鄉柿樹崗村小八里出土偶數同形鼎

圖九// 肥西小八里與光山寶相寺黃君孟夫婦墓的甗形盉

圖一〇// 光山寶相寺黃夫人孟姬墓出土偶數同形鼎

圖一一// 桐柏縣月河鎮左莊村羕國墓葬出土偶數同形鼎
據近年研究發現,東夷族群特別是商末周初的東夷族群,與殷人關系密切[59],應屬廣義之殷遺民范疇,如羕、黃即均為嬴姓。商人與東夷的關系值得深入思考。偶數用鼎的起源,殷遺民墓葬隨葬器物如陶器的“偶數同形”現象,近來亦因周原遺址姚家墓地的發現,為雷興山先生等所揭橥[60],學者亦曾注意到“偶數配列”是殷墟青銅禮器組合的基本形式[61]。當然,“偶數同形”究竟源出殷人、東夷還是吳越族群,尚需進一步討論。偶數用鼎的器用禮俗影響深遠,淮水流域的器用禮俗與漢水流域堅持周制不同,這種禮制上的二元性正是此后楚國特殊禮器制度的源頭[62],學界亦早已注意到東周時期偶鼎制度在南方楚國、齊魯地區的廣泛流行[63]。鐘離君柏墓所出5件銅鼎,3件立耳無蓋鼎屬于典型周制列鼎,兩件有蓋深腹鼎為偶數同形鼎[64],是其分屬不同的禮器器用體系,且各自遵循完全有別的奇、偶數禮制規范。學者已指出,這種彌合兩套器用禮俗的情況是春秋中晚期普遍的禮制實踐現象,代表了東周以降新的禮器使用方式[65]。偶鼎的生命力亦借以延續,降至戰國時期,楚國墓葬如包山二號墓中還有“二鑊鼎、二鐈鼎、二羞鼎、二铏鼎、二升鼎”的偶數器用組合。可見此種器用特征,似表現出“周人”共同體內各族群仍在一定時段和地域內保存有某些自己獨立的文化因素,并由此可以通過在同一墓群中共存的不同文化因素,看到當時族群相互融合的趨勢。
由上述,寧鎮、皖南地區土墩墓葬偶數用鼎的器用禮俗,在傳統認識上之淮夷、東夷的皖北、豫南、山東黃河下游以至近海地區可發現其淵源與流變。至晚在春秋初期,上述廣袤地域中偶數同形鼎的普及與中原地區已普遍遵行的奇偶配比的列鼎制度并行不替、迥然有別,顯示出對“周禮”即周人用鼎制度的膺服下,地方族群器用禮俗的獨立性。
四、小結
土墩墓是周代江南地區典型墓葬遺存,高等級墓葬中所隨葬之青銅容禮器,長久即受到學界廣泛關注,以上在學界銅器文化因素分析基礎上,采用“區位分析”法回溯墓葬器用情境,似可發現寧鎮、皖南、江淮上溯山東沿海地區墓葬青銅器用之偶數用鼎,似乎存在墓葬整體偶數用鼎與偶數同形鼎兩種情況,而后者伴隨中原地區列鼎、同形簋奇偶配比器用禮俗的確定,在春秋初期即在上述地區普遍流行,形成與中原地區的“周制”并行有異的另一種“復古式”的用鼎禮俗。中原、吳越、淮夷諸種文化在寧鎮、皖南地區的交融激蕩,揭示出春秋以后諸侯國族在青銅器用文化層面的交融互攝,并最終凝聚成華夏族群的動態歷史過程。
(附記:本文承蒙朱鳳瀚、劉緒與雷興山三位先生指點,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