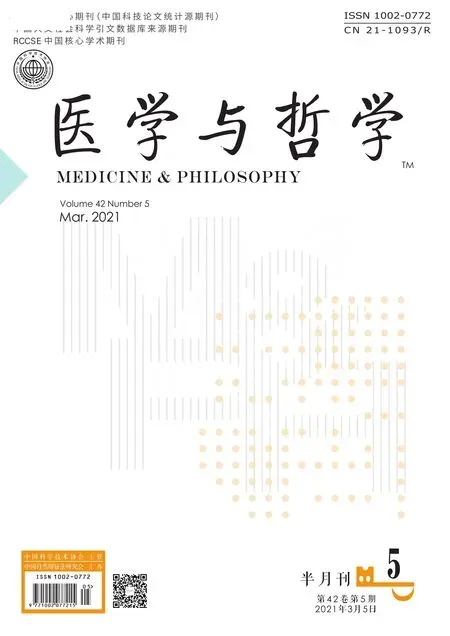清末東北鼠疫鐵路防疫中的等級與階層
袁海燕 陳 琦
近代中國內憂外患,災疫頻發,社會動蕩加劇。全國多處曾不同程度地流行過霍亂、天花和鼠疫等烈性傳染病。以鼠疫為例,較為嚴重的就有1894年港穗鼠疫、1899年營口鼠疫、1910年清末東北鼠疫、1917年山西綏遠鼠疫等。在這些疫病的防治過程中,中國近代公共衛生制度和傳染病防治措施逐漸建立起來。其中,在1910年10月~1911年4月流行的清末東北鼠疫,是20世紀最嚴重的肺鼠疫大流行,死亡總人數高達9萬余人[1]272-273。在這次疫情中,中國政府第一次采取了有組織的現代醫學防疫措施,成為中國公共衛生事業的新起點[1]271。
鐵路作為近代新興事業在提供便利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形成的交通運輸網絡也加速了疫病的傳播[2]。鐵路的運營會出現人群聚集并加速人口流動,導致疫病沿鐵路線快速蔓延,從而造成嚴重后果。在此次東北鼠疫防疫過程中,通過鐵路管制措施有效地縮小了傳染范圍,控制了鼠疫的擴散蔓延,為切斷傳播途徑提供了保障。
1 清末東北鐵路等級車廂設置
東北鐵路是近代中國較為完善發達的鐵路線,在1910年東北鼠疫暴發之時,鐵路已成為東北地區最重要的交通方式,其防疫工作對于控制鼠疫的傳播速度及蔓延范圍舉足輕重。自1897年修筑東清鐵路開始,至1910年,東北地區已建成全長3 124.1公里的網狀鐵路體系,包括東清、南滿、京奉和安奉四條鐵路。但清政府控制的只有京奉鐵路,其他鐵路皆由日、俄兩國管轄[3]。為了適應不同經濟基礎民眾的需要,火車根據車廂配置分為頭等車和二、三、四等車,并施行階梯式購票方式。車廂等級不同意味著車中設備與乘坐人員社會身份、地位的不同。頭等車多是外國人與中國官吏乘坐,配置齊全,裝修精美,票價也最高;二等車條件較差,票價適中;而三等車、四等車主要是針對社會貧苦底層設置的,基礎設施尤其簡陋,票價最低[4]。
中國早期鐵路的旅客車廂里,三、四等車廂各項設備都非常匱乏,車廂內人多混雜、人流擁擠,衛生污穢不堪,環境極其惡劣。東清和南滿等車廂“僅左右兩面上部各有縱橫一尺之窗可以啟閉而通空氣。最可深惡痛絕者則為關內外,其車中無一坐凳,客人多以地毯或毛被等鋪于板上僵臥,一人足占四人之位,及經過大站則旅客涌來,眾皆鴿立,其人數嘗倍于所定之額,致蹂躪行李,擠傷老弱,臭氣充溢,呼吸不靈”[5]18。三等車廂廁所內僅置廁桶1個,設備簡陋且洗掃常常草草了事[6]21。“關內外(鐵路)三等車常以三輛(車廂)合一大小便處,最狹稍肥胖者則不得其門而入,且穢臭難堪,一入其中遺矢滿地,全身為之骯臟,加以貨物腐積,客人狼藉帶臭而出,全車風靡。”[5]19可想而知,在這種人口密集、骯臟不堪、空氣不流通的環境中疫病極易傳播擴散。
2 清末東北鼠疫的鐵路管制
2.1 清廷鐵路防疫措施的提出
隨著疫情愈發嚴峻,“勢頗猖獗, 有向南蔓延之勢”[7]。駐京各國公使頗為恐慌,他們不相信中國能阻止鼠疫蔓延,不斷向清政府施壓。而早已盤踞東北的日俄則想趁此機會介入中國的衛生行政,擴大自己的控制范圍。面對主權和國際壓力,清政府將疫情控制作為外交事件全力應對,開展防疫工作。從中央到地方組建各級防疫組織,與日俄等國建立防疫合作關系,采取消毒、隔離、檢疫等措施并頒布防疫章程[7]。吉林西南路兵備道李澍恩速派醫生實施入境人員檢疫,查驗東清、南滿車站入境的中國人。1910年12月,吉林西北路兵備道于駟興在濱江廳地方成立防疫局,對傅家甸“嚴絕交通,厲行隔離”[8]8186。1910年12月末疫情甚盛,伍連德被任命為哈爾濱防疫總醫官到哈爾濱主持防疫工作。伍連德奔赴疫區后進行實地調查,通過尸體解剖、涂片鏡檢及細菌培養等實驗室研究,證實了此次流行的鼠疫是肺鼠疫(肺炎疫),幾乎完全是由人到人傳播感染的[9]14-15。1911年1月2日,法國醫師(北洋醫學堂首席教授)梅聶趕赴哈爾濱參與防疫工作,憑借其防治腺鼠疫的經歷,認為此次鼠疫亦為腺鼠疫。1月5日,梅聶到俄國傳染病房檢查病人,雖戴了手套以免直接接觸病人,但并未佩戴口罩。6天后梅聶因感染鼠疫去世,側面驗證了此次鼠疫是通過空氣傳播的[9]10-26。
伍連德得出此次鼠疫是通過空氣傳播的結論后,果斷提出了包括鐵路交通管制在內的防疫計劃,上報朝廷建議“西伯利亞邊境滿洲里和哈爾濱之間的鐵路交通必須嚴格管制,并且邀請俄羅斯當局與中國政府在實施有關措施中進行合作”;同時,需要積極“尋求與日本南滿鐵路當局合作”;“(華北)京奉鐵路沿線的衛生狀況也必須密切關注,一旦有鼠疫病例出現,必須采取嚴格的防疫措施”[9]16。情勢緊迫,郵傳部迅速下達指令要求東三省地區實行交通管制,限制人員流動,將染疫者與無疫者進行隔離,從而達到遏制鼠疫蔓延,繼而清除鼠疫的目的。1911年1月13日,郵傳部欽奉設局嚴防毋任傳染內地之旨,特派醫官徐鏡清等分赴京奉鐵路(北京-沈陽)榆關、溝幫子等山海關一帶,在火車站設立檢疫公所,切實查驗,無病方準上車[10]3。
2.2 各社會階層鼠疫感染情況
雖然疫病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其流行受到多種因素影響,除氣候、地理、嚙齒動物數量等自然因素外,也會受生活習俗、社會地位、職業等社會因素所制約。在此次鼠疫流行中,不同的社會階層在染病率上顯示出了極大的差異。根據全紹清醫生在奉天萬國鼠疫國際研討會上所作報告《從傅家甸的統計數字中得出的某些結論》,可知“較低和較貧窮的階層似乎更易于感染鼠疫”,“雖然沒有一個階層是免疫的,但比較貧窮的勞動者似乎更易于感染”[11]286。日本細菌學家北里柴三郎也認為此次鼠疫中苦力是最易感染鼠疫的群體[12]。貧窮階層之所以成為此次鼠疫感染的主要人群,主要和他們的生活條件和職業有關。
貧窮階層以農民和苦力為主。當地農民經濟條件差,生活節儉。苦力大多是關內的農民,他們遠赴關外謀生,主要寄宿于簡陋的客棧,居住環境惡劣;冬天擠在一張大炕上吃飯、睡覺,門窗緊閉,通風不暢,衛生條件非常差[7]。農民、苦力大多從事艱辛的下等職業,缺乏營養,對疾病的抵抗力較低,生病時常不就醫或者用民間偏方[13]。根據《東三省疫事報告書》中奉天省各府系染疫死亡人數職業比較表,可見死亡數與職業相關性強,苦力、農民占了死亡總數的一半多,“以職業論苦力及農民斃者最多,上級社會者最少”[14]。見表1、圖1。

表1 清末東北鼠疫中奉天省染疫死亡人數職業比較

圖1 清末東北鼠疫中奉天省染疫死亡人數職業比較
2.3 按車廂等級停售火車票措施
年關將至,苦力成批返鄉,流動性非常強,一旦染疫,疫情就會沿著鐵路線迅速傳播。“乘火車從北部而來的苦力不受任何防疫上的阻礙和限制繼續涌入奉天”,“奉天的鼠疫死亡病例多數都是乘火車從北部疫區而來”,“每天約有1 000名苦力乘火車從北部疫區來到奉天,其中很多人轉成中國人管理的京奉鐵路繼續南下”[11]516-517。面對疫情可能傳入直隸中央的威脅以及外人日漸緊迫的干涉,如何限制苦力們的流動成為當務之急。
苦力們主要乘坐的是三四等車廂,因此在鐵路防疫中采取了按車廂等級停售火車票的措施。1911年1月14日,外務部、郵傳部商定,停售京奉火車(奉天至關內火車)二、三等車票,“因乘三等車者,多系苦力,尤易傳染時疫”[15]。頭等車廂乘客,則需在山海關外停留五日[10]30。這種按等級停售火車票的措施隱含著對社會階層的差別對待,反映了中國當時陳舊固封的階級觀念。即使在后來疫情明顯緩解后,出入關留驗辦法對不同車廂乘客的規定依然是有區別的,頭等車客在查驗后可以買票,而二、三等客則需要在關留驗五日,有醫生驗單后才準搭車[10]16。
3 中方同日俄關于鐵路防疫的交涉
鐵路防疫是控制鼠疫傳播的重要途徑之一,然而清政府只有京奉鐵路的管轄權,如果日俄控制的南滿、東清兩鐵路不同時采取措施,仍難達到遏制鼠疫擴散的目的[16]121。“此次疫癥,因東清、南滿火車往來,蔓延甚速。”[8]8186有鑒于此,清政府同日俄鐵路局溝通交涉,希望他們也迅速采取停售等級車廂車票和檢疫查驗等手段,阻止疑似攜帶鼠疫的苦力入關。然而日俄以利相計,直到1911年1月中旬“始見停賣三四等票,是時已蔓延不可收拾矣”[10]2。
3.1 俄方采取的鐵路防疫措施
早在疫情之初,俄方為了防止鼠疫在本國境內的蔓延,就采取了驅逐華工并禁止華人入俄的措施。1910年9月,鼠疫暴發初至滿洲里,2名中國人從俄國返回滿洲里染疫身亡后,東清鐵路公司(中東鐵路管理局)立即“特派醫生將華人挨次察驗,其有氣色可疑者約三百余人,一律用火車轉送出境”[6]101。1910年10月,滿洲里地區暴發鼠疫后,東清鐵路停開南下火車五日,華人驗明無病后也只準乘坐貨車廂而禁止進入客房[17]。同時,俄方采取停售樞紐站烏蘇里站火車票的措施,以防止鼠疫向西蔓延至西伯利亞俄羅斯境內。11月23日,禁止華人從滿洲里進入俄境,聲稱“滿洲里一日瘟疫不除,一日不令華人入阿穆爾境”[18]。
然而當鼠疫逐步在中國境內蔓延時,俄方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并未主動采取停運所轄鐵路的措施。東清鐵路公司以“俄國新年,停辦公事”為由,遲遲未停駛火車。1911年1月7日,俄國鐵路管理局總辦霍爾瓦特將軍議定了關于哈爾濱火車檢疫辦法3條,規定哈爾濱車站由中國派醫生到站查驗。然而疫情有加無已,外務部電飭吉林東北路兵備道速與東清鐵路局商明停售火車票。經中方不斷努力溝通,東清鐵路公司才迫于清政府和社會輿論的壓力實行了等級車廂停運的措施。1911年1月20日,俄官開具東清鐵路哈爾濱往來長春等地三、四等車廂停售辦法五條,哈爾濱往來長春、五站、滿洲里三四等車廂均于19日一律停票;其頭等、二等車廂,非經官場及鐵路公司介紹持有特別執照,不準搭車不載華人[10]5。同時,附上了限制疫病傳染規條8條,對華工乘車、限制出入地區、留驗時間、呈驗護照等都有明確的行文規定[10]6-7。
但是俄方表面妥協,實則頭等車廂票價昂貴,二、三等車票不僅未停售且價格高漲。《申報》評論道其“以利所在,不肯停車,嗣以迫于公論,陽為停駛二、三等客車,實在并非停止,不過將二、三等車加價,反得藉此漁利”[19]。在謀利的同時,試圖趁機竊取對中國東北地區鐵路更多的掌控權。并且,俄方的很多措施對華人有歧視性規定。華人乘車要按所購車票降低一檔乘坐,“華人須較外人降下一等,買頭等票則坐二等車,買二等票則坐三等車,并將素不坐客之貨車亦裝載華人,其車位距月臺四尺余高,不設梯階,其車中之污穢惡臭及空氣之閉塞較我國下等人戶之家尤甚”[19]。
3.2 日方采取的鐵路防疫措施
日方對火車檢疫較為重視,1910年11月25日開始在南滿鐵路實行防疫。起初是在火車車廂內實行檢疫,在長春、奉天、瓦房店站配置醫生。1911年1月5日,自在大連發現第一例鼠疫患者后,滿鐵檢疫由車內檢疫改為停車站檢疫,并由警察陪同。自1月8日起,滿鐵開始在旅順、大連、瓦房店、大石橋、營口、遼陽、奉天、鐵嶺、公主嶺、長春等地停車站陸續實施檢疫[20]149-152。
但是對于停售車票事宜,日方一直猶豫不決。因疫勢日盛,南滿鐵路公司決定,自1911年1月14日起停售由奉天開往撫順以及由長春開往雙廟子的三等車票[21],二等車票于20日停售[10]5。1月16日,在安奉(安東—沈陽)線上,“安奉鐵路巡警局總辦廖成章以疫勢東播,安奉路線岌岌可虞,稟請先行派巡警二名協同日本巡警隊于上下車時逐加檢驗”[10]20。24日,興鳳道趙臣翼以安東為東部地區出入必經關口,安奉鐵路并未停駛,鼠疫流行形勢日益逼近,遂同安東縣稅務司等,與日本鐵路各員籌議安奉鐵道檢疫事宜,議定每日火車到站,日本乘客統由七道溝市場內安東站下車,檢疫事宜歸日本自行處置;中國乘客統由沙河站下車,由中國官吏派診察員在車站檢驗[10]23。并頒布專行于中國乘客的檢查法,隔離所留驗人員處置辦法10條[10]23-25。但此時,安奉鐵路行駛如常,清政府一再請日方領事轉告南滿鐵道會社望其可予以停售,最終奉天至本溪的平等車于26日停載,但本溪以南通行如故[10]25。2月28日,日方宣告停售安奉全線平等車票;其特等客,需驗明后方準乘車[10]25。
日方試圖借疫情防治介入中國的衛生行政,從而增強自己對中國東北地區的控制力,向清政府提出了召開日清共同防疫會議的要求[8]8193。1911年2月11日,關東都督大島義昌同東三省總督錫良在奉天首次會晤,雙方展開交涉。自2月28日至4月14日,每周舉行一次,共召開八次。其中3月3日召開的第二次會議中,討論了將大豆等物從中國內地運輸到滿鐵各站之時,須在離各站及市區略遠處的適當場所更換車輛及苦力,如果難以更換,須對車輛及苦力進行嚴格的消毒;對持有中方證明或火車站檢疫醫生給予證明的乘客,允許其乘坐滿鐵車輛;而乘坐一等至三等車的普通乘客,須在收容所里停留七天才被允許乘車。3月11日的第三次會議上,中方提議,要求不區別地對待滿鐵一等車廂的中外乘客。3月18日,在第四次會議中,日方同意了中方要求,將于19日起滿鐵一等車廂實行“混乘”[10]14-20。
綜上,可見日俄皆明了交通阻斷對疫情防控的重要性。然而,出于自身利益需要,起初并不愿停售車票以阻止疫情的發展。即便后來在中方的再三斡旋后予以了配合,在具體措施中仍然是中外有別,對華人乘客有一定的歧視性,不過滿鐵最終同意平等對待一等車廂的中外乘客。對于不同社會階層,日俄則跟中方一樣采取了按車廂等級區別對待的措施。
4 按車廂等級停售火車票的影響
按車廂等級停售火車票的本意是對不同社會階層人士的流動進行區別管制,阻止苦力們乘車以防疫情擴散,但實際效果并不盡如人意,引發了一系列問題。
4.1 苦力對等級車廂停運的應對
因火車站對于社會階層的區分并無確切標準,主要是根據乘客的面容和衣著來判斷,從而給蒙混過關者留下了一個缺口。為了返鄉,很多苦力情愿花重金購買華麗服飾以乘坐一等車。“當阻止苦力回家的命令下達的時候,山東的苦力開始乘坐一等車廂。”[11]369其他承擔不起一等車廂的大量苦力則選擇步行返鄉,造成鼠疫更大范圍地擴散和蔓延。“然苦工等因不能坐車均沿鐵路徒步南行分往范家屯、公主嶺地方者為數甚多。”[22]“該疫不但在沿線各地猖獗可畏,刻已傳播各村莊。”[23]鼠疫從鐵路沿線開始向內陸擴展。見此情形,東三省總督錫良不得不派軍隊把守各路口以阻止苦力南下。
4.2 關內外鐵路交通的阻斷
由于哈爾濱防疫失利,東三省各疫區疫勢不減,死亡人數劇增,僅停止售賣二、三等車票已不能阻止鼠疫的蔓延。京奉鐵路局斷然采取停運京奉鐵路所有客車及貨車的措施,“以鼠疫蔓延迅速,禁載二、三等坐客恐不足以資預防,即將所有客車及貨車于十五日起,一律禁止搭運,以免貽誤”[24]。但錫良對完全停運火車的舉措表示異議,致電外務部指出,京奉鐵路與西伯利亞大鐵路相通,若停售頭等票,將斷絕與世界交通,應當恢復頭等車,留驗后放行[25]。然而北京和天津已于1月中上旬就出現了鼠疫病例,一時間人心惶惶。1月21日,宣統帝下旨:“東三省鼠疫盛行,現在各處嚴防,毋令傳染關內。著外務部、民政部、郵傳部隨時會商,認真籌辦,切實稽查。天津一帶,如有傳染情形,即將京津火車一律停止,免致蔓延”[8]8183。在此情形下,不僅京奉路線頭等車尚未恢復運行,“天津電車與京津之火車,亦擬停止矣”[26]。
4.3 恢復頭等車廂售票,加大檢疫力度
可是隔絕交通并非長久之法,“道路交通如人身之血脈,一或壅滯,百病發生”[10]3-4。1911年2月5日,盛宣懷在致錫良的電文中指出,“外國防疫重在留驗,本不斷絕交通。現在我車一律飭停,系北洋奏準,無如東清、南滿仍未停駛,秦皇島輪船往來更多,各國亦催開車承接”[27]。因京奉鐵路的全部停運,導致大量苦力滯留關外,情緒焦慮,謠言四起,滋生事端。此外,清政府在財務和外交上也面對著很大的壓力,不得不調整鐵路防疫方式。截至1911年2月22日,京奉鐵路“因防鼠疫停售西往車票,路局損失不啻三百萬”[28]。3月7日,郵傳部奏請京奉重新通車,在奏折中陳述道“自京奉火車停駛已近兩月,僅就路利而言,所失殆逾百萬。提還洋債本利,益苦不支。國家稅項、人民商業所被損害,于國計民生,兩有關系。現在檢疫機關漸臻完備,自應嚴飭在事人等分任責成,切實辦理”[8]8195。為緩解各方壓力,清政府權衡再三后開始恢復京奉鐵路頭車售票。
在恢復頭等火車運行的同時,為防止鼠疫繼續蔓延,檢疫留驗制度也更為嚴苛,以保障防疫工作的有序進行。在交通要道增設隔離檢疫所,擴充留驗往來乘客,并分派醫員隨車查驗,列車分段節節查驗。郵傳部專門負責車上驗疫工作,聘請專科洋醫及各醫院西學醫生,分派京奉、京漢兩路,隨車查驗。如發現有疫病,立即送各該地方醫院隔離診治;若在沿途車站發現有疫病,將停售車票,只裝貨物[8]8195。奉天和直隸兩省加大力度設立留驗所。北京地界,由民政部督率防疫局員,診驗兼施[8]8195。京漢一路,也相繼采取鐵路管制措施,湖廣總督兼湖北巡撫瑞澂于漢口大智門及廣水兩車站附近設立防疫所,并建立兩所臨時傳染病防治院,凡是華人病人或疑似病人送院依病情分別管理,對外國感染鼠疫患者,交給各國在漢口的醫院治療[29]。同時,協調日俄予以配合,由中央政府通令東北各地政府,在東清、南滿、京奉、安奉等鐵路大站(重要關卡)和沿線周圍,搭建或借用大批空房作隔離留驗病房檢疫所以實施檢疫制度[30]。
1911年3月開始,疫情已逐漸平息,開通二、三等車廂事宜也提到了議程之上。3月22日,“以疫氛告熄,各醫官會議,關內外火車驗而不留,關外急待乘車之二、三等客甚多,電請郵傳部于二十五日關外概準售二、三等票”[10]5。至此,關內外鐵路開始恢復運行。4月,清政府在奉天(沈陽)召開“奉天萬國鼠疫研究會”,這是中國歷史上召開的第一次國際科學會議。會議指出在這次鼠疫傳播中,鐵路扮演了一個主要角色,不同鐵路公司之間應該聯合行動,以便在所有鐵路線上形成統一的衛生防疫系統;應該籌建一個只為了防疫和衛生目的的聯合鐵路醫務局,從而在鼠疫和傳染病流行時制定控制交通的條例[11]489,512。
5 結語
本來致病微生物對人種、階層并無偏好,疫病也不分地域傳播,防疫理應對所有人群同等相待。然而在實際操作中,無論中外均曾存在對不同社會階層的差別待遇[31]。在此次鼠疫防疫過程中也不例外,在發現苦力等貧困階層為高發人群,鼠疫傳播路線與苦力返鄉的鐵路線重合后,鐵路部門采取了按車廂等級停售火車票的方式,限制不同社會階層人員的流動,以防疫情擴散。發現此舉引發了苦力們的各種應對舉措,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疫情擴散后,及時根據疫情發展調整措施。從按等級停售車票,到鐵路完全停運,再到各等級車票逐步恢復,鐵路防疫應對逐步科學有序。
日俄則多次以清政府無防疫經驗和防治不力為借口,試圖奪取東三省防疫主權,在其管轄地以外采取“自由行動”[20]153-156,趁機在中國謀取更多的權益。對于苦力,日俄也采取了重點防范措施,而且在實施防疫措施時都體現出了對華人的歧視。中國政府在科學防疫的同時,與日俄等國多方斡旋捍衛主權,終于成功控制住了疫情的發展。
另外,此次鼠疫防治過程中凸顯了鐵路防疫的重要意義與作用。鐵路部門(郵傳部)采納醫學專家建議,與地方聯合封鎖疫區、阻斷交通,暫停售票,設置旅客查驗檢疫站,開創了中國鐵路交通檢疫的先河。自此,我國鐵路衛生事業開始起步。1914年,伍連德借鑒歐美各國鐵路站車衛生管理辦法,草擬了《火車衛生辦法》。其中包括:客車內設置痰孟,揭示禁止隨地吐痰及拋棄雜物;頭等客車中配置衛生廁盆,二等客車分設男女廁所,三等列車在兩側設斜坡式廁所;配置急救藥品和夾板等材料以備發生事故時需要;改建后的沿線各站廁所要寬敞,外懸木牌標示等改良辦法。傳染病的鐵路防治工作在1917年~1918年山西綏遠鼠疫、1928年通遼鼠疫等中逐步完善。1918年1月21日,交通部設立防疫事務處并制定《交通部防疫事務處章程》,各路局成立相應的防疫機構;隨后頒布《交通檢疫規則》,規定在重大傳染病流行期間,鐵路行車部門和衛生部門為阻斷疫病傳播所承擔的責任和應采取的防疫措施。這些都為中國的鐵路防疫體系建設奠定了基礎,促進了中國鐵路衛生和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