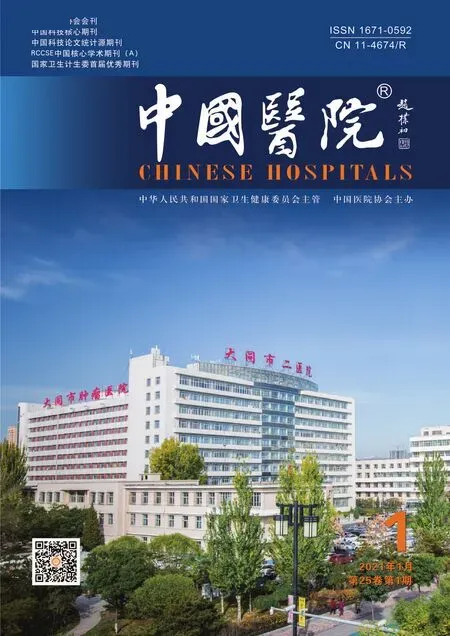傳染病防治法律之比較研究:兼談我國《傳染病防治法》修改
■ 侯 宇 梁增然 鄧利強 沙玉申 武 穎 劉立飛
本文分析基于對英國、美國、加拿大、德國、法國、俄羅斯、日本、韓國等國家和地區傳染病法律規定的整理及編譯,具體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制定的《國際衛生條例》、英國《公共衛生法案》、美國《公共衛生服務法》《國家緊急狀態法》和《斯塔福德災難與緊急援助法》、加拿大《衛生保護與促進法》、德國《人類傳染疾病預防和治療法》、法國《公共衛生法典》、日本《傳染病法》和《家畜傳染病法》、韓國《傳染病防治法》等。作者大致勾勒了各國傳染病防治的立法模式、預防機制、預警及控制機制,以期未來為我國《傳染病防治法》的修改提供參考依據。
1 立法模式總體比較
1.1 立法體例
綜合來看,各國針對傳染病防治的規制主要呈現兩種類型:一是綜合立法,即將傳染病防治納入國家公共衛生服務的全體系運行框架中,不再單獨進行專門性調整,以英國《公共衛生法案》、美國《公共衛生服務法》、加拿大《衛生保護與促進法》和法國《公共衛生法典》為代表;二是專門立法,即有些國家和地區針對傳染病防治進行特別立法予以規制,如德國《人類傳染疾病預防和治療法》、日本《傳染病法》和《家畜傳染病法》、韓國《傳染病防治法》。
1.2 立法目的
從立法目的來看,各國存在較大差異。主要分為兩種類型:一是以全力杜絕傳染病為目的,賦予傳染病防控機關較大的權力,為達成預防與控制傳染病而犧牲公民某些基本權利;另一種則是兼顧公民基本權利和國民健康,對傳染病防控機關的權力與采取的措施做出了必要的限制,凸出對醫師以及弱勢群體的權利保障。實際上,2005年《國際衛生條例》第3條第1款確定了“充分尊重人的尊嚴、人權和基本自由”是衛生防治的基本原則之一。因此,無論是否在本國或地區傳染病防治法中強調公民基本權利與健康,都不得違反該原則。
1.3 管理體制
從各國傳染病管理體制來看,都呈現出中央與地方之間在傳染病防治方面上的合作。在中央一級除了衛生職能部門外,還會設置專門的傳染病預防控制機構,例如德國的羅伯特·科赫研究所。該機構既是政府在生物醫學領域的中央科研機構,也是德國維護公共健康的最重要機構之一,在預防和抵抗傳染病以及分析衛生系統中長期公共衛生趨勢方面發揮關鍵作用[1]。在傳染病管理體制當中,運行良好的公共衛生監測網絡、國家醫療衛生治療網絡、突發衛生事件的調查和控制系統、應急資源的儲備與調配網絡等都必不可少。如美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的主體除了隸屬衛生部的聯邦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負責制定全國疾控戰略以外,還包括各州的醫院應急準備系統(HRSA)負責進行藥物供給、急救救援、信息溝通、檢疫隔離,以及各地城市醫療應急系統(MMRS)負責消防部門、醫院、社區應急救援隊等,進行區域資源調配[2]。
2 傳染病預防機制之比較
2.1 儲備防疫物資
醫療防控物資的儲備對傳染病疫情的防控和救治至關重要。美國《公共衛生服務法》第319條規定, 由衛生和公共服務部長與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合作,并在國土安全部部長協調之下,儲備防疫物資以保障美國的緊急衛生安全。衛生和公共服務部長可部署儲備,以應對實際或潛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保護公眾健康或安全,或在國土安全部部長的要求下,應對實際或潛在的緊急情況。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負責管理“國家戰略儲備”,是儲存抗生素、化學解毒劑、抗毒素血清、維持生命的藥物、靜脈注射,航空維修用品,以及醫療/手術器械的國家倉庫。各州制訂了計劃,與聯邦公共衛生機構合作,以分發來自“國家戰略儲備”現有藥物的“急救包”(push packs)[3]。
2.2 流行病監測預調查
各國和地區都對流行病的檢測予以高度重視,除了日常流行病的調查外,有些國家還對預防(免疫)接種階段強調開展流行病調查。如《俄羅斯聯邦傳染病免疫預防法》第8條第1款規定:“免疫的執行由聯邦執行機構提供,該機構負責制定和實施醫療保健領域的國家政策和法律法規,授權俄羅斯聯邦主體在醫療保健領域的執行機關進行衛生和流行病學監測。”韓國《傳染病防治法》除第29條對預防接種的流行病學調查做出分級分類的規定之外,專門設立第四章“傳染病監測和流行病學調查等”和第9章“檢疫人員、流行病學調查人員、檢疫專員和預防專員”對流行病調查予以詳細規定。根據德國《人類傳染疾病預防和治療法》的規定,羅伯特·科赫研究所肩負著流行病調查所有環節的重任。美國《公共衛生服務法》規定對具有傳染病監測能力的實驗室提供資助,從而加強其公共衛生監測系統。
2.3 對傳播途徑事前預防
阻斷一切可能的傳染源和傳播途徑,是預防傳染病暴發的最有效手段。因此,各國和地區針對各種傳可能染源和傳播途徑進行必要的管控。如日本《傳染病法》第11章對特定病原體進行規范;德國《人類傳染疾病預防和治療法》設第9章“與病原體有關的活動”專門對病原體進行規范,還對有害動植物、癢螨、頭虱采取必要防治措施(第18條),設專章第7章“水”和第8章“對從事與食品有關工作人員的健康要求”做出規定。不僅如此,為了防止動物感染人類或人畜共患傳染病,有些國家對此特別立法強化控制。如日本除《傳染病法》第5條專門規定獸醫職責之外,還通過《家畜傳染病法》進行專門規制。
3 傳染病預警及控制機制之比較
3.1 賦予特定機構宣布公共衛生緊急狀態的權力
各國法律均賦予特定機構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的權力。例如美國,在處理與爆發性傳染病相關的公共衛生危機方面,除總統有權宣布整個國家或相關的地區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以外,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長也有權宣布公共衛生緊急狀態。二者的法律授權主要來自《公共衛生服務法》第319條、《國家緊急狀態法》第201條、第301條和《斯塔福德災難與緊急援助法》。《公共衛生服務法》授權衛生和公眾服務部部長決定是否存在公共衛生緊急情況,應當基于兩個前提:一是疾病或紊亂引起公共衛生緊急情況;二是公共衛生緊急情況,包括傳染病或生物恐怖襲擊的重大暴發。當確定公共衛生緊急情況時,部長有權“采取適當行動”,以及在適當時使用公共衛生緊急基金。公共衛生應急決定持續有效,直至部長宣布緊急情況不再存在或90日期滿(以先發生者為準)。《國家緊急狀態法》授權總統宣布“國家緊急狀態”,總統一旦宣布國家緊急狀態必須立即傳達給國會并在《聯邦公報》上公布,緊急狀態聲明(或同時或隨后的行政命令)必須說明相關機構根據該聲明可獲得的權力或權限。如果總統發布公告或者國會通過聯合決議終止緊急狀態,國家緊急狀態可以終止,除非總統通過向國會發送通知并在《聯邦公報》上公布的方式更新公告。《斯塔福德災難與緊急援助法》授權總統宣布“重大災難”或“緊急狀態”,以應對某事故(或威脅)。一旦宣布,聯邦技術、財政以及其他方面的支持就可向州與地方政府流動。
3.2 常態化的流行病調查和日常申報制度
流行病調查和申報應當法定化,只有形成常態化機制才能實現傳染病的及早發現和控制。如德國《人類傳染疾病預防和治療法》規定了申報義務(第6 8條、第15條)、實名申報(第9條)、匿名申報(第10條)、羅伯特·科赫研究所流行病調查與接受申報(第11條)和其他形式的監測與電子信息報送系統(第13 14、15a條)。韓國《傳染病防治法》第11條規定,西醫、牙醫或中醫以及受雇于傳染病病原體鑒定機構的雇員均有傳染病報告義務。日本《傳染病法》要求對收集的傳染病信息進行分析后,應當用各種合適的方法積極地公開傳染病發生的狀況、趨勢及原因等相關信息,包括相關傳染病的預防及對于治療的必要信息,但應當保護患者的個人信息。另外,傳染病預警還須依賴信息技術以及信息公開制度予以保障。例如,日本《傳染病法》第16條特別規定了信息公示制度的義務,“厚生勞動大臣以及各地方政府負責人,在對依據第十二條至前條的規定收集的有關傳染病的信息進行分析后,應當用新聞、廣播、互聯網以及合適的方法,積極地公開傳染病發生的狀況、趨勢及原因等相關信息以及相關傳染病的預防及對于治療的必要信息。在對前款的信息進行公開后,必須注意保護患者的個人信息。”
3.3 遞進式控制措施
各國對傳染病的控制基本上依據疫情的嚴重程度而遞進式地采取控制措施。大體分為3階段:第一,在傳染病萌發或發生且疫情較輕或不明朗時,采取對飲用水甚至其他用水采取必要的管控措施,強制調查病原、強制對人隔離治療和強制物品檢疫,強制解剖尸體與火化;第二,隨著疫情蔓延嚴重時,各國均上調應急相應級別并做出相應的應對措施,主要包括強制銷毀傳染媒介、采取交通管制或阻斷等措施;第三,當疫情跨越地域進行大范圍蔓延時,各國和地區均將防控級別調至最高級,甚至在中央政府層面成立應急中心以調動全國資源進行抗疫,主要包括征調機構場所及人員、征調民間資源、征用媒體及通訊設備、暫停某些法律在區域甚至全國范圍內的實施、迅速修改法律或者頒布新的應對性法律等。如韓國為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暴發而迅速修改相關法律,并最終于2020年3月4日修訂完成包括《傳染病防治法》第11條對醫生等人員的傳染病報告義務、第17條對流行病的實際調查、第18-3條對培養流行病學研究人員、第20條對尸體解剖、第49-2條對感染弱勢群體的保護措施等多項規定。美國為應對COVID-19疫情,國會也一改往日立法拉鋸式的低效率,在短時間內接連通過了《冠狀病毒防范和響應補充撥款法》(2020年3月6日),《家庭首次冠狀病毒應對法》(2020年3月18日),《冠狀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2020年3月27日),《工資保護項目和醫療保健加強法案》(2020年4月24日)等多項法律。
4 對我國《傳染病防治法》的借鑒
4.1 建立生產與物資、應急能力儲備制度
國家應當設立分布在不同區域的醫療物資戰備庫,各地衛生防疫部門則建立相應的醫療物資儲備中心,二甲以上醫院平時做好必要的防疫物資儲備,防范大規模突發疫情導致的醫療物資短缺。增加平戰結合的醫院、病房設計與建設的規定。從平戰結合的角都出發,我國二甲以上醫院都應在設計、建設普通病房時,應預留隨時將其改造為符合防疫特殊要求的病房(如負壓病房)的能力,以備防疫特別需求。對生產與科研部門提供政策和資金上的支持,新型傳染病與不明原因的傳染病鑒別完全依靠檢測手段,因此必須始終擁有高素質的研發隊伍進行檢測技術以及疫苗、治療藥物與診療技術的快速研發,相關企業具備快速大規模投產并確保產品質量。
4.2 流行病調查制度法治化
首先,對我國日常流行病調查制度予以具體化。盡管我國《傳染病防治法》第18條和第21條分別做出“開展流行病學調查”的規定,但該制度過于籠統,未能對醫療機構、疾控中心及其他部門如何開展流行病調查做出具體規定;其次,除日常流行病的調查外,還應對預防(免疫)接種階段強調開展流行病調查。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尚未規定流行病監測預調查制度,而《疫苗流通和預防接種管理條例》第20條和第42條盡管有所涉及,但未能予以明確。通過建立流行病常態化調查和流行病監測預調查的結合,依托社區診所、醫療機構和疾控中心等一線醫療與防疫人員,整合醫院的院感科、傳染病科和發熱門診,醫療人員在進行日常診療業務同時兼具流行病調查責任。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國家疾控中心應當將衛生應急培訓作為重點項目,并定期對培訓進行績效評估,形成應急培訓評估體系[4]。
4.3 賦予應急指揮機構特定權限
我國于2018年正式組建應急管理部,其職能覆蓋了火災、地震、安全生產及汛情和旱情,但并未包涵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而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雖設置有衛生應急辦公室,但是其指揮調度能力有限,僅限于衛生系統內部資源的指揮[5]。為了真正落實應急防疫的高效性,從執行效率和權責一致要求出發,應明確應急指揮機構權限和法律地位。建議理順《傳染病防治法》和《突發事件應對法》的銜接關系,在賦予應急指揮機構特定權限上分為兩類:一是賦予國家衛生健康委以宣布國家進入衛生防疫緊急狀態的具體職權,并且激活相應的撥款、調配資源、允許尚未被批準使用的藥物醫療器械等在法定程序下臨床試用等權利;二是在國家衛生健康委宣布進入衛生防疫緊急狀態之后,當疫情狀態已經擴大到影響社會系統各方面時,則由國務院宣布國家進入全國緊急狀態。這兩類緊急狀態的期間,應在發布時予以確定;相應緊急狀態下的授權,隨著緊急狀態期間的結束而終止。唯有將應急指揮機構的主體權限予以規范化、法定化,才能將人員征調與物資征用、征收制度予以法定化,最終完善包括醫療資源分配機制、醫護人員調集計劃、社會物資調撥機制、社會捐贈機制、志愿者管理機制等在內的應急聯動機制。
4.4 完善權利保障條款
我國《傳染病防治法》的基本邏輯是國家公權——公民義務,從法律的二維構成“權利和義務”會發現,制度設置多為義務性規定,而權利保障條款相對不足。《傳染病防治法》更加強調在特殊時期(如疫情控制、醫療救治期間)行政管制的能力,公權力色彩比較濃厚。因此,建議增加有關保護公民所應該享有的人身權、財產權、正當程序權利,包括受告知權、聽證權、陳述申辯權以及信息獲取權、行政救濟權等[6]。切實保障公民(包括法人)合法權益的條款,具體包括:對征用、征收他人物資的具體程序、內容做出明確規定。這次疫情就出現了異地征用醫療資源的問題。依據依法行政的基本原理,在立法未對此規定情形下,地方政府采取的征收、征用措施違法;對疑似病例或傳染病病人進行強制隔離或救治時,必須設置和堅持正當程序,保障其合法的人身權、財產權等不受侵害,包括宜居條件、通訊自由、信息知情權、行政救濟權等;對由于受疫情影響,可能會受到較大沖擊的“弱勢群體”給予必要的醫療救護和適當的物資供應。